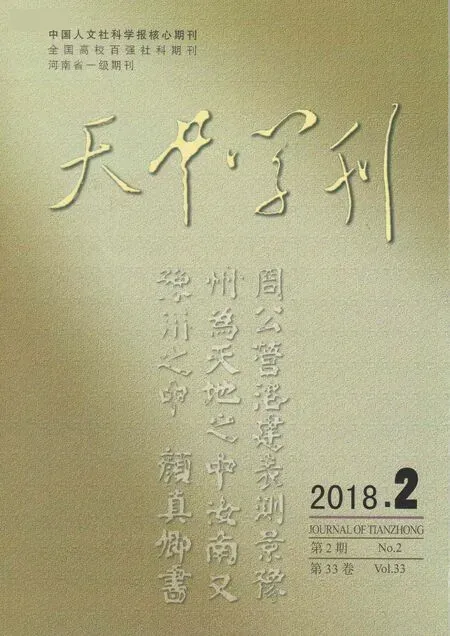自由放任思想与“无为而治”学说之比较
2018-01-29熊燕华
熊燕华
自由放任思想与“无为而治”学说之比较
熊燕华1, 2
(1. 湖北工程学院 新技术学院,湖北 孝感 432000;2. 华中师范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9)
国家与社会的关系问题是人类探讨的一个重要话题。主张“大社会、小政府”的观点在中西方都曾得到不同程度的响应。在欧洲,在与重商主义斗争中而产生、发展与成熟起来的自由放任思想,倡导国家减少自己的职责,将一些原本属于政府的权力让位给社会,主张在一种更自由的自然秩序下让市场发挥调节作用。在古代中国,“无为而治”的学说也呼吁政府清静无为,放手让经济社会自然而然地发展。这两种学说在理论背景、哲学基础、价值诉求、观点主张、历史命运及政策影响等方面存在着一系列的不同之处,也包含着相当多的契合之处。
自由放任;小政府;无为而治;道家思想
权利和权力的关系问题是政治学研究的核心问题,这牵扯国家与社会的互动,政府与市场的博弈以及政治权威和公民个人权利此消彼长的关系。公民国家的合法权限在哪里?换言之,一国之内公民自由和权利的限度是什么?这些问题是政治哲学中最为重要的问题[1]。对于这些问题的回答,有两种针锋相对的观点,一种观点主张扩大政府权限,赞同加强国家干预的“大政府模式”;另一种观点宣扬缩小并降低政府的地位与作用,主张实行让社会和市场自由放任的“小政府模式”。其中,主张“小政府模式”的观点背后有其深厚的西方自由放任思想基础。
西方自由放任思想主张降低政府的作用,充分发挥市场的自发机制,它在西方历经几百年的发展,直到现在依然作为一种非常重要的思维倾向和政策主张在影响社会。在中国古代,“无为而治”学说主张政府不要管得过多,让社会自然而然地发展,以“无为”达到“无不为”。“无为而治”在一定程度上与自由放任思想不谋而合,而且是一种穿越时代、穿越空间、穿越环境的不谋而合。里根在宣誓就职现场引用老子的话“治大国若烹小鲜”,更引起人们对两种思想学说关联性的无限遐想。因此,对这两种不同时代、不同地区、不同文化背景的思想理论进行比较研究就显得十分有意义。
一、自由放任思想与“无为而治”学说的产生和发展
比较近代西方的自由放任思想与古代中国的“无为而治”学说,需要把握二者的发展轨迹和基本内涵。
(一)近代自由放任思想的产生与演化
法国重农学派的主张是西方自由放任思想的先声。该学派认为自然秩序具有优先性和优越性,强调人类生活应以自然秩序为归依,反对人为的干预,主张“放任”。以魁奈为代表的重农学家们制定了一套完整的学说,清晰地规定了人们的自然权利、社会的自然秩序和对团结在社会中的人最有利的自然法则[2]。这些学说为后来亚当 · 斯密宣扬自由放任思想做了理论上的准备。
在重农学派主张基础上,亚当 · 斯密伸出了“无形之手”,提出了趋于规范化、理论性的自由放任思想。他尖锐批判了重商主义的国家干预论,阐释了人类由自然的劳动分工、交换而形成的“大社会”观念和自发秩序,并提出只要由市场机能发挥功能,就可以达成全体之最大利益①。
正是基于此,在上述学派和思想家看来,国家不应该进行过多的干预,国家应是一个“守夜人”,只要实现维持秩序等职能就可以了。积极的自由经济、自由贸易、自由竞争有利于社会的整体利益和全体公民的共同福祉,一切政府干涉都应该受到谴责。
英国保守主义的呼应也为自由放任思想的发展增加了声势。作为大师级保守主义者,伯克主张自由放任政策,反对国家过多地干预社会和个人生活,认为自由和传统不是对立的关系,而是共存的关系。伯克在论及“自由”时说:“我所说的自由,惟一的自由,是那种与秩序紧密相联的自由——不仅依秩序和道德的存在而存在,而且随秩序和道德的消失而消失。”[3]
(二)中国古代“无为而治”的起源及走向
“无为而治”,顾名思义,就是通过无为的手段,达到治理社会的目的。该理论产生于春秋战国时代,创始人是老子,其理论“圣经”就是老子所撰写的《道德经》。老子从“法自然”的宇宙自然观和道论出发,阐述了他的政治思想,提出“是以圣人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4]7,要求统治者减少政治活动,其总的原则即“去甚,去奢,去泰”[4]115。对于民众,也要使其失去有为的机会和条件,所采取的手段就是“虚其心,实其腹,弱其志,强其骨,恒使民无知无欲也,使夫知者不敢弗为而已”[4]16。
西汉前期是“无为而治”思想的发展与成熟期,也是其占据统治地位的时期。在西汉建国的前70年,是道家的黄老学说在政治上和思想上占统治地位的时期。政治上,汉初的几位皇帝和实际政策执行者都是黄老思想的积极信奉者和贯彻者,如窦太后、汉景帝以及萧何、曹参等人。思想上,先后有陆贾、刘安、司马迁等代表人物。
陆贾曾多次向刘邦宣扬黄老道家治国理念,并直言“夫道莫大于无为,行莫大于谨敬”[5]。刘安认为君主应当始终坚守无为原则,以无为之事,因物之自为,顺应自然,正如其中的《诠言训》篇所说“君道者,非所以为者,所以无为也……无为者,道之体也”[6]。作为文学家和史学家的司马迁对黄老学说也有着深刻的思考和细致的研究,并提出了自己的无为思想。他曾言,“道家无为,又曰无不为,其实易行,其辞难知。其术以虚无为本。以因循为用。无成势,无常形,故能究万物之情”[7]。
二、理论背景、追求境界和哲学基础的异同
要对西方近代自由放任思想与中国古代“无为而治”学说进行深刻的、全面的比较分析,就要对这两种学说的理论背景、追求境界以及哲学基础进行一番比较。
(一)理论前提
不管是西方近代的自由放任主义,还是中国古代的“无为而治”思想,都赞同自然界是依照一定的规律变化和发展的,人们按照规律行事才可以实现自己的目标和追求。
自由放任思想要求的是“人为秩序”必须要符合自然规律和自然秩序,一个人按自己的本性法则行动就是按照最高的自然权利行动,而且他对自然具有同他的力量一样大的权利[8]。亚当 · 斯密在《论财富的自然增长》一文中反复提及自然或自然法倾向,并认为这是事物发展的根本[9]。道家学派也十分重视自然规律,宣扬“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4]23。既然人类社会生活所依据和效法的往往是至高无上、伟大广博的天地,君王就应该顺其自然,“顺道化民”。
如果放到更为久远、更为博大的中西方政治思想发展史角度来看,自由放任和“无为而治”两家学说对自然规律的强调,有着类似的理论历史背景。作为现代西方文明发源地的希腊,带给人类的遗产之一就是对自然的重视和对自然法的强调,这对以后的古罗马,包括中世纪直到近代的西方社会都有着深刻的影响。“言必称自然”不光发生在希腊时代或者希腊化时代,中世纪的神权政治和神学万能并没有阻止自然法思想的延续和发展,近代的思想家更是把自然法视为圭臬,视为万物之渊薮。重农学派的理论核心就是崇尚自然秩序,并以此与人为的、法定的实证秩序相对立。自然法理论家认为,人类社会与自然界一样,都必须接受确定不移的法则即自然法的支配,自然法赋予人们某些基本的权利即自然权利,并且构成国家实在法的基础[10]。尤其是对一些自然法理论家来说,人们在自然状态下拥有完全的自由,比如斯宾诺莎曾有言:“天然的状态,在性质与时间两方面,都先于宗教……我们认为的自然状态是先于与缺乏神圣启示的法律与权利,并不只是因为无知,也是因为人人生来就赋有自由。”[11]
在中国,对自然尊崇的传统也是经久不息的,道家思想本质上就是一种自然主义思想。在春秋战国百家争鸣的时代,在攻伐不断、“礼崩乐坏”的情况下,各门各派愈发探寻自黄帝时代就有的那种对天道的膜拜和西周以来发展的天人一体思想。那种将对自然的理解和顿悟推理到人类社会的做法一直伴随着中国历史的沉浮。对自然秩序的向往与追求在道家学派的思想中反映得尤为明显,作为事物规律性和必然性体现的“道”在老子学说中占有核心的位置。在老子的思想学说中,道是价值判断的标准,不仅可以用于区别自然界万物的良否,而且可以用于判断人类社会生活的善恶,只有与道的基本精神相符合的状态才是最理想的状态[12]。
(二)追求的境界
对自然规律或者说自然秩序的共同遵循与坚守,促使自由放任思想和“无为而治”学说走向类似的理想境界。这种境界在经济社会活动中可以概括为:政府尽量压缩自己的空间和权力作用范围,给社会和个人更多的权利做自己想做的事情(法律和道德框架内),以达到个人自由的获取以及个人利益和社会全体利益的一致。政府的过多插手与涉足,只会使事情变得更加糟糕。
自由放任思想一直寻求“最小限度的政治”,倡导的是“管的最少的政府就是最好的政府”。在自由放任主义的背景下,让市场的自发机制发挥作用,政府的职能只是维护正常的社会秩序以保持经济常态化运行。社会和个人被放在第一位之后,就要通过自由竞争、自由贸易的方式在自由市场实现自己的效用和利益。而对道家的无为政治来说,君主应该不过多地干预经济社会的自然运转,通过“绝圣弃智”,才能实现“民利百倍”,通过“绝巧弃利”,才会“盗贼无有”[4]73,也只有通过这种清静无为的统治方式,采取这种放任式的治理手段,才可以达到“天下正”的“理想国”,实现民众的自化、自朴和自己的境界。
当然,两种学说的终点还是不一样的。西方自由放任学说始终把个人放在首要地位,对国家采取工具主义的态度,国家自始至终只是手段,个人才是目的,个人利益和价值的实现是终极目标。而通过对“无为而治”学说的把握和历史事实的考察,可以看出,这种思想观念的终极目标还是为了维护稳定的统治秩序,“无为”乃是一种“君道”,君主必须“无为”才能“无不为”[13]。“无为”是手段,“无不为”才是目的。
(三)哲学基础
自由放任思想和“无为而治”学说在哲学基础上有着一些类似的地方,也有着一些不同之处。对于这种差异性和相似性的分析对于我们更加明确和清晰地理解两种理论有着重要的导向作用。
正如前面所言,自由放任和“无为而治”在理论的来源上有着极其相似的“自然秩序”路径,都相信尽量少的国家干预和尽量多的自发行为有助于个人利益的达成。然而在哲学上二者有着根本的不同,这在某种意义上也是中西思想文化迥异的体现。自由放任思想继承了基督教的罪感文化,对人性持极其悲观的态度,认为人性从来没有好过,将来也不会有什么好转。这种人性恶的哲学观加上中世纪基督教遗留给近代的另一个遗产——对政府和一切国家权力的怀疑、排斥、敌视和疏远,从而为其“存在反政府的某种偏见”[14]奠定了基础。同时,基于这种人性观,自由放任理论指出,个人的“利己之心”可以实现最大化的功利。
“无为而治”学说是建立在道本论之上的,“道”是世界的本原,万事都要符合自然天道的法则,并提出“反者,道之动”。按这种逻辑推演,在道家学派奉行的真伪人性观或者说自然人性观看来,人性没有善恶之分,只有真伪之别。这大大不同于西方的人性恶观,也不同于儒家的性善论、性恶论等。道家学派提倡人们回归真实的状态,那就是无为、无知、无欲的状态,在这种状态下人们实现自己的自由。正如梁启超所指出的,“老子辈所倡此种自然主义,其本质固含有个人的、非社会的、非人治的倾向”[15]。
三、两种思想照耀下的个人和政府
在上述两种思想理论中,作为公权力主体的政府与作为私权主体的个人究竟处于一种什么样的状态和命运呢?自由放任和“无为而治”又是如何对待政府和个人的呢?
(一)对待个人的态度
应该说,自由放任和“无为而治”都对个体极其重视,并视其为理论分析的对象和依托。然而,同时需要指出的是,这两种思想在如何看待个人的价值、个人的利益和个人的行为上有着极大的甚至根本性的不同。
西方自由放任思想始终坚持个人权利的优先性、初始性、先验性和自然性,积极鼓励个人想象力的发挥、个人才能的施展和个体活力的激发。自由主义基于人的自利本性和逐利欲望,给予个人充分的空间和场所,以实现个人的价值和理想。自由放任思想还注意保护每一个人的自由,“任何人都不得侵犯他人的生命、健康、自由或财产”[16]。亚当 · 斯密就公开提出尊重个人的需求和欲望,让人自由自在地生存与活动,就会增长个人的财富和国家的财富。
“无为而治”学说在对待个人的需求与欲望问题上,尽管提出了“为我”主张,但采取的是压制与贬低的态度。通过前面的分析我们知道,道家讲究无为,一方面是针对统治者,另一方面是针对民众。对民众来讲,“无为”就是要消除民众对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追求,只有“常使民无所欲”,才能“使夫智者不敢为也”;只有“不见可欲”,才能“使民心不乱”;只有“不尚贤”,才能“使民不争”;只有“不贵难得之货”,才能“使民不为盗”[4]16。事实上,道家思想对名利是持批判态度的,《庄子》认为,名利之类都属于性外之物,而“外物不可必”[17]。这种对个人的压制,某种意义上是“反自然”的,与西方自由放任极力促进个人利益的思想南辕北辙。
另外,不管是自由放任思想,还是“无为而治”学说,都有着自由的精神气质。自由放任对自由的渴望与向往自不待言,道家思想中也有着深刻的自由情怀,寻求遁世隐居,这有点类似古希腊的犬儒主义学派。但是,这两种思想在个人自由的问题上还是有着不同的内涵,西方自由放任思想侧重于外在的自由,也就是他人、政府和国家没有干涉个人的自由。正如自由主义者伯林所说的“就没有人或人的群体干涉我的活动而言,我是自由的”[18]。而“无为而治”思想所谓的自由更加强调个人的内在自由,追求个人思想的解脱,达到“至德之世”。这或许就是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的“本”与“标”之辩吧。
(二)对待政府的态度
自由放任思想与“无为而治”学说都希望政府采取不干涉主义态度,采取放松对社会的控制以及减少税赋,让经济和社会在自然规律作用下自发增长。当然,这两种思想所包含的不干涉主义思想并不是无政府主义,正如萧公权所说的:“惟吾人当注意,老子无为政治哲学略似欧洲最彻底之放任主义,而究与无政府主义有别。”[19]它们都主张政府在维持基本的社会秩序稳定和国家安全方面发挥作用。不过,二者的共同之处也就到此为止了,面对政府和公权力,两种思想学说有着不同的“脸谱”。
近代的欧洲历史自中世纪演化而来,而中世纪的国家与教会是各自独立、平行、相互对抗地发展下来的。这种持续上千年的独特的政教关系在西方人深层心理上积淀为一种根深蒂固的意识,即国家的权力是有限的,国家权力不可能是绝对的、无所不在的、万能的。自由放任思想就是在这样一种政治文化和思想土壤中成长起来的,对政府的不信任以及对其可能侵害个人自由的恐惧,必然促使个人采取手段对抗这个“利维坦”。自由放任学派所做的就是在经济上缩小政府的经济功能,国家干预被认为不合理而取消,国家关税由于自由贸易原则而被降低或废除。政治上的表现就是通过民主与法律的手段对政府权力进行限制与约束,以减少政府可能带来的破坏,采取的措施就是把政府的权力分为几个部分且让其相互制衡,引入民主机制加强对政府的监控以及法治的不断发展与完善。
“无为而治”学说对政府的态度却与自由放任思想大为不同。那么“无为而治”学说所处的社会文化环境就是中国这个权力高度集中化的社会,且容易形成“保姆国家”的社会。“无为而治”尽管希望“圣人”(即君主)不要过多干预,要“养其民”“不伤人”“无为而民自化”,但最终的目标还是要实现“治天下”,要达到“治道贵清静而民自定”,要追求君王的天下大治。介于此,道家思想对于君主的态度远远不像自由放任学说那样的排斥与疏远,反而有着根本的依赖和依托。
同时,与自由放任思想采取“冷冰冰”的条条框框限制政府的行为不同,“无为而治”学说采用的是“暖和和”的劝谕,要求君主有“德性”和自律,《老子》一书充满了这种对君主的规劝和进言。这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中西文化上的一个区别,即西方文化对制度层面重视多一点,中国文化对伦理道德层面重视多一点,根源则在于中西方文化的哲学根基不同。
四、两种思想的政策影响与历史命运
理论的产生、延续与壮大离不开现实的环境和历史的沉淀,现实政治又会受到理论学说的影响与作用。发端于近代欧洲的自由放任思想与源于春秋战国时期的“无为而治”思想尽管在某些方面有着一致的看法与契合,但二者对政策的影响以及历史归宿却截然不同。
(一)对现实政治的影响
理论总是要为现实政治服务的,也总要对现实政治产生影响。从宏观的历史角度来看,西方自由放任思想对于近代西方各国政府的政策制定和实施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无为而治”学说也对中国古代某些历史时期的政府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但二者对现实政治的作用力与影响力有着量上的极大差异性。
1. 自由放任思想和现实政治的沉与浮
由于自由放任思想更多的是从批判重商主义政策中发展起来的,其政策指向是很明确的。亚当 · 斯密发表《国富论》的时候,英国的工业革命正方兴未艾,市场的价值和功能逐渐外化,英国也逐渐成为“世界工厂”。理论和现实对英国政府的施政方略产生了影响,也使之成了欧洲其他地区自由放任政策的典范。其所采取的自由放任事件包括1829年的天主教解放令,1832年的改革方案,1846年保守党人皮尔对谷物法的废除及此后科布登和布莱特等激进派采取了比亚当 · 斯密还要极端的自由放任立场[20]。1850年《航海法》的废除更是打破了英国长期奉行的关税保护政策,标志着英国成为一个自由放任国家。
自由放任“之风”向东越过狭窄的英吉利海峡,刮到欧洲大陆,对大陆国家的经济政策产生了极大的影响,比如荷兰的经济模式就成了缩小版的英国模式。这股“放任风”还跨过宽宽的大西洋,登陆北美,对美国的政策制定者尤其是反联邦党人的自由贸易政策产生了很大的推动作用。应该说,由思想学说变成政策现实,由一国发展到多国,自由放任的“魔力”就体现在这种政策适应了当时处于上升期的资本主义的发展状态,符合当时资本主义的现实要求。
2. “无为而治”学说和现实政治的起与落
“无为而治”思想在特定时期也对现实政治产生了一定的影响,然而由于理论本身的局限性,加上中国古代社会的历史大背景,其作用的深度和广度并没有自由放任思想对西方世界带来的影响大。
在春秋战国时期,“无为而治”思想的影响也仅仅停留在思想层面,它对现实政治的影响是微弱的。在当时兼并战争不断的现实社会和政治环境下,各国统治者采用的是短期能够强兵富国的法家思想。“无为而治”表达更多的是对现实的不满,对理想世界的追求,是一种理想主义式的政治观。
“无为而治”学说真正用于政治实践是在西汉初期,黄老学说主导了汉初70年的国政。应该说,当时政府治理经济的思想主要有两个大倾向:一是以黄老之学为指导,推崇自然无为,对经济不加太多的干预,任其发展,顺其自然,称为“因之”;一是黄老之外的其他学派,主张政治干预经济[21]。然而,出于秦王朝法家治国失败的教训,还由于频繁战争遗留给西汉政府的破败经济和社会现实,统治者第一次将“无为而治”学说推向政治舞台,使之在政治现实中得以体现,即政府实行“与民休息”政策,安置归农军人,恢复民众田宅,减轻租赋徭役,促进物质交流等[22]。也正是在这一不干涉主义政策的作用下,汉初经济得到明显的发展,社会秩序也得以稳定,形成大一统国家以来的第一个盛世——“文景之治”。
然而,汉初的土地问题并没有得到解决,土地兼并严重,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致使政府的减轻租税政策全无功效[23]。因此,汉武帝之后,政府便放弃了“无为而治”思想及其政策取向,转向了积极的国家干预,这以汉武帝时期“盐铁政策”的出台为标志。此后,在中国历史的政治大舞台上,“无为而治”逐渐淡出。尽管各王朝开始的时候,会采取些类似无为性质的政策,但也只是停留在思想层面的探讨上,很少再上升到国家政策的层面。
(二)历史地位及历史命运
应该说,自由放任思想和“无为而治”学说都在各自的历史时期、各自的影响区域有着重要的地位。然而二者的能量、作用及命运还是不可同日而语。
首先就两种思想学说在自身所处时空环境内的地位而言,自由放任思想远远超过“无为而治”学说。自由放任思想是近代以来西方主流的思想流派,甚至上升到了意识形态的高度。自由放任思想在现实政策上的施展与良性运行加强了其说服力,也保证了其在现实政治和思想理论两个层面的主导地位。“无为而治”自从其产生开始,除了汉初的一段时间,并不在学术领域和国家政治生活中占据核心地位。春秋战国的百家争鸣所诞生的儒家学说和法家学说大部分时间占领着思想和政策的高地,道家学派的思想更多的时候仅仅是一种社会思想补充。
更加明显的区别体现在二者不同的历史发展轨迹和结局上。正如前面所说,自由放任思想在19世纪大部分时间大放异彩,到了20世纪初面对干预主义的挑战而“黯然失色”,理论和政策阵地纷纷丢失。然而,这种思想倾向并没有完全消解,自由放任也并没有完全退出政治领域,到了20世纪80年代,它以新自由主义和新右派的形式再次出现,出现了诺齐克、哈耶克、弗里德曼等大师级的代表人物,自由放任又迎来了新的春天。“无为而治”学说在经历了汉初的高峰期后,再也没有出现类似的盛景,以后逐渐向着玄学等方面发展,也逐步退出了政治历史舞台。
自由放任思想和“无为而治”学说都在各自的历史时期、各自所在的区域产生一定的影响。通过对二者的理论前提、哲学基础、政策影响、历史命运及其对个人与国家的态度等方面进行比较分析,我们在更深刻地理解这两者的差异以及二者所体现的不同时空下人们对自由生活的向往与追求的同时,更要在此基础上深刻地把握由于中西方的文化背景、心理基础和社会生产方式的不同所导致的二者在具体实践层面及其历史命运的差异。
注释:
①具体参见亚当 · 斯密《论国民与国家的财富》(焦妹译,光明日报出版社2006年版)。
[1] 斯金纳,斯特拉思.国家与公民:历史 · 理论 · 展望[M].彭利平,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1.
[2] 拉斯基.欧洲自由主义的兴起[M].林冈,郑忠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128.
[3] 伯克.自由与传统[M].蒋庆,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95.
[4] 辛战军.老子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2008.
[5] 王利器.新语校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6:59.
[6] 赵宗乙.淮南子译注[M].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3:740.
[7] 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82:3292.
[8] 斯宾诺莎.政治论[M].冯炳昆,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11.
[9] 斯密.论国民与国家的财富[M].焦妹,译.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2006:113–115.
[10] 唐士其.西方政治思想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208.
[11] 斯宾诺莎.神学政治论[M].温锡增,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222–223.
[12] 曹德本.中国政治思想史[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70.
[13] 李泽厚.中国思想史论三部曲:古代、近代、现代[M].天津: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7:33.
[14] 罗素.西方哲学史[M].北京:商务印书馆,1976:372.
[15] 梁启超.先秦政治思想史[M].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03:45.
[16] 洛克.政府论:下[M].杨思派,译.北京:九州出版社,2007:4.
[17] 刘泽华,葛荃.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史[M].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2:128.
[18] 伯林.自由论[M].胡传胜,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3:189.
[19] 萧公权.中国政治思想史:上册[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176.
[20] 顾肃.自由主义基本理念[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0:346.
[21] 周桂钿.秦汉哲学[M].武汉:武汉出版社,2010:181.
[22] 张分田.民本思想与中国古代统治思想[M].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8:171.
[23] 钱穆.中国历代政治得失[M].北京:九州出版社,2012:31.
〔责任编辑 叶厚隽〕
The Comparison of Laissez-Faire Thought and “Inaction” Theory
XIONG Yanhua1, 2
(1. College of Technology Hubei Engineering University, Xiaogan 432000, China; 2. Central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Wuhan 430079, China)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tate and society is an eternal topic of human being. The model of “the big society and the small government” that advocates the society to overwhelm the state has received unconscious response in China and the West. In modern Europe, the laissez-faire which emerged, developed and matured in the struggle with mercantilism, advocates countries should reduce their duties, government's power give way to a more liberal society, and realize spontaneous adjustment of the market in the natural order. In ancient China, the “Inaction” theory also called on the government to let the quietism naturally, and let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 freely. There are a lot of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two theories, such as the theoretical background, the philosophical basis, the value appeal, the viewpoint, the historical destiny and the policy influence.
laissez-faire; small government; “Inaction” theory; Taoism
2017-12-01
湖北工程学院新技术学院2016年度教学研究项目(2016JY01)
熊燕华(1982―),女,湖北孝感人,讲师,博士研究生。
C916
A
1006–5261(2018)02–0038–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