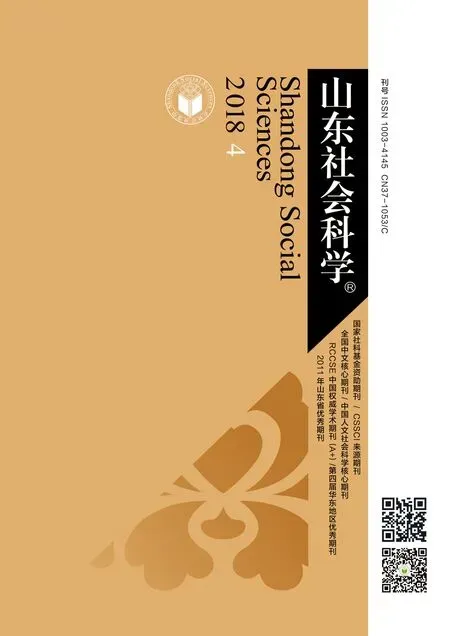“场域”视野下的革命文化
——以沂蒙精神的跨场域传播为例
2018-01-29于晓风
于晓风
(山东大学 新闻传播学院,山东 济南 250100)
文化是一个动态存在。一种文化的生命力,某种意义上取决于其丰富、生动的内部生态。法国哲学家皮埃尔·布尔迪厄(Pierre Bourdieu)的“场域”理论的伟大贡献,就在于将文化作为平行空间的动态存在,与政治、经济、社会发生对话。作为哲学原理和科学体系的马克思主义,需要实践层面的不断论证和文化生态的持续浸润。中国革命历史的壮烈进程,以革命者的热血和建设成就的辉煌记录着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理论一次又一次伟大的胜利。基于这一认知,习近平总书记对革命文化自信的主张,描绘出融合当代中国本土文化生态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宏伟的空间蓝图。
作为中国革命文化的代表,“沂蒙精神”的发生与发展、内涵与外延多维体现了东夷、齐鲁文化传统与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思维的恰切融合。2013年11月2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参观沂蒙精神展时指出:沂蒙精神要大力弘扬,沂蒙地区革命战争的历史不能忘记*黄锐:《习近平:沂蒙精神要大力弘扬》,2013年11月25日,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3-11/25/c_118286985.htm,2017年5月2日。,并高度评价“沂蒙精神与延安精神、井冈山精神、西柏坡精神一样,是党和国家的宝贵精神财富,要不断结合新的时代条件发扬光大”*《习近平在山东考察时强调认真贯彻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汇聚起全面深化改革的强大正能量》,《人民日报》2013年11月29日第1版。。立足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的研究视野加以审视,其内部巨大的生命活力和逻辑张力极具传播价值和导向意义。借助 “场域”理论为革命文化开辟出新的诠释空间,为沂蒙精神跨越场域的传播实践提供理论依据。
一、场域与惯习:文化传播的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
承袭辩证唯物主义的基本立场,被视作“法国最后一位马克思主义者”的皮埃尔·布尔迪厄(Pierre Bourdieu)旗帜鲜明地反对传统文化研究中的主体—客体对立模式、理性/逻辑中心主义和孤立/静态研究方法,将文化“提升到一个决定性的地位”,认为当代社会是以“文化实践及其不断再生产作为基本运作动力”的*高宣扬:《布迪厄的社会理论》,同济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4页。,并以“场域”为语境,深入剖析了文化作为资本与政治、社会之间的关联,及其作为权力生成受到的“惯习”影响,以此奠定了自己20世纪70年代之后的全球影响力。
(一)作为概念的“场域”
布尔迪厄建构的“场域”,被定义为“一种多重位置间客观关系的网络或者构型(configuration)。……根据各种位置的存在及其赋予特定位置行为人或机构的定性因素,位置的属性得以客观限定”*Loïc J. D. Wacquant, “Towards a Reflexive Sociology: A Workshop with Pierre Bourdieu,” Sociological Theory, Vol. 7, No. 1, 1989, p.39.。这里的“定性因素”,主要是指各种位置“在不同类型的权力(或资本)分配结构中实际的和潜在的处境,以及它们与其他位置之间的客观关系(支配关系、屈从关系、结构上的对应关系等等)”*[法]布尔迪厄、[美]华康德:《实践与反思: 反思社会学导引》,李猛、李康译,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第134页。。
一方面,场域内部选项多元而无定论,参与者可任意组合搭配,旨在实施各自的竞争策略。种类丰富的选择结果既体现参与者创新性主观思维,也内蕴特殊场域内置的框架要求和选择限制。另一方面,场域内部又危机四伏,充满竞争,每一个场域内部始终存在统治与被统治,压迫与反抗,甚至场域的划分都充满符号暴力意味,彰显不同权力间的强弱对比与起承转合。在场域的“边界”认知上,布尔迪厄以关系的互动反应加以界定,认为这一“边界就在其作用消失的地方”*[法]布尔迪厄、[美]华康德:《实践与反思: 反思社会学导引》,李猛、李康译,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第134页。。
可见,布尔迪厄的“场域”作为概念,不能被理解为界限分明且僵化的圈地结果,也并非宏观上大而无当的虚拟表述,而是一个内容丰满、生机勃勃、潜力强劲的对象。其场域理论不是一个孤立的存在,而是具有完整系统的知识体系,其间事物动态发展而关系密切,形成一种结构性的内在理性关联。关注关系的“场域”始终处于“内忧外患”之中,内部竞争连绵不绝,势均力敌;外部觊觎贼心不死,虎视眈眈——由此织成一张错综复杂的关系网,整体体现关联性、规则性、斗争性、模糊性四个特征。关联性,指以市场关系为纽带,政治、经济、文化等诸场域得以联结。规则性,指作为社会关系之构型的“场域”将规则强加于每一个参与其中的个体,并由此形成利益争夺和策略运作的空间。正是在这一意义上,“场域”运行各按其道,整体结构得以稳定。斗争性,指“场域”的活力源自无休无止的内部争斗,各种权力关系始终处于动态平衡状态,各类属性资本想方设法谋求理想空间。模糊性,指“场域”边界的不甚明确。客观上,权力资本属性的差异必然导致不同场域之间存在相对界限,然而场域内外确定诸种权力资本孰优孰劣、孰高孰低的标准并非统一且分明,因此,其边界只能模糊设置于特定权力资本作用效果开始减弱的节点位置及其周边。
同时,“场域”理论还建构起一项介于微观层面资本合作与宏观层面国家/社会体系间的中观视野分析。布尔迪厄认为,“场域”自治本质上唯有相对,取决于其内部资本权衡分量,或外部政治、经济场域的干涉性外来资本能力。*[法]布尔迪厄、[美]华康德:《实践与反思: 反思社会学导引》,李猛、李康译,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第134页。正是这一中观方法论层面的探索,使得“场域”理论得以应用于文化传播研究,为历史话语注入了来自关注经济、政治等介入性外部权力资本作用变化的新鲜血液。
(二)“文化场域”的界定
布尔迪厄将“场域”定义为由社会关系构成的结构性空间,受制于不同权力资本间的支配、屈从、对应等关系,理性对弈与暴力争夺无休无止地充斥其间。在此基础上,“文化场域”对应文化资本的作用范畴, 统摄新闻、艺术、科学、教育等子系统。相对于外部的经济场域和社会场域,文化场域整体及其内部的各个子系统保持相对自治并激烈争夺资源,根据拥有资本的富有程度或来自外部经济、社会场域中的资本权力决定自身所处的支配或被支配位置,而资本发生作用的边界却不甚清晰,只能模糊描述为“场域停止作用的地方”。
由此可见,尽管文化的价值判断基于自身属性,例如艺术作为艺术,新闻作为新闻……但其场域资本却取决于参与者。如同新闻场域是由对他者的批判构成一般,不同于表面价值的控诉,更加值得关注的,是文化场域内外资本的竞争,以及不同主权形式之间的张力,即文化场域的特性如何伴随经济发展、政治介入等外部因素发生变化。
布尔迪厄将资本的概念从经济领域拓展至文化领域,作为资本的文化与来自经济、社会场域的外部权力发生关联,文化资本的所有者根据“财产”保有量明确场域斗争中的关系位置。这种关联使得资本必须凭借场域发生作用,而场域又依据资本争夺进行空间界定。文化资本之所以成为场域内外激烈争夺的对象,其原因不惟在于文化场域内部自治权威的建立,而且在于经其转换而成的社会资本和经济资本,可以在文化之外的其他场域发生直接作用。
(三)“惯习”与文化传播
如果说“场域”描述的是文化传播的作用范畴,那么“惯习”说明的则是文化传播的生成状态,包括心理建设和身体行为两个方面。
受马克思主义实践观的影响,布尔迪厄脱离了结构主义的藩篱,独创性地将“惯习”定义为一种“持久而可转化的倾向系统,易于发挥结构作用,有助于生产组织的实践表达不必深谋远虑、蝇营狗苟而能够客观适应其结果”*Bourdieu, P. The Logic of Practice. Redwood City: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2. p.53.。作为导致行为产生的主导倾向,惯习把以往的经验综合起来,每时每刻都作为感知、判断、行为的母体发挥作用*[法]布尔迪厄、[美]华康德:《实践与反思: 反思社会学导引》, 李猛、李康译,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第234页。,是一种外在的内化和内在的外化的辩证关系。当“惯习”与“场域”不期而遇,以实践为介质,后者形塑前者,前者则将后者装点成一个体验真实、价值丰富、意义崇高的空间,“如同水中之鱼,丝毫感受不到水的重量,并认为周遭世界理所当然”*Loïc J. D. Wacquant, “Towards a Reflexive Sociology: A Workshop with Pierre Bourdieu,” Sociological Theory, Vol. 7, No. 1, 1989, p.43.。
上述关于“惯习”概念的本质规定激发和促进了文化传播的理论延伸:首先,“惯习”的后天养成性和社会变量性意味着培养的可能,使不同种族、性别、年龄、阶级、区域之间的文化传播成为逻辑上的必然;其次,“惯习”的形塑机制和生成策略使文化一旦被接受就可持续产生效果,这种持续又具有相对稳定性,为文化传播提供了量化标准;再次,“惯习”依附于环境生态的自发适应性显然具有艺术气质,将文化传播过程中基于情感的主观创作视为合理;最后,“惯习”作为普遍性(集体行为)与特殊性(个体行为)结合的产物,为文化传播的时代化、本土化习得和教养提供了依据。
二、三个导向:革命文化传播的“场域”路径
“场域”的界定提供了文化传播新的审视视角,“惯习”的关注给予了文化传播以新的操作启示。文化传播的核心要义在于遵循文化场域的思维逻辑和行为方式传播预期意图的意识形态,而不是相反。
(一)理性自识
保持立场鲜明的自治身份,抑制价值错位,抵制工具化倾向,不被外在的经济场域、社会场域资本所左右,是文化场域内部以意识形态引领文化属性、保持独立文化品格的首要前提。
就当前我国主流意识形态的传播效果而言,不尽人意之处显然与缺失文化场域的理性自识密切相关。在自我认知不客观、不清晰、不成熟、不全面的情况下,主流意识形态文化产品的全然市场化运作无异于面对来势汹汹的经济、社会资本门户洞开。而为经济、社会资本强势介入的文化场域随之必然发生两种情形:其一,场域内部资源占有丰富、处于支配地位的文化资本如虎添翼,借机开始了文化场域的外部扩张,例如美国主流意识形态的典型形态——个人英雄主义借助好莱坞这一资本托拉斯在全球范围内扩张推广;其二,场域内部渐趋成熟、前景明朗但资源占有不甚丰富、处于从属地位的文化资本,为入侵资本所左右而改变原有成长轨迹,转向靠拢经济、社会资本的预期意图,成为后者开疆拓土的新资源。以文化自信建设为目标的我国当代文化传播面临的压力主要根源就在于此,其中,集中体现中国共产党精神风貌的革命文化传播尤为突出。从革命历史遗迹的过渡旅游化开发,到红色题材影视剧的过度娱乐化倾向,从地方政府看重的革命资源产业式开发,到公民大众乐见的革命文艺群体式参与……显而易见,一旦消费主义介入革命文化,工具主义战胜自治理性,资本构成层面的人、事、物承载的主体革命精神、独立文化理念和内在自由品格就会渐行渐远。
(二)惯习转换
鼓励多元表达,转变刻板印象,培育宽容、客观而理性的传播和接受心态,是文化场域内部自信养成、外部推广延伸的必要手段。
结构和倾向是布尔迪厄解读“惯习”这一概念的两个切入点。结构意义上的“惯习”既是经济、社会由外而内向文化的条件性转化,也是文化场域内部系统由内而外向经济、社会的构成化变形。这是一个互动发展的过程,不存在一成不变或者特立独行的例外。当前我国革命文化的传播很大程度上受制于结构转变的不适。面对受众最为广泛的大众文化,革命文化作为主流意识形态的介入不可避免地会形成文化场域内部的竞争张力,因此必须通过新闻、艺术、科学、教育等文化场域内部子系统的适应性结构调整获得优质传播效果。然而,受政府主导的革命文化长期以来由于传播主体圄于官方思维,将外部社会(政治)场域的观念认识、操作模式和工作作风照搬入文化场域,一再低估文化场域内部的原生惯习,想当然地采取一味灌输、强制命令、缺乏培养、拒绝调整等“强加式”传播方式。惯习的疏离导致受众的不适,传播效果受阻引发文化自信动摇。可见,革命文化在从社会(政治)场域的意识形态过渡到文化场域的资源内容过程中,必须遵循惯习培养的规律,进行适应性结构调整,完成跨场域的资本二次生成。
倾向意义上的“惯习”是被社会熏陶的主观性,是一套外在于身体表达、反映历史进程及社会结构并能够进行持续转换的性情系统。在某种意义上,“惯习”可以看作是一种先天的限制,它建构起文化场域内部资源的自我认知、判断和行为模式。基于这一立场,文化场域内部传播主体和受众倾向的培养就至关重要。就革命文化的传播主体而言,从事主流意识形态传播的政府理应着力于从社会(政治)场域的行政管理者向文化场域的惯习培育者的角色转变;就革命文化的传播受众而言,陷入红色信息冲击的文化场域内部各级参与者也该注意到自身固有的惯习倾向导致的刻板印象、接受偏见和舆论不公。例如,“文化大革命”时期形成的类型人物形象符号化观念根深蒂固,拍摄于1998年的电影《红色恋人》甚至因此遭受过主演选角的腹诽和质疑。因此,主动的惯习倾向意识和转变直接催生宽容的接受心理、客观的评价体系和理性的价值判断,从而为文化传播营造良好的环境生态。
(三)在地培养
马克思主义之所以始终具有旺盛的生命力,就是由于其每当置身于新的语境时,都会作出基本原理的适应性调整,以应对所处地域和时代的经济、社会、文化特征。“场域”理论提供了文化的“领土”意识,厘清了文化资本的内外场域以及内部的子级系统,某种意义上意味着传播环境存在差异的必然。基于这一认知,文化的普遍认同需要注重传播策略,针对目标场域实施惯习的本土化在地培养。这是保持文化场域内在逻辑的核心策略。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历久弥新,其根本在于其与中国本土文化(传统与习俗)在社会(政治)场域内的深入融合。这种融合规定了马克思主义的建设性维度,为区别于欧美的“中国特色”奠定了基础。以毛泽东思想为例,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毛泽东对中国传统文化持批判继承的态度,在他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中,充分吸收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要素,赋予马克思主义以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换言之,也就是使马克思主义拥有了一定的中国文化气质。
社会场域的实践经验为文化场域提供了支持。革命文化作为主流意识形态的传播,首先需要将精神内涵与本土共通价值相结合,完成场域内的信仰重塑;其次,需要将观念内容与本土主流话语相结合,获得场域内的逻辑认同;第三,需要将目标设计与本土现实需要相结合,达至场域内的受众亲和;最后,还需要将手段运用与本土媒介形态相结合,实现场域内的表达落地。在地培养不仅可以弥合东西差异、新旧分野,而且可以重塑革命文化的精神内核,从而生成更为强大的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文化哲学——这才是文化自信建设的核心实力。
三、传播实践:沂蒙精神的跨场域革命文化资本重构
“场域”理论使文化传播得以历史化呈现,也令其制度基础分析成为可能。如果把文化传播置于中国共产党成立、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以来的特定历史时期,那么革命文化恰恰由于时间节点的匹配具有了探讨的意义,而其中实现了文化场域内部子系统多重融合的沂蒙精神最为典型。
沂蒙精神“是沂蒙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中国革命、建设的历史进程中形成的可贵民族精神”*曲筱鸥:《“沂蒙精神”理论研究的历史、现状与对策》,《临沂大学学报》2015年第5期,第35页。,集中概括为“爱党爱军、开拓奋进、艰苦创业、无私奉献”*1998年12月12日,“沂蒙精神”首次提出,1990年2月2日,时任中共山东省委书记的姜春云同志将其概括为“爱党爱军、开拓奋进、艰苦创业、无私奉献”的16字精神。见周广聪、张帆:《沂蒙精神16字来源》,《齐鲁晚报》2011年7月27日第2版。,它与井冈山精神、延安精神、西柏坡精神等并称为中国共产党的红色革命精神,内蕴着革命文化的丰富内涵。站在“场域”理论角度,沂蒙精神通过报刊、歌曲、影视等形式开展的多元文化传播并且成绩斐然,或许可以解读为其作为革命文化资本从政治场域、经济场域、社会场域向文化场域内部子系统的合理移植与对接产生的可见性效果。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沂蒙精神出色地完成了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革命文化的跨场域资本重构。
(一)爱党爱军,开拓奋进——报刊对政治场域的新闻移植
沂蒙精神中的“爱党爱军,开拓奋进”体现的是拥护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革命军队的坚心毅志和追求自由、勇往直前的革命斗志。其传播实践反映了马克思主义作为意识形态从政治场域到文化场域的成功介入。这一资本重构过程的主要载体是文化场域新闻子系统的红色报刊。
新民主主义的革命思潮将20世纪的中国政治场域鼓动得风起云涌。秉承马克思主义思想的中国共产党自20年代初开始在沂蒙地区开展最初的革命活动,传播马克思主义,组建政治组织。伴随抗日战争爆发,1938年1月,毛泽东做出了“努力向山东发展,尤以控制蒙阴、宫县等广大地区为重心”*山东省文化厅史志办公室、渤海革命文化史料征集协作组编:《难忘的历程·渤海篇》,山东文艺出版社1991年版,第70页。的指示,山东抗日根据地就此开辟。1938 年底,八路军山东纵队、中共山东分局成立。1939年9月,八路军第115师挺进沂蒙山区,建立了以抱犊崮为中心的鲁南革命根据地,进一步联合民众参与抗战。1945年12月,中共中央将山东局与北上的华中局合并成立华东局,总部设在临沂。1947年1月,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下令,将华中野战军与山东野战军合并组建为华东野战军,下辖12个纵队,兵力共计35万人,党的高级将领陈毅、粟裕分别担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和副司令员,成为当时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主力部队。这次整编之后,中共中央华东局、华东军区和华东野战军三大机关总部均迁至临沂。沂蒙成为我党在华东区域名副其实的政治和军事中心。
与政治场域的革命运动相呼应,中国共产党把握有利时机,迅速组建团队,在文化场域内部的新闻子系统展开舆论造势,将工作的另一个重心投向意识形态的文化场域落地,为受众惯习培养奠定了基础。
1939年1月,响应中共中央六中全会关于创办地方性报纸的要求,中共中央山东分局的机关报——《大众日报》在沂蒙地区沂水县王庄创刊,办报宗旨定位为“巩固与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国共两党及一切抗日党派精诚合作,共同领导,绝对捐弃成见,避免摩擦,绝不消弱及分散抗战力量”*《大众日报发刊词》,《大众日报》,1939年1月1日创刊号。。这一宗旨可谓政治场域在文化场域的直接投射。当时中华民族危机加深,战争形势紧迫,国共合作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业已形成,中日双方陷入相持局面,军事重镇山东成为必争之地。当时山东境内除了我党建立的敌后抗日根据地之外,还分布着国民党的苏鲁战区和日寇的伪政权,政治形势前景未明、颇为动荡。基于如此背景,创办《大众日报》,旨在鼓舞士气,引导舆论,打破僵局,夺取胜利。
1941年6月,在原大众通讯社基础上,中共中央山东分局组建成立新华社国内首个省级分支机构——山东分社,时任中共中央山东分局宣传部长的李竹如兼任社长,办公地点设在当时的中共中央山东分局和115师师部驻地——沂蒙地区临沐县古城村。成立当天,新华社山东分社即以本社电头播发了《八路军破袭 敌伪皆望风披靡》、《清河区广大青年涌上抗日哨岗》、《泰山区实行统一支差办法》、《临、郯、费、峄人民吁请于总司令合理解决边区惨案》等六篇消息。1945年8月14日,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首个省级行政单位——山东省政府成立的消息由该社播报,传播效果十分显著。
就当时山东文化场域内部资本而言,《大众日报》和新华社山东分社成立之前,由中国国民党山东省政府主理的《山东公报》和《山东民国日报》一直是对抗日伪新闻阵营文化侵略的主要力量。然而,敌强我弱的被动战局导致国共两党兵力分割,条件艰苦,沟通不便,加之政见差异,无法及时向抗日根据地军民反映战况信息,传播内外舆论。《大众日报》和新华社山东分社的适时成立,恰恰可以填补媒介覆盖漏洞,满足特定区域受众信息诉求。这种由需求主导的信息传播,可以自然融合我党作为文化场域参与者的政治场域资本,减少场域内原生资本阻力,实现战争时期马克思主义在人民大众中的进一步平稳落地、生根发芽,其意义绝非仅仅局限在“耳目喉舌”的层面。
考察革命战争时期沂蒙地区的新闻史可见,作为文化场域内部子系统的新闻报刊,一方面形成了与政治场域相关联的文化场域,创办了通讯社和刊物;另一方面明显植入了中国共产党特定时期的政治意图,将英勇奋战、解放人民、夺取胜利的革命精神传播得淋漓尽致。在沂蒙地区新闻场域建构的问题上,与其关注报道内容,场域内外的资本流动、组织实践似乎更加值得追问。在有利的政治条件下,《大众日报》的创刊发行和新华社山东分社的成立,完成了马克思主义由政治场域到文化场域的移植,并凝聚为爱党爱军、开拓奋进的沂蒙精神。
(二)艰苦创业——音乐对经济场域的艺术内化
沂蒙精神中的“艰苦创业”体现的是不畏困难、埋头苦干的实干精神和勇猛精进、持之以恒的拼搏奋斗。其传播实践反映了马克思主义从经济场域到文化场域的合理转型。这一资本重构过程的主要载体是文化场域艺术子系统的音乐(歌曲)。
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认为“存在决定意识”,强调经济基础对上层建筑的决定作用。这一观点印证了经济发展对文化生成的强大影响。无论是欧洲吉普赛民族的神秘占卜、非洲原始部落的鲜艳服饰,还是中国传统社会的血亲伦理,这些流传至今的文化传统大都发生在西方现代文明未曾笼罩的经济欠发达区域。这说明,发达经济形态下的人类,由于具备完备的认知体系和工具技能,可以主动祛魅所处环境,从而不再敬畏自然或崇尚理想。这种自我中心主义倾向使传统人际社会的依附关系逐渐淡化,而后者,恰恰是文化氛围营造的核心依据。
沂蒙精神的发扬光大,某种意义上正是借助了沂蒙山区经济场域的特点。革命战争时期,日寇的围剿扫荡和国民政府的包围给沂蒙山区经济生产造成了沉重打击,加之严重的自然灾害,甚至出现过纵横近100公里的“无人区”*山东省档案馆、山东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山东革命历史档案资料选编》第四辑,山东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00页。。建国初期以厉家寨为代表的大规模整山治水农业运动,改革开放后以九间棚村为典型的修路、引水工程建设,起因均在于沂蒙地区自身相对恶劣的天然多山地理条件。这就为革命文化意义上的沂蒙精神,作为一种介入性资本在原生文化场域内的广泛、顺利传播,提供了来自经济场域的合理支持。
作为一种兼具音乐性与文学性的艺术形式,歌曲的独特之处在于,其作为音乐属性的旋律和作为文学属性的歌词可以分别独立进行媒介传播。一首歌曲的流传,既可能由于人们熟知或热衷其旋律,也可能因为人们喜爱或共鸣其歌词。沂蒙山区素有演唱民歌的民间传统,运用歌曲传播革命文化、陶冶沂蒙精神天然具备广泛的群众基础。以堪称沂蒙精神符号经典的革命歌曲《沂蒙山小调》为例,其最初创作发生在沂蒙抗日根据地建立不久、战争形式严峻、生活条件异常艰苦的1940年。为鼓舞士气、团结群众,抗大一分校文工团授命政治攻坚,主任袁成隆组织编审股长李林和团员阮若珊借鉴沂蒙当地的花鼓调,在沂蒙山第三高峰——望海楼脚下的薛庄镇白石屋村创作完成了《沂蒙山小调》的前身——《反对黄沙会》。1953年,时任山东军区文工团副团长的李广宗、乐队指挥李锐云和研究组组长王印泉在搜集整理的基础上对原曲调进行了重新记谱,并补充填词,完成了最终创作。朗朗上口的曲调辅以简单质朴的歌词,这首《沂蒙山小调》深受军民欢迎,就此流传开去,直到今天。“人人都说沂蒙山好,/沂蒙山上好风光。/青山绿水多好看,/风吹草低见牛羊。/高粱红,豆花香,/万担谷子堆满仓。 /咱们的共产党领导好,/沂蒙山的人民喜洋洋。”歌词中虚构却明确的美好景观(青山绿水,风吹草低)和丰收意象(高粱红,豆花香,万担谷子堆满仓),与现实经济场域的物质匮乏形成鲜明对照,充分满足了沂蒙革命根据地乃至全国人民对革命胜利后的美好生活的向往。更为重要的是,《沂蒙山小调》对于这一想象的描摹并非完全虚构,而是在歌词中着力表达了两个基础:其一是沂蒙山区众所周知的天然环境(人人都说……沂蒙山上好风光),为沂蒙精神寻求到了承袭自悠久东夷、齐鲁文化的历史因缘,从而建立起革命文化惯习培育的地缘基础;其二是中国共产党的场域自治主权(咱们的共产党领导好),在幸福生活与艰苦奋斗之间建立起直接链接,从而暗示出革命文化的合理性及必然性。通过民众喜闻乐见的曲调,这首歌曲广为传唱,人们越是深切体验经济场域的物质匮乏,就越会从内心培育起对既关联原生文化传统又指向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文化的热切期待和无限向往。这种源于经济场域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潜移默化的洗礼,强化着异质文化认同,并将其最终合理化为艰苦创业的沂蒙精神。
(三)无私奉献——文学、影视对社会场域的教育延伸
沂蒙精神中的“无私奉献”,体现的是克己奉公、鞠躬尽瘁、舍身取义的人生情怀。其传播实践反映了马克思主义作为终极理想从社会场域到文化场域的惯习培养。这一资本重构过程的主要载体,是文化场域教育子系统的文学影视作品。
中国传统社会由父子、君臣、夫妇、兄弟、朋友五种伦理关系构建而成。普遍认为,“五伦”既是儒家文化的狭义人伦,也是中华民族区别于西方的伦理情感的根本特征,是一种典型的血亲伦理。地处齐鲁腹地的沂蒙地区自古以来深受儒家文化浸染,对“五伦”建构起的社会关系抱有根深蒂固的普遍认同。革命文化意图传播的阶级意识和共产观念,作为一种血亲之外的伦理认知,要完成介入,不得不面对传统社会的改造,着手新型社会伦理的重建。
中国社会自近代以来不乏对血亲伦理的批判之声。不同于明清时期对“三纲”“五常”的指责,也不同于新文化运动对“民主”“科学”的鼓呼,沂蒙精神倡导的“无私奉献”,可以看作是融合传统血亲伦理认知基础上的对象外扩,将传统的“亲吾亲、子吾子、老吾老……”式的内向性亲缘关怀,向外扩展至秉承同样共产主义理想、共处同一无产阶级的人民军队和革命战友,在不推翻原有社会关系内在秩序的前提下,完成了由血亲到阶级,由家庭到国家的延伸,从而实现了国族主义、革命信仰与人伦道德的融合。这一思路以大众传播领域受众广泛的文学(小说)和影视为载体,尤其有利于革命文化作为文化场域的介入性异质品类开展受众惯习培养,使人们习以为常并乐于参与,最终形成社会关系和文化心理的常态,显示出强大的教育功能。
体现沂蒙精神的革命文学及其改编的影视作品,不是秉承“观照—表现的态度”,而是力图“完成主体阶级的历史使命”*李初梨:《怎样建设革命文学》,《文化批判》1928年2月15日第2号。,通过革命叙事开展中国共产党领导革命的正义性言说,在教育层面完成革命历史的经典化再造。刘知侠创作发表于1961年的小说《红嫂》以及由其改编而成的电视剧《沂蒙》(2008)、电影《沂蒙六姐妹》(2009),可以作为沂蒙精神跨越社会和文化场域、开展受众惯习培养的典型。作品取材于革命战争年代沂蒙山区“红嫂乳汁救伤员”的真实事件,讲述了1947年孟良崮战役结束后的转移途中,人民解放军排长彭林为掩护主力部队身负重伤,躲入山林,昏迷不醒,被上山挖野菜的红嫂无意发现,情急之下,红嫂以乳汁救之并加以掩护,与“还乡团”敌人斗智斗勇,对父老乡亲耐心说服,最终获得支持,将彭林安全送回部队的故事。小说一经发表,立即引起广泛关注,改编为影视作品后,更是在全国范围内产生了长达半个世纪的巨大影响。在“场域”理论视野下,这一现象背后由“无私奉献”引导的跨场域社会伦理重建及受众惯习培育不容忽视。
在血亲伦理建构起的“五伦”中,相较于君臣关系与朋友关系,父子关系与兄弟关系基于血缘、夫妇关系基于姻缘更为亲密。受此影响,中国传统女性的身体呈现保持绝对禁忌,君臣、朋友毋庸讳言,成年女性与父子、兄弟之间也限制严格,唯有姻亲关系下的夫妻基于传宗接代需求获得许可,但也极受时间和场所的制约。小说《红嫂》的核心内容,完全建构在成年女性对非亲/姻关系对象在天然环境(非私密场所)和偶然机缘(非蓄意时间)的坦诚甚至赤裸相见上,这无疑直接挑战了儒家文化传统人伦道德的底线。然而,借助革命文学的叙事铺陈,挑战秩序本应承受的规训和惩罚,为共产主义理想和信仰的崇高意义牢牢遮盖,悄无声息地消解于军民形同母子、阶级弟兄鱼水情深的革命话语中,不但无需羞愧,不必遮掩,反而值得尊重,应该学习。小说、电影和电视剧中的“红嫂”们年轻茁壮,面容姣好,良善聪慧,亲和友爱。人物形象的类型化塑造,更从侧面强化着为革命“无私奉献” 的必然美好。
事实证明,这种以事实为依据、以文学影视为手段的大众传播和群众教育成绩斐然。小说诞生二十年后的80年代,当原中央军委副主席迟浩田重回沂蒙,找寻战争年代救治自己的两位红嫂时,当地年迈的女性纷纷否认,表示理所应当,人人都做,于是无从寻起。在革命文化的伦理道德反转式惯习培育下,红嫂成为了“无私奉献”常态化的代名词。更为重要的是,这一跨场域传播思路,不唯引发了革命战争年代“无私奉献”精神的迅速普及,而且对时下应对西方工业文明引发的现代性危机的思路开拓同样颇有助益。
四、结语
“场域”理论提供了审视文化传播的新视角,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内涵,从某种意义上如同引路人一般指导沂蒙精神完成了从政治场域、经济场域、社会场域到文化场域的资本转移,将作为意识形态、生产原理和终极理想的马克思主义,以文化场域内的报刊、音乐和文学影视为载体,成功植入了原有传统文化场域并培养育成了受众惯习,通过“爱党爱军、开拓奋进、艰苦创业、无私奉献”的具体表达,实现了介入性、异质性革命文化的跨场域传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