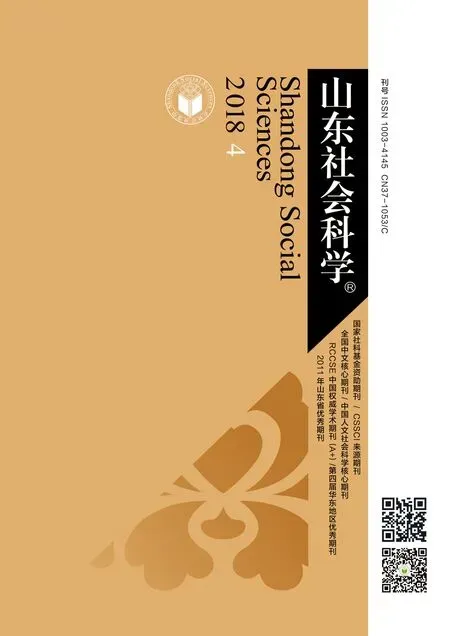色彩时空的多维建构与色彩感知的多重调度
——论席慕蓉诗歌的色彩书写
2018-01-29沈壮娟
沈壮娟
(中国石油大学(华东) 文学院,山东 青岛 266580)
色彩是事物本身的颜色在光影下的复杂呈现,也是人类感知和表现世界的重要方式。色彩感知,是人的生理心理与客观世界交互作用的结果,具有历史性特征,但也具个人性。以文本呈现的色彩感知不受颜料技术的直接制约,且拥有内视觉上的流动性,这种时间品质使其更具“情感与象征的双重功能”*尹成君:《色彩与中国现代文学》,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58页。,因而表现出比绘画更大的自由度与更强的主观性。对色彩敏感或受过专业训练的写作者往往呈现出具有强烈个性的色彩书写,如奥尔罕·帕慕克的“红”、李金发的“灰白”、鲁迅的“黑漆漆”、张爱玲的“青灰”等。席慕蓉系统研习过国画、水彩、油画、蚀刻铜版画、激光绘画等,多次获国际大奖,专业的色彩训练赋予她超凡的色彩感知能力。丰富的色彩表达极有层次地承载了作者的情绪与情感、哲思与审美意识,冲击力极强,是其诗歌艺术魅力的重要来源。已有不少学者注意到诗人的画家身份对其诗作的影响,这些分析肯定了席慕蓉诗作在色彩方面的表现力,但探讨仍未涉及其用色全貌,也并未将色彩书写作为席慕蓉诗歌的本体性特质予以讨论。实际上,席慕蓉的色彩书写并非仅停留在简单的修辞层面,而是以色彩建构了生活肌理与生命脉络。
一、黑白为主的颜色镂刻
颜色词是用来命名和描绘色彩的词汇,积淀着民族情感与文化心理,文学文本中颜色词的使用具有丰富的文化象征意义。席慕蓉的《七里香》《无怨的青春》《我折叠着我的爱》《时光九篇》《迷途诗册》《边缘光影》《以诗之名》《除你之外》这8册诗集*本文以台湾圆神出版社出版的8册诗集为引用依据。这8册诗集囊括了席慕蓉的主要作品,具体为《七里香》(2000年版)、《无怨的青春》(2000年版)、《我折叠着我的爱》(2005年版)、《时光九篇》(2006年版)、《迷途诗册》(2006年版)、《边缘光影》(2006年版)、《以诗之名》(2011年版)、《除你之外》(2016年版)。共包含419首(组)诗,使用颜色词360余次。颜色词的使用频次之高令人瞩目,呈现出时间上的特殊面貌与意义。
(一)颜色词使用的基本面貌
8册诗集的颜色词主要集中于“黑”“白”“绿”“黄”“灰”“蓝”“青”“紫”“红”“褐”“粉”等词,其中,消色类颜色词使用(“黑”“白”“灰”)占57%,中间色(“绿”“紫”)占11%,暖色类(“红”“黄”“褐”)占16%,冷色类(“青”“蓝”)占16%。冷色与暖色旗鼓相当。诗人对颜色词的选择极有侧重,整体而言,“黑”与“白”的使用远超其他颜色词,不同诗集的颜色词面貌又各具特色。
《七里香》和《无怨的青春》两部诗集中,“黑”分别出现了5次和4次,而“白”的使用分别为11次、16次,“黑”远低于“白”的使用频率,与“绿”“蓝”“灰”的使用频率相当。这两部诗集中由颜色词所构筑的色彩世界以白色为主,辅以绿、蓝等色,其他为点缀,如红、紫色。这种搭配方式与春夏季节的色彩相呼应,整体上爽洁又不失活泼。《我折叠着我的爱》中,“白”略高于“黑”的使用频率,其他彩色颜色词共出现了11次,其中“红”出现了5次,是使用最多的彩色颜色词,而“绿”“蓝”两种冷色颜色词只出现了3次。本部诗集呈现偏暖的色调。
《时光九篇》和《边缘光影》则构筑了极不相同的黑色世界。“黑”的使用分别为20次和23次,是诗集中出现“黑”最多的两部。“白”的使用分别为10次、9次。《时光九篇》中其他颜色词的使用较少,但《边缘光影》使用了较多的“灰”与“青”,使诗集呈现浓郁的黑灰色调,其他颜色(包括白色)都成为黑色世界的零星点缀。
与以上诗集不同,《迷途诗册》中彩色颜色词的使用总频次超过了“黑”“白”“灰”消色类颜色词的使用。“黑”“白”“灰”共出现了17次,而“绿”“蓝”“红”“紫”“粉”“黄”“褐”等彩色颜色词共出现了23次,其中“蓝”“紫”“褐”的使用频次都达到了峰值,是最为色彩斑斓的一部诗集,似是踏上了喧嚣的色彩“迷途”。
《以诗之名》和《除你之外》两部诗集用色较为接近,都表现为黑白基色下的浓郁色调。在《以诗之名》中,“黑”“白”分别出现了15次、16次,其他彩色颜色词共出现了近30次。“黄”“红”的使用都达到了峰值,分别为11次、7次。整部诗集色彩浓郁,又因为高明度的“黄”“红”的高频出现而显得格外俊朗与热烈。在最新诗集《除你之外》中,“黑”“白”分别出现了16次、13次,与《以诗之名》极为相似。不同的是,其他彩色颜色词只出现了20次,远少于《以诗之名》。其中“绿”的使用达到了峰值,“黄”也有7次之多,而“粉”“紫”“青”“褐”等颜色词均未出现,“红”的使用也减少到了4次。较少的暖色、较多的中间色再加上较高的纯度,使诗集色调比《以诗之名》更强化了俊朗、开阔之感。
(二)色彩意义的绵延
在不同时期,诗人通过颜色的选择与组合对生命进行色彩编码,绵延出了一条生命之河。白色与绿色向来意义复杂:白色包含圣洁、死亡、恐怖等寓意;绿色包含贫贱、腐败、毒药、生机等寓意。诗人选择了白色与绿色作为生命之河的初始颜色。早期两部诗集中,大量的白色与绿色是青春时代的色彩密码。她在一望无际的绿色之上,用花之白(如《七里香·七里香》,1979;《以诗之名·桐花》,1984)、裙裾之白(如《无怨的青春·十六岁的花季》,1978)来描摹少男少女纯洁秀美的心思。此类调度乍看与其他诗人颇为相似,但却呈现了其他诗作中鲜见的丰富层次,绿与白的内涵被大大拓展。白色借由一再被强调的月光传达出生命中的纯粹初心,此一永恒价值超越了青春岁月的白色书写。她在《两公里的月光》(2003)中写道:“而月色何等明亮/穿越过松林 在这两公里的山径上/我终于相信 此刻/与我们静静相对的 应该就是/那五千五百年完完整整的时光。”(《我折叠着我的爱》,第150页)这种追索,让白色的纯洁与纯粹拥有了岁月厚度。同时,大量的绿色由诗作中的草原带来,作为远离草原的蒙古族人,席慕蓉一再提及绿色草原,这既是对自己民族身份的反复确认,也是对自我生命之根的一次次抵达。绿色是远方,也是故乡。白色与绿色由青春密码成长为个体生命、族群生命、人类生命的底色,鲜有诗人能够完成如此丰富的意义层次,显示出诗人自觉的色彩意识。
紫色融合了蓝色与红色,兼具冷、暖两种感觉,给人的感受复杂饱满。中国传统色彩文化中,紫色虽为间色,但能“夺朱”(《论语·阳货》),是间色里运用等级最高的色彩,“在大多历史时段成为人间最贵之色”*陈彦青:《观念之色:中国传统色彩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12页。。紫色在诗作中尽管出现次数不多,但是每次出现都刻记了生命的怒放状态。在《菖蒲花》(1985)中出现的悍然紫色,宣示着生命的全部激情:“而此刻菖蒲花还正随意绽放/这里那里到处丛生不已/悍然向周遭的世界/展示她的激情 她那小小的心/从纯白到蓝紫/彷佛在说着我一生向往的故事。”(《时光九篇》,第104—105页)从芙蓉清淡的浅紫(《时光九篇·历史博物馆》,1984),到杜鹃大喇喇的粉紫(《以诗之名·以诗之名》,2006),再到鸢尾花怒放过后的深紫(《边缘光影·鸢尾花》,1989),逐一展示了生命怒放的不同阶段。诗人在《迷途诗册》中所呈现的斑斓色彩、冷与暖的对比,加在一起,恰好形成深深浅浅的紫,如同新印象派的点彩技法。怒放之紫,阐释了诗人对生命怒放之态的体悟。
法国色彩社会学家帕斯图罗发现,世界各地的人们不约而同地将黑色作为世界的起始色。*参见 [法]米歇尔·帕斯图罗:《色彩列传·黑色》,张文敬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6年版,第3页。作为孕育了光明的颜色,黑色既是光明的对立面,又是光明的孕育者。在中国现代文学中,黑白两色常代表恶与善的对峙(如鲁迅),当代中国女性书写常把黑色与女性身体欲望相关联(如陈染)。席慕蓉使用的大量黑色,其象征意义更为复杂。在诗人笔下,黑色确实象征了外在世界残酷的一面,但更象征着时间给生命带来的岁月黑洞与记忆海底。深不见底的黑,既具空间意味,更具时间上的宿命感。诗人早期诗作充满了对这一生命悲剧真相的排斥与恐惧,但到了2000年后,其诗作更多地表现为坦然。这与我国其他女性作家仅仅纠缠于女性身体的黑色赋形相比,更具形而上意味。生命以黑色为底,而红色则是黑夜里飞蛾必须扑向的烛火(《以诗之名·执笔的欲望》,2009),是黑暗地底不熄的山火(《除你之外·山火》,2015)。红与黑浑融一体、奋力交响,形成了诗人对生命的大觉悟,见证着诗人的生命由轻盈走向厚重,由狭窄走向阔大,由弱小走向强壮。这种生命力与觉悟力是推动诗人的关注范围由自身逐渐扩展到民族、环境等的内在根由。
席慕蓉以色彩的运动,绵延出一条生命之河。这条生命之河以黑白色为底,绿红紫等色镂刻其上,随岁月而变化绵延,这既是诗人对生命的体悟,又是诗作生命的生成与建构。色彩的绵延展现了诗人生命之河由单纯到浑阔的过程,传达着生命热度;它标志着诗人对色彩的时间性维度的开拓,体现了色彩书写的强烈自觉,是诗人色彩书写的重要特征之一。
二、色彩时空的多维建构
席慕蓉通过夜晚、傍晚、清晨、草原、山林、大海等特殊时间与空间的选择,建构了多维度的色彩时空,形成了强烈的个人色彩。
(一)诗歌时间的光影环境
“光线,是揭示生活的因素之一,是人和一切昼行动物大部分生命活动进行的条件,又是推动生命活动的另一种力量——热量——的视觉对应物。”*[美]鲁道夫·阿恩海姆:《艺术与视知觉》,朱疆源等译,四川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406页。光的变化使万物产生不同的色彩纯度,导致不同的色彩感受。席慕蓉对时间的精心选择也意味着对色彩整体光源环境的精心选择,这使诗作呈现印象派绘画的美学效果。
诗人所描绘的时间常是夜晚,与夜晚相关的黑暗或月色的银白等就成为笼罩万物的光源环境,使万物皆身披月色与黑色。万物的固有色或被隐去,或在月色与黑色中失真,形成某种整体的光晕。诗作题目中出现“夜”的有5篇、出现“月”的有9篇。除去标题,其诗作共出现“夜”近300次,出现“月”百余次(只统计月亮、月光之“月”),远超使用最多的颜色词“黑”的数量。频繁出现的时间还有傍晚与清晨。其中“暮”出现了48次,“晨”出现了30次。清晨的灰蓝与傍晚的夕阳红都成为笼罩全诗的环境色,使万物本身的固有色千变万化,呼应着诗人的主观情感。雨、雾等特殊时刻也常出现在诗作中。除去标题,“雾”“雨”分别出现了65次、56次。这些时刻因雾和雨而呈现整体的灰色。如“若有泪如雨 待我洒遍这干渴丛林/让藤蔓攀援让苔藓层层包裹让浓雾终日弥漫/封锁住 那通往去夏的 山径”(《边缘光影·去夏五则》,第134页),迷蒙的灰,是诗人抑郁心境的外在表征。
引起万物色彩变化的还有春夏秋冬,但是冬季在席慕蓉的诗作中并无太多呈现,这与诗人的生活地域有关:诗人所生活的香港、台湾,植物常青,四季并不分明,由此带来的季节色彩变化并不是太大。秋季的色彩书写较多,山林的由绿到枯黄与赭红(如《秋光幽微》,2002),在诗中着墨较多,以此表达时间的流逝。
席慕蓉诗作的时间环境色彩主要是黑、灰、银白,呈现较暗的总色调,当万物蒙上黑、灰、银白色调时,固有色的纯度降低,被笼在了特殊的光晕之中,形成较为内敛的整体情思氛围,在这种特殊情思氛围的审美“总指挥”*李天祥、赵友萍:《色彩之境——色彩美研究》,化学工业出版社2015年版,第24页。之下,诗人的情感传达显得含蓄内敛,生成了颇具古典意味的诗歌意境。冯乃超、戴望舒等人的诗作也喜欢用黑夜、雨、黎明等营造朦胧的气氛(如《红纱灯》《雨巷》等),但席慕蓉对光影环境普遍关注,相关词汇几乎出现在所有诗作中,这在我国现当代诗人的色彩书写中极为罕见。
(二)诗歌空间的色彩地理
尽管成年后的席慕蓉主要生活在都市,其诗歌空间却鲜有高楼大厦,反复出现的是雨雾风云、山川湖海、星空宇宙、植物动物等。这些事物主要存在于下列物理空间中:草原、山林、大海。从色彩角度看,这些物理空间大致以绿、黑灰为主色调。草原、山林空间以绿色为主色调,大海,星空等以黑灰色为主色调。这些反复出现的空间容纳着诗人的情思,空间中的色彩“不仅抓住人们的注意力,而且激发人们内心的激情与渴望”*[美]保罗·泽兰斯基、玛丽·帕特·菲舍尔:《色彩》,李娟等译,广西美术出版社2008年版,第11页。,空间的主色调与具体色彩的互动就成为诗人情思复杂流动的外在显现。
绿色空间主要有草原空间、山林空间,这两种空间主要与植物有关。以牧草为主的草原空间与以树木为主的山林空间是其他生物的栖居之所,也是诗人的精神故乡。在其诗作中,标题出现“草原”的有3篇,正文中共出现了60余次。“草原”始终就是故乡的符号。如“想着草原千里闪着金光”(《七里香·出塞曲》,1979,第169页)、“长城外草原千里万里”《七里香·狂风沙》,1979,第172页)、“青碧青碧的草原”(《边缘光影·祖训》,1987,第163页)。早期诗作中的草原宽阔无边,青碧中闪着金光,呈现出诗人对故乡的美好想象。随着时间推移,远景中的理想故乡越来越近,逐渐充实,成为一个容纳生命的“碧绿的生命之海”(《边缘光影·蒙文课》,1996,第174页)。这里有河流哺育牧草,有“黑骏马”助诗人驰骋(《以诗之名·黑骏马》,2005,第172页),人与自然互敬互爱。在绿色背景上,羊的白色、火的红色、马的黑色、金色、棕色等都生机勃勃,与绿色相得益彰。随着诗人对真实草原的了解,青碧草原开始变得“枯黄”(《以诗之名·当时间走过》,2009,第177页),变成了白色的“棉花田”与黑色的“煤矿”(《以诗之名·梦中篝火》,2010,第193页),草原由精神故乡变为承载着太多悲欢的“原乡”。可以说,绿色是草原空间的活力和生命所在,绿色消逝,一切也就失去生机。诗人用绿色的消长来记录草原的枯荣,体现了诗人对这一空间深切的爱与思索。
山林空间的绿是低纯度的深绿与灰绿,有时甚至接近黑色,其变化比草原空间更复杂:一条线索是时间流逝带来由绿到枯黄、赭红的变化;另一条是心理线索,当这一空间与作者的潜意识或可怕尘世相关联,就会显现为灰黑色。“林”在诗集中出现了百余次,高于草原的出现频次,可见山林空间的重要性。山林空间的重要植物是树木,落叶树木在春夏显现为绿色,常青树木四季常青。树与树相连阻挡了阳光,树木的高度让这个空间与草原空间不同,更为立体也更为私密,能容纳更为丰富的生物。包孕性是这一绿色空间的首要特征。如“林间有新绿似我青春模样”(《七里香·山月》,1977,第54页)、“我只是想再次行过幽径 静静探视/那在极深极暗的林间轻啄着伤口的/鹰”(《边缘光影·鹰》,1987,第16页)、“譬如林中的你/如何微笑着向我慢慢走来 衣裙洁白”(《边缘光影·边缘光影》,1996,第213页 )、“在暗绿褐红又闪着金芒的林木深处/一只小鹿听见了什么正惊惶地回头/眼眸清澈的幼兽何等忧惧而又警醒”(《迷途诗册·鹿回头》,2001,第110页)。山林空间孕育万物时,万物给山林带来斑斓色彩;当失去这一母性功能时,山林空间“必然也会逐渐失去记忆”(《我折叠着我的爱·悲歌二○○三》,2004,第119页),成为“空寂的林间”(《时光九篇·残缺的部分》,1984,第38页),这一空间就会变色成枯黄或赭红。当山林空间象征世间的不完善或丑恶时,就会变成黑色,如“这尘世是黑暗丛林/为什么 我依旧期待黎明”(《边缘光影·天使之歌》,1989,第45页),黑暗表达了诗人对人世的恐惧。诗人还用森林比喻潜意识与记忆,如“远处林间有些什么闪动着丝绸般柔滑的光芒/是一株黄玫瑰正在我们初识的那个夏日徐徐绽放/远处林间有些什么闪动着丝绸般柔滑的光芒/却彷佛还见你唇角那年轻狡黠的笑意”(《以诗之名·最后的折叠》,2010,第65页)。山林空间与诗人关系密切,是思维与记忆展开的重要场所,其包孕性使灰绿色成为饱蕴生机的色彩。
两类绿色空间,一个是诗人的精神故乡,一个是诗人生活得以具体展开的场所,都具有极强的容纳能力。绿色也因此具有孕育生命的象征意味。在绿色空间中,经常出现的花朵最为耀眼,它们镂刻在绿色背景上,显得格外生机勃勃。白色花朵尤受诗人关注,这些花朵的白不管是在绿色背景上零星闪烁还是浓烈泼染,都格外纯净无瑕。绿色的变化除了意味着这一空间的生命轮回,有时也意味着这一空间的被破坏或被遮蔽。
灰黑色空间也值得关注。除上文提到的特殊时刻的山林空间外,海洋空间也属于灰黑色空间。与这一空间相关的词汇有“海洋”“海底”“海浪”“海风”“海鸥”“海月”“海边”“沙岸”等。搜索“海”“海洋”,诗集中共出现30余次,和海洋相关的其他词汇的使用超过这一数据,“海洋”出现最多的是《时光九篇》,共13次。诗人常用这一空间来比拟情感世界。如“眷恋该如无边的海洋/一次有一次起伏的浪”(《七里香·新娘》,1979,第181页)、“为你走向那满溢着泪水与忧伤的海洋”(《时光九篇·苦果》,1984,第65页)、“我终将是那/悔恨的//海洋”(《时光九篇·真相》,1985,第23页)等。这些句子中,海洋的黑暗深邃是情感的深潜,海洋的起伏是情感的跌宕,这一物理空间成为诗人心理空间的具象化。
“诗歌描写一个静止的简单物体,也常有绘画无法比拟的效果。诗歌里渲染的颜色,烘托的光暗可能使画家感到彩色碟破产。”*钱钟书:《七缀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年版,第40页。诗人通过时空的多维建构,构筑了个人化的绿色世界与黑色世界,分别对应着诗人的远方、现实与内心世界。多维的色彩时空容纳了诗人的个体生命深度,也记录了诗人对族群和其他生灵生存状态的反思。与莫言“绿油油的血”(《木匠和狗》)那种对色彩的纯粹主观与抽象的使用不同,诗人所创造的个人化的色彩时空与现实世界精准对位,犹如印象派绘画对光影与色彩的极致追寻,每种色彩变化都有心理与现实的双重依据。
三、生命意义的感知调度
一位画家的描绘“之所以妙肖自然,主要是由颜色现象所引起的作用,这不是指颜色本身,而是指颜色的明暗之差和对象的显隐远近之差的幻变”*[德]黑格尔:《美学》第三卷(上),朱光潜译,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268页。。由颜色词、时空色彩形成的色彩基本面貌并不能呈现细部的意义,色彩的具体构成方式才是复杂意涵的具体彰显。从色彩之间的意义关系看,席慕蓉诗作中色彩的组构方式主要有三种:对比、映衬、递进。色彩的不同调度方式建构了生命的不同意义。
(一)色彩对比:生命的坚守与对抗
在色相环上,每一个颜色对面(180°对角)的颜色,称为“对比色”(互补色)。把对比色放在一起,会给人强烈的互斥感。在具体的色彩呈现过程中,两种可明显区分的色彩并置就能构成色彩的对比。这既是构成明显色彩效果的重要手段,也是赋予色彩以表现力的重要方式。新月诗派、七月诗派等都极为倚重这一色彩书写方式。席慕蓉在诗作中广泛运用色彩对比,除产生了醒目的如画效果外,还表达了丰富的矛盾性意涵。
席慕蓉的诗作中常出现彩色同黑白两种消色的对比,如“红”“绿”“黄”等。《无题》(1979)中的诗句,“就好像永不能燃起的/火种孤独地/凝望着黑暗的天空”(《七里香》,第125页),完成了“红”与“黑”在色相与面积两个维度上的对比。在巨大无垠的黑色天幕下,那颗不能燃起的小小红色火种,显得愈发无望。同一本诗集里的《孤星》(1979)中,诗人以金色与黑色作对比:“在天空里/有一颗孤独的星//黑夜里的旅人/总会频频回首/想象着 那是他初次的/初次的 爱恋。”(第73页)夜的黑令孤独的星的光芒愈发珍贵,因而凸显了生命中的爱恋之可贵。诗人在此也以色相与面积作双重对比。
较早期的诗歌中,诗人往往藉由对比,凸显小面积与亮色所内蕴的意涵的可贵性,表达对生命、爱恋的肯定与渴望,但1980年代中期发生明显变化。1983年的《迷航》(《时光九篇》,第52—53页)中,年轻岁月的生动与蓬勃,如月之光华,而现在,早已沉到永远黑暗的海底。洁白与黑暗的对比更多地凸显了海底的黑,凸显了对逝去岁月的一种悲叹,充满了凄怆之感。类似的色彩对比也出现在1986年的《沧桑之后》(《时光九篇》,第160—162页)中,“白”“绿”“黄”同时与“黑”的对比也营造出了相似的悲情氛围。《天使之歌》中,诗人通过天使之白翼与尘世之黑暗丛林的对比,写出了一曲梦与理想远逝的哀歌。而在2000年前后的诗作中,诗人通过色彩对比呈现出的是挣扎与抵抗。《诗成》(2000)中,诗人用“炽热的火炭投身于寒夜之湖”(《迷途诗册》,第23页),来象征对生命悲剧的全力抵抗,《四月栀子》(2000)用黑夜中一树白色栀子的盛放,来说明那些青葱岁月并不曾消逝,都是“我”现在的一部分(《迷途诗册》,第30—32页),这种对比让我们深深感受到岁月带来的悲喜交集:悲的是步履越走越蹒跚,喜的是内心越来越坚定。
《昨日》(2005)中,诗人用暮色与阳光的对比,表达了今日之“我”与过去之“我”的遭逢(《以诗之名》,第138—139页),暮色的灰黑并不能掩盖太阳的温暖与炫目,这种对比更多地呈现了诗人对今日之我的接受和对昨日之我的欣赏,二者的“把酒言欢”传达出的不再是激烈的对抗,而是面对岁月馈赐的坦然接受与和解。写于2015年的《山火》,更是通过“黑”与“红”的对比,写出了生命倔强的执着。无论肉体生命如何衰落,精神生命之韧性与力量如穿行于地底岩石中的地火,一直燃烧,永不灭绝。
有时作者并不仅仅对比两种色彩,而是用几种颜色同另外几种颜色来实现对比。《残缺的部分》(1984)中,“曾经那样丰润的青蓝与翠绿/都已转变成枯黄与赭红”(《时光九篇》,第38页),当初相遇时丛林的青蓝与苍翠,已经变得枯黄了,正如生命中的爱,也不可避免地要走向衰败与凋零。通过几种颜色与另外几种颜色的对比实现的象征,比通过两种色彩的单纯对比实现的象征显得更不容置疑,意义也更为丰富。
色彩的对比,呈现出诗人生命个体与外在世界之间存在的由对抗到和解的复杂关系史,色彩对比的丰富层次正是诗人生命的丰富层次。
(二)色彩映衬:生命的多维同构
色彩映衬其实也是色彩对比的一种。但这种对比关系与上述色彩对比关系不同,并非内在的矛盾冲突,而是色彩的相携相衬、相得益彰,如陈梦家《我望着你来》中“红”“绿”“白”“蓝”的互相映衬。色彩的互相映衬在席慕蓉的诗作中普遍存在。
诗人喜欢用绿色来映衬其他颜色,如暖色类的“红”“黄”,冷色类的“蓝”“紫”,消色类的“白”等。如“绿”映衬“白”:绿树白花(《七里香》,1979)、绿叶白花(《植物园》,1977;《诗中诗》,2001)、绿草白羊(《命运》,1966)、绿草白衣(《边缘光影》,1996;《六月的阳光》,2002);“绿”映衬“金”(《祖先的姓氏》,2007);“绿”映衬“红”(《鹿回头》,2001)等。诗人也喜欢用白色来映衬其他颜色,如白云绿衣(《青青的衣裾》,1980)等等。
诗人还喜欢把三种以上的颜色放在一起互相映衬,创造出极为炫目的效果。如《迷途》(2002):“谁又比谁更强悍与坚持呢//去极地寻索冰河的绿/来旷野见证夜幕的蓝/在边缘和歧路上辗转跋涉/还时时惊诧倾倒于/这世间所有难以描摹的颜色//是何等甘美又迟疑的刺痛 这心中/不断去去又复重返的轻微的悸动//是昨日在晨雾里漾开的暗丁香紫/以及此刻 在薄暮的旅程上/不断闪烁着的茶金秋褐与 锈红……”(《迷途诗册》,第56页)一首诗中出现了6个颜色词,加上晨雾带来的“灰”与薄暮的“灰黄”,共出现了8种颜色。其中,“灰”为环境色,“绿”“蓝”“暗丁香紫”“茶金”“秋褐”“锈红”几种颜色并置,既有冷色,又有暖色与中间色,色彩的缤纷正是因为人生旅途的缤纷,令人目眩神迷。
《色颜》(2001)则以颜色为题,“熏衣草紫与紫丁香蓝之间/其实只多了一层薄薄的雾气/威尼斯赭红与圣袍褐之间/少的却是那漂洗过后的沧桑//罂粟红 唇色近乎正朱/歌剧院红的胭脂偏粉/而我独爱那极暗的酒红/是一种不逾矩的挑逗和渴望//当然 还有阿拉伯蓝/那是比天蓝法国蓝还多了几分/向晚的华丽和忧伤//让我想起花剌子模悲愁的苏丹/最后举起的那一把佩刀/在里海的孤岛上 不战而败亡。”(《迷途诗册》,第64—65页)这首诗12种颜色间的意义关系并非一种。“薰衣草紫”与“紫丁香蓝”、“威尼斯赭红”与“圣袍褐”两类颜色分别并置,而两类颜色之间又由冷暖对比产生映衬。“罂粟红”“歌剧院红”并置,与“酒红”产生递进关系,“天蓝”“法国蓝”并置,与“阿拉伯蓝”产生递进关系,而“酒红”又与“阿拉伯蓝”冷暖对比,所传达的渴望与忧伤互相映衬。最后一段,则是“阿拉伯蓝”的忧伤扩大成一个古国的败亡,情感深度加强,意义走向递进。这12种颜色带来的不仅是视觉的盛宴,还有颜色所传达的多维度的生命质地。比起闻一多的相似诗作《色彩》,《色颜》的审美层次显然要复杂得多。多种色彩的相互映衬在《迷途诗册》中较常见,但很少能够达到《迷途》与《色颜》的色彩数量,在其他的诗集中就更少了。
从情感的角度来说,不同颜色会给诗歌带来不同情感,若一首诗中出现大量颜色,需要相应的情感强度、厚度与之匹配,否则会让人感觉浮夸与矫情。新月派(如闻一多)、初期象征诗派(如李金发)的一些诗作把色彩随意堆叠,颇受后人诟病。刘勰在《文心雕龙·物色》中就已指出:“至如雅咏棠华,或黄或白;骚述秋兰,绿叶紫茎;凡攡表五色,贵在时见,若青黄屡出,则繁而不珍。”*[南朝]刘勰:《文心雕龙》,范文澜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第694页。从席慕蓉的诗作来看,大量色彩的出现并无滥用之感,而是各有来处。在一首诗中出现大量色彩,需要技巧与内容的高难度配合,这不但要求诗人感性之饱满,更要求智性之高深,此二者缺一不可。席慕蓉对此有明确的自觉意识:“一个创作者其实需要有极强的理性来配合他的感性,也就是说,感性越强,理性也要更强,否则不可能创作。”*绍雍:《席慕蓉的写作奥秘》,《幼狮文艺》1986年总第387期,第22页。诗人对多种色彩的运用和掌控,无疑是极为谨慎与妥当的,体现了色彩与诗人内在生命丰富性的完美统一。
(三)色彩递进:生命的深度开拓
在席慕蓉的诗作中,色彩书写的另一种方式是在一首诗中运用同色系的不同色彩来形成递进关系,以此表达意义的递进。
1986年的《沙堡》(《时光九篇》,第154—155页),由黑暗的浪潮写起,到海边的沙堡结束,黑暗的浪潮与海边的沙堡分别象征不可回避的命运与生命中的珍贵所在,无论生命怎样汹涌激烈,不可回避的命运的黑暗浪潮终将来临、升高,消融生命的惨淡沙堡。这首诗在表层是“我”对“你”的倾诉,是一个独立个体对另一独立个体的表白;但在深层,“你”“我”一体,连缀成生命的残酷原貌,再巨大的欢喜终要消逝,生命的悲剧性无可避免。这首诗内容的丰富性依赖浪潮和沙堡的形状、性质、颜色来表达。其中黑色浪潮的“黑”随着浪潮的升高,面积由小变大,沙堡的“灰黄”逐渐被“黑”吞没,“黑”在体积上的渐次递进描摹了生命不可回避的悲剧命运,从而传达出普遍的形而上意味。
还有由浅到深、由淡到浓的色彩递进。如《忠告》(1986)中由“灰”到“黑”的递进:“每一个人 都只好/将自己化作动荡的海洋//不断上升 再/不断下降/每一寸的潮汐/是每一分每一秒无所适从的/汹涌和压抑//亲爱的朋友 当你读我/在阴霾的海面上/请不要只注意波浪缓缓的秩序/请再仔细揣想/那在极深极深的海底逐渐凝聚/一直不曾显露的/狂乱的忧伤。”(《时光九篇》,第164—165页)由海洋表面的阴霾到极深海底的“黑”递进,来表达诗人和缓的外在表象之下越往里越激烈的内心世界。《菖蒲花》(1985)中,诗人以菖蒲花从“纯白”到“蓝紫”来说明生命的努力绽放。“白”为消色,而“蓝紫”混合了蓝色与红色、冷色与暖色。菖蒲花由“纯白”到“蓝紫”努力绽放,人生亦应如是。
色彩的递进意味着意义的递进,通过色彩的递进,诗人有效地建构起了生命的深度,从而建构起了色彩的意义深度。这类色彩书写方式也是较为少见的。
(四)单色覆盖:生命的强度展现
有时诗人在一首诗中只涂抹一种色彩,单一的色彩便笼罩全篇,缺少了其他颜色的竞争,单色所蕴含的意义就显得极为霸道。
其中极为醒目的是白色、黑色、灰色的运用。在《南与北》(2003)中,白色成为全诗的意义核心,南方和北方,“她”和“他”,因为白色而心灵相接,“她说:/柚子树开花了 小朵的白花/那强烈的芳香却紧抓住人不放/在山路上一直跟着我/跟着我转弯/跟着我 走得好远。//他说:/我从来没闻过柚子花香/我们这里雪才刚停。//然后 谈话就停顿了下来/有些羞惭与不安开始侵入线路/他们都明白此刻是乱世/忧患从天边直逼到眼前/只是柚子花浑然不知/雪不知 春日也不知。”(《我折叠着我的爱》,第26—27页)白色作为南与北的共同语言,象征生活与生命中无法抹去的美丽,是全诗的意义核心。《生命之歌》(1997)一开始,诗人就说,“如今 必须是在夜里/当黑暗占据了最大的位置”(《边缘光影》,第196页),随着夜的到来,黑色出场,接连出现“黑暗”“黑夜”“黑暗”。时光已把生命吸进黑洞,不论如何努力都无法挽回,一连串的“黑”象征了岁月的湮灭与诗人深渊一样的悲伤。类似用法还出现在《寂静的时刻》(2009)等诗作中,但总体上数量较少。单色所象征的意涵如同一张巨网,强而有力地覆盖了读者,郭沫若就善用单色表达强烈情感。如果诗人的心灵并未达到如此强度,这种用法就会显得虚浮。席慕蓉较少使用这一方式,说明了她用色的慎重。
色彩的对比、映衬与递进,以及单色的高强度使用,是诗人的主要色彩调度方式。在深浅明暗与斑斓琳琅中,情与思、笑与痛、个体与社会,都交迭灌注在诗句里,实现了色彩的最终表达,色彩的印象派艺术得以最终实现。这种表达内在情思饱满深邃,外在表征复杂细腻,令席慕蓉的诗作有了难以言传的艺术魅力。
四、结语
通过复杂的色彩时空建构与色彩调度,席慕蓉极为严谨地从现实生活中选取光影环境,并以复杂色彩的匹配与绵延来表达生命的多重意义,其美学特征含蓄内敛、沉潜深挚,对色彩光影的极致追求不亚于西方印象派绘画,这在中国文学中极为罕见。同时具有诗人与画家身份的古代诗人王维、徐渭等忠实于中国画传统对色彩的理解,遵循五方正色系统,推崇墨色的黑白相生。受西方现代绘画影响,中国现当代文学中的色彩语言日趋自由,艾青、李金发、张爱玲、铁凝、莫言、海男等的色彩书写表现出与传统的巨大差异。他们或者善用带有强烈色彩的意象,或者将色彩进行主观化、抽象化处理,鲜有人的色彩书写能做到既与现实精准对位,又能与主体多重的情感与思考精准对位。席慕蓉将色彩上升为本体性的书写方式,使色彩书写成为其诗学的核心要素,达到了表现与再现的巧妙平衡,不夸张、不虚浮,呈现出一种高贵的单纯之美。色彩书写的复杂源于内心的丰赡,更得益于诗人所受的西方绘画的专业色彩训练,这种特殊专业背景使得诗人的色彩调度达到了令人惊叹的情感强度、意义深度与艺术高度,成为精神展开与诗意建构的主要方式,完善了中国文学中的印象派绘画式的色彩书写模式,完成了自身诗学的一次深度垦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