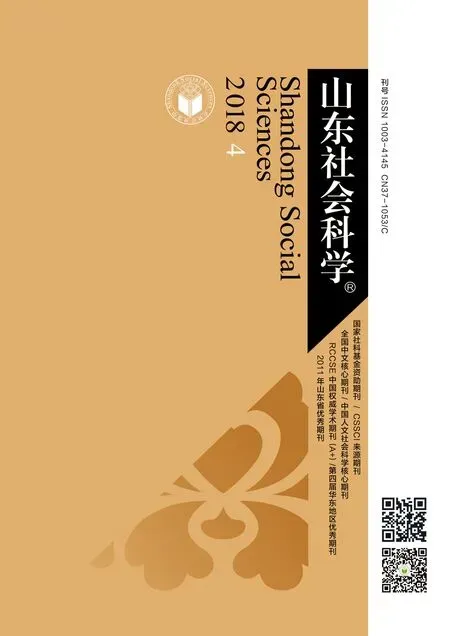列维纳斯的身体思想及其身体美学意义
2018-01-29王嘉军
王嘉军
(华东师范大学 中文系,上海 200062)
法国哲学家列维纳斯(Emmanuel Levinas,1906—1995)的“伦理学作为第一哲学”“伦理学优先于存在论”等提法已经广为人所知,并受到了诸多关注。然而,研究者们往往忽视了“身体”在这一“伦理学”超越“存在论”的浩大工程中的重要作用。我们可以说,如果不把视角转向身体,列维纳斯的哲学计划是无法完成的。因为,在列维纳斯那里,伦理学或哲学对于“重智主义”的超越必须依托于一种溢出于认知之外的感性(sensibility),而这一感性只能落实于身体。故此,列维纳斯对于身体给予了极度的重视,列维纳斯式的伦理主体首先就是一具具身化的身体,是易受他人感染和打动的肉体,而非基于认知、思考、谋划而决断的理性主体。在这个意义上,列维纳斯理应在当代身体思想的研究谱系中占据一席之地。迥异于许多基于存在论对于身体的研究,列维纳斯对于身体蕴含的伦理维度的分析、对于他者的身体的重视,都还未引起足够的关注。对于这一特殊路径的研究,很可能会拓展身体思想的疆域。本文将围绕列维纳斯不同时期的论述,对其身体思想的发展脉络进行简要的梳理,并试图找出其与当代身体美学和中国修身思想共通和互补的可能性。
一、身体作为安置
“身体”问题一直为列维纳斯所重视,而且他一直将其与哲学、政治和现实相关联。在1934年发表的《反思希特勒主义哲学》一文中,希特勒刚上台伊始,列维纳斯就先知般地预感到了希特勒和法西斯主义在其后会掀起的灾难,并对其进行了深入的批判。在这篇被阿甘本称为“也许是20世纪哲学里唯一的成功尝试”*[意]乔吉奥·阿甘本:《潜能》,王立秋、严和来等译,漓江出版社2014年版,第342页。的文章中,列维纳斯指出了法西斯之恶与西方哲学的关联,他强调:“国家社会主义鲜血淋漓的野蛮主义的源头”不是一种临时的疯狂或意识形态失常,而是“一种根本之恶的本质可能性,在其中,我们可以为逻辑所引导,但是如果与它相悖的话,西方哲学就很难充分地确保自身”。*Emmanuel Levinas, “Reflections on the Philosophy of Hitlerism”, trans. S. Hand, in Critical Inquiry. Vol. 17, No. 1. (Autumn, 1990), p.63.这篇文章最有新意的地方在于列维纳斯从身体的角度研究了这种希特勒主义和法西斯主义,他认为西方哲学中的身心二元主义在与一种权力意志结合后,会认同“对于鲜血的神秘的迫切要求,对于一种遗传和过去的召唤,身体作为一种迷一般的机械而服务于它”*Emmanuel Levinas, “Reflections on the Philosophy of Hitlerism”, trans. S. Hand, in Critical Inquiry. Vol. 17, No. 1. (Autumn, 1990), p.69.。
反之,在后来的《从存在到存在者》等作品中,列维纳斯则指出,身体构成了我们存在的基础,我们需要注意到的是我们对于身体的这种原初的依附,而不是将其当作一种精神之纯化的障碍。对于列维纳斯来说,身体,不只为意识提供了落脚的场所、基础,它还是人类介入存在的方式本身,是这一介入的事件本身,因为正是通过身体,通过身体的安置(position)这一事件,我们与世界的关系才渐次展开。所以,列维纳斯说,身体就是“人类介入存在(existence)、安置自身的方式。将它作为事件来把握,就是说它不是安置的工具、象征或症候,而是安置本身;就在身体上,完成了从事件转化为存在者的脱胎换骨的过程”*[法] 列维纳斯:《从存在到存在者》,吴蕙仪译,王恒校,江苏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原译文对于position(安置)的翻译是“位置”。。
他进而指出,身体并不是传达精神性和内在性的外在媒介,身体本身“通过它的安置,完成了全部内在性的条件。它并不表达一个事件,它本身即是这个事件”*[法] 列维纳斯:《从存在到存在者》,吴蕙仪译,王恒校,江苏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87页。。在这一点上,列维纳斯说他受罗丹雕塑的启发颇多,因为罗丹之雕塑的生命力和感染力并不仅来自于人物所要传达的灵魂或思想,更来自于它们的基座与安置之间的关系。*[法] 列维纳斯:《从存在到存在者》,吴蕙仪译,王恒校,江苏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87页。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安置”就是主体得以在实存中立足的第一个事件,而这一事件首先基于的是身体,而非意识。在《总体与无限》中,列维纳斯说得更加明确,“身体的本质就是实现我在大地上的安置。”*[法] 列维纳斯:《总体与无限》,朱刚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108页。至于安置的方式则可能基于主体在《从存在到存在者》中所说的“努力”,也可能基于《总体与无限》中所暗示的享受或劳动。
二、给予他者以身体
“身体”这一议题在列维纳斯的思想中一直有延续,无论是在《从存在到存在者》中对于“疲惫”“失眠”等身体状态和生存状态的分析,还是在《总体与无限》中对于面容的描述和对生存之为享受的强调,以及《别样于存在或越出本质》(以下简称《别样于存在》)中对于亲近和受难等的阐发,都强调了身体作为一种建构伦理主体之基础的重要性。这种对于身体的强调使得他者和他人的来临作为一种溢出认知之外的感性事件而发生,从而使列维纳斯得以建构一种超越传统哲学乃至伦理学之重智倾向的伦理学。如奥克萨拉(Johanna Oksala)所说,列维纳斯之“伦理主体性的极端被动性只有通过具身化才是可能的。伦理的主体在本质上就是一个具身的、肉身的主体,这是一个会被伤害和羞辱的主体。只有在这种身体的易受伤性中,才能升腾起一种为他者的责任,一种在面对超负荷的痛苦和快乐时的被动性”*Johanna Oksala, Foucault on Freedo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5, p.203. 其实列维纳斯的这一思想也可追溯至希伯来遗产,如阿维夏伊·玛格利特所指出,“正是身体上的接近使新约全书把圣经希伯来格言中的‘Re’s’一词翻译成‘邻人’,而不是希伯来词语中一些词语所具有的含义,如朋友、伙伴或同事等。”(参见阿维夏伊·玛格利特:《记忆的伦理》, 贺海仁译,清华大学出版2015年版,第36页。)“邻人”是列维纳斯相当喜欢使用的一个词语,而如上所述,“邻人”一词在圣经中的要义在于其身体的邻近,这一身体为“我”带来了伦理责任,因为邻人可能是受伤之人或易受伤之人。。对于伦理主体的这种易受伤性、敏感性或脆弱性的强调,是列维纳斯后期思想,也即在《别样于存在》这本其集大成之作中对伦理主体进行建构的重点,而这一切都需要落脚于身体。
在《别样于存在》之前,以《从存在到存在者》到《总体与无限》为两个结点,我们可以将列维纳斯对身体的关注也分为两个步骤。在《从存在到存在者》等著作中,列维纳斯主要考察的是身体对于主体生存于世的存在论意义,也即我们前面说的“安置”;在《总体与无限》之中,列维纳斯的考察则指向两个方向,其一承接的是《从存在到存在者》的论述,列维纳斯继续考察身体之于人的存在论意义,并将其从“安置”拓展到了“享受”和“劳动”等范畴;其二,尽管比较隐晦,但列维纳斯其时更关注的其实则是他者的身体对于主体的“神显”,也即对于主体的伦理启示,或曰伦理刺激,这一刺激将向主体颁布伦理命令。这一他者身体之突出代表是“面容”,然而实际上,他人身体的每个部位都可以成为面容,只要它对于主体具有伦理效力。
如果说《总体与无限》更关注的是他者之身体,那么到了《别样于存在》中,列维纳斯又把对于身体考察的落脚点转回了主体。只不过,与之前对于身体之存在论功能的分析不同,这个时候,列维纳斯更为着重分析的是身体的伦理学功能。更准确地说,列维纳斯此时着重分析的是身体如何可以促使主体成为伦理主体,而不仅仅是一个中性的存在论主体。这一分析的关键是“感性”(sensibility)这一概念。在某种意义上,我们可以说身体与感性这两个概念在列维纳斯笔下经常具有相同的含义。其实,这一点在《总体与无限》中即已经初现端倪:
身体、安置(Position)、置身行为―与我自身的第一性关系的样式,我之与我自己相一致的样式―它们与观念论的表象毫不相像。我是我自身,我在这里,我在家,我是居住,我是在世界中的内在。我的感性就是这里。在我的安置中,并没有对于定位的感受,有的是对我的感性的定位。安置,绝对不带超越,与凭借海德格尔式的Da(此)所进行的对于世界的理解毫无共同之处。不是对存在的操心,不是与存在者的关系,甚至也不是对世界的否定,而是世界在享受中的可通达性。感性,生命的局限本身,未经反思的自我的素朴性,超逾本能,而又未及理性。*[法] 列维纳斯:《总体与无限》,朱刚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119页。
在这段话中,我们可以看到列维纳斯继续将身体与安置相等同,但与此同时,列维纳斯也将身体与感性相等同,因为在这里,“感性”与海德格尔式的此在对于存在的“理解”相对立,它所代表的是一种与世界和元素的原初关系、一种不依附于理解的关系,是对于世界和元素的“享受”。这种“享受”是直接的、即时的,不需要任何理性或认知的反思和建构,而这就是“感性”,感性本来就是身体最直接的反应,甚至可以说感性就等同于身体,理解则时常被视为对于感性和身体的超越。因此,在这个意义上,身体也不仅仅是在世界中的安置,还是在世界中之享受。这种身体的感性素朴自然,不简单地等同于动物性的盲目“本能”,因为在“享受”中人们可以更好地安置和通达世界;但它也还未达到“理性”的境界,更未达到伦理的境界。
然而,到了《别样于存在》中,依托于同一个“感性”概念,列维纳斯却开始用其来建构伦理主体。正如,《别样于存在》一书的英译者阿方索·林吉斯(Alphonso Lingis)所说:“他异性不是通过悟性或理解性的主动性而给予的,而是通过感性。在涉及他异性的路径时,人是被动的,他承受它的影响,却不能同化它,他向它敞开,向它的方位、感觉暴露,易感于(susceptible)被感动(affected),被提升或被施痛。这些概念定位了在感性中的他异性的影响,但这种感性不再能被理解为一种综合或双重事件的接受性的一面,这种接受性只有在已经被可理解地把捉之后才是可接受的。 ”*Alphonso Lingis, “Translator’s introduction”, in Emmanuel Levinas, Otherwise than Being or Beyond Essence, Pittsburgh: Duquesne University press, 1998, pp. xxiii-xxiv.尽管关注点已不再相同,但是与《总体与无限》相似的是,这一感性同样需要落实于身体。在《别样于存在》中,列维纳斯首先将这种感性视为一种向他者的暴露,“主体性是感性——一种向诸他者的暴露,一种在与诸他者亲近中的脆弱性和责任,为-他者-之-一己,也就是,表示(signification)……”*Emmanuel Lévinas, Autrement qu’être ou au-delà de l’essence, The Hague: Martinus Nijoff Publishers, 1978, p. 124.这种暴露和表示不只是语言上的“言说”,更是身体上的“言说”,彻底地向他者袒露自身、表白自身、给予自身,这种暴露是要揭开自己,是让自己“皮肤剥露,切肤并切及神经”*Emmanuel Lévinas, Autrement qu’être ou au-delà de l’essence, The Hague: Martinus Nijoff Publishers, 1978, p. 31.,让自己受难,对于列维纳斯而言,这才是真正的表示、真正的意义。如同他引用过的女哲学家薇依所说:“天父啊[……]快剥去我这一躯体和这一灵魂[……]把它变成你的东西,让我的身上永远只留下这一剥夺本身”*[法] 勒维纳斯:《上帝·死亡和时间》,余中先译,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189页。。
故此,列维纳斯说,感性即易受伤性或脆弱性本身,因为主体无处逃避,没有庇护,它把自身完全暴露在他者面前,为了暴露得彻底,他甚至还暴露这一暴露本身,因此他极为脆弱,同时也极为敏感,正因如此,他才能够感受到他者,为他者献身甚至受难,从而成为伦理的主体。“感性即是向他者的暴露。……无法在任何状态的持续或同一性中找到庇护。……在没有任何退缩余地的已经给出中,就好像感性正是所有庇护或所有庇护的缺席所预设的:脆弱性本身。”*Emmanuel Lévinas, Autrement qu’être ou au-delà de l’essence, The Hague: Martinus Nijoff Publishers, 1978,p. 120.对于这种感性和易受伤性,列维纳斯以极为直接的身体状态进行了描述:“它是一种在绷紧的痛苦中的绞动,是在这边(或译“未及”,l'en-deçà)*“en-deçà”与列维纳斯的另一个重要概念“au-delà”(可译为超越、越出或超逾)相对,所指的是在此世或在存在论层面“未及”“外部”的“这边”。因此,他者的来临,或为他者所搅扰的身体痛苦,是在“这边”所意想不到的。的意想不到的维度。它是被从自身撕裂,是比无更少,一种在虚无背后的否定中的拒绝;它是一种母性,在同一中的他者的妊娠。被迫害者的不得安宁不是一种母性的变异吗?不是一种“母腹的呻吟”因为它将要孕育或已经生产的东西所引起的变异吗?在母性中表示的是为众他者的责任,直至为他者替代,直至迫害效果所导致的受难,直至迫害者所沉浸的迫害过程本身所导致的受难。母性,孕育着卓越,它甚至孕育了为迫害者的迫害所担负的责任。”*Emmanuel Lévinas, Autrement qu’être ou au-delà de l’essence, The Hague: Martinus Nijoff Publishers, 1978, p. 121. 列维纳斯最后的论断非常大胆,也颇具争议,受迫害者需为迫害者负责,直到今天,这仍是一种非常难令人接受的思想。
在从《从存在到存在者》《时间与他者》到《总体与无限》等作品中,父性和父子关系都是列维纳斯阐述伦理和时间非常倚重的范畴,然而,在《别样于存在》中父性却在某种程度上被淡化了,继之而起的是“母性”。在列维纳斯的阐述中,“母性、脆弱性、责任性、亲近、交流-感性”这几个概念似乎可以互换,而它们导向的是“触摸,触诊(palpation),向……敞开……的意识,导向纯粹认知从‘完好无损的存在’中获得图像,使自身了解诸物之可触知的实质”*Emmanuel Lévinas, Autrement qu’être ou au-delà de l’essence, The Hague: Martinus Nijoff Publishers, 1978, p. 122.。简而言之,它们都导向的是向他者的敞开,与他者的亲近,而这种亲近首先是身体上的,而非空间上的,是触摸、触诊。
故此,列维纳斯说,“身体的感性经验就此而言就是肉身化。感性-母性,脆弱性,感知——将肉身化的节点绑进了一个剧情之中,这一剧情比自我感知更博大。在这一剧情中,我们在被系于我的身体之前,就被他者所束缚(着重号为笔者所加)。……感性的直觉,已经是一种感知和困扰的模式,被所感纠缠……感性的经验作为一种为他人所困扰,或母性,已经是一种肉身性(corporéité )……”*Emmanuel Lévinas, Autrement qu’être ou au-delà de l’essence, The Hague: Martinus Nijoff Publishers, 1978, p. 123.在这段话中,最值得注意的地方是,与此前将身体当作安置不同,在《别样于存在》中,身体已经不再是主体的安置,安置也不是一个存在论的优先事件;相反,列维纳斯指出,主体在被系于身体之前,或者说安置之前,就已经被他者所束缚、所质询、所困扰……而这种被他者所束缚、困扰和质询又正好在身体和感性中呈现。它的呈现方式就是上文中所说的绞痛和妊娠,生育的疼痛意味的是一种自我的撕裂,这种撕裂并不是同一自我的精神分裂,而是意味着他者的诞生,他者在同一中的诞生,生育的痛苦就是为孩子——为他者所受难,这种受难以生育的强度让主体感受到。生育的身体无法安置,无法系于自身,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也可以说它是“一种肉身化,一种没有回归的放弃”*Emmanuel Lévinas, Autrement qu’être ou au-delà de l’essence, The Hague: Martinus Nijoff Publishers, 1978, p. 127.。换句话说,主体的肉身化,正是由他者而非自我所塑造的,塑造的方式并非“安置”,而是剥露、剥离和撕裂。这一肉身化的主体承受着阵阵疼痛,这疼痛来自于:他者的来临,他者的亲近,他者的困扰。故此,这一“为了他者的自我”或“母性,就是一个为他者受难的身体,作为被动性和弃己的身体,一种纯粹的忍受。这确实是一种无法超越的暧昧性:肉身化的自我,血和肉的自我……”*Emmanuel Lévinas, Autrement qu’être ou au-delà de l’essence, The Hague: Martinus Nijoff Publishers, 1978, p. 127.
这一时刻承受着疼痛、易受伤害的“血和肉的主体”,不同于理性的主体,不同于自我确认、自我回归的主体,不同于理性算计的主体,这是一个不断为了他者而放弃自身的主体。列维纳斯形象地指出,这一主体就像一个饥饿难耐并且正在进食的人,从嘴里拉出自己的面包而给予他人,这种给予是如此彻底,他需要不断地裸露自身、放弃自身、给予自身的一切,甚至给予自己的皮肤。*Emmanuel Lévinas, Autrement qu’être ou au-delà de l’essence, The Hague: Martinus Nijoff Publishers, 1978, p. 124.在这里,列维纳斯再次破除了在物质和精神、身体和灵魂之间的二分,他指出,对于一个饥饿的人来说,给予面包也就意味着给予灵魂,同样,给予他人面包,也就意味着把自己的身体给予他人,用自己羸弱的身体去抵偿他人的身体、他人的生命。因此,在这里给予身体,也即给予灵魂。——“通过将自己口中的面包给予他者,而为了他者从自身中拨出的存在,意味着能够为了他者而给予自身灵魂的能力(原文中几乎每个词语都用分隔号‘-’连接——笔者注)。通过灵魂而对身体的激发,只有通过在主体性中的为-他者-之-一己才能被阐释清楚。”*Emmanuel Lévinas, Autrement qu’être ou au-delà de l’essence, The Hague: Martinus Nijoff Publishers, 1978, p. 126.
三、列维纳斯、身体美学和中国思想
列维纳斯的身体观别具一格,首先是他的晚期思想集中从伦理的角度来讨论身体,这与许多从政治学或美学等角度来谈论身体的当代思想家都有着极大的不同;其次,他非常看重他者(主要指的是他人)对于主体之身体的影响,这种影响是如此巨大和痛切,以致列维纳斯有时候用“创伤”来对其进行形容。这两点都可以形成对现有之身体美学框架的巨大补充。舒斯特曼指出,其所启用的“身体美学”(somaesthetics)这一概念在中文中最恰当的翻译实应为“身体感性学”*[美]舒斯特曼:《身体意识与身体美学》“中译本序”, 程相占译, 商务印书馆 2011年版,第3-4页。,身体美学并不能被仅仅局限为一种美丽之学。通过“感性学”这一连接,其还应该被扩展到政治学和伦理学等诸多领域。而列维纳斯的身体论述,尤其强调的就是其中的“感性”维度,就此而言,它天然就应该归属于“身体美学”。当然,这里的“身体美学”是在一个更开阔的视野上说的,而不唯舒斯特曼所正在建构的“身体美学”。尽管舒斯特曼启用了“身体美学”(somaesthetics)这一概念,并主要从实用主义路径切入了这一研究,但“身体美学”的源流其实不止一支,“身体美学”作为一个正在发展的学科,也应当吸收和融合不同路径的身体之思。
列维纳斯这种特殊的“身体美学”对于现有的身体美学框架最大的挑战或补足,应当在于把研究的视角从关注自我或主体的身体训练转向通过身体对于他者之身体的感受。这种对于他者之身体的感受力具有强大的伦理力量,因为对于他者之生命或苦难的漠视往往来自于对他者之身体的漠视,其次才是对他者之灵魂的漠视。更何况在前面的论述中,我们已经可以看到,列维纳斯实际上把身体和灵魂等同了起来。感受他者的身体往往就意味着感受人本身,感受人性本身。身体是人性最直观的显现,一个无法感受他者之身体的人,也往往可能是没有人性的人。对于他者之身体的感受必须落实于自我的身体上,否则这种感受就只是一种普遍性的认知而已,它并不能真正体察他者、亲近他者、感觉他者。在这个意义上,列维纳斯的伦理主体的塑造也依赖于对于这一主体的身体塑造,而塑造的方向即是以列维纳斯所阐释的感性的方式来感受他者。
遗憾的是,由于列维纳斯在一个极为抽象的高度来谈论身体,且他对于身体的论述往往会走向某种隐喻式的使用,这使得他的身体感性学似乎仅仅停留为一种高渺的理论预设。在列维纳斯那里,主体的身体以一种猝不及防、撕裂自我的方式来遭遇他者和感受他者,这里面有一种崇高的力量,而崇高的发生往往是不可预知的,它具有一种“事件”般爆发的力量。似乎自我的身体先天的、天然的就会被他者所打动、所感发,这里有一种极端的被动性,身体似乎瞬间就被他者所感染、所制约,而非一点点地被他者所打动。在这个意义上,“身体”对于他人的感受并不是经由训练而来的,而是先天就会被他者所裹挟和影响。然而,回归现实,我们却不得不承认,通过身体对于他者身体的这种伦理感受并不是先天就具有的,事实上,对于他者身体的感受本身镌刻在主体与他者的社会交往中,而这种社会交往首先不基于理性的商谈,而是基于感性的接触——眼神交流、握手、拥抱、接吻、触摸,哪怕对于社会交往最主要的媒介——语言,列维纳斯也认为应当首先将其还原为一种基本的身体交流,而非理性交谈。只有这样,语言才是感性的,也才是伦理的。这也就是说,对于他者的身体的感受恰恰也是在我们与他人的身体接触和或交往中被实现和增进的,而不仅仅是一种伦理本能。故此,我们可以合理地推断,对于他者身体的感受也可以在日常的修炼中被培养和增强。
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认为列维纳斯的身体思想可以和以福柯和舒斯特曼等人为代表的当代身体思想形成某种互补。身体是福柯生存美学的重要基础,生存美学中的自我治理首先是一种对身体的治理。在其中,无论是快感的享用还是欲望的节制,直接指向的都是身体。因此,可以说,生存美学也是一种身体美学,而这种身体美学同样是一种身体伦理学。因为生存美学对于福柯而言,即是一种伦理学。骆颖佳(Lok Wing-Kai)指出,福柯晚期哲学中的主体首先是身体,这种具身化的主体(Embodied Subject)就是一个伦理主体,它不只可以关注自身,也可以关怀他者。在福柯晚期的著作《性史二》和《主体解释学》等作品中,受到古希腊“关注自我”概念的启发,福柯也将身体的修炼作为一种塑造伦理主体的方式。能控制自身身体的人,才能够过上一种真正自我关注和伦理的生活,才能够自如地运用自身的自由,而不会导致向他人滥用权力。*Lok Wing-Kai, Foucault, Levinas and the Ethical Embodied Subject, Ph.D. dissertation by the Institute for Christian Studies, Toronto and the VU University Amsterdampp, 2011, pp.26-28.
我们认为,福柯是当之无愧的身体美学的先驱,他已经深刻触及了身体训练与感性和伦理的关系。“身体美学”这一概念的提出者舒斯特曼则以一种更为实用主义的视角,并结合东方(例如中国和印度等)传统中的身体修习与美德训练传统对于这一脉络进行了建设性的拓展。这种拓展体现在:其一,他以一种实用主义的视角,将身体美学建构成了一种哲学论述与身体训练实践结合的综合哲学,从而复归了法国哲学家阿多所说的“哲学作为生活方式”的传统。这种“身体美学既与古典修身功夫同源同构,又有其超越性,即它不是一种内在性的对意识活动的反思,而是一种在实践活动中获得的拓展了身体经验的至善论”*王辉:《论身体美学对西方古典工夫论的现代复兴及其启示———阿多、福柯和舒斯特曼之修身实践的谱系学考察》,《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6期。。
其二,通过大量参考东方哲学,尤其是中国哲学,舒斯特曼将身体美学建构成了一种追求“中道”的理论哲学和实践美学,从而有助于克服西方身体美学论述中的某些极端倾向。比如福柯,舒斯特曼既欣赏他在身体观上的身体力行,同时又批判了他对于身体快感的极端追求,而这种对快感的极端追求很可能“最终将只能钝化我们的敏感性,只能减弱我们的愉悦”*[美] 理查德·舒斯特曼:《身体意识与身体美学》,程相占译,商务印书馆2011年版,第75页。。福柯对于这种身体快感的极端性看法,实际上是根植于西方传统文化价值观的,故此,舒斯特曼说道:“这里我们再一次发现,福柯的性自虐实践非常值得我们认真而严谨的批判。它并没有叛逆地逸出我们传统文化的价值观;相反,它强有力地表达了许多深层的、非常成问题的趋向。这些趋向在历史上将其产生的那些价值和实践包含在自身之内,甚至包含在我们的精神与宗教体验中。”*[美] 理查德·舒斯特曼:《身体意识与身体美学》,程相占译,商务印书馆2011年版,第71页。正因如此,舒斯特曼才试图从追求“中道”和“平淡”的中国思想中寻求建构身体美学的启示,来平衡和中和西方文化传统中对于身体的极端态度——无论其是追求快感,还是压抑快感。
承接这个论断,我们可以说,列维纳斯强调主体身体对于他者的绝对暴露、绝对敞开、绝对献身,以及在为他者承担伦理责任时的极度受难,也暗含了西方的精神和宗教体验,尤其是犹太-基督教的苦修和牺牲等传统。其论述虽然充满了伦理上的崇高感和宗教上的神圣气息,但同时也不免极端化,并且很难真正落实到日常的身体修习中。在这个意义上,中国思想理当与其形成某种互补。中国思想有着源远流长的“修身”传统,这一“修身”既是修“身”,也是修“生”,它本身就既是身体修炼,也是美德培养。如张再林先生所说:
对于古人来说,正如其古汉语所示,“身”字与“生”字异名同谓,“生”被视为是“身”的代称。又古人所谓的“生”乃为“天人合一”之“生”:“尽人道者,动以顺生之几”《无妄》,意即“生”就天而言为“生”,就人而言为“行”。故古汉语中“身”字即“躬”字,而后者同时兼有“亲身”和“躬行”二义。这样,古人的“身”、“行”合一,“身体”即为“力行”之旨由此就揭橥而出。而身体作为道德的载体又意味着身体行为与道德行为须臾不可分离。*张再林: 《中国古代伦理学的身体性》,《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5期。
众所周知,伦理学是中国哲学中的显学,而这一伦理学如上所述又需“躬行”于世,因此,我们也可以说中国哲学就是一种生活方式,它必须落实于“身体力行”。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中国伦理学和哲学也是一种身体哲学,其对于“文质彬彬”“君子之容”等“美形”和“美德”的追求,又使其更显明地具有某种身体“美学”的内涵。从这里出发,我们可以进一步发现中国哲学与福柯、阿多笔下的古希腊哲学及当代身体美学的关联。在它们那里,哲学、伦理学、生活、身体的修炼和美可以较为适洽地融合为一体。对于列维纳斯的哲学而言,这种圆融正可以为其阐述的身体和伦理与日常生活实践的隔离带来弥合的契机。
而反过来说,列维纳斯强调极端他性的伦理学,及其对于通过身体伦理地感受他者的重视,也可以为当代身体美学和中国思想形成有效补充。后二者都更强调的是对于主体自身身体的训练以及美德涵养在此基础上的养成和提高,却忽视了通过身体对于他者的伦理感受同样在美德和伦理塑造中具有重要的地位,甚至更为重要。在中国哲学传统中,对于他者身体的感受往往是从自身身体的感受中外扩出去的,“正如在宇宙论里古人经由该还原坚持‘即身而道在’,即对天道的尊崇首先就寄寓在之于人自身身体的尊崇中一样,在伦理学中古人亦经由该还原强调‘敬身为大’《礼记·哀公问》,即对他人的礼敬首先就植基于之于人自身身体的礼敬之中。”*张再林: 《中国古代伦理学的身体性》,《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5期。“古人伦理学里的身体亦是一经由‘以生训身’的人我合一的身体,天下众生被视为我身体生命的扩充和延伸。惟其如此,我们才能理解何以《论语》谓‘四海之内皆兄弟也……一旦他人被视为我身体生命的体现,那么这就同时意味着为他的社会伦理则必然被视为我自身身体生命的发用。”*张再林: 《中国古代伦理学的身体性》,《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5期。
尽管是一家之言,但以上的概括确实触及了中国传统伦理学与身体关系的某些重要面向。显然,这里有一种自我主义,而这种自我主义又落实于“身体”:主体首先需要敬重自身的身体,再对他人或他者“感同身受”,通过一种共情或感发,把天下众生、宇宙万物连接为一具共通的身体。我们不会把这种自我主义通过比较列维纳斯尊重极端他性的哲学而贬之为一种“自我中心主义”,这种落实于主体修身,将自身建构为道德主体,并“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的诉求是一个指引性的目标,它对于那些致力于成为“君子”的人无疑具有巨大的引领作用。不过,相对而言,其却忽视了与他人或他者相遇所会带给主体的直观的、感性的震颤,这种震颤本身就在塑造着主体的身体。从列维纳斯的身体思想中我们可以得到启示:主体并不是先“有”一个孤绝的身体,再将这个身体延伸到外界,延伸到他者;相反,主体的身体正是在与他者的相遇和碰撞中形成的。这里说的当然不是生理上的身体,而是指身体的感受力,除了自然性的生理反映,身体的感受力显然主要是在与他者尤其是他人的交往中生成的,否则人就与草木无异。所以,对于伦理主体的身体塑造必然不可能绕开他者,不可能先“独善其身”,把“身”修炼好之后,再去关怀他者;相反,这一“修身”的过程本身就需要他者的介入。归根结底,在伦理学中,他者对于自我具有某种优先性,伦理主体的塑造永远不可能在遭遇他者前就完全完成,只有当他者来临时,这一伦理主体才能得到真正的塑造。他者不仅仅是“独善其身”后的自我如涟漪般“外扩”的对象;相反,他者是投入水中的那颗石头,是它的突然介入才使自我形成了涟漪。而且,对于列维纳斯而言,他者还不应当只是一个另外的自我、一个由自我推论出来的类同于“我”者,他者更应当是“我”所不是者。他者之所以是他者就是由于其不可以被自我所完全把握和感受,就像在伦理情感中,他者的疼痛永远不可能被主体真正感受到,因为主体终究不是他者,尽管主体可以通过共情、“恻隐”来根据主体已有的身体感受揣度和体验他者的感受,但终究不能完全把握他者的感受,因此主体的“身体”再如何扩展也无法完全包容他者。也就是说,他者的疼痛会永远溢出主体的身体之外、感受范围之外,他者的疼通不依附于主体的疼痛,他者的身体也不依附于主体的身体。所以,他者的身体,并不仅仅是主体身体的延伸。按照列维纳斯的思路,他会推论说这就说明:他者的疼痛不止异于,还大于和超乎于主体的疼痛,正是因此,我们才需要对他者抱有无限的责任、敬畏甚至负罪感,而这种伦理情感将直接在身体上显现。从这个角度说,“敬身为大”在伦理中所敬之身,首先应当是他者之身,而非自我之身。
因此,从一种伦理视角出发,身体美学如欲超出狭义的“美”或“美丽”的限制之外,就必需引入他者的身体。至于如何通过具体的日常身体训练来提高伦理感受他者的能力,如何建构一套这种系统的身体美学训练,则不是本文可以解决的问题。但可以确定的一点是,这样的训练需要他人的配合和共同修炼,甚至需要某种团队式的协作,这种训练应该本身就是一种社交性的伦理交往,而不只是个体孤立的“独善其身”。之于列维纳斯那种极端的身体观而言,这种训练除了自我与他者的身体互动之外,更需强调对于他者身体的感受,为了让自我的身体沉重地“易感”到他人身体的脆弱性,并且为他人所“受难”,甚至可能需要在训练中制造某种强度的疼痛。 当然,笔者也同意舒斯特曼教授的说法,他所倡导的身体美学修习本身会增强身体的感受力,这种感受力既可以面向自我,也可以面向他者。*在2017年11月美国弗洛里达大西洋大学召开的“美德的身体:东亚视角下的伦理学和身体美学”会议上,笔者就本论文的观点进行了发言,会议的组织者舒斯特曼教授在认可本文学术价值的同时也质疑了笔者在关怀自我和关怀他者这两种身体修炼上的区分,他认为在他的身体美学修习模式下,自我身体的敏锐感受性也会体现在对他人的感受上。只不过这不是列维纳斯意义上以“他者”为导向的身体伦理修炼,在这一修习中,对于他者的身体感受比起对自我的身体感受是次级的,在其中,“他人”在众他者中的特殊地位也没有得到凸显,以列维纳斯的标准来看,它还不够“伦理”。如果将这一“他者”视角拓展为一种伦理政治,那么,在类似的身体修炼中甚至还可以考虑融合不同阶层、不同种族、不同信仰的人。这些人在诸多方面都互为“他者”,然而通过团体性的身体修习,他们却可能亲近他者。
在“身体”议题被广泛置入政治、技术、历史等宏大视野的今天,这样实际的通过身体训练来产生某种伦理或政治效果的构想,无疑显得过于天真,但它却也不失为一种“乌托邦”式的理想,而福柯说过,“人的身体是一切乌托邦的首要扮演者。”*Michel Foucault, “Utopian body”, Sensorium: Embodied Experience, Technology, and Contemporary Art, ed. Jones, Caroline A., Cambridge:The MIT Press, 2006, p.231.既然理论家们把越来越多的议题连接到身体这一点上,那么又怎能忽视对于身体最为日常的照看和修炼?对于身体美学的实用主义视角是符合身体本身的特质的,“身体”本身就不是高渺之物,“身体”的发现如果仅仅被视为一种新概念工具的发明,那它就依旧被“观念”所压抑,“身心二元论”就依旧阴魂不散。身体有自己的“思考”方式,但那主要是通过体验、实践和修炼,在这些层面上,身体都与实用主义和中国思想有一种天然的亲近感。反过来说,对于诸如列维纳斯式伦理和政治视角的引入,无疑也可以拓展现有的身体美学框架,使得身体的修炼可以更开阔和深入地连接世界与他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