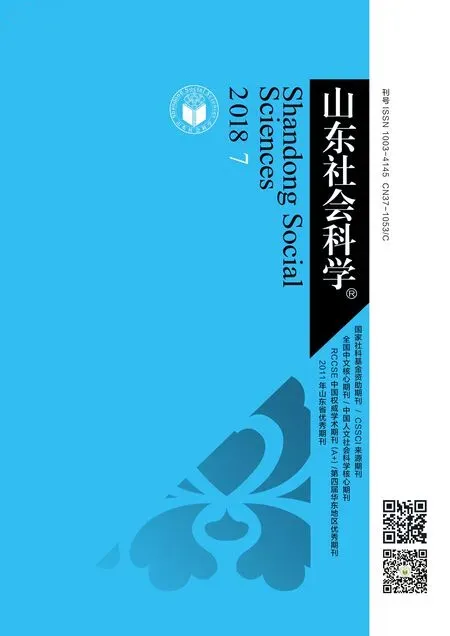齐泽克对多元文化主义的批判
2018-01-29林哲元
林哲元
(华东师范大学 传播学院,上海 200241)
在1960年代西方学生运动和社会运动的推动下,多元文化主义(multiculturalism)首先在美国兴起,1990年代进而成为公共政策和大众日常用语。多元文化主义的起源可追溯到20世纪初早期的黑人研究。1903年黑人学者杜波依斯(William Edward Burghardt Du Bois)在其《黑人的灵魂》(TheSoulsofBlackFolk)中提出,每一个黑人都活在双重意识(double consciousness)的存在之中,黑人既是一个美国人,又是一个黑人,这两种意识在一个躯体中不可调和地相互对抗交战。*参见王希:《多元文化的起源、实践和局限性》,《美国研究》2000年第2期。1924年,美国犹太裔学者卡伦(Horace Meyer Kallen)提出了“文化多元主义”(Cultural Pluralism),以此反对美国社会是一个不同民族融化和再生的“熔炉说”。因为“熔炉说”是将各种欧洲移民的文化认同、价值和生活习惯强制单一化为“盎格鲁—撒克逊”文化,将其他移民文化降低为次等文化。这种文化一元主义违反平等精神,而真正的“美国精神”应该是“民族间的民主”(democracy of nationalities)。早期黑人研究和“文化多元主义”是多元文化主义的理论前身。
多元文化主义原本的基本主张是,不同的民族拥有各自文化的独特性,彼此之间应该相互尊重和包容。后来,其内涵不断扩大。“文化”的基本单位从原来的民族集体(如黑人、少数民族等)拓展到性别领域,加入对女男同性恋、双性恋、跨性别(LGBT)等非主流群体文化的尊重,也拓展到性别外的社会群体,如残疾人、移民工人等等。除了内涵扩大,多元文化主义还日益成为西方人文社会科学学术圈里不可动摇的“共识”。正如鲍曼(Zygmunt Bauman)所言:“这种解决办法(即多元文化主义——引者注)正在迅速变成‘政治正确性’(political correctness)的准则;甚至变成了一条再也不需要被理解的公理,变成了所有进一步深思熟虑的引言,变成了信念(doxa)的基石:不是知识本身,而是所有导致知识的思考的未经思考的、不言而喻的假设。”*[英]齐格蒙特·鲍曼:《共同体:在一个不确定的世界中寻找安全》,欧阳景根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315页。
一般说来,欧美人文社会科学界主流多以捍卫多元文化主义为己任。而身为当今西方激进左翼标志性人物的斯洛文尼亚哲学家齐泽克(Slavoj Žižek)却对多元文化主义提出了严厉质疑和激烈批判。此种理论立场内在的思想逻辑值得我们深入了解并拿过来反思自己,身为第三世界知识分子的我们,多元文化主义对我们意味着什么?本文将首先探讨齐泽克多元文化主义的“经济基础”论;然后考察齐泽克如何将多元文化主义宽容观视为后现代种族主义;最后思考齐泽克提出的超越多元文化主义的途径与意义。
一、“多元文化主义,或者说跨国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
齐泽克《多元文化主义,或者说跨国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一文的题目明显地是对詹明信(Fredric Jameson)的名文《后现代主义,或者说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的致敬式模仿。詹明信引用曼德尔(Ernest Ezra Mandel)观点,将资本主义的发展区分为“市场资本主义”、“帝国主义下的垄断资本主义”和“跨国资本主义(或晚期资本主义)”三个阶段,分别对应于:现实主义、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三种不同的“文化主导”*[美]詹明信:《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张旭东编,陈清侨等译,北京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484-485页。。齐泽克则提出“单一国家范围内的资本主义”、“主权国家之间的殖民主义”和“全球资本主义”三个阶段,他虽然并未论及第一阶段对应的意识形态形式,但以“文化帝国主义”对应传统帝国主义殖民主义、以“多元文化主义”对应全球资本主义。他说:“在国家资本主义及其国际主义/殖民主义阶段之后,今天的全球资本主义再度形成某种‘否定的否定’。起初(当然是就其理想而言)资本主义局限在一个民族国家的范围之内;伴随着国际贸易(主权民族国家之间的交换)发展,随之而来的是殖民国家对被殖民国家的主控和剥削(经济上、政治上、文化上)的殖民关系;这个进程的最后阶段则是殖民的悖论,形成只有殖民统治,没有殖民国家的状态——殖民的力量不再是民族国家,而直接是跨国企业。”*Žižek, S. "Multiculturalism, or, the cultural logic multinational capitalism." New Left Review. 225 (1997). p. 44.齐泽克将全球资本主义这种以跨国企业为基本单位、没有殖民母国的殖民称为“自我—殖民”(auto-colonization)。而“自我—殖民”的特点在于不再是殖民母国与殖民地之间的对立,跨国资本直接由全球性跨国企业控制,而这种全球性跨国企业仿佛割断了与母国之间的脐带联系,对跨国企业来说,母国不过是另一个有待殖民的地区。由于这种“自我—殖民”的新型全球性跨国企业对母国或被殖民国家的居民“一视同仁”——皆是殖民对象,所以多元文化主义成为全球资本主义理想的意识形态,“全球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理想形式就是多元文化主义。从某种空无的全球位置的态度,对待每一个地方文化的方式就和殖民者对待被殖民人民一般——视之为‘土著’(natives),需要仔细研究和‘尊重’他们的风俗”*Žižek, S. "Multiculturalism, or, the cultural logic multinational capitalism." New Left Review. 225 (1997). p. 44.。也就是说,在全球资本主义时代,由于跨国资本高度流动,全球性跨国企业成为新殖民力量的基本单位,而跨国资本自身的“无根性”本质奠定了多元文化兴起的物质基础。齐泽克在《视差之见》中曾经对传统资本主义与今天的全球资本主义进行了归纳,二者的特征正好相反:昔日的传统资本主义以秩序或集中控制来掩盖其内部的混乱(表现为不受控制的社会进程),而今天的全球资本主义则以表象的混乱(对非中心化的“后现代”资本主义的颂扬)掩盖内部国家机器和资本的控制和规训力量的增强。*Žižek, Slavoj. The parallax view. Cambridge, Mass.: MIT Press, 2006. p. 375.“多元性”这种“表象的混乱”与现实资本主义发展阶段状态紧密联系。当前跨国资本占主导地位的历史阶段,多元表象更有利于资本获利的唯一目的。
从表面上来看,全球资本主义呈现为多元状态,例如日本资本的管理方式受武士道精神影响,或亚洲四小龙带有“儒家资本主义”特征等等。齐泽克认为,今天的资本家一再强调自己从各自的文化遗产中获取成功的秘诀,但他们的实际的目的其实是在以此掩盖资本的普遍匿名性。“真正的恐怖不是隐藏在全球资本普遍性之下的特殊内容,而是资本实际上已经成为一架盲目运行的无名全球机器。恐怖的不是(活的、普遍的)机器内的(特殊的、活的)幽灵,而是每一个(特殊的、活的)的幽灵内心深处的(死的、普遍的)机器。”*Žižek, S. "Multiculturalism, or, the cultural logic multinational capitalism." New Left Review. 225 (1997). pp. 45-46.从这个角度说,全球资本主义越是呈现多元状态,就越发彰显与之相反的实质——资本全球化同质化的空前扩张。文化的多元性差异并没有阻止资本同质性前进的步伐,甚至多元性本身就是今天全球资本同质化运行的表现形式。美国跨国速食餐厅在中国卖中式餐点,绝对不是出于对多元文化的尊重,而是资本获取利润的手段。从上述的全球资本主义经济基础的特质出发,齐泽克提出了反对多元文化主义的理由:与部分左派所设想的恰恰相反,多元文化主义并不具有抵抗同一性捍卫差异的进步作用,反而是资本全球扩张的帮闲。“我们在政治正确面前为了少数民族、同性恋、不同的生活风格等等的权利而战斗,而资本主义继续踩着气势昂扬的步伐前进——而今天以“文化研究”之姿出现的批判理论,则积极参与了意识形态方面的努力,力图让庞大的资本主义变成看不见的存在,因此实际上在为资本主义的无限发展进行最根本的服务。”*[斯]纪杰克:《神经质主体》,万毓泽译,台北桂冠图书股份有限公司2004年版,第309页。这是齐泽克对多元文化主义最严厉的批评。更哲学化的表述就是“就当今多元文化主义者对生活模式多样性的颂扬而言,各种差异的繁荣是依赖于一种根本的‘一’(One):彻底抹除‘差异’(Difference)和对抗的裂口。……当我们说到‘繁荣的多元’,我们事实上说的正是它的反面:根本的无所不在的‘同一’(Sameness)”*Žižek, Slavoj. Did somebody say totalitarianism? : five interventions in the (mis)use of a notion. London ; New York: Verso, 2001. p. 238. 中译参考[斯]齐泽克:《有人说过极权主义吗?》,宋文伟、侯萍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84页。。这里所谓(大写的)的“一”或“同一”就是资本的同质化,而“(大写的)差异”或“对抗的裂口”指的就是所有制问题或阶级矛盾。抹除了(大写的)差异或根本对抗的社会,变成可以容纳下各种多元性差别的巨大容器。更具体地进引申,正是在苏东剧变、资本主义看似全面获胜的时代,当改变资本主义私有制这个真正的“(大写的)差异或根本对抗”消失的时候,各种(小写的)多元差异可以被接受,甚至鼓励。这是当今多元文化主义能够在资本全球化时代繁荣的本质原因。
二、恃宽容为傲:后现代种族主义
从多元文化主义作为全球资本时代“自我—殖民化”的跨国企业主导意识形态的经济基础出发,齐泽克批判以多元文化主义为理论基础的“后现代种族主义”——“带着距离的”种族主义,或称“多元种族主义”(multiracism)*Žižek, Slavoj, and Friedrich Wilhelm Joseph von Schelling. The abyss of freedom : Ages of the world. Body, in theory. Ann Arbor [Mich.]: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1997. p.26.。齐泽克这样界定“后现代的种族主义”:“多元文化主义是一种否定式的、倒转的、自我指涉的种族主义形式,一种‘带着距离’的种族主义——它‘尊重’他者的特性,将他者设想为自我封闭的‘真正’共同体,保持着一种距离,使自己享有专有的普遍性位置。多元文化主义种族主义掏空了自身立场所有肯定性内容 (多元文化主义者不是直接的种族主义者,他并不反对他者,不反对他者文化中的个别价值),但尽管如此它保持着‘空洞的普遍’专有立场,从中能够适切地欣赏(和蔑视)其他的个别文化——多元文化主义者正是以对他者特异性的尊重,来保有自己的优越地位。”*Žižek, S. "Multiculturalism, or, the cultural logic multinational capitalism." New Left Review. 225 (1997). p. 44.这段论述击中了多元文化主义者的宽容观的要害:他们以其“宽容大度”的高傲姿态来歧视他人;他们以“尊重”他人个别文化的方式,来突显自身跨文化的“普遍性”的优越地位;他们的“尊重”就是一种“歧视”!这里存在一个扭曲的“普遍—个别”辩证关系。多元文化主义者占据着一个“虚假的普遍性”立场。用黑格尔曾经举过的梨子、苹果、葡萄(个别水果)和“普遍性水果”(“水果一般”)辩证关系来比喻。后现代种族主义者仿佛不再是梨子、苹果、葡萄等个别水果中的一种,而直接占据了 “(普遍的)水果”的位置。*Žižek, Slavoj. Living in the end times. London ; New York: Verso, 2010. pp. 52-53.
后现代多元文化主义种族主义另一个问题是将他者“去他性化”。当他们宣称尊重他者的文化时,那个“他者”事实上是“死亡的他者”,是已经去掉“有害成分的”他者。所谓的尊重和宽容不过是对“去他性的他者”的尊重和宽容,同时是对具有真正他性的他者的拒绝。齐泽克用“泼掉脏水,留住孩子”这个比喻来思考。多元文化主义的宽容企图泼掉民族主义脏水(极端疯狂),留下“健康的”民族意识。然而拉康精神分析逻辑正好相反,“治疗者的目的也不是清除‘脏水’(病症和病态的强迫行为)从而确保‘孩子’(健康自我内核)的安全,而恰恰与之相反,是扔掉‘孩子’(把病人的自我先悬置起来)以直接面对‘脏水’,直接面对病症和构建病人快感的幻想 ”*[斯]齐泽克:《幻想的瘟疫》,胡雨谭、叶肖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74页。。所以,将他者“去他性化”或抽象化,可以说是以真正他者“死亡”(象征秩序杀戮意义下的“死亡”)为代价。这种去除有害物质的逻辑在今天全球资本主义时代十分普遍。“我们现在市场上可以找到一系列祛除自身有害属性的商品:不含咖啡因的咖啡,脱脂的奶油,不含酒精的啤酒……当今宽容、自由的多元文化主义,即体会剥夺了他性的他人(一种理想化的他人,会跳精彩的舞蹈,用生态的、健康的、全面的方式接触现实,但像会殴打妻子这类的特征却都不见了……)。”*[斯]齐泽克、[英]戴里:《与齐泽克对话》,孙晓坤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09-110页。而这种对“去他性的他者”的多元文化宽容观本质上是虚伪的。
反过来说,“去他性”而后宽容的逻辑实际上是它的自己的反面——对真正他者的极端不容忍。这种宽容的真实含义是:“保持距离!”齐泽克将多元文化主义宽容逻辑与当代逐渐扩大的对“骚扰”(harassment)的恐惧结合起来思考:宽容逻辑实际上是对他人的禁止,要人们与你保持一定的距离,不要打扰你。对骚扰的过度恐惧用精神分析学术语来说就是病态自恋逻辑,其核心就是避免被人打扰,与人们保持“适当的”距离。齐泽克在《暴力》一书里提出:“今天,对他人的自由宽容和对他性的尊重与宽大,正是一种对骚扰的偏执式恐惧的对应物。简言之,他者很好,只要他的在场不侵扰我们,只要他不是真正的他者。”*Žižek, Slavoj. Violence : six sideways reflections. New York: Picador, 2008. p. 41.而这种逻辑的灾难性精神后果就是现实感的消失。美国中产阶级社区中人们相互友好地打招呼问候,这些空洞的和颜悦色背后是大家保持“适当的”距离,互不干涉。这种人与人之间过度相敬如宾的距离,最终将导致人与人之间联系感的消逝。1998年彼得·威尔(Peter Weir)导演的《楚门的世界》(TheTrumanShow)正是反映了这样的社会背景。一个生活在美国中产阶级社区的人,往往会产生“这世界是真的吗?”这类疑问,而为了打破这种由于隔绝而产生的存在感丧失的焦虑,往往只能采取扭曲的、恐怖的冒险策略。齐泽克认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出现的“自残”(deliberate self-harm, DSH)现象与“保持距离”的宽容逻辑有关。自残者并非直接的自杀者,而是处于一再重复地伤害自己身体的病态之中,通过鲜血从伤口中流出,自残者企图找回自己的存在感。他者的他性的消失,进而造成现实感的消逝,最终导致自我存在感的匮乏。这种与他人保持隐形距离所排除的东西,以自我伤害的暴力方式回归。
除了多元文化主义将他者“去他性化”,多元文化主义逻辑的虚伪性还表现在对他者文化价值的尊重仅仅局限于无关痛痒的风俗,至于审查何者为重何者为轻的标准则还是高高在上的西方霸权价值观。齐泽克用一个例子来暴露西方多元文化主义逻辑的死胡同。2001年印度掀起一场规模庞大的社会运动,抗议跨国速食餐厅麦当劳以牛油烹制该公司在印度贩售的薯条,抗议者认为这种烹调方式冒犯了印度教对牛的神圣崇拜。抗议的结果是麦当劳公司让步,公开道歉和承诺改进。多元文化主义者认为这是尊重他人文化差异观点的一次胜利。齐泽克对此提出了异议,他提出两点理由来反驳:第一,这种所谓对他人宗教的尊重隐含了一种虚伪性,其运作逻辑是以一种毫无意义的、没有实质内容的形式来尊重他人。如同成人对小孩子说话那样,小孩成天说些天马行空的想法,成人知道那是不现实的,但为了不伤害他们的感情,成人“尊重”小孩的幻想,但并没有真把它当一回事。第二,如果尊重印度人对牛的崇拜,那印度某些农村还存在丈夫过世妻子殉葬的习俗是否要尊重呢?多元文化主义者当然会说不。如此就体现了他们立场的虚伪:多元主义的宽容仅仅是针对那些经过他们审查合格的他者文化习俗。齐泽克说道:“我们其实只接受那些通过我们检验的他人习俗。我们已经把他人过滤了,只有那些过滤过的东西才是被准许的。但就是被允许的东西也是不会给任何人带来麻烦的无关紧要的方面。”*[斯]齐泽克、[英]戴里:《与齐泽克对话》,孙晓坤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29页。这个例子很好地暴露了多元文化主义立场的僵局,值得还在以“多元文化”作为批判视角的左翼思想界的深思。
三、仇恨真正的敌人:超越多元文化主义宽容逻辑
多元文化主义者的另一个在理论僵局还表现在“政治正确”(political correctness)的繁琐追求。“政治正确”在西方已成为日常生活重要的语言习惯。强调避免使用歧视性词语,改用“包容性语言”或“文明词语”,以表达对不同性别、少数民族、弱势群体等的尊重,其内在的逻辑支撑也是多元文化主义。这种语言用法在美国社会最为盛行。例如:用中性的“主席”(chairperson)取代隐含男性中心主义的“主席”(chairman)、用“非洲裔美国人”(African American)取代含有歧视性的“黑人”(Black)或“尼格罗人”(Negro)、用“美洲原住民”(Native American)取代歧视性的“印第安人”(Indian)、用“视障”(visually challenged)和“听障”(hearing impairment)取代“瞎子”(blind)或“聋子”(deaf),甚至为了表达对非基督教信仰人士的尊重,圣诞节问候必须用“节日快乐”(Happy Holidays)取代“耶诞快乐”(Merry Christmas)等等。多元文化主义者热衷于挑剔词语中“歧视”或“性别偏袒”内涵,来达到不同性别、文化、种族等群体之间的相互尊重的目的。在西方学术圈里,其严格程度已经到了让人在词语使用时如履薄冰的地步,成为无人敢缨其锋的“现代禁忌”。
齐泽克对此提出质疑,他在《列宁的选择》一文里指出,“政治正确”支持者不断更换用语,几乎要形成一条词语的链条,例如:“瘸的”(crippled)—“残疾的”(disabled)—“身障的”(bodily challenged)……等等,这个链条可以无穷尽地延伸下去。但是只要链条第一环的侵犯意义还在,侵犯性就会或多或少地转移到下一个环,绵延不绝。而这种扭曲的、施恩式礼貌言辞,歧视意味依然存在,甚至可能强化其中的侵犯性。相较于“政治正确”支持者不断试图逃离词语链条第一环的侵犯性意义而延长链条的做法,齐泽克提出反向的解决方式,与其逃避不如着手正视并改造它。“我们应该主张,唯一有效终止仇恨的方法是创造一个我们可以回到链条第一环的环境,而且以一种非侵略性的方式使用第一环的词句。”*Lenin, Vladimir Ilyich, and Slavoj Žižek. Revolution at the gates : a selection of writings from February to October 1917. London ; New York: Verso, 2002. p. 205.也就是构造一个当有人说“黑人”(Black),但却不再带有任何歧视意味的社会环境或社会意识,而不是企图回避或寻找所谓包容性替代词。反过来说,只要社会结构和社会意识歧视仍在,换什么用词都无法彻底消除歧视,甚至让歧视更隐晦、更难清除。这是典型的齐泽克式直面创伤的思维方法和冒险策略的体现。当然这种作法也有潜在风险,可能会为明目张胆的歧视开了绿灯。但是,不畏风险的勇气不正是彻底解决问题的根本之道吗?
最后,多元文化主义真的是全人类普遍的问题吗?还是西方发达国家少数中上阶层的特殊问题?齐泽克的答案是后者。多元文化主义者内在的反骚扰受害者逻辑就是一个例子。齐泽克认为,“普遍的受害”(universal victimization)概念是不能成立的,必须区分两种受害者。第一种是西方发达国家中上层的“受害话语”。这种受害话语“其实是一种自恋逻辑,任何他者所作所为都是一种潜在的威胁,也就是一种骚扰的逻辑:我们一直都是言语骚扰、性骚扰、暴力、吸烟、肥胖的潜在的受害者而总是受到威胁”。*Žižek, Slavoj, and Glyn Daly. Conversations with Žižek. Cambridge, UK Malden, MA: Polity Press, 2004. p.143. 中译参考[斯]齐泽克、[英]戴里:《与齐泽克对话》,孙晓坤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50页。第一世界的中上层知识分子将自身的困扰抽象地普遍化为全人类的问题。第二种完全不同的“受害话语”是第三世界国家的悲惨现实,无论是自然灾难或战争的受害者,第一世界总是以带着距离的方式看待这些被排斥的人。第三世界受害者无法自己成为主体,而仅仅是第一世界人道救援的“对象”。对西方人而言,灾难发生在“那里”而不是“这里”。“如果声称上层中产阶级关于性骚扰和种族主义言论等‘被害者研究’可以和第三世界那些骇人听闻的苦难相提并论,我认为是非常可耻的一件事情。通过保持这种距离,占主导地位的被害者研究话语是在阻止任何与第三世界受害者的真正团结。”*Žižek, Slavoj, and Glyn Daly. Conversations with Žižek. Cambridge, UK Malden, MA: Polity Press, 2004. pp.143-144. 中译参考[斯]齐泽克、[英]戴里:《与齐泽克对话》,孙晓坤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51页。把西方发达国家的“话语受害”与第三世界的苦难相提并论,就像把减重节食与饥荒挨饿等同视之而令人作呕。齐泽克进一步大胆地批评部分第一世界的左翼学者说:如果你阅读文化研究的教科书,你会觉得性骚扰、同性恋恐惧等问题是当代社会的主要问题。但事实上那些都仅仅是美国中上层阶级的问题,不应该成为左翼奋斗的目标。齐泽克的这种观点在今天美国主导的西方批判理论圈内是触犯众怒的“政治不正确”的言论,但齐泽克认为即使被视为种族主义者或沙文主义者,他也要发起挑战,打破这个禁忌,促人思考。我们生活在第三世界的知识份子更应该自我反思:那是我们的问题吗?
除了批判多元文化主义的“宽容”或“尊重”差异的虚伪性和适用性外,齐泽克还进一步提出了超越和克服的方向。如果说多元文化主义更多地强调他者之间的“爱”,那么齐泽克则是强调他者之间的“恨”——一种共同的“恨”,一种指向真正敌人的“仇恨”。齐泽克以巴尔干半岛在南斯拉夫解体后出现的地区冲突为例予以阐释。2001年,澳大利亚某电视台举办了一场讨论科索沃问题的电视辩论会,出席者包括一位和平主义者、一位塞尔维亚民族主义者和一位阿尔巴尼亚民族主义者。科索沃地区冲突双方的代表各自表述了自己的主张后,那位和平主义者发言说道:不管你们之间的差异如何,你们应该相互宽容,爱对方云云。两位立场对立的塞尔维亚人和阿尔巴尼亚人听到这句话的瞬间,相互交换了一个眼神,意思似乎是:“这个傻瓜在说什么啊?他到底知道我们在谈什么吗?”齐泽克称这个眼神交换的瞬间是一个“神奇片刻”(magical moment),而科索沃问题的解决的可能也存在于这个“神奇片刻”。在这个瞬间出现了真正团结的基础:对共同的敌人的仇恨。齐泽克夸张地描述这种可能的团结——科索沃种族问题解决唯一的希望是对立双方坐在一起说:“让我们杀了这个愚蠢的和平主义者吧!”*Hanlon, C. "Psychoanalysis and the post-political: An interview with Slavoj Žižek." New Literary History 32.1 (2001): p.19.。在别处引用这个例子时,齐泽克补充说明,并不是要把那个善良无知的可怜和平主义者当成敌人,而是要以此强调科索沃冲突的症结当然不在双方的不尊重宽容,将科索沃的局势简化为互相不宽容事实上是转移了问题的焦点,而这种转移将导致问题的实质永远无法解决。科索沃地区冲突的解决契机反而是在共同面对外在的真正的敌人。2000年齐泽克在《易碎的绝对——基督教遗产为何值得奋斗?》里指出:“当面对种族仇恨和暴力时,人们应该彻底拒绝标准的文化多元主义观念,所谓为反对种族褊狭,人们应该学会尊重和宽容他者的他性,形成对不同生活方式的容忍,等等——抵抗种族仇恨的有效方法不是通过直接对立双方的种族宽容,相反,我们需要的是更多的仇恨,是严格意义上的政治的仇恨:把仇恨对准共同的政治敌人。”*[斯]齐泽克:《易碎的绝对——基督教遗产为何值得奋斗?》,蒋桂琴、胡大平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8页。译文有所改动。原文参见Žižek, Slavoj. The fragile absolute, or, Why is the Christian legacy worth fighting for? London ; New York: Verso, 2000. pp.10-11.从齐泽克的思想脉络来看,这个“共同的政治敌人”当然是当今的全球资本主义。解决种族冲突的方法不是多元文化主义所主张的相互尊重、容忍或友爱,而是对准真正敌人(全球资本主义)发难。以此为基础,新的团结才能产生,相互之间的冲突才有解决的契机。
四、结语
齐泽克从当代激进左翼的立场质疑和批判多元文化主义、后现代种族主义和“政治正确”等西方人文社会科学界的主流观点。他首先对多元文化主义的现实基础展开分析,认为多元文化主义是与资本全球化阶段跨国公司的本质逻辑相一致的——有利于资本全球扩张的无根性本质,而跨国资本呈现的表面的多元化掩盖了资本获取利润的单一目的性。多元文化主义虽以反对种族主义为己任,然而实际上是更精致且隐晦难辨的“后现代种族主义”。齐泽克运用拉康精神分析学方法,指出在尊重多元的西方主流话语的背后,隐含着恃“宽容”为傲,专享“普遍性”位置对他者的歧视。而他们所宽容的“他者”是“去除他性的他者”,是无害化的他者,而去除标准还是西方中心主义的。对无害他者的“容忍”与对真正他者的不容忍是一体的两面。“政治正确”也是多元文化主义宽容主义的一种表现。试图寻求中立用词的努力,形成看似进步的语言转变,实则是侵犯性不断转移和隐藏,并未彻底清除。而且这种“政治正确”更多的是满足西方发达国家中产阶级的特殊问题,与第三世界现实的剥削压迫不能相提并论。最后,关于如何超越多元文化主义,齐泽克提出应抛开模糊问题本质的“宽容”逻辑,直面问题,认准真正的敌人展开斗争。
齐泽克对多元文化主义的质疑与反思拉开了激进左翼批判与后现代主义学术主流的距离。齐泽克以拉康精神分析学方法为武器,揭破欧美发达国家学术主流的自觉和不自觉的虚伪面具,展现了激进左翼的彻底批判立场。反对多元文化主义并非反对宽容或互相尊重,而是把大家的注意力引向问题的源头——全球化资本主义。齐泽克或许没有对当前资本主义政治和经济结构进行深刻的分析,也没有提出超越资本主义的现实路径,但至少他指出了问题的所在,为解释与改造现状开辟了新的可能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