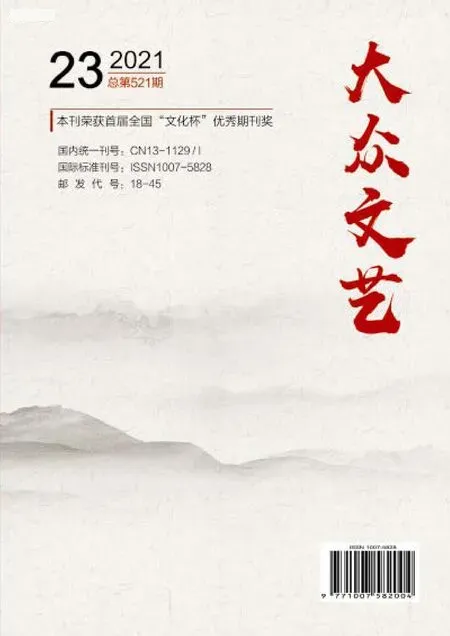鲁敏的“繁荣型饥饿”及救赎
2018-01-29绍兴文理学院312000
(绍兴文理学院 312000)
一、绪论
饥饿自古有之,近现代作家也不断地对这一关键词进行书写。例如张贤亮、莫言等。但他们的饥饿书写更多强调身体层面,也就是饥饿的本义“由食物缺乏所引起的不舒适或痛苦的感觉”。这种饥饿是一种“衰退型饥饿”,是物质匮乏年代的饥饿。随着时代发展,物质的充裕,饥饿的内涵被逐渐扩大,在《饥饿与公共行为》一书中提到:“近年来,许多职业人群可能大大改善了经济地位,从而控制了大份额的可得食物,可就在这样一个繁荣的形势下,仍然产生了一种不可消除的饥饿感,也就是‘繁荣型饥饿’”1。这一现象,日益成为小康时代的一大特点——绝大多数人接受或者被迫接受这个社会,人们改变生活方式的需要与现代社会相矛盾,被现代社会所压抑,由此产生的一种饥饿感。鲁敏在写作过程中开始关注到这一饥饿状态并试图寻找解决之法。
二、饥饿类型
小康时代的饥饿主题日益成为社会关注的重心,人们开始意识到物质泛滥的时代里,饥饿的形态已经从胃上升到头脑。这个时代的病态已经初现端倪,诚如林潇在诗中所写的:“他患病了,一种奇怪的病。走入琳琅满目的超市,竟然找不到一种可以充饥的食物。”2这种病症是时代进步的副作用,也是人类进化所必需经历的过程。在鲁敏笔下,她通过咀嚼母辈的饥饿,自己的饥饿,进一步到谈论这个时代的饥饿,使这种“繁荣型”饥饿显得多样而具体。在她的作品中,“繁荣型”饥饿可以分为以下三种类型:多样型皮肤饥饿,倒置的性欲饥饿,长期的心理饥饿。
(一)多样型皮肤饥饿
对于皮肤饥渴症,美国迈阿密接触研究机构负责人菲尔德指出:人体的肌肤和胃一样需要进食以消除饥饿感,而进食的方式便是抚爱和触摸。因此,“拥抱”成为缓解皮肤饥饿感的方式之一。由此,在鲁敏的作品中,皮肤饥渴症以各种各样的面目出现。就像她在《博情书》中提到的:“人呢,天生都是有饥渴症的,皮肤饥渴,肌肉饥渴,骨骼饥渴······”对于这种症状,究其根本,无非是人类精神世界的外化表现罢了。例如,她的两篇小说就直接命名为《拥抱》、《饥饿的怀抱》。在《拥抱》里,13号就是一个明显的皮肤饥渴症患者。她渴望真正的拥抱,那种自然到来、山洪暴发一般的拥抱,像要死了一般去抱紧另一个人。之所以出现这一症状,就在于她缺乏伴侣的安抚。《饥饿的怀抱》更是直接点明了拥抱的状态——饥饿的。但“拥抱”并不是缓解“皮肤饥渴症”的唯一方式,除了“拥抱”之外,手、脚均可以用来缓解皮肤饥渴感。例如在《荷尔蒙夜谈》中,“手”代替了“拥抱”,成为满足身体饥饿的途径。那个平庸、不值一提的女子,仅仅因为“手”,所以必须参与进这个事件中。何东城坦言:“我必须借助她的手紧紧攥住我,这是最朴素、最根本的一个欲望”。又如《三人二足》中邱先生对于脚的亲吻、吮吸、舔食,小说中有这样一段话:“‘我与脚从此再无勾连’,······他的嗓音里小小地紧了一下,如果不是特别留意,几乎听不出来那血丝般细小但鲜艳的痛苦”。可见,即使邱先生掩盖自己皮肤饥渴症的事实,读者仍能从细节处看出一些蛛丝马迹。可以说,正是这种皮肤饥渴症才成就了《三人二足》。如果邱先生仅仅是由于追逐名利才假意喜欢“脚”,那么作品就错过了一次进入人物幽暗内心的机会,一个复杂的人物就变成了仅仅为谋利而不择手段的形象。
(二)倒置的性欲饥饿
心理学博士安格斯曾提到:“许多男性羞于用语言表达那些脆弱的情绪,比如胆怯、忧虑、遭人中伤、自觉孤独和沮丧失望等,他们通常会以性行为来宣泄这种情绪。”这种现象,显然与鲁敏小说中的男性形象不相符。之所以出现这样的差异,说明鲁敏开始意识到并试图在小说中确立起女性力比多的地位。比如波伏娃曾在《第二性》中写道:“从原始社会到今天,性交一直被当做是一种‘服务’——女性向男性提供的‘服务’”3。但鲁敏却将男性与女性在性欲上的地位进行了倒置,男性不再是性欲的渴求者,而是压抑者。相反,女性反而成为性欲的渴求者,使女性完成了从“女”到“人”的转变。如《六人晚餐》中的苏琴,在丈夫去世后,那每夜必来拜访的焦渴,使她突破了道德的防线。这具疯魔般的皮囊,让她最终成为了一个背德者。她选择丁伯刚的唯一理由便是他的一无是处,使她能够像动物一样与他交合而没有负罪感。可见,两人的交往起源于女性的“焦渴”。这就决定了在他们身体交往的过程中,女性占据了主导地位。“焦渴”这种症状在鲁敏笔下许多中年女子身上都有所体现。如《百脑汇》中的左春,《博情书》中伊姗等。由此观之,女性不再是为燃起男性欲望而存在的工具。鲁敏承认女性性欲的存在,并在笔下将其夸张成男女性欲饥饿的倒置。虽然这是时代发展的必然结果,但这种性欲却是“无爱之性”。她开始正视现代社会“快餐文化”下的性欲关系。人们对“性”的渴求使力比多宣泄的“天地”缩小了,“把爱欲缩小为性的体验与满足”,个体获得的不再是心灵上的充实而是快感。究其根本,这种倒置的性欲饥饿驱使女性被情欲支配而走向道德的反面,是女性对物欲横流的繁荣型社会无声的反抗。
(三)长期的心理饥饿
鲁敏在小说中详细地书写了上至精英社会,下至贫民阶级的心理饥饿。其中,不断出现“空虚”“饥渴”这类象征着“缺乏”的词语,正是体现了在“富裕社会”中,人们过得是一种异化了的生活。人生存于程式化的,异化的世界,由于束缚于特定的活动而显得单一化。正如卓别林在《摩登时代》所表演的沦为人形活扳手旋紧螺母的流水线工人的动作,那便是异化的形式,异化的生活,也正是现代社会的体现。
在进行都市书写的过程中,鲁敏以“暗疾”的形式巧妙地传达出掩藏在表象背后的“空”。比如直接与“吃”相关的暗疾表现者《墙上的父亲》中的王薇与《六人晚餐》中的晓白。两人直接的共同点都在于他们家庭的“畸形”。小说借医生之口戳破王薇,或者以王薇为代表的这一类人的怪异吃欲,即“食物是王薇感知家庭安全感与满足感的重要通道”。这是一种亲情缺失的饥饿。在这种饥饿无法得到满足的情况下,王薇晓白他们只能通过食物来不断地填充。在《饥饿的怀抱》中,一对长期淡漠的父子,一个不停在吃的少女索菲亚,虽然有着短暂的交集,但是,到了最后,仍然是孤独,甚至是无限的孤独。父亲最后产生了一段让他泛起一阵久违的胃酸的一番联想,“真想打个电话给儿子,让他过来,坐到我身边······贴近我的心跳,贴近他的心跳,贴近索菲亚的心跳,贴近所有空空荡荡的怀抱,分辨那些心跳里细小的焦渴与呼唤······并固执地为之命名为饥饿”。这是鲁敏第一次明确地将物质饥饿与心理饥饿联系在一起,可以说,在这篇小说中,融汇了衰退型饥饿与繁荣型饥饿。两者对比之下,鲁敏得出的结论是:衰退型饥饿尚且可以通过“黑疙瘩”来解决,可繁荣型饥饿却是无法可解。
三、饥饿的救赎
鲁敏曾坦言:“阅读上,这些年我一直饥饿,这琳琅满目,饱食终日的饿,以致严重地营养不良······我饿着。我羞耻于这种饿,像得了道德败坏、见不得人的病。这怨不得别人,为什么在大丰大收,供给丰沛到过剩的情况下如此之饿。”为了缓解这种饥饿感,她开始不断地寻找救赎之法。
(一)“东坝”救赎
回到宁静淳朴的东坝去——是鲁敏找到的一条救赎时代饥饿的去路。如果说城市里到处弥散的是由于饥饿而产生的扭曲的需求,那么东坝则是弥补饥饿的乌托邦。鲁敏在东坝书写中不断强调“弥补”,东坝的人物群像大多是先天有所缺陷的,来宝、小达吾提、开音、兰小、宋裁缝······但在这样的一群人身上,却没有繁荣型饥饿的影子。开音不能说话,却在剪纸工艺上表现出极高的天赋;宋师傅对于女人不感兴趣,但能够制作出最能表现女性特质的衣服;虽然有着听力障碍,小达吾提对于气味却十分敏感;来宝与兰小的组合则是东坝人物群像中“弥补”地最完美的一种,这也是鲁敏首次采用“互补法”。在东坝,一切残缺似乎都有了另一种充满审美意味的圆满。但是,乌托邦式的东坝仅仅只是理想状态,时代饥饿依然没有实质性的解决。在写作《木马》这篇小说时,鲁敏就开始了这个思考。都市人刘小木与东坝孩子玉生的互补以失败告终,在文章结尾,小木依然处于“永远在寻找”,却永远找不到东西来填补的状态。因此,鲁敏果断地悬置了“东坝”,太过于“乐天”的主题,对于作家而言,是一种诱惑也是一种陷阱。
(二)死亡救赎
既然“东坝”无法“弥补”这个繁荣时代的饥饿,鲁敏则又走向了另外一个极端——死亡。弗洛伊德曾经提出过对于死亡本能的假设:在死亡本能中他看到了对彻底安宁和扬弃内心紧张的追求,回到母体和回到虚无中的追求4。鲁敏对于“死亡”也存在着个人的偏爱,她直言喜欢薇依说的一句话:“死亡是人类被赐予的最珍贵之物”。因此她试图将现实的饥饿通过肉体的死亡予以消解,出现了程先生之死,柳云之死,姜墨之死,亦梅之死······鲁敏在接受访谈时也曾谈及为何出现死亡的频率如此高,她说道:“我比较熟悉的都是手无寸铁、身无长物的人物与他们的琐碎恩怨,他们没有别的,他们手心里就紧紧攥了自己的一条命,到了某个关头,这就是他们做决定的武器与方式。”而这个所谓的关头,恰恰就是他们承受时代饥饿的一个临界点。
(三)荷尔蒙救赎
可是,死亡终归是摆脱繁荣型饥饿的极端途径。从东坝到死亡,鲁敏一直都不能直面这种饥饿感。接着,她又尝试了第三种方式——荷尔蒙。性本能与死亡本能本身就是统一体,以荷尔蒙的解放来摆脱部分的饥饿意识有着一定的效果。但这一尝试是大胆的,荷尔蒙有着巨大的能量,不易控制。一旦控制不好,则会成为繁荣型饥饿的催化剂,它能够遮蔽自我,也能够发现自我。在《文艺报》上摘录了鲁敏的一段话:“我一直觉得,荷尔蒙,到了中年以后,就不仅是指色、性、欲,它是一个更宽的概念,对个体的困境有着无限的垂怜之意,带点怂恿意味地,牵动着你,在艰难时刻做出听命于直觉和现在的决定······从而获得痛楚中的解放与黑暗中的笑声。”她强调中年,也是因为荷尔蒙是她步入中年的一大感受,但又不仅仅局限于中年,更是触及饥饿的救赎。在《荷尔蒙夜谈》一书中,鲁敏大谈荷尔蒙,曾为许多人所诟病。但是,在这个最好的时代,亦是最坏的时代里,面对这种繁荣型饥饿,荷尔蒙都是一种自我释放,是修改与对抗的一种方式。可性本能终究带有一种原始攻击性,它只能是一种缓解之法,并不是长久之计。
四、结语
在整个时代饥饿的冲击下,鲁敏厌倦了这种机械重复的生活,最终走上了写作之路。从而,她的作品中充斥着使人麻木的工作的需要,麻木不仁的状态的需要。鲁敏的小说是立足于虚妄的,她不断强调:“把虚妄定作这一生的基调,我才有力气,也感到踏实,甚至时不时还有点儿高兴呢”。正是这种虚妄,才使鲁敏很难寻找到繁荣型饥饿的救赎之法。她曾说:“各个阶段,各个方向上,我们都在含糊地占有与失去,追索又重建,虚处生实,实极又念虚。活着即是如此,写作更为典型,妙手空空,空生万物,万物归尘。”这种“空生万物”的意识,才使她难以找到一条切实的救赎之路。她的救赎不是立足于“理想”,就是立足于“荒诞”,却从未立足于现实。可能只有从“虚妄”的写作模式中脱离出来,直面繁荣型饥饿的现状,才有可能寻找到方法去解决这一困境。
注释:
1.[印度]让·德雷兹.阿玛蒂亚·森著.苏雷译:饥饿与公共行为[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第5页.
2.林潇著:小康时代的饥饿[M].阳光出版社,2013年版第14页.
3.[法]波伏娃:第二性[M].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430页.
4.[美]赫伯特·马尔库塞:工业社会和新左派[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1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