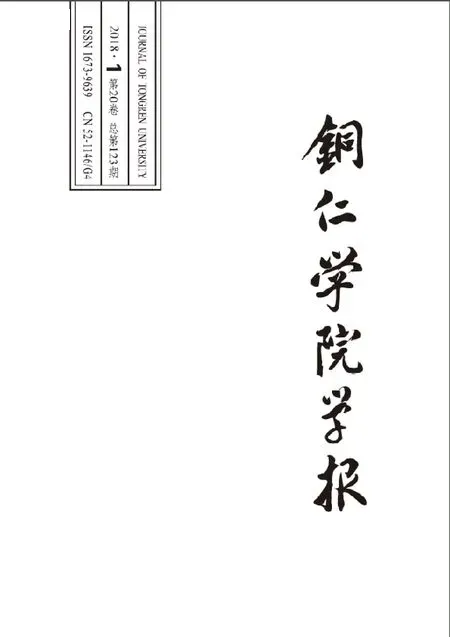论方东树从古文义法对学习陶诗途径的揭示
2018-01-28李剑锋
李剑锋
( 山东大学 文学院,山东 济南 250100 )
方东树(1772-1851)是桐城派文论的集大成者,其诗论《昭昧詹言》卷四设专卷论述陶诗,计八十五条,此外在论述其他诗人诗作时涉及到陶渊明者还有五十多条,附录《陶诗附考》一篇二十二条。诗话设专目论陶始于南宋,南宋中期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宋末江湖诗人魏庆之《诗人玉屑》专列“五柳先生”、“靖节”条目罗列历代评陶言论,宋末元初蔡正孙编撰的《诗林广记》亦有“陶渊明”一目,但多为征引前人意见,极少自己评论;至于诗话设专卷列述自己读陶心得,明人许学夷《诗源辩体》开其端绪,清人诗话甚盛,多有集中评述陶诗者,如沈德潜《说诗晬语》卷上涉及四十多条,方东树《昭昧詹言》设专卷论陶。推源《昭昧詹言》成书之始,乃是诗歌选本的评语,其中古体诗部分采用王士禛《古诗选》为底本。《昭昧詹言》卷一第十五条云:“吾于陶公、谢公,皆依事之大概,移易前后题目编次,俾其语意诸事明晓,而后得以领其妙及语言之次第。”[1]6方东树调整了《古诗选》所选陶诗的次序,大致按照创作年代的先后,此虽不及陶诗全部,当是陶渊明接受史上最早将陶诗编年的一次实践。然而方东树接受陶渊明的主要贡献却不在为部分陶诗编年,作为“把古文理论直接运用到诗歌批评中的代表人物”,[2]650他接受陶渊明的最大贡献是以古文义法论陶诗,凸显了陶诗的跌宕变化之妙,指示了学习陶诗的有效途径。
一、杜公较陶公更为笃实正大
方东树尊崇宋代程、朱理学,格外重视诗人的人品修养,重视诗歌的儒家政教作用,但他持论甚严,对有儒家与佛道倾向的诗人诗作作严格的区分。大略而言,方东树明确推崇主要以儒立身、诗作内涵可以实现儒家兴、观、群、怨目的的诗人诗作,如阮籍、陶渊明、杜甫和韩愈等人及其作品;而严肃贬抑了审美价值虽高但“无当于兴、观、群、怨,失风、骚之旨,远圣人之教”的诗人诗作,[1]387如谢灵运、谢朓、王维等人及其作品。他因此三番五次地评陶渊明云:
有德者必有言,诗虽吟咏短篇,足当著书,可以睹其人之德性、学识、操持之本末,古今不过数人而已,阮公、陶公、杜、韩也。余观太冲,仍是荣华客气,但气格差高耳。[1]97(左思)只说到鲁仲连、子房而止矣,向上更有大人物,非太冲之识所能及矣。庶惟陶公能见之耳。[1]94
陶公说不要富贵,是真不要;康乐本以愤惋,而诗中故作恬淡,以比陶公,则探其深浅远近,居然有江湖涧沚之别。
陶公胸中别有大业,匪浅儒所知,太白胸中蓄理亦多,皆非康乐所望见。读谢诗,令人无兴、观、群、怨之益。
古人变革之际,其立言皆可觇其志性……陶公淡而忘之,犹有《荆轲》等作;康乐不得志,却自以脱屣富贵,模山范水,留连光景,言之不一而足,其志无先朝思也。
(谢灵运)道思本领未深,不如陶。[1]129-130
小谢……口中不要富贵,而身恋之不舍。《朝雨》之篇,自供结状。岂能如陶公之至性恬淡,怀抱如洗也。[1]38-39
求之唐以前诗,惟有陈思、阮、陶、杜、韩,文义与理兼备,故能嗣经、骚,得诗教之正,玄晖未及此也。[1]191
(谢朓)《直中书省》……全无事主之诚、致身图报之意,岂得以陶公高节不乐仕为藉口耶?[1]195
韦公之学陶,多得其兴象秀杰之句,而其中无物也,譬如空华禅悦而已,故阮亭独喜之,陶公岂仅如是而已哉![1]42
桐城派论陶渊明看重他的道德学问修养,如姚鼐论陶渊明首先不是一位诗人,而是有“忠义之气,高亮之节,道德之养,经济天下之才”的贤者;[3]梅曾亮则认为“渊明诗豪不若太白,然其天守全矣”。①方东树论诗也是首先注重人品修养,认为道德是根本,而诗为末用,②陶诗属于“有德者”之言,从中“可以睹其人之德性、学识、操持之本末”,他“不要富贵,是真不要”,“胸中别有大业,匪浅儒所知”,其诗因此与眷恋富贵、缺乏诗教助益的谢灵运、谢朓不同;他的基本立场是儒教,有更深远的文化眼光,其诗言之有物,因此与“空华禅悦”般的韦应物诗、视野有限的左思诗不同。
方东树虽然从人品和诗歌内涵的儒家倾向上充分肯定了陶渊明,但这与前代读者相比并没有提供多少新颖之见。方东树评陶值得关注的是他的贬抑言论,他推崇陶渊明及其作品但仍然不乏苛责,肯定其儒家面目而排斥其道家倾向。认为“陶公所以不得与于传道之统者,堕庄、老也”,[1]111云:
《形影神》三诗,用《庄子》之理,见人生贤愚、贵贱、穷通、寿夭,莫非天定,人当委运任化,无为欣戚喜惧于其中,以作庸人无益之扰,即有意于醉酒立善,皆非达道之自然。……由今观之,杜公悲天悯人,忠君爱国,而不责子之贤愚,其识抱较陶公更为笃实正大也。[1]101-102
庄以放旷,屈以穷愁,古今诗人不出此二大派,进之则为经矣。……阮公似屈兼似经,渊明似庄兼似道,此皆不得仅以诗人目之。[1]5
昔人谓正人不宜作艳诗,此说甚正,贺裳驳之非也。如渊明《闲情赋》,可以不作,后世循之,直是轻薄淫亵,最误子弟。[1]482
陶公诗于圣人所言诗教皆得,然无经制大篇,则于《雅》《颂》之义为缺,故不及杜、韩之为备体,奄有六艺之全也。[1]99
朱熹曾把陶渊明归入老、庄,真德秀明确表示不赞同,认为:“渊明之学,正自经术中来。”[4]汤汉、黄文焕等人注陶也格外强调《咏荆轲》等诗的政治意义。清代读者通观诗史,绝大多数高度评价陶渊明的人品,把陶渊明归入儒家,看作孔门圣贤;但方东树却对此论断持相当的保留态度,此处说陶渊明“似庄兼似道”还算客气,至其《续天道论》则云:“陶公《形神》诗见不出老、庄境地,尚不出佛氏之行愿,而何以希鲁叟之弥缝也?”[5]方东树不是凭感受下此论断的,而是建立在对《形影神》组诗等作品的理解上,他认为“陶公本量,不在此数诗(按,指《咏荆轲》《咏二疏》《咏三良》一类诗作),读《归去来辞》及《形神》诸诗可见。”[1]100陶渊明在《形影神》组诗中排斥喜怒哀乐、主张委运任化是“用《庄子》之理”,这与感情丰富、“悲天悯人,忠君爱国”,像圣人一样汲汲以求的杜甫相比,显然逊色一筹。因此,方东树认为陶渊明的“识抱”不如杜甫“笃实正大”,“陶公所以不得与于传道之统者,堕庄、老也”。也是站在严正的儒教立场,他也否定了《闲情赋》,对陶不能“奄有六艺之全”表示遗憾。有论者因此指出他如此论陶:“不可否认地有其偏狭与武断之处。然而另一方面,若站在方氏推阐桐城派雅正的诗学主张来看,便不难理解其评论中,带有导正时人积极观念的教育意义存在。尤其方东树本身对于国事甚为关心,虽因考场失利而赖馆课讲学为生,犹不忘提携后进,希冀培养晚辈学成诗文的同时,亦具备经世济民的胸襟。”[6]252此论有见地。需要补充的是,方氏遗憾陶渊明“无经制大篇”,不够“笃实正大”,把陶诗置于杜诗之后,当也与他推崇豪雄跌宕的文风密不可分。
二、不易先学而有途径可学
方东树认为陶诗最大的特点是真,真乃元气发露,胸襟自流,是修养至极的天然表现,故陶渊明首先不是诗人,而是知道的圣贤,陶诗是与天为徒,不烦绳削,不是刻意雕琢,巧夺天工。这是方东树对陶渊明诗如其人特点的基本观察,故其评论云:
读陶公诗,专取其真:事真景真,情真理真,不烦绳削而自合。谢、鲍则专事绳削,而其佳处,则在以绳削而造于真。”[1]98
至于陶公之无容心于修辞琢句,杜公之峥嵘飞动,元气浑浑,不可以此例论。[1]187
如庄、屈、陶公、阮公,其知道乎!(评阮籍《咏怀诗》“天网弥四野”)[1]91
汉、魏、阮公、陶公,皆出之自然天成。惟大谢以人巧夺工。[1]41
陶公别是一种,自然清深,去《三百篇》未远。[1]34
陶公不烦绳削,谢则全由绳削,一天事,一人功也。……谢从陶出,而加琢句工矣。[1]131
诗文须神气浑涵,不露圭角。汉、魏以下,惟陶公能尔。大谢以人巧肖天工,已自逊之,是根本不逮,然犹自浑厚。[1]31
如阮公、陶公,曷尝有意于为诗;内性既充,率其胸臆而发为德音耳。钟嵘乃谓陶公出于应璩,又处之以第七品,何其陋哉!宜乎叶石林之辟之也。[1]98
惟陶公则全是胸臆自流出,不学人而自成,无意为诗而已至;东坡亦如是,固是天生不再之贤。虽杜、韩犹是先学人而后自成家,如杜《同谷七歌》从《胡笳十八拍》来,韩《南山》诗从《京都赋》来。
大约陶、阮诸公皆不自学诗来,惟鲍、谢始有意作诗耳。[1]35
阮公、陶公,自尔深人无浅语,不当以诗人求之。[1]98
论陶诗真率自然并不新颖,主要是继承了萧统、黄庭坚等人论陶真旷自然的观点,如元人《诗谱•十五体》谓陶诗“情真景真,意真事真……至其工夫精密,而天然无斧凿痕迹”,[7]360方东树论陶“事真景真,情真理真,不烦绳削而自合”,显然有明显的传承关系。但方东树的论述较为系统,且反复强调,将陶诗与缺少自然真率特点的其他诗人相对比,遂令人印象深刻,此其一;其二,格外强调了创作主体的特殊性,即陶诗本于“元气”性理,首先得益于人品的修养,是其高尚人品和深厚修养的天然流露,是直抒胸臆,没有“客气假象”,[1]222即所谓“深人无浅语,不当以诗人求之”,“曷尝有意于为诗;内性既充,率其胸臆而发为德音耳”,“全是胸臆自流出,不学人而自成”。因此,陶诗“自然天成”,个性风格也十分明显,“自道己意”,[1]11“自见其心胸面目”,[1]82文如其人。因此,陶诗不易学。朱熹云:“渊明平淡自然,后人学他,便相去远矣。”[1]498明人谢榛《四溟诗话》论诗语云:“自然妙者为上,精工者次之,此着力不着力之分,学之者不必专一而逼真也。专于陶者失之浅易;专于谢者失于饾饤。”[1]481谢榛的观点得到后代诗论家的认同。如许学夷:“靖节诗甚不易学,不失之浅易,则伤于过巧。”[8]107贺贻孙《诗筏》云:“真率处不能学,亦不可学,当独以品胜耳。”[9]158叶燮《原诗》云陶诗:“游方以内者,不可学,学之犹章甫而适越也。唐人学之者,如储光羲,如韦应物,……俱不能有陶之胸次故也。”[10]603-604此外,王士禛《师友诗传录》、乔亿《剑溪说诗》、洪亮吉《北江诗话》、章学诚《文史通义》等都表达过类似意见。方东树论陶不易学也是继承了前人观点,比如他曾经摘引朱熹语和谢榛《四溟诗话》。但作为最高艺术水准的作家作品,陶诗又不能不学。方东树在《昭昧詹言》卷四第一条即明确云:“学诗当从《三百篇》来,以屈子、汉、魏、阮公、渊明嗣之,如此方见吟咏之本。”像朱熹一样,方东树不但肯定要学,而且要作为“吟咏之本”来学,于是就产生了如何学的问题。方东树总结前人学陶得失,指示出学陶两大基本思路。第一,先从容易学的诗人学起,即先学会可以学、容易学的作家作品;再去进一步学习陶渊明等最高层次的诗人诗作。如云:
诗有用力不用力之分。然学诗先必用力,久之不见用力之痕,所谓炫烂之极,归于平淡。此非易到,不可先从事于此,恐入于浅俗流易也。故谓学者宜先学鲍、谢,不可便先学陶公。[1]380
学者若不先从鲍、谢入手,而便学此,未有不失之滑浅庸近,如今凡俗所为者也。……若执笔便拟陶公,是黄口孺子,轻学老成宿德,举止风轨纵似之,亦可鄙笑,不惟优孟衣冠,抑且滑熟无力。[1]108
古人文之高妙,无不艰苦者,但阮公、陶公,艰在用意用笔,谢、鲍艰在造语下字。初学人不先从鲍、谢用功,而便学阮、陶,未有不凡近浅率,终身无所知。以此求之,数千年不得数人,纷纷俗士,不足讥矣。[1]110
学康乐之沉厚深重,须经济以明远之俊逸,乃免滞气;学明远久,又入于轻俊,又当济之以康乐。至陶公、杜公则全美。[1]138
学黄必探源于杜、韩,而学杜、韩必以经、骚、汉、魏、阮、陶、谢、鲍之源。取径古,用笔锐,造语朴,使气奇,选字坚,神兀骨重,思沉意厚,此亦诗家极致之诣也。[1]228
方东树认为“如能合陶、杜、汉、魏而兼其胜,乃可俯视谢、鲍”,[1]135陶诗是“诗家极致之诣”,但初学者不应“轻学老成宿德”,而应循序渐进,认为学陶要先从有门径可学的诗人学起,具体就是“先从鲍、谢入手”,学习的时候“每篇百遍燠热”,[1]131于谢、鲍等人主要学习“造语下字”,如何用力,于陶则主要学习“用意用笔”,进而达于“不见用力之痕”的最高境界。之所以特别把鲍照和谢灵运作为学陶前的捷径,一是因为他们“造语下字”等用力的地方有痕迹可学,二是因为“谢从陶出,而加琢句工矣”。[1]131彼此有相似之处。
第二,方东树认为学陶要先做人,在修养上下功夫。对于陶诗“须先求其本领,兼取其文法,盖义理与文辞合焉者也”,而谢灵运、鲍照、谢朓等人只是“取其创言及律法之严”,但是“义理本领未深”,甚至连“文法亦无甚深妙”。[1]98“义理本领”既然与“文法”相对,则“义理本领”主要指其合乎儒家之道的意蕴和修养,这是第一位的,首先需要研求的。方氏引张九溪语云:“文章必以理胜,诗赋乃文之有韵者耳……倘胸无根柢,而徒取涂于五七言中,纵极工致,风骨不凝,寻味甚短,不过陆、潘牢笼中物耳,于陶、杜、韩、苏诸大家之风,弗之悟矣。”③这就明确指出了诗人修养跟诗歌境界关系非常密切,落脚到学陶诗,就是应该有陶一样的“根柢”,即学陶“知道”,为“深人”的根本方面,否则难以达到陶诗的境界。
方东树论陶诗不易先学而有途径可学是桐城派文论在具体诗人身上的运用,是其艺术经验的总结,也是对前人学习陶诗经验的总结。如苏轼、黄庭坚、朱熹等等已经屡次提出陶诗不易学、但仍把陶诗作为学习的经典范本。基于学诗和教育的需要,方东树对于如何学陶的问题作了有效回答。
三、以义法论陶诗变化之妙
方东树具体评点陶诗最值得注意的是以桐城派的义法理论为指导发掘其中“微言胜理”,④揭示其中跌宕变化之妙,这可以看作其指示学陶途径的延伸,是具体的学习例解。《昭昧詹言》卷一论“文(语辞)、理(意蕴物理)、义(文法)”云:“文者,辞也;其法万变,而大要在必去陈言。理者所陈事理、物理、义理也,见理未周,不赅不备,体物未亮,状之不工,道思不深,性识不超,则终于粗浅凡近而已。义者,法也;古人不可及,只是文法高妙,无定而有定,不可执著,不可告语,妙运从心,随手多变,有法则体成,无法则伧荒。率尔操觚,纵有佳意佳语,而安置布放不得其所,退之所以讥六朝人为乱杂无章也。”[1]8陶诗“笔力强,文法妙,言皆有本;寻其意绪,皆一线明白,有归宿,令人了然”,[1]11-12是最为符合其义法的理想作品之一。此分析论之如下。
首先,陶诗语词(“文”)推陈出新、自然新奇。如评《连雨独饮》云:
不过言人生必死,世无仙人,不如饮酒,而用意用笔,俱回曲深峻。天者自然,而己任真,则亦同于天,曰“忘”,曰“无所先”,皆笔之曲也。……起四句本是古人陈言,看他折洗翻用入妙。[1]122
《连雨独饮》词语“忘”和“无所先”的选用很好地体现了陶诗“回曲深峻”的特点。该诗开头四句云:“运生会归尽,终古谓之然。世间有松乔,于今定何间。”此种命运生死慨叹在陶渊明之前屡见不鲜,如《古诗十九首》:“人生忽如寄,寿无金石固”,“人生寄一世,奄忽若飙尘”,“服食求神仙,多为药所误”,“仙人王子乔,难可与等期”,曹植《赠白马王彪》:“虚无求列仙,松子久吾欺。变故在斯须,百年谁能持”等,在诸多名句前翻新实属不易,而陶诗居然“折洗翻用入妙”。又如评《癸卯岁始春怀古田舍二首》之二“平畴交远风,良苗亦怀新”为陶诗名句,“奇丽千古,他人雕肝琢肾不能到”,可谓新颖,但这种新颖与谢朓的雕琢不同,而是“本色自然”。[1]105此外,方氏还指出陶善用虚字、开启后学之句、言简意足等特点。⑤值得注意的是,方东树对拟古诗颇多否定,其原因就是“拟古而无所托意”,即使“东坡和陶,虽自有题,亦觉无味”;[1]37但他却关注到陶渊明拟古诗的特殊,认为“渊明拟古,是用古人格,作自家诗”。[1]37即渊明拟古诗值得肯定之处是有自己个性面目,与个性化相比,语言的创新还在其次。
其次,方东树结合文法的变化之妙凸显陶诗隐微的思想意蕴,认为陶诗之“理”言之有物,表达高妙深曲、鲜明贴切。“理者,所陈事理、物理、义理也”,方氏所谓“理”既包括偏于内容意蕴方面的“事理”“义理”,相当于言有物之“物”,也包括“物理”,即物象之情态神形。方东树在具体评点中注重联系表达方式钩沉“理”的意蕴情态,如评《饮酒二十首》之二十为“义理可以冠集”云:
此首盖以举世少真,而己独一人任真,如鲁哀公云“以鲁国而止有儒一人”也。而此意不便自说,故谬悠其词于饮酒,曰恐负此儒巾也。下二句又就饮酒中为荒唐吊诡,谬悠中又复谬悠之,却又顾题也。……“少真”,谓皆从于苟妄也。举世习非,不得一真,欲弥缝之,道在“六经”。崇尚乎此,庶可以反性情,美风教,成治化,著诚去伪,返朴还淳。无如世竟无一人问津,此其可痛可恨;而己之所怀,则愿学孔子,从事于此,亦欲弥缝斯世,而有志不获,惟有饮酒遣此悲愤也。以用意论,极其恍惚,以文法论,极其恣肆奇妙不测。收言举世皆庸奴,无可庄语,只有饮酒。愈缓愈肆愈远。经所以载道也,载道则无苟妄,而无不任真矣,故归宿孔子及诸儒。言己非徒独自任真,亦欲弥缝斯世,此陶公绝大本量处,非他诗人所能及。故此篇义理可以冠集。……此二十首,篇篇具奇旨旷趣,名理名言,非常恣肆,皆道腴也。[1]117-118
这篇评论虽然是揭示陶诗合道真诚的儒家旨趣,但主要是剔抉其中用意的深曲变化,以评“少真”为例即“以用意论,极其恍惚”;在揭示这些“义理”时,又时时注意提示其表达方式恣肆高妙,即“以文法论,极其恣肆奇妙不测”,“不言己之好,但言人之不好,亦避直取曲,以虚形实也”。推而广之,《饮酒诗二十首》“篇篇具奇旨旷趣,名理名言,非常恣肆,皆道腴也”,义理“皆道腴”,而表达“非常恣肆”。此外,其解《始作镇军参军经曲阿作》亦钩深索隐,卓有高见。评《饮酒二十首》之二十等主要是针对“义理”,又如针对“事理”“物理”评点云:
此诗叙一大事,本末曲折具备……议论精卓,抵论赞。(评《桃花源诗》)[1]110
此忽然慨世庸愚之人,可怜而不悟,而吐属温雅蕴藉,无恶谑丑诋直骂,气象渊懿。(评《饮酒二十首》“有客常同止”)[1]116
此但书即目,而高致高怀可见。(评《饮酒二十首》之五“结庐在人境”)[1]113
“方宅”十句不过写田园耳,而笔势骞举,情景即目,得一幅画意。(评《归田园居五首》之一)[1]106
一往真味,景与情俱带画意。(评《于王抚军座送客》)[1]120
方东树认为“读陶公诗,须知其直书即目,直抒胸臆,逼真而皆道腴,乃得之”。[1]97此论陶诗叙述事理曲折完整,感慨世事“气象渊懿”,写景写物贴切逼真,与情交融,有画意,是其“直书即目,直抒胸臆”的结果,也是与“道腴”真醇联系在一起的特点。
再次,方东树关注最多的是陶诗文法变化之妙。如评《岁暮和张常侍》云:“章法文法,曲折顿挫,变化不可执著”,[1]121评《有会而作》云“读此乃见公用笔之变,用意之深曲,文法妙不测”等[1]121,又认为“《羊长史》篇,文法可以冠集”,[1]118“其文法之妙,与太史公《六国表》同工”,此摘录一节为例:
“中都”不必呆数典,此即指关中耳。此上承黄、虞,下伏四皓,草蛇灰线过脉。若云君当往事佐命,吾当为四皓以避乱耳,却借如此指出,毫不见正意痕迹,其妙如此。前后惟阮公、杜公有之。韩公亦能之。坡则罕见此矣,何况馀人。“路若经商山”,以笔势论,亦是蹴起陡势,神来气来之笔。[1]109
又如评《饮酒二十首》之三(“积善云有报”)云:
言不必计善恶之报爽,但以固穷守道为正。求仁得仁,同一穷死,不如留名没世。一起四句,偏反飞动,先有断决,而后发此端问,先非真有所疑也。反复疑迷,收二句,语势尤劲折,无一平直浅滞顺滑之笔。明明爽报,却云不爽,求仁得仁也。以二人证之,而文法相承互解,言即此所以报夷、齐、荣公也。上言其爽而空言诘之,作波澜,以起下百世之传,折出一荣公,文法变化如此。以福报则爽,以名报则应,文法变化。收忽然自断决截,坚定不复疑,若忽悟彻者然。[1]112
这些评论注意揭示陶诗内部结构的前后照应之妙,突出陶诗“文法”如何上接下递、突起变化、生气灌注的特点。平淡之下有深味,文似看山不喜平。方东树以古文义法理论解析陶诗,解构陶诗平淡的传统观点,极力挖掘陶诗山高水深的一面,这与方氏的艺术宗尚有关,也是对陶渊明接受史类似成果继承的结果。方氏认为“诗以豪宕奇恣为贵,此惟李、杜、韩、苏四公;前此惟汉、魏、阮、陶公、孔北海、刘越石数贤而已”。[1]28-29对于陶诗他首先看重的不是平淡,而是“豪宕奇恣”,如阮籍一样的“宏放”[1]91之作。萧统评价陶诗有“跌宕”“抑扬”之说,黄文焕、吴淇评点陶诗已经格外注重揭示章法和激荡不平的情感意蕴,在方式方法上起了先导作用,只是没有格外关注文法的变化恣肆而已。与方东树同时代的延君寿在《老生常谈》中论陶诗与方氏颇有相通之处,[9]1821他论陶《五月旦作和戴主簿》等诗用字新奇,文法变化,只是没有强调变化中恣肆的特点,也没有系统用于陶诗整体批评。方东树的观点和解读方式在前人基础上进一步定型化、理论化和模式化,其将陶诗归宗于变化恣肆是对以恬淡真醇视陶观点的突破和深化,突破是指不再流于平易散缓之类的表面感受,深化则指深入思索和揭示了陶诗真醇所隐藏的意蕴理路和形式理路。《昭昧詹言》云:“前人说陶诗者甚众,然多迹论常解,无关微言胜理。”[1]101就揭示陶诗用意深曲、变化之妙来说,方东树此言不应归于狂妄。
方东树借鉴唐代古文家李翱的理论从“文(语辞)、理(意蕴情态)、义(文法)”论析诗歌,《昭昧詹言》云:“求通其辞,求通其意也。求通其意,必论世以知其怀抱。然后再研其语句之工拙得失所在,及其所以然,以别高下,决从违。而其所以学之之功,则在讲求文、理、义。此学诗之正轨也。”[1]7由于《昭昧詹言》编撰的初衷是为了教育子弟,所以此段话从阅读接受诗歌的角度自三个方面分层次扼要地指示了“学诗之正轨”。即第一步,最基础的层次是“求通其辞”,这类似于刘勰所云“披文入情”;第二步,中间的层次是“求通其意”,主要指把握诗歌意蕴;第三步,最高一层才是“研其语句之工拙得失所在”,即以笔法、章法等文法为主的表现技巧。这三步三层分别对应着“文(语辞)、理(意蕴情态)、义(文法)”三个概念。当然,最终的阅读学习目的还是为了掌握诗歌创作的方法、达到儒家兴、观、群、怨的教育目的,由此《昭昧詹言》不断指示行之有效的学诗途经,强调以符合儒家人品为目的的诗人修养。在这种诗学理论和教育目的双重作用下,方东树展开了上述对陶渊明的批评⑥。
注释:
①(清)梅曾亮《邹松友诗集序》,《柏枧山房全集》之文集卷六,清咸丰六年刻民国补修本。梅曾亮认为“渊明之诗和而傲,其人然,其诗亦然。”(梅曾亮《杂说》,《柏枧山房全集》之文集卷一)这与方东树论陶诗有自我面目也相通。
② (清)方东树《徐荔庵诗集序》:“古之立言以蕲不朽者,必以德为之本……陶渊明、杜子美、韩退之诸贤,犹可想见其本用。”(《考槃集文录》卷三,清光绪二十年刻本)
③ 《昭昧詹言》卷二一,第一一七条,第502页。“九溪诸论,惟深于文理者知之”(《昭昧詹言》卷二一,第一○九条,第505页)可见方东树对张九溪此论是持赞成态度的。
④ 《昭昧詹言》卷四,第十八条,第101页。按《昭昧詹言》卷四前十八条总论陶诗,后六十七条为针对具体篇目的评点。
⑤ 如《昭昧詹言》评鲍照《和王丞》:“‘限生’二句,即‘人生不满百’意,陶公衍之为五字(按指陶《九日闲居》“世短意恒多”句),更言简意足。”(卷六,第三十五条,第174页)
⑥ 方东树的《陶诗附考》主要赞同阎咏等人考论补证陶侃不是陶渊明曾祖父的观点。对于阎咏的观点,早于方东树近半个世纪的著名学者钱大昕有《跋陶渊明诗集》、与方氏同时而早去世十二年的陶澍有《(靖节先生)年谱考异》驳论甚详。方东树的《陶诗附考》计二十二条,文字短者一二百字,长者过千,条分缕析,言之凿凿,自成体系,可称传统陶渊明接受史上反驳陶侃乃渊明曾祖这一观点最为系统的考论和分析。但毕竟推测过多,难成定论,也不为一般读者所接受。不再赘论。方东树之所以下这一考论功夫主要有三个方面的原因:第一,这是他推重陶诗的表现;第二,是他知人论世观点的实践,他认为“若夫古人所处之时,所值之事,及作诗之岁月,必合前后考之始可见。如阮公、陶公、谢公,苟不知其世,不考其次,则于其语句之妙,反若曼羡无谓,何由得其义、知其味、会其精神之妙乎”?正如为陶诗编年一样,考订陶渊明谱系有助于理解陶诗;第三,与他尚宋代义理之学、不满乾嘉汉学有关,他有《汉学商兑》贬斥钱大昕等汉学大家乱道惑众,而钱大昕正是驳斥阎咏观点、赞成陶渊明曾祖父为陶侃者,故方氏反其道而行之,认为“阎氏此说,卓绝千古”,对钱大昕驳论阎咏的言论严厉驳斥。见《昭昧詹言》卷一,第十五条,第6页;卷一三,第二十六条,第353页。
参考文献:
[1] (清)方东树,汪绍楹,校点.昭昧詹言[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1.
[2] 张健.清代诗学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3] (清)姚鼐.惜抱轩诗文集·荷塘诗集序(卷四)[M].清嘉庆十二年刻本.
[4] (宋)真德秀.西山文集·跋黄瀛甫拟陶诗(卷三六) [M].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5] (清)方东树.考槃集文录(卷一) [M].清光绪二十年刻本.
[6] 张俐盈.方东树《昭昧詹言》论陶诗[J].东华汉学(台湾),2009(10).
[7] 张健,编.元代诗法校考[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
[8] (明)许学夷,杜维沫,校点.诗源辩体(卷六) [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
[9] 郭绍虞,编选,富寿荪,校点.清诗话续编(上册) [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
[10] (清)叶燮.清诗话(下册)·原诗·外篇 (下) [M].南京:凤凰出版社,2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