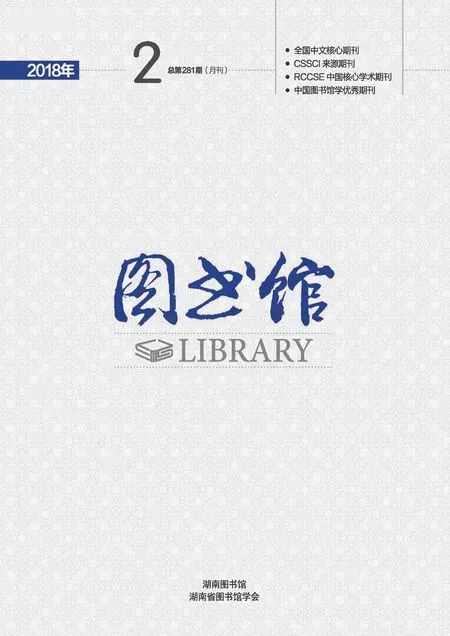古代官府馆藏访求探析*
2018-01-28龚蛟腾刘春云
易 凌 龚蛟腾 刘春云
(湘潭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湖南湘潭 411105)
1 引言
中国的藏书事业,就其历史、规模和发达程度而言,在世界上是独一无二的[1]。而在漫长的文献收藏、整理与管理历史中,我国古代形成了官府图书馆、私人图书馆、寺观图书馆和书院图书馆等四大类型的图书馆体系。其中“学统王宫”的官府图书馆是最早的图书馆形态,其萌芽于夏前、初兴于夏商周、成型于秦汉、发展于唐宋、鼎盛于明清,它们前后相承并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也为近现代公共图书馆留下了宝贵的遗产与难得的经验[2]。古代官府馆藏是统治阶级推行文治教化的工具,更是社会文化积淀与传承的载体,故而历代政府都十分重视官府馆藏访求。正如吴慰慈与刘兹恒所言,“图书馆藏书是图书馆开展全部工作的物质基础,没有藏书就不可能有图书馆”[3]。没有访求就没有藏书,访求是图书馆工作的重要环节和图书馆存在的先决条件。我国古代官府藏书的访求与官府藏书相终始,是一项重要的政治文化活动[4]。各代统治阶级无不视其为一桩大事盛举,加以高度重视,并施以有力措施。求因才能得果,鉴往方可知来!探析古代官府图书馆的馆藏访求是研究古代图书馆事业的一个重要途径,无疑对当代图书馆的信息资源建设具有相当大的借鉴意义。
2 古代官府馆藏访求源远流长
2.1 官府馆藏访求之作用
古代官府馆藏访求历来倍受重视,这是由官府馆藏的重大价值所决定的。首先,官府馆藏具有重要的政治意义,是统治阶级维护政权的标志与工具。“夫教化之本,治乱之源,苟无书籍,何以取法”[5],官府馆藏是国家典章制度图书的收藏处,能为治国理政提供重要参考,又是统治阶级推行教化的基础和凝聚统治力量的精神支柱。其次,官府馆藏是官府图书馆的立馆之本,确保履行“完整、系统地搜集和保管本国的文献,从而成为国家总书库”[6]的职能。官府图书馆是政权支撑的包括国家图书馆在内的整个古代公共图书馆体系的总称,官府馆藏经历代不断充实并妥善保存,使得众多珍贵典籍保存至今。“图书馆每一项功能的发挥,都离不开图书馆的采访工作。而图书馆采访工作的优劣,又直接影响了图书馆功能的发挥。图书馆采访工作,可以喻之为图书馆工作的根基或龙头”[7],官府图书馆要发挥其在政治和社会上的价值,则必须重视访求。第一,访求是建立馆藏的前提,能使官府馆藏完备,全面反映中华文明成果;第二,访求有利于文化成果的妥善保存,将图书集中到官府进行统一管理,有利于其长期存续;第三,官府馆藏访求有积累的大量图书工作经验,有利于图书馆事业的整体发展;第四,访求工作还有利于加强统治阶级对社会思想的控制,访求的同时还对违背政治原则的图书予以毁禁,维护了统治的稳定。
2.2 官府馆藏访求之必然
由于官府馆藏具有重要价值,政府设置了史官、秘书监等相对完善的管理机制,但馆藏资源仍旧无法永久保存。青铜金文会因氧化而锈蚀,碑篆石刻会因风雨而抹平,而简牍纸本更会因蠹虫、火灾等等而残损,尤其是兵戎之后,片纸难存。无论内忧还是外患,官府馆藏都饱经困厄,屡受打击。安史之乱与靖康之变使得唐宋两代完备的馆藏陡然衰败,晚清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文源阁《四库全书》尽成飞灰。在毁灭性的战争面前,无论多丰厚的馆藏都只能任由战火蹂躏。而且太平盛世图书也有困厄。宋大中祥符八年,崇文院失火使得内府藏书“大半煨烬矣”[8],水火无情,祝融之下,纸书难存。明朝时,官府馆藏缺损严重,命令李继先等进行整修,结果李继先反而盗窃书籍,使得馆藏受损情况雪上加霜。根据学者统计,中国典籍曾遭十七次大厄[9],历代官府馆藏看似辉煌,实则危机四伏。官府馆藏损毁的原因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社会原因,如战争等,失去政权保护的馆藏不具有任何反抗战争能力,这一原因对官府馆藏造成的损害最为严重;二是自然原因,如梅雨天气造成的图书受潮、风化造成的脱页和蠹鼠啮咬等等;三是管理原因,如管理不当而造成的火灾、盗窃等,这是导致官府馆藏受损最主要的方面。基于以上三大原因,官府馆藏的补充——访求就显得尤为必要。
2.3 官府馆藏访求之肇始
官府图书馆的历史至少可以追溯到商周时期,而作为图书馆管理者的史官制度至少可以追溯到黄帝时期,譬如仓颉就是黄帝的史官。既然有人管书,那就要有书可管。上古结绳记事,当时史官的工作很可能就是收集并保存结绳等信息载体,这带有原始访求的意味。到商周时期,出现了档案性质的图书雏形——记载甲骨文的龟甲兽骨,这些甲骨就是商周官府馆藏的主要内容。据《吕氏春秋》记载,“夏太史令终古,出其图法…出奔如商”,“殷内史向挚见纣之愈乱迷惑也,于是载其图法,出亡之周”[10],若有乱世征兆,先秦史官会自发地转移本国图籍,以保证其完整性,对接受图书的国家则有事实上的访求作用。春秋时期,孔子受周天子委托编制《春秋》,“使子夏等十四人求周史记,得百二十国宝书”[11],虽然主要是子夏等的个人力量,但也是一次有政府背景的主动访求,且成果丰硕。此外,各诸侯国也建立了史官管理下的藏书体系,如晋之屠黍,楚之伊相等。周秦时代还设置了采访各地风俗、语言等的“輶轩之使”,虽然没有访求的职责,但是他们会将工作成果以奏籍的形式上交并保存在官府馆藏中。先秦的访求具有鲜明的自发性的特点,秦汉时代则是中国官府馆藏访求走向自觉的转折时期。此后,政府逐渐认识到了访求的重要性,历朝历代都大肆搜集图书充实官府馆藏,这也成为统治阶级炫耀文治武功的基本方式。
2.4 官府馆藏访求之定制
自黄帝以来,史官就兼掌图书访求、典藏、整理之事,传续不断,由殷商而至周秦。到嬴政灭六国后,秦中央政府至少有“明堂、石室、金匮、周室”四个藏书处[12]与博士官和御史两套管理体系。既有藏书,必有访求。秦始皇曾“收天下书不中用者尽去之”[13],严格查禁民间藏书,只保留官府馆藏中的秦代史书、《诗》、《书》、百家书籍与一些实用技术型书籍。秦代的访求虽然严厉,但也是通过政府力量进行访求来管理图书事业。秦亡后,汉继承了秦官府馆藏及访求工作。西汉是图书采访工作较有成就的一个时代,期间形成了一系列采访政策与方法,为其后历朝继承与仿效,最终演化为制度,官府馆藏访求作为一项定制便在这时正式确立下来。首先,萧何在攻破咸阳时收取了秦朝的部分馆藏,开启了接收前朝藏书的历史。其次,自汉初颁布求民间遗书的诏令,各代都有鼓励献书的政策,并采取积极措施将投献书籍组织收入馆藏。其三,汉成帝派遣陈农在全国范围内广求书籍,虽无直接证据,但以历代求书的史实推测,陈农求书应是汉王朝第一次派遣专门官员到地方购求书籍以充实馆藏的活动。其四,汉武帝时置写书官,开创了以誊抄来完善补充官府馆藏的先河。西汉奠定了中国古代官府馆藏访求工作的四大主要方式,且东汉延熹二年始置秘书监,统管典籍藏书之事。自此以后,无论是唐宋盛世,还是南北朝乱世,政府都十分重视官府馆藏及其访求,通过各种途径开展访求,并将其作为一项长期性、制度性的工作保持了下来。
3 古代官府馆藏访求方式多样
3.1 接收前朝庋书
官府藏书的来源很多,但主要有两方面,一是接收旧朝秘府所藏,二是由民间(包括藏书家)征求所得[4]。前者即我们所说的接收前朝庋书,也即新王朝(胜利者)接收旧王朝(失败者)的官府馆藏,由此昭示旧王朝的正式灭亡,也宣告新王朝对旧王朝的合理继承。商收终古所出夏之图法,周藏向挚所载殷之图法,实为收书之肇端。后自秦末萧何“收秦丞相御史律令图书藏之”[13]。1612以来,各朝都曾接收了前代馆藏。曹魏曾收袁绍等的藏书,又设秘书令管理馆藏。自东汉置秘书监以来,收得图书得到了妥善保存与有效利用。及至晋朝代魏后,囊括三国,建立起了统一馆藏。到南北朝时,官府馆藏再次分散,并在政权更替时融合。刘裕攻破姚秦,收其藏书;北魏道武帝灭后燕,得其图书;西魏收梁元帝江陵焚书遗存四千卷;周武帝灭北齐,得书五千卷。南北朝时期,图书作为战利品被收入馆藏,以此来宣示胜利政权在乱世之中的强大肌肉。及至隋代结束乱世,馆藏也得到了统一,但是隋末政权动荡,官府馆藏再次分散。后李唐陆续消灭割据势力,顺利接收隋代藏书,官府馆藏又得以统一。到五代十国后,宋朝接收了各国馆藏,后蜀与南唐最为重视藏书事业,两国藏书也使宋初馆藏大为完备。唐宋两朝接收了割据政权的大批藏书,官府馆藏在大一统政权的保护伞之下茁壮发展,但中晚期的社会动荡又使之受到损耗。金亡北宋后,元灭金,北宋藏书遂归于元,及攻克南宋后,悉收得天下之书。到明初平定大都“大将军收图籍”[14]送回南京后,元代藏书又归于朱明。明亡后,官府馆藏中除毁于甲申之祸的部分,其余尽归于清人。王朝初年所收藏书的质量与当时的社会环境密不可分,南北朝时虽各朝大都接收了前代藏书,但是图书质量低,数量少,至于宋元明清四代,则宋代馆藏中的诸多精品在明朝时仍可见,明内府藏书也传至清代。至于一代之中,也偶有馆藏的收集与转移。南朝梁元帝“收文德之书及公私经籍”[15],将馆藏转移到了江陵。唐末黄巢之乱后,孙惟晟占据官府馆藏,秘书省提出将馆藏“付当省校其残缺,渐令补缉”[16]。这是南朝和唐末战乱导致的特例。官府馆藏在历代王朝更替中得到传续,虽在统一政权的集中管理与割据势力的分散典藏中来回切换,但中华文化的优秀成果最终得以系统保存,很好保持了民族文明成果的完整性。
3.2 吸纳士庶献书
吸纳士庶献书是从政府下令献书到接受投献图书的整个过程,共分为三步:政府求书,藏书家献书以及审核图书,收入馆藏。诏求献书有三个重要原因:一是补充馆藏的直接要求,二是通过完善馆藏来巩固统治的根本目的,三是编修史书、校勘馆藏与编制目录的客观需要。汉以前的献书以朝贡上呈地方档案为主,不成体系。至汉朝建立后,曾多番求献,到武帝时又“开献书之路”[15],遂使官府馆藏日渐完备,为刘向、刘歆父子编著成《别录》、《七略》奠定了基础。东汉初期,又大开献书之门,于是“负帙自远而至者,不可胜算”[15],官府馆藏从王莽之乱后恢复过来,并为班固编著成《汉书·艺文志》提供了保障。早期的献书很好地弥补了馆藏的不足,为编目、校勘工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对中国校雠学说的形成与发展有极为重要的影响。在乱世之中,北魏孝文帝也曾下诏求献图书,并加以优赏。南北朝的纳书工作不仅使得官府馆藏得到了补充,更使得优秀的汉文化深入各族,促进了民族大融合的进程。到隋代统一后,经济恢复,牛弘“请开献书之路”[15],馆藏由此不断充实,嘉则殿藏书达到远超前代的三十七万卷。五代时期,后唐庄宗首开以官爵奖赏献书的先河,极为重视馆藏事业;后汉,司徒诩奏请开献书之路,可惜因政权动荡无疾而终;后周世宗注重文教,广纳献书,并多加奖励。五代虽战争频仍,但各国大多重视访求,以期通过官府馆藏来凝聚统治力量,维护政权稳定。宋朝更是代代都曾下诏求书,并通过完善奖励机制来鼓励献书。到明代结束蒙元统治后,随即“诏求四方遗书”[14],希望通过完备的馆藏来支持文教事业,恢复汉民族文化的正统地位。到清初修明史时,顺治、康熙曾多番求书,但由于民族矛盾而效果不佳,乾隆初曾命地方官员“采访近世著作,随时进呈”[17],后四库全书开馆,更是大力倡导献书。下诏求献图书虽是官府主动采取的访求方式,但是主要依靠藏书家的投献,通过调动士庶献书的积极性,促进了图书事业的发展,并加强了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交流,活跃了政治氛围。但除主要靠藏书家投献外,政府也曾利用过国家权威直接索求藏书家藏书。如南宋绍兴十五年,官府曾取“赵明诚家藏《哲宗皇帝实录》进缴”[18],靖康之乱后,宋代官府馆藏几近凋零,直接取索赵家所藏实录只是非常手段,并非一贯措施。
3.3 求购民间遗书
吸纳献书多有局限:一是藏书家不愿献书,“清俸买来手自校,子孙读之知圣道,鬻及借人为不孝”[19],藏书家更注重图书在族内承续而不愿外传;二是投献伪书会造成官府馆藏的淆乱。而接收前朝馆藏只是一时之策。所以历代政府多进行购书以补充不足。自汉陈农求书后,在南北朝时,萧梁最为注重馆藏,经武帝、元帝多番访购,秘府藏书最多时有十万多卷,为南朝之冠,成为南朝图书事业最兴盛的一朝[20];北魏宣武帝时,也曾重金购书以充实馆藏,并取得了良好效果。虽然南北朝社会动荡,但是萧梁与北魏的访购工作很好体现出了政府对馆藏的重视程度之于访求开展的影响。及至隋朝一统后,牛弘即“请分遣使人,搜访异本”[15],通过政权的“天威”与奖赏的“微利”访求图书以完善馆藏。唐初,曾多次购求图书以支持修史、校勘工作;中晚唐的购书则可用“顽强”二字来形容,动乱后的君主们不仅没有忽视馆藏,还积极采取各种方式来恢复馆藏。肃宗、代宗两代曾多次购求图书;广明年间,黄巢为祸,僖宗“即行在朝诸儒购辑”[16]补全馆藏。因战乱而开展的购书,难度最大,责任最重——乱后购书十分困难,但是求购不及,就会导致图书失传,造成文化事业的损失。到五代十国,南唐定基金陵时就曾重金悬赏遗书,重视图书事业,遂使馆藏居十国之先,南唐虽小,但藏书不少,这有赖于长期的购书工作。北宋初,曾多番诏购遗书,以补充馆藏的缺陷与不足。靖康之乱对宋代馆藏造成了沉重打击,需要多途径加以补充,在商品经济发达的南宋,购书成为最主要的方式。到明永乐初,太宗命礼部尚书郑赐派人购书,“勿较值”[14],有效地补充了官府馆藏,并保障了《永乐大典》的编纂。清代,顺治十四年派官购求民间遗书,是清政府正式求书之始[21],乾隆年间编《四库全书》,其中也收录了购于坊肆的通行本。购书并不具有收书与纳书那么强的政治性,更多的只是一种经济行为,但是能有效补充收书与纳书的不足,而且多由政府委派专员到地方进行,对官府图书馆事业的发展有重要的推动作用。
3.4 誊抄官私藏书
誊抄官私藏书即由书手抄写借到书籍以及对残缺馆藏进行缮写,通过抄录保证馆藏质量与数量。在印刷术出现之前,抄写是最直接的创造图书的方法,也是完善官府馆藏最重要的途径。在20世纪发掘的河南安阳和陕西岐山的商周遗址中,先后出土了近3000和近200片有字甲骨,此即商周时期的贞人与史官等的创造。后随着帛与纸先后作为书写载体,抄写的作用越来越突出。汉武帝时,就因“书缺简脱”而“置写书之官”[22],通过抄写以完善馆藏。到南北朝时,梁朝就开展过多次馆藏抄写工作;后赵石虎也曾命人抄写石经,以完善馆藏;北魏时高谧曾“奏请广访群书,大加缮写”[23],有效完善了馆藏,间接为孝文帝改革作出了贡献。南北朝时期动荡不堪,通过诏献与购求来访求具有一定难度,抄写就成了十分重要的途径。到隋开皇年间,曾选拔书手“于秘书内补续残缺,为正副二本”[15],后又开展了多次抄写工作,使得馆藏副本数量极大。在隋末动荡后,仍有不少藏书保留下来,可见抄书对于补充馆藏作用甚大。及至唐贞观中,也曾选拔书手进行抄写工作,至于秘书省等处编制内书手则超过二百人;唐开元七年,“诏公卿士庶之家,所有异书,官借缮写”[16],写成后玄宗令百官观书,都惊叹书籍之广,由此也可见抄写成果的丰硕。庞大的书手团队与长期的抄写工作使得唐代馆藏的数量与质量得以有效保持,成就了官府馆藏写本书的黄金时代。虽然唐宋后印刷术有所发展,但是抄写工作并未终止。宋雍熙元年,就曾借民间藏书“写毕还之”[5],此后各代都曾借书抄写以充实馆藏。及至明永乐年间,曾编纂并抄写《永乐大典》,选拔国子监生等抄得共两万余卷,后嘉靖末期又抄得一份副本。此后明代臣子中虽有如邱濬等重视馆藏建设者,但是由于君主的忽视与秘书监的缺失,使得抄写等工作并未得到有效展开。嘉靖十五年,徐九皋便提议借士庶藏书“送官誊写,原本给还”[24]以完善馆藏,这一提议在馆藏紊乱的明代是很有必要的,可惜没有执行。甚至在清代《四库全书》编纂告成后,虽以“聚珍版印行百馀种”[25],但仍以抄写为主,约抄得二十万册,藏于南北四库全书七阁,抄写人员“共三千八百二十六人”[17],抄写工程规模浩大,历时长久,使得清代官府馆藏达到中国古代的最顶峰。印刷术的发明使得中华文化的发展向前迈了一大步,但是在重士农轻工商的封建社会中一直没能得到较好的技术提升与推广,无法通过印刷来获得稳定的高质量馆藏,抄书也就成了保证馆藏质量的必要途径,也是访求工作的一个重要部分。
3.5 其他访求方式
一是求借于“外国”。在政权割据的时期,官府馆藏随之并存。南北朝时,北魏孝文帝深刻认识到只有融入汉文化,才能更好地维护统治,所以十分重视官府馆藏,以推行汉化改革。北魏太和、南齐永明年间,孝文帝遣使向南齐借书,虽然南齐中有王融等开通之人,但还是没有借书给北魏。孝文帝借书于“外国”的方式在古代由于中国的图书事业长期领先于世界而在大一统时期不具有太大可行性,但为后世采访提供了新思路。中国图书事业的发展需要保持开放的文化心态,积极与世界各国各民族进行互动交流,“取其有益于己者”发展之。
二是抄没于犯官。中国古代官员多有藏书习惯,如果犯重罪被抄家后,藏书则进入官府。明朝严嵩被抄家后,所藏“书籍共八十八部,计二千六百一十三本”[26],其中绝大多数还是保存完好的宋版书,还有字帖、书画等三千余册,都有效补充了明代官府馆藏。清代巨贪和珅被抓后,家产中“文房库笔墨纸张字画法帖书籍未计件数”[26],但应不在少数。丰富官府馆藏并不是抄没犯官藏书的目的,官府馆藏的访求也并不依靠抄没犯官,但不能否认其使官府馆藏得到了完善的事实。
4 古代官府馆藏访求机制完善
4.1 设置专官管理访求
史官自设置以来便兼管访求,但非专任,汉以前之輶轩使则有访求之实而无其名。汉成帝正式遣陈农求书,此后历代求书多派官主管,但主要是他官兼任,并无专职。到盛唐时,这一情况有了转变。“开元十二年,太子中允张悱充知搜访书画使”[27],其职责虽然侧重搜集名画,但访求图书也是其工作内容。访求专官出现于开元与当时的社会状况密不可分,当时国内环境稳定繁荣,统治阶级重视图书事业,促进了访求专官的出现。到文化和经济更加繁荣的宋代,政府更是认识到由秘书监(省)专门负责访求的重要性。宋政和二年,赵存试提议“取访遗书,乞委监官总领”[18],访求由秘书监专门官员负责,提高了访求效率,促进了宋代馆藏的发展。到绍兴十五年,王曮上奏:“宜以求书之政令,命以专行”[18],高宗命秦熺以秘书省提举的身份专职访求工作,使得秘书监正式完全负责官府馆藏全部工作及全部流程,直接推动了南宋官府馆藏的恢复与发展。到明清两代的访求,在中央由翰林院与文渊阁总掌其事,在地方则有提学道与学政官负责具体事宜。图书事业部门专官管理访求,是对秘书监(省)作为国家图书事业管理部门发挥各项职能的肯定,有利于访求的有效开展。
4.2 采取奖励促进访求
图书作为一种商品,具有其价值和使用价值,且藏书者并无义务必须将藏书贡献给国家。所以政府通过奖励来推进访求,奖励机制有两大作用:一是保障访求顺利展开,调动藏书者献书、借书的积极性;二是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形成妥善保存书籍的社会氛围,不至于因官府馆藏的损毁而造成民族文明成果的整体流失。譬如隋初献书就曾以“每书一卷,赏绢一匹”[15]作为奖励,隋代馆藏质量之精良,与吸纳献书有着直接的关系。到更为注重官府图书馆事业的赵宋,则对最终收入馆藏的图书,“一卷,给千钱”[18],在“钱荒”的宋代,“千钱”补偿可谓不菲,这极大激发了献书者的热情。而且投献多者更有当官资格,“量才试问,与出身酬奖”[18]为普通藏书家们提供了转换阶层的途径,间接维护了社会环境的稳定。丰厚的奖励使得两宋馆藏一直保持着较高质量。到清乾隆年间,为编纂《四库全书》,更是大力倡导献书。对于鲍士恭、周厚堉等献书多者,赏赐了《古今图书集成》或《佩文韵府》这些大部头的书籍。这无疑大大调动了时人献书的积极性,使得《四库全书》的编纂建立在坚实的馆藏基础之上。奖励机制抓住了藏书家或求名、或求利的心理,推动了访求的全面顺利进行。
4.3 通过审核监控访求
审核机制,是为了避免有人投献伪书,造成官府馆藏淆乱,而经图书部门专业人员审定投献书籍是否所需,再直接退还或抄后返还,或是给予补偿后直接收入官府馆藏的整个系统过程。伪书的存在使访求成绩因文献质量问题而大打折扣,也对学术研究造成了巨大的影响,所以勘判投献书籍真伪就成了控制访求质量的一项必要措施。两汉刘向、班固整理官府藏书而成《别录》与《汉志》就是对访求所得图书进行审核整理而编著成的清单。到宋代献书,则将访求图书质量与奖励机制赏格进行捆绑,“如实系缺书并卷帙全备者,方许计数推赏”[18],投献书籍需要通过审核才能入藏并给予奖励。这一机制使得宋代馆藏质量尤为精良,聚集了许多民间精品,使历经唐末与五代战乱的官府馆藏得到了较好的恢复与发展。审核机制虽在元明时由于官府馆藏的不受重视而未得到良好体现,但到清代《四库全书》纂修时,又发挥了重要作用。清高宗特地要求地方将访求书籍进行整理后再报送中央,还设置了“校办各省送到遗书纂修官六”[17]38人,专门审核各地呈送书籍,通过后才收录进《四库全书》。审慎对待投献书籍,能够有效减少献书者为贪图奖励而投献低质量图书的影响,是控制官府馆藏访求质量的一项重要措施。
4.4 编制目录指引访求
访求图书并不是盲目进行,而是求取缺书,这就需要有目录作为依据。王俭《七志》与阮孝绪《七录》都是根据《七略》等前代书目编制的佚书目录,皆可作为访求依据。著录于《隋书·经籍志》中的《魏阙书目录》也被认为是北魏访求的求书目录。及至宋太宗求书时,以《开元四部书目》为依据,极大方便了献书访求的进行。开元时期是宋以前官府馆藏最为完备的一个时期,《开元四部书目》对宋代馆藏的恢复与发展有很好的衡量作用。到南宋绍兴年间求书,还将目录“镂板降付诸州军,照应搜访”[18]2830,提升了访求的针对性,极大推进了访求的顺利展开。此外,明嘉靖十五年,礼部“命翰林院查秘阁所贮书籍,有无缺遗不备之处,备开书目”[24]4,由中央和地方各级衙门与学政官联合访求,各有专责。清代乾隆年间,则对编制访书目录提出了新方法,褚廷璋认为应“于各州县志人物传内摘取所著书名,饬各该州县官访购”[28],既按目求书,又符合郑樵提出的“因地以求”的求书之道,使得访求工作得以顺利进行,展现出现代图书馆根据自身发展定位与馆藏目录并结合出版情况来开展采访工作的雏形。由此可见,按目求书既是古代访求的一大保障机制,也是值得现代图书馆继承与发展的优良传统。
4.5 构建理论指导访求
黄宗忠指出:“要建立一个有价值的馆藏……要有正确的、科学的文献采访理论作指导”[29]。经过历代访求工作经验的积淀,宋代开始出现访求理论。“秘府所无者甚多,是求之道未至”[30],郑樵反思造成官府馆藏有限的原因是访求不到位,认为访求工作必须重视从民间访求图书,注重访求方法,拓宽访求途径,因此他在《通志·校雠略》中郑重提出“求书八法”,“一曰即类以求,二曰旁类以求,三曰因地以求,四曰因家以求,五曰求之公,六曰求之私,七曰因人以求,八曰因代以求”[30]。郑樵的访求理论是在提炼历代访求经验的基础上,结合当代官府馆藏的实际情况,不断思考与总结的产物,这既是总结性的成果,也是开创性的理论,为后世访求提供了指导。此后古代访求理论得到了不断完善与补充。如明代祁承与清代孙庆增和叶德辉都有关于访求的论著。虽然这三者阐述的都是私家藏书访求理论,但都是在前代访求经验与理论基础上提出的,而且和郑樵的“求书八道”一起,为现代文献采访学积累了古典理论基础。科学的理论是推动实践发展的不二法门,在不断发展的访求理论指导下,宋、明、清三代访求工作的水平呈现出逐渐上升的趋势,并在《四库全书》编纂访求时达到了最高水准。
5 结语
中国的图书馆事业不是空中楼阁,而是建立在悠远、雄厚的理论基础与实践基础之上,也正是有了古代图书馆工作的开拓、积累与沉淀,才有了现代图书馆事业的辉煌。宏观上系统研究中国图书馆的历史,有利于探索和揭示中国图书馆发展的规律,促进现代图书馆事业的进步;微观上聚焦考察图书馆工作的开展,则能对现代图书馆工作的发展与完善提供更具针对性的启示。古代官府馆藏访求源远流长,上至商周,下沿明清,与悠久的官府藏书事业相伴相随三千余年,在长期的具体访求工作中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形成了一套相应的理论,经由历代传续,不断丰富完善,逐渐血肉充实,形成了完备的体系,其也理所当然地成为古代图书馆学(校雠学)不可或缺的一个部分。虽然随着科技的进步与需求的变化,图书馆文献采访的对象、原则、方式、选择标准、信息获取、处理与传递等方方面面都已发生了重大变革,但有继承才有创新,挖掘并继承古代文献采访知识与智慧仍是我们传承古代图书馆学思想精髓的一个必要环节。
(来稿时间:2017年3月)
1.肖东发,袁逸.略论中国古代官府藏书与私家藏书[J].图书情报知识,1999(3):2-6.
2.龚蛟腾.中国图书馆学的起源与转型——从校雠学说到近现代图书馆学的演变[M].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3:17.
3.吴慰慈,刘兹恒.图书馆藏书[M].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3:10.
4.周洪才.历代官府“求书”概述[J].四川图书馆学报,1989(1):69-72.
5.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M].北京:中华书局,1979:571.
6.蒋永福.图书馆学基础简明教程[M].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12:76.
7.王世伟.应重视图书馆的文献采访[J].图书馆杂志,1998(2):4-6.
8.姚明达.中国目录学史[M].严佐之,导读.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159.
9.瞿嘉福.藏书厄运录[J].宁波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1990(1):97-106.
10.吕不韦门客.吕氏春秋全译[M].关贤柱,廖进碧,钟雪丽,译注.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08:418-419.
11.春秋公羊传注疏[M].公羊寿,传.何休,解诂.徐彦,疏.浦卫忠,整理.杨向奎,审定.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1.
12.李更旺.秦代藏书考略[J].图书馆学研究,1983(1):119-124, 99.
13.司马迁.史记[M].颜师古,注.司马贞,索引.张守节,正义.北京:中华书局,2000.
14.张廷玉.明史[M].北京:中华书局,2000:1567.
15.魏徵.隋书[M].北京:中华书局,2000.
16.刘昫.旧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2000.
17.萧一山.清代通史·卷二[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
18.徐松.宋会要辑稿[M].刘琳,点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
19.来新夏.中国古代图书事业史[M].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03:109.
20.张莹.魏晋南北朝时期梁朝图书文化事业[J].津图学刊,1999(2):80-86.
21.来新夏.清代前期的图书事业[J].社会科学战线,1986(3):333-340, 215.
22.班固.汉书[M].颜师古,注.北京:中华书局,2000:1351.
23.魏收.魏书[M].北京:中华书局,2000:507.
24.龙文彬.明会要[M].北京:中华书局,1956.
25.赵尔巽.清史稿[M].北京:中华书局,1976:6264.
26.佚名.天水冰山录 //中国历史研究社.明武宗外纪[M].上海:神州国光社,1951.
27.张彦远.历代名画记全译[M].承载,译注.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09:105.
28.中国历史第一档案馆.纂修四库全书档案[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39.
29.黄宗忠.文献采访学[M].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1:3.
30.郑樵.通志略[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7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