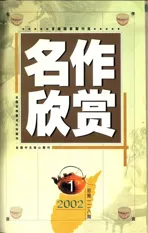文学写作与“伟大的心灵”
——“文学阅读与通识教育”研讨会发言节选(中)
2018-01-28王晓明,童世骏,汪晖等
时 间:2017年10月29日
地 点:华东师范大学
主 办:华东师范大学教务处 华东师范大学对外汉语学院
主 题:“文学阅读与通识教育”研讨会
主持人:王晓明
嘉 宾:童世骏 汪晖 陈思和 贺桂梅
王晓明:现在请第一位发言人、华东师大哲学系教授童世骏。
童世骏:我主要讲文学在通识教育当中可能起到的作用,而且是从哲学角度讲。所谓讲故事和讲道理之间的关系,现在比较多的是一种政治话语,讲好中国的故事,讲好改革开放的故事,把讲故事看作是我们的宣传、交流,包括国际传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方式。讲故事当然不只是为了讲故事,重要的是讲道理。
我自己也是觉得讲故事往往更能讲清道理,我举两个例子。改革开放的道理,比方说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形成一个良好的人际关系。我见过两个文学的文本,一个是《我主沉浮》,一个是《谁能让我》,后者在《人民的名义》里火了一下,新世纪初出版的小说《我主沉浮》更有意思。改革开放充满复杂性、艰巨性,个人利益原则和改革开放的动力是什么关系,利益和价值、荣誉和理想、原则和规则、讲正气和政治都是很复杂的关系,我觉得在这本小说里面有比较好的反映。让你思考比较复杂的关系,后来《人民的名义》是比较简单、概念化的。
我刚才讲的这些复杂的关系,我们做学术的、做理论的可能也在思考,也在研究,但是就没有像小说那样集中,那样清晰,那样发人深省。还有一个例子,铁凝的短篇小说收在她的作品集里面,讲一个送水的农民工给一个二三线城市的富家女子送水过程中的一些感受、一些纠结。最后的结局就是因为停电还是什么把送的水从一楼抬到楼上,送进家门,那时候嘴巴很干,肚子疼,当然前面也有过程,想打扮得体面一点,能够像一个城里人的样子,学得比较有礼貌,会说“请、谢谢”。但是到了家里,送进去以后肚子有点不舒服,要求喝一口水,女主人把手指向了水龙头,这时候他身上带了一把假的枪,用来给煤气点火,他用枪胁迫女主人,最后被抓走了。
这样一个故事可以作为改革开放以来的人际关系的一个很好的分析文本,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基于利益、认同、价值,在什么样的情况下是和谐的,什么情况下是不和谐的。基于价值、认同的和谐或者不和谐,基于利益的和谐或者不和谐,有哪些区别?我自己觉得是可以作为一个很好的分析文本。
讲故事往往更能讲清道理,也可以用来理解为什么那么强调,特别是对外宣传的时候讲中国模式可能太抽象或者太有预设,甚至会引起不少人的反感。但是讲故事,在故事里面体现一些道理,效果会比较好。
第二,听故事往往更好讲理。讲故事的主体还是讲的人,要实现这个效果还是取决于人家听不听,一个是听得到、听得懂、听得见。我们曾经说讲理,更多一层意思是听理,讲故事最重要的也是为了让人听故事。听故事往往更能让人讲理,跟谁比呢?跟抽象的理论论证、抽象的理论表述比,这个我是受一位美国哲学家罗蒂的影响,他在多少年以前已经预见特朗普这样的人会当选,他被认为是最有远见的哲学家。他跟他的老师有多年的争论,他的老师强调论证,罗蒂就觉得论证实际上不起作用,重要的是叙事。讲文学和通识教育,我一下子想到罗蒂,罗蒂会说通识教育最重要的形式是文学或者哲学。他虽然是一个哲学家,但他是在比较文学系做教授,他最有名的几十年都一直在论证文学会提高人的想象力和敏感性。如果简单讲,他有一个观点,讲我们所谓的正义,像罗尔斯这样的会从哲学思想论证,只是更大范围的忠诚,忠诚是对特定共同体而言的,跨越不同的特定共同体,但是他说其实正义无非指的是一种更大范围内的忠诚而已。举个例子,比方说我们讲动物权利,动物权利的主张把正义从人类的范围进一步扩大到有感情的生命体范围。他说这看上去是普通主义的观念,是原则性的观念,实际上仍然是一个人类中心的思想。如果有动物法,其实我们在高校里面管理的时候也是这样,动物发生传染病危及人类,措施很简单,就是杀尽。还有个观点,不能强迫不能使用酷刑,你是从普遍的原则引出这样一个结论,现实很难有这样的结论。但是读了文学作品以后,提高了对于陌生人也会痛苦的想象力,有了这样的感受,就会去同情原本不认识的那些人。
讲清道理和让人讲理讲故事确实有它的优越性,但是不能只靠故事,这是我哲学的立场,也是我跟罗蒂观点的区别所在。确实故事有很大的优越性,我们现在讲中国梦,讲精彩人生,其实都是讲好中国故事,都是在强调讲故事往往更能讲清道理,听故事往往更让人讲理,但是不能只靠故事,还要靠道理或者说阐述论证道理的那些部门。因为故事有一个好坏的问题,这是最简单的,你判断这个故事是好的还是坏的,是主张正义还是反对正义的,让人更残酷还是让人更有同情心的,当然你也可以说罗蒂肯定会说这个判断也是因人而异,因共同体而异的,但是毕竟现在那些理论已经凝聚了多少代人的智慧,是现如今不太用的。论证当中已经充满了叙事的成分,这是从罗尔斯的角度来讲,他是一个技术性很强的、很思辨的哲学家,即使很思辨的哲学家,他的论证已经有叙事在里面。讲故事为什么讲道理,其实讲故事里面也有讲道理的成分,因为讲故事是邀请观众来分析我的一些预设,我在讲故事过程当中是不是顺利,是不是流畅,是不是能够得到呼应,其实也是把我的见识和观众的见识进行平衡,也是一种反思的平衡。最后达成了结论,就是我把这个故事讲下去了,听众把我的结论也能够接受下来,最后达成了一种重叠共识。这是后形而上学时代的论证方式,所以讲故事之所以能够讲清楚道理,让人讲理,不仅仅是叙事,而且是有论辩、有思辨在里面。
举个例子,我以前也谈到过,《天下无贼》之部电影里面,主要讲述刘若英演的女贼和刘德华演的男贼之间的故事。一开始说要偷傻根的钱,但是折腾一段时间以后,女的说不偷了,男贼问女贼咱们都是坏人,你不要以为我们是谁,我们是坏人,怎么就不偷了?女贼就跟他讲说我怀了你的孩子,我想为他积点德。这样一种叙事其实是一种论证,在我们这个时代,你要论证一个道德的结论,其实你要援引的不再是宗教性的,不再是一个大的形而上学的体系或者说是一个古老的传统,其实是每个人内心的情感,其实是使得我们能正常生活的基本的东西还在。尤其是当你想到家庭,想到你下一代的时候,那么这样一种设想,它是一种想象,把听众、读者生动地邀请进来,一起来分享的一种场景,最后形成一种共识,观众会觉得女贼的回答是有道理的,这个道理在什么地方呢?当然哲学家可以做好多论证,但是每个人都觉得这个是很有道理的。
这样一种道理只靠讲故事是行不通的,还是要做分析来把它提炼出来。我甚至觉得这种设问要比罗尔斯的原初状态更有说服力。一个再糟糕的人,如果问他这样的问题,他基本上不会做出非常离谱的回答,这就是人类还有希望的理由,这就是我觉得儒家重视生命、重视家庭传统的力量。
汪晖:现在的通识教育是一个新词,也就是近十年才流行起来的,我觉得现在中国最成功的通识教育构思基本上来自于师范教育。我们看民国时期主要的人文教育设想,因为大学改革没有一个模式,北大有就跟着北大来。但是师范学院从师范学校开始就有一批人在做这个研究,你看1923年做休学制的时候云集了一批人,里面有技术学校,大学没有,但是师范是在里面,师范学校、师范专科学校,为什么?道理是什么?我觉得是因为师范学校、师范专科学校是要给中小学培养老师的。我还是习惯于叫人文教育,我并不太用通识教育。这个设想你看一下历史的脉络就知道了。当时为什么做,一个是公平教育,因为师范从孩子抓起,同时要让他成为社会的成员,不仅是公民,从政治的角度、国家的角度界定的,是有基本的素养,而且要有互相交流的可能性,共通的基础。
通识教育在美国叫博雅教育,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因为美国的大学分工越来越细化,需要在一二年级用博雅教育来补救。这当然是现在社会,我们都知道美国说过现代性里面最核心的矛盾,是专家文化和大众之间的疏离。我们看通识教育也好,博雅教育也好,它希望沟通专家,它是克服现在社会自身的专家化,即专家说的话谁也不懂而带来的主要问题。可以重视一下,应该重视自己当年形成的传统。教育改革当中,把很多师范院校都改掉,我是不以为然的,因为这里面凝聚了很多特别好的经验,特别是教学课程的设置。上午说作品阅读作品课,非常多,师范院校里面基本上三年都有作品课,这是跟一般大学教育不太一样的,但是这个教育的模式我觉得是应该肯定的。
第二,人文教育。人文教育的形成可能比现在大学文学课的形成略早一点,大学文学课有一百五十年。启蒙教育、文艺复兴基本上是宗教世界观和宗教体系发生变异、发生冲击的结果,人不再只是跟上帝有关系,人和人、人和自己的世界、人和自然通过一系列关系的重新界定,来理解人本身和人的世界本身。比如说刚才童老师讲到的正义,不是从上帝那儿来的,要重新加以界定。这些都是人文命题得以产生的最基础的条件,因此人文的概念也不同于我们今天把人文和科技区分开来,人文就是关于整个世界的知识。像达·芬奇这样的人物,一直到康德,都是全人,可以说他们既是科学家、艺术家,同时还是各个领域的可能是各个方面的通才性人物,这些人物就是这个世界观发生重大变异的一个结果。
但是在我们中国,人文教育从开始形成的时候就不是在欧洲宗教世界观的意义上,就像我们不是宗教的,至少不是基督教、伊斯兰教那样一个社会。启蒙运动、新文化运动、新思想运动,人文相对自主独立性的时候,常常是和19世纪居于支配地位的科学世界观对话,这要求自身不完全受制于自然力,人不是一个受自然力支配的人。20世纪20年代科学论证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那时候把文学、哲学、心理学变成科学,把这些知识从自然知识中摆脱出来,在新的学科体系下建立自己的位置。现在文学的位置跟物理、数学、化学是一样的,有自己的学科地位。这样一来,中国的人文教育从诞生的时候就有一个先天的局限性,它为了要跟自然的知识相对抗,也带来一个限制,就是我们对自己生存世界的理解有局限性。我们讲文学教育在这个意义上就变成不再是通识教育,也不再是一般的人文教育,而是变成专业教育。所以现在把文学当成专业,而不是用来理解整个世界和理解人自身的一门学科。
我觉得这是两个局限性。我们生存在其中,我们说局限性的时候不是说简单打破,这种局限的形成总有它的原因,否则会被另外一个东西裁制。我在清华大学才知道怎么被工科裁制,你跟他们说,一定要说你们不懂我们,我们跟你们不一样。为什么你们说的东西我们不能插话,我们说的东西你们都可以乱说,类似这样,这是它的合理性。童老师说故事,这个道理是这样来的。但是实际上我们自己应该知道这是有局限性的,文学是对世界的总体理解,这个部分的局限是很有限的。
我有时候读一些文学作品,今天上午王安忆老师特别提到《战争与和平》这样的作品,它是一个巨大的工程,包括巴尔扎克说写作就是做一个方程式,用这个方程式来理解这个社会,自己从里面分析,要解决方程式。雨果也好,托尔斯泰也好,是全景性描述这个世界。那是被充分激发的时期,在当代的文学里面我觉得这个可能性变得越来越小,我们看一个作品,基本上作家的生活世界就是作品的生活世界,很多状况如此,这个状况在19世纪的文学中是不存在的。19世纪文学都是要去研究生活之外的,比如巴尔扎克要研究葛朗台,研究各色人。当代世界一部分作家的写作往往变成通俗小说,跟通俗文学结合,像19世纪那样的方式似乎是少的。其实文学的经典跟哲学的经典和历史的经典都差不多,都是过去时代人们的生活和斗争的凝聚,完全凝聚在里面,被放在这个位置上。但是文学教育、文学阅读的意思是什么?前两天在清华,我们开一个会,罗伯特讲到怎么理解历史,历史不是自然的,历史是人的活动、生活和斗争、奋斗,到了这儿,它被写在这儿。可是我们看到它的时候它已经死去了,它不是不存在了。后来我举了一个例子,鲁迅的死火,掉在冰窖、峡谷里面,旁边有很多火焰,那是当年的生活斗争、爱和恨,什么都在里面,凝固了。文学阅读是什么呢?就是把这个凝固的死火用我们自己的温暖,或者用我们的技巧和各种各样的方式,把文学的经典和历史当中真实存在过的生活和斗争重新激发起来,把它变成活的东西,变成我们自己生活世界的一部分。对文学的阅读在这个意义上,无论是经典的还是当代的,不可能只是为了一点,一定是重新认识历史和当代世界、认识我们自己的一个方式,这像是要把自己烧毁。现在的人认为人生只死一次,他的意思是我们一生是浑浑噩噩地活着,一生不知道死多少次。不过文学阅读是让人死很多次,是真实的死,你投入到文学阅读当中,像鲁迅写死火一样,温热把自己烧死,在烧死的过程当中重生,变成一个新人,对世界的看法变了。文学在这个意义上帮助我们理解世界,阅读它是提高我们对于过去和现在之间关系的那个再理解。我们想过去的事情,孔子的事情,周公的事情或者谁的事情,那是过去的事情,跟我们无关,可是通过文学,他们变成当代人,变成可以跟我们对话的人。这样的敏感性是文学阅读特别必要的,不仅是文学,我觉得历史、哲学能够有这个创造力、这个敏感性就要从这儿来,而从这个地方来的最起始的感觉,文学阅读是首要的。这是第一点敏感性。
第二个我觉得就是想象力的问题。其实刚才童老师都提到过,因为当代世界的一个问题,比如说19世纪的这些文学,当然不同时期有不同的想象方式,但是我们今天可以知道由于信息、由于媒体、由于这个社会生活的复杂化,比如说我们都承认我们不仅是公民,我们简直就是法的动物,每件事情都是法,法外的世界我们是不知道的。生活世界里面的那些规则告诉我们世界之外还存在什么,我们也是不知道的,即便过去看《星球大战》有惊奇感,现在再看却没有惊奇感了,外部不断地消失,外部不断变成我们的内部。经常有理论家说外部已经不存在了,所以我们的生活和斗争都只能是内部的,不存在外部了。在一定程度上,这是对的,但是也不对。为什么说对呢?这些部分不断被纳入到内部来,但是为什么说它不对呢?不对的原因就是外部总是存在的,只是我们的想象力已经无法抵达这个外部了,我们已经没有能力去想象一个外部了。所以那个大写的上帝死掉了,后来一个个都死掉了,到底那个外部是什么,外部也有,后来就变成了一个规定性,和我们相匹配的规定性。想象力的问题和创造的问题,我觉得是文学世界、文学想象、文学阅读当中特别重要的,要培养年轻人有这样的创造力。所谓的人希望能够只死一次而不是浑浑噩噩,在他的生命当中总是有创造力的,这是非常重要的。
我忽然想到法国的当代哲学家,他说这个世界当中有五个最重要的领域:数学、公理、哲学、爱,还有就是政治。我常常把哲学跟数学放一块儿,把文学跟政治放在一块儿,所谓政治是指日常生活世界每个人都是能动的,这个意义上跟爱的领域是很像的,都是互相激活,创造出新的可能性的意思。政治不只是统治术,政治是创造,每个人都有能力去创造,像新文化运动的时候就有创造,他们要创造新文体,用新的文字、新的方式,这都是对新政治的创立,如果没有这些,20世纪是无法理解的,这是文学在那个时代独特的功能。
这一点也让我想到另外一个问题,最后我说的这句话,我们要不要拒绝一种宿命,文学的时代已经过去了,现在是机器的时代,或者是其他各种各样的时代,因为有19世纪、20世纪,让我们想象文学的威力,恰恰是从文学内部让我们知道一个时代的创造,不是由这些东西决定的,完全是由我们自身的创造力决定的。文学怎么能够形成这种创造力,本身是有特别大的意义。当年我觉得罗曼·罗兰说过一段话,大概在20世纪30年代,他受高尔基的影响,当然对社会主义比较向往,因此他就比较俄国文学和法国文学,他对俄国文学评价很高,但是他特别说到托尔斯泰,也说到雨果。他举了两个例子,他自己做过小学老师,他说我做小学老师的时候我让他们读雨果的作品,我能够感觉到小学生对雨果的作品产生感应和激动。雨果还不只是讲故事,他也说理,看看《悲惨世界》一大段几万字地讲,他的《九三年》完全是政治政论,人生哲理、文学叙述都在里面。后来再读《战争与和平》的时候,他当然是批评法国文学,他当时批评布鲁斯特这些人,说他们完全把人的世界变得内在化,但是他说到最后,转过来了,说当然苏联文学也不是什么都好,也有缺陷,什么缺陷呢?就是对人的内在世界挖掘这方面,他说得很客气,说内心世界、内在世界这个部分的挖掘似乎还有很多需要我们去做的,也就是说人文教育也好,通识教育也好,是要让我们变得敏感、丰富,变得微妙,人和人之间有很多微妙的复杂性,这些东西是文学带给我们最有意思的体验,但是它同时不只是小的,它是能够带着这个创造力把整个时代的感应都放到里面去,有这个感应介入社会生活,同时不失去它的微妙和复杂性,这样一种文学教育就是通识的。在我看来,因为它不会仅仅是专业的文学教育,它可能是历史的,也可以是哲学的,也可以是任何一个类型的。
王晓明:下面请复旦大学中文系陈思和教授发言。
陈思和:对于通识教育,我是深有体会的,因为复旦的通识教育很早,20世纪90年代末就做了。20世纪90年代末我就不做文学了,一直到现在差不多快要退休了,每年都是跟一年级的大学生,而且绝对不是中文系,因为我们规定中文系的人不能听我们的课,都是其他外系的人来,物理系、医科、工科都来上我的课,我讲的是当代文学作品。这十几年下来我自己一直有一个问题,就是说通识教育跟我在中文系上课的差异在哪里?中文系原来有一套规定,把这套规定搬到通识教育里去,面对一批根本不是中文系的学生,而且他们以后也绝对不会从事中文系的工种,这样的同学我要去教他们现代文学史上发生多少事件,有多少社团,文学作品多么重要。我自己对自己一直提出这样一个怀疑,我讲这些给他们干嘛?他们干嘛要听这些东西?
慢慢地我自己在实践当中就摸索了一个通识教育的想法,这个想法不一定对,只是我自己的一个看法。首先我是非常赞成刚才汪晖老师的观点,其实这也是一直盘旋在我心中的,在我看来通识教育也好,博雅教育也好,其实它的核心就是人文教育,这是我的一个想法。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我觉得,我每做一件事都要把自己的道理讲通。我一直在想这个问题,当我们的孩子从读书开始,一直到大学,这个漫长的学习过程当中,他们基本上面对的是三种教育,一种教育是根本不需要学校教育,就是生活教育,生活的教育在日常生活当中不需要学校,他父母、周围的环境会教他的,天冷要加衣服,什么衣服好看,什么衣服不好看,或者走出去待人接物,像一个人丢到山沟里面,必须要生存,也会学会做饭。生活方面的教育来自于生活本身,这个孩子生活经验越丰富,受的教育越多,可能生活能力越强。
第二,孩子要接受的是知识教育。而知识教育就是要学校来教,当然排除自学,自学也是通过教育。小学一年级开始就有一整套教学体系,小学教育、初中教育、高中教育、大学教育,一整套教育体系培养不同年龄阶段的孩子,这些东西包括数理化,包括历史、外语、地理,你不教可能不会,你要通过教学才能互相影响,才能成长。这是今天接受最多的学校教育,也就是所谓的知识教育。
第三种其实是人文教育。我把它定位是一种来自心灵的困惑。一个孩子在小时候,其实也有人文教育,但是我们大家都不觉得。但是慢慢成长到十五六岁的时候,在成长过程当中,在内心跟世界交流当中会产生很多问题,很多有关人性的问题,这种复杂的问题老师是没办法教的,课堂是学不到的,这个是需要另外一种教育,这种教育我界定为人文教育。也就是说人文教育不是针对知识性的问题,不是针对生活性的问题,而是针对你的灵魂,针对你的心灵。人文教育是伴随人的人性成长的,它一步一步往上走,一步一步深入。
今天讲到文学教育,文学教育是这个人文教育当中最基本、最基础或者说最权威的教育。我们今天大学很多所谓通识教育,现在很普遍,有的叫素质教育,有的叫通识教育、博雅教育,等等,其实我觉得归根到底就是一种人文教育。因为它不是为了解决知识问题,不是我们通常理解的理科同学教点文学知识,教点历史知识,也不是说叫文史哲的同学学计算机、数理化,这当然可以,但是不属于通识教育的核心部分,通识教育最核心的就是人文教育。而且不是跟中文系、历史系、哲学系的教育相似的,是凌驾于各个学科教育之上,这样一种针对人的人格培养、人性的成长,针对人之所以为人的教学。这个在国外很简单,因为西方有宗教,宗教可以代替这个。但是像中国,或者现代社会,宗教的力量已经式微了,这种情况下人文教育很自然要取代宗教,我觉得这是高等教育阶段不可缺少的东西。我们今天没有做,今天很多理工科大学往往把人文教育看成是一个知识教育,要懂点文化,懂点知识,懂点写作,像大学语文就是把这个作为教育,我觉得这是不对的。人文教育就是针对人类文明,你上完这门课,你上完这个学期人文教育的课,你走进来和走出去就是不一样,走出去是一个堂堂正正的人,至少是正直的人,理解“人之所以为人”的课,有这样一门课我们的同学就有福了。否则多学点知识,我觉得这不重要,不在人文教育的范畴里面讨论。
为什么讨论文学教育,文学教育不是人文教育的全部,但是是其中最重要的一部分。因为这是陪着人性发展产生的,首先我觉得最能够沟通人性的不是文学,是艺术、绘画、音乐、舞蹈、现代影视等。隶属于文学教育最前面的感性形式,是跟人的某种器官联系在一起的,听觉、视觉、感性,是最接近人性的东西,为什么我们小孩子一开始接受社会化音乐、艺术这样的东西,包括肢体语言,小孩一开始手舞足蹈就是舞蹈的雏形。到了文学教育是第二个阶梯了,需要你有抽象的能力,用抽象的能力理解人性的复杂性。我觉得这是一个绕不过去的话题。
我讲我自己,在十三四岁的时候我读过一本书,这本书一直影响到我以后的所有学术活动。刚刚读中学一年级时,我读了一本巴金的《契约》,这不是他最重要的书,也不是现代最重要的作品,而且当时读的时候不知道是巴金写的,是繁体字。里面写了一个地主吃喝嫖赌,把家里的家产败光了,被家人赶出来了,在外面讨饭偷东西,被抓到监狱里面去,然后装病,最后死在监狱里面了。按照我们一般逻辑来说这是一个坏人,是一个死有余辜的人。但是巴金写这个人物的时候,就用这个人物的儿子,他的儿子也是我读书时候的年龄,十三四岁,这个孩子不知道爸爸犯了错,觉得爸爸为什么老是被人欺负,所以他一直在街上维护他的爸爸,寻找他的爸爸。这样一个细节,当时深深地感动了我,我也说不清楚是为什么,但是那时候就这样一个人物,这样一个倒霉的地主,给我的心灵很大的震动。我就不断幻想,如果这个乞丐出现在我面前,我会施舍他什么,跟他讲什么,脑子里会出现很多样子。后来一直到我长大了,到我后来研究巴金,这跟我后来的人生学术道路有关。这个阅读最重要的是解决了人的同情心问题,因为如果我们现在看到一个蛮横无理的人在打小孩,你同情小孩,这是天经地义的。今天这样的结果完全被认为是自作自受,自己吃喝嫖赌,把家产败光了,是一个败家子,最后变成一个乞丐,这种人在社会上是被人嘲笑的,是坏的典型,可是恰恰这样的人引起了你的同情,这才是真正的同情,是人类不带功利的同情。《悲惨世界》也写坏人,最后一个坏人,人道主义往往对坏人施以同情,而恰恰对坏人也能同情,这样的一个原则,我当时读这本书的感受,与时代主流完全背离,当时就是阶级斗争,都是在讲东坡先生不能怜悯狼,农夫与蛇,要把蛇打死,在这样的教育当中我读了这本书,然后认识改变了。人文教育看上去微不足道,甚至不讲逻辑,跟我们的大意识形态是不一样,但是当触动内心以后,就一辈子忘不掉,这个东西就在你身上长出来发芽了,这就是使人慢慢变成一个自觉的人的最早的启蒙。
文学教育就起到这样的作用,文学教育不讲大道理,就是通过一些形象,这些形象也说不清楚,你可以从这里理解,可以从那里理解,就是这么个模模糊糊的东西。如果有缘分就打动你的内心,作为人性就会慢慢成长起来。文学不是唯一,还有历史,我们为什么读历史,就是把人类几千年的经验拉到我们眼前,让我们看今天的时代。我们为什么读哲学,探讨人在这个宇宙、世界当中的位置,所以文史哲包括艺术,甚至于宗教,我到现在还是认为其实人文教育最高的是宗教,发展到最后人文教育就不是一个理性的东西,不是思辨的,会达到信仰层面。这样一个教育是一个完整的教育,而这个完整的教育绝对不能退回到今天的学科概念,即你必须掌握多少作家的名字,必须了解多少哲学家的经典思想,我觉得这个都不重要,不是不重要,如果当哲学家重要,如果当医生的话就不重要。但是作为医生,作为人文教育,作为人性的提升,我觉得绝对是一种需要的东西。
王晓明:下面请北京大学中文系贺桂梅教授发言。
贺桂梅:其实我非常关注通识教育和博雅教育在中国大学里面的出现,就我的观察来说通识教育这个说法的出现应该是在20世纪90年代后期。那个时候的通识教育基本上就是要求学生在自己的专业之外再修一些别的学科的概论课、通识课。直到最近十多年才开始更多地形成一些独立的通识教育、博雅教育,还有刚才谈到的人文教育的基本理念。
我观察到像北京大学、中山大学、华师大、复旦、清华,都在摸索一种理想的通识教育,也就是说这个改革还在进行中,所以毛尖老师他们做这样一个讨论会,其实是非常有意义的。通识和博雅,强调的是博和通,是让他们一直有一个潜在的对话,对象就是专业化教育。专和通背后有一个古典和现代的差异,因为专业化教育事实上就是现代化教育的一个结果,可以说一百多年来中国现代教育其实每个领域都在朝专业化的方向发展,包括我们的文学教育,最早的时候就出现了文学史教材,大学的文学教育基本上是通过文学史教育完成的,这一百多年我们先学日本、德国,然后学苏联,然后学美国。
总之我认为通识教育、博雅教育这个理念的提出是对一百多年来中国教育专业化、分工化的基本理念的反思和重构。我想把它放到中国的历史脉络里面,刚才汪晖老师也谈到,中国的古典教育其实本身就是一个通才教育,因为古典中国社会其实是没有分工的,而且那个经典是真正意义上的经和典,教育的就是儒家的士,这个士就是要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经典其实是规范性的知识,不仅规范个人,也规范社会,甚至还去规范皇权。所以古典的士是士儒,给了士很高的位置,但是经典教育和未分工的社会机构、教育机构是连在一起的。我们谈通识教育经常听到很多人又开始谈古代士的理想,怎么有天下意识,怎么从个人的修身到天下。我觉得完全搬用古代中国经典教育的传统是不够用的,因为古代的经典教育背后有科举制度,有这样的“学而优则仕”的制度,确实修好了身就可以做官。现代社会面对通识教育也要面对专业化,我自己不认同谈博雅通识教育就是回到经典,而是在更高的层面上沟通经典教育和文学教育的关系。这个背后就是怎么把古代的经典教育和现代的文学教育结合起来。
第二个就是谈到文学,这个文学当然就是现代意义上的文学,我们古代中国的文学其实都叫文,但是这完全是一个西方的产物。同时谈到通识教育的平民和精英之间的分解,其实这个绝对就是一个平民化教育的结果。在19世纪的欧洲最早出现的文学其实是从底层人开始读的,就是工人、妇女,他们有闲暇,而且当时的文学教育就是针对这样的底层人。包括19世纪梁启超他们搞的革命,还有“五四”运动,等等,都有一个这样的观念,即文学要接触的群体是平民和大众社会的主体。所以现在的教育其实有一个特点,刚才汪晖老师讲到公民,而现代的教育大概就是一个国民文学。它特别侧重的就是个人,它特别尊重个人,这个我想可能是跟古代的士的理想是不太一样的。现代的文学是直接跟个人对话。上午格非老师讲的秘密通道,因为是对每个人,日本的评论家就说现代文学的出现适合内在的人,是通识发明的。这个平民化、大众化可能就是现代文学的基本特点。
我自己观察到的一些通识教育和博雅教育,我觉得大多偏向古典文学教育,而相反会忽视20世纪以来的现代文学经验。譬如说像格非老师就教育学生去读《红楼梦》,《红楼梦》可能就是18世纪古典中国社会的状态。事实上我们作为一个现代人可能更接近的经验是20世纪以来的文学经验,所以我其实是很认同毛尖他们开设的通识课程,和其他学校不太一样,他们特别重视20世纪的经验。比如说他们的课程是20世纪中国爱情文学、现代城市文学和现代电影经典,等等,很注重20世纪的经验。作为一个今天受教育的学生,他们其实是已经充分现代化,他们可能跟现代的经验有更亲和的关系,当然20世纪文学经典不稳定,是在一个经典化的过程当中。所以通识教育在讲授或者传授现代文学的时候,其实还有一个再经典化的过程,就是在通识教育的过程当中再对这一百多年来的现代文学进行筛选。这是我讲的第二点,我非常希望通识教育能够更多关注20世纪以来的经验,因为最近这些年传统文化热,在学科的偏向上就是古代文学越来越受关注。好像最近这十多年现当代文学不太重要了,就是人们对现当代文学的经验关注不够。
谈谈文学位置的问题。我们今天怎么来通,怎么来博?应该用文学来通各个学科,首先陈思和老师刚才谈到文学虽然是重要的,但不是唯一的。但是我觉得文学有它不可取代的独特位置。首先文学跟电影、电视剧这种图像文化的差别在于,它们都是艺术,但是文学是用文字,这个文字是一个文明的密码,而且它有最复杂的,像汪晖老师说的敏感性、复杂性和个人性。虽然讲一个故事,可能文学也可以讲,电影也可以讲,但是我觉得文学有可读性,有不一样的意义。这是文学和其他艺术相比的位置和特质。如果和历史、哲学比起来,文学有一个最突出的特点,它是情感的关注,它关注的是人的心、灵性、情绪、感性,文学作品有一个效果,它在感性上打动了你,这个就是哲学可以讲一个道理,也是童老师讲的,讲故事和讲道理的关系。所以相对于历史和哲学来说,文学的优势在于它是一种情感的教育,它会极大地激发人的感性。但是文学又不是一个纯粹的情感教育,比如说跟音乐和绘画比起来,文学还是有价值观的,还是有思想的,甚至接近汪晖老师讲的文学事实上在是重新想象和构造一个世界,这个世界是一个总体性的,所以我就在想我们这些搞文学研究的人来谈通识教育,我们可以设想一个通的方式,就是以文学作为基础,来通历史、哲学,来通人文和社会科学。比如说谈爱情,爱情这个话题是一个社会学的话题,是一个心理学的话题,是各种社会科学都会触及的话题,但是如果立足文学把其他学科都打开来谈的时候,它就不仅激活了文学,其实也把各种社会经验都激活了。他们还谈了一个主题是城市,其实也有相应的,这种设计很有效,可以跟学生的经验发生关系,可以从感性出发,可以到达各个层面。这听起来有点文学中心主义,我只是说可以立足文学而通其他学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