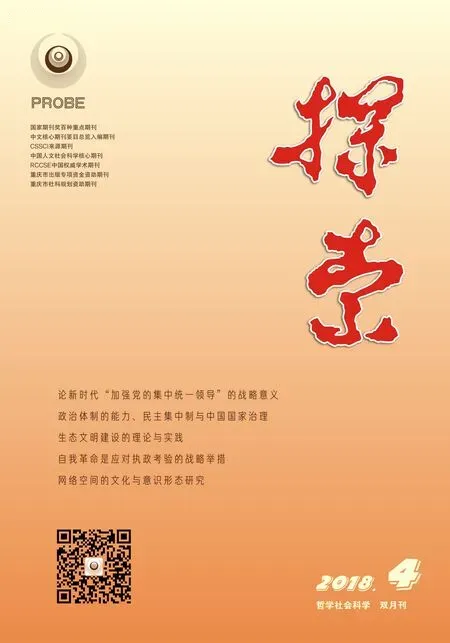“可持续发展”到“生态文明”:赢得生存之战①
——国外学者关于生态文明的释义
2018-01-27韦震
韦 震
(海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海南海口571158)
可持续发展概念的提出是为了使人类免于生态危机的危害,但“可持续发展”的概念也使人对当前环境问题的严重性视而不见。总体上看,生态环境问题仍旧处于边缘地位。“可持续发展”概念的初衷是为了通过激发人类应对生态领域的威胁,厘定生态危机的问题域,廓清生态危机的危害等,使人类能够充分理解生态危机的复杂性,并由此创造一个新的社会秩序,构建新的文化基础,描绘新的生态蓝图。正如保罗·利科(Paul Ricoeur)所指出的那样:这是一个“等待被实现的梦想”[1]xxi。基于此,“生态文明”使人具备反思当下和思考未来的能力。通过生态过程形而上学思维,更使之具备一种为新的全球文明提供文化基础的潜力[2]1-7。
1 可持续发展
“可持续发展”的概念有问题吗?正如迈克尔·雷德克利夫(Michael Redclift)30年前在他的著作《可持续发展:探索矛盾 》(Sustainable Development:Exploring the Contradictions)中观察到的那样:“可持续发展”将“可持续”同“发展”结合在一起,每一部分都有问题,甚至是彼此间的对立[3]15。“可持续”意味着“维持现状”的可能性,给予人坚持的希望。“发展”的概念强调事情的进步。一般而言,“发展”通常会被认为是一个具有积极意义的褒义词。
“可持续发展”的概念具有指向上的模糊性。在《我们共同的未来:环境和发展世界委员会》(Our Common Future:The World Commission on Environment and Development)中将其定义为:“既满足现代人的需求又不损害后代人满足需求的能力。”[4]43“发展”更侧重经济发展。如果依据各国经济发展程度的好坏来进行“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划分的话,那么,“经济好”被定义为“发展好”,但发展的含义远不止如此。即便是发达国家,也依然应该继续保持发展的状态。理查德·诺加德(Richard Norgaard)指出:“历史中演绎着不同的文化与生命的故事。这些故事总是在不断演进,相互交织,或同迷途之人一同消逝于历史的潮流。但现在,故事的主题是无限制的经济增长,关于从拥有越来越多的事物中获取无穷无尽快乐的故事。”[5]1
由此可知,所谓的“可持续发展”绝非仅仅指经济发展的可持续,还指生态保护的可持续,具体指生态保护的维系条件。也就是说,需要综合考量可持续发展的生态基础、在经济发展压力下的可持续性及生态系统的完整性等。
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可持续发展理念本身是邪恶的(malicious)。这个概念的发起者有着最纯粹的动机。其重要性体现在布兰德调查报告(Brundtland Inquiry)《我们共同的未来》关于“如何能够为全人类确保一个更美好未来”的相关论述中。我们需要重新定义可持续性,以使其能够关注生态系统的健康可持续发展,而不是沉迷于以牺牲自然资源为代价来换取GNP的增长。这就是艾伦(Allen)、泰恩特(Tainter)以及胡克斯特拉(Hoekstra)在《供给侧可持续性》(Supply-Side Sustainability,2003)一书中的观点。正如莱斯理·斯克莱尔(Leslie Skair)所指出的那样,新的全球统治阶级看到了他们霸权所面临的最大威胁来自于环境运动及统治阶级自身在应对环境问题上的失败。通过上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国际商会”(International Chamber of Commerce)的操作,他们建立了一个绿色商业网络来定义环境政策,并在1990年建立了“全球环境管理倡议”(Global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 Initiative),目的在于通过自我评估,推广自愿准则。斯克莱尔认为:“大企业通过建立一个可持续发展历史集团,以反对它所遭遇到围绕单一生态危机以及生态运动有威胁性的反主流文化。”[6]206这一新的全球统治阶级,被约翰·珀金斯(John Perkins)称为公司帝国[7]xv。
在研究美国新保守派的崛起在政治上的重新定位时,乔治·莱考夫(George Lakoff)对其重要性进行了相关阐释。他展示了新保守主义战略家有意打造一个连贯的、基于道德秩序的政治意识形态,彼此束缚以确保言论的正确性。支撑这一道德秩序的基础类似于“家长制家庭”(patriarchal family)。寄望于政府不再干涉,就如同成年子女希望他们的父母不再干涉自己一样。它涉及分解福利国家,私有化公共资产,并且消除在市场运行以及它最强大代理上的所有限制。任何社会中的政治和经济事件都可以通过这种语言与话语体系来解决,构建讨论来让所有反对者发现他们自己能够接受这些架构,提供替代选项作为这些新保守主义所提倡的目标的细微修改。在此道德秩序下,人类完成了对自然的征服与统治,自然存在的唯一意义就是为了实现人类的目标。
美国这种新保守主义一直与更广泛的新自由主义运动相一致,且已经成为其一部分,通过促进自身利益,能够在最大程度上服务所有人的自身利益,公共机构会被诋毁为“无效的”和“没有竞争力的”。正如菲利普·米卢斯基(Philip Mirowski)和迪特尔·普拉为(Dieter Plehwe)在《朝圣山之路:新自由主义思想集体的形成》(The Road from Mont Pèlerin: The Making of the Neoliberal Thought Collective,2009)中所指出的那样,成立于1947年的“朝圣山协会”(the Mont Pèlerin Society)在全球范围内廓清了所有的政治和经济讨论议题,旨在通过全球化市场取代凯恩斯经济学及其社会民主议程。
凯恩斯主义议程不仅包括通过收入的重新分配,将金融部门从属于经济的生产部门,以及通过对国有企业施加财政政策以增加政府对经济的参与度等方式来维持充分就业,还包含海曼·明克西(Hyman Minksy)也指出,随着人们对更崇高目标的追求,市场经济的重要性将会逐渐减弱[8]115。
这一切都被新自由主义搁浅。自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新自由主义在转化方面的成功不仅在右翼,更重要的是,前左翼政党接受了新自由主义议程作为行政议程的唯一现实基础。通过维持国家的现状来控制他们自身经济并保护他们的社区不受全球市场的掠夺。尽管这些政策在过去取得了成功,但现在看来具有局限性[9]vi-x。塔基斯·福特普洛斯(Takis Fotopolous)在《新世界秩序行动》(The New World Order in Action,2016)中表明,控制这些左翼政党的新全球化政治阶层已表明他们不能够跳脱出新自由主义框架进行思考,即使在面临希腊国家危机以及全球金融危机时也是如此。正如明可夫斯基(Mirowski)所表明的,只有当新自由主义能够通过诉诸市场,通过所谓“终极生控体”来为可持续发展制定政策,环境问题才可以得到承认[10]334。如果市场不能厘定并处理环境问题,阐释导致环境问题的根本原因,那这些问题将永远无法得到解决,其背后的逻辑是市场的扩张以及通过市场交换定义的经济增长相关性等。“可持续发展”作为新自由主义框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阻碍了人类对生态问题严重性的感知和认识。
2 生态文明和跨文化主义
除“生态文明”的概念外,还有诸多致力于解决我们所面临的生态危机的理念,如:生态社会主义(eco-socialism)、地球民主(earth democracy)、包容性民主(inclusive democracy)以及生态时代(an ecozoic age),“生态文明”的概念作为其中最具包容性的,其积极作用也是最突出的。文明不仅是致力于外部强大民主环境的积极构建,同时也是对生命内在价值的高度认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所有概念都可以相辅相成,共同促进文明的发展。那么为什么环保主义者要与“生态文明”的概念相一致呢?
这背后涉及诸多现实原因,其中最主要的就是中国政府对生态文明概念的顶层设计及积极推广。中国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将在全球生态治理中扮演更加重要的角色。同时,与美国、欧洲或俄罗斯相比较,中国未来受到(包括气候不稳定在内)的生态威胁,比其他大国大得多,因此,在全球生态危机应对及生态治理领域,中国有更充分的理由去表达中国话语、贡献中国智慧、提供中国方案,生成可供其他国家借鉴与参考的生态治理新范式。对此,中国政府一直保持清醒态度,果断采取积极举措。中国正在以惊人的速度制造和安装太阳能电力和风能系统。根据国际能源署(IEA)的统计可知,中国将负责全球40%的可再生能源的增长。2016年,全球太阳能电力(PV)容量增长了50%,超过74千兆瓦,中国的贡献将近一半[11]152。但这显然还远远不够,中国的二氧化碳排量占世界的30%,生态治理任重道远。那些在中国致力于“生态文明”理论内涵与实践路径研究的学者,其实是在进行一场过程复杂、内涵丰富且意义深远的探索。生态文明的概念始于前苏联,可能是由伊凡·弗罗洛夫(Ivan Frolov)提出[12]158-161,在中国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发展迅速。为此,时任环保部副部长的潘岳做出了积极贡献[13-15]。2007年11月,在胡锦涛主席和温家宝总理领导下,中国政府将追求生态文明作为国家治理理念和战略;2018年3月11日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第三次全体会议投票表决,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生态文明”写入宪法。就概念本身意义而言,生态文明的理念促进了中国传统思维方式的复兴及与西方思想的融合。
厘定文明的概念对于理解“生态文明”的内涵至关重要。“文明”内涵十分丰富,包括两点:第一,“文化”通常与“对差异的认知”以及这种差异的价值相关联。单凭一群人就判定“何为正确理解世界的方式”以及“何为有效组织社会的方式”的观点是错误的。第二,概念本身具有张力,文明与进步的思想紧密相连,这种进步要求我们不断前进并且创造全球文明。这种张力富有成效,阐释了发端于俄罗斯和东欧的跨文化主义思想。
跨文化主义发展是同“多元文化的相对主义”对立的。这种学说认为,人类能够通过文化将自身从生物必然性中解脱出来,同时也通过接受跨文化主义将自己从特殊文化的狭隘性中解脱出来。米哈伊尔·爱泼斯坦(Mikhail Epstein)认为“跨文化思想及其存在的基本原因”是“通过文化本身实现对文化的解放”,产生出了一个“跨文化的世界,它在每一个现存的文化中,而不是与其他文化相隔离”[16]298。这并不意味着解散现有的文化并建立一个同质化的全球文化。人类真正需要的是一个多元化、相互交融的文化,通过不同文化间的“合流”实现相互学习借鉴、彼此映照。这是创造力追求真理、正义和自由的基本条件,俄罗斯哲学家弗拉迪米尔·比布勒(Vladimir Bibler)认为,“文化只有在文化的边界上才可以生存和发展”。
这种跨文化主义提供的批判性观点能够使特定文化成员重新审视他们自身文化的不同。首先,它支持这些文化与跨文化主义相适应,使这些文化能够促进不同的观点形成对话,提升文化创造力的认知。其次,中国文化具有天然包容性。中国不仅吸收了欧洲文明、文化的先进要素,同时也回归到儒家思想中汲取素养。然而,生态文明的支持者也在鼓励一个更为激进的道教传统思想,其主要特点是对自然及其内生动力的欣赏,对平等主义的认知及对导致冲突、破坏和谐的厌恶。道教思想的复兴总体来讲不仅对中国,对全世界也至关重要,因为这些哲学是在战国时期文化解体和战胜国短暂残酷统治之后(公元前221-206年)逐步形成并发展起来的。这些思想建立在一个更加人道的社会秩序基础之上[17-18]。
中国生态文明的支持者同时也受到欧洲文明的影响。他们以马克思主义的人文主义形式为标准(包括生态马克思主义),关注克服剥削关系,将市场从属于民主组织的社区,并且创造一个人们能够充分发掘其潜力,能够为共同的社区贡献力量的社会,包括全球生态系统,从而获得工作中的成就感[19]。在这种情况下,他们使自己能够与这些维护以上目标的欧洲思想传统保持一致。本质上讲,这些都是激进启蒙运动的思想[20]25-28。通过推广这些思想在中国的传播,生态文明的支持者实际上是在将这些思想传递到全世界。从这个角度而言,如果激进的环保主义在中国流行开来,那么中国与其他世界大国的竞争将会能够避免直接冲突,基于军事力量的竞争以及基于此的威胁都可以避免。中国在胡锦涛主席和温家宝总理领导下形成与“华盛顿共识”针锋相对的“北京共识”,这种共识更加开放与包容,更加适合本国发展;而“华盛顿共识”包括对发展中国家实行自由市场、自由贸易以及紧缩措施,危害他们的社会和经济,以使这些国家受全球公司帝国的奴役。生态文明支持者的胜利将使中国在创造全世界文明的斗争中起到领导示范作用,重新定位人类在自然中的位置,以克服全球生态灾难的威胁。在西方社会对生态文明的推广也会强化其在中国国内的影响力,其结果就是一个崛起的世界大国将会成为解决全世界生态问题的主力军,并推动全人类朝着一个新的文明前进。这个文明能够包容文化与文明的多样性,广泛凝聚全球多方共识,生成全球范围内追求幸福美好生活的合力,共享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带来的生态福祉。
3 生态文明与激进的启蒙运动
跨文化主义的发展可以消解欧洲文明中虚无性所引发的混乱和冲突。显而易见,左派和右派之间的简单二分法,使每一种政治哲学都在两种极端之间,因而不再能够像从前一样解释世界上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这一点在前马克思主义者——卡斯托里亚迪斯(Cornelius Castordiadis)身上表现尤为明显。卡斯托里亚迪斯不仅对苏联非常失望,同时也对马克思主义非常失望。他总结道,在马克思的早期作品中,马克思分享了太多他所批评的观点的假设,也正是因为这种原因,苏联成为官僚主义形式的资本主义。他预见,随着苏联的解体,全球范围内的资本主义国家将会更加具有压迫性和破坏性,财富和权利两极分化更严重,致使人类走向更大的生态毁灭。所谓的新自由主义实际上是官僚资本主义,本质是跨国公司和政府的管理者,代表跨国集团的利益,取代资产阶级成为压迫性的统治阶级。为了解释所发生的一切,卡斯托里亚迪斯指出现代主义一直有两个基本的不同的景象:自治以及对世界的技术掌控。两者是冲突的,卡斯托里亚迪斯也描绘出对世界性技术控制追求的趋势是如何破坏区域自治的景象[21-22]。他的分析的预见性是基于认识到这一划分已经引起了越来越多的关注,同时也引发了越来越多的尝试摆脱当下困境的努力与尝试。
卡斯托里亚迪斯通过研究古希腊民主的诞生和发展,形成并发展了他的自治概念。这对现在我们思考应该去往哪个方向或许没有太大帮助。然而他这种对自治的追求和对世界技术掌控的追求之间的分歧,与玛格丽特·雅各布(Margaret Jacob),以及最近乔纳森·伊斯雷尔斯(Jonathan Israel)所发现的“激进的”和“温和的”启蒙主义之间的分歧相一致[23-24]。雅各布发现的分歧的典型特点是,激进的启蒙运动接受了乔达诺·布鲁诺(Giordano Bruno)对自然的神话以及关于人类是自然的一部分的概念,并且继续文艺复兴对平等形式的共和主义的追求,这实际上是一种对自由和强大的民主的捍卫。温和的启蒙运动是基于梅森(Mersenne)、加塞迪(Gassendi)、笛卡尔、霍布斯、牛顿和洛克等人在17世纪所领导的科学革命,反对布鲁诺的自然热情并且重新制定了自由的概念,反对文艺复兴的自由思想。维护这种自然的观点是为了使其受人类的目的所控,科学革命也取代了自由思想,保护生命和财产,同时也能够接受不同宗教信仰的人们。这场革命被斯蒂芬·图尔敏(Stephen Toulmin)称为“反文艺复兴”[25]24。文艺复兴的重点在于对人文主义的发展以及人们进行自我管理所需要的教育和机构,温和的启蒙运动促进了占有性较强的个人主义和占有欲[26]17-19。因此,18世纪温和启蒙运动的支持者十分反对文艺复兴思想。
为对温和启蒙运动作出反应,激进的启蒙运动首先是地下运动,捍卫和发展文艺复兴时期的遗留。从那时起,它就一直是一股重要的力量。通常被妖魔化为斯宾诺莎主义,在随J.G.赫尔德(J.G.Herder)、费希特(J.G.Fichte)、弗里德里希·谢林(Friedrich Schelling)以及早期浪漫主义流入德国之前,由卢梭(Rousseau)和狄德罗(Diderot)所提倡。像康德和黑格尔这样的哲学家是矛盾的,但自由主义和年轻的黑格尔学派则完全与激进的启蒙运动结盟。在马克思早期的作品和约翰·斯图亚特·穆勒(J.S.Mill)后期的作品中,在19世纪后半叶的英国和美国的理想主义者中,在实用主义者、人文主义者、生态马克思主义者和过程哲学中均得以体现。一旦这段历史被揭露出来,想不通激进的启蒙运动来完全理解怀特海和过程形而上学则是不可能的。文化和文明的概念都是激进启蒙运动的产物,突出了激进启蒙运动的支持者们的核心思想即发展人民,培育和教化人民。然而,激进启蒙运动的特征则是符合自然的内在价值,激发牛顿宇宙学的挑战,发展自然动态观,一个反简化的生物学和人文科学形式的人类科学。
虽然文明的概念并不是政治哲学的核心,但实际上它包含了激进启蒙运动的所有理念。这个词来源于拉丁语civitas,即公民的社会团体(cives)或公民(citizens),通过法律将他们联系在一起,赋予他们一种彼此间的公民责任与权利。法律也有自己的生命,创造了一个公共机构或公共实体(civitas的同义词)。随着罗马帝国的扩张,这个词被用于那些允许某种程度自我管理的国家。因此,文明意味着能够通过接受教育,实现自我管理,从而获得人性的美德。受希腊人的影响,教育一直被视为文明的中心。文明是一个过程的名词,它暗示了一个持续进行着的文明进程。文明的定义与野蛮和堕落相反[27]167-189。野蛮是一种未受文明感化人的状态。堕落是文明的堕落和腐朽,使人比野蛮人更糟糕。野蛮人常常因为他们的优点而受到赞美,尽管这些优点是有限的而且常常伴随着巨大的暴行。野蛮人通常被定义为缺乏计划和组织长期的能力,不能够对他们的生活和制度进行反思,不能够从他们部落以外的人的角度去思考的一群人。颓废的人缺乏所有的优点,除了能够使用通过文明并为满足自身目的而创造出的语言和制度。正如詹巴蒂斯塔·维科(Giambatista Vico)所描述的,这是最终的文明疾病……就像许多野兽一样,人类已经习惯了各自关注自身的利益并且将其做到极致,或者为了自身的骄傲,和野兽一样,稍微遇到不满意就会发怒并且猛烈的攻击。因此,无论他们的身体多么强大,他们仍旧像野兽一样,在精神和意志深沉的孤独中生活,几乎没有人能够和其他人达成一致,因为每一个人都只想任性的追求自己的快乐[28]1106。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怀特海在《观念的冒险》(Adventures of Ideas)中为定义文明的努力应该被理解。尽管承认衡量文明的价值有悖古希腊和罗马至高的标准,怀特海认为有必要重新定义文明来超越这些标准。他指出,文明的本质是“真理,美,冒险,艺术与和平”[29]IV。虽然怀特海阐明了这些术语的意义,但鉴于建筑和城市规划理论家克里斯托弗·亚历山大(Christopher Alexander)的作品,我们还可以进一步发展出美丽的地方。亚历山大认为美是一种客观的,与整体和生命相关的世界性感知质量。他将美与生命等同,认为一个事物的美丽并不在于它的外表,而与它的方式有关。现在它是怎样的实际上涉及不同的正在进行的事件之间的关系……所以最终真正重要的是内在生命[30]56。我们所认为的美丽也会被认为更有活力,更有益于生活,不管是在考虑一个建筑、一个城市、一个场景还是一种生活方式,这个标准都适用。
此外,还应当突出自由和正义的重要作用。自由,就像文艺复兴时期的公民人文主义理解的一样,与奴隶制相反,在奴隶制中,人们会受到那些他们依赖的或者会伤害他们的人的任意决定的影响[31]x。自由需要有条件,包括经济安全和教育,发掘一个人充分的潜力去参与社会,提出质疑,重新制定社会和组织的目标、信仰、价值观和体制,以及维护自己的权利,而不必担心遭到报复。正义是适当地识别出在思想和行动维度中人为何物,人的历史,人的经历,他们对社会的贡献是什么,他们的目标是什么,他们的潜力怎样,无论是人、社区、文明或非人类的生命形态,包括生态系统。正是在争取自由和正义的斗争中,对真理、美丽、冒险、艺术和和平的追求获得了全部的意义,可以被看作是定义激进启蒙运动的目标。对自由的追求需要冒险、艺术和和平,而正义的追求需要真理和美。
4 激进的启蒙运动和生态
如果未来的文明是一种生态文明,那么它的宇宙观将会建立在生态思想上。生态学是对生物群落及其所创造的家庭个体的研究,是关于这些群体如何能够共同地转变他们的环境且增强他们的生存条件的一种研究。生态文明的概念不仅需要生态文明被非常严肃地对待,还需要它取代当前对世界的假设以及我们所处的位置,作为文明进步的条件。正是因为如此,它才会是生态文明。那么文明的进步为何要求这些呢?
让我们回到对文明的品质的定义上,正义意味着任何事物被理解的方式都是正确的。因为每种情况和情境都被我们的基本形而上学假设所影响,对正义最重要的是这些形而上学的假设是有效的。全球生态危机,以及未能解决这一问题,实际上是一种定义现实的缺陷的表现方式,被现代的机构体现和复制的现实现在主导着世界并指导人们的行为,无论是个人的还是集体的行为。人类现在基于一种错误的关于自身模型和其在自然界中的位置的假设去行动,正如唐纳德·米库列奇(Donald Mikulecky)和詹姆斯·考夫曼(James Coffman)所主张的那样,带来的结果将会是有效的疯狂。这是科学唯物主义的胜利的体现,这不仅是在自然科学中,也是在人类科学中,最重要的是,在经济学中也是如此。它已将我们的最终目标界定为无休止地扩大商品生产,将生活界定为一种为生存而斗争的斗争,在这种斗争中,进步需要消除不那么适合的人。只有通过接受科学唯物主义,人们才能平静地接受,把一切和每一个人作为工具,尽可能有效地加以利用,使利润最大化,或作为对手被打败、征服、杀害或听任其灭亡,并对物种、生态系统、种族和文明的破坏漠不关心。它使得全球化市场对生活的方方面面的负担合法化甚至使其成为基础,正如生态经济学家真弓浩三(Kozo Mayumi)所说,生态上可持续的企业在经济上不可行,而那些经济上可行的经济企业在生态上是不可持续的[32]125。正是通过对真理的承诺,激进启蒙运动的支持者提出了挑战并试图取代科学唯物主义成为我们宇宙学的最站得住脚的基础,以及我们对生命和人性的描述。如果过程形而上学是有效的,那么我们造成如此大规模生态破坏的制度和行动是极其不公正的。本质上,这是怀特海在他写的科学唯物主义的后果时所提出的,这是一场巨大的灾难。19世纪的口号一直是为生存、竞争、阶级斗争而奋斗。怀特海认为,19世纪的信念主要有三个来源:一是表现在宗教复兴、艺术以及政治思潮上的浪漫主义思潮;二是为思想开辟道路的科学跃进;三是彻底改变人类生活条件的科学技术。怀特海还指出,生物通过同周围环境之间的相互适应与改造,从而达到相互协助的目的。这个规律在自然界中得到了验证[33]256。
这一发现对美国生态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基于它后续出现了共生关系的研究,以及生态学的新方法[34]320。这也引发了林恩·马古利斯(Lynn Margulis)和詹姆斯·洛夫洛克(James Lovelock)的盖亚假说,马古利斯的论点是,共生是进化的核心,我们都是共生的,洛夫洛克声称自然是通过清除掉那些污染了自己的巢穴的生物进化而来的。
现代性是由温和的启蒙运动主导的,它将物理学作为终极科学。这已被视为所有科学的理想模型,并确定了它们的相对地位。物理学受到生物学的挑战,有时被描述为系统的有机体,被认为是定义现实的终极参照点。然而,要成功地应对这一挑战,物理学必须以自己的理由来面对。怀特海关注物理学及其在生物哲学上的发展进展。然而,对生物体的捍卫并没有成功推翻科学唯物主义。牛顿的科学模型仍然占据主导地位。当怀特海对进化论进行深刻的观察时,生态学只是处于发展的早期阶段。许多生态学家随后试图通过促进对还原主义的解释,削弱对主流科学的挑战,以及对生态学的轻视来提高其地位[35]40-50。生态学现已成熟,恢复了原有的动力。罗伯特·乌拉诺维奇(Robert Ulanowicz)声称,生态学应该被认为是定义所有科学的参照点。正如他在自己的书《上升性的生态视角》(Ecology,The Ascendent Perspective)中写道:生态学占据了有利的中间地带。事实上,生态学很可能会提供一个更受欢迎的平台来寻找可能给科学带来广泛影响的原则。如果我们放松了对偏见的控制而支持作为一般原则的机制,我们在这种思想中看到的第一个迹象就是生态学,病态的纪律实际上会成为科学思想的一个重大飞跃的关键。一个全新的用以看待生态世界里的事物如何发生的视角,可能会打破目前阻碍人们理解进化现象,发展生物学,生命科学,甚至是物理学的概念上的僵局[36]6。
目前的物理学停滞不前,这与它无法理解复杂性并声称生物本身只是高度整合的生态系统的自身缺陷息息相关,这为这一主张提供了强有力的辩护。在后来的一本著作《第三扇窗》(A Third Window)中,乌拉诺维奇为过程生态学进行了辩护,这是生态形而上学的基础[37]x-xiv。也就是说,宇宙的最终存在必须被看作是创造性的过程,或者是活动的自我约束模式,以及动态交互中的过程,而不是物体或事物的配置。科学的焦点应该是在过程和机会事件上,而不是法律,因为乌拉诺维奇说:法律是在不成熟的过程中出现的,最终变成了静态的、堕落的形式。生态符号学家认为,生物本身是高度一体化的生态系统,生态系统是由符号性的纽带构成的,并将地球上的生命描绘成全球符号域的发展。他们为洛夫洛克盖亚假说提供了深层次辩护[38]。
生物渗透学和生态系统学是通过等级理论得以捍卫,根据这种理论,新秩序是通过新的授权约束产生的,新的种类的生物(包括人类)出现了新的秩序[39]。符号化过程,从最原始的形式到人类文化,涉及约束活动并促进新的约束。对正义的不断增长的认知,认为其是生态社区的联合参与者的最为合适的认知,限制了人们的生活方式,现在则可以被看作是革命的非常重要的一个特征,使现在人类对全球生态系统现今制度的内在重要性的认知潜力达到顶点,并相应地限制他们的活动。正是这种在正义的推动下的进化性进步,让世界变得更美,并带来了一个更活跃、更有益于生活、更有生命力的世界。
也就是说,生态学为捍卫和进一步发展“过程”世界导向提供了基础,整合了怀特海、皮尔斯和其他过程形而上学者的工作,并推动了后还原主义科学,在自然主义基础上支持人文科学的人文主义方法,同时也为捍卫、反思和推进人文科学提供了基础。这一生态视角是通过人类生态学、生态经济学和政治生态学发展起来的,也是重新构建其他所有人文科学和人文学科的框架,这涉及改变人们理解道德、政治和技术的方式。
5 生态环境的伦理、政治和技术科学
道德不应该仅仅被看作是一种关于如何生活的目标的论述,而是我们努力实现的目标。这是所有人文学科都应该关注的,而不仅仅是伦理哲学,也正因如此,人文学科应该被视为比科学更重要的东西。正如米哈伊尔·爱泼斯坦所写的:人文学科和科学的关键区别在于人文学科的学科和研究对象是一致的;在人文学科中,人类是由人类所研究且为了人类的目的。因此,研究人类也意味着创造人类本身及人类自身的构建。从实践意义上看,人文主义创造了人类,因为人类被文学、艺术、语言、历史和哲学的研究所改变:即人文的人性化[40]7。
人类通过创造新的形象,符号和概念来创造自己……人类并没有在事物的世界中发现如何通过自我描述和自我投射来建立他们的主观性[40]8。正是因为如此,人文学科才应该是评价性的和辩论性的。对于人文和伦理来说,通过生态学来创造人性又意味着什么呢?
从本质上来说,通过生态学来了解自己是为了熟悉自己作为群落中的一员的基本事实。一个人的性格发展及实践行为等都是在扩大或破坏这些群落,并且可以据此做出相应的价值判断。实质上,这也支持并扩展了奥尔多·利奥波德(Aldo Leopold)关于土地伦理的看法:“当一件事情是为了维护生物群落的完整性,稳定性和美丽时,这件事情就是正确的,反之,则为错误的”[41]224。它将这一概念从一个社区扩展到一个由社区组成的综合体,即所谓的“社区之社区”的概念(communities of communities)。对这些社区的贡献主要是家庭生产,或对这些社区的生态化[42]。同时,评估一个人自己,一个人的行为以及一个人与人类社区和组织的产品,不仅仅是他们的健康和生命是否得以提高,更重要的是,这些社区和组织是否能够以一种提高其他的社区的生命的方式发展,包括它们所从属的更广泛的生态群落。我们所需要考虑的终极群落就是全球生态系统的现今制度,人类与这种构成的生态系统和生物体在过去的100 000年左右共同进化。
从这个角度来看,可以很明显得知,群落彼此之间存在威胁。例如,癌症是细胞群落,对他们所在的生命体的健康和生命构成威胁。人类组织如果能不能发挥积极作用,其功能与肿瘤无异[43]15。正如健康的细胞能够带来自然康复,健康的社区也能够启迪人们积极参与到政治中。
通过生态思维进行的人类科学转型是为了促进通过政治进行的社会转型,这和实证主义的人类科学的方法有很大的不同。这不是一个将人客观化并且参与到社会工程中去的事情。这是文化的转型,使得人们本身能够成为这种转型中的共同代理。也就是,社会科学服务于民主。理查德·诺加德指出,有三种方式可以让大部分人在复杂的社会中协调他们的活动,通过官僚机构,通过市场和民主制度[44]122-135。这三种方法中的任何一种都不可能完全消除,但是它们之间相互联系的方式是非常不同的。无约束的市场由跨国公司主导,消除经济安全,在新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下,使人们受企业管理者的奴役,这实际上是市场和官僚机构反对民主的联盟[45]51-70。通过财富的集中,完成对具有思想控制作用的广告业和公共关系发展的控制,并颠覆和改变公共机构使其能够服务于企业追求利益最大化,任何有意义的民主在大多数国家都几乎被完全破坏了。就连美国前副总统艾尔·戈尔(Al Gore)也认为,所谓“民主”,在美国已经不复存在[46]。正是这种对市场力量和公司管理者的奴役促使了生态破坏以及对它的严重反对[47]96-110。以前的共产主义国家证明了政府官僚机构在控制市场方面的权力毫无民主可言,这与不受约束的市场一样具有环境破坏性[48]266-277。真正民主的实现带来了高度的环保意识。瑞士和丹麦,则是相对环保的国家。创建生态文明需要组织培养不同层次的民主国家,需要尽可能多的权力下放,开发和维护市场以外的公共机构,通过以上可以培养公共领域和文化生活,实施民主计划,以控制市场和官僚机构[49]25-56。
我们应理解对政治至关重要的追求自由的努力奋斗,尽管有与其相反的将其三种形式均包括的相反的言论——摆脱奴隶制,摆脱束缚和追求有价值的目标的自由,其中的第一点和第三点更为重要[50]。奴隶制最糟糕的一种形式即为被迫以一种毁坏个人生存条件的方式生活并且行动,而现在通过全球市场以及泰勒制管理主义的兴起,大多数人都生活在以上的境遇之中。将知识和决策制定权集中在管理层的手中,而破坏他们所管理的就业保障[51]99-112。自由的概念不仅是免除受奴隶制的束缚,还应该是能够自由地生产生活,以一种能够增强而不是毁灭自由和生命的方式进行实践活动。正如新黑格尔主义哲学家T.H.格林(T.H.Green)说道,当我们谈论自由时,我们是指一种积极的力量或能力去做或者享受那些值得去做或者值得去享受的事情。格林认为真正的自由在于追求全人类自由的共同福祉,他认为:当我们通过其在自由方面的成长去衡量社会的进步时,我们通过对社会福祉做出贡献的这种能力的发展和执行来进行衡量,我们相信社会的成员都被赋予了这种能力。简而言之,是通过每一个市民尽自己最大努力的这种巨大的能力[52]199。
现代世界的自由首先应该被看作是争取对市场、官僚机构和管理人员的这种民主控制的斗争,市场和官僚机构的体制转变是为扩大而不是破坏民主[53]129-159。通过促进人类生态学,生态经济学和政治生态学的制度主义形式的发展,以使得这种民主控制得以实现,并使人们能够理解世界并且参与到决策制定中。促进这一控制将会要求尽可能多的产品的本地化,创造出理查德·诺加德所描绘的“为治理杂论社区而进行的被子间的拼接”。代替技术治理,以及包括本国货币在内的经纪机构,以使其成为可能[54]139。
我们仍然需要科学技术知识来改造自然。从给世界设定框架到揭露其可预测性到对其进行完全的控制,技术再次被认为是一种能够促进生态系统发展和健康的手段,包括个体的有机体和人类社区,所以在行动中,这些社区的成员增强了这些生态系统的健康和生命[55]167-195。这其中所蕴含的关系可以显而易见地从与农业的关系中看出来,人类的活动不应当是毁灭性的,而应该是以提高生活质量为导向的。例如,亚马逊热带雨林中最肥沃的地区,植被最健康的地区是人类掩埋木炭的地区。全世界的土壤都可以通过这种方式变得更加肥沃,在这个过程中从大气中回收碳并减少强温室效应的风险。范达娜·席瓦(Vandana Shiva)在印度领导了一场运动,回归到更传统和自力更生的农业的形式,包括培养健康的生态系统,同时有许多适于该条件终止的种类,而不再需要施肥。与此同时,她揭露并攻击了支持全球市场和生态破坏农业企业的机构[56]1-5。韦斯·杰克逊(Wes Jackson)正在开发具有高种子产量的多年生植物,这将强化生态系统,同时大规模减少维持生命所需的投入[57]1-14。医学可以认识到有机体之间的共生关系并试图创造有利于人类健康的生态系统。如果没有全球市场的专制,制造业就只能局限于生产可以回收的商品,正如威廉·麦克唐纳(William McDonough)和迈克尔·布朗嘉特 (Michael Braungart)在《从摇篮到摇篮:重塑我们做事情的方式》(Cradle to Cradle:Remaking the Way We Make Things)中所提出的那样。建筑物密集的环境被认为是参与到了自然的形态建成,可以被重新设计以促进社会和文化生活以及群落的民主组织,增强他们控制市场和官僚机构的能力。这也是克里斯托佛·亚历山大(Christopher Alexander)的观点[58]。这是因为欧洲城市比美国城市更接近这种形式,且欧洲人的生态破坏行为比美国人更少[59]215-216。
可持续发展这个概念默认了自然同经济的分离,这一“分离”需要弥合,才能够保障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生态文明”则直面人与自然的关系(被认为是生态危机的根源性问题)。“生态文明”呼吁通过文化和社会转型克服这种人与自然二元对立的、占主导地位的思维方式。这一转变涉及对伦理、政治和技术科学的根本性反思,这是基于过程形而上学,通过生态学的科学阐述。这涉及人们对这些话题的思考方式的根本性转变,需要引用这些跨文化主义带来的资源。中国哲学与欧洲哲学不同,从探索对生命的本质(Being)的描述开始,通过给予特权而不是寻找“方法”(the way)或者“道”(Dao)。由于中文不使用冠词,因此“一种”方式和“这种”特指的方式都隐含在这种追求之中。对欧洲思想成果的吸收与借鉴应当建立在对生态文明建设追求的基础之上。这包含了对人类自身及生态系统发展的追求。正如孔子说道:“人能弘道,非道弘人。”[60]28对于道家而言,这包括顺应自然的方式而生活。中国的环保主义者一直在弘扬生态文明的前沿。在此过程中,他们打破壁垒,融合中西方文明。最重要的是,他们以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方法论为指导,借鉴生态科学、自由与民主的概念,考察文明的兴起和衰落的历史。当然,生态文明这一概念有理想化色彩,但却是值得人们共同努力,采取行动去实现的伟大梦想。正如恩斯特·布洛赫(Ernst Bloch)在他的著作《乌托邦精神》(The Spirit of Utopia)中写的:“我在,我们在,则足够。我们现在必须开始。命运一直掌握在我们自己手中。”[61]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