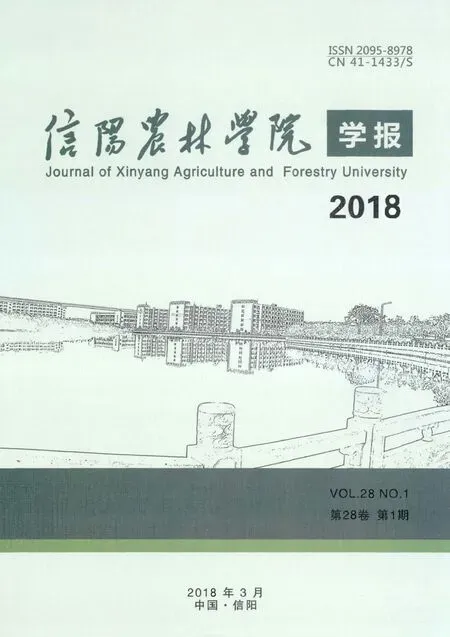生态视域下《爷爷和我》的生态悖论解读
2018-01-27吴畅畅
吴畅畅
(郑州大学 外语学院,河南 郑州 450000)
1 罗伯特·鲁瓦克的《爷爷和我》
罗伯特·鲁瓦克的《爷爷和我》这部小说曾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风靡台湾,时隔三十年再次风靡台湾,受到了热烈欢迎。鲁瓦克以其简洁和淳朴的写作风格被誉为“第二个海明威”。作为作家、探险家和猎人的鲁瓦克在这部半自传体小说中,展现出他的爷爷对其终生不可磨灭的影响和教导。正是在童年与爷爷的生活中,小男孩不断地成长和形成自我。因此,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这本书也是一部成长小说。全书共分为二十八个章节,记叙小男孩与爷爷朝夕相处的日子,直至爷爷去世。在这部小说中,爷爷通过打猎活动,教给小男孩各种关于当时野生物的生活习性和打猎技巧,不仅如此,更重要的是对小男孩传授的人生知识。故事中关于小男孩和爷爷打猎的活动,在当代人看来难逃破坏环境之嫌,事实上,小说正是通过问题的反面来呼吁和倡导环境保护,向读者展示生态环境保护的重要性。在打猎和教导的成长过程中,大自然给予小男孩身体和心灵的影响不可磨灭,以至于影响了小男孩之后的人生轨道,即在大自然中汲取力量和平复躁动,从而达到精神生态的和谐。生态文学以注重人与自然的和谐及提倡自然中心主义、反对人类中心主义为旨归,其文学特征在于以生态思想和生态视角为出发点,将自然为本的文学和以人为本的文学并列;其中心维度是把握人类与自然的互动生成关系,考量自然如何影响人的生存和心灵[1]。因此,本文旨在从生态角度解读这本小说,挖掘其中的生态保护意识以及对当代生活的启示意义。
2 珍爱与猎杀:人与动物之间的生态悖论
从开始到结尾,打猎是连接小说所有要点的织带。从第一天开始打猎起,爷爷就要求小男孩养成打猎的好习惯,关于打猎的数量、对待动物的心态以及怎样拿枪。在小男孩第一次接触打猎的时候,爷爷教给他的是怎么打鹌鹑。爷爷这样对小男孩说:“尊重是一项美德,我敢讲,在任何情况下,无论是对待鹌鹑、狗,或是人,都会用得着的。”[2](P7)这样简单的一句话,透露出来的不仅仅是爷爷对待自然的平等态度,即赋予这些动物人性,更为重要的是他将这种对环境的态度以身作则地传递下去,让小男孩从第一天起就不要以居高临下的态度去随意对待自然。因为正如《圣经》的《申命记》所记载,“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以手还手,以脚还脚”。人类怎样对待自然,自然就会怎样回馈人类。因此,从一开始爷爷就让小男孩对自然心怀敬畏。
在刚开始打猎的时候,爷爷首先教给小男孩的就是要尊重动物和爱护他们,把他们当做人一样去对待,只有这样才能和谐共处。像这样的教导,在小说中比比皆是。在这些教导中,爷爷教给小男孩最重要的狩猎知识,就是为什么去打猎,换言之就是打猎的动机。猎人是为了需要才去打猎,不论是猎杀一只鸟、一条鱼,亦或其他动物,最为关键的是猎人是出于需要的目的而不是为了嗜杀而去打猎。从这句话就可以看出,爷爷和“我”所从事的打猎活动是为了生活所需而并不是恶意杀戮,超过需求以外的猎杀就是受欲望驱使的滥杀。这种受不同目的驱使的打猎是与环境能否建立和谐关系的关键。一旦出于欲望的驱使去捕杀猎物,生态不和谐也就因此开始。与爷爷相对的另一种猎人则应该是谴责的对象。在第十二章“爷爷的规矩”这个章节中,作者似乎有意列举了像“乔”一样的反面猎人。他在平时和蔼可亲,可是一到林子中打猎的时候就像变了一个人似的,不肯收手而且贪恋打猎,好像沉迷于肆无忌惮的猎杀中,使得整个捕猎环境沦落为一幅血腥和残忍的画面,展现出人类自私和冷酷的一面。因此,爷爷和乔打猎几次之后便不再和他一起打猎,因为他破坏了打猎的轻松和闲适的氛围。不仅如此,他还毁坏了打猎的基本原则和最初的意义,仿佛投入到了无尽放纵的欲望游戏之中。以乔为代表的猎人,正是践行了人类中心主义这一思想的必然结果和真实写照。面对自己的征服欲望,很多人放肆地杀害那些无辜生灵,以期获得某种满足感和成就感。正是因为有这样的猎人存在,才使得生态环境失衡,造成人与自然关系的紧张。
3 欲望与治愈:自然对人类精神的疗治
在当代生态环境批评中,精神生态批评也享有一席之地。爷爷从一开始教给小男孩的这些规则和准则,其实就是为了让小男孩保持精神上的生态平衡。精神生态失衡最为明显的例证莫过于二元对立这一原则的提出,在所有的等级结构中,总有一方位于核心和主导地位。爷爷教给小男孩的不仅仅是一些看似繁琐的规矩,实则是让小男孩在物质需求急剧上升的年代,保持精神上的生态平衡。也只有这样,小男孩才能在生活中感受到意义的存在。因此,与环境保持和谐的关键就在于人类怎样对待自己的欲望问题。
一战以后的美国人之所以被称为“迷惘的一代”,原因就是其精神生态的失衡,导致精神上的虚无主义。在经历极度残酷和纸醉金迷的生活之后,人生的意义无从寻找,从而导致大肆酗酒和癫狂。因此,爷爷对小男孩猎杀的训诫,是为了让小男孩更好地感受人生的意义和价值,感受万物的和谐共存和平等。对自我欲望放纵的结果很可能是毁灭性的。对于欲望的看法,自古以来就受到哲学家的关注和探讨。欲望的性质究竟是什么,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的看法和理解。在伊壁鸠鲁学派那里,欲望与快乐联系在一起。他们认为,在追求快乐的时候,即满足欲望的过程中总是摆脱不了痛苦,过度的享受最终导致痛苦,这也是“欲壑难填”的道理[2](P99)。在柏拉图那里,欲望是一个“消极、被动”的词语。欲望被看成是出于人的本能、不受控制的自然的情感,一种将人引向堕落的“不好”的情感,与恶相联系。在亚里士多德那里,欲望被分为两个部分,一部分是有逻各斯的,另外一部分是没有逻各斯的。他指出:我们的欲望应当是适度的和少量的,并且不违背于逻各斯[3](P94)。在霍布斯那里,欲望是一种积极促使人行动的动因。在其著作《论公民》中,他指出:生活就是行动,而行动离不开欲望[4](P68)。在其另一部传世之作《利维坦》中,霍布斯更是说出“没有欲望就是死亡”[5](P56)这一惊人论断。在休谟那里,欲望则与道德联系在一起。休谟最为人熟知的就是其关于道德的“动机理论”,即动机的产生是由信念和欲望结合而起作用,反对道德信念能单独激发道德动机。休谟认为信念和欲望是不同的存在,在没有欲望的支持下,信念不能单独激发任何意志活动。斯宾诺莎认为“自然的欲望是一种束缚”,欲望是人的本性之一。在康德那里,欲望与道德、幸福等概念联系在一起,“按照康德的观点,意志是人的‘欲求能力’。如果人的‘欲求’是出于‘自然欲望的意图’,是为了追求‘欲望对象’,就会为自然欲望所束缚,则人的意志就是不自由的”[6]。在黑格尔那里,自我意识是欲望。在弗洛伊德那里,欲望则是紧紧与力比多联系在一起。在拉康那里,欲望与需要(need)、需求(demand)有着紧密的联系。纵观以上各个时代学者们对欲望的探究和论述,伊壁鸠鲁学派关于欲望的论述还是比较中肯和适切的。追求快乐是人的本能,人不可能违背自己的天性,但是要意识到在满足欲望和追求快乐的过程中所遭受的痛苦。
“欲望”也正是在保持生态环境平衡和精神平衡之时,所遇到的最为有力的对手和障碍。对欲望的放纵,致使以“乔”为代表的猎人走上歧路,无尽地屠杀动物。而对欲望的放纵,虽一时看来并未有明显的危害,实则表现出对人的精神生态平衡的威胁。“乔”的肆意猎杀正说明其精神生态的失衡,所以,解决生态问题首先要解决人类自身的问题[7],而人类自身最大的问题则是怎样去理性对待自己的欲望。
4 失衡与平衡: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
在文中,作者似乎有意并置以爷爷为代表的克制的猎人和以乔为代表放纵自己的欲望的猎人。乔对待打猎是一种满足自我欲望和肆意享受的人类中心主义立场,这种人在对待自然的时候并没有将动物与人放在平等的位置上,而是把动物看成是凸显人类优越感和自我能力的工具,这种人应该是被谴责的对象。而以爷爷和小男孩为代表的猎人则代表着谦逊和有良知的人类,他们在自然面前显示着自己的谦卑,将动物放在了与自己同样的高度,尊重和保护大自然中的生物。爷爷和小男孩的打猎活动完全是出于一种生计的需要,虽然也猎杀动物,但却在其可承受范围之内,他们的打猎活动是一种绿色、和谐的方式,在尊重自然的基础之上,对自然适度索取。
在打猎活动之外,作者还展现给读者一幅幅如画的风景。如描述小男孩和爷爷在寒冷的冬天去猎鸭时,作者从视觉和听觉两方面展现了大自然给予人类的美妙一幕。“沼泽上空,只听得这群红翅膀黑羽毛的鸭子,歌声嘹亮,响彻云霄。顷刻之间,发出各种声音,有一曲万人大合唱:嘎嘎的沼泽鸡,哇哇的鹭鸶,呱呱的青蛙,和四周呷呷的野鸭声相唱和。”[2](P31)在与自然的相处中,小男孩塑造了性格,并且得到了精神的升华。虽然这些在当时他并未意识到,但是从作者的语气中明显可以感到对那时候跟着爷爷在自然中学到的东西的怀念和感激。在小男孩急于去打猎的时候,爷爷觉得这样性急的猎人不可能成为一个好猎人。因此,爷爷就带着小男孩去钓鱼。虽然小男孩在当时并不是很理解,但是爷爷这样告诉小男孩:“藏在你所看见的深水中的鱼,是地球上的一种和平象征;对你自己来说,也是良知的象征。钓鱼使人有时间思考,有时间集中自己的思想,再把它有条有理地整理清楚。”[2](P47)从爷爷的话中可以看出,爷爷不仅希望小男孩可以在打猎的活动中体会到人与自然和谐的重要性,更希望小男孩在大自然中形成自己独特的性格,即在大自然中学会思考和养成思考的习惯。正是在这种沉思中,小男孩逐渐与大自然融为一体,使自己成为大自然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就像在末尾,爷爷最后临终遵守的诺言一样,他绝不会在打鹌鹑季节的第一天就死去。最终爷爷带着满足和欣慰,回归到大自然的怀抱之中。正如《圣经》中所指出的:人来自于尘土,仍要归于尘土。这个回归的过程,就是再次与自然融为一体的过程。
5 结语
生态文学在文学文本中空前地凸显人类的重大困境,并对这种危及人类整体未来的困境加以审美解答,从而激发起人类与非人类的自然世界联系的内在情感,寻找人类与自然重归于好的和谐世界的新途径,探索人与自然互惠发展的新伦理[1]。当前,国家提出“美丽中国”和“可持续发展”的口号,保护环境是每一个人不可推卸的责任与义务,也只有在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前提之下,才能实现可持续发展这一宏伟目标。
[1] 王岳川. 生态文学与生态批评的当代价值[J].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2): 130-142.
[2] 罗伯特·瓦鲁克. 爷爷和我[M]. 谢斌译. 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
[3] 亚里士多德. 尼各马可伦理学[M]. 廖申白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
[4] Hobbes.OntheCitizen[M]. Lond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8.
[5] 霍布斯. 利维坦M]. 黎思复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5.
[6] 杨秀香. 论康德幸福观的嬗变 [J].哲学研究,2011(2): 1-8.
[7] 杨丽娟,刘建军. 关于文学生态批评的几个重要问题[J].当代外国文学,2009(4):50-5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