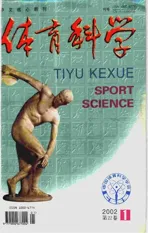从“形而上学式”到“历史主义式”体育哲学——始于体育概念无穷性困境的思考
2018-01-27康义萌
高 强,康义萌
从“形而上学式”到“历史主义式”体育哲学——始于体育概念无穷性困境的思考
高 强1,康义萌2
1.华东师范大学 体育与健康学院 中法体育科学研究中心,上海 200241;2.淄博职业学院 体育与健康教学部,山东 淄博 255314
形而上学式与历史主义式是两种体育哲学样式,形而上学式体育哲学困于体育概念的无穷性困境,而历史主义式体育哲学正方兴未艾。以现象学及存在主义的理论剖析体育概念的无穷性困境,形而上学式体育哲学中存在的逻辑困境得到了纾解,从中挖掘了历史主义式体育哲学得以构建的体育“他者性”与“注视者”角色两个出发点。在布克哈特、尼采与福柯3位学者的理论襄助下,体育“他者性”与“注视者”角色在体育的文化属性与身体行为属性中进一步阐发,形成了历史主义式体育哲学的基本框架与论证结构。历史主义式体育哲学是一种新的体育哲学样式,既开启了全新的理论探讨模式,也使体育哲学的发展更为契合当代哲学的发展进程。
体育哲学;形而上学;历史主义;现象学;存在主义;文化;身体
1 从体育到“体育”:形而上学式与历史主义式体育哲学
体育哲学的研究往往始于将体育转化为“体育”,即为诸多的体育现象寻找一个定义,使之成为“体育”概念的研究理路。而体育有着斯芬克斯般变换的面孔,又与多种现象纠缠交错,试图对其进行固化的定义就如流沙逝于掌心,逾是紧抓却逾是流散。对体育概念的定义既无力全然涵盖体育现象的社会变化又迷失于体育现象的历史流变,呈现为体育概念的无穷性困境。针对这一困境,采用形而上学与历史主义两条研究进路的体育哲学家分别使用了“堵”与“疏”的两种截然不同的回应方式。
诸多体育哲学论家以形而上学的方式为体育概念作出众多界定,形成一种“围追堵截”的态势。但无论体育概念界定的逻辑多么圆融自洽,貌似坚固的体育概念在日新月异的运动参与方式下倍显疲态,疲于应付由于体育模糊的外延边界而带来的种种挑战。Bertard Suits在游戏层面上对体育的定义较为闻名。他以“限定规则制造不必要的障碍”来规定游戏,并在游戏之上加诸“更多的身体技艺”“更强的专业化”来规定体育[17]275-276,使之形成体育概念。然而,无论Suits如何巧用维特根斯坦的游戏理论,精致的理论内核始终无法规避体育概念的无穷性困境。身体技艺的形式与方式的差异性与变化性近乎无穷,专业化的程度与范围的界定近乎无解。诸如体育究竟是否应当局限于身体运动,还是应该拓展到棋类、电子竞技等比较考量心智但又几乎没有身体运动的活动等问题,都一次次地冲击着形而上学式定义的逻辑堤坝。当代体育哲学狂飙突进般地引入各种哲学理论来修补形而上学式定义的逻辑堤坝,希望寻找到“万灵药”般的哲学理论来一劳永逸地解决体育概念的无穷性问题总是徒劳无功的。
英国哲学学者Connor已认识到对体育进行形而上学式定义,形成体育概念的努力所犯的是方向性错误。诸多体育概念的定义并非不够精致,用典并非不够精到,而是南辕北辙。形而上学式定义无疑寻找趋于抽象的、普遍的、一劳永逸的概念。但在Connor看来,无论体育呈现出何种变化无常的面貌,它都是历史地呈现在人类整体心智之中的。基于这一层批判,Connor走出了一条“疏”的道路,即不再试图找寻一种或几种哲学理论体系以期全然涵盖体育的种种变革,给出完备的体育概念。他所试图描绘的是体育与人类心智遭遇的历程,换言之,便是探讨体育在人类心灵中的呈现。此举在实质上是探讨人类心智的变化历程。人类心智有着历史的变化过程,而以历史哲学分析见长的历史主义学派致力于将人类历史与人类的思想进行整合。故Connor推定对体育史的历史哲学分析是一种历史主义式体育哲学的构建初试[16]14-19。从体育到“体育”不再以一个概念定义的模式简而论之,引号内所包含的是人类对体育的思考过程。作为哲学家,Connor关注的领域较为宽泛,他意旨于重新构建体育哲学的讨论框架,对体育哲学中的诸多问题进行了铺陈,却未尝雕琢重构从体育到“体育”的历程。Connor所采用的历史主义方式缺乏必要的哲学理论阐释,仅是一种灵光乍现的反思。Connor针对的也仅是体育概念问题,未能深入切口进行理论构建。从体育到“体育”,是一个从现象到概念,从外在实体到人类内心思考的过程,对它的解析是当代现象学所倾心关注且着力分析的。本文发端于Connor的批判,以存在主义及现象学理论直击体育概念无穷性困境形成的人类心智根源,继而结合Connor所倡导的历史主义分析模式,以哲学论者对体育的阐释规避无穷性困境,在更为广阔的哲学背景下形成体育哲学新论调。
2 历史主义式体育哲学的理论构型:存在主义与现象学理论襄助
既然形而上学式体育哲学的方法无助于体育概念的无穷性困境的疏解,便需要排除“堵”的方式,而专注于分析为何形而上学式体育哲学无法解除体育概念无穷性困境的束缚。当代哲学史上,现象学及其后续存在主义流派对形而上学的批判是冷静尖刻的。学者们直击了形而上学的内部核心,为破解体育概念的无穷性困境撕开了第一道裂口,亦形成了历史主义式体育哲学的理论构型。
2.1 作为“他者”的体育:体育概念的存在主义解构
法国存在主义学者西蒙•波伏瓦对“他者”的哲学分析为突破体育概念无穷性困境提供了一条路径。作为女性主义的思想奠基者,一般认为波伏瓦笔下的他者是指女性,但她对他者的分析已超越了女性主义范畴而进入了哲学本体论讨论的核心。体育作为一种人类的“他者”,形而上学式的体育哲学对体育概念进行不遗余力的定义,正是强制对“他者”进行形而上学定义,这也正是导致了体育概念困于无穷性的根源。
首先,体育中鲜明的身体性是导致体育成为他者的首要原因。“他者”中存在着“他性”。“他性”是人类思维的一个基本范畴。他者的形成与人类文明的形成相伴,波伏瓦论道“从自然状态到文明状态的过渡,是通过人用一系列对立的形式去设想生物学关系的能力来确定的,这些关系以确定或者模糊的形式所呈现的二元论、互相交替、对立和对称,与其说构成需要解释的现象,不如说是构成社会现实基本的和直接的材料”,所以,“他者的范畴像意识本身一样原始。在最原始的社会中,在最古老的神话中,总是可以找到自我和他者的二元论”“主体只有在对立中才呈现出来;它力图作为本质得以确定,而将他者构成非本质,构成客体”“他者是因为主体将自己确认为主体,才成为他者”[12]11-13。在主体逐渐凸显的过程中,他者的内容也渐渐丰富,所有被人类认为是与自身不同的存在都被认作是“他者”。自然首先被人类认作为第一个他者。波伏瓦认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认为“人类不是一种动物,而是一个历史现实。人类社会是一个反自然:它不是被动地忍受自然的在场,它使自然为自己所用”[12]77。结合以上波伏瓦的两点论断,人类身体的“他者”地位昭然若揭。从波伏瓦与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看,人类与自然是一种主客体关系,在此中自然不仅包括外在于人的自然,同时也涵盖了人类生物学意义上的身体,而作为“主体”的人类却就此远离了自然与身体,成为一种纯粹的、无身体的“我思”,由此形成了身心二分。换言之,作为“我思”的人类赋予了自然“他性”,同时也将人类自然的身体拉入了他者的范畴之中。作为身体行为的体育自然地作为了身体的衍生,受到了主体——作为“我思”的人类设定,具备了“他性”,成为“他者”。
然而,主体与他者的基本区分尚不足以破解体育概念的无穷性困境。主体的自我超越性与随之而来的异化性则是关键所在。波伏瓦认为,作为主体“人类不是一个简单的自然物种,并不追求物种延续;它的计划不是停滞,它要趋向于自我超越”[12]89。但主体与他者之间又存在着一种吊诡,虽然主体创造了他者,但是主体却存在着异化倾向——因为“主体对它的自由感到焦虑,便在事物中寻找自身”[12]72,所以,主体会把自己的超越性投射到他者身上,希望得到他者的肯定,这样,他者时刻扮演着一个“注视者”的角色[12]251,255。人与体育,正如人与镜中的人像,是主体与他者的关系,无疑人控制着、决定着体育的种种形象,但是体育,却能利用主体异化的倾向扮演着“注视者”的角色,演绎着人的“超越性”。
在波伏瓦“他者”理论的襄助下,体育概念的无穷性困境的人类理智根源便得到了解释。形而上学式体育哲学学者试图以逻辑的或者哲学家的经典言论给予体育一个确定的“体育”概念,然而,他们未尝明白的是形而上学式的逻辑分析是人们用来分析主体人的思想的工具,以这些手段和工具来分析作为他者的体育,所形成的论断当然是南辕北辙的。而Connor所倡导的历史主义式体育哲学则是在根本上规避了无穷性困境,不再使用哲学理论分析镜中人像——他者,转而分析形成他者的主体——人的思想的历史梳理。
2.2 作为“注视者”的体育:走向现象学的体育哲学思考
在波伏瓦“他者”理论下,形而上学式体育哲学试图定义体育概念的逻辑困境得以凸显,历史主义式体育哲学的转向也随之形成——从分析“运动者”转向了分析“思考者”。在前者,以运动者为对象的形而上学式体育哲学中,体育哲学的理论与研究对象发生了错位;而后者,以思想者为对象的历史主义式体育哲学的分析对象是人们以思想史的方式对体育所进行的思考。研究对象的转变带来了理论的转向,一个不得不答复的问题油然而生,即如何在哲学的逻辑起点上将人们对体育的思考区别于人们对善恶、对生命等问题的思考,进而如何将体育哲学区别于伦理学、生命哲学等哲学分支学科。该问题也是体育哲学得以形成的一个基本问题,所以,体育哲学区隔性的思考也是形成体育哲学转向的逻辑基础,而现象学对哲学基本出发点的重新定位为体育哲学的区隔性带来了启示。
毋庸置疑,“哲学的任务在于追求知识或真理”[10]2,而大多的哲学学者便直奔“知识”或“真理”主题而去,所以,哲学的论述往往给人以“开宗明义”“为天地立心”之感,如维特根斯坦便在《逻辑哲学论》开篇直言:“世界是一切发生的事情。”[11]25学科风格使然,无论是采用何种态度、观点,哲学对于世界本原、人性善恶等问题多采用直抒胸臆的方式。现象学则在哲学积极主动思考世界大道之余反观自身,开创性地反思了哲学思考本身的研究理路,并由此带来了一系列的哲学变革。现象学先行者布伦塔诺直言:“对真理问题的研究首先必须找到真理之所在,即在哪些领域内存在着真假问题。”[10]3布伦塔诺的理论转向是深远的。他论道:“显然,物质实体只能是实在的或非实在的,它们本身无所谓真假。真假问题只能出现在与物质实体相对立的那个领域,即意识领域或心理现象领域。”而意识领域可以区分为“心理现象”和“物理现象”两大类,前者是“心理活动”,如思考、分析、批判等,后者是“心理活动的内容(印象、观念等)”[10]3。与之前的哲学思想迥然不同,布伦塔诺并不倾心于分析心理活动的规律也不致力于用哲学理论统摄物理现象,而另辟蹊径关注两者之间的关联的方式——意向性。布伦塔诺认为,“意向性是一切心理现象的最根本特征,意向性就是心理现象与物理现象之间的关系,也是心理活动与其内容之间的关系”[10]3。与其说现象学是一种理论创见,毋宁说现象学为哲学作出了限定。哲学的触角不再在天地间飞扬而专注于人类的思想。转至体育之域,体育的行为、体育的规则等都可以成为人思考的对象。换言之,体育是与人类意识相对的物质实体(物质实体并不仅限于有形体的实体,也可以是社会实体等无形实体)。在“他者”理论的揭示下,这些并非是体育哲学的研究对象。体育哲学研究转向了人类对体育的思考。“人类对体育的思考”的表述是宽泛的,甚至是使人捉摸不透的,但“意向性”概念却为基于“思想者”的历史主义式体育哲学开拓了前进的道路。现象学大师胡塞尔的理论工作是有积极借鉴意义的。在胡塞尔看来,“意义所指的就是意识的意向,对意向的观念性把握就是意义”[10]13。由此看出,哲学的真正作用在于分析人类意识,而意识的重要特征落于意向性,然而只有解读意义才能通晓意向性。在意义层面上,胡塞尔作出了基本的区分,“因为意义是一种观念性存在,也就是典型性或一般性的存在,它与个体性或实在性的存在是对立的。这两者的基本区别在于,个体性或实在性的存在具有明显的时间性,而一般性或观念性的存在则具有明显的非时间性”[10]13。胡塞尔深入了“意义-意向”结构之中,阐明了“赋予意义的活动”是“在语音、知觉和意义意念之间建立联系的意向性综合活动。在这种活动中,下述两种独立的活动被联系在一起:一种是形成表达式,即构成具有交流功能的语音的活动;另一种是形成意义的活动。当人们有目的地使用表达式来表达思想时,就有一定的理智活动赋予表达式以一定的意义”[10]14。
综合存在主义的“他者”理论与现象学的“意义-意向”理论,体育概念的无穷性困境得到了破解,体育哲学形成了新的逻辑出发点——主体对体育“赋予意义”过程的逻辑与历史的展开。因为赋予意义的活动可以分为两部分,这也形成了历史主义式体育哲学研究进程的两个阶段。首先,主体人对作为他者的体育形成认识,即赋予意义的活动的前半部分,形成关于体育的“语音、知觉的表达式”。这便是人们为认识体育进而为体育“赋值”的道路,可以被认作是一条认识论的道路;其次,作为他者的体育对于主体人又扮演着“注视者”的角色,承载着主体的“异化”史。从表面上看,这是一条体育史的道路,但从深层次而言,是厘清人们是如何将体育纳入史学思考的过程,即一条历史哲学的道路。认识论与历史哲学的结合,形成了历史主义式体育哲学的探讨模式。
3 历史主义式体育哲学的哲学考察:体育的文化内涵与身体性
存在主义及现象学的理论构型,破除了形而上学式体育哲学一直困顿其中的体育概念无穷性困境,也进一步丰富了Connor所倡导的历史主义式体育哲学的理论内涵。然而,单纯的理论构型是空洞的,体育哲学是一门部门哲学,既需要与哲学理论衔接,同时需要深入体育的具象。体育哲学又与单纯的体育史研究有着巨大分野,但历史主义的特征又需要体育哲学不能脱离体育史而存在,无论是体育的“他者性”还是“注视者”角色都需要在具体的体育史中落实。历史哲学的考察方式正是历史主义式体育哲学样式的进一步展开。历史哲学理论体系庞杂,但是大多秉承着从历史哲学内在逻辑构建到史学史研究的展开的研究理路。前者以哲学的方式深究历史发展的规律,后者则是将史学研究本身视为研究对象,进而分析史学家的思想传承轨迹[9,13]。布克哈特、尼采与福柯3位学者虽然在学界分属于不同的研究场域,但若以体育的视角观之则能发现其中显然的联系,在历史哲学考察下共同丰满了历史主义式体育哲学的理论,先后展开了历史主义式体育哲学研究样式的2个阶段。
3.1 布克哈特:体育“他者性”的文化内涵
在现象学解析下体育的“他者性”得到了揭示,也摆脱了一直困顿形而上学式体育哲学的体育概念无穷性困境。但仅在现象学层面上的解析是一种“排除”的态度,历史主义式体育哲学仅具备空洞的哲学论述而离体育甚远。不同历史学家对于体育史的层进式界说正是人类对体育展开思考的心路历程,也正是体育的他者性被逐渐灌注的过程。那么,体育史进入史学家的视野,体育与历史学的初见之时历史学的研究样式是极其重要的。这就需要回归到史学思想史的过程中去。实然体育史的研究由来已久,但是其中蕴含的思想方法并非始终都能成为历史主义式体育哲学构建的思想来源。体育史思想方法的转化来源于史学界对体育史中“历史知识”的考量,而这一考量的形成直接来自于20世纪70年代到90年代体育史研究从社会史研究范式向文化史研究范式的转变[18]12-19。文化史研究范式正是历史主义式体育哲学进一步完善的学科契机,也正是布克哈特对体育史的涉入为体育的他者性注入了文化内涵,是历史主义式体育哲学分析理路的第一阶段。
3.1.1 体育“他者性”文化内涵的基本界定
布克哈特对“文化”的诠释是对体育的他者性内涵逐渐展开的第一层。而布克哈特的文化观与他对历史观的解读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在他看来,“历史观所关注的就不是行动、事件或那些看上去促成这些事件的伟人,而是这些事件发生时的文化背景”,由此,“他教会了我们如何把一个时代当做一种文化现象,而不仅仅当作某种政治和权力结构,或政府组织来看待”[14]11。这种研究历史的理念与方法被后世的学者称为“文化史”模式。“文化”一词在今天看来似乎是非常泛化的,宏观至世界发展大势,微观至个人举手投足,皆可称之为文化。但是在布克哈特眼中,“文化”一词却意味深长,它源于人们对历史的解释。“对布克哈特来说,对历史事件的解释并不在于寻找它们的缘由,而在于发现它们的相互关系,寻找原因只是一种片面和伪科学的两维的思想方式。社会并不是一个由事件组成的线性系列,而是一个高度复杂和相互作用的系统,任何因素的某种变化都可能会对其他因素造成多重的影响。而且,人们信仰和行为本身远比他们的信仰是否真实或是否有用更为重要:事件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对作为一个‘事实’的事件的理解,这件‘事实’既非真实,又非虚假,只是为人们所相信。”[14]13-14在这一层说理中,布克哈特揭示了文化史研究的要义所在,人类的“信仰”和“理解”是历史研究的主题。为了区别黑格尔等人,吉尔伯特对布克哈特进行了精要的概括,“无论思想对历史发展有怎样的重要性,人们再也不能从人类理性以及理性无所不在的统治的玄思中,推演出未来的历史发展进程”,“个人的意图”“洞察力和意志”成为文化史学派关注的重点,也成为了布克哈特眼中文化的要义所在[1]11。
布克哈特及其引领的“文化史”转向的意义是深远的。它使史学研究既摆脱了强调抽象精神对历史发展起决定作用的黑格尔式历史决定论,也避免了历史实证主义对因果链的过度强调。布克哈特秉承着这一思维方式,将“仪态、风俗和行为模式以及节日和其他种类的大众文化的表达方式”带入了历史研究之中。“体育锻炼”就以“文化”的形式进入了史学研究的视野[14]13-14。由此,体育史的研究便深烙上“文化史”的印记,体育的“他者性”便以“文化”的模式逐步展现。
3.1.2 体育“他者性”文化内涵的史学展开
在布克哈特的《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希腊人与希腊文明》两部作品中,体育作为一种大众文化的表达形式进入了文化史研究之中。在《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中,他将体育以一种社交形式进行呈现,与文学、音乐、社交语言等社交习俗并举。在今天看来,将体育视为一种社交形式已是一种流于俗套的观点,以此挖掘体育史的流变过程也乏善可陈。所以,从表面上看,布克哈特此举也似乎无法在体育哲学层面上作进一步深化。但若将布克哈特的转变置于历史学的转变过程中,它的哲学内涵就得到了彰显。在《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中,布克哈特在“廷臣”的社交生活中提及了体育锻炼。在他看来,“廷臣”的社交生活是为了“培养他自己”,是自己在“一切事情上,不论是外界的还是内心的都泰然自若、出类拔萃,说明他是一个具有非常独立不羁的性格的人”。体育是一种“建立在个人完美的抽象观念上的”“高贵的游戏”,目的在于形成“完美的所谓的骑士锻炼”[15]421-422。可以说,虽然在该书中所言不多,布克哈特却为体育的文化内涵定下了基调——一个“重新发现个体”的途径[1]68。相比起在《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中对体育蜻蜓点水般的论述,布克哈特在《希腊人与希腊文明》一书中专用了一章《赛会时代》对古希腊竞技进行铺陈展开。与《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一书一脉相承,布克哈特将古希腊竞技落实在个人的生活状态上。但是真正透露出布克哈特意图的是布克哈特对于古希腊竞技的特殊写法。在布克哈特笔下,竞技活动“不再能够满足只是为了提高军队的战斗力而进行的军事训练”,而是一种“生活方式”。参与竞技的人追求的是“高贵、富有和优秀三者相结合”的“优秀品质”[15]225-226。
布克哈特将古希腊竞技的呈现定位于个人的“生活方式”及“优秀品质”的做法在今天看来也已耳熟能详,从中也似乎难以形成体育哲学的衍生。而他对体育史的另一个重要贡献,在于将文化史研究的品性“迁移”到体育史研究之中,具体呈现为他将记叙古希腊竞技的文学作品作为呈现古希腊竞技的素材,甚至不排斥虚幻、甚至虚假的描述。吉尔伯特道破了其中关鞘:“文化史家不打算从材料中了解过去的 ‘事实’;他研究材料是因为它们表达了以往时代的精神。因此,它们是不是准确的事实、是在撒谎或夸大其辞或杜撰都无关紧要。”布克哈特的文化史话语下的生活并非我们的日常生活记录,而是“他们的所想、所思,他们能看到什么和能做什么”[1]101-102。由此,从布克哈特出发,古希腊竞技、古希腊竞技传说与古希腊人的生活连为一个整体,缺少任何一环都无法形成在文化史层面上对体育史的解读。
3.1.3 体育“他者性”文化内涵的哲学衍生
作为史学家,布克哈特赋予体育史以文化史色彩,而与此同时也为体育的他者性进行更为深入的澄明。深究布克哈特在文化史层面上对体育史的梳理过程并非是对体育中的“运动者”的描绘,而转向了对体育的“思考者”心路历程进行梳理。此举正契合了现象学对体育哲学的重建过程,破除了形而上学式体育哲学纠缠于本体论的讨论,进而促成了重要的认识论转向。针对体育本质的思考不再拘泥于“体育是什么”而是“人们是如何思考体育的”。对体育概念无穷无尽的本体论疑问自然得以化解,无穷性困境也不再是体育哲学学者无法绕过的逻辑障碍。
对于体育哲学而言,引入并反思布克哈特的文化史转化并不是一种“三十六计走为上的”的诡辩策略,它形成体育哲学一个整体性的转变,使体育在他者性上重新定位。首先,作为他者的体育,它的价值是意向性的,它并不能给予身体或者身体行为以确定的概念定义,但是却引发人们对自身的文化乃至自身存在的思考;其次,体育的价值又是整体性的。它虽然是出发于人的运动行为,但是它却能够连接人类整体性的知识成果。
可以说,布克哈特对体育史的改造实现了历史主义式体育哲学进行哲学考察的第一个层面:人对体育的关注使体育行为附着了认识论价值。由于不同人群、不同的历史阶段对体育关注的方式不同,造就了体育不同的意义。诚然,布克哈特对体育的关注是有限的,即便他关注了体育锻炼,也未进一步深入。他只是将古希腊竞技视为一个古希腊文化形成和表现的途径。更为苛刻地说,虽然布克哈特笔下的体育已经存在了导向与形成特定文化的特质,但是归根结底它依旧是古希腊文化的一个被动投射。“他者”中的“注视者”内涵,即历史主义式体育哲学研究理路的第二阶段则需要引入同时代的尼采与后继学者福柯才能实现进一步完成。
3.2 从尼采到福柯:体育“注视者”角色的身体呈现
3.2.1 尼采论古希腊竞技:人类身体行为与世界规律
在思想史中,布克哈特与尼采关联颇深。尼采将布克哈特称为“我们伟大的导师”,而布克哈特亦视尼采为知音,赞其文风“宏大和有力”,称其为“伟大的天才”。“除了他们的会晤所产生的创作热情之外,毫无疑问,布克哈特和尼采对希腊世界所共同拥有的最富有意义的独特认识就是希腊和现代文化(按照尼采的看法)中的‘竞技’的重要性认识”,他们二人共同发现“个人之间的竞技和对追求卓越的渴望居于早期希腊人世界观的中心位置”,但是一般认为,布克哈特对竞技和竞赛“已经独立地作出了系统阐述,并开始忙于具体地论证这一发现对于理解希腊文化的各个方面所产生的影响了”[14]29-30。
两位学者之间存在着差异。布克哈特是以一个历史学家身份对古希腊竞技进行研究,其深远目的在于突破兰克等人设置的客观主义历史学派的障碍,更为偏重于历史学研究方法层面上的反思和推进意义。而尼采却更多的以一个兼具犀利笔触与天马行空思想的狂人面貌现于世。他对古希腊竞技史的描述与解释更具备了哲学反思的意味,为体育的“他者性”注入了“注视者”角色的内涵。
尼采对体育注视者角色内涵的注入是有先期理论铺垫的,身体与古希腊人世界观的关联是古希腊竞技形成注视者角色的第一要义。尼采借伯里克利的身体进行阐明。“当他作为著名演说家站在他的人民面前,优美静穆得如同一尊大理石的奥林匹斯神像,镇定自若,身披褶皱纹丝不动的大衣,脸部表情未尝稍改,不苟言笑,声调始终铿锵有力,与狄摩西尼迥然有别……当此之时,他就是阿那克萨哥拉的宇宙的缩影,‘奴斯’的肖像,‘奴斯’在他身上为自己建造了最美丽奇异的缩影,‘奴斯’的肖像,‘奴斯’在他身上为自己建造了最美丽奇异的屋宇。那建造着、运动着、区分着、整理着、俯视着、充满艺术创意、不受外界决定的精神力量,仿佛在他身上人化,变得清晰可见。……‘奴斯’最奇妙、最合目的的举动想必是那个圆形原始运动,因为当时精神还是浑然一体,尚未分化。”“伯里克利言说的效果想必像是这个圆形原始运动的一幅象征图画。因为,他在这时首先也感觉到了一个威力无比、却又有条不紊地运动着的思想旋涡,它逐渐扩展,用一个个同心圆俘获和拖走了远近的一切,演讲结束之时,业已把整个民众重整而致井然有序,使之面目一新了。”[4]221“奴斯”是古希腊人对宇宙大道的一种描述。在尼采的描述中,宇宙大道通过人的言说与动作进行呈现。可见,尼采在文思上延续了布克哈特在文化史层面将人之思与人之史相结合的治史做派,并将其扩展到人之本的哲学本体论维度上。
既然身体及身体行为承载了人的本质,但是在尼采眼中并非所有的身体行为都能形成如此的意义,只有在音乐艺术中呈现的有规范的身体动作才有此禀赋。非造型的音乐艺术——“狄奥尼索斯艺术”正是代表。与注重造型的“阿波罗艺术”相对,狄奥尼索斯艺术是一种醉的艺术世界,“是从本性中升起的那种迷人的陶醉”,“在狄奥尼索斯的魔力之下,不仅人与人之间得以重新缔结联盟:连那疏远的、敌意的或者被征服的自然,也重新庆祝它与自己失散之子——人类——的和解节日”[4]]21-22。探究狄奥尼索斯艺术,正是尼采用以窥视古希腊人内心深处的途径,而狄奥尼索斯崇拜的仪式——酒神歌队的表演正是一管窥镜。而对于歌队的表演,尼采所着眼的并非音调、节奏,而是一种“统一的旋律之流,以及无以伦比的和声境界”。尼采详述了这种充满着象征性的狄奥尼索斯音乐——“在狄奥尼索斯的酒神颂歌中,人受到刺激,把自己的象征能力提高到极致;某种从未有过的感受急于发泄出来……现在,自然的本质就要得到象征的表达;必需有一个全新的象征世界,首先是整个身体的象征意义,不只是嘴、脸、话的象征意义,而是丰满的让所有肢体有节奏地运动的舞姿。然后,其他象征力量,音乐的象征力量,表现在节奏、力度和和声中的象征力量,突然热烈地生长取来”[4]25。在尼采的描述中,由人类的历史到人类的思考再到对世界本质的回答得到了诗意般的阐释。他将古希腊史落实在两种艺术形式的斗争对立上,而这两种艺术形式直接反映了古希腊人的思维方式的转变。然而,尼采并不止步于此,他以象征的方式将人的身体行为与世界本质相关联,这就为体育的哲学解读打开了新的局面,作为注视着人类主体的注视者,体育形成了新的内涵。
体育中的身体与身体行为反映人类主体异化的形式,体育中的竞争正是其中的催化剂。尼采在《荷马的竞技》中为体育中的竞争找到了神话根源——两位“不和女神”。一位“不和女生”是“作为更古老的女神,孕育而生黑夜”,另一位“不和女神”却“置于泥土的根茎上和芸芸众生当中,作为一个更好的不和女神。她也驱使笨拙的人去劳作;倘若一个缺乏财产的人看到另一个富有的人,那么他急忙以同样的方式播种、种植、建造房屋;邻居与努力致富的邻居展开竞赛。对于人们来说,这个不和女神是件好事。制陶人和制陶人怄气,木匠和木匠怄气,乞丐妒忌乞丐,而歌唱家妒忌歌唱家”[2]207。尼采此举为竞技找到了一个更为宽泛的定义,拓展到象征世间的对立统一上。第一个“不和女神”象征着世界中最为基本和宽泛的对立,白昼与黑夜,而第二个“不和女神”则是积极促进人类社会发展的动力。人类社会愈往前发展,人类主体的异化程度便愈深。体育既是世界对立统一的象征性表现,同时也标志着人类主体的异化。在世界对立统一的基础上,尼采还试图在竞技中寻找到象征世界运转的机制——游戏。“对于原始状态的那种混沌的混合,在它尚未有任何运动之时,在不断增加任何新的基质和力量的条件下,究竟需要做些什么,才能从中产生现有的世界及其规则的天体轨道,有规律的岁月交替形式,形形色色的美和秩序……这只能是运动的结果,然而是特定的、精心安排的运动。这种运动的本身就是‘奴斯’的手段,而‘奴斯’的目标该是把同类事物完全分离出来。”[3]122“‘奴斯’既不受原因支配,也不受目的支配,其一切行为,包括对原始运动的发动,只能解释为自由意志的行为,其性质类似于游戏冲动。可见希腊人启齿欲说的最终答案始终是:世界开始于游戏。”[3]127可见,尼采为古希腊竞技赋予了象征世界运行规律的意义,“酒神的颂歌里,人受到鼓舞,最高度地调动自己的一切象征能力……自然的本质要象征地表现自己;必须有一个新的象征世界表现自己;必须有一个新的象征世界,整个躯体都获得了象征的意义,不但包括双唇、面部、语言,而且包括频频手足的丰富舞姿”[4]25。尼采大胆地将音乐与古希腊竞技关联,直言“在荷马与品达之间,必定响起过奥林匹斯秘仪的笛声,直到亚里士多德时代,音乐已经极其发达了。这笛声仍使人如醉如狂,以其原始效果激励当时的一切诗歌表现手段去模仿它”[4]41。
在此,尼采为体育注入了注视者角色——以象征的形式承载了主体人异化的过程。换言之,体育是一种机制,在体育中,世界与人获得了存在的意义。尼采虽然关注了古希腊竞技,但是所言甚少。体育作为注视者的角色并未完全呈现,内在运作机制也尚未阐释清楚,而实现进一步完善工作的则是现、当代法国思想家福柯。
3.2.2 福柯:“注视者”角色与身体行为训诫
尼采与福柯的思想血脉相连。前者的“上帝之死”与后者的“人之死”都是在竭力粉碎形而上学沉珂。但就福柯看来,“对尼采而言,‘上帝之死’意味着形而上学的终结,人杀死了上帝,但人并未占据这个依然空闲着的位置”[7]12,所以福柯致力于完成尼采的未竟之业。在福柯的论述中,文化依旧是论述的重要概念。福柯在《词与物》中阐明了历史的“间断性”,即“有时候,在几年之内,一种文化不再像它以前那样所想的那样思考了,而开始思考其他事物,并且以不同的方式思考”[7]14。不难发现,文化与人的思考方式紧密关联,随着人思考的方式一样间断发展。而福柯的“人已死”中的人是指传统哲学家,尤其是笛卡尔、康德、黑格尔等人笔下的“一切生成和一切实践的原初主体”的“先验主体”[7]14。
福柯的做法完全破坏了形而上学追求普遍、放之四海而皆准概念成立的基础,无论是概念本身还是形成概念的人都是间断的,所以“福柯欣赏尼采的 ‘谱系学’或者 ‘真实的历史’。因为它能区分、分离和分散事物,能释放歧异性和边缘因素,能让间断性在主体身上穿行和涌现,它所依据的是充满机缘的力量关系的逆行和权力的侵占,所强调的是界限、断裂、个体化、起伏、变化、转换、差距、所凸显的就是无先验主体的、分散的、散落的、非中心的、充满着偶然性的多样化空间”[7]15。相比起尼采诗意的表述方式,福柯的论证就更具思想者批判的严整性。如果说尼采确定了体育作为一个人类异化史的注视者的角色,关照着人类的思维规律,而福柯则在注视者的角色中注入了具体身体训诫特征。
相比起尼采对遥远的古希腊先民的竞技活动的描述,福柯则关注了更为贴近现代体育的近代军操,尤其关注了它对人体的塑造过程,从中发现身体训诫对人的“异化”作用。福柯细致地梳理了17世纪到18世纪士兵形象的转变,从17世纪“他(士兵:笔者)的体魄和胆量的自然符号,他威武的标志。他的肉体是他的力量和勇猛的纹章”,而在“18世纪后期,士兵变成了可以创造出来的事物。用一堆不成形的泥、一个不合格的人体,便可以造出这种所需要的机器。体态可以逐渐矫正。一种精心计算的强制力慢慢通过人体的各个部位,控制着人体,使之变得柔韧敏捷。这种强制不知不觉地变成习惯性动作”[6]153。由此福柯认为,从17世纪到18世纪,士兵的形象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由身体的自然符号变成了作为“机器”的人。简言之,便是人的身体逐渐被视为一种机器。在这个过程中,两种精神性因素被“造就”出来,一是“灵魂的唯物主义还原”,属于“解剖学-形而上学领域”,负责“功能与解释的问题”;二是“一般的训练理论”,属于“技术-政治领域”,是“由一整套规定和与军队、学校和医院相关的、控制或矫正人体运动的、经验的和计算的方法构成”[6]154。不难看出,这两种精神性因素就是实现体育概念形而上学定义的关键,诸如“体育是有规则的身体运动”“体育是身体教育”等交相辩难又层出不穷的定义方式看似千变万化却又万变不离其宗,“体育是什么”的发问方式正是一个“解剖学-形而上学领域”的逻辑框架,而宾语“有规律的身体运动”“体育教育”则是后者“技术-政治领域”。可见,福柯在对军操的人类身体“异化”过程的谱系学式描述却实实在在地将有关体育的形而上学概念全然解构。形而上学概念,并非一个先验的存在,而是在运动行为中“被制造”出来的。为体育行为寻找一个形而上学的定义正是一个本末倒置的做法。体育作为人类异化史的注视者,福柯为其注入了自我呈现与自我解构的特性,同时又符合了历史主义式的考察过程。
从尼采到福柯,虽然两人对古代体育与现代军操的论述都较为简短,但却为当代体育哲学的改弦易辙奠定了理论基础,他们两人共同完成了体育作为人类主体的注视者角色。尼采赋予了体育注视者角色,而福柯精致地刻画了体育的注视者角色。前者为体育造就了批判性,通过审视体育可以窥视人类思维转变的历史,而后者则为体育赋予了生成性与解构性,形而上学的体育概念正是在体育的实践中、体育与其他社会机制千丝万缕的关联中逐渐生成继而逐渐消散的。只要体育的实践继续存在,概念的变迁既是有迹可循,又是生生不息。
4 走向开放的体育哲学
体育概念的无穷性困境是横亘在当代体育哲学发展道路中的斯芬克斯。斯芬克斯之谜的答案正是人一生的历程。面对无穷性困境的形而上学式体育哲学已经遭遇了逻辑天花板,无论是精巧的哲学理论还是深刻的哲学家思想都在这层逻辑天花板下溃败下来,使当代体育哲学的发展拘于表层的横向衍生而很难深入哲学研究腹地。历史主义式体育哲学是绕过了形而上学式体育哲学的思维囹圄,展开了体育哲学的新的思维图景。
形而上学式的思考方式及在此样式下生成的体育哲学是较为符合当前学人的思维方式——对概念的讨论定义继而生成对认识问题、伦理问题的讨论,可谓是“逻辑严整”的系统化体育哲学推进方式。然历史主义式体育哲学诞生于形而上学式体育哲学主导之时,所以它的确立需要在逻辑起点和方法论层面进行重新的定位。
4.1 体育的“他者性”:历史主义式体育哲学的逻辑起点
如果说形而上学式体育哲学的逻辑起点在于清晰定义体育概念的话,而定义体育概念的无穷性困境正为历史主义式体育哲学提供了发展的契机,形成了新的逻辑起点。在历史主义式体育哲学理论的重新审视下,体育概念的无穷性正是体育本身他者性的呈现,也正是说明了体育是从人主体中生长出来的,受人主体的变化而变化。体育本身就不具备被形而上学化的基础,它只能形成反映人类主体异化的注视者作用。
在体育的他者性与随着形成的注视者角色下,形成了体育哲学的逻辑起点,首先它是排斥性的——排斥了单纯的定义行为在体育哲学研究中的核心地位,而转向解释人对体育的思考过程,继而形成了历史主义式体育哲学的内在建构性。从表面上看,历史主义式体育哲学解构了先前的尤其是形而上学式体育哲学研究,使原有从概念定义出发的体育哲学讨论方式限于窘境,甚至无所适从。而从深层次看,历史主义式体育哲学研究范式形成了新的体育哲学分析的阐释性进路。任何样式的体育哲学都不能回避引入哲学家及其思想,解析体育活动的诸多表现形式,而历史主义式体育哲学的做法是为前两者带来新的组合方式,形成新的图景。
4.2 体育的“注视者”角色:历史主义式体育哲学的逻辑展开
4.2.1 哲学家与体育哲学
毫无疑问,哲学家及其引领的思想流派是体育哲学得以推进的重要思想源流。但是如何借鉴、引入哲学家的理论与方法一直萦绕在体育哲学学者们的心际。“拿来主义”“开卷有益”式的借鉴固然无可厚非,但无法摆脱的,是体育学与哲学毕竟是处于不同的学科背景,有着全然不同的研究对象[5]。对哲学理论进行目的性的裁剪,进行削足适履般的借鉴方式,在体育哲学研究早期往往是不得已为之,而在体育哲学研究者的学科背景构成日渐丰满的今天,引入哲学理论的方式的重要性日益凸显。历史主义式体育哲学所转变的,正是在体育哲学中引入哲学理论的方式的转变。
历史主义式体育哲学秉承的基本出发点是体育是作为人类的创造物。哲学的价值在于人类对于自身、创造物及外在世界的思考。无论是文化史学家,还是尼采、福柯等哲学家,都是深刻地检讨了人类的思维方式。基于他们对体育或者身体活动的思考而形成的思想史考察正是历史主义式体育哲学的展开。虽然从表面上看,历史主义式体育哲学不能形成形而上学式体育哲学所宣称的对体育本体的确定性认识,形成种种“坚实的”逻辑构建基础上的哲学理论体系,但是在历史主义式体育哲学的视野下,哲学家对体育的论述不再提供对体育“本质”“规律”的正当解释,但却能形成人类对体育进行哲思的“工具箱”。而历史主义式体育哲学所秉承的正是一种历史解构与谱系学的方法,检讨在不同时代人们在各个领域对体育,尤其是对其中身体与身体行为的认识,并将其中的思想逻辑核心进行呈现,以凸显人类身体意识的转变过程。
4.2.2 体育史与体育哲学
针对当代体育,社会学家布迪厄有一个著名的“布迪厄之问”——为何懂得体育的人不知如何言说,而懂得言说的人却无视体育?布迪厄从社会学角度发出的疑问却引发了更为深层次的哲学思考,即言说与体育之间是否存在着天然的隔阂。布迪厄的深意在于指出了体育无法与人类言说方式匹配,是一种“沉默的身体行为”。针对“布迪厄之问”,当代欧洲部分新锐体育哲学学者将体育哲学引向了体育科学的方法论研究实在是矫枉过正的做法[5]。历史主义体育哲学虽然专注于人的思维,但是在一个全新的维度上连接了人的思维与体育哲学,重新规定了体育哲学的任务。从学科本身的发展层面上看,历史主义式体育哲学是以变革的态度迫使体育哲学直面当代哲学的变革。20世纪现象学大家梅洛•庞蒂为哲学重新规定了任务,“哲学不是一个词,它对‘语词的意义’不感兴趣,它不为我们所看见的世界找一个语词代用品,它不把世界转变成言说物,它不置身于说出的或写出的范畴内,就像逻辑学家不置身于陈述中,诗人不置身于诗句中,音乐家不置身于音乐中那样。它要的是把事物本身、把事物沉默的本质引向表达”[8]13。在现象学看来,追求概念的准确定义正是一种“找一个语词代用品”的做法,也正是形而上学式体育哲学的理论基础。历史主义式体育哲学是现象学反思与历史哲学梳理协作的产物。现象学反思使体育哲学不再试图将“体育现象”转化为各种语词,即不再试图将定义“正确”“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体育概念为首要任务,而完成的是一个让“沉默的身体行为”发声的工作。现象学完成了历史主义式体育哲学的理论基石,但历史主义式体育哲学只有“他者性”的理论基石无疑是空洞的,只是形成另一种形式的形而上学式体育哲学。历史主义只有在具体的历史情境与史学史情境中才能实现对形而上学的批判,才能真正使“沉默的身体行为”发声。体育史、体育史学史与现象学批判相结合正是一种发声机制,兼顾了人的思维,同时又指向于体育,是一种现象学“意向-意义”理论的实践化,也是将沉默的体育引向表达的方式之一。同时,体育哲学与体育史的结合也并非单向度的,体育史亦可以在结合的过程中反思治史的理念与方式,使体育史的研究能向史学史与思想史研究纵深发展。
历史主义式体育哲学是一种新的体育哲学样式,突破了原有的追求概念体系严整的形而上学式体育哲学,是当代哲学家对形而上学展开批判时的产物。同时,它也是一种开放式而非封闭式的哲学样式,也在一定意义上体现了“大而全”,试图解释各种体育现象与体育规律的体育哲学理想已是室迩人遐。体育史及体育史学史的涉入只是其中一条批判路径,随着哲学视野的拓展,更多的思想工具会以更为合理与恰当的方式进入体育哲学。
[1] [美]费利克斯·吉尔伯特. 历史学:政治还是文化[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11,68,101-102.
[2] [德]弗里德里希·尼采.尼采遗稿[M].哈尔滨:黑龙江教育出版社, 2012:207.
[3] [德]弗里德里希·尼采.希腊悲剧时代的哲学[M].北京:北京联合出版公司,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14:122,127.
[4] [德]尼采.悲剧的诞生[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
[5] 高强.体育学与哲学:基于学科关联的历史考察[J].体育科学, 2016,36(11): 82-90.
[6] [法]米歇尔·福柯.规训与惩罚[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9: 153, 154.
[7] [法]米歇尔·福柯.词与物——人文科学的考古学[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1.
[8] [法]梅洛·庞蒂.可见的与不可见的[M].北京:商务印书馆, 2016: 13.
[9] 瞿林东. 继承白寿彝先生的史学史思想遗产[J]. 北京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0,(3):5-13.
[10] 涂纪亮.胡塞尔的意向性理论[M]//中国现象学与哲学评论(第一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5.
[11] [奥]维特根斯坦.逻辑哲学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25.
[12] [法]西蒙娜·德·波伏瓦.第二性[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6.
[13] 杨耕,张立波. 历史哲学:从缘起到后现代[J]. 学术月刊,2008,(4): 32-39.
[14] [瑞士]雅克布·布克哈特.希腊人与希腊文明[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
[15] [瑞士]雅克布·布克哈特.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6.
[16] CONNOR, STEVEN. A Philosophy of Sport[M]. London: Reakti-on Books, 2011:14-19
[17] MCNAMEE M, MORGAN W. Routledge Handbook of the Philo-sophy of Sport[M]. London, Routledge, 2015:275-276.
[18] POPE S W, NAURIGHT JOHN. Routledge Campanion to Sport History [M]. New York, Routledge, 2010:12-19.
From“Metaphysical”to“Historical”Philosophy of Sport—An Reflection from the Infinite Dilemma of Sport Conception
GAO Qiang1,KANG Yi-meng2
1.School of Physical Education and Health, Sino-French Joint Research Laboratory of Sport Science,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Shanghai 200241, China; 2.Zibo Vocational College,Zibo 255314, China.
“Metaphysical” and “Historical” are two patterns of philosophy of sport. The metaphysical pattern is trapped in the “Infinite” dilemma of “sport” conception, while the the historical pattern is just ongoing. Whereby the phenomenology and existentialism deconstruct the “Infinite” dilemma of “sport” conception, the logical difficulty of metaphysical pattern is dredged ,which leads to uncover two basic characters of “the other” and “observer” in sport that inspires the historical pattern. With the theoretical support from Burckhardt, Nietzsche and Foucault, “the other” and “observer” have got further development in sport as cultural and bodily character, which construct the basic framework and construction of demonstration of historical philosophy of sport. As a hopeful pattern of philosophy of sport, historical pattern inspires fully new theoretical way leading to it more appropriate to the development of contemporary philosophy.
G80-05
A
1000-677X(2018)01-0063-08
10.16469/j.css.201801009
2017-12-05;
2018-01-12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12CTY001)。
高强,男,副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体育哲学与体育史,E-mail:gaoqiang.ecnu@hotmail.com;康义萌,男,讲师,主要研究方向为体育教育史,E-mail:55103712@q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