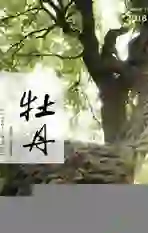五世缘
2018-01-25汪天钊

一
我有两个亲外婆,年少的我和伙伴们在一次玩耍时无意之间透露了这么一个情况,当时就有聪明的孩子反驳,态度不用质疑:不可能!我是个开蒙很晚的人,初中了还不辨亲戚关系,一直认为所有的亲戚关系都理所当然,有两个亲外婆也是正常的事情,我说有什么不可能,两个就是两个,你们只有一个才是不正常呢。
一个外婆家所在的村子叫“谢岗”,另一个叫“周小庄”。为了区分开来,我管谢岗的外婆叫“谢岗外婆”,周小庄的叫做“西乡外婆”。两个外婆的年龄不差上下,都是慈祥和蔼的高龄老人,從没有感觉出她们哪一个对我有明显的疏远冷淡。孩子们的自制力太差,做错事并不要紧,要紧的是孩子们做出很多危险的事情,而后果和伤害一无所知,比如在柴禾窝里玩火,去离村很远很深的围堰里洗澡,爬很高很细的树枝头,把鞭炮放在玻璃瓶子里点燃,把老鼠药当做糖丸享用,孩子们的事让人担心着呢,我在不同时间去了不同的外婆家,两个外婆关切的表现如同一个人,可两个外婆谁也不认识谁,也从来没有碰过面。
谢岗外婆去世时我还没有上学,西乡外婆去世时我已经上了初中,但谢岗外婆在我的印象里保留得更早更深。
谢岗在我们村子东面,是邻村,大概二里地,两个村子的田地只隔了一条小河,干活的人经常站在小河对岸打招呼、拉家常。谢岗的“近”给走动造就了客观上的便利,抬脚就来抬脚就走,只要愿意,一天打几个来回都不晚;西乡的“远”带来了很多不便,除了年来节道,平时很少走动。自我有记忆时,西乡的外婆从没有来过我家;我最初知道的亲戚,就是谢岗;我去的最多的亲戚,也是谢岗;我最熟悉的老表伙儿,也是谢岗的老表伙儿;我关于亲戚的记忆,大都与谢岗有关。
那时的农忙季节,大人们经常在夜里还要下地干活儿,比如乘着如同白昼的月光割麦拉麦,秋天挑红薯擦红薯干。我们还小,睡熟了被偷走也不知道,哪里看管得门户,这时候谢岗的外婆就来了,住到我们家里。听母亲说很多时候她并没有让谢岗外婆来,是她主动要来的,我家里的情况,似乎她比我们家里所有成员更了解,需要的时候她就会准时出现。老人们不知道是因为好操心还是本来就少瞌睡,几岁的我在深夜醒来时,屋里的煤油灯大都在亮着,谢岗外婆不是在收拾这就是在收拾那,什么东西都摆放得有条有理,家里也难得的干净。我还模糊地记得谢岗外婆会纺线,有天晚上一直纺到我母亲从地里回来。墙是土坯墙,格外吸收光,谢岗外婆变了形的影子似乎是被镶嵌在了墙上,能触摸到凸凹感,沧桑厚重。
说起来我恨不得钻地缝儿,我尿床一直尿到初中,每次在梦里都是被憋得慌里慌张地找地方,总算寻到了一个没人的地方或厕所,可尿完马上就醒了,糟了,尿在了床上。在学校里我不敢晒被子,湿的地方大都是被我压在身下暖干的。只要谢岗外婆在我们家里,我尿床的次数相对少了很多,谢岗外婆总是在一定的时间段里千呼万唤,我这才迷迷瞪瞪地醒来,站着睡着觉尿了尿。
谢岗外婆是小脚,岁数又大,走路摇摇晃晃,来去要接送她,她坚持不让,只好由着她了,她掂着小脚碎步自己来又自己去。两个村子之间的那条绳子一样的小径,田野里的庄稼,一年的春夏秋冬似乎都被谢岗外婆的身影摇晃得醒来或睡去。
长大了经常听父母说,我们家历经很多艰难的关口,都是在谢岗外婆家的帮助下才度过的。
我家是地主成分,原有的房屋都被分掉,爷奶在父亲十多岁的时候就去世了。我父亲弟兄三人,我大伯和小叔去世时也都很年轻,我父亲其实是一个孤苦伶仃、无家可归的人。我父亲是一个乡村教师,常年漂泊在外,照顾不了家,我母亲嫁给父亲之后的十多年,原本就没有在我们自己的村庄里生活,一直住在谢岗的外婆家。
我大哥对谢岗外婆家的感情远远比我们深厚得多,他是在外婆家出生的,跌跌撞撞学步,呀呀学语,直至一个无忧无虑的少年,压根还不知道谢岗并不是自己的家。大哥的名字和我们姊妹几个不同,是按着舅家老表们的字牌起的,他实际上已经成为了外婆家大家庭的一份子了,他和舅家的老表们已经融入了一种亲弟兄们的情谊,这和他们后来维系着一种旷世持久的来往有着必然的联系。
我没有见过我的谢岗外公,当时我听到他的事情并不以为然,现在我才知道,他的境界我只能望之项背,虽然谢岗外公也是芸芸众生中的一个世俗之人。有年秋收农忙时,外公晚上在场里看庄稼,目的毫无疑问。有天晚上真的来了盗贼,他正好醒着,村人彼此都很熟悉,从任何一个方面都能轻易地判断出一个人是谁,比如身高、走路的样子、说话的声音、哪怕是一声咳嗽声。所以,那盗贼一出现,谢岗外公一眼就认出了他。他正好面对着他,话说郑板桥苏轼老前辈们曾留下了吟诗驱贼的千古佳话,谢岗外公虽不会吟诗,但他完全可以佯装弄出一些声响来以示提醒,比如咳嗽几声。可外公竟然轻轻地翻过身去背对着盗贼,那盗贼悄悄地观察一会儿,没发现动静,结果大模大样地偷走了几捆子的谷子,就象拿自己的一样。
我父亲年轻时候干了一件他一生都难以启齿的事情,他在我们子女面前从没有说过,是母亲亲口告诉我的。那年家里卖了一头驴,那头驴是家里唯一值钱的家当,卖的钱用来是买房子的,说好的,第二天一手交钱一手写契约,我母亲从谢岗回到我们村里住的房子是借住的。头天晚上我父亲却神使鬼差地去赌博了,运气非常不好,一直输,他输红了眼,若不是赢家坚决主动结束,整个驴子的钱都能输光,但还是输掉了半个驴的钱,买房子自然成了泡影,父亲不敢说,他哪敢说啊,死了的心都有。没过几天谢岗外公来了,父亲本以为外公要狠狠地训斥他一顿,但谢岗外公似乎什么都不知道,只是问他还缺多少钱才能把房子买下来,父亲嗫嚅着回答了,没想到谢岗外公竟然有备而来,把缺额补上了。自此以后,我家才居有定所,真正拥有了属于自己的一个家,除了我大哥,我们姊妹几个都是在这个家里出生的,长大成人,生活。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是一个极其特殊的时期,在很多人的记忆里,都是无法忘却、痛彻心扉的痛。我的大姐——一个七岁健康活泼的女孩子的生命就在那一年停止的。我大哥和我母亲也都已经饿得面黄肌瘦,几乎认不出来了。事实上,他们如要继续呆在自己的家里,也逃脱不了我大姐的命运,因为村里食堂已经断了顿,两天没有任何东西吃了,母亲当时已经头晕目眩。就在这时候谢岗外婆来了,她把我母亲和我大哥接了去,谢岗的情况也非常严重,但不管怎样食堂还没断顿,外婆家从自己挣扎在生命线上的食物里榨挤出来一份儿分给我母亲大哥,他们把以沫相濡诠释得一丝不苟,至真至纯。
我父亲曾经犯过错误,被劳动改造了几年,我的母亲——一个个头瘦小单薄、带着几个幼小孩子的村妇独自一人面对生活,艰难和窘迫可想而知,体力上的磨难,歧视的羞辱是对一个女人命运的最大嘲弄。在这期间,得到最多最大的帮助,自然还是谢岗外婆家,即使这种力量可能极其弱小,却是决定天平倾斜的那股力量。当父亲回来时,交还给他的依然是一个好端端的家、完整的家。这绝对是一个非常家庭,我父亲是幸运的,我们是幸运的,我们家是幸运的。
二
我父亲是一个散漫惯的人,一生都得过且过、随遇而安,他一生一世最大的、能夠看得见摸得着的物质财富就是我家由谢岗外公资助购买的三间土坯房子,低矮窄促、破旧昏暗。在我眼里,岁月的颜色是乌黑的,因为我家的屋子都是乌黑乌黑的,不知道经历了多少岁月。房子经常修补,不知道修补了多少次,漏雨的地方总是不能根治。父母二人一辈子就在这样的老房子里生活,直至终老。我母亲总是说跟着父亲一辈子是窝窝囊囊的,从没有扬眉吐气过。我记事起,结婚的条件就提高了,房子要求的是砖墙,如果有“出前檐”,挑剔的村姑都无话可说。到了我结婚时,平房、楼房已渐成风气,然而,我们弟兄三人都是在这样的老房子里结婚生子,然后依次离开。
家庭成分不好,又没房子,加上我大哥本人个头瘦小,肤色较黑,他的婚事曾是一个无解的难题,一晃就是二十七八岁,在农村,绝对过了茬儿。事实上,像我大哥一样境况的那代人,很多都打了光棍,或结婚很晚。有的娶了四川女人,有的娶了离过婚的媳妇,拖儿带女的。谢岗外婆家有三个舅舅,大舅二舅都是本分传统的农民,八十多岁了还能刨地开荒,日子殷实。小舅是个“公家人”, 在县城工作,在当地算是一个不大不小、多少有点影响的“官儿”。小舅对我们家帮助都是潜在的,根本性的,影响着我们家庭的整个走势、格局。人挪活,树挪死,大哥一直呆在家里无疑死路一条,小舅给大哥找了个差事,在当地油田的一个单位食堂里上班,油田的经济效益非常好,工资高,发放及时,福利也好,是无数人向往而不能至的一个地方。我大哥在食堂里其实就是一个伙夫,经过多年的历练,厨艺还算可以,有几样拿手好菜。我见识过大哥的刀功,真不错,他能把葱切得如头发丝一样细,他蒸出来的馒头也格外的筋道。千万可别小瞧了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的临时工,对于乡下人来说,绝对是人生的脱胎换骨、命运的重大转折,让人羡慕嫉妒恨,应该就是冲着大哥是一个“有工作”的人,才有人肯给大哥提亲,才有姑娘嫁给了他。婚后大嫂肠子都悔青了,他们两口子生气时,大嫂总是骂我大哥:驴屎疙瘩外面光,听着好听!其实大嫂也挺满足的,我大哥脑瓜子灵活呀,从油田食堂里回来之后学会了照相,在镇上开了一家照相馆,大嫂当起了老板娘。还在镇上买了房子,是走出村庄最早的人家。
我二哥的一生都是在小舅羽翼的庇护下生活着,他对小舅的感情比谁都深厚。二哥上中学时就跟着谢岗小舅,当时小舅家并不富裕,其他人还都在乡下。我二哥高中毕业时,正好小舅的单位在社会上招聘代办员,二哥便在其中,虽不能彻底改变命运,但在那个时期,在一定程度上,也算是给他人生涉世之初提供了一个较好的平台,把一个家庭所有的不利因素降低到了最小程度。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去新疆打工的人,大部分都是盲流,比如摘棉花,非常艰苦,去了一次就很难想去第二次。那时我二哥也去了新疆,但有别于盲流,没有经历过种种不可想象的非人遭遇,他去的是一个应该叫做“家”的地方,因为他带着小舅的亲笔信。小舅的舅家老表在新疆兵团工作,那封信不是简单的嘱托,而是一种信誉,小舅的舅家老表当年在最艰难困苦的时候,也受到了谢岗外婆家不少的帮助,他们一直也在默默地铭记着。他们对我二哥的好,是把我二哥当做报答谢岗恩情的对象。有了这种背景,我二哥在新疆安稳地生存了下来,长期定居在了那里。
我姐是天底下最笨的一个人,学习成绩一塌糊涂,家务也做不好,她瘦小单薄,笨嘴拙舌,懒惰,在她身上发现不出有任何的优点,我父母一直担心她将来的生活,不知道会把她折磨成个什么样子。老天就是这样的不可思议,姐却是天底下命运最好的一个人,她来到县城做生意,起初租了一个摊位,卖化妆品、领带、裤头、袜子等小商品,后来又卖衣服,生意居然做得有声有色,由此我姐才嫁在了县城,完成了由一个村姑到“城里人”的世俗过程。我姐夫对我姐也非常好,家务几乎都是姐夫做的,冬天多冷的天,都是姐夫喊我姐起床吃饭,现在还是。市场就在我小舅家北边,很近,虽然小舅家和我姐做生意没一点联系,我姐总是说,每想到小舅家就在身旁,不由自主地就踏实和自信起来,这种支撑是什么也不能替代的。
按当时的政策,我父亲退休了符合安排一个子女接班的条件,我便接了父亲的班。当时教师的情况很不好,拖欠工资拖得很厉害,我觉得自己来源于旁门左道,呆在教师行业里不合适,我父亲竟然也迁就了我的任性,觉得要改变一下,但他最终还是放下了一个男人的尊严,花甲之年的他才知道凭借自己的力量来完成这件事是多么的艰难,他不得不再一次求助于谢岗小舅。此后,我便在县城里当时效益较好的化肥厂里上班,人生有了将近十年的“工人”历程。或许,正是因为这样的身份,我结婚是“裸婚”,只花了二百块钱,尽管妻子从来不承认这种事实,从没有因为后来我由一个工人变成一个农民,一个农民变成一个行色匆匆、四处漂泊的农民工而说一个悔字,也没有因为生活窘迫而说一个怨字、一个苦字。
非常惭愧,我们姊妹几个鸡犬还是鸡犬,但切身沐浴了恩惠,恩惠是把不确定的变成了确定,偶然变成了必然,恩惠不是赐予的,而是雨点落在头上一样的降临。
母亲父亲相继去世后,我觉得自己就是一个被抛弃的孩子,孤苦无助,再也没有了依靠。一次我在小舅面前放声大哭,泪流满面,哭得嗝嗝的,一句话都说不完整,在场的人们都惊愕地看着我。我不记得我当时都说了些什么,小舅都说了什么,只记得他喊了我一声孩子,我哭得更厉害了,全身都在剧烈地抖动,一声孩子,是我这么多年来听到最动听最温暖的语言。
三
走亲戚似乎是一种俗不可耐、毫无意义的事情,你来了他往了,你给他拿多少东西,人家也再给你带多少东西,最后还是自己的,实质上就是你吃亲戚一顿饭,亲戚吃了你一顿饭,彼此来去匆匆,彼此都要为对方忙上忙下。以前走亲戚的道道更多,端午节带什么礼物,八月十五又是什么礼品,春节又是什么都是有讲究的。在我们老家,现在还在遵循着好多习俗,一年一年地重复,一年一年地传承下去。走新亲,则更需谨慎了,否则能直接影响着婚事,或者引起一场很大的冲突。
亲戚之间的关系远远不是这样简单,很大成分上,往来是亲戚关系的一种直接体现,维持着亲戚之间相对恒定的温度,不管这种温度高或低。有很多的亲戚,可能因为某一个事情就反目成仇,一生一世就再也没有来往。亲戚关系也并不是七大姨八大姑一样浅显地依附,比如一家贫穷,一家富裕,富裕一家趾高气扬,财大气粗,或经常歧视贫穷,那么贫穷一家也绝不会一味地趋炎附势,断亲的时候痛定决然,就是要饭,也要绕过他的门槛。所以亲戚的关系有时候是很脆弱的,能够坚持往来的本身,就是一种沉淀,沉淀着相互之间的那种平淡的亲情、理解包容。
晚年的老人们,腿脚不便,很难相见一次,相见一次,他们就唠叨个没完,从光着屁股唠到古稀之年,从上一辈唠到孙辈家庭里的每一位成员,去世的健在的,吃喝拉撒、鸡毛蒜皮子。对于他们,亲戚可能意味着是一种倾诉,这种倾诉有别于世界上任何一种的倾诉,没有任何顾忌和负担。分别时,一个坚持要送,一个坚持不要送,在争执当中他们走得很远了。一个说,慢点。一个说,哎,知道了。一个说,不知道时候才能再见面,能不能再见面……这样的分别,往往就是诀别,生死两茫茫。
亲戚当中,第一个去世的是谢岗外婆,在夏天卧床不起,生了严重的褥疮,褥疮里生了蛆。接下来是谢岗的二妗子和西乡的舅,二人都是食道癌。我上初一时,西乡外婆去世了。我高中毕业那年,谢岗大舅去世了,患的肺癌,紧接着,大妗子也患了肺癌去世,她大约是吸了二手烟的缘故,我大舅的烟瘾很大。一个个地相继去世,无论是感情或深或浅,每回想起来,都是一种黯然。他们毕竟都是和我们有着生命交集的人,有着内在联系的人。
亲戚走动没有任何规则,似乎也存在着一种规律,就是两个家庭中其中一方最后的一个长辈去世,也就预示着亲戚终结的可能。主动权就由他们的儿子掌握了,如果他們儿子当中没人担当起走亲戚的角色,那么亲戚就到此为止。一旦双方的长辈们都去世了,终结没商量,绝大部分人家的亲戚都是这样的状态下终结的,也就是说,亲戚走动实质上只是一辈儿,老表们这一辈儿相互走动的就非常稀少了。
走亲戚,走亲戚,不走动,就不是亲戚了。
随着亲戚长辈们的不断去世,我家的亲戚越来越少。当我的大舅和大妗子都去世了,和大舅家的关系终止了。当我的姑父去世了,和姑家老表的关系终止了,当我的母亲去世后,母亲娘家的亲戚全部终止,后来我父亲也去世了,我想,我家的亲戚应该是全部画上句号的时候了。让我万万没有想到的是,当年在农历十月一,不仅仅是谢岗的老表们都来了,谢岗小舅再一次出现在我的面前,他是当天所有亲戚当中唯一的一位长辈。
每年大年初二,我准时就会到小舅家里走亲戚,每当见到了小舅,就感受到了一种莫名的慰藉,我不会向他索取什么,他也没有能力为我做些什么,一切都不为,只为他能健康地活着,我能看到他。小舅还是走了,四年后因为肾功能衰竭而去世。
我小舅去世后,花妗子曾劝我:孩子,你们都忙,我一个将死的人有什么可牵挂的,不要来了吧!我理解花妗子的意思,我说妗子你怎么这样说话,只要您在,我无论如何也要把我这一辈儿走完啊!我分明也看到花妗子眼角里的泪花,她说,好,孩子,将这一辈儿走完!
近些年,我一直在外打工在外,全家也都在外地,平常的一切都简化掉了,春节也没回去。见到花妗子的次数更少了,但每次回去,我都要看望她。见到花妗子我都忍不住地说道:妗子,好好活着,活着一天,我回来就有一个家,就有归依!
花妗子也一再叮嘱,好,好好活着,娃子,你的孩子结婚时可要一定说要,老妗子一定要去!
我说,好,一定,一定通知你!
花妗子是老亲旧眷当中唯一的、最后的长辈了,她八十多岁了,已是人生风烛残年,看上去虽然很矍铄,但我知道,她就像一株即将成熟的麦子,一次比一次勾头,更像春蚕,一时比一时透亮;不知道为什么,随着年龄的增长,现在的感情却越来越脆弱,每次分别,眼泪都在眼眶里打转,我都不敢回头再看她一眼。
四
对于逝者,我们那里是要待大客的,待大客的意思就是招待客人的酒席是全桌酒席,十几个盘子十几个碗的,必须要有火腿儿、鸡子、鱼等基本大件。待大客是隆重的,是对逝者的一种纪念,也是昭示逝者曾经的存在和现在的存在。很多生者一生卑微,蚂蚁一样活着,死后才成为真正的主角,成为中心,那么多的人和他发生着这样或者那样的关系,他不曾辉煌,却与辉煌有关。一般情况下,要为逝者待五次大客,埋葬当天,一个月,一周年,三周年,十周年,十周年是最后的一次,十周年之后,逝者才算是真正意义的安息,很少人再来打扰他,他给这个世界带来的各种信息才趋于尘封。
一个人不管他生前是多么的显赫辉煌,多么门庭若市,多么善良或者是多么丑恶,一旦死去,罕有人能记得他,很快被无声的岁月所掩埋,被无数新生的啼哭所代替,被生者依旧忙忙碌碌的生活所践踏,被尘世继续的喧嚣所封存,一切继续,一切平静如初。他去世的日子,记得他的亲人和亲戚也是一次比一次地减少,一个月虽然离得太近,但还是有人太健忘,事到临头才猛然狠狠地捶打一下自己的额头,大声惊呼:糟了,看我糊涂得!一周年,有的亲戚还在惦记着,但就是记不清具体的日子,需要提醒或者重新确认。三周年,除了逝者的子女能记着逝者的祭日,所有的亲戚都已经淡忘,记着的,仍然需要提醒或者重新确认。抱外孙不如报门墩,逝者生前对待外孙和自己的孙子一样对待,甚至还有些偏袒,但很多逝者的孙子和外孙连葬礼都不能参加,别说祭日了,祖辈的生死、曾经对他们的悉心呵护远远比不得上他们正常的生活和一场轰烈或者不轰烈的恋爱。到了十周年,很多粗心的子女都需要提醒,至于亲朋好友的答卷,都是一张白纸;所以待大客的人数是一次比一次少,一次比一次冷落。
2015年,我父亲去世已经整整十个春秋了,为不为父亲待十周年大客,我纠结了很长时间,和我姐有着很大的分歧。我说待什么大客啊,老亲旧眷多年前都不走动了,都断了亲,人家有事没通知咱,咱不知道也没有去,现在怎么好意思通知人家呢?就是自己的家人也难以聚在一起——我大哥也已经去世,侄子在南方打工,二哥远在新疆,父母生病到死,他都没能回来见上一面,平时就没有联系,大家庭中有他没他没有什么影响;姐的儿子在外地上大学,我全家在洛阳,到时候能不能全部回家是另一回事,这样算来,父母养育了四个儿女,在他们十周年的时候确定能回去的只有我和我姐,所以我的意见是亲戚一律不待,自家人能回去的尽量回去,最好一定回去,照一张全家福,这是很难得一次机会儿,也是最好不过的理由了。姐说这是父亲最后的一次事情了,为什么要省略?只有惊动起来,这才是真正意义的纪念,我懂我姐说的,虽然是给活人看的,有点世俗,至少让父亲在那些认识他的人们的记忆里再一次复活,再一次成为议论的主题,念着他的好念着他的为人念着他的事情,至少再刷新一次父亲曾经的存在,让他消失的速度再慢一点,再慢一点。我妥协了,该通知一声就通知一声吧,实际上父辈们的亲戚能通知的就只剩下两家了,一家是谢岗的花妗子,一家是姑家老表。
当天,该来的人都来了,都在意料之中,也有意外,但意外的稍微转动一下脑筋,也不意外,比如谢岗二舅家的二老表来了,二舅家大老表的儿子也来了,我并没有通知二舅家,可能是花妗子通知他们的,他们就是来,来一个人就可以就代表了二舅家,事实上他们来了两个人。我猜测大老表的儿子是应该代表他父亲——我大老表的,但很快我就发现了明显的不一样,大老表的儿子和我的侄子之间非常亲热,这亲热绝对不是客套,装是装不出来的,他们之间有说不完的话题,在酒席间两个人频频举杯,一饮而尽,气氛融洽而热烈。背后我问侄子他们二人为什么这样熟悉,侄子说他们在一起。
在一起?我真的有点始料不及。
是的,我们这几年一直在一起。侄子看着我诧异的神色再一次肯定。
原来,二舅家的小表姐一家人在广州的中山市打工多年,在那里买了房子,安家落户了,大老表的儿子去南方打工其实就是奔着他姑姑而去的。我的侄子也在中山市打工,靠的竟然也正是这位小表姐。这样的关系未免太经不起风吹草动的了,何况,这位小表姐已经去世,然而,那位我从未见过面的表姐夫对待我的侄子和对待大老表的儿子一样视同己出,不分彼此。这些年来,他们一直在走动着,我大哥去世的时候,他们来了,我小表姐去世的时候,我侄子去了。他们说,在他乡,他们就是最亲的亲人。我这才意识到,大老表的儿子今天的到來,不是冲着我父亲来的,也不是冲着我来的,他并不是代表着他的父亲,他代表的就是他自己,他冲着侄子来的,我父亲的十周年这样的场合,不过是他们相处的一个平台而已。
他们在一起,他们的孩子也在一起,那些孩子将来的记忆里,一定会有着我们小时候曾经的记忆,一样的味道,一样的情感。
岁月无痕,但我知道,谁与我们曾经一起走过,我们的后辈,将与谁走过。
五
我父亲去世时,我给我的族家四叔打了电话,当时他在南阳儿子那里,我想让他回来,他在族家德高望重,我想他会回来,我们两个人的关系很好,事实上他没回来,我心里很难过。事情过后他给我解释了不回来的理由:你父亲埋在哪里呢?没有人能替你做了得主。
一个似乎很熟悉,却又很陌生的坟头突然划开我早已忘却的记忆。那个坟头在东岗的田地里,东岗的那块地很大,就只有那一个坟头,坟头虽然很小,在庄稼收割之后还是能一眼发现它,孤单寂寞。最早分责任田时,这座坟头就曾分在我家的责任田里,它是谁的,哪家的,男的女的?一切都是空白。我从没有见过有烧纸的痕迹,谁来上过坟,不管是清明、十月一、还是春节,它不知道被遗忘了多少年。在我的眼里,它不过是一个妨碍耕作的土丘而已,野草兀自葳蕤兀自萧瑟,阳光兀自热烈兀自黯然,月色兀自丰满兀自清瘦;风儿吹过了无痕迹,它从不告诉人们时光里曾经发生过什么。
好多年之后,当我才知道了它的主人是谁时,我惊讶得半天没有缓过劲来,它竟然与我家有关。我父亲一生娶了两个妻子,听老人们说第一个肤色很好,桃红的面容,一个美人儿,待人处事的口碑也好。不幸的是她患上了民间叫做“老鼠疮”的疾病,这种疾病现在应该叫做“淋巴结核”,在那年代是不治之症,她嫁给我父亲没几年就死掉了,没有留下一男半女。父亲的第二个妻子才是我的母亲,生下我们姊妹四人。这个坟头,就是父亲第一个妻子的坟头。就是我谢岗外婆的女儿,唯一的一个女儿。那时我才确定无疑,谢岗外婆并不是我的亲外婆,西乡外婆才是我母亲的亲生母亲。谢岗外婆的女儿去世之后,他们一如既往地看待我的父亲,看待女儿一样看待我的母亲,我母亲也认了这门“娘家”。
知道与不知道是一样的,似乎在印象里从来不曾存在过,我们姊妹四个人谁也没有来过这里,给她烧一炷香、一张纸,磕一个头、做一个揖。在我母亲去世之后,有一年大年三十我父亲才来过一次,是我一生见到唯一的一次。我父亲去世,他和我母亲合葬是天经地义、理所当然的,谁能想到东岗的那个坟头呢?四叔说我父亲在生前曾经给他说过,他死后要与他第一个妻子合葬,只是我父亲因心脏病猝死,没来得及遗嘱,就是遗嘱,能随了他的心愿吗?我也回想起来了,我父亲去世时谢岗小舅曾经问过我准备把父亲埋在哪里,我随口而出,当然是我母亲身边呀,我母亲的坟头在我家的老坟里,南边邻村的南边地里,两处坟地距离很远,又隔着这个村子,谁也看不到谁。谢岗小舅什么都没说,只是点了点头。
四叔的顾虑如当头给了我重重的一榔头,一下子颠覆了我所有的想当然,我恍然明白了过来,明白了父亲为什么会有那样的意愿,也明白了埋葬我父亲时为什么那样顺利;自责、愧疚、纠结一股脑地淹没了我,我无法表达我的心情,我无法体验到当我告诉谢岗小舅我们的决定时他当时的心情;我不知道,如在当时他真的要求我父亲和第一个妻子合葬,我会不会还是现在这样的心态,事实上他终究没有以哪一种理由来绑架我们,哪一种理由,都无可辩驳,我们都没有任何理由拒绝。东岗田地里的那个坟头——谢岗外婆的女儿、小舅的姐姐,真正地成了游鬼孤魂。
她知道吗?她身后有关两个家族许许多多的往事,面对即将一个世纪的沧桑岁月,还在鲜活地谱写,一切,皆缘她而起。
责任编辑 杨 枥
汪天钊,70后,高中文化,民工。河南唐河县人,现居洛阳。作品散见《牡丹》《奔流》《山东文学》《延河》《散文选刊》等多家文学期刊。曾获首届奔流文学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