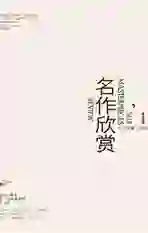中西“神圣疯子”的“恶”
2018-01-25陈小玲
陈小玲
摘 要:中西方宗教信仰不同,但却有相似的“神圣疯子”。在马塞尔·埃梅作品《呆儿木什》与丁国祥作品《癫子良云》中,二人共同书写的“神圣疯子”异于一般的宗教信仰者,如界限模糊的善恶观,伦理与宗教上善恶的对峙。然而“神圣疯子”不恶不疯。通过“神圣疯子”的“恶”,可反思人是如何从单纯追求生、欲、利的自然人,升华为真善美的文化人。
关键词:神圣疯子 恶 马塞尔 埃梅 丁国祥
我们常把人对命运的抗拒、个人与社会的冲突、智者与庸众的斗争、理性与张狂的分离等人称作“疯子”。西方在圣与俗的对立中产生了“神圣疯子”。而在中国的传统下,我们也有着佛学影响的“神圣疯子”,这是不同宗教文化下相同的文学样态。
《呆儿木什》是法国作家马塞尔·埃梅的一篇短篇小说,刻画了一个拥有强壮体魄的疯子呆儿木什。埃梅笔下的呆儿木什犯了死罪。但忏悔师却通过谈话发现,他的心灵如泉水一般纯净清澈,没有邪念,木讷的表情和言语似乎没有灵魂。他杀人的动机只是为了音乐。上帝将三位老人复活,一切都清零,但他还是没有逃过“法律”。
《癫子良云》塑造了一个执迷佛教的疯子良云。因为患上了精神疾病,所以从一个资优生变成一个辍学生。他的精神病况传闻席卷了他的生活全部,而他的精神也越来越不正常。最后,他被关在远离村子的谷场。几年后,一个故友的探访却让良云的疯蒙上了一个问号。二人共同书写的“神圣疯子”不同于一般的宗教信仰者,如界限模糊的善恶观,伦理与宗教上善恶的对峙。反思“神圣疯子”的同时,我们可以看到人是如何一步步成为人。
一、“神圣疯子”合理的恶
善恶是宗教永恒的话题。各门宗教中,传统的解释通常将恶看作是百害无一利。宗教中常有“恶”冲破阻碍成佛得道。如《呆儿木什》中呆儿木什希望能够每天都听到音乐。而靠年金生活的三个吝啬老人却常常让他不能如愿,于是他杀死了这三个老人。世上的人认为他犯了杀人罪,呆儿木什最后也不觉得自己有错,也不在乎死刑。《癫子良云》中良云希望保护他的猪朋友,把好心给他加几片猪肉的父亲的眼珠子挖了下来。这些都是“恶”。
宗教中的恶是可以被原谅的,“恶只是善的一种低级形式”。《圣经》言:“神看着一切创造的都甚好。”内含“从恶出发,也可以回归上帝”之意。佛教也云:“放下屠刀,立地成佛。”“恶”可被原谅,被拯救。《呆儿木什》刻画了许多耶稣的故事,诉说的教条是上帝可以原谅每一个有罪的人,只要他的心思纯正。而《癫子良云》展现了小乘佛教的思想,人生本苦,赎罪而活。大凡宗教,都是让人弃恶从善的。在这里,两篇文章中的恶并不是值得赞叹的品质,而是作为一种契机,引人去从善,引人皈依,得道。
阅读过程中,不难发现作者悲悯情怀很深。行文间常怀同情的笔法去刻画两个疯子,刻意描绘“神圣疯子”的合理性。首先,两位作者都借助了一个俗世认可度高的角色去与疯子直接对话。《呆儿木什》中,作者借助了忏悔师这个人发出感慨:“这是个搬运工的身体,儿童的灵魂,他杀了三个瘦小的老人,并没有什么邪念,如同一个孩子打开布娃娃的肚子,又或者扯下布娃娃的胳膊腿……”《癫子良云》中借助章若吉的耳朵,听到了良云诉说他的苦难与得道;还借助章若吉的眼睛,描绘出村子内部自身存在着问题:“月光还没有暗下去,章若吉清楚地看得清父亲的脸色和眼神。也看到了父亲回头向村西牛栏望去的动作。”这些人物作为文学上的一种中介,浸润了作者的情绪再现在文章中,文章同时具有第二人称、第三人称的叙述,使得文章合情合理。“疯子”之恶在于痴,而“痴人”有其可恨之处,却亦有其可怜之处。
再者,文章中刻意引用了许多宗教中的禅语照应原典。《呆儿木什》中情节中不断反复的“小耶稣”和呆尔木什变回小婴儿的神显;《癫子良云》中良云充满智慧的言语以及袭母事件中,呼喊的“我不想做人”。这些故事上有意无意地与《圣经》的小耶稣代替世人受罪重新降生的故事、小乘佛教“诸行无常、诸法无我、诸漏皆苦、涅寂静”的“四法印”相照应。
最后,文章中的时间描写隔绝了宗教的“现代化意识”,使得他们的疯癫是可以被原谅的。《呆儿木什》写在二战前,作品中有着浓浓的20世纪20年代法国的乡村气息。《癫子良云》中,能够看到中国现代农村的影子,书写的时间状态是中国20世纪60-80年代的事情。兩个“神圣疯子”的生活年代存在“宗教边缘化”的倾向。
总而言之,两位作家安排了一条向善的解脱之路给两名“神圣疯子”,并且在这个过程中,极力描述了他们的心路历程,显得合理妥当。
二、伦理与宗教上的善恶对峙
这里需要注意的是,宗教的“恶”与科学的“恶”是不一样的。从伦理方面看,两人是犯了故意伤害罪,但是在宗教上,良云只是犯了人生三苦“贪嗔痴”中的“痴”。这种错误,人人都会犯。
初看《呆儿木什》和《癫子良云》的前半部分,会发现作者刻意怀着悲悯之情,制造了两个“宗教狂热者”。呆儿木什杀了三个弱小的老人,丝毫没有反悔之意,良云枉费了父亲对自己的关心,挖掉了父亲的眼珠子,令人害怕。马克思曾说宗教是一种颠倒的世界观,是“还没有获得自身的自我意识和自我感觉”。恩格斯、尼采等哲学家的宗教批判都消解了对上帝的盲目崇拜与神圣权威。这些先知的哲学家们都看出了,不将上帝的虚构合理消解,人性之光无法照耀。
假设缺少了宗教的光环,呆儿木什和良云之间闪耀的向教之心,在这些哲学家的眼中便显得黯淡无光。但他们的人性之美便又重新焕发出光彩。
当他们面对心爱之物时:呆儿木什唯一的应声就是哼唱促使他犯罪的那支乐曲。良云被倒吊在屋柱上时,眼球突出,目光凶残,鼻子的呼吸声震天响,嘴里却念起佛号:“阿弥陀佛,菩萨救我。”而后良云在回忆他的痛苦——平静——痛苦的时候,脸上显现超脱年龄的成熟,使得这个人充满了人性与哲理的光辉。
这些人性之美在消解了刻意的宗教环境后,显得这两个“神圣疯子”的固执格外迷人。作者描写疯子的人性之美,目的是赞扬这些心灵纯粹之人。endprint
文章的后半部分便逐渐显现出了“疯子”以外的世界,伦理要求兄友弟恭、案子要公正评断。相比之下,那些旁观者的行为又是如此的荒诞。《呆儿木什》中的判决官因为害怕承担责任,将此事一层一层地向上級请示;《癫子良云》的父亲兄弟得知良云精神有问题后,就没有将其当作人看待,倒吊在屋顶十几天,晚上兄弟们轮流来揍他。这些疯子以外的人,除了作者刻意挑选的第三者,其余都是空有伦理道义形式,全无行为章法的人。看上去,这些旁观者的世界展现出来的“正常”更加疯狂。
文章中伦理与宗教的矛盾就像是互为挡箭牌。伦理和宗教两者本质之间确实存在矛盾,但文章中更多的是心口不一之人制造出的矛盾。旁观者处死呆儿木什的行径是善是恶?检察官、监狱长等等的人物都有着各式各样的龌龊想法,故此,他们给出了这样的指令:“杀人凶手蜷缩了一点儿,这种事绝不能用来妨碍司法条文的执行。”检察官们真的重视法律吗?并不,他们每个人都在言升迁之事。在处决呆儿木什一事影响到自己时候,用接收到的“法律指令”说话。这些人竟不如一个疯子来得纯粹与实际。旁观者依赖伦理,生活在伦理中多年,然而伦理却不是他们所信仰的,于己有用时,自己满口伦理仁义,于己有害之时,满口利益当先。这难道不是一种“恶”?
伦理与宗教上的善恶对峙并不是简单的二元对立,但是在世间拥有纯粹的心灵,并且忠于自己的内心之人,实在难得。呆儿木什和良云便是这样的人,忠于宗教信仰时,便放下屠刀,超脱了金钱、工作、生死,只求达到痴迷之物。最后得到救赎时,整个人脱胎换骨,涅重生。这不得不归因于“神圣疯子”比常人更纯粹的心灵,更勇敢的追求。
任何作品都是现实生活的记录。它们记录了个人对自然、社会、思维三大科学领域的反映形态与认识过程。马塞尔·埃梅的《呆儿木什》与丁国祥的《癫子良云》反映了“神圣疯子”这一共同的母题,便是从“神圣疯子”界限模糊的善恶观入手,然而,我们分析伦理与宗教上的善恶的对峙后,便知“神圣疯子”并不恶也不疯。人从单纯追求生、欲、利的自然人升华为真善美的文化人,最重要的是要保持自己的赤子之心。
参考文献:
[1] 马塞尔·埃梅.呆儿木什[J].南方文学,2017(1):39-41.
[2] 丁国祥.癫子良云[J].南方文学,2017(1):34-38.
[3] 曾祥芹,韩雪屏.阅读学原理[M].开封:河南教育出版社,1992.
[4] 金丽.神圣疯子——从《圣经》视野解读西方文学系列论文之七[J].广西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1):132-136.
[5] 陈坚.贝施特和智论“恶”的宗教价值——兼谈宗教中的“善恶”观念[J].宗教学研究,2005(3):97-103.
[6] 丁麟茜.西方宗教批判的意义及其限度[J].云南社会科学,2017(1):62-68.
[7] 居纳尔·希尔贝克,王寅丽.宗教批判与意识现代化[J]. 哲学分析,2010(1).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