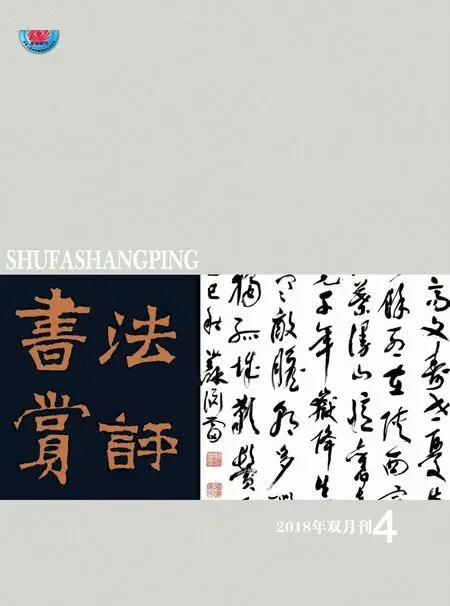论苏轼对米芾书法取法转变之影响
2018-01-25
米芾是北宋著名书法家、画家、书画理论家,与苏轼、黄庭坚、蔡襄合称 “宋四家”。后人提及米芾师法,多谓其得晋人笔意。如邓肃评曰 “米芾楚狂者也,作字清远,有晋宋气”;[1]蔡絛评曰 “时窃小王风味”;[2]《宋史·米芾传》中亦评米芾 “得王献之笔意”。[3]米芾书法脱胎晋人,已是公论。然米芾初学,并非从晋人入手。
米芾尝自云其十岁学碑刻,浸润于周越、苏子美手札。晚年在 《自叙帖》中,亦提及自己初学书时先学写壁,研习七八年颜体后学柳公权、欧阳询。后长时间追摹褚遂良,又转师段季展。至此所临习者,皆为唐人。而后突然尽弃唐人,开始接触魏晋法帖,入魏晋平淡。再上追师宜官、 《刘宽碑》,又慕 《诅楚文》《石鼓文》之高古。可知米芾并非从一开始便有 “好古”的意识,而是从取法近人、唐人转折到远追高古,而影响米芾发生这个转折之人,便是苏轼。
苏轼与米芾相交二十年,二人年龄虽相差十四岁,但从雪堂初识到苏翁逝世,两人友情从始至终亲密无间。米芾终其一生都保持着对苏轼的尊敬,苏翁逝世后,米芾为其写下的五首情真意切的悼亡诗,便可视作二人一生友谊之缩影。米芾之所以对苏轼终身持有这份深厚友谊,最重要的原因,应是苏轼对米芾在书学道路上的引导。
一、对崇晋卑唐思想的影响
据温革记载:“米元章元丰中遏东坡于黄冈,承其余论,始专学晋人,其书大进。”[4]这次改弦易辙,是米芾书学生涯上的一大转折点。
苏轼对魏晋书法的欣赏是终其一生的,不仅对二王等魏晋书法顶礼称赞,亦极为看重唐人和近人书迹中蕴含的魏晋风气,如评颜真卿的 《东方画赞碑》:“颜鲁公平生写碑,惟 《东方画赞碑》为清雄,字间栉比而不失清远。其后见逸少本,乃知鲁公字字临此书。虽大小相悬,而气韵良是。”[5]此等语与其说是在推举颜书,不如说是为了称扬逸少。评张旭的 《郎官石柱记》亦云其字:“作字简远,如晋宋间人。”[6]这一取向在背后暗示着苏轼实将唐人置于晋人之下,将批评的标准定为是否合乎魏晋古法。
而米芾早年习书,一如上文所论,多以唐人和近人为范本。因此当他转向请教苏轼时,以魏晋笔意为审美评判标准的苏轼自然会加以劝说。而第一次见面,米芾就听从了苏轼的建议。我们从米芾元丰五年前后的书迹变化中,便可看出此次见面对米芾书风丕变的影响。
米芾现存最早的书迹是元丰 (1080)三年所书的 《阎立本<步辇图>观跋》,是年米芾刚满三十岁,帖中笔力稍逊,结体不稳,个人书风未见端倪。米芾晚年自评 “壮岁未能立家”,[7]此帖即可为佐证。元丰四年(1081)的 《道林诗》帖,紧结耸肩,受欧阳询影响明显。同年所书的 《砂步诗》,又带有沈传师笔意。而至元丰六年 (1083)的 《方圆庵记》时,欧体笔意已几近于无,隐有圣教气息,如 “于”“皆”等字。是年正是米芾去往黄州见苏轼后的第二年。米芾幼年学书,二十余年间浸染于唐宋书风之中,至此方悟魏晋高古。
而除了这次黄州相会,对米芾由唐溯晋的转变尤为重要的,是元祐二年 (1087)至李玮府观晋帖。李玮时为驸马都尉,能章草、飞白、散隶,收藏丰,犹钟晋帖。米芾造访李府时苏米正同在京城,颇多宴游。而苏轼恰与李玮相熟,亦曾至府中观帖,苏轼 《辨法帖》中提及其 “后又于李玮都尉家,见谢尚、王衍等数人书,超然绝俗”。 《题晋人帖》中亦有 “余尝于李都尉玮处,见晋人数帖”。可见苏轼亦是李府常客。米芾此时入京待职,官微言轻,与许多当朝达官显贵的交往多是经由苏轼引见,如受苏轼之邀赴驸马王诜府邸参加 “西园雅集”。此次米芾前去李府观摩,应亦是受了苏轼的影响或引见。后米芾在李府看到武帝帖时,专意提及苏轼:“昔眉阳公跋赵叔平家古帖,得之矣!”[8]此次李府观帖,是米芾第一次接触到大量的魏晋真迹,给米芾留下很深的印象,后 《武帝书帖》 《好事家帖》 《太师行寄王太史彦舟》等帖,都详细记录了此事。魏晋书迹的文采炳焕使米芾的眼界有了极大提高,也使他的书学思想发生很大转变。
自黄州相会与李府观帖后,米芾卑唐崇晋的思想愈演愈烈。
譬如对张旭的态度变化,在元祐元年 (1086)的 《张季明帖》中,米芾评张旭 《秋深帖》为 “长史世间第一帖也。其次 《贺八帖》,余非合书”。虽斥张旭除 《秋深》 《贺八》二帖外之书迹皆非合书,但仍不掩对此二帖的欣赏。而至元祐二年米芾在李府看到 《晋武帝帖》后,便大加贬损张旭:“其气象 (指武帝帖)有若太古之人,自然浮野之质,张长史、怀素岂能臻其藩离?”[8]于同时所书的 《张颠帖》更直指 “张颠俗子,变乱古法,惊诸凡夫,自有识者”。到了涟水任上时,在寄给薛绍彭的诗中,更不忘批 “张颠与柳颇同罪,鼓吹俗子起乱离”。[9]批评张旭不循古法,媚俗惑众。这与苏轼对张旭的态度大同小异,苏轼对张旭虽时有较为公正之肯定评价,但心中仍将长史列为低晋人一等 《书张长史草书》中即对张旭醉后作书的习惯作出质疑:“此乃长史未妙也,犹有醒醉之辩,若逸少何书寄于酒乎?”认为张旭喜酒后索笔挥洒的事迹,正说明其书未臻妙境,方需寄于酒兴,若为逸少则无此醒醉差别。而对于怀素,两人更加同仇敌忾,米芾曾言 “怀素獛獠小解事,仅趋平淡如盲医”,苏轼亦有“怀素书极不佳,用笔意趣,乃似周越之险劣”[10]之语。其余的唐人书家,除去褚遂良得而幸免,其他人在米芾这里的遭遇也大致相同,就连米芾曾倾力学过并大加赞赏的欧阳询,也逃脱不了被一路贬低的命运。
而对晋人,米芾也与苏轼一般,极尽溢美之能事。米芾虽因狂性难改,时对 “二王”有贬低之语,但总体态度还是肯定的。元祐三年 (1088)米芾从苏洎处得到褚摹 《兰亭》后留下题跋:“爱之重写终不如,神助留为万世法。”将 《兰亭序》视为如有神助方能写出的足为万世师法之杰作。又如为王羲之 《王略帖》所书的题跋:“吾阅书遍一世,老矣,信天下第一帖也。”将 《王略帖》直捧为天下第一。而在遍观李玮所示米芾的晋贤十四帖后,米芾亦极为推重晋武帝、谢安等人书迹。如评武帝帖 “书纸糜溃,而墨色如新,有墨处不破”。狂妄如米癫者,对此书迹也发出 “岂临学所能,欲令人弃笔研也”[8]的叹息。后在建中靖国元年 (1101)所作的《太师行寄王太史彦舟》中又写道:“磨墨要余定等差,谢公郁勃冠烟华。当时倾笈换不得,归来呕血目生花。”不仅评谢安书迹为冠,甚至因求帖不得呕血。米芾 “倾笈”以换晋帖之事时有之, 《米襄阳志林》亦详记米芾曾以九物换取刘季孙所藏王献之帖: “以欧阳询真迹二帖,王杂雪图六幅,正透犀带一条,砚山一枚,玉座珊瑚一枝以易。”在米芾心目中,书远胜于画,晋帖远胜于唐帖,但凡米芾看中的晋帖,必用尽各种手段求之,于是有倾囊购取,有作假掉包,有作势跳河以威胁。虽有些手段不甚光彩,但亦反映米芾对晋帖实是爱不忍释。
二、对远追篆隶的启发
除了崇晋卑唐外,米芾 《自叙诗》所提及其中岁后的师法转变,还有一大改变便是开始远追篆隶古法。米芾在其 《自叙帖》中提及他入晋魏平淡后,又 “笔便爱 《诅楚》 《石鼓文》。又悟竹简以竹聿行漆,而鼎铭妙古老焉”。[11]米芾篆隶二体书并无惊人之处,此悟给米芾带来的,更多是鉴赏水平的提高与对古意的更深一层领会。苏轼虽未明言示之米芾留心篆籀笔法,但苏轼对秦篆亦向来极用心。苏轼曾做 《石鼓歌》赞颂石鼓文字 “上追轩颉相唯诺,下揖冰斯同鷇鹁”。[12]犀利地点出石鼓承上启下的历史意义。熙宁九年 (1076)又登琅琊台见秦 《琅琊台刻石》,作下 《刻秦篆记》:“夫秦虽无道,然所立有绝人者,其文字之工,世亦莫及,皆不可废。”苏轼向来崇尚 “君子之书”,极重人品与书品的关系。无道暴秦所立之文字,能得苏轼如此推重,足可见其对此秦刻石书迹的重视,未完全因人废书。苏翁既有此一层欣赏,又兼及对米芾的提携后进之意,米芾后来对篆籀突发的兴趣,或亦同出自苏轼提点。
三、发生影响之成因
米芾的这些转变,对其书法生涯的影响是巨大的。取法乎上的学习奠定了米芾中后期书法的基调和风格,也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米芾在书法艺术上达到的高度。
当时与米芾相交的书法家,非止苏轼一人。同为米芾好友的薛绍彭、刘泾、黄庭坚、蔡肇、蔡京等人都是当时名噪一时的书法家。米芾与这些人时有交流书艺。但不同于苏轼,他们对于米芾书法上发挥的影响甚微。之所以他们无法如苏轼一般对米芾发生转折性的影响,原因或有三。
一是由于这些人自身水平所限。如薛绍彭、刘泾二人,与米芾交情颇为深厚,时有书信往来。然三人虽为至交,但在艺术道路上,此二人对米芾的影响并不深,主要原因在于薛、刘二人的眼界及艺术水平有限。
米芾在 《书史》中曾提及,薛绍彭来书告知米芾他新收了钱氏王帖,米芾反劝薛绍彭倾囊购取 “二王”以前帖,殷殷劝说薛绍彭 “二王之前有高古,有志欲购无高货。殷勤分语薛绍彭,散金购取重跋题”。[13]劝解薛绍彭不要将眼光只停留于 “二王”法帖之上。在涟漪任上,米芾也曾寄诗与刘泾表达过相似态度,“刘郎收画早甚卑,折枝花草首徐熙。十年之后始闻道,取吾韩戴为神奇。”[13]从 “早甚卑”“始闻道”等字眼,即可看出米芾对刘泾早年一味师法近人的做法颇为轻视。在 《书史》中,米芾也言及刘泾“方是时,刘泾不信世有晋帖”。[14]并作诗直指刘泾 “唐满书奁晋不收,却缘自不信双眸”。可见刘泾眼界不高,初时习画多学今人,习书多学唐人,不敢直追古法,收取晋帖。从米芾对薛、刘二人此种近乎教诲的态度,及薛、刘逊于米芾的艺术水准,实此二人确无资格为米芾翰墨之师。
二是米芾自身的狂性使然。米芾虽终身不对苏轼执弟子礼,但苏轼在其心中实是亦师亦友。同为宋四家的黄庭坚,只就草书论,亦足以为米芾师法,但米芾偏自瞧不上他。黄米两人渊源颇深,米芾长子米友仁的字即是黄庭坚为他所取。但私交归私交,米芾对黄庭坚的书法一向多有非议,其晚年自许 “襄阳米芾,在苏轼、黄庭坚之间”。[15]便已明白地将自己置于黄庭坚之上。徐度 《却扫编》卷中记载:“余尝见元章所藏一帖曰, ‘草不可妄学,黄庭坚,钟离景伯可以为戒’。”[16]黄庭坚最引以为傲的草书,尚且被米芾列为后学应引以为戒的反面例子,欣赏况且不能,遑论受其影响。平心而论,黄米二人在各自均擅长的行书领域难分伯仲,而黄庭坚的草书造诣远高于米芾,米芾对黄庭坚的轻视,出乎其癫狂傲世的心理。米黄二人年龄相差无多,且黄庭坚确无苏子那般超凡脱俗的人格魅力和学识修养能让米颠心领神服,自然无法在目下无尘的米芾这里讨到什么好处。且二人交游集中在元祐时期的五、六年间,时间不长,互通亦极有限,不似苏米二人相识时间长达二十年,沟通亦较频繁。
三是由于掺杂了政治等功利因素,使得本应平等纯粹的书学交流变质。米芾与蔡京,少年相识,交往时间长达四十年,在翰墨笔戏之间也多有交流。米芾所作 《太师行寄王太史彦舟》中有 “我识翰长自布衣,论文写字不相非”之语。但关于二人交往前期的记载不多,后期又从平等的翰墨之交变质为米芾对蔡京的趋炎附势。如崇宁元年 (1102),蔡京受徽宗重用还朝,米芾一见多年未有联系的故友飞黄腾达,立即恭维蔡京 “大贤还朝,以开太平,喜乃在己”。[17]一面赞颂蔡京 “大贤”得用,将开太平盛世,一面表示自己作为蔡相 “微时交”,也欣喜万分,刻意拉近自己与蔡京的关系。后米芾晚年通过蔡京的举荐拜书学博士,再为蔡京献诗:“百僚朝处瞻丹陛,五色光中望玉颜。浪说书名落人世,非公那解彻天关。”[18]卑微之色溢于纸上,谀词之极几丢尽文人风骨。
有此心理背景,就可理解米芾对蔡京书法的评价为何反复无常。蔡絛的 《铁围山丛谈》记蔡京有日问米芾:“今能书者有几?”芾对曰:“自晚唐柳,近时公家兄弟是也。”[19]《海岳名言》又记宋徽宗召米芾询问其对当世书家的看法,米芾对曰: “蔡京不得笔。”[20]同一个问题,截然相反的两种回答,掺杂了功利的色彩后,评价往往就失去了客观和真实。米芾将自己降格为蔡京炙手可热的权势下的附庸,言语尚不能出自真心,何能真心求教,诚心受教。
而这与苏米的纯粹友谊判若云泥。米芾初识苏轼时,苏轼被贬黄州谪居雪堂。米芾不畏牵连仍前去拜会这位正在倒霉的文豪。苏轼被远贬定州时,米芾也仍屡屡与之书信往来。在两人长达二十年的交往中,苏轼屡遭贬谪也屡受荣宠,米芾并未因其贬谪而疏远,也未因其好运而阿谀。苏米二人不掺杂功利色彩的友谊,实是二人在艺术上相互交流、影响的基础。
苏轼与米芾是矗立在古代书坛的两座高峰,二人友情极为纯粹质朴,至始至终都建立在纯粹的文艺交流与惺惺相惜之上。对二人书法艺术成就高下的评断,后世众说纷纭。然米芾拜谒苏轼时,米芾书名未盛,而苏轼已是名满天下的文坛领袖、艺坛巨擘,不可否认苏轼的指点对米芾真率书风的形成,确是发挥了重要的引导作用。
注释:
[1](宋)邓肃 《栟櫚集·卷二十五》,载于文津阁四库全书本,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第1133册,第372页。
[2](宋)蔡絛 《铁围山丛谈·卷五》,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版。
[3](元)脱脱等 《宋史·卷四百四十四》,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13123页。
[4](清)翁方纲 《米海岳年谱》,见黄正雨、王心裁辑校 《米芾集》,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255-256页。
[5](宋)苏轼 《苏轼文集·卷六十九》,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2177页。
[6]同上,第2206页。
[7](宋)米芾 《海岳名言》,见卢辅圣主编:《中国书画全书》第1册,上海书画出版社,1993年版,第976页。
[8](宋)米芾 《宝晋英光集·卷八》,文津阁四库全书本,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第373册。
[9](宋)米芾 《宝晋英光集·卷三》,文津阁四库全书本,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第373册,第165页。
[10](宋)苏轼 《苏轼文集·卷六十九》,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2179页。
[11](宋)米芾 《宝晋英光集·卷八》,文津阁四库全书本,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第373册。
[12](宋)苏轼 《苏轼诗集·卷三》,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100页。
[13](宋)米芾 《宝晋英光集·卷五》,文津阁四库全书本,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第373册,第170页。
[14](宋)米芾 《书史》,见卢辅圣主编:《中国书画全书》第1册,上海书画出版社,1993年版,第970页。
[15]《廷议帖》,元符三年书,宋拓 《宝晋斋法帖》,行书。
[16](宋)徐度 《却扫编》,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83页。
[17]《新恩帖》,崇宁元年书,纸本,行书,高31.8cm,今藏故宫博物院。
[18](宋)米芾 《宝晋英光集·卷四》,文津阁四库全书本,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第373册,第168页。
[19](宋)蔡絛 《铁围山丛谈·卷五》,文津阁四库全书本,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第1037册,第603页。
[20](宋)米芾 《海岳名言》,见卢辅圣主编:《中国书画全书》第1册,上海书画出版社,1993年版,第97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