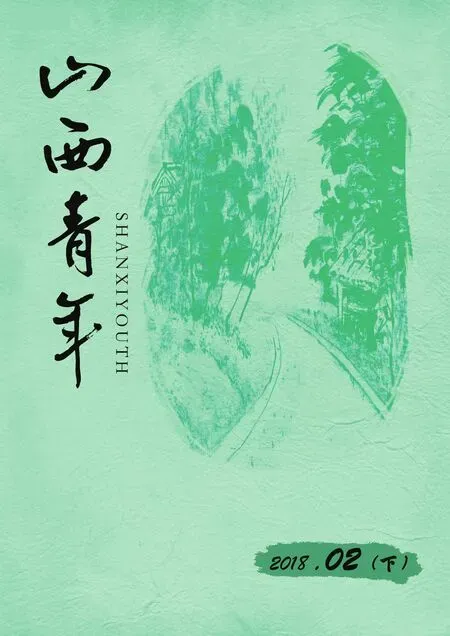《史集·中国史》专有名称对音研究综述
2018-01-25李瑞
李 瑞
(北方民族大学,宁夏 银川 750021)
13-14世纪蒙古不断向外征战,扩大版图,建立了地跨欧亚的蒙古帝国。由于大蒙古帝国的建立,东西方的文化交流和贸易往来高度发展,波斯旅居了来自各民族的学者,拉施特直接借鉴了各民族学者带来的历史文献,并得到了各民族的学者的帮助。
其中被称为“世界史”的部分记述了印度、富浪、中国、阿拉伯、以色列等世界各民族和国家的历史。“中国史”部分是根据一部现已失传的汉文史书于1304年翻译编写而成。由于《史集·中国史》中上及三皇五帝,下及辽金元,列举了历朝历代几乎所有帝王的名称及其统治年代,因此将这部书中的以波斯文拼写中国古代历史的词汇收集起来,其波汉对音是研究《史集》成书年代也就是中国元代时期的语音情况的非常有利的一笔材料。
西方学者从17世纪便开始对《史集·中国史》进行研究,早期主要集中在对《中国史》的辨析问题上。西方学者第一篇专门介绍和研究拉施特《史集·中国史》的文章是德国汉学家傅海波的论文《从汉学角度对拉施特中国史的几点评述》。
最早在我国,首次注意并详细介绍《史集·中国史》的是刘迎胜先生的《丝路文化》一书。在其《小儿锦研究》一书中也提到《史集·中国史》,并提到在《中国史》中出现的大量的中国历史的术语,这些历史术语以波斯字母的形式拼写并保留下来。将这些以波斯字母拼写的中国历史词汇收集起来,可以了解“小儿锦”出现之前波斯人拼写汉语的一些重要重点。
20世纪90年代,北京大学青年教师王一丹在伊朗德黑兰大学攻读博士学位期间以拉施特的《中国史》为题,答辩通过后在伊朗以波斯文出版。在其归国后,其研究又出了汉文本《波斯拉施特<史集·中国史>研究与文本翻译》。本文将以王一丹教授的汉文本《波斯拉施特<史集·中国史>研究与文本翻译》为底本,对该书中所提及的中国历史术语进行分类研究,以期了解该书的成书年代即中国元代时的汉语的语音情况。在国内外对《史集·中国史》的这些研究中,并未有涉及到从语音方面对书中所提及的专有名称进行研究的方面,但是这些专有名称的对音情况仍然是研究元代语音的十分有参考价值的材料。
对于元代的语音研究,各家目前尚存在分歧。声母方面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1、中古知庄章三组的变音该不该分成两组;2、中古见组细音的变音该不该分出一组;3、[]母是否存在以及部分中古“疑母”变音要不要另立一类。韵母方面主要有:1、入声韵是否消失;2、[m]尾韵的消变情况。
《史集·中国史》中的波汉对音材料反映了元代时期的语音系统。其语音系统如下:
1、[-m]尾已经开始消变。元代时期的代表语音《中原音韵》出现了[-m]韵尾消变的情况,这个消变是从唇音开始的,就是通常所说的唇音异化。而在《中国史》中的[-m]尾韵研究中,不仅唇音开始发生了变化,其他声母的字也开始消变。
2、入声韵尾。入声字研究将把书中提及的专有名称中的所有入声字选取出来,通过对其对音的分析,对元代的入声是否已经消失做出自己的判断。《中原音韵》是元代汉语的代表,所以均以《中原音韵》为观察点。目前学界对于元代入声是否存在尚未定论,主要有三种观点。第一种认为《中原音韵》尚有入声,以陆志韦、杨耐思为代表;第二种认为《中原音韵》入声已经消失,以王力、赵荫棠为代表;第三种认为《中原音韵》中入声已经消失,但当时读书音中还有入声,以薛凤生和蒋冀骋为代表。
以《史集·中国史》中的对音材料来看,笔者同意第三种观点。材料中共有64例入声字,其中有7例仍以塞音或摩擦音收尾。剩余的50多条例证对应开音节的是元代入声消失的绝好证明,但是其中以塞音和清摩擦音收尾的例字,也证明了元代时期的口语中尚有入声存在。
3、知庄章三系合一。宋代西北方音知章合一,庄系已经开始与知章相混,到了《中原音韵》,知庄章是否合并,目前仍存在两种不同的观点,一种认为在《中原音韵》中知庄章三组声母完全合并;一种认为在《中原音韵》中知二和庄是一个声母,章和知三是一个声母,但是在支思韵中章变得同庄。从《中国史》的对音材料来看,知庄章三系的声母大多对音为[],个别既对音[]又对音[ʃ],一个为舌叶浊塞擦音一个为舌叶清塞擦音,以《中国史》的材料来说,元代时期的知庄章三系已经合并。
4、疑母字大多并入了影喻。疑母开始脱落,较早的资料见于《尔雅音图》和吴棫《韵补》的音注。《中国史》中所反映的波汉对音的材料中的疑母字并没有存在仍读作[]声母的,已经全部并入的影喻母。
[1]王一丹.波斯拉施特《史集·中国史》研究与文本翻译[M].北京:昆仑出版社,2007.
[2]蒋骥骋.阿汉对音与元代汉语语音[M].北京:中华书局,2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