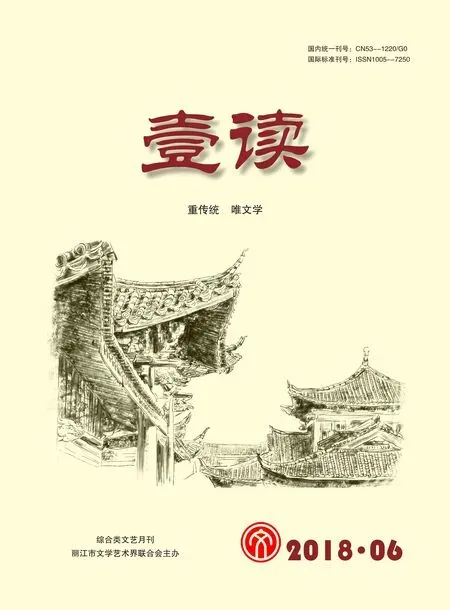遇见王祥夫
2018-01-25罗开华
罗开华
相遇是缘。
一次与他的普通相遇,竟然在我的生活中溅起朵朵浪花,让我心动、喜悦。他时髦的形象、灿烂的微笑、诙谐的话语、总是在我耳边萦绕。于是,我记下了和他相遇的过程。
2016年12月 25日,在欢迎“全国著名作家永胜行”的晚会人员中,就缺王祥夫。之前,我似曾见过他,但不了解他。
第二天,我与随行人员去六德他留山采风,吃中午饭时,一阵“哗哗”的掌声响后,他出现在了我眼前。他着一件黑色长衫,面料很粗糙,或许是纯棉的。他最吸引我的,不是围在脖子的红色围巾,也不是红扑扑的脸蛋,而是高鼻梁上架着的墨镜。那圆圆的、小小的、漆黑的镜片后面,好像藏着一双“色咪咪”的小眼睛,有点儿逗人发笑。好家伙!我的大脑里突然闪现:电视剧、上海滩、黑老大等字眼。
“对不起大家,我迟到了,先罚一杯”。说完,他双手举杯,向大家致歉。接着,“咕嘟”一声,一杯他留人(云南少数民族,彝族支系)的自酿酒就下了肚。他左手拎着酒壶,右手拿着酒杯,向每一个喝酒的人敬酒。当他来到我身旁向我敬酒时,我只是礼貌性地呷了一小口,他却“咕嘟”一声,又下肚了。知道吗,那一杯足足有一两多呢!他喝酒的动作是那样地优雅、别致、潇洒。
午饭后,我们继续到永胜瓷厂采风。走在瓷厂的大道上,他留烈酒(他留人自酿的白酒)把他醉得步履蹒跚,以至于要人驾着才能行走,早已没了刚喝酒时的潇洒形象。
我尽量把照相机的焦点从他身上挪开,生怕他那“丑陋的形象”(当时我就是这样想的),侵占我的内存。
我们参观、交流、采访。从一个车间走向另一个车间。当来到展示大厅时,瓷厂厂长已经准备好笔墨纸张静候多时了。聪明人,就是能够提前预知、提前准备、提前行动的人。瓷厂厂长就是这样一个人。原来,他早已准备好笔墨宣纸,要请名家们为瓷厂题词了。只见他恭恭敬敬地用双手把毛笔递给云南著名诗人雷平阳,雷平阳欣然写下了“山城瓷都”四个字。一阵掌声后,王祥夫也在众人的簇拥下也出场了。我挪开照相机,静静地等待这个“醉汉”怎样弄出“笑话”来。
只见他从雷平阳手中接过毛笔,颤颤巍巍地来到桌前,用左手按住纸的一角,在洁白的纸上写下了“瓷都之光”四个大字。他笔势雄劲、姿态横生,字迹既像脱缰骏马,又像蛟龙飞天,哪有酒醉的样子呀!我从一阵又一阵的掌声、喝彩声、欢呼声中惊醒,急忙把照相机的焦点对准他,便“咔嚓咔嚓”地按下了快门……
于是,我重新认识了他。
第三天,按日程安排,我们上午先去程海螺旋藻厂参观。坐在去程海的车里,他那以众不同的形象总在我脑海里闪现,我感觉,似乎之前在哪里见过他。我拿出手机,在百度搜索框里输入“王祥夫”三个字,“王祥夫简介”便跃入眼帘: “王祥夫,男,1958年生,辽宁抚顺人,中共党员,大专文化。历任大同市照相馆摄影师,中共大同市委党校讲师,山西文学院专业作家,山西省作家协会副主席。云冈画院院长,当代画家。” 吓着我的,不是这么多头衔,而是他的文学作品。如长篇小说《米谷》《生活年代》《百姓歌谣》《屠夫》《榴莲 榴莲》等七部;中篇小说集《顾长根的最后生活》《愤怒的苹果》《狂奔》《油饼洼记事》等五部。散文集《杂七杂八》《纸上的房间》《何时与先生看山》等六部。短篇小说集就多得无法一一列举了。他的获奖作品同样多得吓人,如散文《荷心茶》、中篇小说《顾长根的最后生活》分别获得第一、二届“赵树理文学奖”散文奖和中篇小说奖第一名;他的短篇小说《上边》获第三届“鲁迅文学奖”短篇小说奖第一名。长篇小说《种子》英译本还获得了美国丹佛尔奖。总之,他的文学获奖作品多得难以一一累述。
突然,行进着的车变得颠簸起来,我只好收起手机,把目光投向车窗外。我把记忆的“胶片”在大脑里进行几次回放,终于想起来了,原来,在“2014国际·丽江大家高峰论坛”上,他为我们作过报告。车继续颠簸着前行,不知不觉中,已经驶向了通往程海保尔螺旋藻厂的土路上。
我们来到保尔螺旋藻厂,在工作人员的带领下,从生产车间到深加工车间,从包装车间到销售平台。最后,在会议大厅倾听程海保尔集团董事长谭国仁详细介绍产品情况。由于我是这次活动的摄影师,必须用影像记录活动的全过程,所以,我只能走在整个队伍的最前面。奇怪的是,在队伍前面,很难见到他的踪影,不知藏哪儿了。离开程海保尔螺旋藻厂,我们又赶往清水古镇,去那里的目的,是为了让大家了解一下边屯的那段历史。清水古镇,勘称“丽江第一村”。历史上的清水村是重要的交通驿站,历史资料记载,明永乐二年时,云南布政司在澜沧卫设驿站,一个设在卫城北胜,另一个就设在清水驿,使这里成为丽江唯一一个官方乡间驿站。从边疆沃土拓荒之早,中原汉文化积淀之深,清水古镇都堪称云南边屯文化重镇。一村四进士就出自这里。在参观“土司所”时,他似乎很喜欢古式木结构中的“雕龙画凤”,特别是对那几块雕刻古文字的踏步石很感兴趣,一边弯腰仔细观察,一边还和作家们议论着什么,好像在寻觅中原文化留下的遗迹。在行至一段土胚围墙时,他又被上面长满的植物所吸引,连连问随行:“这是什么、这是什么?” 随行只能摇头说不知道。他却拉起一串仔细观察,如痴如醉,不愿离去。有位本土作家告诉他,那叫“爆竹花!”听后,他称赞说:“这名好!红彤彤的,喜庆、形象!”
离开清水古镇,是去“永胜·云南边屯文化博物馆”参观。在“毛氏宗祠”里,他对毛泽东祖先从江西、湖南充军到云南永胜毛家湾的过程了解得特别详细,总是紧紧跟随讲解员认真听讲,还时时向讲解员提问。
程海湖,又名黑伍海,是永胜最大的淡水湖也是滇西第二淡水湖,云南九大高原湖泊之一,世界上天然生长螺旋藻三大湖泊之一。由于自然条件得天独厚,对它的开发与保护一直困扰着当地政府。把全国著名作家邀请到这里,是请他们来出谋划策的。走出“边屯文化博物馆”,作家们在程海湖边吃完有程海鱼的中午饭,大家兴致勃勃地登上程海管理局的巡逻快艇,环湖绕一圈,以加深对程海湖的印象。
蓝天、白云、温柔的阳光、碧波荡漾的程海湖,时时有海鸥从巡逻艇上空掠过。这么迷人的景致,让作家、诗人如痴如醉。他们纷纷登上二层船沿,要我帮他们拍照留影,在云南,在永胜留下他们美好的一瞬间。尽管拍留影让我忙前忙后,我却时时留意他的动向。但在二层船舱和甲板上,总是寻不到他的踪影,他好像就待在一层船仓里。本想在船上与他合影留念的,只能留下遗憾了。
下午四时,我们来到了三川翠湖村。三川,因有盟川、汇川、济川三条河流流经坝子而得名。翠湖,是因芮官山脚下九股泉涌出相汇而形成的。这里最美的季节是夏季,万亩荷塘碧波万顷,红白莲花随风摇曳,不是江南,胜似江南。明代郡人罗俊明诗云:“九龙潭水静无波,堤畔人家总种荷。霞映一湾朝日浅,花香十里千风多。沙明藻绿青蒲间,鸥宿鱼游白鹭过。一副吴宫新制锦,数声越女采莲歌。”
翠湖的田园风光,小桥流水特别美,作家诗人们来到这里便三三两两分散开来,让我的拍照记录无从下手。于是,我索性丢下相机,也去“自由”活动了。走出“农家乐”不远,我却看见他正和几个在河里洗莲藕的妇女说话。他说: “这藕真白呀,我从未见过。”
“还可以生吃的!”一妇女说着便抛了一根给他。他接过后,先是看了看,然后又闻了闻,最后真的生吃了起来。还连连说:“甜,好吃,真好吃!”
离开洗藕的妇女,他朝荷塘走去。他走到荷塘边,对着大片大片的残荷发呆……
晚餐时,他被翠湖农家乐里的“荷花宴”惊呆了,连连称赞:“好看、好香、好吃!”那晚,他好像又喝多了。
12月28日一大早,他又神采奕奕地站在了出发前的车子旁,丝毫没有“醉”的样子。
我们一起又去了鲁地拉电站、涛源的“金江古渡”等地参观。下午,我们回到了永胜县城,并在宾馆会议室参加了由永胜县委宣传部组织召开的座谈会,作家们对四天的永胜行进行了总结性发言,他在总结会上也做了热情洋溢的讲话。他说:“写文章就是写自己,写作是一门科学,是一门深奥的学问。作家要把自己当作最普通的人深入民间、深入生活。写作一定要接地气……”座谈会结束,“全国著名作家永胜行”活动圆满完成。
对于永胜,我在后来他写的《永胜散记》中看过这样的描述:“永胜真是个好地方,这里的土地好像有无穷的力量,一路走来,割过的稻田里都已经长出了青青的蚕豆,虽说是在云南的永胜,但眼前的一切却实实在在让人想到江南。这就是永胜给人的一种错觉。或者说永胜这个古老的地方藏着一个江南。虽然时间已经是十二月的时光,而这里,触目都是一片青翠。”
12月29日,我与作家们一起去丽江。根据丽江市文联的安排,由我继续陪同作家们在丽江的日程。中午12点,我们抵达了丽江。
在丽江,没有官方安排活动计划,而是受云南诗人雷平阳之邀,直接驱车去参观他原在单位“云南建工集团”在丽江的承建项目“文海水库建设”项目。
文海,位于丽江玉龙雪山主峰西南麓,平均海拔3180米,是云南丽江拉市海高原湿地省级自然保护区的片区保护区之一。面积676公顷,其中,水域(文海)仅160公顷。丽江没海,有很多人没见过海,于是,把湖都称作海,如程海、拉市海、文笔海、九子海等。其实,它们只不过是很小很小的湖,有些只是小水潭而已。
文海由古老的冰蚀湖演变而成。湖水有点奇怪,秋冬季为丰水期,春夏季却为枯水期。这里也是丽江的旅游景点之一,春夏季有很多种呼不出名儿的野花盛开,芳草茵茵,引来很多游客。两年多来,经工人的建设,堤坝升高了,蓄水面积一直朝雪山方向延伸,给人一种拉近了雪山的感觉。
作家一行来到坝堤,一个个和雪山合影,和雪山下的圣水合影。唯独不见王祥夫。我四处寻觅,想和他合影留恋,可还是见不到他。
12月末的文海,因受雪山的影响,气温已经很低了,即使是在大白天,也只会在4-5度的样子。由于太冷,我们在大坝上没坚持多久,只好往回赶。
我们来到云南建工集团丽江文海水库建设项目部,那里的工作人员已经发燃炭火,等待我们吃烧烤了。他和工人一起忙着为我们准备吃的。只见云南著名诗人老六乐呵呵地跑到我们面前说:“大家一定要多吃点多喝点哦,这可不是普通牛肉,是高原牦牛肉哦!”我们按照喝酒的类别不同分别坐下,我和喝啤酒的坐在一起,他和喝白酒的坐在另一边。
我们吃着、喝着、聊着。寒冷的只不过是季节,而人情和心境却是温暖的。大家吃饱喝足后,三三两两围着炭火继续闲聊。他却随着夕阳向东不断前移的光,独自退到了房檐下,感受着即将消失的温暖。他的眼神似乎在我身上停留了片刻,又从我眼前闪过。于是,我听到了他的招呼声:“摄影的,你过来。”听罢,我朝他走了过去。
他招呼我坐在他身边,并和我聊了起来:“其实,我也很喜欢摄影,在一家照相馆待过很久。”
“那您的摄影技术一定很棒?”我说。
“也不一定,摄影和画画,我更喜欢后者。”他说。
我们俩就这样聊着,除了摄影和画画,聊得更多的就是文学。他说写文章虽然没画画赚钱,但也是他生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生活的日常。他说他还喜欢收藏,特别喜欢奇石、怪石。喜欢养花、种草、还喜欢小动物……
我被他的勤奋所感动,更为他丰富多彩的生活日常喝彩。
夕阳躲进了西山,失去阳光的高原不仅仅只是寒冷,而是孤寂、疼痛、恐惧。
天空很快暗了下来,我们匆匆离开文海。
回到丽江古城,气温升高,大家都有了精神,于是,一起去古城里喝茶。
古城里的灯光很亮,虽然不是白天,但有些地段的光亮还是显得十分地刺眼。古巷里的行人不少,但步履匆匆。
我们选定一家离大石桥最近的小酒吧,这样,既可以看到桥上行人的模样,又可以倾听到潺潺的流水。喝着啤酒、普洱茶;听着音乐、磕着瓜子。让生活的节奏慢些慢些再慢些。
他喝啤酒的频率十分的缓慢,与喝白酒判若两人。他点了一首慢节奏的歌。我无暇听,只是看他嗑瓜子的样子:拿起瓜子,先慢慢剥壳,一粒、两粒、三粒,然后再一粒一粒丢进口里慢慢咀嚼,再后就是呷上一小口啤酒,给人一种特别享受的感觉。
哗啦啦的雪山清泉穿过大石桥,在我们身旁流淌,像电视连续剧《木府风云》里的动人故事,又像是忽必烈与阿良“夜分手”的惜别话语。总的看来,它好像在诉说着丽江纳西族五千年来的历史变迁。
第二天,在丽江的告别午宴上,他又和大家一起相互敬酒,说着五天来,在丽江、在永胜的各种真实感受、说着惜别的话语……
午宴结束,我送他到了丽江机场。在机场VIP候机室里,由于酒的原因,他靠在沙发上睡着了。我拿来毛毯盖在他身上,候机室里,立刻响起了他并不刺耳的鼾声。
大约三十分钟后,他醒来了,我们又聊起了关于人生、关于家庭、关于文学、关于书法、关于绘画等话题。接着是握手、是拥抱、是挥手,是藏在心里还来不及倾诉的话语!接着是匆匆离去的脚步、是渐渐消失的背影、是飞机起飞时的轰鸣。接着是在我写这篇文章时,一直萦绕在耳边的他写的《永胜散记》中那句:
“永胜,比如此刻,我很想远远喊它一声,就像喊我的一位好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