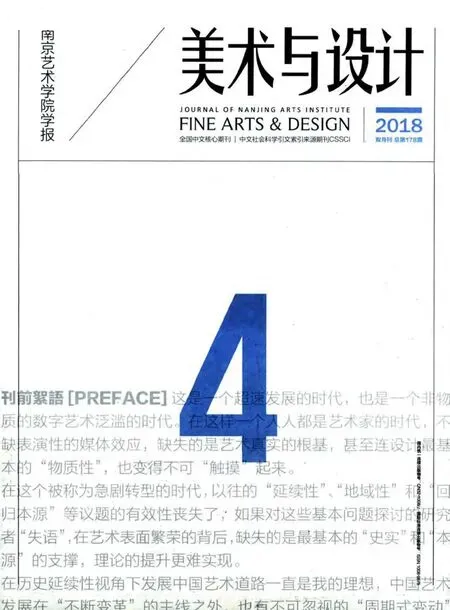中国古典园林中“游观”的美学阐释①
2018-01-25屈行甫华中科技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湖北武汉430074
白 舸 屈行甫(华中科技大学 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4)
动态的游观是园林欣赏的一种重要方式。作为典型的微缩空间,中国古典园林中丰富的自然景观和人文意蕴仅仅靠静观是无法完全展现的,还有赖于动态的、有机的、往复的观赏过程,即游观。正所谓“步移景易”,“步移”体现的是游观的时间性,“景易”讲的是在时间进程中的空间变化。在闲庭信步的游观过程中,主体凭借着流动的视觉感受和深层的心理体验领略到园林中变化多端而又富有诗情画意的空间景象及其蕴含的审美趣味。
已有学者对游观进行了多角度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两个层面:一是对游观问题的一般性阐释。比如陈从周认为游观有较长的游览线,而游观与静观是相对而言的,二者之间是形影相随、相得益彰的关系[1]。潘谷西指出游观是依次展开的
连续观赏过程,而园林风景也是一系列在动的过程中依次展开的连续构图[2]。持类似看法的还有杨鸿勋,他讲园林景象构图始终是相对游观来考虑的,而观者能够既定构图的景象中感受到的是一系列景面重叠印象的总和[3]。刘巍、朱光亚强调静观接触的景象是共时性的,游观则是历时性的,由此园林给人的审美感受是空间流动的综合感受,是四维的时空构成[4]。二是从园林史以及造园文化的视角探讨游观。比如,顾凯认为对动态游观体验的重视发生在晚明以后,而且是在受园林中画意追求的影响下形成的[5]。张家骥认为游观的理念基于“空间往复无尽论”,而后者则是根源于中国古老的哲学思想“无往不复,天地际也”的空间意识[6]。以上学者的探讨可谓是各有优长,加深了学界对游观的认识,尤其是刘巍、朱光亚对游观的时间性以及园林空间四维性的阐释颇有启发性。不过,就目前取得的成果来看,关于游观的问题还有很多地方需要进一步的阐释,比如对游观进行本源式的探求,分析游观的思想本质、效果显现的审美特点等等。基于这一视角,本文将主要从美学的视角探讨中国古典园林中的“游观”体验,以期对学界关于游观的研究有所裨益。此外,因“借景”贯穿于游观过程中,本文还将进一步阐释借景理论的内涵。
一、游观的美学本质:“以大观小”
笔者翻检古代园记中关于游观体验的记载,发现其中关于主体与园中物象之间关系的描述颇为深刻,对揭示游观的本质有很大帮助。比如,北朝时期郦道元讲到“池上有客亭,左右楸桐负日,俯仰目对鱼鸟,水木明瑟,可谓濠梁之性,物我无违矣。”[7]唐代白居易说“乐天既来为主,仰观山,旁睨竹树云石,自辰及酉,应接不暇。俄而物诱气随,外适内和。”[8]从“俯仰”“仰观”“旁睨”等用词可以看出,游观不是置身于外的对象性观看,而是身心惧往,与园中景象相周流、环转。而“物我无违”“物诱气随,外适内和”等说法,印证了游观过程中主客体之间的关系——物我合一,而不是主客二分。同时,这也反映出古代中国人的宇宙观念②刘巍、朱光亚认为园林在某种意义上成为中国宇宙观的“形而下”表达,并指出中国的宇宙模式实际上是有无相生的“气”的宇宙,而园林体现的特性正是“气”的特性。见刘巍、朱光亚.“气”与中国园[J]. 古建园林技术,2004(2):20-24。。进而,由此可窥测出游观的美学本质。
在中国古代哲学的观念里,万事万物的本原是“气”,而整个宇宙则是气运动变化的历程。宇宙生命皆因气禀而相互连通、彼摄互荡,由此组成的世界是气化流行的大生命、大全体。生活于这种气场的人也被气所充盈,并与万物一并沉浮于气的节奏中,即“与天地精神相往来”。而人的心灵也是气韵流荡的,他对事物的观照就不是感官或理性的认识,而是以体现着整体、浑沦生命之气的心灵与被观照之物体合无间。浸润在中国传统思想中的游观也体现出气化哲学的智慧来。游园者依凭着宇宙之气息、节奏来流动地观照园林中的景观,以充足的生命之气去拥抱物象,与之相互摩荡,实际上也是“用心灵的眼,笼罩全景,从全体来看部分”“把全部景界组织成一幅气韵生动、有节奏有和谐的艺术画面”[9]。因此,从本质上看,游观就是“以大观小”,这里的“大”“小”不是数量上的对比,而是整体与部分的关系。“大”是讲的全部,是观赏者所承载的气化生命世界。“小”讲的是进入观赏者视野的园林中的景观,是局部的个体。而观赏的过程就是秉承着气之节奏来来组织、编排园林中的单个景象,将其串联成整体。园林游观中的俯仰、宛转、徘徊、盘桓就是“以大观小”的具体实践,而主体对园景的观照“不是从固定角度集中于一个透视的焦点,而是流动着飘瞥上下四方……把握全境阴阳开阖、高下起伏的节奏。”[9]从而达到“天地与我共生,而万物与我为一”的境界。
二、游观效果的审美特点
由上面推知,内蕴着“以大观小”理念的游观可以说是一种节奏化的行动。造就这种节奏感有园林营造方面的因素,不过更重要的在于游观体验的引导作用。其中,主要的引导方式是路径体验。这是视觉经验的重组,综合了不同方向、位置、距离的观景感受,熔铸为主体审美想象的构成因素,并呈现为适意的游观体验。因循着游观过程的曲折、起伏、顾盼、错落有致,主体将原本是片段化、分割化的空间片段统合为完形的结构。所以说,游观效果呈现在对空间的组织上,即在打破园林物理空间限制的基础上建构属于观者主体的心灵空间。而且,游观是与主体情感密切相关的时间历程,其体验的效果也必然呈现相应的特征来。
1.以时率空
游观的一个重要特征在于它是蕴含着时间的空间体验。理解这点,还要从中国古典哲学中的空间意识谈起。在古代中国人的思维中,空间不是孤立的存在,而是与时间紧密相连的①郝大维、安乐哲指出“对中国而言,时间遍及万物而不可抗拒;它不是物质的派生物,而是其一个基本方面。”而“在古代中国,‘世界’和‘宇宙’的表达就清晰说明,时间和空间是绝不可分的。”见郝大维,安乐哲.中国园林的宇宙论背景[M]//童明,董豫赣,葛明编.园林与建筑.北京: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知识产权出版社,2009:164-165。。这在阴阳五行、律历思想中都有明显的体现。而且在时空的关系中,“时”是占主导地位的,是逻辑的在先。如宗白华对时空关系的阐释:“时间的节奏(一岁十二月二十四节)率领着空间方位(东南西北等)以构成我们的宇宙。所以我们的空间感觉随着我们的时间感觉而节奏化了、音乐化了!”[9]也就是说空间感的形成是以时间为前提条件的。这一观念影响深远,并积淀为中国人文化心理结构的组成部分。反映在园林欣赏中,包蕴着时间观念的动态观赏成为显现空间的重要方式。而由此呈现的园林空间就带有了时间的属性,更为准确地讲,这是“以时率空”类型的动态空间②冯仕达讲“中国的时空观念是具体的——时间不是先验的直观形式,也没有为了容纳具体事件而设想一个抽象的时间隧道。传统文献总是按每个园林自己的时间场域,实时地记述着具体园林的状况。”见冯仕达.中国园林史的期待与指归[J].建筑遗产,2007(2):44.所谓“具体园林的状况”也包括空间的形态特征。冯说也暗含着园林空间是在不同的时间场域中呈现的意思。。
其中,“时”的统领有两种表现形式。一是行进过程中的“时”对园林物理空间的打破和重构。各式各样的墙体、廊道、门洞、建筑等结构的营造将园林分割成相对独立的空间单元,但路径、节点等元素的精巧设计使无法移动的景象在时间性的游观体验中结成一种充满动感的有机体形态。也就是说,时间的渗透起到了串联和重组的关键作用。它使得固定位置的景观不再是零碎和分散的“点”,而是被演绎为园林连续、动态整体中空间“网”中不可分割的部分。在此,时间因素参与到园林空间的表现中。进一步可以说,游观体验中使三维空间流动起来,从而转变为四维时空。并且,游观过程中时间的演进不是线性的。它随着流动观照中景观的丰富变化(疏密、掩映、遮挡、委婉曲折等)而有着节奏的变换,如快进、停滞等。时间的这种节奏性变化对主体的空间感受有着直接的作用。主体在游观中生成的心灵空间也因此有节奏与韵律感。正如张锦秋所讲:“人在其间活动无论从内而外还是由外而内都经历着一种时空连续的发展过程。人对空间内景物的感受随着时间的逐步推移和视点视角的不断变化而节奏化、音乐化了。”[10]
二是不同天象条件下游观空间的多样化显现。天象是古代占星学研究对各种自然现象的泛指,包括日月星辰的出没,春夏秋冬四季间的变换,风雨光电的气象类型等等。这些天象信息影响着游观的效果。古代园记中有很多特定天象条件下的游观记载,如清代黄廷鉴在《梅皋别墅图记》中对四季中不同空间体验的描述:“园之中,春初梅花百本,香雪漫空;二三月红桃绿柳,百卉争妍。入夏红蕖的皪,荡漾清漪,竹风袭人,翛然忘暑。于秋则岩桂早黄,畦菊晚艳,岚翠霏霏,与香气错落几牖。冬则霜枫烂漫,参差掩映,一望无际,加以朝晖夕阴,气象百变,四时之景,无不可爱。”[11]“香雪漫空”“荡漾清漪”“岚翠霏霏”“霜枫烂漫”等景观体验是以时间的连续变化与演进(即四时的交替)为前提的,并因此呈现出带有不同时间属性的空间效果。可以说,此类天象条件下的游观效果也属于“以时率空”的形态。
2.层次空间
如前所讲,在游观的体验中,园林空间完成了从三维到四维的转化,可谓是“活”起来了,并因此与观者的行动同节奏。而游观造就的空间与审美主体流动观照相协调的重要特点就是其层次性。那么,这种层次性有什么内涵呢?首先,从否定的角度看,它不是由焦点透视或散点透视形成的层次。一方面,焦点透视法是以固定的视点将空间中的物象以几何的方式稳定下来。它强调对象的远近、距离、大小等科学性的关系。而游观则正相反。身体姿势、气候条件以及观察的距离、视角的不断变换,使得游观中“没有固定、个别的视点,没有按下快门的停顿,不存有刻意摄取孤立、局部、静止的个别视域”[12]。此种情形下的流动观照完全不具备焦点透视中视网膜成像的条件,由此视线中的景象很难呈现出稳定、匀质的透视效果。所以,主体所体验到的就不可能是由焦点透视法所生成的一幅幅相对独立的“景面”。游观是“以大观小”式的整体观照,是以心灵来统观全景,所观之景象之间没有边界的划分,不存在类似于景面的单元结构,进而,主体的审美体验也不是由一系列景面层次所叠加成的综合意象。另一方面,散点透视的视点不是动态的,但每一节点的成像依然是从某一固定的视点所聚焦形成的,依然摆脱不了焦点透视的成像法则。散点透视形成的层次结构与焦点透视并无本质的区别,而与游观形成的空间层次性则没有关联。因此,从散点透视的视角对园林进行画面式的解读[13],这也是值得商榷的。
其次,从肯定的角度看,游观空间的层次性是因主体心理感受的连续性节奏变换引起的。它是指主体对物象系统的空间体验呈现出的层次变化特征。比如王世贞在《弇山园记》中的记述:“舟行阁前,平桥不可度,两岸皆松、竹、桃、梅、棠、桂,下多香草袭鼻。直北可数丈,则为‘东弇’之‘东泠桥’,桥下两岸皆峭壁,犴牙坌出,寿藤掩翳,不恒见日。”[14]在进入“平桥”、“东泠桥”的前后过程中,生发出“香草袭鼻”与“寿藤掩翳,不恒见日”两种完全不同的体验。类似的这种连续性变化反映的其实是空间的“层次性”推进。将“层次性”展现得更突出的是游观中的“戏剧性效果”[4],如钟惺在《梅花墅记》中的一段叙述:“指修廊中隔水外者,竹树表里之,流响交光,分风争日……折而北,有亭三角,曰:‘在涧’,润气上流,作秋冬想,予欲易其名曰:‘寒吹’。由此行峭蒨中,忽著亭,曰:‘转翠’,寻梁契集,‘映阁’乃在其下。”[8]从“竹树表里之”的廊道胜景到“在涧”亭,再突转到“转翠”亭的动态观赏中,不仅有“流响交光”、“润气上流”、“忽著”的不同身体或视觉感受,也同时呈现出了不同层次空间的显著转变。游观空间的这种层次性,与园林营造中以隔景、障景等方式造成空间层次的区分,在内涵上明显不同。后者属于物理空间的层次,前者则是基于主体心理感受的空间的层次化显现。
那么,游观空间的层次性是不是分割了园林的空间呢?答案是否定的。相反,正是由于游观的作用,使得园林的空间呈现出有机的、内在的完整性。这是因为,一方面,虽然园林营造在空间的表现上是一个整体,但各要素之间是物理上的外在联系。而只有游观主体以“气”将各部分连贯起来,融会整个空间为有机统一的生命体。另一方面,尽管游观空间层次之间有转折、不连续,但并没有断裂。空间层次的区分是节奏化的表征,而空间的内在是连续、统一的,即所谓“似离而合”。
3.情景交融
在讨论完游观的时间性、层次性之后,还有一个层面不容忽略,那就是主体的情感因素及其对游观效果产生的影响。游观离不开“情”,因为观照的主体是蕴含着情感的主体。在游观过程中,情与景是浑融合一的,即所谓“情景名为二,而实不可离。”一般地讲,中国园林美学中的“情”大致有三层意思:一是指由景触发的情绪反应,比如激动、亢奋、消沉、心荡神驰等。二是指主体对景物感知所生发的感情内容,即所谓“化景物为情思”,包括各种形式的情感状态,以及记忆、联想等。如李调元在《醒园图记》中的记述:“每五六月之交,绿柳含风,坐卧终日,可以忘暑。稍下又为清溪草堂,春时啼鸟绕屋,桃花三两枝,令人移情。”[11]此处的“情”就是第二种意义上的。三是指包含心性、意趣等内涵的心灵状态,反映着主体的精神涵养、审美品位和趣味。如计成在《园冶·借景》中讲:“寒生料峭,高架秋千,兴适清偏,怡情丘壑。”[15]此处的“情”就是第三种意义上的。而古代园林文献中的“意”也往往表达出这层意思,如陈璂卿在《安澜园记》中的叙述:“亭后修竹秀石,翛然意远,迤西东向跨水而居者,为‘竹深荷净’,‘环桥’上当其面。”[11]此种的“意”即指心灵。
如上所说,“情”有三层内涵,那么情景交融是哪种意义上的呢?首先,它不是情绪反应与景的结合。这里的“情”是因景的兴发感动而自然生发的,其实质是景(“物”)对主体的刺激,即“景生情”。主体对景是被动的关系,而所触发出的情也是顺应景的,随景的变化而不同。此种情形下的情与景不是对等的,因此也不可能相互融合。其次,情境的交融也不是“化景物为情思”下的情景关系。与前面正相反,这里情是主动的,而景只是引发情感的媒介,如李渔的阐释:“情为主,景是客。说景即是情,非借物遣怀,即将人喻物。”[16]此时的景是“情中景”,它沾染了浓烈的感情色彩,是服从于抒情的。所以情与景的这种关系也不是均衡的交融、统一。最后,情景的交融应该是心灵与景物的相互契合。计成在《园冶·借景》中的说法道出了情景交融的本质:“然物情所逗,目寄心期,似意在笔先,庶几描写之尽哉。”[15]其中“物情所逗,目寄心期”讲的是心、物的互动关系。前面两点已经包含了这层意思。事实上,情景交融的机制中也不排除前两种因素的渗透,因为它就是在心物感应的基础上实现的[17]。不过,更重要的是“意在笔先,”所彰显的道理。这里的“意”不是指个人的情绪、情感,而是指心灵、精神层面的生命情调。意在笔先不是讲以主体的意志来裁夺景物,而是讲主体的统帅作用,即以“情”(“意”)熔铸景物。在情景的融合中,“景”不仅仅是物质性的存在,还转化为主体的“情性相关物”[18],如计成在《园冶·掇山》中讲:“信足疑无别境,举头自有深情”[15];“情”也沉淀于景中,生发出无穷的意蕴,即所谓“庶几描写之尽哉”。这就是“以大观小”的典型体现。如前所讲,作为客体的景与主体都因处在气化世界中,从而呈现出生命的共通性。情景之间相通、共感,自然能凑泊默契、浑然无间。
情景交融使“景”升华为“境”①如杨锐指出:“景”是视觉感受,“境”乃身心体验。“境”是“情”与“景”的交融。见杨锐.论“境”与“境其地”[J].中国园林,2016(6):6-11。,观者在其中也获得了丰富的体验。比如王世贞在《澹圃记》中描述的一段游观体验:“桥长可七十赤,广五之一,每至落照时,暝色浮动,碧芦红蓼,自有渐无,人语鸡声断续于烟景间,徙倚以待东镜之吐,潜颕入波,镕金四注,惊鳞时响,纤玉腾跃,夜分愈閴寂,四顾泱漭无际,呼酒数行领之,却忆吴兴于碧浪。”[14]前几句是游观气氛下的景观,而“徙倚以待东镜之吐”则是讲情景的相款相迎,“待”是从心到物,“吐”是从物到心。正是在这种“情往似赠,兴来如答”的物我互动中生发出了“却忆吴兴于碧浪”的诗情画意。这就是游观效果的“境”。
从“景”到“境”的转化是游观体验的重要价值显现。如果说“以时率空”和“层次空间”侧重于在时间进程中重组园林的诸要素,那么情景交融形成的“境”可谓是在心灵中再造从属于主体的空间。而且,情景交融是贯穿在整个游观之中的,所以园林的空间也可被称为“情景空间”。
结 语
总之,游观不仅仅是目观,也是心观。它是一种与心性、意趣密切相关的体验形式,同时也渗透着主体的记忆、联想等。游观的美学本质在于“以大观小”,这是古代中国人独特宇宙观的体现。从美学的视角看,作为一种体验,游观是节奏化的行动,其效果呈现出“以时率空”、“层次空间”和“情景交融”等特点。通过对游观体验的考察,还可扩展阐释古典园林中“借景”理论的视角:借景不仅仅是古典园林营造的一种手段,也是游观体验中的重要环节②赵纪军认为“‘借景’本质上并非某种特定的、基于物象的‘设计’手段或手法,而可视为在风景经营中丰富生命体验、经历生命旅程的一种途径”。见赵纪军.中国古代亭记中“亭踞山巅”的风景体验[J].中国园林,2017(9):10-14.。正如计成所讲:“如远借,临借,仰借,俯借,应时而借”[15]远、临、俯、仰等概括借景的词汇同时也有行为、动作方式的意思,表达出了主体观照方式的丰富变化。“应时而借”则点出了顺应时间的借景具有“以时率空”的特性,即借景实现的空间效果是在不同的时间条件下形成的。所以说,借景不是孤立的行动,而是动态过程的一部分,明显地体现着游观体验的特征。如冯仕达的阐发:“借景是一种游走性思维,此彼远近、此时彼刻、外景内心由游走性思维贯穿起来,体验其中而不自知。”[19]此外,借景也是实现情景交融的一种方式。正所谓“因借无由,触情俱是”[15]借景并无特别的定式,唯一的标准是能否触动主体的情。由景生情,情景继而相互融会以成“境”,这也是“借景”在游观中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