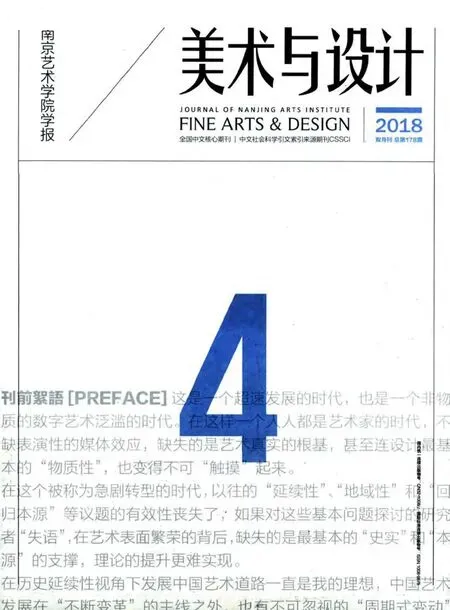方召麐的艺术
——浅谈中国现代水墨画文化传统的延续与跨文化的现代性探索①
2018-10-23香港大学香港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所香港
华 硕(香港大学 香港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所,香港)
引 言
方召麐(1914-2006)生长于无锡世家,是无锡爱国实业家方寿颐和夫人王淑英之女。她自幼攻读经、史、文学、哲学,兼习书画,先后游学曼彻斯特、香港和牛津,转益师事钱松喦(1899-1985)、陈旧村(1898-1958)、陆辛农(1887—1974)、赵少昂(1905-1998)、张大千(1899-1983),接受严格的传统书画技法训练;并从饶宗颐(1917-2018)、刘百闵(1898-1969)、唐君毅(1909-1978)、吴世昌(1908-1986)、大卫·霍克斯(1923-2009)研习中国古典文学。②1937年,方召麐在曼彻斯特大学攻读近现代欧洲史并与抗日名将方振武之子方心诰结婚;1939-1948年战乱时与家人流寓于纽约、上海、香港、桂林、重庆和天津;1950年方心诰骤逝于香港。1954年9月方召麐入香港大学,重续早年因战乱而中断的学业,师从饶宗颐、刘百闵、唐君毅攻读中国文史哲。1955年从香港大学毕业,同年2月在港大中文学部系主任林仰山教授和刘唯迈的支持下于香港大学冯平山图书馆举办为期三日的个展,展出作品约百帧。1956年方氏赴牛津大学研究院的玛格丽特夫人学堂访学两年,研究《楚辞》,教授为H. H. Dubs,研究导师为汉学家大卫·霍克斯和吴世昌,旅英期间于牛津、剑桥两大学和德国慕尼黑大学举办展览,并在慕尼黑和马堡大学参加汉学研究会议。
下文试从方氏具代表性的作品之风格分析出发(即视觉作品于结构及形象上的个体特征),就其对中国现代绘画风格变迁历程中的创新和推动,结合20世纪中后叶全球艺术史之跨文化背景,作重点论述。③此处援引沙比洛将对“风格”的定义:形式因素或母题、形式关系和品质。参见Meyer Schapiro, “ Style.” In A.L.Kroeber ed.,Anthropology Today (Chicago, 1953), p.287-312。对方氏艺术生涯的研究有助于梳理和把握20世纪中国水墨艺术嬗变的历史脉络及文化逻辑,重新理解和认知现代艺术史的跨文化命题。
一、承袭中求深化创新
方召麐在20世纪60年代之前,主要通过临摹老师和近代名家作品,承袭既定图像语汇和风格。钱松喦、赵少昂和张大千这三位代表截然不同的创作风格而在各自领域内取得非凡成就的艺术家作为其绘画老师对她个人艺术风格的演变和形成至关重要。
1920年代末至1930年代初,南京、上海和苏州的艺术院校多偏西洋画教育,无锡美专仍坚持培养国画人才为重。钱松喦在1927年至1933年任无锡美专的美术教员,负责教授美术理论课《艺术概论》和美术课教学。1933年,无锡美专被并入苏州美专,钱松喦与陈旧村合办振南美术函授学校,而方召麐就在该校的面授班里师从钱松喦和陈旧村习山水和花鸟画,掌握正统的笔墨技巧,并有机会在无锡白浪画会举办的群展里展示自己的作品。[1]

方召麐《饮露聊自洁竹蝉》1952 方召麐基金会收藏

方召麐《梅雀图》1953 美国亚洲艺术博物馆收藏
1950-1953年期间,方氏拜岭南派赵少昂为师学画,主要依靠临摹赵师画稿,结合写生创稿和书法训练;并已有机会和老师在日本东京和英国伦敦联合展览作品。④1950年9月方心诰突然逝世,遗有子女八人,方召麐经营丈夫留下的进出口公司,复向赵少昂拜师学艺,而赵师也希望她能通过艺术缓解丧夫之痛。1953年9月26日,方召麐陪同赵少昂夫妇抵达英国伦敦在马尔勃罗画廊举办中国画展览—其中180幅是赵少昂作品,20幅是方召麐作品;师徒一行在三个月内游览法国、意大利、瑞士、美国和加拿大等国。参见通讯记者, 赵少昂、方召麐将在伦敦展览艺术[N],工商晚报, 1953年9月27日. 亦参见通讯记者, 赵少昂飞英将漫游欧洲各国, 华侨日报[N], 1953年9月22日. 亦参见记者, 她以诗作画,新加坡自由报[N], 1955年9月30日。在师事赵少昂的三年里,方召麐工岭南派花鸟、虫草和走兽。《饮露聊自洁竹蝉》(1952年)是以岭南派典型的撞粉法、没骨技巧绘制的效法赵师之作,通过明暗对比,呈现具有通透质感的竹节;而蝉也是赵少昂擅长且广为世人知晓的题材。题款“不肯逐金貂,饮露聊自洁”以娟秀的小楷书完成,与岭南派绘画风格所呈现的精致秀逸之气质相得益彰。在《梅雀图》(1953年)的款识中,方召麐补充道:“无论用笔、构图,皆赵老师教也”。
彼时的方召麐或未能想到四十多年后同样以梅花为题材的作品会以截然不同的风格和构图呈现。《齐欢畅》是方召麐追求表现自我的典范作品。采用仰视的角度描绘盛放的梅花,以草书线条和飞白处理随意蔓延的梅枝,表现和畅春色里恣意生长的浪漫的生命力。她以诙谐的手法绘制老少青年十八位。值得注意的是,于草席上盘腿而坐的人物为无锡特产水蜜桃和桃子包围,这些夏季才成熟的果实不可能与梅花同季,是艺术家借桃意寓思乡之情,类似于其1958年和张大千合作的《菌菇思故乡》。
1953年,方召麐在港于大风堂拜张大千为师,时逢张举家南迁,直到1958和1960年才得以赴巴西圣保罗随侍张师分别三周和一个月,获观张师所藏八大、石涛等古人名迹。[2]1954-1958年,在香港大学和英国牛津大学研习期间,方氏接触到吴昌硕、齐白石、傅抱石的作品,受到这些古今大师的启发,她尝试采用更具表现力的方法,创作出一批泼墨荷花和山水(如《墨荷》)。①齐白石富有表现性的巧拙风格以及经典构图对方影响贯穿于50年代中期至60年代末。有艺术史学者认为方召麐50年代末的泼墨取代著笔的风格转变是受到石涛和朱耷之奇肆超逸、简略精练的风格之影响。参见沈揆一、安雅兰(编).香港赛马会呈现—道无尽: 方召麐水墨艺术展[G]. 亚洲协会香港中心, 2017: 84。这批金石入画的泼墨作品预示其将开启新的形式和表现实验,逐步踏上和岭南派画法全然不同的道路。
二、东西问道和复归传统
1961年至1969年,方召麐为照顾和陪伴赴欧留学的子女迁居伦敦,其间往返于新加坡、美国、苏格兰和中国大陆,举办画展之余游诸欧美博物馆、美术馆和画廊,还陪同张大千在伦敦参观郑德坤藏画。在这段时期,她结识了一批旅欧新派中国艺术家,其中包括后来成为其忘年之交并多次合作的无锡籍旅美艺术家丁雄泉。②方召麐和丁雄泉1997年合作完成《以书法写树及人物》,人物和树的浓墨勾擦由居香港的方召麐完成,而以鲜艳的粉色和绿色完成的染色由丁雄泉在上海完成。方召麐尝试以新的创作媒介、题材和方法,创作实验性的抽象水墨画及油画。[3]值得一提的是,在纽约抽象表现主义画派全盛的60年代,旅居海外的华人艺术家们纷纷投入非传统的笔墨实验,如张大千的泼墨重彩山水,吕寿琨强调透明感和光影对比的香港山水。

方召麐、张大千《菌菇寄思乡》1958美国亚洲艺术博物馆收藏

方召麐《墨荷》1961香港艺术馆收藏

方召麐《抽象风景》1962美国亚洲艺术馆收藏

方召麐《静穆》1966大英博物馆收藏
从60年代中期起,方召麐便逐渐认同石涛不求步履古人而图创“我自有我”的宗旨,尊之为艺术信条。其一,以本心自性作为艺术之起源,艺术创作基于对心性的认知和对个人情感的尊重;其二,不为画法、画派拘束,从传统中再觅中国艺术精神之核心。[4]1966年,方召麐作《静穆》,通过湿笔渲染和浓淡渐变将山水画的元素抽象到最原始和简单的圆形和墨块,而款识则引用石涛《画语录》。①该作于1972年被英国大英博物馆收藏。部分学者和策展人将该作定名为《静穆》,根据1968年英国伦敦格罗斯维诺画廊的画展图录《方召麐画展:1968年1月30日至2月23日》将该作定名为《静穆》,应是从展览时的英文画名”Tranquility”翻译而来。另有学者和策展人根据题款定名《无法之法》。方召麐书画选集[G], 三联书店香港分店和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联合出版, 1986年, 图版65.
“石涛云,太古无法,法于何立立于一画。众有之本,万象之根;见用于神,藏用于人,而世人不知,所以一画之法,乃自我立。立一画之法者,盖以无法生有法,以有法贯众法也。又云泥古不化者,是识拘之也。识拘于似则不广,故至人无法,无法而法乃为至法。”——《静穆》(又名《无法之法》)(1966年)
尽管方召麐意欲以西方技法改良传统水墨画,取道中西、采用“折中”与“合璧”,其结果仍类似于深信绘画应当根植于自然以及中国文化传统的吴冠中、林风眠等现代水墨画家——并未脱胎换骨,亦无意彻底冲破东西方艺术的藩篱。[5]方召麐在多元并进地尝试抽象画、非中国画材质等创新方法后,决意向传统中国文化传统复归,同时采纳西方现代表现主义和抽象表现主义流派着重表达内心的情感的趋向。
方在60年代时对待西方现代艺术的态度之转变和迂回,足见“新”与“旧”、“东方”与“西方”的界限是灵活的,异文化间藩篱的构筑是非单一线性的。这反映了中国现代水墨艺术家在改良传统水墨的转型历史进程中所面临的复杂的跨文化协商;在一定程度上可被视作艺术家在充分意识到强势的西方话语主导国际艺坛时所作的观念上的回应,在一定程度上呈现为对身份的“自觉”,本质是民族性与时代性的冲突和协调下的产物。[6]艺术史学者沈揆一和安雅兰指出,钱松喦在1930年代撰写美术史领域的文章,旨在激发年轻读者想象力,切合在西方文化占主导地位的现代美术教育体系中保护和挽救中国绘画的文化价值,而方召麐很有可能受到钱师影响。[7]

方召麐《泛舟绝壁下》1970年香港艺术馆收藏

方召麐“守拙存吾道,幽居近物情”钤印
1970年,方召麐在美国加州卡密尔张大千居所登门学习一年,广泛临摹其所藏古画。同年底,方召麐与张师在“可以居”园中散步时的师生对谈促使她树立洒脱而独立于文人画笔墨规限框架之外的个人风格。在评论毕加索、石涛、金冬心、齐白石等画家以及部分当代画家时,张氏赞誉毕加索的“生”——题材作风不断创新、具备丰富的情感和超高的想象力,以及石涛的“拙”——具真淳古意、稚拙、质朴之风。他认为高超的画艺当兼具“生”与“拙”的境界,方可令人百看不厌。此后,方氏毕生未停下对“拙”“生”之意境的追求。[3]19
1970年,方召麐在伦敦画室创作取自杜甫诗句“系舟接绝壁,杖策穷萦回”的《泛舟绝壁下》,意境虚渺。这是方召麐在经历了迂回于东西艺术之间的十年后,决意复归传统的代表作,标志其开启根植于中国山水画传统的多元化现代性探索的新阶段;该作被1972年出版于伦敦的方召麐作品集英文版图录刊登在封首。[1]封首艺术家将宣纸揉皱后染色并擦出山石纹理,以此取代皴法。有学者指出,她或受到同时期王己迁的皱纸皴法和李可染强调明暗对比的风格启发。[7]95值得注意的是具有个人特色的新颖构图方式,广泛见诸其后来的山水画作:在画面中轴线稍偏左的位置以山间水道切割左右山体,大胆的纵向留白与浓、淡墨擦染出的山体取得画面布置与配色的平衡和立体感。
中国大陆对外开放后,方召麐有机会回国参观博物馆的珍藏文物,汉代石雕和汉魏碑学对其影响深远。1973年,方氏“参观北京故宫博物院返港后忆西汉汉石俑之“髣髴”,创作《石俑》。[3]28《石俑》经材质转换和视觉挪用,使得风格类似的题材跨材质传播而呈现。[8]方氏模仿并简化汉代石雕和画像,重新组合演绎跪坐汉人物石雕于宣纸平面。人像的线条极简,忽略对真实比例和立体感的追求,舍弃“状物”式描摹;这使得原具有叙述性格的汉代石雕在方氏的画笔下增加抽象美感,减弱人物叙述性个性。[9]不计较形似的石俑反映的终是中国画“以形写神”的观念和古拙朴鲁的审美意趣。方召麐对汉代雕塑造像艺术之所以能快速吸收,是因为她在过去二十多年面对不同文化艺术之碰撞时,力求保有独立之精神,为积累个性化的创作语汇预先铺设好道路,这些汉代人物造像具有的表现力和唤起生命力的能力立刻引起了画家的共鸣。
《长江三峡》中视觉元素的动态布置和重彩处理标志方召麐艺术创作道路的重要探索。该作完成于1978年,创作耗时一年。她参照、借鉴书法艺术对于线条偶然效果的营造,注意采用流畅与顿挫、正与侧、断与连、飞白与涨墨或浓墨等强化反差效果的基本技巧,意在取得刚柔得中的平衡感和气势如虹的张力。

方召麐《长江三峡》 1978 香港艺术馆收藏
1984年,69岁高龄的方召麐开始研习碑学,临碑帖、写篆,改良字体,追崇朴质浑厚的书法风格。而在此之前,方氏书画创作已日臻圆熟,把握书法艺术富有变化的笔触和线条贯注于水墨画。其书由柳公权、颜真卿、王羲之入门,再临孙过庭、怀素草书,学吴昌硕、齐白石等人金石笔法入画,而习汉魏碑学则促风格转向淳朴——老练中含生涩,自如挥洒兼营稚气。明末清初的文人学者通过搜集前代文献证经补史,并且意识到汉碑和二王书法不同的以“古拙”为核心的审美意趣:用笔飞动,姿态变换,不衫不履,而有真淳古意。[10]其实笔墨之巧拙之道也是文人画家所推崇的重精神、舍形式的审美观念。又如陈师曾在《文人画之价值》中所道:“文人画中固亦有丑怪荒率者,所谓宁朴毋华,宁丑怪毋妖好,宁荒率毋工整,纯任天真,不假修饰,正足以发挥个性。”[11]而方召麐的作品在欧美艺术界广泛展出,也使得“书画同源”的中国笔墨之道为西方艺术世界所认识、理解和传播,并被赋予突出艺术家个人表现的现代美学意味。①如1982年10月伦敦许漠士画廊为方召麐举行的个展图录中《书画同源》的英文策展词介绍到,方召麐通过结合树木、房屋的书法性用笔及其周围包裹性的大面积书法题款,揭示了中国画书画同源的真谛;以书法线条作为重要的表现性元素,而非文字本身或描摹的景物母题。参见伦敦许漠士水松山房主人收藏之中国艺术图录(笔者自译)。
三、跨文化的现代性流变与香港现代水墨
方氏于1950年后寓居香港、伦敦进行创作,广泛实验,在此后五十多年的艺术生涯中,风格三年一小变,十年一大变。每期受不同的文化、社会背景变迁影响,于东西文化的交点上多元并进、迂回而行。她在海外多地举办展览,进行跨文化的艺术和学术交流,在同时代中国画家中属罕见。笔者认为对其艺术风格的跨文化分析(transculturality)需和孕育香港现代水墨运动的社会和历史背景联系起来。[12]自上世纪50年代起,在吕寿琨和刘国松等人的影响和带领下,处于英殖民时期的香港水墨画艺坛开始积极探索体现近代东西方相混杂的思想和形式,意在开拓异彩纷呈的水墨新语汇和新秩序。
方召麐和吕寿琨(1919-1975)都出生、成长于内地,在1948年抵港。居港岁月叠合二战后香港地区经济发展最具有活力的时期。香港为旅居海外的华人艺术家提供和世界各地沟通交流的机会,也正是在这样的历史情境下,这些居港华人艺术家不断地推陈出新、热衷于笔墨实验,旨在突破保守落后的文艺局面。吕寿琨和方召麐的老师赵少昂是好友,而方、吕二人在1955年始有书信往来,并在60年代共同参加海外画展。②1955年2月吕寿琨就方召麐在香港大学冯平山图书馆举办的个展给她亲笔致信恭贺展览成功,热烈赞扬其天分和勤奋并存。方召麐和吕寿琨于1967年参加苏格兰国家现代艺术美术馆展出的现代中国绘画展,并于1968年在伦敦格罗斯维诺画廊前后举办展览。参见黄熙婷.方召麐与香港.沈揆一、安雅兰(编).香港赛马会呈现—道无尽: 方召麐水墨艺术展[G]. 亚洲协会香港中心, 2017:73.吕氏的个人风格形成于70年代初,而方则较之更晚十年确立独特的个人风格。
吕寿琨是香港现代水墨运动中承前启后的开拓者。他在60年代末和1970年间形成最具代表性的“禅画”风格,以莲为母题。吕氏“禅画”影响之巨、声誉之隆直接开启香港新水墨运动。[13]他使用平扁宽阔的底纹笔兼或排笔,在不易洇水的玉版宣上以重笔、阔笔焦墨击纸,上点淡彩与清水调和的丹红,追寻飞白金石的意趣和纵横淋漓的阳刚之美。[14]禅画系列以莲的形象象征旭日,常有圆形、弧形的笔触状形,意境近气势磅礴的山水画。

阿道夫·戈特利布《Burst系列》1958私人收藏

吕寿琨《禅画》1970香港艺术馆收藏

方召麐《磐石之固》1981方召麐基金会收藏
若将禅画和抽象表现主义画家阿道夫·戈特利布(Adolph Gottlieb)的《Burst系列》(1958年)及方召麐的《磐石之固》(1981年)作对比,虽然三者所呈现的视觉效果有类似或相通之处,实则存有较大文化差异。吕的作品源自东方禅意,莲象征永恒纯洁,寓意天人合一,画家希冀在创作过程中取得个人精神境界和画意的融合。戈特利布追求不经意间由身体行动造成的效果,本质是情感价值取向通过画笔和身体的运动得以表现的产物。①香港中文大学博物馆馆长姚进庄博士曾于2017年10月于爱丁堡大学举办的会议《艺术和翻译-台湾,香港和韩国》宣读论文《在翻译中发现:吕寿琨对战后美国艺术的解读》,分析吕寿琨对战后美国现代艺术的广泛学习、吸收及与对东方艺术的见解,并指出吕试图构建现当代西方艺术家和中国古代画家之间的关联,以此为基础探索当代水墨如何发展成为当代中国艺术的灯塔,避免盲从全球当代艺术趋势。
吕、方的抽象水墨是在有计划的前提下实验笔墨的结果,突破传统笔墨的规限,扩充中国水墨画的语汇;而且他们的实验基于自然物象——一是莲花,一是巨石阵,吕、方二人呈现的主观对自然的观照是戈特利布所无意追求的。
方召麐在1981年完成的《磐石》,较戈特利布晚了二十余年,较吕氏的禅画晚了十年,而有趣的是这几幅作品之间潜在的视觉挪用现象。笔者认为研究不同文化、社会背景的艺术作品之间有意或无意的“挪用”现象有助于增进对香港乃至中国现代美术流变的理解。援引艺术理论学者Saloni Marthur对“挪用”(appropriation)的定义:发生在相同文化背景下或不同的文化背景之间的索取和占有视觉因素的行为,且这种行为往往不需向原创者征询。[15]澳大利亚艺术史学者Ian McLean指出对“挪用”概念的探讨需与殖民社会和后殖民社会的特殊文化背景联系起来。[16]
香港艺术家王无邪在1959年发表的《绘画之传统与现代精神》一文中呼吁:“我们当然不能绘画立体或野兽(作为基础则例外),而需企图找寻一个新的创造形式,在这形式中,才能发挥我们的个性,而不受西方的艺术家的光芒所掩,最高明要求是仍然将我们的创造形式,归入与我们自己的东方画系,与西方画系分庭抗礼。”[17]方召麐、吕寿琨的抽象水墨作品所呈现的潜在视觉挪用现象确实说明,在60、70年代,生活在香港地区的华人艺术家与西方艺术世界的沟通愈加频繁,且不可避免地受到抽象表现主义和更早期的印象派、立体主义等流派的影响、感染甚至冲击。他们面对前卫的西方艺术进程作出不同凡响的回应,在各自的艺术道路上探寻将中国艺术融入国际艺坛发展之潮流的新方法,建立中国绘画新的表现方式。
四、题材创新:自我表达和人道主义精神

“梁溪方氏”钤印
方召麐的山水画作常怀思念祖国之情,从1970年代起,多幅画作取材自无锡古运河沿岸乡亲的生活;并多署名“梁溪方召麐”,用“梁溪方氏”之印。②梁溪,古运河名,流经无锡市,其源于惠山,北接运河,南入太湖。元王仁辅所纂《无锡志》载:“古溪极狭,南北朝时梁大同(公元535—545年)重浚,故号梁溪,南北长三十里”。富庶的太湖地区长期作为江南地区重要的经济枢纽,在文人书画史和文化史上的地位举足轻重,也正是在这样重视文化、经济基础殷实的环境中,幼年方召麐在家塾跟从陶伯芳习书画经文,同时从杨四箴夫人学习英国文学和欧洲历史,尤钟书法。方氏作于1983年的《故乡太湖》足见思乡怀感,题款是:“念对故乡之感情可谓与岁俱增,今在伦敦画室怀念故乡父老叔伯亲戚,同临太湖风景。父母祖先坟墓以及泥人、玩具、食品,皆为怀念对象”。
方召麐不顾自宋以后中国传统文人画以最小化人物形象而衬托山水之雄伟、静谧的“出世”常态,而采取积极的“入世”价值观,描绘欣欣向荣、具有真实生活气息、甚至颇有幽默气息的场景。[18]《故乡太湖》以蜿蜒小道作为左下角岸边陆地的分割线,由近及远可见五位游湖的路人,其中着朱砂色上衣、梳长辫的女子背影最引人注意。类似的女性形象常见于方氏山水画作,如《长江南岸风景》(1967年)、《青绿山水》(1978 年)、《智者乐山》(1982年)、《克密尔回忆》(1982 年)和《继续攀登及峰》(1986年)。

方召麐《自画像》 1978 美国亚洲艺术馆收藏
评论多突出方氏作为超然于儿女妩媚之态、迭变出新、风格大气沉厚的女性书画家身份,及养育众多儿女的伟大母亲形象。①饶宗颐曾评价其三峡组画“沉厚而浑穆, 尽风雨晦明之状,信可上泣真宰,自古女中画家之所未有者也”。王植波评价“小楷书中,没有拘谨约束的迹象,不类巾帼所为,这大概是她平时为人亢爽的缘故”。朱琦认为方召麐作品所体现的胸襟之豁达和生活之广阔深入,在女性艺术家中罕见。参见饶宗颐序. 方召麐书画集[G]. 方召麐出版于香港, 1981: 3. 参见王植波. 序方召麟书画展, 华侨日报[N], 1955年2月16日.参见朱琦. 香港美术史[M]. 三联(香港)有限公司,2015:198.笔者认为方氏作品中对女性形象的描绘实是突破文人山水不出现女性形象的保守规限,自觉且自信地彰显女性身份。②女性史学者秀家珍(Joan Judge)认为方召麐在追求艺术的道路中战胜了中国传统的性别规限,将艺术事业的发展置于照顾和教育子女之前。她提出方召麐得益于寡妇身份而带来的社会资本,得以作为张大千的女弟子,而未受非议。笔者认为秀家珍的观点有待核实和讨论。作于1970年伦敦的《责任轻减》(Relieved of burden)中,方在款识中写道“曼儿、顺儿毕业于剑桥及伦敦大学后,顿感责任轻减,此后当可以有涯之生从事艺术之创作矣。”参见秀家珍. 一位世界性的民国淑女:历史文化语境下的方召麐. 沈揆一、安雅兰编. 香港赛马会呈现—道无尽:方召麐水墨艺术展[G]. 亚洲协会香港中心. 2017:58-60. 参见方召麐作品集[G].英国Thompson & Thompkins出版社,1972,图版18. 且值得注意张大千招收女弟子人数众多,根据《大风堂同门录》,张大千招收的女弟子内地有 25人,在港、澳、台和海外不完全统计有 9人。参见李永翘. 张大千年谱[G]. 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1987: 550-551.如作于1973年的《指点江山》里,向左倾斜的巨松树荫下有一男一女正观赏高耸入云霄的山峰,方有意识地将红衣女子形象置于画面中心位置。她在1987年补题:“中国山水画里看山者都是男士们,难道妇女就从来不看山的吗?”
方氏在选题方面的创新不拘于表达对故乡河山的感怀和对女性身份的自觉自知,而是敏锐体察人文社会的动态,借助传统的图像语汇,实现“现代生活与历史的重新融合”,将新的题材引进中国山水。[19]例如她1979年作《船民流亡图》,描绘满载从越南出逃的难民之货船在香港海上漂浮等待救援的场景,色彩鲜艳,又具有戏剧感。③1979年7月,港英政府在日内瓦签署处理越南难民问题的国际公约,将香港列为第一收容港,1979年一年内有逾68,700越南逃难者抵港。方氏亦于《船民流亡图》作跋,回忆其1944年中日战争期间举家湘桂大撤退时,携六个孩子举家颠沛流离的逃亡经历,应对家国动乱、个人逆境,她感慨:“由桂林柳城,经金城江、六甲,都匀(濒)频死者数次,仍就活着到贵阳、重庆,侥天之幸也!”字里行间洋溢着个体生命的危难艰辛和对灾难的共感,寄予漂泊者以同情悲悯,彰显人道主义精神和不惧磨难的勇毅性格。

方召麐《怒海浮沉》1981香港艺术馆收藏
小 结
艺术史学者石守谦在对比文人笔墨和非文人笔墨时指出,文人画的笔墨规范体系有两大支柱:其一即强调以书法用笔入画,讲究笔墨的质量和书画同法;其二是指创作图像造型时遵照程式化的形式因素,如《芥子园画谱》可被视为文人画的程式汇集。[20]方召麐的水墨画创作符合第一条“书画同源”的主张,而背离了后一条所强调的程式化的图样形式因素,尤其在勾皴点染的技巧、敷色、构图和选题方面,与文人画体系形成渐行渐远的明显疏离。④方召麐惯用中轴对称的构图与文人画追求的灵秀幻逸的意境相背,她常以纵向河流、瀑布切割画面,形成左右对称的结构,且以呈中空长方形的几何型山体包裹。笔者又注:七十年代的方氏创作可见受张大千的青绿泼彩山水画风格影响的泼墨山水—以厚重青绿设色搭配浓墨,配合焦墨书法勾描山石,突显山石肌理质感,气韵苍率奔放。
此处援引艺术史学者李铸晋对现代水墨画特征的诠释,[21]以区分现代水墨使之独立于传统文人画、水墨画的范畴。[20]13-17第一,现代水墨画在材料上除了使用传统的毛笔、水墨和宣纸外,还向非东方的美术汲取新意;⑤方召麐常用的材料有:单宣、羊毫、狼毫、山马笔、花青、石黄、赭石、石青、石绿、墨、朱砂、洋红。第二是建立与西方现代美术的关系,通过参考和观察西方美术进程,与之对话、互动,使水墨画具有具有现代性的观念、形态和风格。现代水墨的核心在不彻底抛弃传统笔墨的基础上创作出具有时代特征的水墨作品;反应或评论现代的历史背景、社会情境,并跨文化、跨地域地参与同时期的艺术流派或艺术运动之互动。
方召麐是生长于江南并拥有世界胸怀和跨文化视野的现代水墨艺术家。她系统性地承袭中国传统水墨艺术的笔墨规范,重“表意”的书法线条用笔,并以此为基础进行拓展,通过选题、构图等方面的大胆创新从而和传统文人山水产生相当的区分。在艺术生涯里方召麐在东西文化的交点上寻求多种可能的创建,于多元并进的同时迂回而行;并在面临文化间的碰撞与转接时,勇敢地将传统中国水墨引入更为多元的现代艺术的新领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