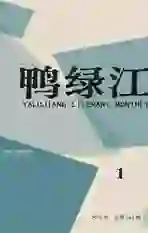漫谈翻译莫言
2018-01-24葛浩文史国强
葛浩文+史国强
上世纪80年代初,为研究中国著名女作家萧红,我在东北度过了不少时光,不仅接触了一大批中国作家,还读了不少当代小说。80年代是“文革”后的十年,出版的小说不如后来的多,好作品更是凤毛麟角。后来读到莫言的《透明的红萝卜》,其颠覆性的语言、充满张力的叙述和幽暗的氛围,深深地打动了我。回国后我又在杂志上读了他的《天堂蒜薹之歌》,小说是全文刊登的, 就像赫尔歇在《纽约客》上发表的《广岛》,是一次发出来的。《天堂蒜薹之歌》与我读过的中国小说大不相同,那种写法我还从来没碰到过,确实让人耳目一新!于是通过中国作协(当时莫言还是解放军的军官)给莫言写信,问他可不可以把小说翻成英文。他回信说可以。小说还没译完,又读到了《红高粱家族》。读完后,我认为《红高粱》可能是将中国当代文学引进西方的第一部作品。所以我暂时放下《天堂蒜薹之歌》,改译《红高粱》。此后我开始翻译莫言的作品。有趣的是,我最先读到的《红萝卜》,到目前为止却是最后翻译出版的。
翻译与变通
相信大家都知道,有些中文用语或词句,是无法翻译或者译不好的。究其原因,既有语言层面的也有文化层面的。当然译者也可以变通,但效果并不完全理想。译者可以选择略过不翻,也可以加脚注,但脚注多少要影响可读性,一般商业出版社是不同意的。再就是在不妨碍叙述的前提下,添上解释性的文字。偶尔也需要你创造性地翻译。我翻译台湾的讽刺小说《玫瑰,玫瑰,我爱你》遇上一个双关语,要是翻成英语的话,双关的意思就没了。我在英语里也找了个双关语加入译文,可谓天衣无缝,但译者并不总是这么幸运。小说的语调、幽默、双关当然是不能逐字翻译的,但至少要能让读者感受到小说的风趣特色。我读译成英文的外国小说,有时会遇上没翻译的文字,比如德文小说翻译成英文,有些德语用词直接引入英译,我不懂德语,但并不感到陌生或甚至反感,只要能通过上下文猜出来就没有问题。这样的变通也是可行的,但在中译英时,恐怕还是很难。
译者与作者
对译者来说,与作者保持联系是必要的。有时译者不一定清楚暗指或象征的功能和目的。遇上隱晦的词语或所指,我会请教莫言,经过他解释以后,可以决定怎么翻译更合适。我还曾给他的小说挑过错,他也能接受。读者未必。译文改过来了,但原文没改,拘泥对等原则又中英文皆通的读者可能以为是我译错了。要是不改的话,我的英文读者可能会认为是我翻错了。二十年来,连同电传和电邮在内,我和莫言之间的通信足有一百多次。他来我家作过客,我们还多次在中国和澳大利亚见过面 。
我个人认为,莫言的长篇中,《酒国》的叙述技巧最为高超。故事的结构安排与众不同:小说叙述分成四条线,其中的两条线是虚构的莫言与他的读者通过写信完成的。小说里自然少不了幽默和讽刺。结尾时四条线索如四条溪水流到一起。要想知道《酒国》的妙处,非亲自读一遍不可,三言五语是说不清的。
最具挑战性的翻译,则非《檀香刑》莫属。故事发生在晚清,其中人物之一是一个刽子手,许多行刑的细节,翻译时常会令我毛骨悚然,甚至有翻不下去的感觉。但对我来说最难的还是语言。一般来说,在英语允许的限度内,我尽可能地模仿莫言的语言风格。英汉两种语言的差异实在太大,要把小说翻好,就不能只按字面的意思翻译,而是得把注意力放在再现原文的“效果”和精神。比方说,《檀香刑》有五个主要人物:刽子手赵甲;刽子手的儿子赵小甲;地方官钱大老爷;茂腔艺人和他的女儿。他们五人说话各有特点,深浅各不相同,凡此种种我要在译文里逐一表现出来,钱大人说话的语气和用词,当然不能和茂腔艺人的女儿一样。所以说翻译《檀香刑》难度最大。
翻译与“创造”
不少人问我,翻译时是与作者共同创作,还是严格地扮演译者的角色。如我所说,英汉语言差异太大,所以要避免“创作”是不可能的。虽然翻译还没达到与作者共同写作的程度,但仅仅把作者的话变成译者的话是绝对不行的。拉丁语系的译者比较“幸运”一些,同源的语言,有很多字基本上是一样的,加上有时同属基督教文明,世界观、人生价值也比较相近,所以翻译起来容易一些。我并不轻视那些同源语言之间的翻译,但我们应该牢记,有些用法在一种语言里灵验,但在其他语言里就不起作用。举个例子,中文说一个男人老实或是一个女人命硬,这都不容易翻译成简洁易懂的英文,当然需要某个程度的“创造”。
我终于托了莫言的福
才过了75岁,我与比我年轻的太太林丽君教授还在翻译几部中文小说,在所谓的百忙之中接到华东师范大学之请,要赶往上海参加“镜中之镜:中国当代文学及其译介研讨会”。2013年10月,我与丽君在中国的大江南北走了几个城市,一连数周东奔西跑,就中国文学如何才能更好地走出去发表演讲,演讲是成功的,可没想到却把这身老骨头搞得筋疲力尽,回国后暗下决心,要等相当时间之后再动身远行。2014年的4月末,又碰上华师大金教授的盛情之邀,希望我到会并演讲,说除了“可疑分子”(学者、老师、学生)以外,与会者还有中法、中德,及中日翻译和三位我曾经译过、喜欢与之见面的小说家:王安忆、阎连科、毕飞宇。我哪能不去呢?太太勉强批了。
4月中旬,我们备上一份比较有批判性质或可说相当尖锐的讲稿,在科州机场上了飞机,先飞到旧金山,然后转机,在空中经过十二个小时的漫长等待之后,才到达上海的浦东国际机场。人是很累,但不饿,也高兴见到来接我们的老朋友陈总编辑与他的夫人。此前朋友沈女士预订了套房,我们住下后就开始倒时差。头两天一边休息一边在不同的餐馆品尝上海各式各样的菜肴。
开会的日子终于到了,像所有的会议一样,这次会议有高潮也有低潮;后者包括本人的演讲吧,其实演讲后的第二天在报纸上引起了不少的争论(有一批特现代的记者暗地里用手机一页一页地照大屏幕上的中文稿子,尔后断章取义地发在报上,这还是后话)。作家与翻译家的对话引来观众的阵阵喝彩。午饭之后,下午的活动就开始了。先是几个专家的精彩报告,可惜,报告还没有结束,我的身体就不听话了:左脚开始不听使唤,走路甚不便,差点没摔跤。怎么办?我溜到走廊请从沈阳特地南下的年轻讲师小潘把我太太叫出来,金教授和他的学生小孙也跟着出来,很关心地打听情况。我本人也感到紧张,想着或许是中风的征兆什么的,但我似乎没有他们紧张得厉害。然后又来了一些人,包括法文系王主任在内。商量的结果是把我赶快送到医院。哪个医院呢?中山医院最近,但是那里没熟人,而王主任的丈夫是师大医院的耳科大夫,还是去远一点的吧。主任打了电话,教授叫了车,我们便上了停车场似的马路。半小时后(我安安然然地坐在后座看“风景”)就到了医院的急诊处,主任的先生在门口等着。endprint
轮椅立刻出现了,不便走路、不乐意坐轮椅的病人就被推到里头检查。神经科的蒲大夫立刻开始询问病况。大夫跟周围的人说,这位说流利普通话的长者就是诺奖得主莫言的翻译。啊!大家表示敬意。他们知道了大概情况后,马上抽血,进行EKG,也送到另一处,作头颅CT而后又回到蒲大夫那儿。大夫应该在五点下班,现在已经快七点了,他仍然愿意继续服务。这次该——啊!表示谢意。他说EKG/CT都没问题,血压高是高一点(人在医院,可能中风,能有低血压吗),最好还是在医院住上一晚,好好观察再说。我说No,太太说Yes,结果就轮到病房去了。一路推我的护士跟人说,他(我)就是莫言的大翻译(这是我的记忆;太太说全归胡扯)到了病房我们三个人——沈阳师大的小潘跟着护理——开始处理我的新环境。这次我能肯定那位特别善良的护士长告诉她部下的白衣天使们,他(仍然是我)是莫言的译者。大家微笑着悄悄走开,又重新投入工作。
好容易告别了其他人——一直陪护、一直关心我的大学教师们,我们三人就开始划出各人的地盘——莫言的译者睡床,太太睡长椅,少年陪护睡短椅。还沒入睡之前,隔壁的一位中年女人(这是两人的病房——另一个病人是年近90的老头,他身边女人好像是女儿)过来很客气地要我给她写几个字。她固然不知道我是谁,恐怕更不知道莫言何许人也,但她由于我们的谈话得知我是一个值得给她留下个什么东西的人。我哭笑不得,同时也感动了。我给她签了名——她起码该知道此人是谁。后来她偷偷地用iPad照了相。
晚上,吃了一点小潘在外头买的零食后就准备入睡。病房条件简陋一些,尤其是厕所没给人什么好感,但因为服务周到,服务员态度甚佳,我真的睡了一晚上的好觉。太太和小潘如何,我不敢问。
第二天早上先来了护士小姐,之后是大夫。问了情况,看没事,就答应我解放。穿好衣服,最后一次坐上轮椅,就滚到出口。受了VIP招待的我慢慢穿過人山人海的、找不到关系的老百姓,上车回酒店。脚还是有点痛,但没有中风或其他重病。昨夜大雨,今早太阳出来,天空灿烂,心绪万千,一切都很顺利,我真托了莫言的福。如果有福气再见他一面的话,我一定要当面谢谢他!
作者简介:
葛浩文(Howard Goldblatt),生于1939年,美国著名汉学家,印第安纳大学中国文学博士。为2012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莫言作品的英文译者,是有史以来翻译中文小说最多的翻译家。
译者简介:
史国强,山东莱州人,现为沈阳师范大学翻译与文化传播中心教授,出版《喜福会》《赛珍珠》《格利弗游记》《上帝知道》《布什自传》《普京自述》《简·方达回忆录》《灼痕》《暮光地带》《时光倒流》《塞林格传》《加西亚·马尔克斯的早年生活 》和《对话潘基文》等多部译作。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