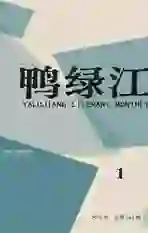六故事
2018-01-24于德北
于德北
之所以把这六个小短篇编织在一起,以平适的面孔和读者见面,实在是因为父亲去世后,我对生活与创作有了更贴切的认知。小说永远都是一根树桩的横切面,任何剖面都可以成为一个以待深究的片继。故事可以问解人生,人生却不完全是故事。人生是被月光漂染的一个蒲团,越安静的时候,越能散发出真谛。
父亲生前是一个编辑,也是一个“科普作家”,为了“科学普及”和农业技术推广做了大量的文字工作,比如化肥与农药。他曾对我说过:“三十年前笃真的事,三十年后却成了大害,这个事实本身就是小说,无须伪造。有些小说只需踏踏实实的记录,不必虚夸的技巧;记住化肥和农药本身,关于其利害的所谓的小说也就获得了所谓的高于生活的资本。”
当初我并不理解他的这段“放言”,现在想来,里边有朴素的大智慧。收拾这六个小短篇,就是要佐证父亲的一番教导,放下虚华的技巧,记录下我所见到的真实。
——是为题记
小 径
我认识一位作家,以前我们是好朋友。曾经有一段日子我们不是朋友了,但不知今后我们还会不会像以前一样,互相拥有纯真的友谊。这个作家长得很粗糙,说粗糙不光是长相,他的品性也很粗糙。所以,每次提起他是一个作家的时候,我总为这个美好的称谓感到有一点……不值。
这个作家原来在一个县城的文化馆工作。他爱人是大夫,两个人有一个儿子,宝里宝气的十分可爱。
按说这样一个知识分子家庭,在小县城挺让人羡慕的。双职工,而且,两个人的工作单位都不错,还没有开不出支的现象发生,虽然作家偶尔拖资,但却很快也被县财政解决了。
作家写了不少东西。
省里的评论家评论他的作品说:由于他长期生活在社会的底层,对平民百姓的日子更加了解,所以他的作品通篇透露出一种平易的、真实的、和蔼可亲的气息……
我认为这是一段非常别扭的话,但作家常禁不住自喜。
他总喜欢把那些美丽的愿望、美好的情感说出来。
作家写过一篇关于离婚的小说。月光,惨白的月光照在小说女主人公比月光还要惨白的鞋上。屋里没有开灯。窗外街灯的余亮从厚厚的窗幔缝隙钻进来,长长的一条,映在地上,像一把剑。
作家对我说:“当时她想:这剑无情地割断了他们五年的婚姻生活。”
现在,她感到真的很冷。
作家写,是离婚彻底击伤了这个女人!
作家写这篇小说的时候,已经来省城进修半年了——省作协给各个地区崭露头角的作者创造了一个进修机会,作家当然是这批人中的佼佼者。他来省城进修,原本下决心写出点好东西,可谁知道,他很快就陷入到他为自己涂抹的月光里了。
按说一个作家喜欢女孩子本不为过,谁让她们长得那么迷人了。
这是作家的话,很幽默。
作家爱上了一个写散文的女孩,我们叫她秀芝吧。这个名字挺朴素的。一天夜里,秀芝拿着自己写的散文找到作家,让他帮着看看。作家认真地看了,看后俩人就交谈起来,恰那天学校组织大家去看内部片,作家因有小恙没有去。至于秀芝为什么不去,我们不得而知。反正二人谈得很投机。
后来作家提议去喝酒,踏着有月光的小径去酒馆。
作家喜欢月亮。
他说:“你看月亮。”
秀芝说:“像银子。”
作家第一次听人说月亮像银子,觉得很有趣,就哈哈大笑。他总认为他的笑很有魅力,其实很粗糙,像他爱人说他:“你以为你笑得很动听,其实这么多年了,我就想告诉你,你的笑声里有沙子!”
一个大夫的忠告如此富有诗意。
关于离婚的事,作家征求我的意见,因为我们那时是好朋友,他觉得我的意见很重要。记得是在一次远行之后,我俩坐在道边,我思忖半晌,说:“还是不离吧。”
我还说了其他一些话,包括很功利地为他分析离婚的利弊,他当时也深为接受。谁知下午的时候,秀芝就找到我,说了一堆抢白我的话,令我十分尴尬。
作家离婚了,领着他的新妻子回小城了,他们有病还到他前妻的那个医院去看,不知他、他的新妻子和他的前妻碰过面没有。他和前妻的孩子归前妻抚养,作家说,这是他最痛苦的事!
可是,这“最痛苦的事”于作家来说也就持续了一年多吧。后来,他的新妻又给他生了一个女孩。满月那天,他又慷慨高歌,说:“这是他最快乐的事!”
痛苦的事,快乐的事,在他那里都过于随便了。难怪,有了这样的生活后,他以及他的新妻子都渐渐地在文坛销声匿迹了,那些曾经赞美过他的评论家们也三缄其口,提及他的“遗憾”,却面面相觑,不再发声。
是为也
傻子是一个孩子,十岁,在育智小學读书。育智小学原来不叫育智小学,叫隆礼路小学。后来好像这个城市的傻孩子越来越多,所以,就把这么一个本来并不怎么重要的学校改成了育智小学。学校的主体是二层日式小楼,有花园,前花园平了,早就平了,做操场。后花园依旧,只不过多了一个厕所,是后建的,很不协调。
傻孩子的父亲是一个小职员,母亲是高干子女,他们的结合跟这个故事无关,跟这个故事有关的只是这个傻孩子。这个傻孩子是他们生的,很胖,眼睛小小的,鼻子很大。
育智小学和早市傍近,只隔一道院墙。
每天,傻孩子的父亲送他上学,像老虎送羊。傻孩子是老虎,走在后边,一边走一边摇晃,笑的样子平常又奇怪;父亲像羊,悄没声的,脑袋僵在肩膀上,一动不动。早市上的小摊主一见他就忍不住笑,笑他的呆板,并无恶意。
有一次,孩子的母亲来送他,大家忽地噤了声。
那女人大个,白皙,走起路来款款有致,眉眼中透着一股灵气。
于是有人按书上读过的路数猜测这一家人,猜来猜去也只是猜猜,并不知真正的底细,但小买卖人的乐趣似乎也在于此,谈过也就谈了,生意好时,谁还会记起这许多。endprint
“嗬嗬嗬——哟——”
突然有一次,傻孩子站在墙边大叫。
他的样子像什么?
离他近的远的小买卖人就笑得前仰后合。
傻孩子止了声,努力瞪大眼睛看众人,眼睛越瞪越大,渐渐又小,渐渐眯成一条缝,猛地弯腰拾起地上的石头乱掷起来。
他说:“别让我再看见你!”
他说:“你赶快给我消失!”
他说:“不要惹我不爽!”
他狂怒的举动让大家吃了不少苦头。
以后的日子,傻孩子频频袭击早市上的人,他用书包背石头,进了校园之后,就藏在墙后狂轰滥炸,一包石头投尽之后,还扒上墙头看看动静,然后才跑去教室坐自己的位子。
早市的人去找学校,学校的老师苦笑着没什么可说。
他一个傻孩子,你有什么办法。
傻孩子的父亲来给大家赔礼道歉,細细查点损失的物品,一一做了赔偿,对大家拱拱手说:“大家就还当他是个三岁的孩子吧,多多原谅,多多原谅。”
开始大家都忌讳一些东西,不好开口。
后来有一个愣小子说:“他毕竟不是三岁孩子了!”
一句话出口,气氛一下紧张起来。
愣小子说:“原谅原谅,他总扔石头也不是个事啊!”
傻孩子的父亲向人群看看,寻到说话的人,点点头说:“我有办法!”
第二天,早市的人像往日一样拥拥挤挤,也许生活本身的故事无穷无尽,无始无终,真的并没有谁认真想过傻孩子父亲的办法。要是傻孩子再次袭击大家,大家会再次愤怒。可如果傻孩子今天风平浪静,人们只有在买卖闲下的时候才会交流:“傻孩子今天挺消停啊!”
可不就是这样!
七点四十分。
老虎和羊准时出现在路口。
羊走在前边,老虎走在后边。走着走着,羊突然停下来:“嗬嗬嗬——哟——”大叫了一声。
面对这父子,大家不知怎么回事,显然傻孩子也愣了一下,但他很快咧开大嘴笑了。继而笑得前仰后合,指着他的父亲,笑得说不出话来。
父亲说:“别让我再看见你!”
父亲说:“你赶快给我消失!”
父亲说:“不要惹我不爽!”
说完,他从地上拾起几块石头向儿子脚前掷去,并跑过去把儿子书包里的石头都倒在地上。
儿子笑得更加不可开交,他指着父亲说:“你有病啊!”
儿子说:“瞧你那样,傻了吧唧的。”
就从这天起,父亲变得“弱智”了,而那个儿子,因为享受了“正常”,毛病改了!
无人说得出这是一幕什么剧,也无人说得出这幕剧的最后结局。傻孩子依旧是傻孩子,父亲依旧是父亲,偶尔,孩子的母亲来送他上学了,有人会问另一个人,说:“瞧这两口子都挺不错的,怎么会有这么一个儿子呢?”
另一个说:“谁知道呢!”
守 街
我在湘西认识了一个姓滕的人。
他说他是贵阳人,身上顶了案子,幸好家中有人上下走动,把事给平下来了。但他觉得在贵阳没法混下去,就出来。向东,走到怀化,又转到这里。这里是凤凰,沈从文先生的故乡。他给我讲,内地的三蛇酒都是假货,真的三蛇酒要用金环蛇、银环蛇和五步蛇配制,而且要活蛇,这样泡出的酒才有效用。
他说:“效用!”
这个词用在这,我觉得很新鲜。
那天,我从吉首赶到凤凰时,天已近七时,黑了,半山一片灯火,漂亮得很。我从车窗探出半个身子,看沱江清清浅浅,无波无纹,细品处,风侵檐瓦、水润柱根的纤细之声也浸漫开来,非常人能够体会。
就觉得在凤凰应有奇遇。
车至宾馆,订下房间,简单洗漱。拎着一瓶酒出来,问三问四,直奔沈先生故居去。天太晚,故居已关了门,宽窄的门洞让人不觉生出感慨。愣愣地站一会儿,一头折回来,满心思要寻一个小店喝酒。
路那边灯火很亮,灶上的火也红,便直进去。
迎面的就是姓滕的人。
我叫了一个家常豆腐,叫了一个腊肉炒辣子,自启开带来的酒,依一个角落小酌起来。
姓滕的不是老板,是厨师。老板也姓滕,苗族。姓滕的人也姓滕,但是汉族。大约过了四十几分钟,店间的客少了,灶上也不忙了。姓滕的人就过来,先笑了,然后坐在我对面。我也笑笑,随手拿了一个杯,请他呷酒。湘西的人都管喝酒叫呷酒。我这样说了,他复又笑,说:“我是贵阳人,我们喝点酒吧。”
这是一个挺幽默的变化。
这时,老板也过来,大家简单地寒暄,算认识了。
老板指着姓滕的人说:“老哥手艺可好!他在北京饭店干过,他哥哥在北京谋差事,有大本领。老哥去北京饭店干过,干了三年,呷他菜的都是外国人,都竖大拇指!”
我好奇:“你怎么知道?”
老板说:“老哥讲的。”
姓滕的人就说:“在北京饭店好干,客人反而多不挑三拣四,怎样做了就怎样吃,吃起来满是滋味。”
停停又说:“北京饭店这样大的饭店做出的菜还有差?”
自然差不了。
说话间,姓滕的人起身到灶上去一次,不一会儿,又回来,用小碗盛了一点东西给我。一碗底朝天椒上散落着几个奶白色的小蛋蛋。他说:“这是野蜂的卵,在山上采来的,用油炒过,好吃。”
尝一尝,果然不错。
接下来的时间多半听姓滕的人讲他自己。
他说:他在贵阳开一个八层的大酒楼,见过大钱,他帮过一个东北人,是牡丹江的,到贵阳办货,钱丢了,他让他在自己的酒店白吃白喝住了八天,临走还拿了一千元钱给他,东北人非常感激。
他连说了三遍。
他说:“你们东北很冷,我去了一次,看那个朋友,本来想找个活干,可太冷了,受不了,回来了。”endprint
我说:“你开八层大酒楼,为什么还要出来做?”
他沉默一会儿说:“犯错误了。”
酒楼是公家的,他经营,后来犯了经济上的错误,被开除了公职。
他说:“我爱交朋友。”
他说,他的钱也多为朋友花了,人生就这么回事嘛。
我细打量他,长脸,眼睛不大,脸膛红红的,一笑牙齿很白,而且十分整齐。他约我第二天中午再来,他烧两个东北菜给我吃,他让我一定来,并约好下午一起去一家蜡染厂看看,他认识那里的厂长,当地一个比较有名的画师。
酒罢,我要回去,他坚持送我,送到宾馆,又到总台要了我的登记单看看。
他说:“明天一定来。”
我点头。
一夜无话。第二天早上,我起来散步,远远地见他正和一个服务员说话,我觉得有趣,要过去打招呼,他却匆匆地走掉了。服务员看了我一眼,也匆匆地走掉了,好像他们之间在说一个什么秘密。
我站在那里,想昨日并无醉酒,所言所谈,历历在目,他见了我为何又不打招呼?
多了一个心眼,简单地收拾行囊,悄悄地走到街上去,雇一辆车,装好东西,然后告诉服务员退宿,然后去沈先生故居去,这是个不大的院子,房子已非常古旧,有一个管理员坐在那里,手边读着先生的《边城》。我花两元钱买了门票,她就把所有锁着的门打开,这院子没有灰尘,但我觉得院子里灰尘很重,脚下的步子轻了,再轻,久久望着先生的手稿,无话,提了包出门,赶自己的行程。
也曾犹豫一下,去不去赴那个约会呢?
唉!算了,先生笔下的湘西人物如此丰富,我怎么知道我面对的这个姓滕的人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物呢?让车夫把我直接送到客运站,截住一辆中巴,直奔着麻阳去了。
回头望一眼凤凰,这美丽的小城。
回头望一眼凤凰,却见姓滕的人从远处急急地奔客运站,他是要远行,还是来寻人?要是寻人是来寻我吗?车过沱江,一切都远了,但我忘不了姓滕的人,他挺有意思,他使我一想到凤凰就会念起他来。
尽管,我并不知道他是干什么的。
湘 绣
先是坐在天子山的石阶边和几个土家族小伙子闲谈,他们给我讲一种小飞鼠,在天子山常见,能在树林间飞来飞去。他们还讲山歌,说《马桑树》连三岁的孩子都会唱,他们不好意思地推我敬到他们眼前的烟,推来推去又接下,急忙寻火点燃。这几个小伙子是山上一家旅馆的服务员,干的工作好像是拉客人,他们问我,我们这帮人的导游在哪里?看来他们要寻找一些生意。
我们交谈的地方在路边,在一个很随意搭起来的木条上。许是坐的人多了,那木条已经油亮亮的。我只顾着和他们交谈,并没看其他的地方。等谈话停下来,我才发现我的对面是一个店铺,一个漂亮的女孩正注视着我。
见我看到她,她不好意思地低下头,随后又抬起头,说:“你这个人真和平。”
她说第一句,我没听明白,笑着问她:“你说什么?”
这回我听明白了,她说的意思是我这个人很平易,很和藹,没有架子。
可为什么用和平这个词呢?真是好玩极了。
我在她的摊位上买了一包烟,然后,循着一条石板路到我们订下的宾馆去。
站在天子山顶,看西海云雾,耸立的石峰,远处的一抹青绿,偶尔听到一二吆喝之声,感觉非常愉快。夕阳在西海的那边落了,晚霞映透了半个天。过路的男子嘴里哼着山歌,并友好地冲你笑笑,也有轿夫收拾家什下山,身影飞快,转眼就消失在歌楼的那边。
我很想喝点酒。
但因会议的羁绊,直到晚上九时半才得以自由活动。
匆匆穿上外衣,沿着山顶的路向有光亮的地方去。却是白天和土家族小伙子闲谈的地方。别的铺子早已关了门,更有一些店主挤在一处看一台黑白电视,是一个老掉牙的裹脚剧,难得大家看得津津有味。
我又见到那个女孩。
她坐在铺子的灯下,手里打着毛活,看到我过去,忙站起来,双手搓着不知放什么地方好。
“要点什么啦?”她问。
“啤酒。”我说。
“要几多?”
“四瓶。”
她显然惊讶了,小心地说:“四元钱一瓶的。”
我说:“可以。”
她去架上取来。
面对黑黑的群山,我很想和她说点什么,可不知道怎么的,我有点不好意思。尴尬半天还是开了口,问她叫什么名。
“罗英。”
问她多大?
她说:“二十四岁。”
说完,她转到铺子的后边,继而传来一阵叮当的响声,很轻微,等她回来时,我的面前多了一碗腊肉。
“吃吧!”她低下头。
我尝了一口,味道真美。
“你这个人真和平!”我说。
她抬头看看我,我也看看她,开心地笑了。气氛一下轻松下来。我告诉她我是一个作家,来这里开会,我特别喜欢喝酒,喜欢和人聊天,也喜欢听山歌。我问她:“你们土家的女孩谈恋爱还对山歌吗?”
她摇摇头,说:“过去对,现在少了。”说完叹口气,眉间多了一点烦扰。
我想起《马桑树》那支歌,自己学了半瓶醋,还差半瓶没注满,何不请教一下。罗英还真欣然。她让我把我学的给她唱一下,我觉得难以启口,她一个劲儿地鼓励我,我才小声唱了一句。
她说:“不对,是这样。”
马桑树上搭灯台,
写封书信与姐带,
郎去当兵姐在家,
我三五两年回不来,
你自己的好花别处栽。
她小声教一句,我学一句,四瓶啤酒喝掉,这支歌的调子和第一段词就全学会了。我还想学第二段,她却不教了,说天太晚了,会影响别人。再说别人看到她这样高兴,会以为她的日子很好过,会生气的。endprint
这种理由倒挺奇特。
我们说话的当口,有一个半大孩子走过来,凑近我,问我按不按摩,一小时一百块钱,他还打一种很花哨的手势,笑容里充满暧昧。我没应声。罗英却挥手赶他,用土家话“哇啦哇啦”地说着什么。
半大小子跳着走了。
罗英还拾石头打他。
从他们的表情里我大致明白了他们对话的意思,半大小子也许在说:“你轰我,难道你要把他留下?”
罗英说:“你放屁!”
罗英拾石头打他,他就逃掉了。我沿着他的脚步声也向宾馆去,心里却多少有一点动荡。我回头看罗英,她还站在灯影里,她举起手中的线团,冲我摆了摆。
天黑了。
第二天,我将随团下山,走过罗英的铺子时,我把两盒“太太口服液”送给她,她有些不知所措,又有些欢喜,双手接到盒子,一个劲儿地问我:“你要什么呢?我送你什么呢?”
我想想,说:“送我一支歌吧。”
她脸上的灿烂比秋日的阳光还美。
我下山了,走出好远,身后传来罗英的歌:“马桑树上搭灯台,写封书信与郎带,你一年不来我一年等,你两年不来我两年挨,你钥匙不到我锁不开!”
是《马桑树》第二段。
她唱得那么开朗,那么好听!
一个学生
有一年,我的朋友得了心脏病,请我去给她代课。这课不难代,说白了,就是讲文章。讲各个历史时期的好文章。讲诗经某篇,楚辞某段,古诗十九首,三曹、庾庆、陶渊明、竹林七贤、李杜、元白、三苏、王安石、元小令、关汉卿、明清小说、晚明小品、龚自珍。开列了很多,基本都熟悉,稍加备课,便可“开坛”。谦虚说,可以和学生共同探讨着把课代下来。
一共三十二堂大课,讲了四个月。挺累。
课讲完了,大受欢迎。最后一堂课,兼做告别,有学生跑上台来,把一捧鲜花送给我。
心里很自豪。
在我的学生中,有一个女生,人长得很饱满,性格也开朗。我讲课的时候,她来得最早,总是坐在第一排,双手托腮,每每做沉思状。有一次,我讲《史记》中《项羽本纪》,讲到垓下突围一节,她竟然落泪了。她十分动情地伏在书桌上,双肩一耸一耸的。
我从心里喜欢上这个学生,引她为知己。
试想,在现在的孩子当中,有几个可以理解项羽的英雄气概,又有几个人能够知道项羽的狭隘呢?
那以后,我每次讲课,都要观察一下她的表情,她的一颦一笑,多多少少对我有一些影响。
有一天,我因为宿醉,头疼得很,她坐在下边看了半天,似乎有所觉察。下课的时候,她特意等在门口,见我出来,竟约我出去吃饭。她领我到学校附近的一个小店,要了一碟清淡的小菜,要了一碗热汤面,一杯白酒,看着我把这些东西吃下去。
我问她:“你为什么不吃。”
她说:“看着你吃,你昨天夜里一定喝酒了。”
我问:“你怎么知道?”
她笑一笑,说:“我爸爸也是这样。”
我覺得她很可爱。
有了这次交往,没有课的时候,她也经常到我工作的地方坐一坐,每次走的时候,都要让我推荐一本书。我那里的书实在多得是,便依照她的喜好,介绍一两本。四个月的时间,她大约也读了十几本书。那段日子,我正给我的孩子选日本读物——他学的是日语,所以,手边的日本文学作品比较多。我向她推荐了吉本芭芭娜、青山七惠、石黑兼吾等人的作品,也推荐了川端廉成和三岛纪夫的作品。后来,她对我讲,她喜欢三岛的《午后曳航》和《潮骚》,我并不感到奇怪。
转眼到了期末。她突然又约我吃饭,我欣然前往。不想,这一次赴的是“鸿门宴”,她直截了当地向我要期末考试题,并声称不是为自己要,而是为班里的几个男生。那几个男生几乎不来上课,我如何能把题给他们呢?就算他们一堂课不落,我也不能违背原则。
她从口袋里拿出六百元钱,放在我面前。
我大惑不解。
她却十分老道地说:“都这样,他们买题还不行吗?”
我真的有点愤怒了。
她见我生气了,脸有些红了,既而眼泪落下来,一边收钱,一边小声说:“我也是为了帮帮他们,花那么多钱来读书,怎么也得过呀。”
我沉默着,未对她的话做出反应。
这件事就过去了。
期末考试,有五六个学生挂科了,不知道是不是她要帮助的那几个男生。
经过四个月的休养,我的朋友可以上班了,我也顺理成章地退出“历史讲坛”。我的那些临时学生也因为升了一级,马上要应付实习和毕业,而和我失去了联系。我喜欢的那个女生,偶然会发来短信,都是一些礼貌的问候。又一段时间过去,这样的短信也没有了。
今年春天的时候,我突然接到一个短信,是外地来的,手机号码很陌生。
“我换手机了。”
过了一会儿,又发一条:“我是某某,意外惊喜吧?”
又一条:“我想买一个摄像机。”
“我差四千元钱,可以借给我吗?”
“你可以开条件。”
我整个人都蒙了。
我不知道这样的信息该不该回,要回怎么回。我犹豫着,大半天的时间过去了。
傍晚的时候,她又发来一条短信:
“胆小鬼,吓着你了吧?”似乎在调侃我。
我终于还是没回那些短信,因为我实在不能以这样的方式借四千元钱给她。让我没想到的是,又几天之后,我误拨了她的电话,她的号码“并不存在”了。
我一时愣在了那里。
送 灯
月光照下来,雪野一片银白。
工作的关系,我羁留在这个远离都市的山区小镇。镇子不大,几十户人家,因交通不便,在这样的季节很少有人进出。
对于小镇,我是完全陌生的。endprint
人近中年,父母身体不好,孩子正在读书,妻子因生活的焦虑而越来越变得喋喋不休。单位正在改制,也许我这一次回去,就已经被列入下岗的名单。还有,与曾经的朋友投资生意,不想一阵下来,自己的钱赔光不说,连借贷的钱也收不回来……
这一切足以让我变得颓废了。
我借住在一个猎户的家里。当然,他现在已经不再打猎了,靠开杂货铺为生。他老了,不再有什么奢求,唯一的乐趣就是借着烧酒回想穿行于密林深处的那一段段时光。
“看过送灯吗?”他问我。
我摇头。
他告诉我,这是山里举丧的一个仪式。家里人要为死去的人送灯,以照亮他奔赴黄泉的路。据说,那路上也开着花,有灯光的照耀就不会显得过于可怕。
于是,就听到了唢呐声声,悲切而悠长。
这镇上还真有一个老人故去,据说享年八十五岁。生前是铁路工人,在两条钢轨间一走就是几十年。
“去见识见识吧。”猎户说。
我點头。
我们沿着夜路一直往西,终于到了村口。
映入眼帘的是大红的棺木直横在院子里,棺木周围拥挤着黑压压的人群。送灯仪式刚刚开始,一个喇叭匠子头戴孝帽,手抓大号的唢呐跪在棺头。另有三个人跟在他身后,唯一的差别是头上无白。
跪着的那个人从指关节到肩关节依次放了四盏灯,两条胳膊就是八盏,加上头顶的一盏,一共九盏。九盏灯亮着,在寒风中扑扑作响。
他们就是要把这九盏灯一盏一盏地摆到棺木上去!
唢呐声起。
跪着的那一个一边吹着断断续续的悲音儿,一边绕棺一周。头平臂曲,九盏灯纹丝不动。
回到棺头,有人喊:“乐停——”唢呐师傅送的第一盏灯是一帆风顺灯!乐起——”
乐起了,又是一周。
第二盏灯是二龙戏珠灯。
后面依次是三阳开泰灯、四季生财灯、五福临门灯、六六大顺灯、七星高照灯、八面玲珑灯、九九归一灯。
这唢呐声悲,尤其是在寒冬的夜里,让人骨头都丝丝发凉。
也许是唢呐的旋律触动了我的心境,想想那未曾谋过面的离世的老人,此时此刻就站在不远的地方,和家人依依惜别。
只可惜,谁也看不见他。
我在麻木中有了一点感伤。
那个领头的唢呐匠子从我身边匆匆走过,腋窝下夹着唢呐,手里点着刚刚得来的赏钱,嘴角禁不住滑过一丝温暖的微笑。
我想,他应该是满足的。
“喝点吧!”身边又有人问他。
“喝点!”喇叭匠子回答,口气果断而坚定。
“咱们回去喝点?”双手袖在怀里的猎户问我。
“喝点!”我的心里好像也多了一缕光明。
又起风了,雪,一片一片地落下来。
【责任编辑】 行 者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