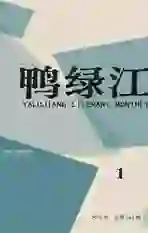留长辫子的女人
2018-01-24傅杰
傅杰
1
我年轻时当过兵,退役回来没多久就和一个名叫欣的女人好上了。那是缘于一次谋杀,我要杀的那个人是我们镇长。我现在已经忘记了我们镇长的名字,也许压根儿我就没在意他叫什么,光想着犯罪了。当时的情况是,镇长特别宠爱欣,社会上管这种情况叫包二奶。不过我想当杀人犯与欣当不当二奶没有关系,倒是与我爸、我妈、我哥关系密切。
本来我不想提我爸,只想讲述我和欣的故事。可是不说我爸,这个故事就过渡不下来,所以我还得先从他开始说。我爸从农村出来,最初在镇政府食堂当炊事员,几年后转正当上了食堂管理员,那就是官了,这官搁谁头上没特殊情況是不下厨的。可是轮到我爸还得下厨,因为厨房里有一位女临时工,我爸得以师傅的身份帮助她干活。后来这个女临时工就嫁给我爸了。我不知道他们俩人的感情是怎么建立起来的,因为他们是长辈,无论如何我也不敢妄加猜想。可以让我想象的是,我爸当时娶我妈所要承受的压力有多大;因为在农村老家,还有一位牵挂他的女人和一个孩子。
我从来没见过我爸的前妻,事实上我也不可能见到她。只记得在我读小学时的一个夏天,我们家里突然出现一位年轻小伙。他忧郁的眼神,黑瘦的面庞,个头和我爸差不多高,只是没我爸胖。我爸告诉我这个小伙是我哥,今后将由他接送我去“一小”念书。我当时什么也没想,根本就没考虑我这位哥哥的来历:为什么叫他哥哥?过去怎么没见过他?
我哥不会骑自行车,接送我上学只当个伴儿,别出啥闪失,主要是怕人贩子把我给倒卖喽。大人们的担心很有必要,我却不懂,以为驮我的自行车闲了,我哥哥陪我还不是照样自己走吗!有一次我起床早了点,就偷偷地一个人走到学校。我爸知道后不饶我哥了,批评他没有责任心,缺少兄弟深情啥的,说得实在是邪乎。我哥委屈得要哭。这事怪我不怪我哥,事后我给我哥赔礼,用零花钱给他买了一盒玉溪烟。
我小时候常去食堂混吃,因为那里好吃的太多了,我不主动去吃,我妈下班也给捎回来,倒沾了偷的嫌疑。与其麻烦她老人家担惊受怕,倒不如我主动前往,赶上什么吃什么。有一天我爸告诉我,往后别去政府食堂了,再去可就现眼了。这时我才知道他们分别调离了食堂,我爸去外地深造学习,我妈也当上了计生站干部。那年我爸不到三十岁,距离他收监等着枪崩刚好二十年。我爸离开镇政府食堂一路下来,最终坐到副镇长的位子,谁也不知道在他美好的憧憬当中,是否想到自己的未来会有一粒花生米大的弹丸等着他。
其实我们大家都一样,脑袋往枕头上一搁,做什么样的梦就由不得自己了。
我哥在我们家住不到一年,就搬到单位的宿舍里去住了,这时我妈才告诉我,我和我哥是同父异母。
我哥不在家住还时常回来吃饭,但他并没有坚持多久,可能跟他的忙碌有关,后来就很少回家了,更别说和我们一起吃饭了。我始终认为我哥是个能人,他发展得很快,我当兵走时他就是镇上的经济名人,经营着两家餐馆,一家定位工薪阶层,另一家则是用公款吃喝的天元大酒店。也许就因为他太能耐了,后来才做了不可饶恕的罪人吧。
2
我不知道我爸的死跟谁有关,我哥只是电话里告诉我,说爸爸在牢里等着枪崩,回来瞅他一眼吧。
我回来时我哥告诉我,我爸收监后他背运背到家了。他定位公款吃喝的天元大酒店转租给了别人,花去的百万元装修拿回来还不足个零头。我哥转租酒店的原因是,我爸被抓时有人放出话来,如果花钱可以保他一条老命。我们家原本有些钱,提审我爸时都被他当成非法收入上缴了,我哥动用了他的全部积蓄,同时转租了酒店。我哥说即使不急等用钱,他也要把酒店转手,因为我爸这棵大树倒了,没人再用公款到我哥的酒店来吃喝,消费转向别处。没想到的是,屋漏偏逢连阴雨,面向工薪阶层的酒店又失火了,几个包房不但烧得面目全非,还烧死一个打工妹,打工妹的家人张口就要五十万。五十万在我哥眼里过去不算啥,现在就是个天文数字了。可他跟我说,人家一个好端端的黄花闺女给烧死了,那是多少个五十万也买不回来的。无奈之下我哥卖了我们家的三居室,把我妈接到他的饭店来住了,我回到家,只想知道我爸被判极刑的全部经过。毫无疑问,我爸吃的那粒枪子不是无缘无故的。他贪污受贿,败坏党风,违反国法,我哥说这些都是事实。可是——我哥又说,败坏党风违反国法的就他一人吗?要不是他还想在仕途上往前多走一步,也不至于落得如此下场啊!言外之意,我爸在官场遭了别人的暗算。
我哥又气愤地补充说,镇长那个王八蛋,明明是他贪污公款,明明是他乱搞女人,却让咱爸当了替罪羊,我们当儿的不报此仇,他老人家九泉之下能瞑目吗?
家里发生的一切我全然不知,我哥的想法是让我与行刑前的我爸见上一面,可我回来时,我爸的骨灰早就运回老家,被埋在一个半阴半阳的山坳里了。
我哥说,为了保住我爸的那条老命,他凑足了二十万块钱,让我妈去行贿镇长。我哥说,一个打工的黄毛丫头还值五十万呢,咱爸一个堂堂的政府官员,没个一二百万哪下得来?钱是啥东西?钱是王八蛋,没了咱再赚。我哥跟我说这话时依然显得很有魄力,他咬着后槽牙,左手的俩指头伸出个剪子形,没办法,让咱爸掉价了。二十万现金凑足后,我哥就与镇长约定了地点。我哥跟我妈说,镇长同意见咱,这事就成功了三分之一,如果镇长把钱收下,这事又成功了三分之一,那一成就看运气了。我妈并不怀疑镇长的低劣人品,她担心我哥说的话是否属实、镇长有没有与法律掰手腕的本领。
镇政府在护城河北岸,通过一架吊桥与南岸的主街相通。我妈拎着一个肥大的休闲布兜走向吊桥中央,在那里停下,久久地望着远方。吊桥下面的水很少也很浅,视力所及之处,偶尔有小片干涸的河床凸显出来,仿佛脑壳上的斑秃在我妈眼前摇来晃去。我妈扶稳铁索,努力镇静自己的心情,尔后从口袋里摸出一个灵巧的小盒打开。盒盖的反面立刻映出一张憔悴的脸,我妈觉得那张脸上,并没有让她再进行修饰的地方,就把小盒盖好装进了口袋。
我妈的准备工作做得还是挺充分的,为避免撞见熟人,她把时间提前了一个小时,也就是早七点钟左右。装钱的兜子也是极不起眼的休闲布兜,兜里除了钱,还装了几盒降压药。她心里不停地默念着准备好的台词:早晨好镇长,麻烦您把这几盒药给老胡捎去,他现在啥样我也不清楚,本来他血压就高,我担心……endprint
“台词”到这里基本上就结束了,往下可以逢场作戏,通常情况下,这时候应该是以泪洗面。这时候的泪水有多种含义:忏悔、痛苦、请求怜悯等等,关键是面目表情传递给镇长的信息最重要。
镇政府大院里有个老头摆弄着竹扫帚,他的身边弥漫开灰色的粉尘。我妈走过去喊了一声关大爷您早!老头说早啥呀镇长他们比我早。我妈现出惊讶状,说镇长都来了?老头翘一翘下巴,小声说,你没看见他的车吗?我妈看见镇长的车子停在人造盆景旁边,好像等待多时了。她忽然产生一种不祥的预感,边往楼里走边转头后看,好像有人坠在屁股后头,或是在什么神秘的地方监视她。
镇长办公室在四楼,我妈敲开那扇门,看见镇长坐在老板台后面吸烟。我妈一进屋他就把烟掐灭了,问,东西带来了吗?我妈心跳得非常厉害,昨夜默诵的台词也来不及细想,只是顺口回答带来了,随后就把兜子放在镇长的桌面上。在这里我妈强调一个细节,那就是镇长把兜子揪了一下,大声地咳嗽一声。我妈对这个细节的理解是,镇长揪了一下兜子是证实钱的数目,完后再向外面的人使动静。果然镇长咳嗽完,被我妈反手关死的门居然打开了,进来两个穿制服的人,从他们的着装上判断,这两个人是检察院的工作人员。至于他们埋伏在什么地方,这已经不重要了,要紧的是他们的出现目的何在?是偶然碰上,还是早有预谋?我妈希望是前者,但她悲哀地感觉到自己已经被一根无形的绳索套住了。
我妈当时真可怜,惊恐地望望身后,就把求助的目光投向镇长。
镇长跟穿制服的人说,你们来得正好,她就是老胡的妻子,是来上缴赃款的,你们拿去数数有多少。
镇长说这话时,语气就像打圆场,而他揪起兜子的神态,更像屠夫努力抓出猪下水时的模样。我妈一阵心寒,不由得打了一个冷战。
我无法想象我妈在那种情况下还能说什么,还能做什么……
我媽告诉我,她那时差点就晕过去了,后来慌慌张张地就站到吊桥上,最想做的事情就是从桥上跳下去。我听到这里,肺都要炸裂了。我想我妈没从吊桥上往下跳,一定想到了我,一个远在他乡正准备实现将军梦的儿子。我妈说,是呀,不是想到你,我早随你爸去了。
我几乎是咬牙切齿地发誓,不把镇长干掉,我就把自己给劁喽!
3
我要谋杀镇长的最初动机就是从这里开始的。
我跟我妈说,您别拦我,让我去弄死他!又说,你们在家遭了这么多罪,我在部队却打着理想旗号,一门心思想当官,我不是人啊!
我情绪一上来,我哥就把我给抱住了,他满眼含泪地对我说,兄弟,咱爸可就咱们俩,咱能让他失望吗?
我说,放心吧哥,这仇一定要报。
我妈坐一旁呆若木鸡,见我们哥俩要在镇长身上动真格的就说,问问那二十万块钱还要的回来不,那不是赃款,要是要不回来就算了吧。
那太便宜他了,我哥说,我们要弄死他。
我说,对,我们要让他死。
我哥的情绪感染着我,我说我明天就去找镇长。
第二天是星期一,这天上班的公务人员应该是齐的,可是,镇长办公室的门怎么也敲不开。有人告诉我,镇长下乡了,过几天才回来呢。我信以为真回来傻等。我不知道得等多少天,问我妈,她说鬼才知道呀!于是我决定不能傻等,又去敲镇长办公室的门,仍然敲不开。这时又有人过来告诉我,说镇长去市里开会了。我就想,这不明摆着躲我嘛,可是镇长没有躲避我的理由,除了我妈我哥没人知道我要找镇长索钱呀!
我苦恼极了,满肚子火撒不出去,浑身的劲使不出来,晚上跟我哥喝酒,满嘴都是狂妄话。
我说,哥呀,你给我一把菜刀,我到镇长家里找他去。
我哥说,不行啊兄弟,那等于送死呀!
我说,我不怕,我要给咱爸报仇。说着话敲碎了一个啤酒瓶,握住瓶颈朝自己的脖子上就划。我哥上前抱住了我胳膊,瓶碴儿在我的领口处乱抖。我大声地喊叫起来,你松开,别拦我,不能给爸报仇就让我去死吧!我哥抢过瓶碴儿,把我摁到床上。我躺下来,浑身像挨了荆条的无数遍抽打,一点动弹的劲头都没有了。我妈走进来,给我抹眼泪,只抹一下就控制不住自己,哭了。
我哽咽着说,妈……您别哭……
我一门心思想找到镇长,把什么都忽略了。我喜欢大自然,可是我的心情决定我必须放弃大自然的诗情画意。即使我推开窗子打量镇子的美丽布局时,眼里始终是丑陋的色调,根本看不出哪个地方有多美。比如山上遍布着金黄色的树叶,我看它们就像老女人脸上的牛皮癣。再比如我从电视里看到冰河开化的镜头,居然从中嗅出狐臭的味道。总之,人的心境不好,多美的事物也是丑的。
因为找不到镇长,我成了热锅上的蚂蚁,好像遭谋杀的不是镇长而是我。终于有一天,我哥兴奋地告诉我,是他亲眼所见,镇长住在贵宾楼里。贵宾楼是镇上相当级别的一幢建筑,不是一般人可以入住的,镇长住在那里应该没错。不仅如此,我哥还向我透露了镇长所住的准确房间:八楼,8028。
我哥问我,敢去吗?
我说,我就等着这个时刻呢,怎么不敢去!
我哥说,那你打算怎么下手?
我说,先找到8028,单刀直入跟他要钱,如果他拒绝,我就打发他上西天,要是他把钱如数给了,我就饶他一顿暴揍。
我哥沉吟片刻,说,万一他答应给钱,手头上没那么多咋办?
我立刻明白了我哥的意思,向镇长索钱不能给他喘息机会,一旦让他腾出手来,我不但拿不到钱,很有可能连小命都得搭进去。可是我不知道怎么办,就看着我哥等他明示。
我哥说,兄弟,咱爸的命二十万都没留住,难道他个镇长就可以留住吗?他比咱爸多条鸡巴还是多个脑袋!
我不太明白我哥的意思,依然用刚才那种眼神看着他。
算了,我哥一挥手潇洒地说 ,那二十万咱不要了,咱就要他的脑袋。这话好像说到了我的心坎上,我兴奋地附和说,对,就要他的脑袋。我哥这时提到一个人,那是一个留长辫子的女人,她叫欣。当时,我哥只是简单地介绍了欣的一些情况,然后问我,如果欣在场怎么办?endprint
我说,她一个小三,在跟前又能怎样?怕她什么呢!
我哥说,最好把她支走,别伤及无辜。
我说,那就让她离远点。
我哥长出一口气,点着头说,你去吧,回来我给你压惊。
第二天下起了大雾,各种声音掩埋在雾沼里,显得支离破碎、凌乱不堪。听着那些声音,我忧心忡忡地走进大雾里,每一步都像踩在梦里的棉花团上,眼前迷茫,脚下无根。老远看见贵宾楼顶琉璃瓦旁边,一块一块的雾团轻盈地浮起来,又滞重地落下去。我心里猛生了胆怯,就想万一我让公安给捉住,那要等到什么时候才能见到我妈呢?忽然想起我妈站在吊桥中央差点跳下去的情景,我浑身的血液又沸腾起来了。
4
我开始被保安拦住时显得很镇定。他们问我是干什么的?找人还是住宿?我说我到镇上办事来了,打算在这里住一宿。保安就让我办理住宿登记。我说我只住一宿不交押金行不行?保安说不行,五百元一分都不能少。我说我不住那么贵的。他们说我们这里都是高档房间。我就不再啰唆了。其实,我跟他们啰唆只是伪装一下而已。
我走进七楼一间向阳的房间。里面只摆一张标准床。红色地毯,银灰色墙壁,蓝色的壁灯挂在床头上方。我没觉得这个房间有多高级,就去了洗手間,在镜子前面观察自己脸上的气色,还用现成的卫生清洁剂喷了身上的衣服,然后就离开了房间。
我到了八楼,在走廊里现出找人的样子。我发现8028房的门并没有关严实,有一条线形缝隙若隐若现。我想里面肯定有人,礼貌地敲了两下。门自动敞开了,一股花粉的气息弥散过来,我眨巴眨巴眼睛就看见了欣。
后来我在南岸西岭的出租屋里,几次和欣谈到第一眼看见她时的感受,全都不是很准确。我说她像画家正在描绘的模特,但又不是那么机械呆板。我说她纯粹就是一张成功了的绘画儿,她反对说她缺乏画里的耐品气质。我说那你就是魅惑人的女妖,显然这又有失偏颇。当时我看到的情景是,欣坐在靠窗的一把圈椅里,手捏瓜子正嗑,好像在倾听谁的诉说,神态非常专注。她没穿长裤,一块乳白色的方巾遮住小腿以上的部位。没捏瓜子的那只手放在胸前,现出呵护态势。窄瘦的肩膀露出一双蓝色吊带,坠着下面的什么衣服就看不见了。我留意到她护胸的那只手旁边,有一条黑而粗长的辫子,像乌蛇一样闪着幽暗的磷光,辫梢在她平静的膝部也跟蛇信子差不多。我有一种被震慑的感觉,又不得不硬着头皮走进去。
我问,镇长在吗?
欣朝前探了一下身子,反问我,你就是小胡吧?
我心里一惊,说,你怎么知道我的名字?
欣冲我微微一笑没有说话。
我心里没底,惊慌地现出凶狠相问她,告诉我,你怎么知道我的名字?
你小声点,欣用商量的口吻说,从现在起听我的,好吗?
凭,凭什么听你的?我说。
先回到你的房间去。她说。
她居然知道我在这里订了房间!我狐疑地望着她,好半天没敢动地方。
听话,她平静又坚决的口气,回到你的房间去,什么都不要说。
我真的被她弄蒙了,乖乖地听了她的话,等我回到七楼推开房门,发现屋里坐着俩警察。其中一个问我,你是小胡?
我说,是。
另个又问,是不是退伍回来的那个小胡?
我说,是。
我说完这话就想撒腿开溜,可是我的身后又出现俩警察。光眼前这两个我还能对付,我军体拳打得不错,眨眼间又蹦出两个我就不自信了,不过我还是和他们理论起来。
我说,你们想干什么?
他们说,跟我们走一趟。
我说,跟你们干什么去?
他们说,别废话,到时候你就知道了。
说话间我被他们给铐上了。我不服,暗想,我是想杀人来着,可毕竟没形成事实,他们没根没据的怎么说铐就铐啊?我叫喊着,被他们拉拉扯扯地拖下楼。
楼外停了一辆警车,周围好像还有便衣。我被他们连拖带拽地上了车,一个二百多斤的胖子死死地压住我。我叫不出声来,只忙着喘气,心想,完蛋了!
我在那间只有一扇窗子的小屋里待了差不多有十天。开始并不清楚那里是什么地方,反正吃得还不错,就是每天没事干,想和送饭的聊聊天,他也不搭理我,不过凭感觉,这里的人好像对我没什么恶意。
最初几天我有些心烦,提出请求,让他们给我妈我哥送个信儿,就说我想他们了,让他们过来看看我。我的请求遭到拒绝。我又琢磨,我之所以待在这里,完全是那个留长辫子的女人捣的鬼,如果不是她设好圈套,我怎么会套得如此牢实!我就大声叫喊要那个女人出来见我,我有话问她。结果不用说也能猜出来,根本就没人理我这个茬儿。我心里诅咒他们,发誓出去后跟他们打官司。我的心思竟然被那里当官的猜透了,一天送饭的给我捎来一本法律书,让我闲着没事学习学习,搞不好将来还能用上呢。我看了几页没看进去,随手扔到床底下。后来几天心慢慢平静下来,替我爸报仇的想法竟然淡了。便想,就算我能走出这间屋子,也没办法弄死镇长了。我在心里跟我哥说,哥呀,等我出去你打我吧,谁叫我这么笨呢!我责怪着自己,心又觉得乱了,最好的解脱办法就是让床板把脑袋托稳,暗里数着数,然后就在不知不觉中死过去了。醒来才明白不是真死,因为我在死的过程中,出现许多花里胡哨的场面,非常动人,于是就想着再“死”一遍。其实我很少做梦,因为梦是现实的翻版,我从不把不可能的现实寄托到梦里去。这样的观点,决定我在那间小屋里漫无目的地等待下去。有一天,我似乎预感到是个晴朗的日子,我被一阵风轻轻唤醒,拉开小屋的门板,穿过幽长暗冷的走廊,向大门外跑去。来接我的不是我妈,也不是我哥,居然是那个留长辫子的女人——欣。
5
我的预感非常准确。
几天后,欣站到我的面前,她一句话也不说,把我从小屋里领出去,一直领到我哥的饭店,指着窗玻璃说,现在你自由了,还不好好谢我?endprint
我才不谢你呢,我蛮横地说,我感谢我的预感。
预感?她笑了笑,你还预感到了什么?
我说,我哥给我准备了酒菜,我妈正煮着面汤。
做梦去吧!她拉下脸来,将头扭向另侧。
我不明白她什么意思,用淫亵的目光斜视她那条長辫子,不怀好意地跟她说,你别走,回头我有话问你。我紧走几步上了台阶,忽然感到脚下打滑,原来台阶新铺了大理石。抬头看屋里,有人正刮墙上的底灰。有门隔着,我听不见里面的声音,只看见他们相互打着手势。是搞装修吗?我推开门大声喊,哥——哥——
没人应声。
我又喊,妈——你在吗?
也没听见我妈的声音。
屋里乱七八糟,几个干活的工人站在高处俯视我。我仰视他们问,你们看见我哥了吗?
几个人相互看看,一致地摇摇头。
我又问,你们没看见我哥?
有个人终于问,你谁呀?
我懒得搭理他们,赌气骂了句“傻帽”,就朝厨房走去。厨房的门上了锁,转身又向我住的房间走,里面放着我的牙具、军被和一本描写妓女的外国小说。可是那间包房门像死人咬住的牙齿,根本打不开。怎么回事?我找遍每个角落,满地的狼藉愈加使我忐忑起来。我返回大厅,不得不与几个干活的工人套近乎。
我说,师傅们辛苦了,你们不认识我吧?我是这里老板的亲弟弟,你们肯定认识这里的老板了?就是雇你们干活的那个人,知道了吧?
一个人俯视着我说,雇我们干活的是痔疮。
我不解地问,痔疮?痔疮是谁?
那人说,痔疮就是拉屎老流血的那个。
我说的不是他,我哥拉屎不流血的。我说。
那也是痔疮,我看见过,他每次拉屎都流血,医生让他把酒戒喽,他就是不听,所以一喝酒就拉屎,一拉屎就流血,医生说……
别他妈说了!我简直无法忍受这个人的顽固,大声地问,你不是这个镇子的人吧?
是不是咋的?想打架?
不想——我喊叫着,你快告诉我,这里的老板哪儿去了。
几个人都给吓住了,不管我怎么说都无动于衷。我只好暂时离开,到镇政府去找我妈。欣没等我出来就走了,她后来告诉我,她当时气坏了,本来是领我回来取行李,没想到我是那么混蛋透顶。
我来到计生站,那里的一位阿姨告诉我,说我妈跟我哥走了。我不明其意,让她说具体点。阿姨犹犹豫豫地,嘴里像含着什么东西,欲言又止。
我说,您就直说吧。
阿姨说,我们大家都感到奇怪,你妈她究竟是怎么了?
我说,我妈她怎么了?
唉——阿姨叹口气,怎么跟你说呢?他们说你妈是女人,你哥是男人,我就不信,女人心里除了男人,就没别的了吗?
我以为这位阿姨侮辱了我妈,就从窗台抓起一个花盆朝她砸过去,幸亏她躲闪及时,不然当场就得毙命。
6
十多年前的那个晚上,我们这个小镇迎来一个传统节日。天上飘气球,胡同里塞满人,墙皮的颜色都和人脸一个样,始终是瀑布般的声音一直持续到下半夜。我躺在路灯下,早就感受不到自己的存在了,我想我肯定死了,很难说这个世界再跟我发生联系。冥冥之中感到一丝痛痒,睁开眼睛,借着路灯的晕光发现了一只老鼠,它在我的脚踝部戏谑地撕咬着什么。我抽回那条腿,老鼠勇敢地追过来,脑袋不管不顾地朝我裤管里扎。我感到奇怪,腾地站了起来,从裤管里掉下一样东西。老鼠机敏地抓住,我听见它啃啮的声音,低头去瞧,原来是一块月饼。它是这个传统节日的唯一象征。我当时差点就哭了!我想这一定是个好心人,把我当成了乞丐,自己买的月饼省下来送给我吃,担心别人拿去,就捅进我的裤管里……
我在我妈单位摔了一个花盆后,又跑回我哥的饭店,疯狂地喊叫。我不相信那位阿姨的话,可是我确实见不到我哥和我妈了,他们去了哪里呢?谁告诉我?
那个外号叫痔疮的人正在喝酒,有人跟他耳语一阵,他就用一双脏套袖堵住我的嘴。几个粗壮的大汉把我当狗似的捆了起来,装进一辆面包车里,从镇子的西街开始,围着错落的建筑转了好几圈,最后把我扔在一堆垃圾旁。拆开绳子,冲我屁股踹一脚,我跪进垃圾堆里。车开走了,喷过来的尾气和垃圾的臭气搅成一团,我混在其中,像个没头苍蝇似的跌跌撞撞。我自认为是个有理想的青年,当我扎进垃圾堆里的那一刻,看见我的军被也让痔疮的人当成了垃圾扔进来,直觉得天塌下来了,七零八碎的星光砸进我脑袋,再从眼里蹦出来。我还能想什么?我还能做什么?
我当时的情况非常糟糕:我爸因为严重犯法让政府给毙了,我妈和我哥便不知去向,这是怎么回事呢?我想能帮我解开这个谜团的只有欣了,所以我决定去找她。当我要离开那路灯,脚下的老鼠居然咬住我的鞋后跟,现出恋恋不舍的样子。我说吃你的去吧,就轻巧地将它拨开了。
由于家丑不可外扬的原因,我们家的那些事我本不该多讲。可是为了这部书稿的完整性,至少别留有太多的遗憾,我必须将我所了解到的一些内容丰富进来。尽管这些内容完全是道听途说,满满的差不多都是水分,但它可以表明我当时的处境很恶劣,同时也让我明白了什么是人心。
有那么一段时间,我在农贸市场卖菜,几乎每天都能听到关于我们家的故事。那些日子正赶上一家老厂改制,百余名职工下岗待业,有大部分人到农贸市场讨生计。他们不会使秤,开始也不敢张嘴叫卖,却一肚子牢骚,满嘴反动话。就是这帮人把我们家的事演绎得有声有色,活灵活现,跟亲眼看见了似的。总之,我们家的那点事民间版本有多种,我将有代表性的版本抄录如下:
……那时候土地还没承包,镇政府食堂来个小丫头,岁数不大老想转正提干,就跟食堂管理员勾搭上了。那管理员家里有老婆孩子,等把那小丫头肚子弄大了,只好离婚娶了她。那时候离婚可不照现在说离就离,没有特殊情况是离不开的。要是按着那时的条款,那管理员就得开除公职回家种地去,可他愣是把婚给离了,还没碍着他走仕途。镇上的人差不多都认识他,从食堂出来当民政助理、财政所长,最后在副镇长的位子上栽的跟头,给崩啦!他儿子在他没死之前和他老婆就不干净。那小子听说长得挺标志,比他后妈没小几岁,借他爸的光当了天元大酒店老板。要是按古人所说,老夫少妻,早晚都是别人的。他年龄那么大了,那玩意能好使吗?女人年纪轻轻,受得住那份煎熬?他还有个小儿子,当兵回来就杀人,前两天电视里说的那个瘦高个,就是他小儿子,肯定也得死。唉,这家子人,没他妈一个好东西!endprint
我所听到的不仅这么多,还有一些是我妈和我哥的爱情细节,都是入不了耳目的淫秽话,恕我不能摘录。即使摘录部分,我最初听到时也差点给气死。谁愿意把自家的丑事抖落到大街上呢?何况那些丑事都是添枝加叶,甚至是凭空捏造的。不过我在很短的时间里,就敢于面对这些事情了,不管是哪個版本,统统在我脑子里过滤了一遍,当时我通过理性分析,是这样看待我们家的那些传闻的:
我爸确实当过镇政府食堂的管理员,我妈也是从那里开始的人生第一步。至于他们谁先“勾引”谁并不重要,关键是他们有了共同语言,顶着强大的压力,冲破传统世俗的困阻结合了,并且有了我。我当时的地位很惨,在民间的多种版本里,居然都是未婚先孕的不法胚子。听上去很不舒服,再细想也没什么大不了的。因为现在这种情况非常多,多数新娘都打过胎,或者挺着几个月的肚子步入新婚殿堂。与现在相比,我爸跟我妈只是有点超前而已,没什么大惊小怪的。是否可以这样理解,别看我当时是个胚芽,却是左右伦理道德的要命因子。为了尽快让我合法化,也是保住必要的颜面,我爸摆出破釜沉舟的态势,下决心离婚娶了我妈。至于他们后来的性生活是否和谐,这就不好说了。我当然希望他们的性生活和谐,可那是两个人的私事,自己不说外人不好打听。不过我想,我爸比我妈确实大好多,生理上不服老不行,不能因为要面子就说违心话。尤其是我后来跟欣学了解剖生理知识后,对民间的这种“性生活不和谐”说法,基本上持默认态度。但我并不因此默认别的,主要是对我妈的人格侮辱性言辞和臆测。我妈永远都是伟大的、纯洁的,不管我爸多么败类,我妈是任何人都不允许臆测和猜想的,她的伟大和荣光永远都在我——她儿子的心里。
我现在还记得讲述此版本的是个半大老头,曾在镇上的老厂当车间主任。他说他闺女在镇政府当过电话员,后来电话普及电话员一职被撤销,他闺女就去一家门市当主任了。我看那半大老头不像说假话的人,如果不是他后来提到我爸的小儿子,我差一点就信他了。我爸的小儿子就是我,我在他的讲述里却被政府判了刑,事实上,我正在他的身后忍无可忍地聆听他对此版本的炮制。不过我又想,尽管我没被叛刑,却实施了杀人计划,就算是捕风捉影,也不能说半大老头讲得没着一点边。实在让我无法忍受的,是他把我妈所谓的隐私当成笑料随处抖,可我无力也无心驳斥他。我当时的境况很差,更不愿意让人知道我跟他们讲述的主人公有瓜葛,所以我就接受了我被政府判刑的事实。既然正常秩序的人群里不再有我,我站出来证明什么只能是自取其辱。何况我妈跟我哥确实不知去向了。
以上就是我当时对民间给我们家制造的传闻所持的全部态度,可能有往自己脸上贴金之嫌,但我是诚实的。
下面继续说我和欣的故事。
7
街上行人散尽,各种声音也都平静下来。我夹着被子站到贵宾楼下,仰视高高的纽扣一样的楼窗。我知道,欣就住在里面。现在正是睡觉喷香的时辰,冒冒失失地往里闯行吗?一名保安靠近我,问我是不是找人?我说是。他说你要找的人不在这里,到别的地方找去吧。
我说,你知道我要找谁,就撵我走?保安说,让你走你就走,怎么不长记性呢,这么快就把上次的事给忘了?从这话里我听出点味道,夹起被卷快速地离开了。
我当时很像偷完情欲回阴间的野鬼,眼瞅到了鸡鸣时分,却找不到回去的路,心里起急都想哭。还别说,我腋下的军被此刻有了灵气,好像听见它跟我说,我是有过理想有过大抱负的青年,当兵时得过奖……如此一大堆的鼓励话,让我觉得自己还能活下来。
我之所以在南岸西岭那个地方租房子,是因为那里距菜市场比较近,而我的架子车又比较轴的缘故。我的房东告诉我,想干蔬菜生意得去外地批发,那里比本地便宜多了。可是我出不去,我的本钱有限。镇子西郊有几个蔬菜大棚也批发青菜,只是利润薄,没多少挣头。唯一的好处是可以赊账,却不赊给我,他们说我是生面孔,担心菜批出去肉包子打狗一去不回了。我回来求房东给我担保。房东开始不应,我嘴皮都要磨破了也不行,后来就跪下求他,说,我爸爸犯法给枪毙了,我妈跟我哥都下落不明,我现在没一个亲人了,您就是我的亲人,您要是不信我,看我的被褥,看我的牙具,那可都是部队发的,我是在大熔炉里锻炼过的人!
房东是个善良人,他把我拉起来,说,我瞅你也不像是骗人的主儿。
房东跟我去了西郊的蔬菜大棚,又帮我找了一台农用三轮车把青菜拉回来。我的屋里除了一张摆床的位置,余下的地面堆满了各种青菜,看着它们我肚子就感觉撑得慌,想装进架子车拉到市场遛一圈。房东说,先把青菜归置利索,该戳的戳起来,该盖的盖上,反正一天也卖不完。房东提醒得很及时。青菜属娇嫩之物,伤热就烂,着冷就冻,所以先学会保管青菜很有必要。我是生手,生手积累的每一点经验都要付出代价。我后来跟欣说了我那个时期的小委屈。她说,你都死过一回了,还在乎再活一次呀?可那些日子我真是要顶不住了,麻烦事一件跟着一件披到我头上:工商税务、市场管理、地痞流氓,他们都是冲着我的钱来的,有时候卖一天的菜都不够打发他们。加上我对青菜的保管缺乏经验,开始那段时间做的都是赔本买卖。房东倒是挺乐观,宽慰我说,别怕,卖完了我还给你赊去!
8
我以为我再也见不到欣了。有一天深夜,我居然在梦里的一个三岔路口发现了她。她的样子很特别,着装与这个季节形成极大的反差。都下过一场小雪了,她还是我在贵宾楼看见时的那身打扮。我问她你不冷吗?她像没听见似的不回头,只把她那长长的辫子甩了甩,然后向左手的那个胡同里拐去了。我拉起架子车就追,却怎么也拉不动,车轱辘跟钉住了似的……
我说过我从不把不可能的现实寄托到梦里去,我醒来后就想,既然梦里看见了她,第二天的青菜摊儿上会不会见到她呢?那一整天我都怀着极大的期盼徘徊在我的摊位周围,一会儿看东门,一会儿望南门,最后愚蠢地跟自己打赌,赌她从西门进来,否则,晚饭就不吃了。事实上我在离开市场的那一刻,沮丧地问自己,她没来,打赌还算数吗?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