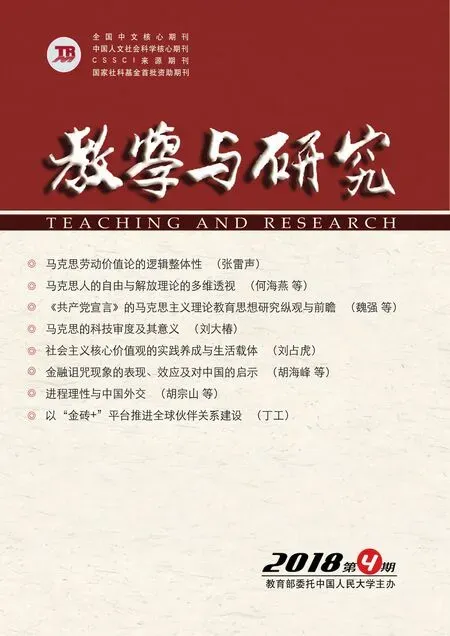唯物主义的内在逻辑:形而上学(后)现代性的超越之镜
——以马克思主义物质观的基本向度及其存在论意蕴的再揭示为视角*
2018-01-24
马克思主义物质观的确立,无疑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乃至现代西方哲学史上都具有里程碑的意义。但长期以来,由于对其基本向度及存在论意蕴的发掘和揭示还不够深入全面,不但影响到了人们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把握和运用,以及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身的发展和完善,而且更容易让人产生马克思主义哲学已经彻底摆脱了西方哲学论域的错觉,进而有将马克思主义哲学与西方哲学对立起来之虞。更有甚者,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在面对现当代西方哲学的重大理论现实问题时,始终处于一种失语的状态,进而将其贬斥为一种自然哲学、政治学或社会学。有鉴于此,我们有必要对马克思主义物质观的基本向度及其存在论意蕴展开全面而深入的发掘和揭示,还原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深奥内涵及其发展逻辑,回应现当代西方哲学特别是现代性与后现代性存在论之争的时代难题,凸显其批判性与革命性的实践本质,消弭人们之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误读,促进哲学社会科学的繁荣和发展。
一、马克思主义物质观的基本向度及其存在论意蕴的再揭示
众所周知,20世纪初,列宁在马克思恩格斯辩证唯物主义物质观的基础上,对物质概念作出了进一步概括:“物质是标志客观实在的哲学范畴,这种客观实在是人通过感觉感知的,它不依赖于我们的感觉而存在,为我们的感觉所复写、摄影、反映”。[1](P35)尽管这一概括言简意赅且几近家喻户晓,但至少从三个方面为我们进一步厘析新唯物主义与一切旧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之间,既纠缠不清又凿枘难入的一系列难题提供了科学的维度与视域。这些维度与视域的深入发掘,无论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科学性、革命性和实践性本质的进一步彰显,还是对于其存在论意蕴的深入揭示,都具有非常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一)物质与意识的关系维度及其存在论意蕴
列宁这一物质概念的提出,直接源于恩格斯对于“全部哲学,特别是近代哲学的重大问题是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的精准把握。其中,思维与存在(物质与意识)的关系维度,不但为列宁从客观实在性与感觉(思维)的关系维度来概括物质的哲学形态提供了首要的视角,而且为我们廓清形而上学意义上的意识及其与生活世界的存在论关系,掘明意识形态意义上的意识及其理论和现实上的根源提供了方法论。
对于形而上学与生活世界关系的探索,无疑是哲学研究中最为核心的议题,尽管人们对于它的理解见仁见智,但如若将其归结为一种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则无疑又是争议最少的,即如海德格尔所说:“形而上学就是一种超出存在者之外的追问,以求回过头来获得对于存在者之为存在者以及存在者整体的理解”。[2](P137)但事实上,人们在“追问”的过程中,却往往容易将形而上学的存在与生活世界的存在割裂开来,而使其表现为一种独立的抽象存在,这也正是马克思“反对一切形而上学”,[3](P159)将哲学研究转向“对象、现实、感性”的存在的真正根因所在。正是通过这一转向,不但扭转了本体论的研究方向,将人的现实存在及其感性活动纳入了本体论的范畴,而且还扭转了认识论和实践论的研究方向,将人的感性活动和现实需求纳入了认识论的范畴,将人之于真善美的追求、之于全面而自由的发展纳入了实践论的范畴。而这一转向的存在论基础,则正是将物质与意识的关系维度,进一步切身和具化为一种客观实在性与感性活动的关系。
另一方面,意识形态与上层建筑的存在关系,也是任何一种政治哲学必须予以澄清和构建的关系。按照马克思的观点,就意识形态表现为一种自在的存在、独立性的外观而言,它是虚假的,就意识形态与现实社会生活的必然关联而言,它又是真实的。[4](P10)这即表明,不同意识形态之间的相互对立,不仅有其“虚假性”的一面,而且还有其“真实性”的一面。具体而言,其虚假性表现为理论上的形形色色的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之争,其真实性则表现为现实生活中的不同党派之争,这也正是《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的主旨所在。随着1905—1907年的革命失败,布尔什维克党内的马赫主义者联合孟什维克党和社会民主党等党派,将批判的矛头直接指向了马克思的唯物主义,指认它不但是一种“真正的神秘主义”,而且不过是一种翻新了“二元论”。为此,列宁在将物质与意识的关系进一步明确为客观实在性与感觉的关系的基础上,将俄国马赫主义还原至贝克莱的唯心主义谱系,而揭穿了其通过对代表无产阶级利益的马克思主义的修正,来重构一种代表资产阶级利益的意识形态的真实企图,进而捍卫了马克思主义无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地位,扬显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独特的存在论蕴涵。
(二)人的主体性维度及其存在论意蕴
正如恩格斯所说:“在远古时代,人们还完全不知道自己身体的构造,并且受梦中景象的影响,于是就产生一种观念:他们的思维和感觉不是他们身体的活动,而是一种独特的、寓于这个身体之中而在人死亡时就离开身体的灵魂的活动”。[5](P277)这是蒙昧时代的人们关于感觉意识的一种外在性理解。近代以降,在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和启蒙运动的推动下,人的自我意识不断为各种哲学思潮所聚焦,并开启了近代西方哲学的认识论转向,即意识到“我们”已经自觉不自觉地参与到了认识活动之中,或者说我们的认识过程中有“主观性”参与其中。这即意味着,列宁关于物质的客观实在性与我们的感觉之间“复写、摄影、反映”的内在关系问题,在其本质上是一个关于我们的感觉的功能和界限的问题。
而这在马克思主义看来,首先,正如“意识是人脑的机能”一样,我们的感觉也是我们的身体的一种机能。正是通过这种机能,使我们在实践活动的过程中不断地获得了关于外部世界及我们自身的认知,进而不断地形成了系统化、理论化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为我们进一步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实现真理性认知与价值性认知提供统一的尺度。其次,也正是在这一过程中,我们不断地建构起和意识到了感觉的主体性功能及其有效性结构。由于这种主体性“是对象性的本质力量的主体性,因而这些本质力量的活动也必须是对象性的活动”。[6](P167)因此,这种主体性功能正如马克思在批判费尔巴哈时所提出的“能动性”,其有效性结构正如马克思在批判黑格尔时所提出的“受动性与能动性的统一”。最后,这种作为感觉与客观实在性关系意义上的受动性与能动性的关系,在其发生现象学的意义上,则进一步表现为一种源于身体与物质的感觉活动,基于逻辑与历史相统一的辩证关系,趋于一种人的全面而自由发展的唯物主义历史观。这样一来,不但肯定了人的主体性的存在与地位,而且厘定了其在认识和实践活动中的作用与限度。
正是将这种基于能受一体意义上的人的主体性维度注入了历史唯物主义,使我们对于物质概念的理解和把握不断地从抽象走向具体,对于世界的物质同一性原理,以及唯物史观的内在逻辑与基本架构,不断地具有了一种切身性的参与和领悟。与此同时,也正在这种参与和领悟的过程中,不断扬显了马克思主义物质观将生活世界的全部纳入其中的存在论意蕴。这无论对于“认识你自己”的历史之谜的真正解答,对于“开启人性之蒙”的启蒙承诺的兑现,还是对于马克思主义人本逻辑与科学逻辑这一双重结构的理解,对于以人民为中心这一新时代思想的价值意蕴的掘发,都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三)辩证法的实践维度及其存在论意蕴
正是基于客观实在性与感觉关系之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存在论意蕴,以及人的主体性在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过程中之于历史唯物主义的存在论意义,列宁进一步揭明了认识活动“从生动的直观到抽象的思维,并从抽象的思维到实践”的辩证性,及其从“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无限反复与发展的过程性。而在这里,无论是这种基于物质与意识关系维度以及人的主体性维度之上的存在论,还是这种认识活动的辩证性与过程性,归根结底又统一于实践活动,正是在这种统一中,辩证法的丰富内涵才不断得以体现。
一是统一和体现于认识的总路线之中,即认识不但源于实践,其结果必须接受实践的检验,而且认识的发展必须依靠实践,这在表明认识与实践之间一体两面且须臾不离的存在属性和辩证关系的同时,无不体现了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实践内涵及其历史唯物主义向度。二是统一和体现于认识的本质之中,即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和实践的基础上主体对于客体的能动反映。这一方面表明,马克思主义反映论是一种作为认识活动的主观辩证法对于客观世界和实践活动的辩证法的反映论,即“历史从哪里开始,逻辑就从哪里开始,历史是如何发展的,逻辑也是如何发展的”;另一方面表明,这种反映又是受到历史条件和实践活动的制约,即“历史发展到哪里,逻辑也发展到哪里”。可见,不仅这种能动的反映活动与实践活动之间是一种密不可分的辩证存在关系,而且辩证法、认识论、唯物论、历史观与实践论之间亦是一种统一的存在关系。三是统一和体现于真理的相对性与绝对性之中,即无论是作为一种互为前提的辩证存在关系的真理的相对性与绝对性,还是作为这种相对与绝对关系的根源的思维的至上性与非至上性,其前提和根源在现实性上,又都是以实践活动为基础。四是统一和体现于认识的目标之中,即首先,真理性目标与价值性目标互为前提,而这种互为前提的前提又是以实践活动为前提。其次,真理性目标与价值性目标的统一又必须以伦理性目标为旨归,即统一于人类命运共同体意义上的人、自然、社会的和谐共处,而这种统一亦必须以实践活动为前提。这不但体现了实践活动的伦理学向度,亦即体现了辩证法的全部内涵与视域:社会辩证法、实践辩证法、思维辩证法、历史辩证法和自然辩证法的统一。
由此可见,马克思主义辩证法不仅是一种关涉认识活动与实践活动的辩证法,而且更是一种基于真善美整体意义上的关涉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辩证法,它为我们克服形而上学的知性思维,走出一切观念论的形式逻辑,悬置一切旧唯物主义的直观范式,批判欧洲中心主义和沙文主义,都具有积极的理论和现实指导意义。与此同时,马克思主义物质观的基本向度及其存在论意蕴的再揭示,无论对于唯物主义内在发展逻辑的进一步还原和展现,还是对于仍然困扰于现代性与后现代性存在论之争的现当代西方哲学,亦将提供一种有益的借鉴和尝试。
二、马克思主义物质观之于唯物主义内在发展逻辑的再揭示
按照哲学史的划分,唯物主义大体经历了三个阶段:古代素朴唯物主义、近代形而上学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如若将它们之间交互批判与超越的关系置于马克思主义物质观的基本维度与视域,即将“猴体解剖”置于“人体解剖”的维度与视域,则无疑为我们进一步打开和再现唯物主义内在发展逻辑提供最为有效的“钥匙”。
(一)古代朴素唯物主义的物质观及其限度
依据西方哲学的传统,人类对于世界的唯物主义认识肇端于早期希腊的自然哲学阶段。作为古代素朴唯物主义的早期代表,这些自然哲学家不但认为整个世界是由一种或几种自然元素构成,而且还认为这些自然元素之间是一种相互作用和转化的关系,即“万物兼在流动着、变化着、不断产生和灭亡的过程之中”。[7](P19)如在赫拉克利特那里,“这个世界对任何东西都是同一的……它过去、现在和将来永远是一团永恒的活火,并在一定的分寸上燃烧和熄灭”。[8](P49a,30)通过转化,“每一事物都变幻成火,火也变换成每一事物”。[8](P49a,90)在对事物的认识和领悟上更推崇理性,认为无知者的眼睛和耳朵有时又是“坏的见证”。[8](P118)而对社会秩序的维护则要求人们必须依赖于法律,因为“一切人间的法律都受到一条神的法律的滋养”,[8](P107)而“神是日又是夜,是夏又是冬,是战又是和,是不多又是多余”。[9](P25)这就导致在伦理观上重上帝而次人类,认为一个人只有从他对世界的神圣秩序的信赖中产生的满足,才是最高的善。[10](P50)
针对巴门尼德对于以赫拉克利特为代表的早期朴素唯物主义的攻击,德谟克利特采取折中的方式,将唯物主义推向了一种介于自然元素和抽象存在之间的原子论。但与巴门尼德不同,德氏宣称非存在就等于存在,充实和空虚是一切事物的基本成分。其中,充实又被分成无数粒子,它们非常微小以致于难易被感知;它们自身不可分割,但相互之间又被虚空所分割;它们完全充满了自己的空间,因而被称作原子或密集体;它们既无生成也不会消灭,在基质上完全是同质的,只能从形状和大小上来区分;它们不会发生质变,只会发生位置和数量的变化,因此,事物的一切性质取决于原子的形状、大小、位置和排列。重量、密度和硬度等诸如此类的性质属于事物本身所固有,感觉的性质只表示事物作用于知觉主体的方式。[8](P116-156)由于原子之间在数量和大小上的区别,始终处于一种排斥与聚集的运动状态,进而形成分离的、孤立的原子复合物和诸世界。而社会生活进步的动力主要源自于人的需要,但对于善的认识的需要会高于官能的刺激的需要,灵魂的安宁、精神的和谐也会高于身体的欢乐或痛苦。[8](P264)
综上所述,在以自然元素和原子论为代表的古代朴素唯物主义那里,物质与意识的关系维度已经进入了人们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视域,只不过表现为一种在感性和理性割裂情况下的推论和猜测,整体上在科学性和抽象性等方面尤显不足。如在本体论上将整个世界想象和推测为一种自然元素生成衰灭的过程和结构,在认识论上体现为一种直观式的反映和想象式的推理,在实践论上体现为一种真理尺度与价值尺度的分离,在社会历史观上体现为一种蒙昧的“二元论”。其次,人的主体性维度还完全被排除在本体论和历史观之外,在认识论和实践论等方面也仅仅体现为一种受动性,在世界的物质统一性确证上仍然局限于用自然元素及其结合方式来解释世界的存在,也即遵循的是一种自然主体性原则。最后,辩证法在这一时期已经广泛使用,正如恩格斯所说:“古代希腊的哲学家都是天生的、自发的辩证论者”。[7](P19)只不过囿于范自然主义和循环论的预设,还没有与实践活动结合起来,从而使得人、自然与社会的关系完全遵循的是一种自然法则。
(二)形而上学唯物主义的物质观及其限度
近代以降,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确立及其之于自然科学的倚重,朴素唯物主义直观和想象(推理)意义上的原子及其结构得到了科学证实,物质世界的运行规律也得到了牛顿力学的揭示。近代科学的这种求真实证精神不但使得古代自然哲学的解释力受到了挑战,神学世界的存在论基础变得岌岌可危,“警惕形而上学”成为一切科学行动的导言,而且使得感觉经验及想象推理被实验科学及数理分析所取代,感性与理性之间的“断裂”重新得到了弥合,世界统一性的元素结合论转向了机械因果论。
而就人们对于世界的唯物主义理解而言,一旦用自然科学意义上的物质概念取代哲学意义上的物质观,就不可避免地滑向了形而上学唯物主义。在牛顿那里,整个世界首先被想象为一架机器,上帝被设想为这架机器的设计师和第一推动者,其他的一切存在物则被设定为这架机器的零件,并且都按照力学规律在运行。开普勒则把太阳光想象为一种牵引行星围绕太阳的向心力,把人的感觉想象为一种由外物刺激感官而推动神经和心灵的机械运动。伽利略和玻伊尔则干脆把感觉接受外物的性质称为一种物质意义上的“第二性的质”。爱尔维修和拉美特利则把人的精神活动归结为人的感觉活动,把人的感觉活动归结为机械活动,最终得出了“人是机器”、“心灵是物质”的机械唯物主义结论。霍布斯则把整个世界分为自然物体和人工物体,前者属于自然哲学研究的范畴,后者(包括社会中的伦理学和政治学)属于公民哲学研究的范畴。[11](P386)费尔巴哈则进一步提出,“上帝的本质就是人的本质”,而人本学的对象就是以自然的第一性为前提的整个自然界,因此任何存在(包括世界、社会、人、现实感性等)都属于自然的客体。但在“思维与存在的统一”关系中,“只有将人理解为这个统一的基础和主体时,才有意义,才是真理”。[12](P181)这样一来,人就变成了理性的尺度,但却“仅仅把理论的活动看做是真正人的活动”。[13](P499)此外,近代哲学在继承古代和中世纪哲学追求纯粹智慧及其思辨精神的同时,也发扬了以谋求经世致用智慧为目的的实践精神,但仅以改造和控制自然的科学主义为圭臬来改造社会、人性乃至整个生活世界。
职是之故,相对于古代朴素唯物主义,近代唯物主义借助自然科学的成就,无论在本体论和认识论还是实践论等方面都取得了极大的突破,但囿于自然主义、实证主义和机械因果论,总体上表现为一种片面化、实证化的形而上学特质。首先,就物质与思维的关系维度而言,在本体论上体现为一种范自然主义与机械因果式的结构体系,在认识论上体现为一种自然客体与科学思维、客观存在与直观反映的关系,在实践论上体现为一种科学实证和功利主义的关系,在社会历史观和伦理道德方面,完全遵循的是一种机械因果论意义上的自然法则。其次,就人的主体性维度而言,已经直观到了人的主体性在本体论和认识论上的地位和作用,但总体上体现为一种机械因果论前提下的科学思维活动,因此,还仅仅表现为一种机械(受动)的自然主体和思维主体。在实践观上已经凸显出了人的功利性的价值诉求及其求真务实的科学精神,但囿于将“人是目的”的启蒙原则误读为人类中心主义,将“自然法则”演绎为丛林法则,而造成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断裂,导致人与自然关系的紧张。就辩证法而言,基于自然主义和机械因果论的双重前提,及近代哲学对于科学精神和功利主义的推崇,而将辩证思维片面化为科学思维,将实践活动片面化为科学活动,最终导致实践活动的多元向度与丰富内涵无法从本体论、认识论和社会历史观等方面真正进入辩证法的视域,或者说辩证法的真正意蕴与内涵在这种形而上学的范式内还无法得以充分体现。
(三)辩证唯物主义物质观的当代形态
正是在与一切旧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斗争过程中,马克思主义的物质观——辩证唯物主义——才不断得以确立,但一种理论的生命力还必须体现在,与现当代各种哲学思潮的斗争中不断丰富和发展自身,辩证唯物主义更是如此。
首先,部分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将辩证唯物主义解读为人本主义,夸大唯物辩证法的“主体性向度”,将辩证法限定在社会实践领域,而否定其自然向度。如卢卡奇认为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仅限于社会历史领域,如果将其扩展至自然界,则就又退回到了黑格尔的哲学体系。列菲伏尔主张将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看作是一种主客体关系,如果要将自然的维度纳入其中,则就消解了辩证法的革命性。萨特甚至断言,辩证法不是别的,就是实践,就是人的活动的逻辑,如果将其人为地外推至自然界,则会将辩证法置于一种先验的逻辑之中,最终陷入一种新的神学。霍克海默和阿多诺都反对将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本体论化,马尔库塞将辩证法直接等同于历史方法,阿尔都塞也只在社会学的意义上来理解和运用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奥热甚至在其超级人类学导论中,在过剩的意义上否定了此时此地的真实性,而仅仅承认“使我们产生认同感和依赖感”的意义生成之地,即精神产生之所。[14](P29-37)
其次,部分科学主义者将辩证法的辩证矛盾直接理解为逻辑矛盾,责难辩证法就是为“不相容者”辩护,最终“使其信仰者疏远于科学思维”而趋向相对主义。如波普尔指出,由于辩证法一味地强调矛盾的合理性,取消一切是非界限,而终将自身导向了诡辩论。如果一味地采取“接受矛盾”而非“改变矛盾”的态度,那么矛盾对我们而言将变得毫无意义。[15](P456)邦格则将辩证法的矛盾观抽象为“对于具体客体的每一性质都有一个反性质”的命题,如推和拉的关系等。但通过举例分析后他又指出,“并不是每一个性质都有这种反性质”,如质量等,因此而否定了辩证法的矛盾普遍性,进而将本体论层面上的矛盾的辩证性和普遍性降次为形式上的单一性和特殊性,最终否定了“形式逻辑是辩证法的特殊情况”的事实而从方法论上倒向了形而上学。[16](P61-63)事实上,上述两种用形式逻辑考量辩证逻辑的观点并非个案,而是1950年代以来在西方特别是英美哲学界占据统治地位的观点,这不但影响了现代科学思维的丰富与发展,而且影响了辩证思维系统的丰富与发展,如利波维茨基就在其“超级现代性”的理论中,就取消了矛盾的对立面,而将其描述为一种无限的、无原则的同一性。[17](P46)
最后,在物质与意识的关系维度方面,一是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消费社会的兴盛,如巴塔耶、鲍德里亚等后现代主义就主张用符号生产取代物品生产,用交换价值取代使用价值,用符号政治经济学批判取代政治经济学批判,用象征交换与死亡来代替历史唯物主义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二是随着后现代主义对于现代性批判的深入,如德里达、福柯、德勒兹等将辩证唯物主义溯源于基础主义而予以解构。三是随着对于技术现代性及其技术伦理批判的深化,如约纳斯在责任伦理观的基础上,将马克思主义物质观看作是一切专制主义与不平等的意识形态根源。四是随着信息时代的来临和信息科学范式之于各个领域的渗透,新时代的信息哲学在承认世界的物质统一性的同时,又揭示出信息所具有的不同于物质的独特存在方式和性质,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世界的物质和信息二重化存在的观点。五是随着量子力学的发展及其纠缠理论的猜想,对辩证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提出了质疑。
马克思主义物质观正是在迎接和回应新的质疑与挑战的过程中,结合新时代的理论和实践,特别是现当代自然科学的最新发展成果,展现出了更加丰富的内涵与形态。在物质与意识关系的本体论上,一方面,它只承认自然的“优先性”,并立足辩证唯物主义的视域,不但将其进一步具化为一种基于客观实在的感性活动之上的对象性存在关系,具体指向人、自然、社会、历史等全部存在要素之间的对象性关系;而且将其进一步具化为一种人本逻辑意义上的生活世界与形而上学的关系,以及科学逻辑意义上的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另一方面,它不但将现代人文社会科学的最新发展成果,如符号消费、解构主义和责任伦理等思想纳入了意识形态的范畴,而且将现代自然科学的最新发展成果,如信息、量子等存在形态纳入了物质的范畴,从而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物质观的物质与意识的关系维度。在认识论和实践论上,遵循的是一种客观规律性与主观能动相统一的原则,充分肯定了认识活动在实践活动中的积极作用。在历史观和伦理学上,遵循的是一种人本逻辑与科学逻辑双向互动的原则,充分肯定了逻辑思维在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的重要意义。在人的主体性维度上,在肯定人在认识活动和实践活动中主体性地位和作用的同时,充分认识到了其受动性的一面及其之于人的主体性的存在论意蕴,因而建构起了一种人、自然、社会、历史之间的交互主体性的关系视域,并体现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的“五大发展理念”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倡导与建构之中。在辩证法的实践维度上,将人、自然、社会和历史等存在全部纳入了辩证法的范畴,不但肯定了自然规律之于社会规律、历史规律和人的活动规律的基础地位,以及自然辩证法是社会辩证法和实践辩证法的基础,而且明确了实践辩证法、社会辩证法和自然辩证法之间的相互关联与互补关系,将它们共同视作唯物辩证法的组成部分和应有之义,进而不断确证和深化了辩证唯物主义、实践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高度统一的时代意义。
三、马克思主义物质观之于形而上学(后)现代性存在之基的超越
“人的重新发现及其主体地位的确立”无疑体现了现代性的根本特质。与此相应,“人是什么”及“人的主体性观念”也就分别构成了现代性的主题和根基。而按照西方哲学的传统,作为现代性存在之基的“主体性原则”,其合理性必须是由“形而上学”来提供。而当这种形而上学将“理性”确立为主体性的本质后,现代性的自我确证问题就还原为“理性”形上能力的论证问题。正是围绕这一主题,基于“理性内涵”的多维阐发,形成了多元纷呈的“主体性思想谱系”,从而使得形而上学主体性及其理性范式的“争论”,始终成为现代性与后现代性交互批判与超越的核心议题。
一方面,就主体性的意识与身体理性范式的思想而言,从笛卡尔“我思故我在”的意识理性主体的推出,到康德“理性为自然和道德立法”的形上能力的确证,揭明了现代性的理性主体世俗化、意识化本质。为了克服理性主体的二元论困境,黑格尔将主体性形上至“绝对精神”,并在意识理性范式内实现了“主体即实体”的同一。基于对理性主体“实体化”、“实证化”危机的反思,胡塞尔将主体性的存在之基回溯至“生活世界”,在意识理性范式内将主体性推扩至交互主体性,推动了主体性的现象学运动。然而,以施莱格尔兄弟、诺瓦利斯为首的德国浪漫主义,却以诗化“反讽”的方式对理性的意识化展开了首轮批判,并被追溯为后现代主义的先驱。之后,克尔凯郭尔、尼采、海德格尔、萨特、梅洛·庞蒂等存在主义思想家通过对生命主体的强力意志、生存伦理、身体意识等理性内涵的发掘与推扩,在形而上学主体性的理性范式内掀起了一股身体理性取代意识理性的后现代主义思潮。而以霍克海默、阿多诺等为代表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基于“启蒙辩证法”的反思和“否定辩证法”的创构,揭明了传统形而上学二元范式的辩证本质,开启了现代形而上学主体性的二元理性范式批判与拯救的第三条道路。
另一方面,就主体性的语言与交往理性范式的思想而言,以维特根斯坦、伽达默尔、阿佩尔、罗蒂等为代表的德美哲学家,通过对20世纪语言学转向中语言理性范式的解释学反思,指出真理并非取决于语言结构,而是取决于交往共同体在不断实践、对话、适用等语境中的交往理性,而形成了一股主张多元主体的后现代主义思潮。而法国思想家如福柯、德里达、利奥塔、鲍德里亚等,则通过对结构主义主体性哲学的逻各斯中心主义、语音中心主义、符号主义等形而上学传统的解构,形成了另一股无主体性的、碎片化的后现代主义思潮,并以此来终结现代性。法兰克福学派另辟蹊径,在与实用主义的交汇融合,及与解释学、后结构主义的交锋中,开启了现代性的“后形而上学”向度,彰显了实践哲学的学术价值与现实意义。哈贝马斯以“形而上学之争”为切入点,从普遍语用学的视角论证与建构了“交往理性”和“后形而上学思想”,重新把现代性确认为“一种未完成的计划”。韦尔默在辩证调和现代性与形而上学内在张力的基础上,形成了其精致的伦理对话模式和独特的民主文化观念,极大地丰富了“后形而上学现代性”的实践理性内涵及语用学转向的规范内核。
通过对现代性语境中主体性思想的谱系学梳理,再现了形而上学主体性的丰富内涵及其理性范式的多元向度,为我们进一步理解和把握现代性的精神实质及其发展路向提供了线索和场域。但是,囿于(后)现代性诸思想流派对于主体性及其理性范式在理解与确证上的传统形而上学视域,又使其陷入了相互扞格、凿枘难入的囹圄。就这种传统形而上学而言,囿于其在存在论上将起源和有效性、概念和概念物、同一性与非同一性等基本范畴的割裂或同质,而导致其在方法论上的片面化、实体化的偏执与同一。因此,要消弭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的存在论之争,不但要厘清不同主体性思想及其理性范式之间的内在关联,还要通过形而上学的批判与拯救来重构现代性的主体性原则。
而按照马克思主义的物质观来看,不同主体性原则及其理性范式一定是在人类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实践活动过程中,主体意识的不断觉醒和生成及其行为方式的规范和自觉。而无论是人的主体意识还是其行为方式,又是历史性地生产和自觉的,是与人类社会的生产方式直接相关联的,它不但关系着主体性的外延与内涵,而且还关系着与其直接对应的理性范式。反之亦然,主体性的外延内涵及与其直接对应的理性范式,又反映着不同的生产方式。而就主体性的外延而言,最理想的边界是与自然和谐共处的全人类,就其内涵而言,最理想的结构是人的身心一体基础之上的各种潜能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反映在其理性范式上则具体指向人的意识、身体、语言、道德、艺术、伦理等方面的合理建构与规范。而如上所述,其合理建构与规范的前提是生产方式的不断发展与完善。这种发展与完善的最理想形态则是体现人自由而全面发展的生产方式的无限逼近与建构,即“彻底的人道主义”与“彻底的自然主义”的统一,也即“彻底的共产主义”。这种无限逼近与建构,不但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物质观的基本向度(物质与意识的关系维度、人的主体性维度、辩证法的实践维度)及其基本视域(实践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而且体现了形而上学的起源(现有的生产生活方式)和有效性(实践活动中主体性的不断生成及生产方式的辩证运动)的基本向度及其基本视域(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终极关怀)。
这样一来,马克思主义物质观的存在论意蕴与形而上学(为了区别于传统和现代形而上学,姑且称之为后形而上学)之间,不但在其形式上是同构的、内容上是同质的,而且在其运行方式和价值取向上也是一致的。马克思主义物质观的基本向度及其视域与(后)现代性的存在论基础之间,不但是一种知性与理性、抽象与具体、逻辑与历史相一致的存在关系,而且是一种互动、互补与互构的存在关系。概言之,马克思主义物质观的基本维度及其存在论意蕴为(后)现代性的存在论基础提供了基本架构与视域,(后)现代性的主体性原则及其思想谱系丰富和深化了马克思主义物质观的基本维度与视域,进而丰富和深化了马克思主义物质观的存在论意蕴。
参考文献:
[1] 列宁专题文集·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2] 海德格尔. 路标[M]. 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
[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 第2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
[4] 吴晓明, 陈立新.马克思主义本体论研究[M]. 北京: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
[5]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M]. 第4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6]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 第42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7] 恩格斯. 反杜林论[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
[8] H. Diels. Die Fragment der Vorsokratiker[M]. Berlin: Weidmann Verlag, 1912.
[9] 北京大学哲学系外国哲学史教研室编译. 古希腊罗马哲学[M]. 北京: 三联书店,1957.
[10] 策勒尔. 古希腊哲学史纲[M]. 翁绍军译. 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11.
[11] 北京大学哲学系外国哲学史教研室编. 西方哲学原著选读[M]. 上册. 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
[12] 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集[M]. 上卷. 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
[13]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M]. 第1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14] Augé, M. Non-places:Introduction to an Anthropology of Supermodernity[M]. London: Verso,1995.
[15] 波普尔. 辩证法是什么?[A].猜想与反驳[C].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6.
[16] 邦格. 辩证法批判[A].科学唯物主义[C].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9.
[17] 利波维茨基. 超级现代时间[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