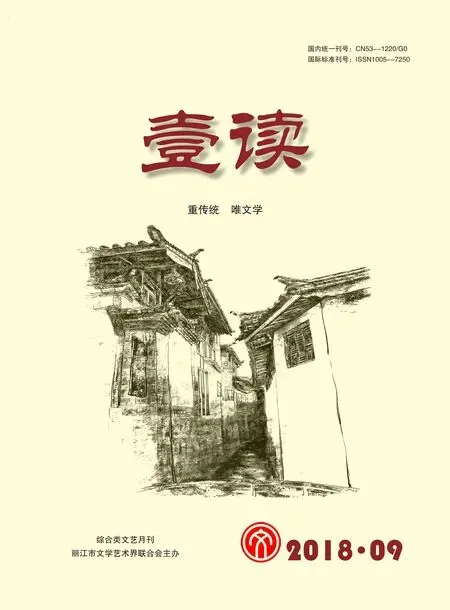沙玛大哥
2018-01-24芭纳木
芭纳木
在二零零三年的那个暑假,曾经有过一段难忘的经历,里面有一个我一生都难以忘怀的彝族大哥。
那时我还在宁蒗县城当老师,有幸参与县里的一个调研项目去牦牛坪,是平生第一次去到一个人口多又纯粹的彝族聚居区。同行的四位男同事也都是彝族,他们做彝族毕摩文化方面的调研工作,我负责拍摄图片资料。现在他们个个都成了彝文化专家,我则成为了一个老文艺青年。这并不妨碍我们变成了一生的挚友,因为我们都是追求纯净灵魂的人,和深爱着自己民族文化的人。
牦牛坪是宁蒗县城东边高山上的一个平坝,海拔高,气候冷,土地多产量少,那时只有洋芋、荞麦、燕麦和蔓菁。那里的洋芋是我吃过的最好吃的洋芋,沙沙的,甜甜的,是老天赐给那块美丽却曾经贫瘠的土地最好的礼物。初到那里,放眼望去,视野开阔辽远,广袤的土地上,荞麦花和洋芋花美得无法形容。山坡上绿草茵茵,点缀着星星点点的牛和绵羊,牦牛们在这个季节则进入了更高的山里。迎面而来的风带来了周边森林的香气,花的香气,还有泥土和青草的香气,令我兴奋不已。我从小都是这样的一个人,只要有美景,就会立马爱上这个地方,不管吃住的条件怎样。我很庆幸,现在依然如此。
第一个晚上,村委会杀了头一百多斤的猪做成坨坨肉招待我们,这是彝族比较高的接待礼仪了。记忆中吃饭的人很多,大家都很热情,风景又好,村委会的房子也不错,在那里睡得很好。第二天一早,我是在几个男同事亢奋夸张的洗漱声和高声谈笑中醒来的。起床去洗漱时,一位四十多岁身形魁梧,长相憨厚的彝族大哥慌忙过来帮我打水。我笑着对他说我会打井水不用帮忙,但他还是帮我打了水,并解释这不是井是地窖。我那时还想着井和地窖不都一样,把水桶放下去打水提上来不就可以了。后来喝过了水才知道,井水和地窖水区别可大了。早餐时,见到这位大哥在厨房里给我们做苦荞粑粑和煮茶,我才知道他是村委会请来的炊事员。因为成年人不可以让比自己还大的人伺候你,我马上就过去帮他准备早餐。他很客气,觉得你是县里来的专家,不能让你帮忙,我却执意要帮。这样,我知道了他的彝族姓是沙玛,我就叫他沙玛大哥了。他的汉语还可以,他和我的男同事之间用彝语交流时,简单的我也能听懂,同为彝语支的摩梭语和彝语很多单词是一样的,半听半猜就好了。
苦荞粑粑我从小就很爱吃,那地窖水煮出来的茶就难以下咽了。颜色浑浊不说,还苦,涩。“从没喝过这么难喝的水。”我在那里叫嚷。沙玛大哥笑着不语,那几个男同事就数落我了。说牦牛坪自古缺水,现在还是政府帮忙修了水窖,下雨时把雨水存起来,一年才有水喝。“哦。但是周围都是森林,植被那么好,应该有山泉水,怎么不把山泉水引到村里呢?”我又问。他们告诉我,离这里最近的一眼山泉来回要走七八公里,而且方圆几十公里只有那一眼泉水。我心想完了,这一周我就只能喝这苦涩的地窖水了。想到这里,我的记忆突然就被打开了。在我很小的时候,曾经当过解放军的爸爸,经常会讲他以前参加剿匪的故事,其中有一段就发生在牦牛坪。一九五九年,当时编号为三六七八部队的解放军在牦牛坪剿匪,土匪一直占据了那里唯一的一眼泉水。有一次他的两个战友趁天黑去取水,结果被躲在林子里的土匪开枪打死了一个,另一个跑了回来才得以幸存。后来经过长期争战,才夺得这一眼泉水。如果这地方真的只有一个泉眼的话,那就应该是这一眼泉水啊!我开始兴奋起来。另外,我的小姨也曾绘声绘色的跟我讲过,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县文工团会去牦牛坪慰问演出,她当时是团里的舞蹈演员。每次去,那里的彝族姑娘们会提前一天,来回走十几公里路,把文工团喝的、洗漱的水背好等着。那时我就会想,该是多淳朴多善良的人们,才会用这样的方式来欢迎给他们送去精神食粮的人?在那样一个缺吃少穿的年代里,还能有如此美好的心灵。那这些可爱的人们应该是我周围的这些人了!我立马激动地给男同事们讲了这两段故事。他们跟我开玩笑说我现在是他们的敌人了,因为我是解放军的女儿,他们是土匪的后代。我就跟他们嬉皮笑脸:“好吧,敌人就敌人咯,反正还不是从此要一锅吃饭,有本事就不要跟我一起吃!”一整个早上,我们就在那里贫嘴,憨憨的沙玛大哥就在那里看着我们笑。从那时,我就隐隐感觉到他身上有一丝孤独和苦楚,我甚至于在想他是不是孤身一人,所以才会这么享受地看着我们说笑打趣,所以一个大男人才会来村委会做饭。当然关于这个猜想,后来的答案是否定的。
那天傍晚,当我们回到村委会时,沙玛大哥已经煮好一大锅鸡肉和一大锅米饭等着我们了。那是高山的彝家养了两年以上的大肥母鸡,又香又油,那漂在鸡汤上的金灿灿的油,至今还清晰地浮现在我眼前,现在已经很少能吃到那样的鸡肉了。虽然我现在回老家也能吃到正宗的土鸡肉,但我们坝区和高寒山区的鸡肉真是没法比的。沙玛大哥给我们摆好碗筷就到门外抽烟,无论我怎么叫他他都不进来和我们吃饭。那几个男同事跟我说不用喊了,他可能是客气,也有可能村委会主任要求他不要和我们同吃。我一下子觉得不舒服了,都什么年代了还讲阶级,人又不多,才六个人,一起吃不就好了,但在人家的地盘上我也不好安排。于是我拿了个大碗,夹出最软和的几块留给他。因为不能让比你大的人吃你的剩饭剩菜,还因为我早上见到他笑时,一整口牙没剩几颗了。鸡腿也留了一个给他,因为在摩梭家里,鸡腿是给家里的男长者吃的,他比我们几个都大,又是给我们做饭的辛苦的人,理应由他来吃。我就像个摩梭主妇一样在彝族家里安排着饮食,现在想想真是可爱啊!这回男同事们不再玩笑我了,而是赞赏地看着我,随我安排。
之后的那天,令我至今还在过意不去、还会湿了眼眶的事情发生了。早饭时,我突然发现茶水的味道变了,变得好喝了,苦和涩的味道荡然无存,我高兴得又在那里嚷嚷开了。沙玛大哥见我喜形于色,也开心地看着笑。一个男同事说,因为昨天早上我说地窖的水苦,不好喝,沙玛大哥就一大早背着个二十斤的塑料壶去背山泉水了。我顿时感动得说不出话来,接下来就为自己的不当言辞劳累了别人而羞愧难当,在那里连连致歉,沙玛大哥自然也是憨憨地笑,那就是没关系的意思。男同事们见我实在是抱歉的样子,便安慰我,说因为昨晚给沙玛大哥单独留了鸡肉,还一天帮他干活他才感动了去背泉水给我喝的,叫我放心喝吧,还说托我的福,他们也喝上了好喝的泉水。我这才安下心来,也暗自窃喜:我对别人的关心竟然马上就得到了回报!
后来的几天,虽然我一直要求沙玛大哥不要再去背水,我可以喝地窖的水的,但他嘴上从不做回应。每天早上,那个发黄的二十斤装塑料壶,依然会如期地,安静地摆在厨房的墙角,装满甜甜的山泉水,装满一个魁梧木讷的彝族汉子对一个善良活泼的摩梭妹子的喜爱之情。我们俩一个出生在宁蒗县城的东面高山上,一个出生在离县城好远的北面的永宁坝子,中间相隔近二百里,因为这壶饱含爱意的泉水,让我们有了兄妹一样深的感情。整个宁蒗县恐怕有数都数不过来的山泉水,数都数不过来的家庭,为何这一眼泉水,独独使得我们这一家中有三个人,和这眼泉水,和泉水周围的人有这样的缘?莫非冥冥之中有神灵的安排?我常常会思考这个问题。
那一周,我和沙玛大哥相互合作,默契地安排着一日三餐。牦牛坪气候冷凉,很少有蔬菜,偶尔会有人家的屋后种着几棵青菜,几丛小葱,路过时我就会去跟人家买。但那些善良的人从不会要钱。后来蔬菜我就不再提钱了,直接讨要。鸡蛋、鸡就买,我们有生活补贴,而且还是归我管,每次我都想多给点,但结果是从来都没买贵过,山里的人真是淳朴啊。有时我还会直接钻到人家的里屋去翻老洋芋和老蔓菁,要回来做菜。直到那次才发现,这山区的彝家真是困难啊,七月没过,新洋芋没出来,家家都只有不多的一堆老洋芋堆在屋角了,再有个半袋荞麦,半袋燕麦,有点买来的白米,就是条件比较好的了,每次我看到这一切时心里都不是滋味。
沙玛大哥教我揪去老洋芋长长的芽,削了皮做菜吃,因为洋芋芽有毒不能吃。吃老蔓菁就只有芽可以吃,整个块茎基本上是中空的,边上是干瘪的,没什么可吃的了。也是在那一次,沙玛大哥教我用荞麦的嫩叶做菜,炒菜煮汤都可以,十分好吃。每次用蔓菁芽做菜时,我就跟沙马大哥说这是彝族老爷爷的胡子,从地里摘回来的荞麦叶子,我就说是彝族老奶奶的罗锅帽。后来蔓菁芽就被男同事们戏称为“彝族老倌儿的胡子”,荞麦叶被他们戏称为“彝族老妈妈的罗锅帽”,感觉我们天天都在吃人的胡须和服饰一样。生活虽然清苦,却过得充满了趣味。
那时,几个男同事豪情万丈,激情满怀,常常被各种美好的愿景和宏大的规划亢奋得不会饿也不会累。我那时并不懂毕摩文化为何,以及它对于彝族的意义,但也深受他们感染。当然现在我知道了,毕摩文化对于彝族,是精神的源头,是思想的出路。一个民族的思维结构和行为模式,只有它的原始宗教可以去梳理和指引。这在其他民族也是一样的。我前面这个几千年来能够固执地死守自己信仰的民族是值得尊敬的!无论这种信仰的实用功能在今天究竟还有多大。
我就这样跟着他们翻山越岭,走访周边的村寨,午饭常常晚点。但只要看到美景,看到古朴纯粹的民族服饰,举起相机就忘了饥饿和劳累。我有幸看到了成片成片的红豆杉树是多么的美丽,风吹过时,沙沙作响的她们是那么的高贵和优雅。有幸看到了长坡上洋芋和苦荞和燕麦如何把绿色渐变。有幸看到了成百上千林立的木条,造就的栅栏充满了力量和节奏的美感。有幸看到了彝族大妈一根一根搓出的羊毛线织成的只有三个颜色的羊毛裙,是那么的朴素而庄重。有幸看到了彝族女孩将自己的情感和对色彩的认知,一针一线诠释在刺绣里,悄无声息。有幸看到了平时略显卑微的彝族妇女们,打跳时是那么的热情奔放,完全压倒了男权的样子……啊,太多的幸运。我将这所有一切,拍成了图片,保存下来,也记在心里。当我老了走不动的时候,我才会把这一切画成画,让人们看到,那个时候的美!
一周的调研结束了,由于我有另一个项目要参加,较男同事们提前一天返回县城。临走,我交接了财务,把组里用剩的笔记本、碳素笔等文具全部送给沙玛大哥,因为他家里有读书的孩子,我真的有些挂念。有多少次想找去他家里看看,但总是想着他会不会不好意思,最终没去成。当我收拾好行李,坐着村里唯一的一辆跑县城的吉普车,离开村委会的那个清晨,这五个男人显出了不舍的情绪。也是,我不在了他们多无趣啊,只剩下了酒。沙玛大哥依然是笑笑的,没说什么,但那种笑和之前有点不一样了。我倒没有更多的不舍,那时我满以为这个地方离县城又不远,我还会回去的。想着可以约人去摄影,或是可以去画画。但是离开了十五年,却再已没回去过了。
回到县城的当晚,我打了个电话给村里小卖部,想了解下他们的情况。那时牦牛坪还没手机信号,我们都去小卖部用座机和外界联系。正好村委会主任在那里,他告诉我,从我走后,沙玛大哥就开始喝酒,喝得烂醉如泥,中午晚上都没做饭,那几个男同事自己做的饭。那一刻,我的心揪着疼。我是何德何能,一周,让一个荒山僻野里的中年大哥,和我有了这样的情感。可以为我早起一个多个小时去背泉水,无论我讲什么,可以静静的倾听,然后报以兄长般慈爱的笑容。是的,我知道,他把我看成了一个给他枯燥贫穷的生活带来欢乐的人,一个仿佛生在和他不同的地方,等他过了半生才来相见的,处处关心和爱护着他的妹妹。结果这种相聚如昙花一现,马上就过去了。所以他才不顾自己的职责,连最后一天的饭都不做了。
是的,此生不止一次看到过,一个个刚性过火的彝族男人,当他脆弱到不堪一击时,会如何用酒精为自己剩下的路壮行。我都懂。我仿佛看到了《巴黎圣母院》里埃斯梅拉达对于卡西莫多的意义,仿佛看到了《人猿泰山》里珍妮对于的泰山的意义。虽然这两个故事里是爱情,我们是亲情,但那种兄长般的喜爱,和妹妹般的依赖之情,多数时候这两种情况是相通的。因为这两个故事最后都是悲剧,让我尤其伤感。
大概一周后,我把所有照片冲洗出来,把村里人的照片挑好,准备请那位吉普车司机带回去给村民时,才发现竟然没能给沙玛大哥拍一张,也许是在一起时光忙着做饭了。那时真的好后悔啊,想着下次回去找他补拍,结果再已没回去了,一晃就是十五年。
去年,牦牛坪终于接上了自来水。知道消息后的那天,我无比的兴奋,真心为牦牛坪人民高兴,在网上到处留言,评论。因为我知道常年喝地窖水是什么滋味,常年没有充足的水洗头洗澡洗衣服是什么概念。我们离开牦牛坪后不久,国家低保政策开始在村村寨寨铺开。后来,牦牛坪大量引进了中草药种植产业,加上交通便利后,劳务输出和农产品输出,让那里的经济收入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那些我们走访过的农户,应该早就大变样了。
现在,我已移居丽江多年,每次回老家,看到牦牛坪山梁上那些充满诗意的白色风车时,我都会想,我的沙玛大哥应该也过上好日子了吧?子女应该都成人了吧?但同时也会有一丝担忧,一个动不动就喝酒的中年男人,会不会健康欠佳,已经去世了呢?那我就真见不到他了。
人生就是这样,你会有一两个虽然已经不再联系,但一直会像挂念自己的亲人一样挂念着的人。你明明知道相隔不远,可以马上就去寻找,但似乎又没有更为充足的理由去找他们。既然这样,那么,就让他们继续长驻在你的心里吧!等有一天缘分到了,自然就会再相见。此刻,只想真挚的祷告,我那个彝族的哥哥,还在离我不太远的地方活着,活得平安和顺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