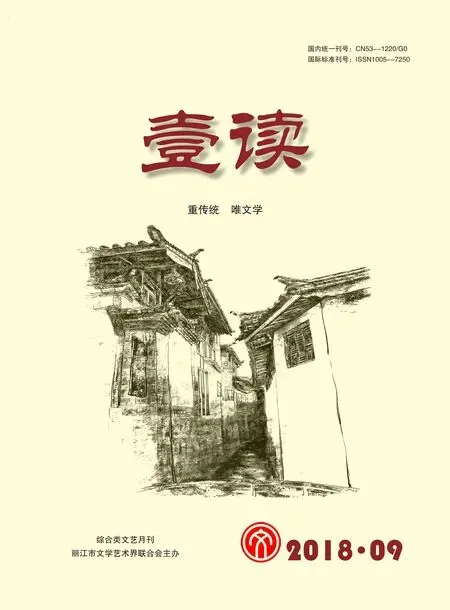摇摇晃晃的人生
2018-01-24谭功才
谭功才
一
我说我在南方有座花园叫濠景的时候,你是否有点吃惊?接下来就要说“但是”了。但是,拥有它的主人很多,而我只是众多主人中的一份子而已。确切点说,我仅仅拥有这座花园的某个小单元而已。
我这样的表述,你便知晓此花园乃我眼下甚至将来都要安放身体的一处居所。这样表述,是基于对自身情况的特别了解。很多年前,我能从外省来到这里,还能安顿好自己的身体,已足够不易。这些年经历过一些风风雨雨,总的说来还算风调雨顺,比上不足比下有余罢。况且,眼下还有正在求学的两个孩子。大的大三,小的才高一。
我说我这个读高一的小女孩是收养的,很多人都不太理解。按照国家对咱少数民族的照顾,是可以有两个孩子的。我们这代人捱过的苦,就只差观音土没吃过了。挨饿的那些年月,作为人最基本的尊严和自信心几乎完全被摧毁。别的地方我不甚清楚,就我熟悉的这一代人,绝大多数选择了只要一个孩子。
缘分同样与时代无法割裂开来。就在我们坚持自己现实观念的时候,我们与一个可爱的小姑娘结下了缘。谈不上觉悟多高,更谈不上什么思想境界。大女儿需要一个伙伴,这对她的成长是有重要作用的,且政府每个月还有一定的补贴。经济上不太为难的前提下,我们接受了这种缘分。于我们夫妻而言,付出的无非就是更多的时间和精力而已。刚好那时我们还算年轻,何况夫人一见面就喜欢上了这个才两岁的孩子。
十年时间一晃过去,孩子不再享受政府补贴,等于彻底打乱了我们当初的计划和生活节奏。现在,我们要用一个孩子的钱去供养两个孩子念书,显然有些捉襟见肘。这些年来,我们不仅要为两个孩子,还有双方的父母也花费不少,而且老人长期身体不好,老家的医保在这里又不管用,钱得掐着来用,最后总算坚持到老人离开这个世界。现在,肩上的担子是轻松了些,心里却空荡无比。有时候想起来眼眶湿湿的,就是掉不下泪来。
像我们这种境况,你说还能搬迁到哪里去?好在我们对物质诉求的感觉较为迟钝,一日三餐怎么将就都不为过。身体有个安放之地,比之父辈,我们就是掉进福坛子里了。况且,我还有一份在外人看来较为眼红的工作,怎么对付或者僵持这一生都不成太大问题。倒是这颗心,总有点悬在空中的不踏实,且随着年岁的递增某个东西时不时就捅我一下,疼痛扩散却不知具体部位。当年辗转打拼奔波,看似游荡的灵魂毫无落地之感,实则总有一种牵挂在远方,看得见又抓不着。而现在,当我的躯体不再流浪,灵魂却总让我无法省心。
记得刚来广东头几年,我们一直都在为老家拥有一幢属于自己的房子而做着种种努力。我一直告诫或者说鼓励自己,我仅仅就是路过广东,终究要回到属于自己的地方。那究竟是一块什么样的土地?我们的远走如此决绝不就是要彻底背叛泥土吗?可是,当我们在另一片土地上好不容易自己焐热自己,却又被现实的泥土僵持或者绊倒。孩子唯有在更好的土壤里生长,才有可能不再重蹈父辈之辙。否则,我们的背叛就是不彻底的,甚至是极度的失败。
那年,我怀揣着积攒已久的两万元,从广东打道回府,图谋在故土真正站立起来。最终的结局可想而知,经过系列深度考察,那块土地其时并不适合生长商品经济,一咬牙,我们遂将这两万块钱变成了购买他乡商品楼的首期款。买楼那几天,夫人踩着一辆破单车到处兜转一个星期后,最终选择了濠头这套每平米不到两千的商住楼。它的名字叫濠景小区。
二
濠景小区与濠景花园又有着怎样的关系?
其实,濠景花园就是濠景小区。我买房的2000年左右,沿海发达城市已不时兴“小区”概念了。那时电台电视台报纸和各种纸质非纸质媒体全方位的宣传,无论位置优势或是价格优势,他们共同的目标就是将人们带进某个“花园”,成为他们的业主。而我付了首期而成为业主的这个濠景小区,还在沿用“小区”,实在颇感意外。
正如你所熟知的广州又叫花城。广东四季如春,常年花开不败,无论走到哪里,总走不出花的海洋。务实的广东人称居住之地为花园,再自然贴切不过。刚从内地来广东那会儿,听人说某某住某某花园,还靠,花园里怎么住人嘛。
买房后那些年,花园不再时髦。试想一下,这也是花园,那也是花园,大家都住花园,岂不毫无档次之分了?精明的开发商与时俱进引进了“豪园”“豪庭”,想必是土豪在主导这个社会吧。再后来,土豪开始攀附文化,花园的名字越来越具有文化属性。随之而来又有了较为个性化还沾点文气的名字,听涛居啊汇星台啊蓝波湾啊等等。不管外面的世界怎么变幻,我所住的小区依旧。业余时间的我,是喜欢看书写作投稿,与外面联系较多,联系地址就被我自作主张将濠景小区变成了濠景花园——小区人都这么告诉外人,咱没理由拖人家后腿吧。再说,花园嘛,毕竟在档次上要比小区高那么一点点,面子上也不至于太那个。
就像乡下人进城,换了一身新行头,骨子里流淌的还是乡人血液。小区可以变成花园,却摆脱不了开发区的管辖。尽管与城区一步之遥,孩子读书还是只能在乡下。眼看着城里人的孩子全都进了好学校,又相继考上了更好的学校。说实话,也曾有过些许后悔。当初就为了开发区房价便宜,失去了更多,说到底还不是咱手头银两紧逼,谁不想住城区?略感自慰的是,人家问我在哪里工作,我说在城区,且孩子最终没太给我们丢脸。
人是一种特别难以琢磨的动物,往往顾及所谓的面子丝毫不考虑后果。当初,我擅作主张将濠景小区改为濠景花园事小,还在前面直接冠以中山市的衔头,我那贫民窟直接就升级为地级市濠景花园了。那次北方来了份包裹,快递员打电话说正在花园楼下等我收取。折腾了半天才搞清楚,那人在西区。噢,想起来了。西区那边是有个濠景花园。邮件最后肯定是收到了,却辗转了不少工夫。事后我在想,估计正是因为西区有了濠景花园,如果再用“濠景”那就只能变身小区了,何况我那所谓的花园,花都没有几朵,几棵树而已,叫小区也算实至名归。
没过多久,城区孙文路向东延伸,地处路边的濠景花园摇身一变成为这条路上的节点。原本属于开发区的濠景小区,也跟着变换身份为孙文东路N号濠景花园。之前的那些误会或者说曲折,似乎并未对我产生实质性的影响。既然政府都确定了我在这条路上所属的某个号码,按照门牌号码找到我当属正常。哪知又出现了旧瓶装新酒的问题。邮局分拣时一看地址前半部分是孙文东路,理所当然就将邮件划归东区处理,但在投递员具体投递过程中,才发现我的门牌归属开发区管辖。邮件就这样被打回,再一次辗转到开发区。如果开发区那边按照正常投递流程和速度的话,迟到几天是肯定的,哪知那边往往是等一个小地方的信件积压到一定程度才会投递。此种情况,如果现在仍有普通邮件来往的,想必如我一般,有着怎样的切身体会。如此一来,我收到信件就比乡下更乡下了。
如今的时代,信件于我而言,迟到早到已无多大意义。无非就是订阅的杂志或是发表后的样刊而已,现在网络那么发达,电子版早就看到了。要说造成的麻烦,主要体现在稿费单。到现在都还有北京一家杂志汇来的一笔稿酬,不知在哪个邮局睡觉或者打转转。我在北京某杂志开有专栏,每个月有那么几百块钱的稿酬。他们一般是一个季度发放一次,也就是说这笔稿酬至少都在千元以上。不是我不在乎这千多块钱。我有我最固执的想法,大不了退回去再汇过来。你若与我较真,党和人民政府的话当耳边风?我是自己随便整出来的一个子虚乌有的地址吗?我地址错了吗?
我不知道我的心境是否代表了当今大多数草根一族。我敢肯定,与我同样有着小小虚荣且固执得可爱的人不少。这个时代,较真的人太少了。我要说的是,较真绝不是火气重。较真的人往往会赢得道理,失去的更多,因而放水流舟或是随波逐流的,反而会得到更多。你说,明知道会失去,还一个劲往前冲,不成为烈士才怪?有人说,低头就是成熟。低头无非就是得到更多而已。
三
买房子哪里就做得了甩手掌柜,这也是我买房后的切身体会。贾平凹说,想一天不安然,就来客人。想十年不安然就建房子。想一辈子都不安然就找情人。其实,买房子同样不那么安然。
有人说,割肉是一刀一刀的割才疼。房地产商却不这么认为。像我一般的打工一族,原本就没有几两肉,哪里够本挨得了一刀?地产商精明得很,你边长肉他边割,最高年限可被割肉达30年之久。三十年是个什么概念?几乎是你一生精华的全部之所在。从二十几岁走上工作岗位开始,差不多到退休,你都得驮着房子这个外壳负重前行。回头又一想,租房每月差不多上千,几十年之后即便空壳也有一套自己名下的房子,大抵也可算得上没白来这个世间一趟。
没有一个安定的窝内心不会真正踏实,这是国人共有的心病,其实也昭示了传统农业大国几千年来从未真正踏实过的根本。分期付款是要单位开能力证明的。硬着头皮找单位盖章,这证件那证明的一大堆,七弯八拐总算拿回了一张盖了很多章的房契。心想着,后半生就卖给了房子,从此生是别人城市里的人死是别人城市里的鬼了。
两万来块钱就能买房子,这在内地人看来多少都有些不靠谱。我说这话的时候,并未特别说明我东挪西扯还借了八万块钱。这么多钱之于现在的我来说,依然不是一个小数目。买个毛坯房当然无法住进去,即便简单的装修,也还要好几万块。在这边打工的亲戚朋友不少,很多都是我带过来的,你三千,他五千,大帮小凑算是筹齐了装修费用。
侄子送我一套沙发,表弟送我一套餐桌椅,再从市场买回杂木电视柜,将原来出租屋里的十七寸彩色电视机放上去,外加上一大堆书,和一堆坛坛罐罐杂七杂八的生活用品。就算是我们在别人的城市里正式有了自己的安乐窝。
二十年前在别人的城市里能够拥有一套属于自己的房子,尚属一件非常牛逼的事。有房子就说明你在城市里定居了,再说白点,你就是城里人了。于是,老家的父母亲戚朋友脸上有光,乡人也给你竖大拇指。你走在老家的任何一条道路上,甚至只要知道你的名头就会主动与你搭讪,还会说一大通赞美诗一般的话语。如今的乡人与城里人一样变得那么现实和世俗。他们当然并不知道你是实实在在的“负翁”。你自己也知道,这个世界上的人,谁没有虚荣心。背着“负翁”还得整一场像样点的酒席。毕竟相当部分人连负翁也暂时做不起。再说,乔迁之喜嘛,不管用何种方式购买的房子,终归是自己的。人一生中像这样的喜事又能有几回?
曲终人散。我拖着疲惫的身躯和一身酒气回到新居,将自己重重往沙发上一扔,迷蒙的双眼四处流转。洁白而耀眼的墙壁,悠悠放光的地板砖,豪华的欧式灯,将我全身激活,思绪禁不住开始浪迹天涯。特别值得说明的是,那两套豪华欧式灯是当年一起在文学战壕里摸爬滚打的兄弟送的。他的成功转型,让我这个坚守文字梦想的人既感到骄傲,又倍感前进道路的崎岖与艰难。所幸的是,物质的丰沛与否实在对我不具备多大的诱惑。当然,也曾萌发过甚至践行过经商的道路,最终发现不是那块料而及时收手。
新鲜劲很快就会随着平凡日子的流逝慢慢耗尽。接下来面对的就只剩下每个月的供楼款了。
供楼首先得从贷款的最长期限开始。也就是说按照我的贷款期限是十年,得从第十年往回还款。再详细点说,就是首先还的贷款必然是利息最多的第十年,然后以此类推慢慢递减。虽说每个月也就千多块钱,这在2000年那时并不是一个太小的数目。按照当时的工资水准,应付过去也还不成多大问题。小孩六岁上学已开始实行九年义务教育,基本上只要对付生活费和其它兴趣班的费用。隔三差五尚能呼朋引伴小聚,甚至去酒吧泡上几个小时,耗掉青春阶段那些多余的能量。
这种看似步入正常轨道的城市生活,正在流水一般的时光中将我的青春一点一点消解。
四
濠景花园是一个不到两百户人家的商住小区。这种合乎标准的住宅小区,在当时的濠头算得上最早的为数不多的商住小区之一。因为占地面积不大,绿化率远远无法与后来的小区相比。就因为户型不错,价格便宜,又与城区很近,一开盘就几近售罄。几乎都在同一时段装修,然后便陆陆续续入住。
我是在小孩上一年级或者二年级才发现一个有趣现象的。居住在这里的主人大致上都在一个年龄段,也就是说像我这种年龄的,且绝大部分是外省人。在这座城市里工作了七八年左右,手头有点小积蓄,孩子正需要一个学位念书,然后一咬牙便过上了所谓的城市生活。其实,后来我也想通了,与其每个月交那么多房租,还真不如买楼。虽说每个月都在供,最起码供够了房子终归是自己的。住在自己名下的房子里,就有一种比较奇妙而细微的自豪感和满足感。
人真是一种奇特的高级动物。在乡下过日子的时候大家彼此频繁往来,亲密无间,如果谁不懂得人情世故孤家寡人,那是要被人戳脊梁的。而当他们一旦进入城市生活,一下子就变得与城里人一样老死不相往来了。就我所入住的C幢来说,一梯两户总共十四户人家,至今有几个楼层的还未打过照面,就更别说打交道了。那时,岳父跟着我们过日子,整天没什么事做,倒是将整个楼层的基本情况摸得非常清楚。哪家是做老师的,哪家是做警察的,哪家男人死了,女人经常带不同的男人回家,他都了如指掌。为此,我老婆还曾转弯抹角说过他爸,别管那些淡闲事。直到老人家过世我忽然间明白过来:我们整天都在忙自己所谓的事业,很少时间陪伴老人。再且,老人虽说住进了城市,思维方式依然没有多大改变。他与人沟通的语言依然是地道的西南官话,若是北方人倒也勉强能沟通。若是沿海地区的,有时候对方怎么也整不明白。老爷子就试图转换成蹩脚国语,明明只要稍微再转点弯就达到效果了,就是转不过弯来。我们心里都跟着干急——这是哪门子语言嘛。有时候想起来,一个人偷偷笑呐。
最难接受的就是老爷子从外面回来从不换拖鞋。天晴当然问题并不怎么明显,只要不去洗手间。如果从洗手间出来,地板砖上准是一行清晰的带有颜色的脚印。下雨天或是回南天那就更麻烦,然后就将地拖放在洗手间门口,看不顺眼了就立马拖一下,也想借此提醒一下老爷子。偏偏老爷子熟视无睹,话又不能说得太明白。上了年纪的老人小心思特别多,弄不好得罪了还不晓得。
老爷子和我们一样都是起早床的人,几乎每天五点多雷打不动。然后开始在后面的阳台上洗衣服。那时的小区大多数人还在睡梦中,老爷子说话声音又大,好几次话到嘴边硬是又给吞了回去。有过之前的教训,我们不敢轻易说老人的不是,免得他又吵闹着要回湖北老家。想当初,费了很大周折才将在老家新建的房子贱卖,将两个老人接到身边,为的就是照顾方便。那天清早,晨运回来的我还在楼梯间二楼,就听到七楼阳台老爷子的声音,用我们乡下的话说,就是大声夸气。他正在为一件事情同我老婆沟通。早晨的小区格外安静,更加凸显出老爷子那口西南官话。我再也忍不住了,我要告诉老人,这里是城市,公共空间是大家的,不像咱山区,天吼垮了也没几个人听得到。或许是我也憋太久了,那天的语气可能有点偏重。结果可想而知,我是彻底得罪了老人家。估计临走前他一直都未能想通,一直对自己百依百顺的女婿,怎么说变就变了?在他离开我们两年后的今天,我也一直问心有愧。如果我再轻言细语点,或许老人家就不会那么生气。不生气就会心里顺畅。心里顺畅或许就能再多活几年。我是计划老爷子八十寿诞给他好好贺一番的。孰知八十还差那么几个月就离我们而去了。
现在回想起当初将老人们硬生生从柔软的泥土里挪到硬梆梆的城市,除却照顾方便之外,为的就是城市的医疗水平远比乡下高得多。他们为我们后人吃的苦有卖的,多活几年享点我们的福是应该的。就拿老爷子早年落下的腰间盘突出来说吧,我这里离医院近,最起码有个三长两短也有个照应。事实的最终结局呢?老爷子是多活了几年,但他心里真那么舒坦吗?心里不舒坦捱多几年世界又有何用?如果我们有更多的钱,也不至于让他忍受那么久的腰椎疼痛,每个月只能挤出几百块钱给他做医药费,勉强缓解那旷日持久的揪心的疼痛。再说,面对突如其来的心肌梗塞,我们还是无能为力只能眼睁睁让他撒手而去。
老爷子跟着我们在城市居住的十几年时间,真正能与我们说上话的时间却甚少。每天清早,老婆起床做早餐,我们夫妻俩在极短的时间里吃完早餐,就得匆匆忙忙赶着上班。中午我们都在各自的单位用餐。而晚上很多时候我都在外面应酬,待我回到家中,老爷子大都睡觉了。偶有早归,我们也说不上几句话。我和老爷子唯一可交流的就是央视三台。我对戏曲频道和新闻频道一点都不感冒。甚至对新闻的真假而态度完全相反,我曾多次试图改变老爷子那些固执的观念,最后都在不欢中而散。老爷子在旧社会长大,新社会里因为成分问题挨过整,怄过太多的气,偏偏脑筋被洗得格外干净。
日子当然得分成一天一天的对付。老爷子每天吃完早餐就到处找砖头,整块的,半截的,用尼龙胶带装起来,今天一点,明天一点,慢慢积攒围成楼顶的几大箱菜畦。从一楼到楼顶,整整八层。那么多的砖头,那么多的泥土,都是老爷子一手一脚从几公里外的地方弄回来的。没有一年半载,是绝对办不拢的事情。南方天气热,楼顶种的菜,特别是瓜果之类的,每天要浇好几次水。起初,老爷子就将洗碗洗菜的残汤剩水用胶桶装起来,往楼顶提。随着后来楼顶菜地面积的不断扩大,他又收集了不少大小不一的坛坛罐罐放在楼顶收集雨水。后来,老爷子的腰间盘越来越严重,以至于空手上楼都不太方便了,我们这才将七楼的自来水管牵引到楼顶。
五
刚入住濠景花园大概也就三两年时间,小区里许多家的孩子就开始要跨进学堂门槛读书了。我之所以书面用濠景花园而口语用小区,觉得还是顺口点,也更实在。农村里出来的嘛,小区已足够了。
那时,小区最闹热的时段应该就是周末的夜晚了。平时都有家庭作业,孩子们几乎都被关在家里。只有到了周末,孩子们就像脱缰的野马,预约了似的集中在小区楼下,你追我赶,各种游戏玩得带劲。你是知道的,小孩一旦玩疯便不知道回家的方向了。大概九点来钟十点不到,总会听到操着各种地方的口音在小区上空回旋。那定是在呼唤不肯回家睡觉的孩子了。每每此时,仿佛就最真实地触摸到了这人间烟火的温度。
女儿自然也是这群孩子们中间的一员,而且还成了他们首领。这与女儿天生的侠女性格有关,也难怪后来她居然就偏偏放弃音乐而喜欢上了跆拳道,并在这条路上有所成。但是,最终的她却又再一次神奇地走回了音乐这条道路,也算得上是奇葩一枚。
那年中考,恰巧考试数学那天,身体出现心跳加速而不得不去医院治疗,从而严重影响到当天两门课程的考试成绩,最终距离重点高中还差几十分——女儿不出意外地进入到了一所普通高中,如果正常发展不出意外,估计上一般的本科都困难。为了确保孩子将来能接受到更优质的高等教育,我们选择了报考艺术特长班。女儿似乎继承了我先天音乐细胞的基因,经过音乐老师的试音鉴定后,我们总算吐了一口气。想当初,女儿很小的时候,我们就为她买回电子琴之类的乐器,目的就是想她能够在音乐方面有所发展。孰知,后来女儿却喜欢上了跆拳道,并从小学四年级开始一直坚持到初中毕业。转了一个大圈,最终女儿还是回到了最初的音乐道路上,不能不说造化弄人,有着强烈的宿命味道。当然,虽说现在的她正在念音乐教育这个专业,至于以后的人生究竟该走着什么样的道路,仍属于一个未知的将来。
正如女儿小学同学瑾茹,当初学习成绩还算不错,后来随着年龄越来越大而出现越来越强烈的逆反,以至于初中阶段常常逃课。父母想尽一切办法,终归毫无任何效果。为了管住孩子,父母甚至将其送到老家江西一家封闭式学校读书,最终还是徒劳。孩子未毕业就走上了社会。几年前女儿曾在一辆公交车上偶遇她当年这个小学同学,听说她正在城区一家服装店卖服装。于瑾茹父母而言,女儿实在是他们心头的一个疼痛。但是,话说回来,将来的女儿究竟会成长到什么样子,仍是一个未知数。这个金钱挂帅的社会,只要你赚到了很多钱,无疑就是成功的人士。否则,你谈什么都是枉然。
想起很多年前刚住进小区那会儿,那些孩子们还是一群屁颠屁颠的娃儿,眨下眼,他们一个二个就成人了。有的在读大学,有的即将上大学,最小的也都将近进入高中了。曾经将人生看得那么漫长,似乎没怎么整明白就糊里糊涂过完了大半辈子。小学那阵子,我爷爷曾在我的笔记本上写下:记得少年骑竹马,转眼就是白头翁。那时怎能理解爷爷对整个人生的喟叹?如今想来,爷爷辈过着那种艰难的日子都在感慨岁月如流水,而今蜜一般的生活,岂不更是日月如梭?
有时候一个人在楼顶看看四周的风景,或是某个东西在心里撞击了一下,是免不了要回忆和总结前半生的。古人说,四十而不惑五十知天命,虽说在当今整体寿命平均值提高不少的前提下,是应该有所前移的。事实上,按照个人的观察,大概也就那么五年左右的时间而已。记得某次在某大学充电,教授是这样总结人生的。他说,二十岁谈理想,三十岁谈事业,四十岁谈成就,五十岁谈经验,六十岁谈感想。可以说基本上勾勒出了我们此生的人生轨迹,一般情况下不会出其左右。
而目前的我也正处于知天命的节骨眼上,除了思考孩子的将来之外,恐怕想得最多的莫过于自己的将来了。
六
曾写过一篇《家在东区外》的小文章,表达过自己在城区和乡下之间小心翼翼周旋的复杂心理。我所居住的濠景花园,在身份上属于开发区的濠头管理区。在实际地理位置上则又几乎与城区是一个整体。这也是当初选来选去最终选定这里的决定性因素。老辈子说,人穷心事多。说自己在城区工作吧,又住在乡下,二十几年了还开着摩托车上下班。很多朋友都说不合我身份,劝我早点买台车,还说上下班方便,应酬有面子。你道我怎么说?濠头到单位不到十公里,摩托车只要十几分钟,走博爱路顺溜哩。应酬?不是有专车接送到楼下吗?谁何曾有过如此待遇?这也是事实。在别人的城市里混迹了十来二十年,的确也做了不少实事,贡献了不少力量。我头顶也因此有了一圈圈比较耀眼的光环,属于有点身份的那种了。
说到底,还是缺钱这个根本性问题。选择文学事业作为自己毕生的追求,当然也就意味着要舍弃很多,譬如物质上的。这世界并非烂到家了,一样有懂我心思的人。说文人追求的是境界啊。这面子给得真给力。多好的台阶。说句实在话,钱这东西谁不爱?只是我见惯太多人间生死,比大多数人淡泊而已。舍弃精神层面的东西去刻意追求物质,到目前为止还没养成这习惯。将来估计也没多大可能性。就拿我住的这贫民窟吧,同一幢楼的好几家都换了新房,我却还在建设楼顶的空中花园,一点也没有移动的迹象。我常安慰自己,文人嘛,首先要静得下来,才有成点小气候的可能。我也想移动,那只是身体上的。每每有机会,我总会到处走走,开阔一下视野,呼吸一下外面的空气。回过头来,又开始在自己的田地里耕耘。
我是一个彻头彻尾的乡下人,当初怀着一腔热血为追寻自己的理想一头撞进了城市的大门口。二十多年的异乡生活与遭遇,也曾有过短暂的茫然和徘徊,也曾差点就倒在了生活的脚下。就像刚刚住进濠景花园那时,有点迫不及待地洗刷从乡下带进城市的泥土,甚至一度有点飘飘然的晕乎。而现在,当大多数将自己的标签快要擦洗干净的时候,我却接过了岳父传承给我的衣钵,守着楼顶那倾注了他太多心血的一方薄薄的土地。
那时候哪里想过要在别人的城市里落地生根,又哪敢想能在一个完全陌生的地方开花结果。世事也只有在这个变化得你都惊讶的时代,才真正称得上世事如棋。试想一下,我们上一代要跨出一个小小地域的门槛都何其之难,何谈数千里之外完全异样的南国。即便冲出了人为设置的某种藩篱,又岂敢奢求进一步的非分之想。事实上我做到了。我身边很多人都做到了。禁锢的时代就像冰点,春夏秋冬的自然法则谁能阻止?
我可以非常自豪地对人说,我站在了属于自己的土地上,尽管它的下面还有钢筋和水泥的混合物,我已不再在乎脚下摇晃的地球,以及地球上摇摇晃晃的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