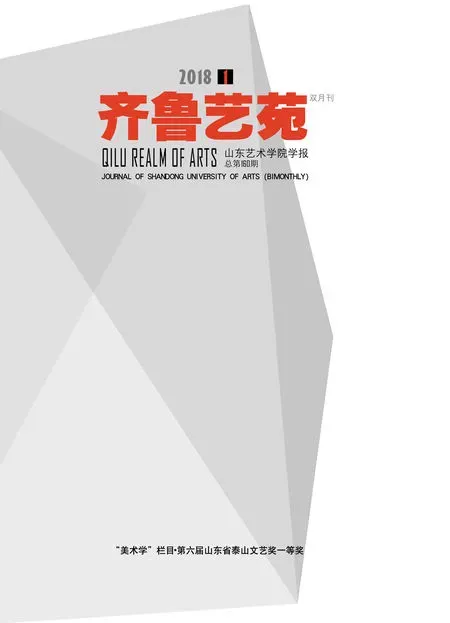陈英雄“三部曲”中的母国想象及其他
2018-01-24迟婧婧
迟婧婧
(上海大学电影学院,上海 200000)
经典越南的形象是来自西方“他者”视角下的东方越南,丑陋脏乱的街道、恐怖的热带丛林、连绵的雨水、兽性的俘虏、卖笑的女人、疾病、战争、阴谋、梦魇,在“西方中心主义”的电影叙事中构成其主要面相与经典元素。即使在试图还原一个地道乡土越南的奥利弗·斯通的影片《天与地》中,仍不乏以西方眼光为中心的怜悯与偏颇,越南民族情转为凝滞灰暗;将越南印象的重点置于湄江的影片《情人》中,杜拉斯在凸显越南这个自己童年生活过的国度时亦没有察觉到沿袭了“他者”对越南想象的“暴力”。越南电影的民族性在后殖民语境中,伴随着被遮蔽抑或缺失的本土文化身份,被迫文化性地失语。
继包括美国越战电影、洋溢着异国情调的法国怀旧电影、以越南为背景的香港黑帮片这些越南电影的“三副面孔”之后,直面现实矛盾、重塑国族共同记忆的越南本土电影以及近30年来将母国记忆与国籍国文化融合的海外越裔电影与前三类电影一齐构成了由五个不同文化建构的越南的阐释文本。相较于封闭固守本土传统或下意识地“妖魔化”地建构越南想象的影片,处于母国与国籍国“夹缝”*“夹缝论”(in-between-ness),原文将此论点用于解释处于英国与中国之间的香港正处于一种“殖民者与殖民者之间”的夹缝状态。原观点见周蕾:《写在家国以外》,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94页。身份中的海外越裔电影在某种程度上更能理性客观地挑起对越南的话语重新叙事的重担。导演陈英雄在其“三部曲”中,更是将对母国的回忆重现在影片中,随后在惊觉祥和的故土记忆被打碎之后直面沧桑的现实,开始反观内省,在母国与国籍国之间完成了想象性的“和解”。海外越裔导演在文化殖民语境中逐步赢得对于越南叙事的话语权。
一、诗意幽婉的母国记忆
未及成年,陈英雄即已在法国生活,对于母国越南的想象仍是记忆中安稳静好的时光岁月。1993年其第一部剧情长片《青木瓜之味》便迫不及待地将想象中的越南置于镜头之下,幽婉得近乎静止的时间、阳光下的蚂蚁、滴水的青木瓜、白瓷盆里的清水……从头至尾包裹着影片。陈英雄镜头下的越南是曲径通幽的、东方式奇观的,影片中除却开头几声飞机轰响的画外音向场外人暗示这是战时的背景,镜头没有离开“家”这一场所,在纷扰的50年代背景中,越南式的家庭却仍然是达观自制、不乏温情的。
在对母国的记忆重现中,对家庭的探讨其实是陈英雄对民族性思考的镜像投射。《青木瓜之味》中数十年如一日坚守家族的老夫人、隐忍持家的少奶奶、自始至终朴实聪颖善良的梅;《三轮车夫》里为家庭奔波忍受侮辱的家姐、手轻脚快懂事的家妹、承受丈夫背叛独自抚养儿子的女老板;《夏天的滋味》中在经历感情变故之后重新生活的三姐妹,“三部曲”均以锦心绣口的女性为主导。在民族母题方面,陈英雄以家庭为原点扩散至对整个民族情怀的美好期冀。在被欺压剥夺主权的越南土地上,女性地位无论是否卑微都无一不是深明大义、善良自足、毫无做作的形象,这种美好的“隐喻”正是陈英雄对母国记忆的呈现,沉着的画面、达观思辨的人生态度与淡雅环境的烘托,一致将其东方表意化的诗意展露无遗,融有东方哲思的镜头语言亦对越南历史、现实以及未来命运做了积极思考。
二、支离破碎的母国想象
《青木瓜之味》对越南的记忆呈现无论是色彩、构图还是镜头运动,都显现了东方奇观之美,伊甸园式优雅的东方奇观与越南殖民影片中的景观展示相去甚远。类同于同时期中国大陆影片《红高粱》《黄土地》把民俗奇观搬演至镜头之下,其中表现出来的明亮是自我臆想式的,小人物的坐怀不乱、自我救赎隐喻着民族性的活力依旧。去国怀乡的陈英雄起始对母国的想象是一厢情愿的,的确有失偏颇;后来他带着文化心理的反思和对当代的凝视,重新对越南影像做了调整。
(一)现世沧桑
继《青木瓜之味》后,陈英雄开始直面越南人心中不想追忆的过去和逃避无用的现实,在隐藏的焦虑之后,把残酷痛苦的生活触目惊心地拎在镜头下。罪恶之花在1995年的《三轮车夫》中被撕开重新审视,卖淫、毒品、抢劫、杀人……在片中毫无遮掩,血淋淋地暴露在镜头下,直白又强烈。陈英雄的文化自觉致力于把这些影像打造成关于越南现实的万花筒。
与祖父、姐妹相依为命,在底层挣扎的三轮车夫在苦难的生活中过得安然自得,后来却落入了车行老板娘的黑帮贩毒圈套中,被囚禁、被鞭打、被迫接受残酷的黑帮生意,直至到心甘情愿加入到黑帮之中;在这个过程中,家姐被欺骗沦为妓女,同样受到侮辱和伤害。车夫起先逃脱反抗,被灌以汽油作为惩戒,在惮于恶势力的欺压之后壮胆试刀放火害人。随后在警察的围追堵截下,车夫从下水道逃离,沾满污垢、蠕动着脏虫的脸浸于污浊的鱼缸中,却在镜头上留下一丝邪魅的笑;掐断壁虎的尾巴、噬掉金鱼、扎瞎混混的眼睛……车夫由背离人性时的恐惧无助转而为自我麻痹逐渐堕落,作恶甚至让他产生了快感,以至于后来车夫向帮首“诗人”恳请加入到黑帮中。终于麻木的车夫在人性最黑暗的时候用蓝色油漆涂满全身,企图用最幼稚的手段获得“母亲”的关注和对强加于自身的罪恶的彻底驱逐。没有嘶吼和势大力沉的场景,罪恶就在表面沉静的镜头里缓缓流动,它找到你、赋予你痛苦却无法靠一己之力摆脱。暴力在陈英雄的诗意镜头中无处不在。影片对沧桑现世的叙述,也正映射了被殖民、被欺压、被迫认同暴力的越南殖民史。
(二)内省的想象
1. 父辈的缺席
在陈英雄的电影中,对女性的刻画映射了对民族性温情一面的渴望,对男性的描摹则是对权力缺失的愤恨苦闷。“三部曲”中,男性无一例外地或主体性缺失或身份性缺失,由《青木瓜之味》隔三差五窃取家里维持生计的钱财外出的男主人,到《三轮车夫》中开场便不复存在的父亲,再到《夏天的滋味》中对家庭不贞的丈夫,无不如此。其中《三轮车夫》的主要事件围绕车夫和“诗人”两位男性铺展开,男性的形象依然处于被恶势力支配的地位。《夏天的滋味》中的男性身份是摄影师、画家,是较少参与社会物质财富创造的角色。毫无心机被设圈套的车夫在运输毒品之后,噩梦惊醒喊道:爸爸!车夫悟到父亲逝去之时的人生寓意,想找回被庇护的臂膀,在恍惚中将自己与父亲的身体融合为一,对权力的渴望在车夫的喃喃自语中反而揭示得更为透彻。车夫失去的表面看是父亲,其实喻示的是民族的方向。
“诗人”的父亲处于半缺席中,他拒绝父子间的交流,唯一一次出场即是对儿子的鞭打。受伤的“诗人”缺失了父权意识,只能靠母性扭曲的爱来抹除掉父权丧失的痛楚,沦为女老板的恶势力帮佣。“诗人”在一次次为家姐介绍卖淫生意时的彷徨无助却又毫无逆反的胆量中,逐渐丧失了作为一个男性尚存的权力尊严。丧父的车夫和视父亲如无物的“诗人”都是传统断裂的受害者,也是越战暴力的隐性受害者[1](P16)。陈英雄在用现代手法白描罪恶对于平凡个人的蹂躏的同时,也回到了民族性的主题上来,以小见大,做出了他对越南民族的现实困境的理解和阐释。
2. 身份的丧失
西方他者眼中的“东方主义”是自我臆想、有失偏颇、带有夸张成分的想象的产物,强势文化的无意识想象性地建构着第三国家的民族情貌。而海外越裔电影体现着被母国与国籍国双重文化放逐的身份[2],处于身份不明状态下的越南电影也失去了自己的名字,仅仅充当了战争和殖民的痛苦记忆空间。
《三轮车夫》中的人物几乎没有名字,对白不多,只有在被问及的情况下才会展开对自我的叙述,主动的话语权在静默中被擦拭干净,对于身份的主体性更是茫然无知,这即是越南民族及平民个人、梦魇般的回眸与自省。车夫没有名字,“诗人”也没有名字,同样没有几句台词,后者的身份在父亲那边被强行删除,在母亲的有限关爱中也得不到生活的温情,在两方的权力争夺中竟获取不到任何一方的承认,他因此毫无“主体性”可言。这也正是战后越南的尴尬处境:在被殖民后无力彻底摆脱强权的奴役,又耽于自身弱小的能量,只能在殖民国强权中小心翼翼博得势力的扶持,在权力的此消彼长中难以确认自己的主体性。
三、认同与反照的想象“和解”
经历了对母国越南民族的“幻想”之后,直面沧桑现实的残酷、致力于将影像作为展现越南现实万花筒的陈英雄也在对抗与妥协中寻找着平衡。越南民族若要定位自己的现代位置并确认所谓的“越南性”,必然要经历“去美国化”“去法国化”的双重过程,陈英雄在影像上进行文化寻根的同时,也找到了构建混杂身份的路径。
(一)文化寻根
1.找寻曾有的富足与自立
与母国的多年隔阂使其形象在陈英雄的镜像中变得模糊飘忽,但其对故土的旧时记忆在“三部曲”中却无形渗透着,它是《青木瓜之味》中飞机轰响的混乱世界里仍然保持静谧淡然的家庭,是《三轮车夫》中人性终有回归的良善,是《夏天的滋味》的翠绿河川与夏日荫凉,更是默默持家、渐长智慧的梅,是隐忍美好的家姐,是知足常乐的莲,也是努力回归灵魂、摆脱罪恶的车夫、断然与恶决裂的“诗人”……纯粹优雅的越南想象在陈英雄的镜头中缓缓流动。
2. 自我救赎
外界的罪恶和欲望对人的控制,是个人无力摆脱的。《三轮车夫》中车夫所承受的极恶不是自我欲望的化身,而完全是被强加的。纷扰餐厅中低头擦鞋的家妹、在舞厅中无所适从的车夫、心虚流鼻血的“诗人”、被强迫卖淫而痛哭流涕的家姐,在镜头下的他们都是单纯不谙世事的人,非心恶而是他者恶,是“耻感文化”*参考美国人类学家鲁思·本尼迪克特的观点,她曾将日本的政治思想喻为“菊与刀”,将日本文化界定为“耻感文化”,即越是甚微反易招来黑暗边缘势力对他生存的介入和占领,处于底层的人只有选择屈从和逃亡。的外在强制特性消解了内心的力量和人的主体性。
在母国与国籍国的混杂身份中,陈英雄在潜意识中将自己作为殖民国的“合谋者”,在影像中找寻人性纯良之时亦在为自己“赎恶”。车夫几次逃离反而被“恶”严酷惩罚,逃脱无门尝试加入“恶”之后灵魂却陷入了迷幻无力的状态。在儿子被意外撞死后,车行老板娘受到了内心的惩戒,在自反中发现了普世的母爱,于是解除了对车夫的压榨。“诗人”不言语、不作为恰成为恶势力的帮凶,最终在与家姐的爱情中发现了自己的罪恶,厌倦了迷茫和煎熬、纠结,并果敢地杀死嫖娼者,也即杀死自己的同谋者,最后点火自焚完成了灵魂的复原。影片《夏天的滋味》的直译是“阳光直射”,陈英雄的镜头直面恶势力,深掘人性的欲望面并期待自我救赎,从中也隐喻出陈英雄从对自我文化身份认同的困境中走出来,通过“自省”让迷失的灵魂得以回归。影像中融入的亦是对整个民族的自省和期盼,充满强烈的东方人文的思辨力量。
3.重塑国族记忆
或经受战乱或遭遇破败,唯有灵魂自赎、安守淡然的幸福是最大的满足,这是在陈英雄影片中亘古不变的哲理,也是重振民族心理的精神原力。集体记忆是对过去的事件与情境高度选择的结果,它主导着公众对其历史身份的认识[3](P138-139)。培养一种共享的记忆对于国族认同的建构而言至关重要。将社会残酷现实撕开揉碎置于镜头下的《三轮车夫》中,向被绑架的警察细数自己子弹伤痕的黑帮头目,把每一颗子弹的位置以及所受的苦难一一愤怒地向对方展示,这也是越南民族直面自己被蹂躏的过去的曲折暗示。
完整的集体记忆塑造机制除了要强调记住什么外,还应包括要忘掉什么的内容,惟此方能克服历史断裂和社群离散,确立国族认同所必须依循的连续性和统一性原则[4]。影片中,得知“诗人”为自己报仇而自焚的家姐在长椅上迷茫徘徊,然后被小男孩率性地牵起手拉着往前走。母国的伤痕仍在,这片土地上的人已有力量引着民族往前行进。影片中的诗句恰也完整映射了民族的历史、现在与未来,由“没名字的人/没名字的河流”到“灵魂渐露曙光,人类安居于大同的世界了”,再到结尾镜头扫过法属高档小区,落在了低矮杂乱的民居上,车夫载着祖父和俩姐妹在阳光下缓缓前行,“昨天猫回来了,我们以为它早已死去,可是它却比以前更加美丽,简直帅得几乎认不出来,猫晒太阳睡觉,猫脸上有一道伤痕”。至此,关于整个母国的想象及国族记忆叙事完成。
(二)解惑身份迷思
1.夹缝生存的身份游移
自幼切断与母国联系的陈英雄在现代社会的游走中处于尴尬面对故土家园、难以融入西方世界的两难夹缝中,在影像中他反而游刃有余地进入了对母国的想象中,这也是他寻找自身文化身份的“父权”象征。赛义德在《东方学》中指出,每一种文化的发展和维护都需要一种与其相异质的并且与其相竞争的一个自我的存在。自我身份的建构,总是牵涉到对于我们不同特质的不断阐释和再阐释[5]。生活在别处的原乡人,在民族情绪和文化情结上与母国无法割裂关系,游走在异域的他国原乡人时时处在两种不同文化的夹缝中。陈英雄处于母国与国籍国的双重身份中,自我与另一个异质的自我共同构建了其对越南影像的想象。他将目光聚焦在越南现实社会真实流动的矛盾中,不刻意、不掩藏,凭借文化自知和自觉在身份游移中找到了镜头阐释下的母国影像和自我的位置。
2.东、西交融的身份认定
陈英雄“三部曲”中影像的叙事将东方传统深厚的文化底蕴一以贯之,侧重意境的营造和情怀的书写,在叙事上往往点到为止,不进行多余的意义阐释,留下空白和深意交与观众领悟。这种含蓄的叙事手法与中国大陆费穆的“文人电影”有相似之处,注重隐喻和象征意义。布莱松“以平易现真知”的创作风格在《青木瓜之味》《夏天的滋味》中得以延续和渗透,家庭的描摹、长镜头的运用又与小津安二郎的风格极度相似,《三轮车夫》对人物在近乎疯狂状态下的快感与迷幻呈现正是约翰·福特提倡的用现实主义手法表现历史事件的创作概念,对意象的营造和氛围的捕捉体现在《青木瓜之味》《夏天的滋味》中是对茂瑙印象主义风格的模仿,《三轮车夫》中黑帮头目教车夫开枪的一幕也正是向《教父》致敬。
东、西互融在“三部曲”的电影制片中也表现出来,三部影片均为法国或其与越南、德国共同制片,在资金和人才方面亦没有拘囿于单一民族。这也从一个侧面证明:正是导演在寻找到了自我身份定位之后,才能在创作手法与制作中于东、西方文化和资本中游刃有余地行走。
3.互为镜像的“他者”
《青木瓜之味》给予人们的是一个有关越南的“时间滞后”,以东方的奇观引起世界的注意;《三轮车夫》是反其道行之,在法国殖民这个“时间匮乏”的空间中呈露出第三世界文化处境的“时间滞后”[6]。被殖民时期,越南历史及其文化被错认、置换及取代,越南是沉默的,必须由西方为它代言。陈英雄自身即处于身份存在的夹缝中,漂流海外的经历使得他处于一种“丧父”和“寻父”的状态之中。可以类比的是,越南电影处于五种阐释性文本的混杂中,影像的身份亦是不明确的。因此,在解惑身份迷思的问题时已不仅仅是影像自身或者导演个人,而是涉及到整个国族的身份建构。
福柯亦强调权力产生于且实行于由两个或更多的人或实体所形成的关系之中,并且处于这一关系中的双方均对对方行使权力,尽管程度并不相同。权力本身即含有这样的意义,要想获得权力——即能够对另一方施加作用——就必须服从使双方关系得以建立的秩序[7]。在谋求越南
影像独立性与竞争性的同时,必须将自己纳入对立的权力秩序之中。尽管对外界的模仿在一定程度上表明对其的某种服从,但这一模仿的内在含混性却也同时构成了反抗。陈英雄影片中的被殖民化的多元背景没有被排斥,反而打上越南民族性的标签,在叙事中既担起了民族性的背景,也用异域风情做了装饰,若想在国际秩序中得到主体性,越南电影必须被置于这一框架中解释。陈英雄的“三部曲”恰好在叙事的构成元素及镜头语言上创造了东方式奇观——诗意思辨性的越南民族,这种寓言化的表意又把越南带入世界历史中,将滞后的越南时间与世界空间相弥合。
与张颐武笔下对中国第五代导演的批判观点不同,陈英雄没有选择将越南影像文化转码为具有世界性普世矛盾叙事,抑或将其对母国想象转为“他者化”的表现,使之成为一个“被看”之物,相反,他在关注本土现实与民族矛盾的同时,也在对外界影像的认同与反照中进行了自省和期盼,达成“和解”。
霍米·巴巴的“混杂性理论”指出,“混杂”是一个长期稳定的电影生存状态,它并非中介或电影发展的跳板。陈英雄将对母国越南的记忆想象与流动认知成功投射于影像中,消解了胶着对立的“二元”创作思路,在后殖民语境中找到了“他者”与自我融合的弹性创作空间。
参考文献:
[1]张会军.影片分析透视手册[M].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2003.
[2]万静.第三世界电影的一面旗帜[D].山东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09.
[3]MCCOMBS,MAXWELL.Setting the Agenda: The Mass Media and Public Opinion[M].Malden: Black,2004.
[4]郝延斌.韩国古装电影的中国想象及其他[J].戏剧,2014,(1).
[5]高远.越南影片《盛夏时节》——评价与导演访谈[J].世界电影,2002,(2).
[6]张颐武.后新时期中国电影:分裂的挑战[J].当代电影,1994,(9).
[7][英]裴开瑞.跨国华语电影中的民族性:反抗与主体性[J].世界电影,2006,(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