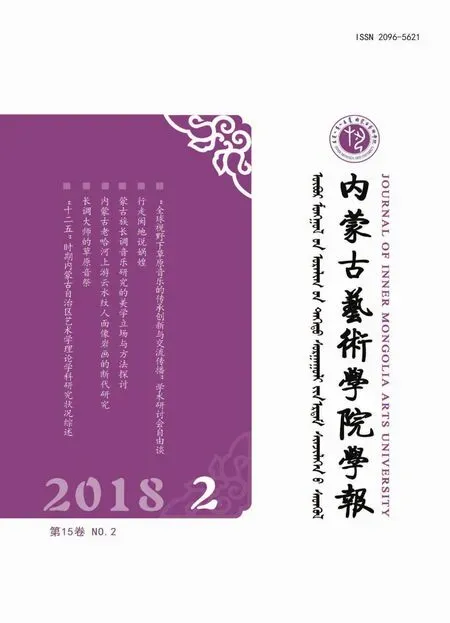《个体·传统与新世界
——吴云龙四胡艺术研究》书评
2018-01-24宋雪微
宋雪微
(内蒙古艺术学院,内蒙古 呼和浩特 010010)
内蒙古艺术学院青年教师苏雅撰写的《个体·传统与新世界——吴云龙四胡艺术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年)一书,在蒙古族传统音乐研究领域,是一部具有独特视角和创新思维的学术专著。本书关注的研究对象吴云龙先生作为蒙古族四胡音乐领域的杰出代表,其一生横跨传统与现代。吴云龙先生在内蒙古艺术学院民族音乐传承驿站工作期间,苏雅既向他学习四胡演奏,梳理演奏技法,并对其四胡艺术进行了系统而深入的口述史研究,并在此基础上撰写出本书。作为身兼专业四胡青年演奏家和民族音乐学理论硕士这一双重身份的作者,既能够以局内人的视角,自如地触及四胡音乐本体,又能以研究者的客位立场,审视和讨论音乐文化问题这也奠定了本书具有更全面更专业的研究想法与思路。
《个体·传统与新世界——吴云龙四胡艺术研究》一书是以吴云龙为研究个案,由历时性“人生史”的展现和共时性四胡演奏“套路”问题的探讨双重思维展开。将人物及其承载的四胡艺术放置在20世纪以来蒙古族社会文化历史背景中,通过对人物成长及技艺历程的剖析,从而探究个体发展与背景文化、当代专业四胡艺术建构与传统之间的联系。同时从四胡音乐的程式性与即兴性及二者之间的关系切入,提出四胡演奏中的“套路”概念,用形态分析和音乐比较的方法,展现口传音乐中普遍存在的“套路”问题,以及个体的风格“套路”与传统之间的关联,从而达到书中所提出的“通过吴云龙的个案来看整个蒙古族四胡艺术传统”的一层目标,并进一步从四胡音乐本体层面研究辐射至整体的历史、社会、文化层面,达到“通过吴云龙个体看近一百年来蒙古族音乐发展整个时代”的二层目标。
在整本书的论述中,是以两层目标的“倒叙”结构展开,共由绪论和六章内容以及书后四个附录组成。作为正文的六章可归为三部分:第一部分为第一章,是对东蒙四胡文化历史变迁的大背景给予分析,将器乐放置在动态变迁中研究,并在整体观中反映变迁历程。第二部分为第二章到第四章及第六章,是对吴云龙人生史与艺术史的探究,体现出文化与语境对个体艺术的塑造,以及个人对文化的传承与发展。第三部分即第五章,为本书的亮点章节,以表演理论“口传性”音乐研究为切入点,作者以局内人视角把“即兴加花”范式变为乐谱文本,专业技艺性分析乐曲是在一个隐形的曲调内进行即兴表演,进而对吴云龙的四胡演奏套路进行探究。这是对个人技艺分析的突破性研究,更对以后学者探究个人演奏“套路”提供了基本范式方法。本文将从以下几个方面对作者如何以人为主线来探究蒙古族四胡艺术的发展以及传统与现代文化的融合进行论述。
一、个体与传统
个体是在传统中被塑造,传统又是通过每一个具体的个体来代代相传并创新发展的。本书的第一个基本视角是通过吴云龙这一蒙古族四胡艺术中的代表性个体人物,来讨论蒙古族四胡悠久的传统以及这一传统在当下的演变。
在时代语境这一大文化背景中,个体与传统之间是什么关系,个体技艺又是如何形成的。根据博特乐图的观点,在对“受”①的主体性与主动性的分析与胡尔奇的技艺传承中指出“在胡尔奇的知识体系与技艺的传承中,知识源是多元的,它既可能是人,又可能是其他形式的媒介。另一方面,在口传世界里的传承渠道是无限多样的。”[1](240)我们可以看出口传艺人的技艺习得,不是在单纯的师徒关系中被建构,而是在多方向中汲取形成。同样,作者在第三章第三节中,对传授吴云龙先生四胡技艺老师的演奏技法进行细致的描述与剖析,从继承启蒙老师连申德的弓法,到吸收扎纳的弹奏、策·仁钦的演奏韵味、阿兴嘎的指法,再到对著名四胡大师孙良的“强弓”与“开弓音头”和图·朝鲁快弓的借鉴,吴云龙进行了兼收并蓄的传统民间音乐技法学习,为我们展现出传统民间艺人的技艺习承方式,以及个体艺术的形成过程。
个人民间音乐的形成,是在不断吸取各流派传统民间艺人的演奏技巧和风格韵味中,融会创新发展成自己的风格技法。正如博特乐图所言:“任何一个歌手都想继承老一辈,但却又追求与同代者的差别。也就是说,他们在继承同一个东西的同时,却又追求一种‘个别’”。[1](36)本书作者对于这些传统技法的分析把握具有条理性,对于四胡的专业术语和技术性分析用局内人的视角解读。同时笔者认为,这些技法的习得,不仅展现出吴云龙如何在吸收传统技法的多样性上,形成自己的演奏套路与风格,更从侧面体现出传统民间艺人的技艺习得方式所具有的“多向性”,并且在不断的吸收与创新之间赋予民间音乐新的生命力,从中更可以窥探到民间传统音乐生生不息的真正动因。
本书第四章,作者论述吴云龙先生的乐曲创作时,不仅结论性的显现出,吴云龙为何会创作出如此之多的乐曲,更为我们展现出,他个人的创作是与蒙古族传统音乐文化底蕴不可分割的。其中第一节,探讨吴云龙对乐曲《白马》的创作细节,即以科尔沁民歌和东盟民歌为素材,运用现代西方作曲技法创作出具有典型蒙古族音乐风格的四胡乐曲。显现出蒙古族传统文化所具有的生命力和创新力,在当今社会的高速发展中,不断地与当代文化融合、发展、创新。在创作中,运用蒙古族传统音乐文化元素,结合西方作曲技法形成了新的艺术形式,更突破了传统曲目的简约化,使体裁更加丰富多元。
在传统与现代文化发展中,个人的艺术发展是桥梁,是纽带。一方面,吴云龙先生在现代社会中所创作的四胡乐曲,展现了传统文化在现代社会中的发展与运用,在传统的基础上进行创新使传统与现代融会贯通,不断推动蒙古族四胡艺术发展前进。另一方面,运用传统元素进行现代四胡乐曲创作,受到观众欢迎,这显现出在时代的变迁中,大众审美发生了多样性的变化,人们的审美和艺术需要在不断嬗变,这促使艺术家在乐曲创作中要更加多样化。同时,就乐曲创新问题而言,这亦是时代思潮的问题,就那一时期文化发展而论,多注重于创新,崇尚于运用中西结合的发展思想,作者敏锐地对当时主流文化的发展趋势进行了适时的阐释与解读。
在第五章传承教育问题的论述中,作者指出,吴云龙作为横跨传统与现代、民间与专业的四胡艺术大师,兼具传统民间四胡“工尺谱”和“口传心授”的学习机理,与现代专业乐曲、乐谱的创作,这使他可将传统与专业的教学方式进行融合创新。笔者认为,现在学校式的教学追求的是普世化、标准化的教学方式,而将吴云龙这种传统带有地方性知识的授艺方式,贯穿于现代教育中无疑是教学的一种创新更是民间“音乐味道”的传承。传统音乐有着顽强的生命力,它既可以以本身的面貌呈现,亦可以通过现代作品得以再现,个体艺术文化来源于传统又扎根于传统,同时又是传统的发展与延伸。作者通过对个体与传统之间互动关系的探讨,来体现音乐文化在传统与现代的变迁中,如何通过个体来延续与发展。传统与现代既是相对,同时又联结在一起,而在这其中人则是文化发展的媒介。通过相关章节的探讨,从吴云龙身上显现出传统文化的传承方式与个体的艺术发展进程,更由二者的双向互动中可以“从小观大”的体现出艺术的发展方向。
二、个人与时代
本书的另一个基本视角是将吴云龙放置在蒙古族四胡百年发展的历史进程中,从“个人对时代的代表性以及时代文化的融入”和“时代对个人艺术的影响”,这一对双向视角来展现吴云龙四胡艺术成就形成的时代背景,讨论吴云龙个人如何顺应时代要求而不断发展的过程。通过本书,可总结出吴云龙艺术生涯的大体轨迹:孩童时代的四胡爱好者,成为少年时代的“小民间艺人”;青年时代的业余文艺团体演员,而后成为专业团体演员,最后成为优秀的四胡演奏家、四胡音乐作曲家;并在后续的发展中他又尝试四胡教学与传承,而在21世纪的时代背景中,他又成为一名国家级“非遗”传承人,这完成的是一个时代到另一个时代的跨越。更是以他为例,来探讨四胡艺术及四胡艺人到艺术家的时代历程,和其背后的原因与动力。
在书中,作者通过吴云龙的人生史来体现个人与时代的关系,以及四胡艺术的发展走向。在个人与时代的关系中,其最明显的一点就是个人身上所具有的时代性,这是时代赋予人的烙印。吴云龙身上所负载的四胡文化具有强烈的时代特征即:传统性与现代性。传统性是指原生文化的原生特征,没有受到任何西方文化的侵染;现代性是指社会赋予四胡特有的文化发展思想,受社会、政治、经济的影响。作为横跨传统与现代的个人,在社会发展中他的人生史就是一个时代的缩影。正如张君仁所说:个人构成社会,社会塑造个人。[2](247)人的一生在每一个阶段所经历的事情皆是在社会整体中进行,而对于个人人生史的研究其实质就是揭示个人与社会的关系。
本书第二章到第四章是针对吴云龙人生史的探究,从传统社会中的小艺人,到社会转型与角色转换,再到从演奏到作曲可总体分为三个部分:在传统社会中学习艺术;在社会转型中完善艺术;在现代社会中创造艺术。作者通过围绕吴云龙先生进行个人人生史和艺术史的双向探究,不仅是展现吴云龙的成长历程,更是探讨个人艺术的发展与时代变迁的关联。在文中作者论述了社会转型对艺人的改变,以及社会推动力的问题。但就艺人的认同转变而言,尤其是吴云龙先生在社会转变后的认同改变,书中并没有进行阐释。笔者认为,社会发展变迁是不可逆的,但音乐艺术的发展和人身份的改变一部分是人的认同转变,是人主动去接受这些转型与变迁,而后产生的音乐与人之间的双向互动。
在本书第四章中,作者指出吴云龙为适应社会变迁中四胡艺术舞台化的需要,将四胡从原以合奏乐曲为主,转变为应时代需求而创作出大量独奏乐曲,或创新性的与其他乐器合奏形成新的音乐风格,以此来说明时代进步可以影响并改变艺术的发展轨迹。其次,作者在对吴云龙先生个人艺术发展的探究中,将他放置在20世纪中叶民间传统音乐发达的时代背景中,在无数的优秀民间四胡表演艺术家的培养下,使他的音乐具有坚实的传统音乐基底,传承着具有蒙古族传统民间音乐文化特征的音乐。作者将个人放置在时代中进行讨论,从而展现个人与时代的关系,通过这样的整体观个体更具全面性特点。同时,笔者认为时代进步更有发展塑造人的作用,四胡舞台化的反向作用是为吴云龙个人提供了发展机会,社会在发展个人也在发展。转型中社会对个人的影响,以及个人对社会转型所作出的一系列应对机制,都可窥探出个人与社会的发展关系,以及时代对个人的塑造推动作用。
在社会发展中,个人在时代中的角色定位,个人与传统之间的联系都可在人生史中展现出来。通过个人来展现时代的艺术,通过社会来研究个人更可在整体观中把握研究的清晰脉络。个人的成长历程中可显现出时代发展的需要,书中吴云龙四胡音乐舞台化的创作和个人身份的转变,亦可体现出时代对人和艺术发展的导向作用。音乐的发展糅合在时代潮流的动向中,通过个人可以展现出一个时代的音乐风格特征。
三、套路与演奏
在本书中,整体上是以历时性的视角进行展开,以个人为核心探讨个体与传统,个人与时代的发展脉络。在套路与演奏中,同样体现出了个体与传统的关系,但作者采取的是共时性的分析研究方法,通过对比吴云龙与孙良与伊丹扎布所演奏的乐曲《八音》,呈现出传统音乐的稳定性、程式性与表现在个体层面上的即兴性、个性化特点。
本书的第三个视角,是基于对蒙古族四胡音乐技法的本质性问题进行分析研究与理论阐释,同时对不同地域流派的区域风格进行总结,进而分析吴云龙先生四胡的演奏套路与个人风格。在第五章中,作者阐释了在内蒙古地区内形成的三大主要区域风格:科尔沁、察哈尔、鄂尔多斯,并对地域风格和流派音乐进行讨论。作者指出,在不同的地域文化中塑造了不同的风格特征,但在蒙古族传统文化的大基底下四胡的演奏技巧是趋同的。地域风格在乐曲演奏时会展现出具有该地域特色的演奏特点,不同地区以其不同的地理、文化建构使演奏风格各不相同又趋同。在具有本土的文化特征中,同时具有演奏风格的统一性又有地区色彩的多样性,而个人演奏风格实质上是地域、流派的缩影。虽然自然生态环境对文化塑造是至关重要的,但笔者认为还需要关注其中的社会因素,例如科尔沁这个特殊的地理位置,社会人口迁移使大量汉族移民流入,致使当地文化出现了浓厚的蒙汉交融的特质,典型体现在四胡乐曲中的的汉族民间曲调上,这均与当地特殊的地域、生活和社会历史存在着密切关系。
书中就何为风格?何又为套路?二者有何区别?这一系列的问题给予讨论。作者提出“个人风格”是听得见摸不着的,而“个人套路”是真实反映在技法上的。风格与套路是既相互联系又有区别的关系,套路可以体现在技法上而风格是表演的外在表现。演奏者在演奏时既有个人风格在,又有个人的套路在,惯用的技法、变奏、指法这都是个人套路的外在反应,而套路会直接影响个人的风格与创作。同时笔者认为,“个人风格”是演奏家运用自己实用的演奏技巧加上自己的审美需要而产生的表现形式;“个人套路”是演奏家自己习惯运用的即兴表演和加花形式而产生的演奏套路,这样对于四胡局外人更简单易懂些。
在本书中,关于吴云龙四胡套路的研究,作者首先从四胡音乐的“口传性”特点切入分析。其“口传性”思考理论来源于口头程式理论和表演理论(Performance Theory)。表演理论认为,口头艺术是一种表演,表演则是一种交流的模式。[3](7)作者提出乐器代替“口”并且传统四胡音乐的创作、表演过程都不依靠于乐谱,是直接在乐器上产生音乐 ,是与“口传”音乐的思维特征相符合的。笔者认为传统民间音乐中讲究的是一个“活”字,它不是固定的,而是灵活多变的,这个“变”与作者提出的即兴性是吻合的。同时作者指出即兴性不是随意的,而是在一定的曲调基础上进行,这也就彰显了四胡音乐具有蒙古族传统音乐的“口传性”特点。在本书中,作者对四胡音乐同一乐曲的多次演奏版本进行比较分析,总结出乐人在演奏中的即兴加花是在一个隐形曲调内进行,这正与博特乐图博士的研究相吻合。博特乐图博士将口头诗学研究方法,运用于蒙古族说唱音乐研究中,提出“曲调框架”这一学术概念。他认为:曲调框架是一种能够与主题相结合并生成“歌”的曲调生成结构。[1](42)同时,民间传统的四胡演奏多是无谱的口传心授,因而同一乐曲经不同乐人演奏会有不同的音乐文本产生,在同一“曲调框架”下,不同乐人的“即兴加花”演奏会赋予乐曲新的文本和生命。这更与洛德的“口头程式理论”[4](145)中“一般意义的歌”和“具体的歌”相对应。曲调背后的隐形框架为“一般的歌”,而每次在曲调框架基础上乐人运用即兴加花,或特有的演奏习惯所产生的不同的、新的文本可为“具体的歌”,不断在变化中发展生成。作者将四胡音乐研究与表演理论相结合的研究方法,是具有突破意义的四胡研究,突破了对四胡音乐一味地乐曲分析和风格总结的研究瓶颈。
同时书中作者指出对吴云龙先生套路的分析是建立在即兴上,而套路又是演奏者即兴加花的依据和规则。基于这样的观点笔者认为,在演奏运行中“即兴加花”就像一组组代码一样,演奏家在“曲调框架”基础上,将“即兴加花”代码进行不同的组合产生新的表演文本。并且每一次的演奏都不是绝对“完成式”,而个人套路则在演奏中具有重要作用,它可以影响到最后表演文本的生成。在实际演奏中演奏者会在保持曲调的基本框架上,根据不同的场合和情感对乐曲做出相应的处理,弓法、指法、变奏等都在随时的变化中,演绎着民间音乐的“活”!例如,书中有一段对《八音》乐曲演奏的评价:《八音》不仅是为欣赏,而对于游刃有余的演奏家来说,它是用来“游戏”的。参与在这种表演当中,演奏者充分发挥自己的能力,体会套路与即兴带来的音乐“游戏”的乐趣。[5](130)
在传统的大河中,传统不是一直静止不变的,它是稳定与变迁共存的综合体。唯有掌握、领悟传统音乐才能够成为传统的代表者,在民间艺人的“套路”研究中亦关联到“即兴性”与“曲调框架”的“以不变应万变”的理论探讨。吴云龙这一个体身上所展现的不是单一的文化表象,而是一个群体的文化发展特质,同时民间音乐的魅力正源于它这种无限的生命力与创造力。
四、经验与启示
《个体·传统与新世界——吴云龙四胡艺术研究》一书是人物的研究,又是音乐和文化的研究,其新颖的研究视角和理论方法的运用,无疑会给读者带来启示。首先,由书中集中探讨的个体与传统;个人与时代;套路与演奏这三个维度的问题中,可以相应的反映出美国民族音乐学家蒂莫西·赖斯(Timothy Rice)的“三维立体研究模式”②:“历史构成——社会维护——个人创造和经验”的借鉴。而本书的写作思路恰恰可以显现出,吴云龙先生在这样的三维模式中如何对民族传统音乐进行创造与发展:在历史的维度上,从出生到学艺的进程中形成音乐技艺的构成;在社会变迁中完善发展音乐;在文化、技艺的积淀中进行个性化的创造。这展现出一个整体的音乐发展机制,进而从个人身上揭示出当代四胡艺术与传统四胡艺术的关联。
第二,作者从整体出发,形成两条平行的探究路线,在生活环境——艺术家——音乐创作的三者关系中,对艺术家个体的成才之路进行探究,并在地域风格——流派风格——个人风格的形成关系中,探索个人艺术风格的发展。在对吴云龙先生四胡演奏套路的研究中,以表演理论的“口传性”切入,指出四胡器乐的“口传性”特点与其本身的内部运行机理不可分割,民间四胡音乐的传承方式为“口传心授”,在音乐表演中具有丰富的即兴性,创作中不依靠任何乐谱,这种乐器的“口传”思维与歌唱的“口传性”相一致。并在“曲调框架”的隐形架构下,其内部的生命力不断运行,使音乐在一直延续、生存、发展。
作者在研究理念上基于对蒙古族传统音乐的发掘与保护,望更本真地保留音乐的原生性,探究其内在的发展规律。诚然,对于书中的方法运用和描写,希望可以做出一些探讨,书中的人物研究是以人生史与口述史相结合的研究方法,以传记书写中夹杂人物口述资料,这样可以生动而全面的将个人人生史展现出来,但同时也会导致某些地方的描写过于繁琐,吴云龙口述资料后,作者又对其复述解释一遍,这使文章的内容出现重复,两种研究方式的结合要重新考虑编写的问题。
《个体·传统与新世界——吴云龙四胡艺术研究》一书具有创新意义和学术价值。借用郭乃安先生的一句话“人是音乐的出发点和归宿,因此要把目光投向人。而把目光投向人,不仅意味着在音乐学的研究中关注人的音乐行为的动机、目的和方式等,还意味着在种种音乐事实中去发展人的内涵,或者说人的投影。”[6](2)人是音乐的创造者和承载者,因此对人的研究至关重要。像吴云龙这样的大师人物,他本身也是一个鲜活的“音乐史”。同时,对于某一个乐种代表性人物的研究是蒙古族学术上至关重要的基石研究,时间不等人,对于健在的艺术大师所承载的艺术资料进行抢救挖掘是当务之急。而本书在蒙古族传统音乐研究中,弥补了对四胡艺术大师吴云龙进行全面深入研究方面的空白。
人不是孤立存在,在发展过程中与社会、历史是不可分割的。对于人的研究更不能只局限于人本身,正如本书是探讨吴云龙个人与时代、传统、社会变迁的关系,在其人生经历中可以折射出时代的特征,而在社会变迁中可以反映出艺术的走向。对于传统民间音乐文化的研究更要立足于“民间”,民间传统文化发展有着顽强的生命力,这不仅限于它的历史,而是有着丰厚民间土壤的滋养。正如书中民间艺人技法的形成,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在不断吸收其他艺人的技法上,创新融合形成自己的演奏技巧,这与现在独尊一师的学校培养模式截然相反。现今对于民间音乐的研究,我们不能停留在固化的思维中,应打开思路多思考音乐形成的背后动因。同时在传统器乐研究中,对以往的平面描述,历史梳理,曲目技法归纳与分析实为浅层探究,民间音乐有其特点“活”性,这也是民间音乐世代发展的内部动力,本书中从“表演理论”出发,对吴云龙个体四胡“套路”研究是对音乐“活”性的探究,它既是个体的特点,也是传统文化的特点。而我们对于传统音乐的研究,更要将目光投向个体、投向人。
注 释:
①博特乐图在《表演、文本、语境、传承——蒙古族音乐的口传性研究》一书的第五章(228页—233页)中对“受”进行了深度的剖析,他阐述了“受”包含为“授受”和“施受”两种,前者为民俗世界传承中双方有明显的教授者和接受者的主体性关系,而后者为无意识的教授和学习者的主动性接受关系。
②蒂莫西·赖斯(Timothy Rice)的三维立体研究模式是在符号学的基础上进行修改,并探讨关于音乐形成过程的问题:人是如何在历史性构建、社会性维护、个人创造和经验中创造音乐的。并且,这个三维模式仍运用梅里亚姆的分析层,但不同点是梅里亚姆的概念、行为、声音是单向,而赖斯的这个三维立体模式是双向的,是相互作用的。
[1]博特乐图.表演、文本、语境、传承——蒙古族音乐的口传性研究[M].上海:上海音乐出版社,2012.
[2]张君仁.花儿王朱仲禄[M].兰州:敦煌文艺出版社,2004.
[3](美国)理查德·鲍曼著,杨利慧,安德明译.作为表演的口头艺术[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
[4](美国)阿尔伯特·贝茨·洛德著,尹虎彬译.故事的歌手[M].北京:中华书局2004.
[5]苏雅.个体·传统与新世界——吴云龙四胡艺术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
[6]郭乃安.音乐学,请把目光投向人[M].济南:山东文艺出版社,19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