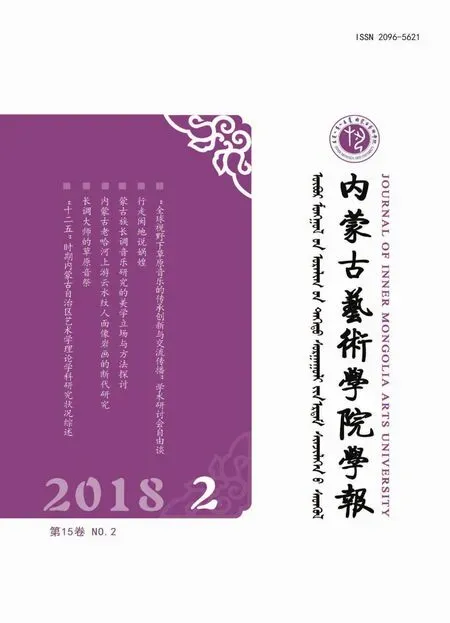精神与情感:中国传统首饰艺术审美与文化的契合会通
2018-07-03赵忠刘程
赵 忠 刘 程
(1.2.南京财经大学,江苏 南京 210023)
一、首饰的涵义:一种被社会认可的“理性审美过程”
在我国古代时期,首饰的取材往往与变化多变的自然界有着很大的依赖关系,并和人工审美材质的探究相结合起来,探索出多种多样的材质和首饰分类。据《后汉书·舆服志》曰:“上古衣毛而冒皮”,用饰物来表达对于美、禁忌、崇拜以及性的装饰。如在浙江余姚河姆渡遗址中发现4只形似辣椒造型并用兽齿制成的颈饰,一方面,这种材质的使用包含对自身体魄和勇敢的赞美,这种饰物赋予了更多原始文化巫术意义。另一方面,虽然说艺术品不能脱离基本的造物属性,但首饰是以特殊的艺术形式构思成一种孕育的物化过程,“因为这是一件无比重要的事实,……任何艺人都对自己的媒介感到特殊的愉快,而且赏识自己媒介的特殊能力。这种愉快和能力感当然不仅仅在他实际进行操作时才有。他的受魅惑的想象就生活在他的媒介能力里;他靠媒介来思索,来感受;媒介是他的审美想象的特殊身体,而他的审美想象则是媒介的唯一特殊灵魂。”[1](31)
中国传统首饰艺术所使用的材质主要包含有金、银、玛瑙、绿松石、铜、竹子、骨、玉、蚌等。艺术家就是运用材料进行生命活动的再创造,一件作品的诞生就是一个幻想构造的孕育过程。按照首饰的实用功能性可分为六大类。即:发饰(簪、钗、梳篦、扁方、步摇、花钿、华胜等)、耳饰(耳环、耳坠、耳珰)、项饰(金项圈、璎珞、项圈锁、长命锁、筒状锁、银质挂件、别针、纽扣、领扣等)、手镯(壁钏、金银钏、金银镯、戒指)、佩饰以及服饰等品类。
二、物化的历史遗存:中国传统首饰文化空间与多样性的本源回溯
原始社会的首饰艺术是介于感性基础上的拜神活动,而商周时代则是我国青铜艺术达到顶峰的时期,也是承载着描绘人的内心思维活动的外在表现物。那个时期首饰艺术被作为青铜艺术的一个种类,也凸显着人类对于技术与材料的检视。“它运用的语文这种弹性最大的材料也是直接属于精神的,保留最有能力掌握精神的旨趣和活动,并且显现出他们在内心中那种生动鲜明模样的。”[2](19)随着大规模丝绸的生产,首饰文化也渐渐地形成生产与佩戴的制度化和社会化。那个时期,首饰艺术是作为一种区分尊卑贵贱的礼仪象征功利性而存在的,不但有阶级的等级内涵风韵,而且还赋予这些饰物宗教性的乌托邦理想。《礼仪·土昏礼》:“女子许嫁,笄而醴之称字。”商周时期首饰中的人文精神更加关注于等级观念下的人生主题,去探讨新的“肉体的形而下”的鄙俗化和对人性的亵渎,无论高堂还是社会制度,这时期首饰意义最主要的是裂解了在原始社会神性的基础去控制人们的行为举止与观念。
到了秦汉阶段,儒学的核心价值观的提出适合了这个时代为君主服务的观念,并影响与改变了春秋战国时期的车途异轨、衣冠异制的局面,“礼仪之邦”的教化则使得首饰文化肩负着让社会的各种行为规范的“内化于心”。再加上与西域加强了交流和沟通,人们的审美指向和构建逐渐“调适着与根深蒂固的入学关系,加之教人救赎的佛教给人哲思。”[3]首饰艺术在这时期大量地在各个阶层中出现,实用化的首饰用品在这时期演变为塑造贵族妇女、体现财富、美化发饰、象征信物的重要修饰体。如重庆明墓出土的金发钗以及湖南长沙马王堆汉墓帛画中的墓主人头上佩戴的缀有珍珠饰品的步摇最为典型。
隋唐是中国封建社会一个富裕而又强大稳定的时期,社会安定、人民生活富裕,文化高度交流和融合。这个时期的儒学教义也经历了被批判、打倒和重新焕发生机的局面,为首饰文化在不同阶层的发展提供了契机。隋唐时期的妇女,把雍容华贵、雅致的咏叹、追求瑰丽美艳的饰物,通过不同种类、不同材质来表现审美内涵的人生意味,把更能超越一切“无我”的根基作为“展示自己的外部动作和内心活动。”[4](154)如唐代的发饰品种就有“簪、钗、梳、篦、步摇、翠翘、金银宝钿和搔头等。”[5](17)品类已经超越了商周秦汉,并突显对不同人性精神和宗教制度的激活。隋唐以降,首饰的实用已不再是这时期主要的纲领性的制度了,而是鲜活的理性与感性的相互交融的人生价值观。如新疆吐鲁番阿斯塔那墓出土的绢画中饰花钿的妇女,以及广州皇帝岗出土的唐代发钗和周昉《簪花仕女图》中的侍女所佩戴的项圈。如在唐·杜牧《樊川集》三《代吴兴妓春初寄薛军事》中描写女性“雾冷侵红粉,春阳扑翠钿。”在敦煌莫高窟第98窟壁画中的三位饰面靥的女子头戴巨型的凤凰式样的发钗以及步摇,梳高髻,并饰以满头繁缛的发饰。可以说这种炫丽多彩的大唐理性化与哲学化运用首饰艺术来充实民族自身的审美意蕴,大大促进了人格与唯美的道德视阈化。
宋代在首饰造型、形式、装饰以及材质等方面较唐代更显内敛并依然继续继承唐代旧制,对女子来说首饰在其日常的梳妆打扮过程中所起的作用非常重要。在马端临的《文献通考》中记载:“皇佑元年诏,妇人所服冠,高毋得逾四寸,广毋得逾一尺。”[5](23))宋代女性所佩戴的首饰在品类上花样增多,官营的首饰作坊在制作材料和造型上更显得珠光宝气,气势逼人。宋代女性与儿童佩戴的饰物除簪、梳、钗、璎珞外主要还有项圈、长命锁、银质别针、儿童银质挂件、梳,其材质有象牙、兽角、玳瑁、金、银、玉等等。如敦煌莫高窟壁画中妇女头上用金银珠翠制成的“冠梳”。据陆游《入蜀记》记载,西南一带的妇女,“未婚嫁者率为同心髻,高二尺,插银钗至六支,后插大象牙梳,如手大。”[5](17)如宋代《晴春蝶戏图》延伸的银质戒指三枚以及四川成都双流南宋墓出土的银质手镯等。如“江西彭泽北宋易氏墓出土的半月形卷草狮子纹银梳,存有唐代遗韵。”[5](25)此梳在梳子的中段錾刻有卷草纹和狮子造型,狮子嬉闹在卷草纹中,显得玲珑美观,上部刻有一些植物纹饰,雕刻精细,富丽堂皇。宋代女性不但追求时髦,而官方更加提倡简朴,反对过于华丽,宋宁宗时期还把宫中妇女所拥有的各种首饰饰物付之一炬,以表示其对于奢侈之风的反感。如在宋代,银质手镯失去了大唐的富丽堂皇的时代精神,取而代之的是“以生命的呼唤写出了真正的诗篇,从而使作品由世俗的浮华走向深挚的人生慨叹,并对天道人事展开寻绎。”[6]
明清是中国封建社会最后两个专制、统一的王朝,两个时代饰物的材质、图案以及造像更加趋向日渐式微和吉祥寓意,由民间的艺术活动形式转变为官作坊,在保留唐宋的某些特征前提下,在观念内容上转向世俗正统化:“由元代规定的‘顾姑冠’回到汉宋以来的戴凤冠、着霞帔的装扮。”[7](116)如北京定陵出土的皇后凤冠。首饰的使用也区分不同的人群,这样就产生了种类的多样性,制作工艺更加精致,如錾刻、花丝、镶嵌以及鎏金等。宝石、玛瑙、翡翠以及珊瑚等贵重材质运用到宫廷首饰文化中,反映出浓郁的等级世俗情怀。而民间首饰文化多以银质材料为基础。据(清)张廷玉的《明史·志卷067志第四十三·舆服三》记载:“今群臣既以梁冠、绛衣为朝服,不敢用冕,则外命妇亦不当服翟衣以朝。命礼部议之。奏定,命妇以山松特髻、假鬓花钿、真红大袖衣、珠翠蹙金霞帔为朝服。以硃翠角冠、金珠花钗、阔袖杂色绿缘为燕居之用。一品,衣金绣文霞帔,金珠翠妆饰,玉坠。二品,衣金绣云肩大杂花霞帔,金珠翠妆饰,金坠子。三品,衣金绣大杂花霞帔,珠翠妆饰,金坠子。四品,衣绣小杂花霞帔,翠妆饰,金坠子。五品,衣销金大杂花霞帔,生色画绢起花妆饰,金坠子。六品、七品,衣销金小杂花霞帔,生色画绢起花妆饰,镀金银坠子。八品、九品,衣大红素罗霞帔,生色画绢妆饰,银坠子。首饰,一品、二品,金玉珠翠。三品、四品,金珠翠。五品,金翠。六品以下,金镀银,间用珠。”如北京海淀区青龙桥董四墓村明墓出土的明代累丝镶嵌宝金钗,此件饰品采用御用金色,运用累丝、镶嵌、錾刻等工艺加工而成,钗中焊接了一个金钱盆,配上玛瑙,色彩夺目,意趣高远。在装饰题材上,人物故事、福禄寿、神话、动植物(花草为主)、龙、凤、麒麟等母体纹样被錾刻工艺嵌进饰物的表面物质体中。如清代福建地区的银器仕女游春银配饰、香包式鎏金银挂饰以及长命富贵莲生贵子银锁等等都是比较著名的作品。除了以上的题材之外还有莲生贵子、八仙过海、望子成龙、状元及第、白蛇传等具有程式化的吉祥故事教化题材。作为强势文化的载体映入明清主题易趣的具体物像世态的观照中,这种观照可以说典型地反映了人性的解放和多元文化的艺融,消解了宫廷与民间无法克服的审美趣味,促使着各自的审美趣味观推动饰物向独立的“以意为主”的个性情感脉络发展,从而形成内容与形式、实用与装饰相契合的并充满思想品质为载体的视韵精神氛围。如清代的一路连科如意银锁,这是一件祈福孩子科举及第和平安祥达的银质配饰。在一个底纹满铺由数个球型物连接起来的银锁,造型别致,把吉祥文字和图形有效地结合了起来。整个锁的主锁用錾刻的工艺手法刻出莲花、鹭鸶鸟和四个吉祥文字“百家保锁”,整个主锁呈心型。这种将极为精神性的图案与现实生活中的世俗性结合在一起,是我们民族所独具特色的一种品格。随着社会的发展,民国以后,我国的服饰逐渐西化,一些装束已经不复存在,女性的装扮也逐渐简洁,一些佩戴别针和耳坠风俗习惯的区域逐渐被排挤到农村。如民国时期的这件双寿桃献寿银锁,此饰物由錾刻的桃叶和双桃,右侧錾刻有象征“福”到的蝙蝠和祥云图饰,整个银锁表达了作者对生活的美好期盼。

图1. 三娘教子錾花银锁①

图2. 一路连科鎏金如意锁②
三、社会现实的诉求∶“祈福纳祥”饰样存在的意义
中国传统首饰艺术是我们整个民族智慧和历朝历代优秀的艺术家心血的共同结晶,也可以说,它是传统文化精神的主要承载物和表现物,他们以吉祥情感、未经世俗渲染的视界来呈现不同民族的思维状态。其艺术创造力和古典意识已经超越某个时代、阶级、民族、区域,颠覆和消解了人文理性化的美学诉求,当然,传统世界里对首饰艺术中的情感描写是一个动态的、是被理解的经典思想,以及它对现实世界认知阀限的“怯懦”以及对主题的深层次指涉。
“祈福纳祥”是中国传统民俗感情中一个重要的表现主题,特别是在传统首饰艺术图案中,他们把生活场景中的诗情画意运用在外部空间的一些形象与手法上,形成了具有时代内涵的统一融合体,这里面也牵涉到区域风俗所带来的不同核心价值观。所以,它是运用图案来传达对神灵崇拜和连通已有的思维定势。
据(晋)吕忱的《字林》曰∶“祯祥也,福也。”在国人的人生世界中,对于“吉祥与福气”有着鲜明的民族情感和理性思考认知,尽管社会的某种文化性只是存在于传统的乡村价值观和乡土风俗体系中,但是吉祥文化在同时推进民俗文化的柔性精神需求的心路历程中,似乎不经意间将这种文化的媒介饰物赋予所呈现的形态中,并渗透到社会的每一个体的内心深处,从本质上说,“祈福纳祥”就是一种神思和境界,它是人们将这种目标作为传统中国人一辈子的所追求极致的远大志向,化作为尊崇几千年的文化道德品格。这种现实的诉求反映了人们对未来生活美好的期盼。
祈福纳祥装饰归纳起来有以下几种:动物纹饰,狮子纹饰、麒麟、龙、凤、鸭、松树、蝴蝶、仙鹤、蝙蝠以及青蛙等。狮子纹饰为最为常见的纹饰装饰,它在汉代从波斯传到中原之后,被历朝历代大量使用。如六朝中的陵墓雕刻中的辟邪、石禄以及麒麟等,都是以“狮子”为造型基础,它象征着降妖除魔、官位亨通、吉祥如意的意旨。如清代的麒麟银质挂件,整个挂件长385毫米,主件高80毫米,主件上錾刻有一只瑞兽——麒麟,整体作漫步状,身上有一男童双臂抱有如意,雕刻精美。下坠是錾刻程桃形符号,象征着平安。植物纹饰这类图案运用纹样的谐音或者该图案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民俗意义,来阐述媒介连通内外世界的传承性,这类纹饰主要有花卉纹饰、牡丹、莲花纹、葫芦、桃子(树、叶)、竹子等。植物纹饰经常伴有动物纹饰一起出现。如民国时期的双寿多子银佩饰,整个银饰有一只下坠的石榴和两个寿桃组合成“八”字造型,寿桃寓意着人生长命百岁,而石榴里面有很多的种子则象征着繁衍后代的理想和现实诉求,在寿桃表面錾刻有深浅不一的花纹,造型奇特,寓意深邃。
显然,“祈福纳祥”文化本身在充分强调装饰的文艺本质语言外,似乎并没有完全抛弃图案本身所拥有的内涵意义和本质属性。在受制于特定民俗情感环境与语义形象的同时,对民俗、区域伦理视角所形成的寓意范畴和理念话语实施了大量的视觉图形的“转换”。如民国时期山东的鹿鹤同春银挂件,整个挂架的形象塑造保持了鹿和仙鹤本身的形态,把鹿的矫健和鹤的体型修长生动展现出来。为了实现图像的转换,在两种动物中间穿插一种植物,质朴的民风和吉祥如意的概念通过符号、虚拟环境中产生出来,它“会营造出特殊的氛围,而使参与者在哀伤、敬畏、光狂欢与审美的不同情境中获得行为规范、道德训诫与心灵净化。”[8]这种独特的文化韵味为各朝各代首饰文化的审美功能奠定了包容性的人文基础。如这件清代时期的富贵平安银佩饰,整个饰品有上下两部分组成,主体运用花瓶、双鱼以及牡丹錾刻而成,花瓶寓意着平平安安,牡丹象征着富贵,双鱼借谐音与“余”的同音。主体纹饰下坠饰有“喜鹊登梅”图案的古钟和錾刻有桃叶的寿桃,运用焊接的工艺把几部分连接起来。整个挂件制作工艺精湛,塑造物象的手法简洁明了,不愧是一件难得的佳品。

图3. 麒麟送子银锁③
四、结语
中国传统的首饰艺术是反映和映衬中国人的民间风俗信仰的社会文艺与历史体系,它是陪伴着人类服饰社会向前发展的一种社会意识形态,它倾听着有意味的个性创造下的生存境界,呼唤着从原始社会的人类本源精神到民国乡土气息视角的生命感悟,将独特的首饰文化的空间与实践寄予更广泛的精神自觉世界,它是我们现代首饰设计的“故乡”,是“关于自己的根的一次次探究……,它也是一个精神故乡和一个文学故乡。在它身上寄于我的怀乡和还乡的情结。”[9]
注 释:
①图1为《三娘教子錾花银锁》,图片来源:唐绪祥,王金华:《中国传统首饰》,北京:中国轻工业出版社,2009年版。
②图2为《一路连科鎏金如意锁》,图片来源:唐绪祥,王金华:《中国传统首饰》,北京:中国轻工业出版社,2009年版。
③图3为《麒麟送子银锁》,图片来源:唐绪祥,王金华:《中国传统首饰》,北京:中国轻工业出版社,2009年版。
[1]鲍桑葵,周煦良 翻译.美学三讲[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3.
[2]黑格尔,朱光潜 翻译.(第三卷下册)美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
[3]张维青.魏晋六朝时期玄学思想与审美观照的契合会通[J].济南:齐鲁艺苑,2005(3).
[4]李建军.小说修辞学研究[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
[5]杭海.妆匣遗珍[M].北京∶三联书店出版社,2005.
[6]袁济喜.论六朝文学精神的演化[J].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1(1).
[7]周天.中国服饰简史[M].北京:中华书局,2010.
[8]汪政.乡村文化建设中本土资源的文学书写[J].江苏社会科学,2009(1).
[9]周新民,苏童.打开人性的皱折-苏童访谈录[J].小说评论,2004(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