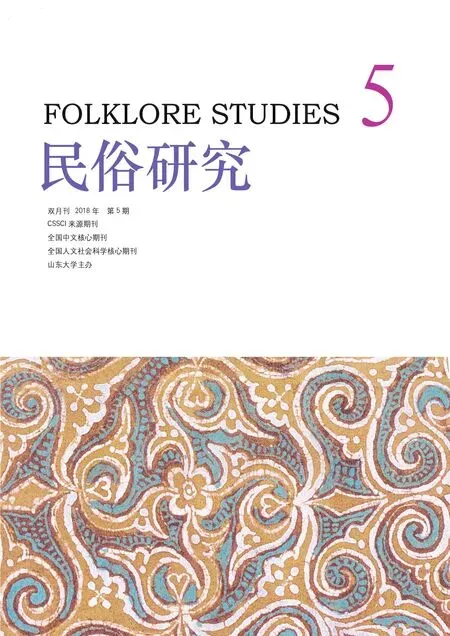现代性的两面性与民俗艺术的传承困境、机遇及其应对
——以湖州石淙蚕花为例
2018-01-24季中扬
季中扬
“所谓‘民俗艺术’,系指依存于民俗生活的各种艺术形态,作为传承性的下层艺术现象,它又指民间艺术中能融入传统风俗的部分。”*陶思炎:《民俗艺术学》,南京出版社,2013年,第1页。早在20世纪20年代,日本学界就开展了民俗艺术研究。*约在1926年的年中,数十名日本民俗学者、文艺家、美术家、建筑家、音乐家共同发起、成立了一个小型学术团体,取名为“民俗艺术之会”。该会于1927年1月创办了自己的学术刊物《民俗艺术》。此后,“民俗艺术”的概念得到了广泛传播和接受。1940年代,国内学者常任侠*常任侠:《民俗艺术考古论集》,重庆正中书局,1943年。、岑家梧*岑家梧:《中国民俗艺术概说》(1944年),《中国丛书》选印:《中国艺术论集》(影印本),上海书店,1991年。等也提出了民俗艺术范畴,但并未做系统研究。20世纪90年代,尤其是新世纪以来,民俗艺术研究得到了学界重视,出现了一些系统性的理论著述。*如张士闪、耿波:《中国艺术民俗学》,山东人民出版社,2008年;陶思炎:《民俗艺术学》,南京出版社,2013年。晚近十来年,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程的影响下,民俗艺术的活态传承问题成为民俗艺术研究领域的焦点问题,如黄静华、陶思炎讨论了民俗艺术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活态传承的要素*黄静华:《民俗艺术传承人的界说》,《民俗研究》2010年第1期;陶思炎:《论民俗艺术传承的要素》,《民族艺术》2012年第2期、2013年第1期。,王伟、卢爱华提出了民俗艺术产业化问题*王伟:《民俗艺术产业化的路径研究》,《学术论坛》2010年第8期;卢爱华:《民俗艺术产业化发展探析》,《东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4期。,赵跃、朱冠楠、杨旺生等分别基于韩国四物游戏、苏州胜浦宣卷的个案研究,讨论了民俗艺术的现代功能转换与价值转向等问题*赵跃:《文化传播视角下民俗艺术的传承与再生产——以韩国四物游戏为例》,《民俗研究》2017年第3期;朱冠楠、杨旺生:《民俗艺术的现代性遭遇——以苏州胜浦宣卷为例》,《江苏社会科学》2017年第4期。。诚然,在社会现代化过程中,民俗艺术所依存的社会根基坍塌了,民俗艺术成了“文化遗产”,从“生活文化”变成了“民俗艺术”,问题是,究竟是怎样的文化逻辑与意识形态促成了民俗艺术成为“文化遗产”与“艺术”的?民俗艺术自身又是如何应对社会文化现代变迁的?这是一个需要进一步追问的问题。
一、现代性的两面性
民俗艺术由“百姓日用而不知”的日常生活文化变成了“民俗艺术”“文化遗产”,从思想意识层面来看,这与现代性观念密不可分。
现代性作为一种思想观念,源于社会的现代化进程。吉登斯就认为,现代性是一种“后传统的秩序”,“意指在后封建的欧洲所建立而在20世纪日益成为具有世界历史性影响的行为制度与模式”,“大略地等同于工业化的世界”。[注][英]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与自我认同》,赵旭东、方文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第3、16页。整个社会由农耕社会进入到工业社会,民俗艺术赖以存在的社会基础彻底改变了,在人们观念变革之前,民俗艺术事实上就已经被历史所否定、抛弃了。不仅是农耕社会中使用的竹编、草编、藤编、麻编、线编、棕编、柳编的各种日常生活用具,纺织、印染、刺绣的各种服饰,精心雕饰的木器、竹器、陶器、瓷器等,已然被工业制品所取代;诸如年画、剪纸、傩戏、傩舞、农谚,以及完全从日常生活中分离出来的、具有高度审美性的地方戏、木偶戏、皮影戏、评书、快板、鼓词、琴书等,由于离不开农耕社会的文化结构与文化空间,也大都从日常生活中消失了。在社会历史的滚滚车轮下,民俗艺术似乎只能有一种命运,然而,由于现代性意识,我们看到了民俗艺术历史命运的转机。
现代性作为社会现代化的产物,它是社会现代变革在思想意识层面的反映,因而它首先表现为一种对过去与传统的否定意识。正如唐文明所言,“现代性首先是一种时代意识,通过这种时代意识,该时代将自身规定为一个根本不同于过去的时代”[注]唐文明:《何谓现代性?》,《哲学研究》2000年第8期。。现代意识是通过否定“过去”确立起来的,“现代”成为一种观念,其本身就意味着这是一个断裂的时刻,即现在与此前是不一样的。在现代意识中,过去习见的各种事物往往成了历史陈迹、奇风异俗。正如约翰·费斯克所言,在现代文化空间中,只有大众文化是“我们的”,民间文化则是“他们的”,有着一种原初的陌生性,“郊区家室中‘农民的’篮子或是‘土产的’陶器,总带着某些异国情调”。[注][美]约翰·费斯克:《理解大众文化》,王晓珏、宋伟杰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第179页。也就是说,在现代意识中,人们不会再相信传统民俗艺术携带着某种特殊的“灵韵”,能够沟通日常生活世界与神圣世界,相反,“祛魅”之后的民俗艺术却显露出了一身不合时宜的土气。在这样一种现代性意识中,我们显然看不到民俗艺术历史命运的转机。
其实,现代性是有着两面性的,它在否定过去、传统之时,又可能“发现”或“发明”过去、传统新的价值,因为现代性是一种新的价值观念,一切传统事物都面临着“价值重估”。在这种现代性意识中,人们首先看到了民俗艺术作为过去时代“遗留物”的历史价值,进而赋予其“文化遗产”的新身份。只有“发现”或“发明”这种新价值,人们才会乐于购买、收藏这些不合时宜的东西。虽然过去的东西总是有一定历史价值的,但是由于民俗文化的历史叙事大多是模糊、错乱的,人们向来不太看重民间遗留物的历史价值,更遑论当代民间艺人的制作了。这也就是说,现代性意识虽然赋予了民俗艺术“文化遗产”价值,但却难以高估其遗产价值。其次,只有在现代性意识中,人们才可能主要从艺术、审美角度看待民俗艺术,民俗艺术才有可能获得“艺术”身份。在传统社会中,民俗艺术也是具有一定审美价值的,但这种审美价值是依附、从属于某种实用价值的,只有现代性意识才能生发出纯粹的审美观念,才会将“对象”从语境中完全剥离出来,仅仅作为一种“表象”来观照,在这种“分离式”“对象化”的审美方式中,民俗艺术才可能脱离日常生活文化,成为独立的审美观照对象,进而成为“艺术”。事实上,我们看到苏绣、剪纸、年画被装裱、放置在画框中,成为一种镜框艺术,就是这种审美现代性的产物。但是,需要指出的是,由于审美现代性是以学院的、精英的艺术观念看待民俗艺术的,又难免贬低民俗艺术的审美理想与艺术价值。
明了了现代性的社会基础及其两面性,就很容易理解民俗艺术在现代社会中的传承困境及其机遇了。在社会现代化过程中,民俗艺术失去了其依存的社会基础,大多数民俗艺术都丧失了其固有的社会与文化功能,很难依靠自力传承与发展下去。其固有功能丧失同时意味着这些民俗艺术失去了接受群体,即使投入大量人力、物力将其保护起来,延长其生命,也很难融为现代文化要素。正如马凌诺斯基所言,一切文化要素“一定都是在活动着,发生作用,而且是有效的”[注][英]马凌诺斯基:《文化论》,费孝通译,华夏出版社,2001年,第15页。。如果在新的文化框架中旧的文化形态不是活动着的、有效的,而是生硬地附着在新文化之上,即使在一定时间内保持着所谓的“活态”,也终究很难融入到新文化的血肉、肌理之中。因而,民俗艺术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之关键是解决其现代功能与价值问题,现代性的两面性恰恰为解决民俗艺术的现代功能与价值问题提供了思想基础。正是由于现代性意识,民俗艺术才成为了非物质文化遗产,成为了民俗艺术,具有了某种现代功能与价值。因而,如何在遗产价值与艺术价值之间找到结合点与平衡点,可能是民俗艺术在现代社会中应对困境、实现活态传承的关键。下文将通过考察浙江湖州石淙蚕花的当代状况,来具体讨论民俗艺术在现代社会中的困境、机遇及其应对。
二、民俗艺术石淙蚕花的“前世今生”
据农史专家王利华所言,北宋时期,江南蚕业就已发展成熟并逐渐雄踞全国之首,当时两浙路每年向朝廷上供的丝绵占全国总数的2/3。[注]王利华:《古代江南蚕俗述略》,《中国农史》1992年第4期。湖州,明清时期蚕桑产业尤为兴盛,顾炎武曾说:“湖塘业已半为桑田”[注](明)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浙江下》,严佐之等校点,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2416页。;同治年间的《湖州府志》称:“尺寸之堤,必树之桑;环堵之隙,必课以蔬。富者田连阡陌,桑麻万顷”[注]同治《湖州府志》卷二十九《舆地略·风俗》。。蚕桑产业兴盛是蚕桑文化发展的基础,最迟至明清时期,湖州地区就已经形成了丰富多彩的蚕桑民俗文化,包括马头娘娘、蚕姑、蚕花五圣的传说,种桑养蚕的农谚、禁忌,因蚕神崇拜而兴起的庙会,与种桑养蚕相关的岁时节日习俗与人生礼仪习俗等。在这些蚕桑民俗文化中,湖州的石淙蚕花就是比较独特的一种。
所谓石淙蚕花,是一种民间手工艺,就是用彩色的皱纸,做成仿真的花朵。其制作手艺并不复杂,先将皱纸染色,剪成花瓣状,用柴须做成花梗,从花蕊开始,由内而外依次扎制,最后用棉线或丝线扎紧。蚕花的民俗用途主要有三类:一是蚕事期间绑在蚕架、插在蚕门上,或放置在蚕室里、蚕匾上;二是用于婚丧嫁娶等人生礼仪方面[注]石淙当地人结婚的时候会为新娘置办一个蚕花匾,称为“嫁蚕花”。蚕花匾内除了放着寓意吉祥的花生红枣之类外,还放置“小蚕花”,几支小蚕花配上几支桃形果实,称作“开花结果”。此外,新娘头上要戴蚕花,胸前也要佩戴蚕花。石淙之外,杭州一带家有老人是石淙太君庙香客的,儿女结婚时也会来购买“护心花”一类的蚕花。;三是作为妇女的头饰,蚕事期间或庙会活动中戴在头上。民俗文化影响力的核心指标是“讲究”,民众对某种习俗越是讲究,意味着对这种习俗越是看重。过去蚕花的使用是很讲究的,不同场合需使用不同类型的蚕花。根据蚕花用途的不同,传统的蚕花可以分为五种类型:一支单花加一片叶,称“小蚕花”,主要用于蚕妇掸蚕、插于蚕事用具上驱邪、婚丧嫁娶时讨吉利等;由两朵花合成一支,花瓣或叶片上攀附一个蚕宝宝,称“双蕊花”或“蚕宝花”,主要用于庙会、节日插于蚕妇鬓角;花型较大的一种,称“护心花”,庙会时蚕妇佩戴于胸口;四五朵蚕花扎于一枝,称“埭头花”,旧时流行用作妇女的发簪;两朵花形较大的锯齿状蚕花上下排列,周边绕有小型花片,称“蝴蝶蚕花”,庙会时持在手中。
关于石淙蚕花的起源,在民间叙事中,有两个传说。一是蚕花娘娘的传说。据说,蚕花娘娘在清明节化作村姑踏遍了含山[注]含山在湖州善琏镇,被视为蚕桑圣地,石淙镇与其毗邻。每寸土地,留下了蚕花喜气,此后谁来脚踏含山,谁就会把蚕花喜气带回去,得个蚕花廿四分[注]蚕花有三种意涵,一是仿真花朵,二是蚁蚕,三是指蚕茧。“蚕花廿四分”是指蚕茧双倍好收成。,因而,在含山庙会期间,不仅桐乡县、德清县境内的乡民,乃至嘉兴、吴江等地的蚕农也前来“轧蚕花”[注]“轧”为吴方言,是“挤”的意思。“轧蚕花”这个俗称突出了庙会期间人多、热闹的特点。可能出于弗雷泽所谓的“相似率”原理,在民俗文化心理中,往往认为越热闹,事业越红火。。前来“轧蚕花”的蚕妇们纷纷争购石淙人出售的彩纸蚕花,簪戴在头上,以祈求吉祥如意。二是西施的传说。相传,西施从越国前往吴国,途经杭嘉湖蚕乡时,把美丽的花朵分送给蚕妇,预祝蚕花丰收,那一年,果然是家家蚕花廿四分,从此相沿成习,杭嘉湖蚕乡的蚕妇们就有了簪戴蚕花的习俗。
民间叙事大多渺不可考。从文献资料来看,至少在明代就已有蚕花买卖。明末清初湖州人董说在《村居述》一诗中说:“耆旧集中看故国,田家谶里证残经;卖花人到话新事,除却看山总厌听。”[注](明)董说:《丰草庵诗集·卷七》,清初刻本影印版。乡村所卖的花,大概不是真花,而是纸扎的蚕花。清代留下的相关记述尤为多,如朱恒《武原竹枝词》:“小年朝过便焚香,礼拜潮音渡海航。剪得纸花双鬓插,满头春色压蚕娘。”其后注释曰:“正月三日为小年朝,习俗以是日航海至普陀烧香。戴纸花,号蚕花。”[注](清)朱恒:《武原竹枝词》,清刻本。浙江省嘉兴市嘉善县图书馆藏。又如光绪《石门县志》:“春时,妇女烧香,鱼贯于路……归时率买纸花攒髻,曰:买蚕花。”[注]嘉庆《石门县志》卷二十四《补遗》。清代崇尚蚕花习俗影响很深,甚至僧界也不免此俗。据湖州人汪日桢《湖蚕述》所言,“俗于腊月十二日、二月十二日礼拜经忏,谓之蚕花忏。僧人亦以五色纸花施送,谓之送蚕花”[注](清)汪日桢:《湖蚕述》卷二“浴种滃种”,蒋猷龙注释,农业出版社,1987年,第35页。。石淙蚕花艺人回忆说,1950年代前,一些石淙村人带着蚕花外出到富阳、绍兴、嘉兴、无锡、塘栖等地“送蚕花”,换取一些粮食、衣物来补给家用。有此可见,由于民俗文化的巨大影响力,石淙蚕花曾经是乡村经济中一种有影响力的手工业。
1980年代之后,中断多年的石淙蚕花又逐渐复兴起来,尤其是2005年国家启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程以来,石淙蚕花得到了地方政府的高度重视,不仅给予传承人生活补贴,还建立了石淙蚕花文化馆,中小学开设了蚕花校本文化课程,每周邀请蚕花传承人前来授课。此外,蚕花文化馆还成立了“缤纷小蚕花社团”,每月邀请蚕花传承人前来为社团成员授课两次。石淙蚕花与众多民俗艺术的处境不同,并非仅仅在“保护圈”内完全依靠“输液”而活着,它仍然保有一定的消费市场,主要依靠自力保持着良性的活态传承。当下石淙蚕花制作主要分布在石淙镇的集镇、南坝村、花园湾村、羊河坝村、银子桥村、姚家坝村、镇西村、石淙村等地。“据石淙村党总支书记李彬彬介绍,蚕花制作已成为该村一个不小的产业,300多户人家有一半以上都在做,有的人家一个清明节就可收入四五千元。像北街自然村,家家都在做。”[注]冯旭文:《石淙蚕花:年年花开盛》,《浙江日报》2015年1月6日。石淙蚕花的销售遍布杭嘉湖地区,每年清明节前,蚕娘们纷纷带着精心扎制的蚕花,前往含山、桐乡等地销售,更有蚕娘将蚕花带至杭州灵隐寺、余杭、萧山等地庙会上售卖。每年农历正月十一、清明节、九月十六均有来自苏州、嘉兴、嘉善、德清等地数以万计的香客慕名前来“石淙太君庙”进香朝拜,购买石淙蚕花。据说,石淙镇目前还有二十家左右从事蚕花销售的门店,我们在调研中看到了五家,问了一下经营情况,普遍都说一年下来毛收入20万元左右,纯利润高的可达五、六万元,低一些的也有三、四万元。也就是说,时至今日,石淙蚕花还保持着一种比较良好的活态传承状态。
三、石淙蚕花对现代社会变迁的应对
由上文叙述可见,石淙蚕花这种民俗艺术根源于杭嘉湖地区的蚕桑业。在蚕桑业发达时,为了祈求吉祥,蚕事中大量使用这种民俗艺术,蚕农对其也格外虔敬,在蚕室中摆放蚕花时甚至要举行隆重的祈禳仪式,当地人称之为“请蚕花”。在庙会、节日、人生礼仪中使用蚕花也是为了祈求养蚕顺利、蚕茧丰收,而不是为了审美性的装饰。据蚕花艺人回忆,旧时,石淙镇举行太君庙会活动的时候,不戴蚕花的人或祭品是不允许进出太君庙的,认为这是对三位亲姆[注]据当地民间口头所传,太君庙始建于南宋咸淳十年(1274),原名协顺庙,为祭祀北宋安徽泗州县兵马都监陆圭而建。陆圭开盐船至石淙,在姚家入赘,生显济、通济、永济三女。宣和年间,石淙发生严重灾荒,陆圭开仓放粮,救活了无数饥民。后来,陆圭率军队在浙江桐庐的七里滩打败了方腊率领的农民起义军,但在率师返回钱塘江时,因船沉而被淹死。陆圭死后,朝廷封他为广陵侯,后又被封为“南堂太君镇海潮王”,在石淙的石淙荡东岸建庙并赐庙号“协顺”,其妻姚氏被封为锦花夫人,三个女儿分别被封为显济、通济、永济夫人,人称大太君、二太君、三太君。因此,民间称“协顺庙”为“太君庙”。民间相传,陆圭夫妇和三个女儿是婴幼儿童的保护神,亲昵地称呼显济、通济、永济夫人为太君亲姆,认为三亲姆尤其灵验。据说,农历正月十一和九月十六是陆圭及其三女儿生日,因此,每年这两天都要举行盛大的庙会。和镇海潮王的不恭敬。含山庙会时,见蚕花娘娘也要戴蚕花,表示对蚕花娘娘的尊敬和信诚。然而,在现代社会,湖州地区已经很少有人从事蚕桑业了[注]当代湖州地区蚕丝加工业仍然比较兴盛,但其蚕茧、生丝等原料大多不是本地所出,而是来自广西、贵州、云南等地。,蚕桑民俗文化的影响力已经衰微,在这种情形下,石淙蚕花还有一定的消费市场,还能保持良性的活态传承,这是为何呢?
我们发现,这首先与石淙蚕花所处的文化空间密切相关。石淙镇周边有诸多庙会,而且这些庙会在历史上大都与蚕神信仰密切相关,尤其是石淙镇的太君庙会与邻镇的含山庙会。这些庙会成了当下石淙蚕花的重要销售市场。南京艺术学院李立新教授在考察含山蚕花节/庙会后写道:“站在含山塔顶远眺,只见从蚕花路到古运河两岸,五彩缤纷的蚕花将整个含山地区妆扮成一个花的海洋,歇波亭、之字道、蚕花地、石孔桥以及商贩、蚕民、村姑、孩童、游客……全被淹没在蚕花之中了。”[注]李立新:《蚕月祭典——湖州含山蚕花节考察记行》,《艺术百家》2010年第1期。笔者于2018年4月5日考察含山庙会时发现,李立新教授10年前看到的“花的海洋”已经消失了,虽然还有十来个出售蚕花的摊位,却已很少有人购买。究其原因,可能与含山庙会收取门票,导致当地民众不愿购票上山参拜蚕花娘娘有关。据石淙当地人说,石淙镇太君庙会也是石淙蚕花主要销售场所之一,每一个前来的善男信女都会在进庙前买一朵蚕花,男性信众一般将蚕花插在帽子上,女性信众将“小蚕花”插在发髻上,离开庙会前还会买一些蚕花,用来放在船舷、家门、床沿等处,祈求平安、吉祥。庙会向来是各种民俗艺术汇聚的公共文化空间,庙会期间不仅集中上演小戏、秧歌、傩舞等民俗表演艺术,同时也是剪纸、泥塑、面塑、纸扎等民俗造型艺术的交易场合。在庙会这种即圣即俗的特殊文化空间中,潜藏于人们内心深处的传统民俗意识不自觉地就被激活了,消费传统民俗文化符号成为文化认同的一种易于采用的表征。因而,保护庙会这种民俗,就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空间保护,实质上是在现代文化空间中嵌入了一个特殊的文化“生态壁龛”[注]“生态壁龛”(ecological niche)一词在生物学和生态学中经常使用,是指一个种群在生态系统中,时间和空间上占据的位置及其与相关种群之间的功能关系与作用。贡布里希最早使用这个概念来分析艺术与社会文化系统之间的关系。参见高尚学:《“艺术生态壁龛”:贡布里希的一种独特艺术文化史观》,《社会科学家》2014年第5期。,为传统民俗文化活态传承建构了一个小环境。
其次,石淙蚕花的良性传承也与其不断调适、能够应对社会文化变迁有关。一是功能方面的调适。当下蚕花在保佑蚕桑生产方面的民间信仰功能已经大为弱化,很少有蚕农因蚕桑生产的民俗活动需要前来购买蚕花了,但是,由于民俗文化影响力的惯性,人们仍然认同蚕花是吉祥的,因而在婚丧嫁娶中,清明节祭祖、扫墓时以及庙会上,还在习惯性地将蚕花作为一种吉祥物,尤其是清明祭祖,已经成为蚕花消费的重要事由。人们不仅把蚕花视为婚礼上的吉祥物,而且将其看作爱情的象征物。据说,受到李商隐的“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诗句的影响,在含山蚕花节上,不少年轻人也争相购买蚕花赠送情人,以示对爱情的忠贞不渝。[注]冯旭文:《石淙蚕花:年年花开盛》,《浙江日报》2015年1月6日。此说究竟是否确实,很难验证,但是,这无疑是石淙蚕花的一种新的民间叙事,这可能进一步推动了石淙蚕花文化功能的现代转换。二是价值取向方面的调适。随着石淙蚕花民间信仰价值的弱化,其娱乐与审美价值愈发得到重视。当下庙会上人们争相购买蚕花,与其说是为了祈求吉祥如意,不如说是为了与众人一起娱乐。这些游人中,除了虔敬的香客,很少有人愿意出高价购买传统手工制作的蚕花,适应此需求,市面上销售的蚕花大多是从义乌购买成形的花片和各种零件,然后在石淙组装的“塑料布蚕花”。手工制作的蚕花也并不完全恪守传统,普遍采用丝绸或塑料纸代替皱纸,用铅丝代替柴须梗,这样制作的蚕花不易褪色,花梗质地比较坚硬,不易折断,搬运也比较方便。此外,不少当地人开始购买石淙蚕花作为家中日常装饰,蚕花艺人适应此需要,不仅在材料上大胆变革,而且开始重视艺术设计与创新,推出了满束多枝多叶的“满堂灿”、大朵荷花形状的“莲荷蚕神”,以及单只或一束仿真的玫瑰花等新类型蚕花。很显然,美观、实用,而不是恪守传统,是当代石淙蚕花的主要价值取向。
值得注意的是,当下石淙蚕花一方面在价值取向上讲究美观、实用,开始重视艺术设计与创新,另一方面仍然主要用于婚丧嫁娶等民俗活动与日常装饰,这与完全脱离日常生活、认同“纯艺术”的苏绣等民俗艺术不同。这为我们思考民俗艺术“在日常生活中传承传统”与“审美转向”[注]关于民俗艺术的审美转向问题,可参阅季中扬:《“遗产化”过程中民间艺术的审美转向及其困境》,《民族艺术》2018年第2期。之间能否并行不悖这个理论问题提供了一个典型案例。当地文化站负责人曾对我们说,石淙蚕花材料普通,工艺简单,很难像苏绣、木雕那样成为一种现代工艺美术,因而活态传承的困难较大。其实,用于日常生活的民俗艺术大多材料普通,工艺简单,但这并不妨碍它们成为具有高附加值的现代手工艺术。比如在日本,许多曾是日常生活中使用的民俗艺术都成了珍贵的现代手工艺术。这些日常生活中的民俗艺术之所以能成为现代手工艺术,一方面在于传承人有文化传承意识,另一方面还在于他们有现代艺术理念,能够真正审美地对待自己的手艺。也就是说,能够自觉地在“日常生活中传承传统”与“审美转向”之间找到结合点。这种自觉意识非常重要,而且这种自觉性唯有现代性意识中才能生成。社会文化总是处于不断变迁之中的,并非只有在现代社会民俗艺术才需要不断调适来应对变迁,但唯有现代性意识才能使其调适与应对由不自觉而自觉。
总而言之,正是在现代性意识中,民俗艺术具有了文化遗产价值与独立的审美价值,只有人们自觉地将这两种价值取向统一起来,在传统传承与审美转向之间找到一个结合点,才能更好地解决民俗艺术在日常生活中的活态传承问题,而不是将民俗艺术变成博物馆艺术或画廊中的“纯艺术”。
四、余 论
石淙蚕花与诸多民俗艺术不同,在现代社会中,它由于实现了功能转换,调适了价值取向,仍然能够不依靠外力保护而活态传承,但是我们也看到了其中隐藏的问题。一是蚕花已经不再主要与蚕事相关,还叫蚕花吗?当地非物质文化遗产管理人员就认为,只有庙会上的蚕花才是真正的蚕花,清明祭祖以及家庭装饰用的蚕花并非真正的蚕花,充其量只是一种纸扎艺术而已。其实,任何一种民俗艺术,其功能与形态都是变动不居的,“老辈传下来的”“向来如此”等话语,不过是一种民间叙事,一种文化幻觉。事实上,江南地区簪戴纸花、绢花习俗远比“蚕花”这个名称要久远的多,只是到了明清时期由于蚕桑文化强大的影响力,人们才称各种纸花、绢花为蚕花。其时,很多场合使用的纸花、绢花也与蚕事活动无关,但人们仍称这些花为蚕花,可见“正名”在民间并非什么要紧事。二是当下市场上几乎没有传统的纸扎蚕花,大多是从义乌购进花片组装的,这还叫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活态传承吗?其实,一旦民俗艺术所依附的民间信仰力量弱化,就不会那么讲究传统,其用材、工艺等就会随着社会生活发展而不断变化。我们在调研南京“秦淮灯彩”时发现,现代花灯制作的工艺、用材也没有恪守传统,传承人甚至以不断创新为能事。[注]被访谈人:曹真荣、戴玉兰;访谈人:赵天羽,南京农业大学民俗学专业2016级硕士研究生;访谈时间:2017年11月17日下午;访谈地点:南京市秦淮区大油坊巷75号南京东艺彩灯厂。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角度来看,这是符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国际公约》提出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在各社区和群体适应周围环境以及与自然和历史的互动中,被不断地再创造”这个原则的。因而,现代蚕花制作是否使用传统的材料、工艺、花型,这并非是关键问题。关键问题在于,不管是传承人,还是一般从业人员,仅仅依靠社会需求,而不是外力保护而让蚕花艺术活态传承下去。我们在调研中发现,当地人在日常生活中会购买蚕花用于家庭装饰,这就意味着人们已经开始主要从审美方面看待蚕花艺术了,蚕花艺人能否抓住这个契机,手工制作出具有高度审美价值的蚕花,真正实现蚕花艺术功能与价值的现代转型,这是值得石淙蚕花传承人与当地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管理人员认真关注的问题。现代性的文化逻辑已经在理论上担保了这种文化自觉,但文化自觉成为现实还需要多种社会力量的不断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