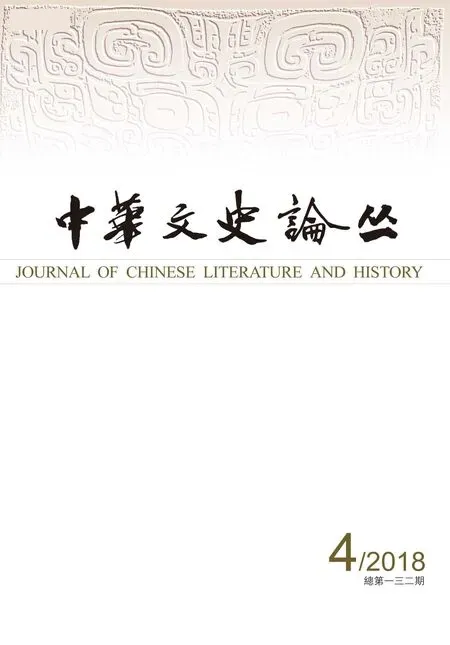從水德到木德
——前秦建立與權力更迭中的合法性訴求及其運作*
2018-01-23李磊
李 磊
提要: 通常認爲前秦繼承前、後趙法統而在五德次序中自居木德。然而苻健建構政權時,極可能自居水德,在五德次序上承西晉而否定前、後趙。苻氏原與前趙相敵對,在短暫歸附的幾年中與其關係亦十分疏離。石虎時期,苻氏雖主動歸附,但在其歷史敍事中,苻氏爲石虎父子所猜忌,缺乏君臣之義。苻氏居木德始自苻堅。苻堅爲解決合法性不足的問題,行“内禪”、造圖讖、重建歷史敍事。苻堅改居木德,改“蒲”爲“苻”以應“艸付應王”圖讖,隱含以木承水的“内禪”之意。前秦建立及苻堅奪權的歷史經由苻堅的敍事重建,形成車頻《秦書》、崔鴻《十六國春秋·前秦錄》以至於《晉書》相關載記的敍述傳統。
關鍵詞:前秦 苻堅 五德次第 政權建構
現代歷史學將十六國歷史納入到4世紀歐亞大陸民族大遷徙的整體運動中敍事,然而與歐洲情況不同的是,建立十六國的少數民族已經在漢晉王朝舊疆内長期生活,其所建立的政權亦地處關中、關東等周、秦、漢、晉王朝的核心地區。[注]參見唐長孺《晉代北境各族“變亂”的性質及五胡政權在中國的統治》,《魏晉南北朝史論叢(外一種)》,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頁122—184。李磊《4—6世紀東亞族羣的立國與中華空間的延展》,《全球史評論》第十輯,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6年,頁154—170。因而,這些政權毫無例外地面臨着統治合法性問題。最先舉兵的并州屠各曾以“漢”爲號召,試圖將其政權納入到漢朝法統中。前趙、後趙則放棄這一路線,或以匈奴單于冒頓配天、或强調胡漢之别,試圖建立與漢晉並存的胡人法統,建構新的合法性敍事。[注]羅新《從依傍漢室到自立門户——劉氏漢趙歷史的兩個階段》,《原學》第五輯,北京,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1996年,頁148—159。
後趙崩潰後,中國北方經過複雜的演變,形成關中前秦與關東前燕的對峙格局。建立前秦的苻氏與前趙、後趙均有君臣關係,苻堅的“五胡次序”説也給漢、前趙、後趙留下位置,因而通常認爲前秦繼承後趙法統。[注]羅新《十六國北朝的五德曆運問題》,《中國史研究》2004年第3期。然而苻氏在後趙覆滅後轉而依賴的是東晉位號,進入關中後又建構獨立的秦政權,其與前趙、後趙之間的法統關係其實需要作進一步的梳理。不僅如此,苻堅政變奪苻生之位,無異於改朝换代,其所圍繞着合法性問題而作的政治操作足以改變苻健、苻生時的合法性敍述。因而,苻氏政權的合法性建構問題十分複雜,不僅反映了後趙崩潰後北方政治權威建構的多面向性,同時也反映了諸如五德説、禪讓制等政治傳統是如何在政治實踐中得以保存與發展的。本文旨在以前賢研究爲基礎,對前秦建立之際及苻堅奪權過程中的合法性訴求問題及其運作略作探討。[注]相關學術綜述參見,三崎良章《五胡十六國の基礎的研究》序論《日本における〈五胡十六國研究〉研究と本書の目的》,東京,汲古書院,2006年,頁3—18。劉國石、高然《20世紀十六國思想文化、社會史、民族關係史、史籍整理及考古研究綜述》,《中國史研究動態》2007年第4期;劉國石、高然《二十世紀十六國政治史、人物、經濟史、軍事史研究綜述》,《中國史研究動態》2007年第8期。
一 苻堅“五胡次序”説再考辨
前秦建元二十一年(385)六月,苻堅在五將山爲姚萇俘獲。姚萇求傳國玉璽於苻堅,並自認爲次應符曆,苻堅叱之曰:
小羌乃敢干逼天子,豈以傳國璽授汝羌也。圖緯符命,何所依據?五胡次序,無汝羌名。違天不祥,其能久乎!璽已送晉,不可得也。[注]《晉書》卷一一四《苻堅載記下》,北京,中華書局,1974年,頁2928。
崔鴻《十六國春秋·前秦錄》所載與上引《晉書》相同,失“圖緯符命,何所依據”一句。可見唐人修《晉書》時即使未采納崔鴻著述,亦與之史源相同。陳勇釋苻堅所謂“五胡”爲劉淵、劉聰、劉曜、石勒、石虎等“五主”,認爲前、後秦交替之際,“五胡”的法統得到非漢族羣的普遍認可。[注]陳勇《從五主到五族:“五胡”稱謂探源》,《歷史研究》2014年第4期。
然此一記述疑問頗多。苻堅被俘時,其衆奔散,身邊僅侍從十數人而已,此後苻丕、苻登朝廷已爲重建之政權。[注]有關苻堅之死與兩秦政權交替的關係,參見李磊《淝水戰後關隴地區的族際政治與後秦之政權建構》,《西南民族大學學報》2018年第7期。可知這一記錄並非來自於苻堅及前秦一方的實錄。後秦方面的歷史記述,曾有扶風馬僧虔、河東衛景隆並著《秦史》,但姚氏覆滅後,所殘缺者多。[注]浦起龍《史通通釋》卷一二《古今正史第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頁334。《隋書·經籍志》載《秦紀》十卷爲北魏左民尚書姚和都所撰。[注]《隋書》卷三三《經籍二》,北京,中華書局,1973年,頁963。姚和都於姚興之世任太子右衛率,姚泓之世任給事黃門侍郎。[注]姚和都事迹見《晉書》卷一一八《姚興載記》,頁3003;卷一一九《姚泓載記》,頁3015,3016,3120。苻堅叱責姚萇之語,頗有損姚氏尊嚴,當不至於爲後秦宗室兼重臣姚和都所直書。
按劉知幾所述,宋武帝入關,訪秦國事,並無所獲。前秦滅後,曾參撰前秦國史的秘書郎趙整於商洛山中隱居撰寫,元嘉九年至二十一年(432—444)馮翊車頻總成爲三卷,河東裴景仁正其訛僻,删爲《秦記》十一篇。[注]《史通通釋》卷一二《古今正史第二》,頁334。按邱敏考述,趙整爲略陽人,前秦覆滅後爲東晉雍州刺史郗恢徙至襄陽,卒時六十餘歲。[注]邱敏《〈十六國春秋〉史料來源述考》,《西北第二民族學院學報》1991年第1期。車頻整理趙整著作亦是得到劉宋梁州刺史吉翰向朝廷的推薦。[注]《史通通釋》卷一二《古今正史第二》,頁334。裴景仁撰《秦記》則在劉宋孝武帝大明元年(457),“時殿中員外將軍裴景仁助戍彭城,本傖人,多悉戎荒事,(沈)曇慶使撰《秦記》十卷,敍苻氏僭僞本末,其書傳於世”。[注]《宋書》卷五四《沈曇慶傳》,北京,中華書局,1974年,頁1539。由此可見,前秦事迹的記述者雖爲北方漢人,但有關秦史的編纂則基本上有晉、宋朝廷或官府參與其間。
陳勇認爲苻堅叱姚萇之言中的“五胡”與晉穆帝升平元年(357)褚太后還政詔書中“五胡”指稱相同。[注]陳勇《從五主到五族:“五胡”稱謂探源》,《歷史研究》2014年第4期。這也表明苻堅此言或經由晉、宋時人語境而被轉述、闡發。故而,苻堅叱責姚萇之言出自趙整、車頻一系或裴景仁之著述,固當有所本,但亦具傳言性質,反映時人心理之所趨。記述苻堅之言的重點在於否定姚萇政權的合法性(“五胡次序,無汝羌名,違天不祥”),並將東晉法統置於五胡之上(“璽已送晉,不可得也”)。在此意義上即便有“五胡次序”説,但也絶非具有獨立的法統性質。這一敍述方式符合東晉以後秦爲敵人的政治情態,以及符合宋武帝、宋文帝的一統之志。因而,苻堅叱姚萇之言並不能反映其將苻氏法統觀建立在“五胡次序”之上,亦不表明苻堅將苻氏法統自貶於東晉之下。
二 苻洪之得名與苻氏之得姓
苻氏政權之立,始於皇始元年(351)苻健稱天王、大單于。次年,苻健稱皇帝。與屠各劉氏相比,苻健稱尊號缺乏可追溯的歷史資源,如漢王朝、匈奴單于的法統;與石勒相比,又缺乏一手締造的政治軍事集團以作依憑,缺乏一統華北的功績以作資本。故而,苻氏甚爲看重讖言,苻生使者出使涼州,即以“信符陰陽”來論述苻氏統治的合法性。[注]《晉書》卷一一二《苻生載記》,頁2874。《晉書·苻健載記》記述苻健稱尊號後讖言出現之事:
新平有長人見,語百姓張靖曰:“苻氏應天受命,今當太平,外面者歸中而安泰。”問姓名,弗答,俄而不見。新平令以聞,健以爲妖,下靖獄。會大雨霖,河渭溢,蒲津監寇登得一屐於河,長七尺三寸,人迹稱之,指長尺餘,文深一寸。健歎曰:“覆載之中何所不有,張靖所見定不虚也。”赦之。[注]《晉書》卷一一二《苻健載記》,頁2871。
“苻氏應天受命”的讖言自然有利於苻健建立統治,苻健之所以將傳播讖言的張靖下獄,或是出於擴大讖言影響的考慮。河中出巨屐證明張靖所言讖言出自“長人”之事爲實,張靖下獄與獲赦便營造出讖言爲真的戲劇性傳播效果。值得注意的是,傳達讖言的“長人”之迹的出現源於大雨、河溢,即與水有關。這似乎藴涵着苻氏對其五德次第的理解。《十六國春秋·前秦錄》記載苻氏最初得氏及苻洪得名之由來:
其後家池生蒲,長五丈,節如竹形,于時咸異之,謂之蒲家,因以氏焉。
先是,隴右大雨霖,百姓苦之,謡曰:“雨若不止,洪水必起。”故名之曰洪。[注]《太平御覽》卷一二一《偏霸部五》,北京,中華書局,1960年,頁585下欄。
苻氏原爲蒲氏,蒲生於池中。對苻氏崛起具有決定性影響的人物苻洪之得名也源於隴右大雨。百姓謡言“雨若不止,洪水必起”,實以大雨霖作爲苻氏興起之預兆。苻氏得氏與苻洪得名,均與水有關。這些記述當源於苻氏建國後的官方記述。按《十六國春秋·前秦錄》所述,建元十七年(381)八月,“堅收起居注及著作所錄而觀之,見苟太后、李威之事,慙怒,乃焚其書”。[注]《太平御覽》卷一二一《偏霸部六》,頁590下欄。可知苻氏政權有修起居注的制度,對君主及其宗族有系統性的記載。苻堅焚起居注及相關著作之事,當是秦亡後趙整的追述。
《晉書·苻堅載記上》列撰述起居注者爲著作郎趙泉、車敬。[注]《晉書》卷一一三《苻堅載記上》,頁2904。《史通》錄撰述者爲趙淵、車敬、梁熙、韋譚。[注]《史通通釋》卷一二《古今正史第二》,頁333。趙淵即《晉書》中的趙泉,唐人修史避諱改“淵”爲“泉”。[注]《晉書》卷一一三《苻堅載記上》校勘記引《晉書斠注》,頁2904。趙泉、車敬皆死於建元十七年(381)焚書之前。梁熙爲氐族貴族,與其兄梁讜齊名,文才爲燕、秦所重。梁熙曾任苻堅中書令,建元十二年(376)滅亡前涼後,被委任爲涼州刺史,主政河西直至建元二十一年(385)爲吕光自西域回師所滅。[注]《晉書》卷一一三《苻堅載記上》,頁2897—2898;卷一二二《吕光載記》,頁3056。從梁熙終苻堅之世始終被委以重任的遭際來看,苻堅並未遷怒於著作郎,而且苻堅所慚怒者爲苟太后宫闈之事,似與修史中的意識形態無關。這使得苻氏早期的相關記載在焚書之後也具有以原樣留存的條件。
經過焚書,此前有關苻氏的記述留存甚少,《史通》言“後著作郎董誼追錄舊語,十不一存”。[注]《史通通釋》卷一二《古今正史第二》,頁333。儘管如此,《隋書·經籍二》載《秦書》八卷,爲何仲熙所撰,“記苻健事”。[注]《隋書》卷三三《經籍二》,頁963。聶溦萌推測何仲熙即爲梁熙之誤寫。[注]聶溦萌《十六國霸史與十六國時期的官修史運作》,《西北民族論叢》第十三輯,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6年,頁41—64。若此,則苻氏早期的歷史經由時任著作郎的梁熙記述,保存於《秦書》之中。更大膽地推測,苻氏得氏、苻洪得名、苻健得長人“應天受命”等與水有關的讖言,或許都是苻健稱尊號時所造,旨在論證苻氏之得水德。這些苻健時之事,經由梁熙《秦書》記述,進而影響《十六國春秋》及《晉書》的編纂。
若苻健稱尊號時以水德自居這一推測無誤,則苻健將其正統性直接上承於西晉之金德,而否定了此前北方政權以及南方東晉政權的正統性。從北方政權正統性建構的歷史來看,以劉曜稱趙皇帝爲界分爲兩條路線: 此前,劉淵以漢室自居,稱漢王、漢皇帝以否定魏晉的正統性;此後,魏晉正統性基本得到承認。[注]羅新《從依傍漢室到自立門户——劉氏漢趙歷史的兩個階段》,《原學》第五輯,頁148—159。羅新《十六國北朝的五德曆運問題》,《中國史研究》2004年第3期。劉曜“以水承晉金行”、“牲牡尚黑,旗幟尚玄”,[注]《晉書》卷一三《劉曜載記》,頁2685。將趙之法統上接於西晉,建構了“漢魏晉趙”的譜系。然而繼興的石勒只承認“漢魏晉”,卻繞開屠各劉氏的漢、趙法統,“以趙承金爲水德,旗幟尚玄,牲牡尚白”。[注]《晉書》卷一五《石勒載記下》,頁2746。由此可知,儘管自西晉末年以來北方地區先後存在着漢、前趙、後趙等政權,且彼此間具有千絲萬縷的聯繫,但是在政治意識上,尚未認同具有一致性的正統譜系。苻健稱尊號時直接以西晉繼承者自居,無視包括後趙在内的此前北方政權的正統性,這其實是前趙、後趙等先前政權一貫的做法,也是符合當日普遍的政治認識的。
三 苻氏與前、後趙之關係
關於苻健自居水德的推論,還可從苻氏與劉、石的關係中得到相關證據的支持。苻氏崛起於劉聰經略關隴之時,又前後被劉曜、石虎委以官爵,因而與劉、石均發生過實質上的政治關聯。按《十六國春秋·前秦錄》所述,苻洪崛起於略陽後,劉聰曾遣使拜苻洪爲平遠將軍,但不爲苻洪所接受,苻洪“自稱護氐校尉、秦州刺史、略陽公,羣氐推爲首”,劉曜建趙國,“以洪爲氐王”。[注]《太平御覽》卷一二一《偏霸部五》,頁585下欄。按《晉書·苻洪載記》所述,苻洪被劉曜“拜率義侯”。[注]《晉書》卷一一二《苻洪載記》,頁2867。《魏書·苻洪傳》記苻洪在率義侯爵位之外,還被劉曜拜爲寧西將軍,並被遷於高陸。[注]《魏書》卷九五《苻洪傳》,北京,中華書局,1974年,頁2073。
值得注意的是,《十六國春秋·前秦錄》敍苻氏之起背景時的用語是“屬劉氏之亂”,《晉書·苻洪載記》中的相應表述爲“屬永嘉之亂”,可知劉氏之亂指劉淵、劉聰、劉曜傾覆西晉之事。《十六國春秋·前秦錄》用語較之《晉書》更爲原始,極有可能是襲自《秦書》或《秦記》原文。若此,苻氏對漢、趙政權持否定態度,這與苻洪拒絶劉聰平遠將軍之授的態度是一致的。
劉曜入據關中後與氐、羌衝突不斷。光初二年至三年(319—320),黃石屠各路松多起兵於新平、扶風,附於南陽王保,“秦隴氐羌多歸之”。路松多被劉曜擊敗後,退保隴城,南陽王保則至桑城,“氐羌悉從之”。[注]《晉書》卷一三《劉曜載記》,頁2685。可見在劉曜與南陽王保的鬥爭中,秦隴氐羌選擇歸附於南陽王保。光初三年(320),劉曜殺巴酋徐庫彭等,“於是巴氐盡叛,推巴歸善王句渠知爲主,四山羌、氐、巴、羯應之者三十餘萬,關中大亂,城門晝閉”。[注]《晉書》卷一三《劉曜載記》,頁2686。所謂“四山羌、氐、巴、羯”,按劉曜委派的車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都督雍秦征討諸軍事游子遠的進軍路線,當是雍城、安定、上郡之衆,以氐、羌爲主。[注]《晉書》卷一三《劉曜載記》,頁2687。
光初五年(322),劉曜親征仇池,“仇池諸氐羌多降於曜”。[注]《晉書》卷一三《劉曜載記》,頁2691。此時陳安據秦州上邽,又奪汧城,“西州氐羌悉從安,安士馬雄盛,衆十餘萬”。[注]《晉書》卷一三《劉曜載記》,頁2691—2692。苻氏所居之略陽臨渭,其西爲上邽,東爲汧城,從政治地理推斷,苻氏或許正爲追隨陳安的西州氐羌之一部。光初六年(323),陳安敗,“氐羌悉下,並送質任”。[注]《晉書》卷一三《劉曜載記》,頁2694。按《晉書·姚弋仲載記》所述,“劉曜之平陳安也,以弋仲爲平西將軍,封平襄公,邑之於隴上”。[注]《晉書》卷一一六《姚弋仲載記》,頁2959。姚氏原處扶風郡榆眉,劉曜平陳安後遷之於隴上。以此類比,苻洪被封爲寧西將軍、率義侯、氐王,並被遷於鄰近長安的京兆郡高陸縣,或許正是在同一時期。以後,劉曜“置單于臺於渭城,拜大單于,置左右賢王已下,皆以胡、羯、鮮卑、氐、羌豪桀爲之”。[注]《晉書》卷一三《劉曜載記》,頁2698。渭城地處長安北,西北爲高陸。苻洪所居離單于臺不遠,其正當以“豪桀”身份歸屬於單于臺。
雖然没有更多史料論述光初六年至十二年(323—329)這段時期苻洪與劉曜政權的親疏關係,但是可以從劉曜敗於洛陽後苻洪西遷回隴山之事,推斷苻氏與略陽故地仍然有着十分密切的聯繫。在劉趙時期關隴的政治地理中,隴城時常成爲反劉曜勢力的根據地。光初三年(320)黃石屠各路松多退保於隴城,光初六年(323)陳安亦退保於隴城。因而苻洪西遷保隴山或許暗含獨立於劉趙政權之外的政治象徵意義。
相較於與前趙政權之間短暫而若即若離的關係,苻洪與後趙之間的關係似乎要密切一些。然而這種密切關係是在前趙滅亡後苻洪審時度勢的結果。劉曜洛陽之敗後,劉熙等奔上邽,石虎進入關中。苻洪所據的隴山正在石虎西進的路上,苻洪選擇主動投靠石虎。對於苻洪的投靠,《十六國春秋·前秦錄》形象地描述了當時的場景:“虎跣出迎之,拜冠軍將軍、監六夷諸軍事、涇陽伯”。[注]《太平御覽》卷一二一《偏霸部五》,頁585下欄。涇陽在隴城西北,地處安定郡。從軍事地理上説,此地並不在石虎西進上邽的必經之路上,但卻是氐、羌聚居之地。石虎“跣出迎之”正是看到苻洪在解決氐、羌問題上的利用價值。苻洪的冠軍將軍、監六夷諸軍事、涇陽伯之任,實際上是緣於石虎借助苻洪穩定安定一帶的戰略考慮,這一地區,石虎暫時還無暇顧及。對於這一授受,《晉書》的表述是“委以西方之事”。[注]《晉書》卷一一二《苻洪載記》,頁2867。
在前趙殘餘勢力覆滅以後,氐、羌在屠各王羌的率領下舉兵與後趙對抗,“隴右大擾,氐羌悉叛”。石勒派遣石生進據隴城,擊敗了王羌。[注]《晉書》卷一五《石勒載記下》,頁2747。所謂隴右,乃指隴山以西之地。雖然難以判斷苻洪在此次戰亂之中的立場,但從建平四年(333)石生起兵關中,苻洪西結張駿自保的態度來看,在石生鎮守關中的數年裏,苻洪並未與石生結成密切的關係。石生敗亡後,苻洪率二萬户下隴東,如馮翊,被石虎拜爲護氐校尉,進爵爲侯。[注]《太平御覽》卷一二一《偏霸部五》,頁585下欄。從軍號上看,護氐校尉較冠軍將軍爲低。《晉書》言“洪説季龍宜徙關中豪傑及羌戎内實京師”。[注]《晉書》卷一一二《苻洪載記》,頁2867。石虎徙民有兩次,一次是滅石生後,徙雍、秦州華戎十餘萬户於關東;另一次是敗郭權後,徙秦州三萬餘户於青、并二州諸郡。[注]《晉書》卷一五《石勒載記下》,頁2755。苻洪是在前一次中被遷於枋頭。[注]《太平御覽》卷一二一《偏霸部五》,頁585下欄。在石生與石虎對峙時期,苻洪自稱晉平北將軍、雍州刺史,[注]《太平御覽》卷一二一《偏霸部五》,頁585下欄。並未打出石虎陣營的政治旗號,可見二者關係之疏遠。頗疑苻洪向石虎提議徙民實爲察知石虎動向後的迎合之舉。故在東遷後,苻洪由護氐校尉升爲龍驤將軍。[注]《太平御覽》卷一二一《偏霸部五》,頁585下欄。
在石虎統治時期,苻洪的處境相當微妙。按《晉書·苻洪載記》所述,冉閔曾勸石虎密除苻洪,然而“季龍待之愈厚”。[注]《晉書》卷一一二《苻洪載記》,頁2867—2868。《苻健載記》的記載則相反,“季龍雖外禮苻氏,心實忌之,乃陰殺其諸兄”。[注]《晉書》卷一一二《苻健載記》,頁2868。《晉書》的記載相互牴牾,可見《苻洪載記》《苻健載記》具有不同史源。《苻健載記》或源自《秦書》,反映了苻健時的意識形態,若此則苻健對於石虎統治是持負面看法的。《十六國春秋·前秦錄》的相關記述是:“佛圖澄觀苻氏有王氣,虎陰欲殺之,洪稱疾不朝。”[注]《太平御覽》卷一二一《偏霸部五》,頁585下欄。佛圖澄爲西域僧侣,石勒、石虎崇信以預測吉凶,常有靈驗。《前秦錄》所述不見其他記載。從事理上推斷,倘若石虎欲殺苻洪,這非苻洪稱疾不朝所能幸免的。這條記載似乎是苻氏在建構政權時的追述,其目的既在於借助佛圖澄來論述其有“王氣”,而且旨在闡述石虎對苻氏無君臣之義。
按上述的歷史記述,苻氏在石虎時期實際處於被監視、限制與利用的位置。苻氏作爲一支相對獨立的政治軍事勢力的崛起,緣於石虎統治末期太寧元年(349)鎮壓梁犢的戰事。此戰中,苻洪與姚弋仲一起受石斌節制。石斌是石弘延熙年間(334)擊敗郭權、佔據關中的軍事統帥。石虎以石斌節制苻洪,隱含監督之意。按《晉書·苻洪載記》所述,石遵即位後去苻洪都督之職引發他的怨恨,從而導致苻氏叛離。[注]《晉書》卷一一二《苻洪載記》,頁2868。蔣福亞認爲“石遵罷免苻洪秦雍都督、雍州刺史的官職,不許他到關中赴任”,故而苻洪於枋頭舉兵。《前秦史》,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1993年,頁29。陳勇認爲:“苻洪雍州刺史一職,此時未遭罷免。”《〈資治通鑑〉十六國資料釋證(前秦、後秦國部分)》,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5年,頁28。事實上,在隨後的石鑒之世,苻洪仍較深參與石氏内部之爭,他同石祗連兵與石鑒相爭。[注]《晉書》卷一七《石季龍載記下》,頁2791。對比可知,《晉書·苻洪載記》的敍事重點是石遵對苻氏的刻薄,而非苻洪對石氏政權的維護。這顯然是源自苻氏一方的歷史記述,旨在否定石氏與苻氏的君臣之義。
綜上所述,苻氏原爲前趙對立方,即便在短暫歸附於前趙的幾年中,其與前趙的關係也較爲疏離。石虎統治時期,苻氏主動歸附,並被遷徙至枋頭。但在苻氏的歷史敍事中,枋頭時期是遭到石虎父子相繼監督、謀害的歷史,彼此間缺乏君臣之義。由此可知,在苻健建構政權之際,他有充足的理由否定前、後趙的正統性,而將其五德次序直接上承於西晉。
四 苻堅自居木德與前秦合法性論述的重建
苻氏自立旗號始於石鑒統治末期(350年正月),苻洪自稱大將軍、大單于、三秦王。[注]《資治通鑑》卷九八晉穆帝永和六年,北京,古籍出版社,1956年,頁3102。不久苻洪爲降將麻秋所鴆殺,苻洪臨終遺言“所以未入關者,言中州可指時而定”。[注]《晉書》卷一一二《苻洪載記》,頁2868。可知苻洪稱王的志向在於“定中州”,而非偏安關中。《資治通鑑》載:
(石)鑒懼洪之逼,欲以計遣之,乃以洪爲都督關中諸軍事、征西大將軍、雍州牧、領秦州刺史。洪會官屬,議應受與不;主簿程朴請且與趙連和,如列國分境而治。洪怒曰:“吾不堪爲天子邪,而云列國乎!”引朴斬之。[注]《資治通鑑》卷九八晉穆帝永和五年,頁3098。
胡三省注:“蒲洪直欲奪取之而後已。”[注]《資治通鑑》卷九八晉穆帝永和五年,頁3098。苻洪誅殺主簿程朴,只因他提議與後趙連和,苻洪借誅殺程朴表明自立爲天子的決心。值得注意的是,即便是在程朴的概念中,後趙的國家形態也僅僅是“列國”,程朴與苻洪在否定後趙的正統性方面並無二致。[注]陳勇:“蒲洪將‘天子’與‘列國’對舉,後者指‘分境而治”,前者指一統之局。”《〈資治通鑑〉十六國資料釋證(前秦、後秦國部分)》,頁28。更何況在後趙崩壞之局中,苻氏並未直接繼承後趙的政治遺産,苻洪所資憑的十萬之衆爲西歸路經枋頭的秦、雍流人。胡三省認爲即是咸和四年(329)石虎破劉胤所遷的氐、羌十五萬落與咸和八年(333)破石生所遷的秦、雍民及氐、羌十餘萬户。[注]《資治通鑑》卷九八晉穆帝永和五年,頁3098。在此意義上,苻洪稱尊號自不會將其合法性論述過多立論於與後趙的繼承關係。以後苻健在五德次序中自居水德而越過劉、石,其實是對苻洪政治路線的繼承與發展。
苻生即位後,曾派遣閻負、梁殊出使涼州,在與張瓘的對答中多次闡釋了秦與前趙、後趙的不同。如“趙多姦詐,秦以義信,豈可同年而語哉”,“今上道合二儀,慈弘山海,信符陰陽,御物無際,不可以二趙相況也”,[注]《晉書》卷一一二《苻生載記》,頁2874。這些言辭皆表明苻氏政權以居高臨下的姿態看待前趙、後趙歷史。
按《晉書》卷一一二所附《王墮傳》,苻洪在稱尊號之前,曾製造讖言以作動員。“(王墮)明天文圖緯,苻洪征梁犢,以墮爲司馬,謂洪曰:‘讖言苻氏應王,公其人也。’洪深然之。”[注]《晉書》卷一一二《苻洪苻健苻生載記附王墮傳》,頁2880。梁犢事起於石虎太寧元年(349),按《王墮傳》所言,此時苻氏應王之讖言出現。《十六國春秋·前秦錄》記載讖言的具體内容爲“艸付應王”,與該讖文相關者還有“孫堅之生,背有符(艸付)字”。爲與讖文相應,苻洪“遂改姓符氏”。[注]崔鴻《十六國春秋·前秦錄》,《太平御覽》卷一二一《偏霸部五》,頁586上欄。《晉書》作“讖文有‘艸付應王’,又其孫堅背有‘艸付’字,遂改姓苻氏。”見《晉書》卷一一二《苻洪載記》,頁2868。
然而“孫堅背有‘艸付’字”,按《十六國春秋·前秦錄》所言,“趙建武中,其母苟氏祈西門豹祠,歸而夜夢與神交,遂孕,十二月而生,有神光之異,自天屬庭,背有赤文,隱起成字,曰‘艸付臣又土王咸陽’,祕而莫之傳也”。[注]崔鴻《十六國春秋·前秦錄》,《太平御覽》卷一二二《偏霸部六》,頁588上欄。苻堅薨於建元二十一年(385)八月,時年四十八歲,照此推算,苻堅出生於石虎建武三年(337)。苻堅出生即背有赤文,若從時間角度而論,“艸付應王”的讖言當最早出現於苻堅出生的建武三年(337),而非梁犢起事時的石虎太寧元年(349)。《十六國春秋·前秦錄》這一記述上的矛盾似乎揭示“艸付應王”的讖言爲苻堅奪位後所造。
苻洪在稱尊號時,或許由王墮爲之製造讖言,但其内容未必是“艸付應王”。之所以將苻氏應王的讖言宣講者記述爲王墮,或許與王墮在苻生執政時的境遇有關。王墮時任司空,疾苻生寵臣董榮、强國如仇讎,故而被董榮設計在“以應日蝕之災”的藉口下被殺。苻堅奪位後,追復其本官,“以禮改葬之,其子孫皆隨才擢授”。[注]《晉書》卷一一二《苻生載記》,頁2873;卷一一三《苻堅載記上》,頁2885。王墮作爲苻洪舊臣而被苻生所枉殺,這對於奪位的苻堅而言,在建構統治合法性方面十分有價值。當苻堅重構歷史敍事時,將“艸付應王”的讖言歸屬於明天文圖緯的王墮,是再合適不過的安排。此舉不僅可以將苻堅的意識形態上溯於苻洪時期,亦可借王墮之死來否定苻生統治的合法性。
苻堅之所以製造出“艸付應王”的讖言,除了表明自己天生異相(“背有赤文,隱起成字”)受天命之外,還旨在否定苻生的統治。苻生爲苻健第三子,太子苻萇死後,苻健以“以讖言三羊五眼應符”,故立苻生爲太子。[注]《晉書》卷一一二《苻生載記》,頁2872。這一讖言或爲苻健所造,以苻生獨眼的生理特徵來“應符”。很顯然,在這一政治運作中,苻生獨眼不僅未被視作生理缺陷,而且還被高看爲“應符”的異相。然而,按《十六國春秋·前秦錄》所述,苻洪稱苻生爲“瞎兒”而戲之,引發苻生的激烈反應。[注]《太平御覽》卷一二一《偏霸部五》,頁586下欄。這一記述將獨眼視爲缺陷,導致苻生爲人所輕視。頗疑這一故事經由苻堅奪位後的闡釋。
單就身體而論,苻堅亦有缺陷。車頻《秦書》載,苻堅六歲(343年)時,司隸徐統見而異焉,語左右曰“此兒有王霸相”,而左右反問徐統“此兒狀皃甚醜,而君以爲相貴,何也”。[注]《太平御覽》卷三八二《人事部二三》,頁1763上欄。由此記載可見苻堅相貌甚醜,《太平御覽》編纂者將此記載歸入卷三八二《人事部二三》“醜丈夫”條目之下。苻生的生理缺陷,“祖洪甚惡之”,苻堅之醜,“祖洪奇而愛之”,苻洪對苻健言其“非常相”。[注]崔鴻《十六國春秋·前秦錄》,《太平御覽》卷一二二《偏霸部六》,頁588上欄。若單是以貌取人,苻洪不至於對同爲孫子的苻生、苻堅有太大差異。這一記述的差異顯然是經過苻堅奪位後改造所致。
按照現存史料所述,不僅苻洪對苻生、苻堅的評價兩極分化,時人的輿論亦然。苻堅之醜被徐統視作“有王霸相”,苻生獨眼卻一再遭到歧視,如時人以“瞎兒不知法”的謡言中傷苻生。《晉書·苻生載記》載:“既自有目疾,其所諱者不足、不具、少、無、缺、傷、殘、毁、偏、隻之言皆不得道,左右忤旨而死者不可勝紀,至於截脛、刳胎、拉脅、鋸頸者,動有千數。”[注]《晉書》卷一一二《苻生載記》,頁2879。蔣福亞認爲苻生之忌諱乃是因爲受到親貴權臣們不斷嘲弄的緣故。[注]蔣福亞《前秦史》,頁60。《十六國春秋·前秦錄》記述截脛等刑罰以千數之事,但在敍事邏輯中並未將其歸因於苻生目疾之諱。[注]《太平御覽》卷一二一《偏霸部五》,頁587上欄。可見苻生因忌諱目疾而動輒刑虐是一個經由史家不斷再理解、疊加而成的歷史記憶。苻生目疾受嘲弄可能存在其事,但與苻堅之醜而被“奇而愛之”一樣,都是經由苻堅奪權後再敍述而塑造的形象。或許這便是建元十七年(381)八月苻堅焚起居注及著作所錄之後新的國史敍事。
苻堅奪位後,永興元年(357)六月去皇帝之號,稱大秦天王。[注]崔鴻《十六國春秋·前秦錄》,《太平御覽》卷一二二《偏霸部六》,頁588上欄。此前苻生稱皇帝。按照谷川道雄的説法,之所以稱“天王”,乃是因爲對稱“皇帝”尚有躊躇。[注]谷川道雄著、李濟滄譯《隋唐帝國形成史論》,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頁245—249。《晉書·苻堅載記》記載,“堅及母苟氏並慮衆心未服,難居大位”。[注]《晉書》卷一一三《苻堅載記上》,頁2884。苻堅之躊躇,顯然是緣於其不具備繼承的合法性,而憂慮衆心未服。從苻洪、苻健、苻生的繼承次第來看,苻氏政權遵循了父子相繼的原則。苻健臨終前,兄子苻菁曾試圖政變奪位,卻“衆皆舍杖逃散”。[注]《晉書》卷一一二《苻健載記》,頁2869,2871。苻菁雖在苻氏入關過程中立有大功,然而卻没有繼承權,故其奪位不得人心。按《晉書·苻健載記》所述,苻健爲苻洪第三子,諸兄爲石虎所殺,故而得以繼位。苻健原本立苻萇爲太子,苻萇死後才立苻生。[注]《晉書》卷一一二《苻健載記》,頁2869,2871。可見苻氏在繼承權上遵循長幼之序。在奪位政變中,苻堅之兄苻法的地位不弱於苻堅。奪位後,“(苻堅)以僞位讓其兄法,法自以庶孽,不敢當”,不久,“堅母以法長而賢,又得衆心,懼終爲變,至此,遣殺之”。[注]《晉書》卷一一三《苻堅載記上》,頁2884。可見苻氏雖有嫡庶觀念,但是並非繼承權方面不可動搖的鐵律,“長而賢”仍然是首位的,所以纔有苻堅讓位又隨後殺害苻法之舉。
正是因爲苻堅在繼承權上既未父子相繼,又未遵循長幼之序,按選賢任能又未必强於苻法,這是苻堅稱帝躊躇的原因。苻堅稱天王,從苻氏政權的立場來看,最高統治者從“皇帝”貶爲“天王”,乃是因爲正統性不完備。與君主降號相伴,王爵也被降爲公爵,如苻法由清河王更爵爲東海公。[注]崔鴻《十六國春秋·前秦錄》,《太平御覽》卷一二一《偏霸部五》,頁587上欄。降爵這一程式通常發生在禪讓改朝换代之際,如曹丕受禪“以漢諸侯王爲崇德侯”,[注]《三國志》卷二《文帝紀》,北京,中華書局,1982年,頁76。司馬炎受禪封“魏氏諸王皆爲縣侯”。[注]《晉書》卷三《世祖武帝紀》,頁51—52。頗疑苻堅是以比擬改朝换代的方式來處理與苻生法統之間的關係。
司馬睿建構東晉政權之時,因其爲宗室疏屬,曾遇到稱帝合法性不足的問題。故而“依魏晉故事爲晉王”,[注]《晉書》卷六《中宗元帝紀》,頁145。即遵循魏晉禪讓的模式,先在原王朝體系之内立國稱王,再行禪讓而登皇帝位。田餘慶先生認爲司馬睿稱晉王,即是將原吴國改易爲晉國,在此基礎上進一步即晉皇帝位。[注]田餘慶《東晉門閥政治》,北京大學出版社,1989年,頁40。司馬睿的即位詔書中引《尚書·舜典》“受終文祖”之典,以堯舜禪讓來比喻兩晉之間的政權更替。對於堯舜禪讓,時任史官的干寶將其定義爲“内禪”,認爲“體文德也”,而與“漢魏外禪”不同。[注]干寶《晉紀論晉武帝革命》,《文選》卷四九《史論上》,北京,中華書局,1977年,頁687。參見李磊《東晉初年的國史敍事與正統性建構》,《史林》2018年第5期。
苻堅奪位之後所面對的情形與司馬睿相似: 身爲宗室卻無直接繼承權,其政權的合法性建構既要與前朝相切割,同時又要予以繼承。因此,苻堅以“内禪”的方式處理與苻生的關係是一種較爲恰當且有例可循的政治運作。在這個意義上,苻堅稱“天王”與司馬睿稱“晉王”相同,皆是在前朝的天下體系之中先建國,再由“天王”或“王”的身份“内禪”爲皇帝。羣臣的爵位降等,亦有雙重解釋,一是前朝爵位隨例降等;二是成爲天王羣臣,其爵位自須低於皇帝羣臣的等次。
“内禪”畢竟是一種禪讓,隨之而來的是五德次第問題。姚萇稱帝時,“自謂以火德承苻氏木行,服色如漢氏承周故事”。[注]《晉書》卷一一六《姚萇載記》,頁2967。可知苻堅政權爲木德。如前所述,苻健政權極有可能以水德自居,承晉金行。頗疑苻堅爲了解決稱帝的合法性問題,推動了苻氏政權内部的意識形態革命,即以木德代替水德。
《十六國春秋·前秦錄》記載苻堅起事之前,“長安謡曰:‘東海大魚化爲龍,男爲王女爲公,問在何所洛門東。’東海,即堅封也,第在洛門東”。[注]《太平御覽》卷一二一《偏霸部五》,頁587上欄。這一謡言極有可能是苻堅政變前所造,以便於政治動員。從“東海”、“大魚”等意象來看,此時苻堅似乎仍然以水德自居。苻堅即位後,依據新平人王彫所陳説的圖讖而自居木德。《晉書·苻堅載記下》記載王彫之説辭:
謹案讖云:“古月之末亂中州,洪水大起健西流,惟有雄子定八州。”此即三祖、陛下之聖諱也。又曰:“當有艸付臣又土,滅東燕,破白虜,氐在中,華在表。”[注]《晉書》卷一一四《苻堅載記下》,頁2910。
所謂“三祖”當指苻洪、苻健、苻雄。“洪水大起健西流”,取水爲象,隱寓苻洪、苻健時代的水德。“艸付臣又土”,乃“苻堅”二字之拆字。可知“艸付臣又土”的讖言出自於苻堅即位後,由王彫所上。如此,“艸付”的讖言既不出現於苻堅出生的建武三年(337),亦不出現於苻洪準備起事的太寧元年(349),而是苻堅即位的永興元年(357)。“艸付應王”的主角亦非苻洪,而是苻堅。
同理,“遂改姓苻氏”者極有可能是苻堅而非苻洪。《資治通鑑》以永和六年(350)爲蒲氏“改姓苻氏”之年,此前皆稱苻洪爲“蒲洪”。[注]《資治通鑑》卷九八晉穆帝永和六年,頁3102。然而《晉書·苻生載記》載苻生“夢大魚食蒲”,“以謡夢之故,誅其侍中、太師、錄尚書事魚遵及其七子、十孫”。[注]《晉書》卷一一二《苻生載記》,頁2878。陳勇:“蒲洪改姓苻氏,在永和六年(350),《晉書》此前皆稱‘苻洪’,蓋以敍述之便。《通鑑》作蒲洪,則更爲準確。”《〈資治通鑑〉十六國資料釋證(前秦、後秦國部分)》,頁31。若“蒲”象徵族源,苻堅亦爲所出,象徵他的大魚當不至於自食其始源。苻生夢大魚食蒲,無論是真有其事,還是苻堅所造之歷史敍事,都表明“蒲”被看作與苻生姓氏相關。倘若苻堅即位後,爲了應“艸付臣又土”的讖言,其改“蒲氏”爲“苻氏”的可能性極大。如此,苻生夢大魚食蒲的象徵是苻堅奪位並改姓。
苻堅自居木德,正是以應“艸付”圖讖,同時亦隱含水生木之意,在五德次第上生於苻健、苻生所居之水德。一言以蔽之,苻堅爲了解決其稱帝合法性不足的問題,行“内禪”、改姓氏,自居木德正是其中的一個重要環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