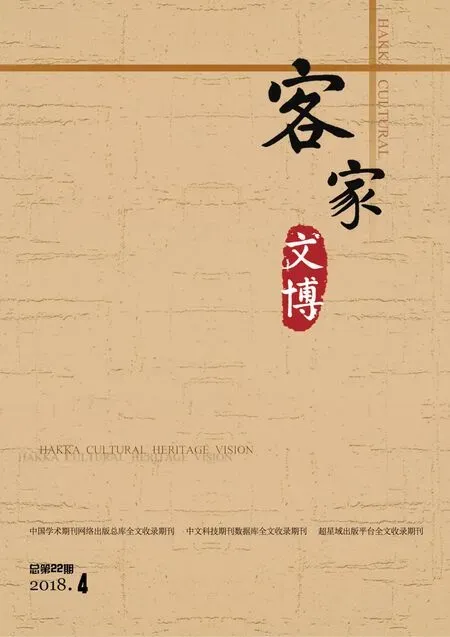客家方言与客家人的宗族观
2018-01-23练春招
练春招
客家是中原汉人南迁聚居的社会群体,这个群体既有地缘的联系,又有血缘的联系。由于客家的迁徙往往是以一族一姓为单位的,姓氏和宗族便成了客家群体的一个个具体的行动单位。到了新地定居之后,几经繁衍,也还是以姓氏为单位聚居,因此,宗族便成了客家存在和发展的一个基本依据。它对于客家社会文化的各个方面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连方言的分布、演变和发展也受到这种观念的制约。
一、按姓氏区分口音
一般来说,方言口音的形成总是以地缘为依据的。但是,由于客家人有特别强烈的宗族观念,不同的姓氏由于迁徙时间不同而住在一处,尽管地缘上是一致的,其口音却仍有区别。因而,在同一个自然村中,由于姓氏不同,迁徙时间不同而口音不同的现象也常可发现。例如,闽西武平县东留乡新联村社下坝自然村就有两种口音,李钟两姓是清代时由城关迁去的,迄今已繁衍了十三四代人,但他们的方言几百年如一日,至今仍保留城关口音;他们的隔壁邻居尽管是同一自然村,但只要是不同姓,口音即不相同,如上社下坝的北片与大阳村相接处有刘姓,即讲东留本地话,当地人称本地话为“濠坑腔”,濠坑腔与城关话的区别主要表现在声调及个别字的读音不同上,濠坑腔的声调是去声不分阴阳,城关话的声调是浊去归上声,由此而产生两种口音腔调的差异。字音的不同表现在声韵调方面,如“菜”字,城关音读[tshu52] ,濠坑腔读[su52];又如“鸡”字,城关音读[ki45] ,濠坑腔读[tþiai45];再如“饭”字,城关音读[phu n31],濠坑腔读[fan52]。但总的来说,濠坑腔与城关话是大同小异的,通话毫无困难,只是交谈者彼此心里明白,但谁也不学谁的口音,谁也不愿改变自己的口音而已。
东留乡的新联村有八个小自然村,其中,新联村驻地的小自然村-龙头岗下是建国后从社下坝析出的,其村的口音也以李钟两姓来区分。外姓的女子嫁进李钟两姓家中,在夫家必须按李钟两姓的规矩讲话,且必须尽快改变自已原来的口音,并教子女讲夫家的话。若是嫁进很久都改不了原来的口音,则会受到夫家人的指责,而且,村里同姓家族还会拿她的异姓腔调作为取笑材料。在李钟两姓中间,还流传着这样的谚语:“食男饭转男声,不转男声骨头轻。”意为,吃了男家的饭就应该说男家的话,否则就是不识好歹。这两姓的孩子在当地上学,如果学了当地的“濠坑腔”,回家后也要受指责。由于李钟两姓的这种规矩世代相传,所以其口音也就世代不变,虽然都是在同一“屋”相结合来命名。此外,还有“姓氏+屋+坑”“同化。这里当然有其他复杂因素,但宗族观念无疑是其中重要的影响因素之一。
二、“屋”与客家的聚族村落
“屋”在客家方言区指房子,各地客家方言均把“家里”说“屋下”,“回家”说“转屋下/归屋下”,以此来命名自己的所居之地也是顺理成章的事。广东省通行闽粤客三大方言,以“屋”作通名的地方为客家方言区,这是客家方言区地名的一大特色。根据马显彬对《广东省交通地图册》的统计,广东省带“屋”字的地名有977个1。该地图册所辑录地名未必到自然村,实际“屋”字地名远不止此数。同样的意思潮汕及雷州半岛的闽方言区以“厝”名之,粤方言区则通说“村”。
由于客家南迁过程中往往以族姓为单位,到了新地定居之后,村落的名字往往就以聚居的宗族姓氏来命名。在客家地区,有许多地名冠以姓氏,而姓氏之后出现的通名最大量的就是“屋”字。以福建省武平县为例,《武平县地名录》中辑录了带“屋”字的地名共176个,其中124个与姓氏有关。如曾屋、宋屋角、杨屋、罗屋、吴屋、陈屋、钟屋、刘屋、王屋、李屋、上徐屋、朱屋、下廖屋、下舒屋、王屋角、谢屋、刘屋角、曾屋、雷屋、郭屋、何屋、上潘屋、程屋、廖屋、周屋、丘屋、石屋、林屋、余钟屋、老张屋、新张屋、上陈屋、下陈屋、下高屋、上高屋、黄屋、练屋、游屋、赖屋、傅屋、张屋、杜屋、蔡屋、老熊屋、邓屋、上何屋、下何屋、郑屋、邹屋、蓝屋、薛屋、林屋、尧屋、徐屋、上戴屋、下戴屋、毛屋、曹屋、潘屋、巫屋等等。从这些地名可以看出该村落的聚族特征,即至少村里大部分都是同族同姓人,所以才以自己的姓和氏+屋+凹”“姓氏+屋+湾”“姓氏+屋+角”“姓氏+屋+塘”“姓氏+屋+寨”等地名形式,如“钟屋坑”“赖屋凹”“谢屋湾”“宋屋角”“黄屋塘”“曾屋寨”等等。这种“姓氏+屋”的地名是客家地区族群认同的思想结晶和现实表现。
三、宗族的内聚与外御
人类是社会的动物,自古以来,人们就不能离群而独居,必须结合成一个个社会群体。客家是南来的后到之人,为了对付先期住着的“主”和改造陌生的环境,他们特别需要团结合作。一个个大家庭的合作力量还很有限,必须有宗族也即“自家人”的大联合。因而,客家人的宗族观念还表现在同一宗族对内具有强大的凝聚力,对外则具有强烈的排他性。如前所述,客家人在迁移中有不少是以姓氏为单位的,到了定居点之后,他们也就以族姓为单位,同一族姓聚居一处,日久繁衍,人口增多,族姓规模越来越大,形成同姓村落。加以客家所居的闽粤赣地区是个丘陵起伏的山区,一个个同宗族姓分住在一个个山间平地便成了一般的聚落形式。有的虽未形成聚族村落,但同一族姓的人总是聚居在某一处。这种聚族而居的村落或村片的血缘性非常明确,如武平县平川镇城北片红东村北方坊均为李姓居住,李姓人认为,凡鞭炮声所及之地,都应是李家的天下。外姓人很难进住,即使进住了,家庭也往往繁衍不兴,因为受到精神上的压力和物质上的局限,无法安居乐业。又如,粤西廉江县石角镇的刘傅一姓,主要分布在榕树、山腰、田头三个管区,这三个管区90%以上的人都姓刘傅。据说,300多年前就有人这样预言:“梁断鼓烂箫不响,塘干湖溓郑归天。”其中,梁、鼓(古)、箫(肖)、塘(唐)、湖(胡)、郑等均谐音指姓氏,溓,客家话音[liam31],指水干涸,意为其他姓氏都别想在这个地方生活下去。这种以族亲为线索组成的社会群体实际上就是一种放大了的家庭。他们日常所使用的社会称谓,往往就是根据不同的性别、年龄和血统关系的远近,把家庭称谓对号入座套上其他族人。按照辈分,同乡的祖辈称为“××公”“××婆”“××叔公”“××叔婆”,父辈称为“××伯”“××伯”“××叔”“××叔”,同辈的长者称为“××哥”“××嫂”。辈分的差序是不容僭越的,因而有“白头哥,坐地叔”的说法。意思是,只要是同辈,即使是白发苍苍的老汉和乳臭未干的童稚,也必须以兄弟相称相待;但若是叔辈,还是牙牙学语的幼儿,侄辈的老汉也应当尊称他为家叔。这种亲属称谓的延伸使用是由宗族观念所决定的,它反过来又巩固和加强了血缘的关系。由于同乡同姓之内的成员都是“自家人”,所以,对内,就形成一股无形的内聚力,能互相提携;对外,则有强烈的排他性,当遇外人侵扰时,能一致地联合抵抗。因而,不但是个人,就是大家庭,也必须得到宗族的保护,才能得以生存和繁衍。客家谚语“同姓同族一家亲,打断骨头连着筋”(或说“一姓亲,一族亲,打断骨头连着筋”),“拳头向外打,手指向内弯”等就是表现这种精神的名言。客家地区的著名建筑围屋、围龙屋和土楼,亦是客家人强烈宗族观念的重要明证。在客家的群体结合中,血缘关系高于地缘联系,这是无疑的。同一宗族在迁移散居之后又派生繁衍了外地的村落,仍要联合建立大宗祠共同祭祀,并把这种祭祀活动当作宗族发展世系的重要信仰形式,利用祖灵观念与祖先崇拜,使之成为宗族体系相互团结的精神支柱。平时若遇有宗族之间的争斗,则异地同宗也必定团结一致,共同对外。
移居海外的客家人也是最有宗族观念的。日本人竹越三郎著《台湾统治志》评语:“客家是台湾最开化,最坚强和最富民族意识而不易统治的民族(按,客家为汉族一支,本身不是独立的民族,可称为“民系”引者),他们的团结力尤为惊人,以致政府当局,不得不限制他们的住居地区,使其不得聚集在一处”2。客家人的这种强烈的宗族观念在民族的危急关头可以升华为民族正义感,使他们富有保种、保族、爱国爱家的心理和同仇敌忾的精神。客家人的这种精神曾彪炳于中国近现代史册,从金田村到黄花岗到井冈山,无一没有客家人用鲜血写下的光辉篇章。但是,强烈的宗族观念也容易滋生狭隘的种族思想及小集团意识,产生内部的不团结和分裂。共同对付了外族异敌之后,接着便是内部的争斗。太平天国革命也正是因为打上了这种烙印才导致了最后的失败。
四、宗族观念与传统文化的承续
客家人强烈的宗族观念在一定程度上也促进了文化的进步。客家人对于所谓睦族、显亲扬名、光前裕后等极为重视,在这种观念的影响下,做父母的莫不希望自己的子弟能按部就班地读书。有的家长还抱着“讨食(要饭)也爱(要)缴(供)子女读书”的决心,希冀的是子女读书成名后能光宗耀祖,为家室宗族增辉。作为家长,如果自己的孩子一个个都是在家里“捏泥卵/揢泥团”(抓土块,指做农民种田),“鼻牛屎窟”(闻牛屁股,指放牛),那他们也会觉得脸上无光。而且,宗族内部编族谱、写祭文、排字辈等工作,不识字也无法做到。因而,旧时客家各宗族往往都置有相当数目的学田,将“儒资谷”(即田租)拨出一部分来作为族内子弟读书的补助费用,奖励成绩优秀的学生,如有登科,则奖赏更丰。科举时代客家地区宗族助学办学之风非常普遍,法国籍天主教神父赖理查斯曾在嘉应州传教20余年,他在清末出版的《客法词典》自序中说:“因为客家人的每一个村落都有祠堂,那就是他们祭祀祖先的所在,而那个祠堂也就是学校。全境有六、七百个村落,也就有六、七百个学校,这真是一桩骇人听闻的事实”3。可见,在现代教育兴起之前,客家地区主要是通过宗族教育来传承文化的。客家地区尊师重教风尚的形成,在一定程度上也是与客家强烈的宗族观念有关的。
综上所述,由于历史的原因,客家人普遍具有较强的宗族观念,这种观念影响了一代又一代客家人。在客家地区,不仅地名留下了宗族社会的印迹,建筑也深深地打上了宗族观念的烙印。作为客家群体标志的方言,亦不无例外地受到这种观念的影响和制约,前文的论述可见一斑。
注释:
1 马显彬.客家方言地名“围”[J].嘉应学院学报,2012(3).
2 见《外国人对客家文化的评价》.《客家研究》第一集.同济大学出版,1989年.
3 同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