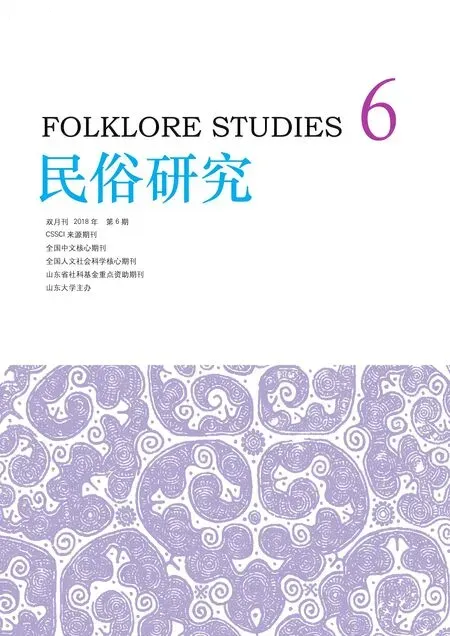中国的行业神崇拜:民间信仰、行业组织与区域社会
2018-01-23邓庆平王崇锐
邓庆平 王崇锐
在中国民间信仰异常庞杂的神灵崇拜系统中,行业神是非常独特的一种类型。所谓“行业神”,即从业者奉祀的与行业特征有一定关联的各种神祇的总称,是一种极具中国特色的行业性民间信仰文化。纵观中国学界关于行业神的研究,既有自民国时期开始的各类行业祖师信仰的调查与研究,也有概述性的通论著述,更多的则是各类行业神的个案分析,成果可谓丰硕。然而,与学者热衷于对中国民间信仰研究的总结和反思不同*中国民间信仰的研究,自20世纪二三十年代兴起以来,在近百年的学术发展历程中,早已成为民俗学、人类学、社会学、历史学、宗教学等不同学科背景的学者们共同关注的热点问题。对于相关领域的研究成果,已有很多学者进行过或全面、或专题、或阶段性的学术史梳理和理论反思,代表性的综述论著可参见王铭铭:《社会人类学与中国研究》第五章《象征与仪式的文化理解》,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路遥等著:《中国民间信仰研究述评》,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综述性文章如陶思炎、[日]铃木岩弓:《论民间信仰的研究体系》,《世界宗教研究》1999年第1期;钟国发:《20世纪中国关于汉族民间宗教与民俗信仰的研究综述》,《当代宗教研究》2004年第2期;王健:《近年来民间信仰问题研究的回顾与思考:社会史角度的考察》,《史学月刊》2005年第1期;范正义:《民间信仰研究的理论反思》,《东南学术》2007年第2期;高丙中:《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课题的民间信仰》,《江西社会科学》2007年第3期;符平:《中国民间信仰研究的主体范式与社会学的超越》,《浙江社会科学》2007年第6期;吴真:《民间信仰研究三十年》,《民俗研究》2008年第4期;陈勤建、毛巧晖:《民间信仰:世纪回顾与反思》,《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3期,等等。,关于行业神崇拜的研究,迄今却无一篇专文进行过系统梳理*对于某些单一类别的行业神信仰,也有一些综述性文章,如陈志勇关于戏神的讨论(参见《近百年来中国戏神信仰之研究》,《民族艺术》2011年第3期;《戏神研究的观念、方法与戏剧史意义》,《民族艺术》2013年第5期),但从整体上总结与反思行业神研究的文章却付之阙如。,这与中国行业神研究的学术价值与现状极为不符,也不利于研究的进一步深入。
从关注角度和研究取向来看,中国行业神崇拜的现有研究成果大致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类是循民间信仰的研究理路,或从民俗学角度考述行业神的种类、源起、各行业祖师的故事传说、通过田野调查分析行业神崇拜的仪式实践及其文化意涵,或从历史学角度考订行业神崇拜的变迁轨迹;第二类则侧重关注行业神崇拜与特定行业之间的关联,结合文集、碑刻、社会调查等文献资料,分析行业神崇拜对于行业组织的整合、维系发挥了怎样的功能;第三类则在中国民间宗教研究的“社区传统”基础上,借鉴区域社会史的研究视角,将行业神崇拜放在特定区域社会的历史发展脉络中加以考察,旨在揭示行业神崇拜的地方性特点,或透过区域性行业神信仰考察地方社会的发展进程。需要说明的是,上述分类只是为了便于概述和区分不同研究角度的特点,更多是为了叙述方便,而在具体研究实践中,这三种研究取向并不是非此即彼的,因此在介绍相关研究成果时,可能会出现互有重合的现象。同时,本文旨在说明行业神信仰研究的重要议题并对研究路径进行反思和展望,对于相关研究成果的介绍难免挂一漏万,尚祈方家指正。
一、20世纪上半叶行业神研究的起步
中国传统社会的行业神崇拜现象,大致是伴随着两种学术路径进入到学者的视野中来:一是发端于20世纪20-30年代中国民间信仰的民俗学研究取向;二是20世纪初以来中外学者对中国传统行会问题的关注。
一般认为,对中国民间信仰较早进行学科性探索的代表性学者是荷兰人高延(J.J.M de Groot 1854-1921)和法国人葛兰言(Marcee Granet 1884-1940)。而中国学者将民间信仰作为研究对象,则开始于1920年代中国民俗学的建立时期。在那个学科意识与学科分际尚未精细化的年代,兼顾文本与田野的民俗学者秉承“到民间去”“唤起民众”的文化自觉,将研究目光投向“民众生活上的一件大事”——朝山进香。[注]顾颉刚:《妙峰山进香专号引言》,李文海主编:《民国时期社会调查丛编(一编)·宗教民俗卷》,福建教育出版社,2014年,第55页。在20世纪的20-30年代,顾颉刚等人组织了关于北京妙峰山进香活动的田野调查,江绍原、容肇祖、许地山等学者撰写了关于民间社会各种迷信活动的分析研究,北京大学《歌谣》周刊、中山大学《民俗》周刊发表了大量各地风俗迷信的调查报告和评介文章,这一系列或旨在关注民众生活、或旨在批判信仰活动的反科学性进而改造社会的学术活动,开启了“中国民间信仰的民俗研究取向”[注]陈进国:《中国民间信仰研究述评——以大陆地区为中心》,路遥等著:《中国民间信仰研究述评》,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42页。。作为一种独特的民间信仰,行业神崇拜正是在这样的学术语境下开始受到学者们的关注。
早在顾颉刚关于北京妙峰山进香活动的田野调查中,就已经发现香会中有一些“职业团体”,如万寿善缘缝绽会,由“皇城内外新旧靴鞋行旗民人等诚起”,为沿路香客免费修鞋;又如拜席老会,是京城席业行业公会,为妙峰山沿路茶棚提供各种用席;还有京城“正阳、崇文、宣武门外”铜锡匠行结成的乐善巧炉圣会,专在中道沿路茶棚为香客补修铜锡瓷器等等。[注]顾颉刚:《妙峰山的香会》,李文海主编:《民国时期社会调查丛编(一编)·宗教民俗卷》,福建教育出版社,2014年,第69-70页。顾颉刚并没有说明这些“职业团体”前来朝山进香的原因,倒是全汉昇在研究中国行会史时进行了解释:“为什么各行会都来这么远的一个山上来进香呢?原来各行的祖师——如技巧工人所崇拜的鲁班及一般行会所祭奉的关帝及财神的神位或神殿都在这里。”[注]全汉昇:《中国行会制度史》,上海新生命书局,1934年,第130页。这类关于中国行业神信仰的记述,零散见于民国时期各地民俗文化的社会调查中,但大多非常简略,更不是专题性的研究。
这一时期,出现了两部以行业神崇拜作为专门研究对象的代表作,一部是刘佳崇璋的《北平各行祖师调查记略》,一部是叶郭立诚的《行神研究》。前者是田野调查报告,后者则是真正意义上的学术研究论著。
刘佳崇璋对20世纪上半叶北京各行祖师进行过系统的调查,并写有至少8集的《北平各行祖师调查记略》[注]刘佳崇璋:《北京各行祖师调查记略》,首都图书馆藏传抄本,1961年。,被学者誉为“专门将祖师爷作为一个单独的题目进行调查研究的首创者”[注]岳永逸:《磕头的平等:生活层面的祖师爷信仰——兼论作为主观感受的民俗学》,《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3期。。但是,目前仅能在首都图书馆看到调查纪略第8集的传抄本,在这一集中,刘佳崇璋记载了酸梅汤摊贩、大饽饽铺、农园和茶馆四种行业的祖师。从这保存下来的唯一一集中,可以看到刘佳崇璋对于当时北京城中各行业祖师的调查非常全面,不仅细述各行业祖师崇拜的来源、传说、奉祀情况,还尽可能展示各行当的日常运营、发展状况及其社会环境,甚至还精细描绘了各行器具的示意图,如酸梅汤摊贩的铜招子、冰盏碗儿,饽饽铺的吊炉、闷炉、皂炉三种不同的灶具,将行业神崇拜的文化意涵、行业生存的社会情境融于日常生活的具象化中。所以,学者认为刘佳崇璋的调查“有着今天国内学界还在广为效仿西方的‘延展/伸’的情境分析方法(situation analysis)的意识”,具有极高的学术价值,“从调查纪略的文本本身而言,这本在半个多世纪以前的调查纪略有的理念、方法并不逊色于以善于调查著称的日本学人和改革开放后群起效法西方的国内诸多学人”。[注]岳永逸:《磕头的平等:生活层面的祖师爷信仰——兼论作为主观感受的民俗学》,《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3期。
1946年,叶郭立诚撰写完成《行神研究》一书,这是第一部以行业神崇拜作为研究对象的学术专著。[注]叶郭立诚:《行神研究》,(台北)中华丛书编审委员会,1967年。据作者自序,可知该书“脱稿于民国卅五年秋,藏之于行篋二十年”。其实,早在20世纪30年代末叶郭立诚已经主持了对北京东岳庙的调查,撰有调查报告,其中对东岳庙中的行业神殿堂——显化司、鲁班殿、马王殿、喜神殿以及行业团体的祀神活动有过简略记述。[注]叶郭立诚:《北平东岳庙调查》,李文海主编:《民国时期社会调查丛编(二编)·宗教民俗卷上》,福建教育出版社,2014年,第149-150页。《行神研究》一书体例完备,除去引言与结语,全书共分为九章,即行神定义、行神分类、行神史料研究、工业行神、商业行神、职业行神、行神祈祀、北平行神庙宇,涉及了行业神崇拜的各个方面,奠定了后来学者讨论这一问题的基本框架。对于何谓“行神”,叶郭立诚首次给出了全面、清晰的定义:
行神者即同业者共同崇奉的神祇,即俗所谓“祖师爷”也。吾国行会,每推一历史上或传说上的名人与神为本行的祖师,斯人或神即为本行业的发明者,利用此崇拜的中心以召集团体,统治会中份子,推进本行业务,行会领袖即为行神的主祭者,每年于行神的诞日例有大祭,斯时会员全体出席,祭后即举行会议,商定本会公共事宜,选举会首,改定官价,处罚犯规者,咸在神前举行,以示其神圣尊严与公平无私,最后共享神胙,更有献戏娱神,即以自娱,藉此联络感情,加强团结焉。[注]叶郭立诚:《行神研究》,(台北)中华丛书编审委员会,1967年,第3页。
这一定义不仅涉及行业神的基本内涵,也包含了行神的来源、奉祀仪式以及社会功能。依据行业性质的不同,叶郭立诚将行业神分为工业行神、商业行神、职业行神三类,再细分为若干类别(如工业行神就划分为土木建筑、家具、衣服装饰、饮食品、书籍文房用品、药及消费品、杂项共七类)进行逐一说明。同时,作者对于不同行业奉祀本行祖师神的仪式实践也做了详细的研究,包括祭祀祖师的目的与会期、公费的筹款方法、酬神演剧等祭祀活动内容等等,均一一述之。特别难能可贵的是,叶郭立诚还将记录行业神信仰文化的书籍分为民间俗籍、传统典籍、外人研究三类进行了史料梳理,对于继续推进这一问题的研究可谓助益甚多。
除了上述中国民间信仰研究视域下行业神的调查与研究外,20世纪初中外学者对中国传统行会的关注,是中国行业神研究进入学者视野的另一个机缘。中国行会史研究的起步,最早可以追溯至19世纪末20世纪初,主要是一些外国人撰写的田野调查性质的论著。直到1909年马士(H.B.Morse 1855-1934)出版《中国行会考》一书,才代表着西方学者对中国行会史的关注转向了较为深入的学术研究。《中国行会考》将中国行会分为手工业行会、商人会馆和商人行会三类加以考察,在手工业行会和商人会馆两类中,都设有“共同崇拜”一节,讨论中国传统行会内部的宗教信仰问题,并与西欧行会进行对比。马士已经观察到中国各行会存在“共同的行会崇拜的迹象”,出现了“与某些寺庙相联系的行会”,行会“与宗教的结合”是一种惯例,比如在温州,药行要求其新成员付一笔入会费给药神庙,铁匠行的行规则明确规定“在城市庙堂里召集会议,在戏剧娱乐和宴席期间”商定工资价目和商品价格。[注]参见彭泽益主编:《中国工商行会史料集》(上册),中华书局,1995年,第63-64页。但由于马士在讨论中国行会的共同崇拜时,更多的是将英国行会中的宗教互助会作为参照系,因此,他更关注的是教派、宗教感情等西方宗教文化语境中生发的问题,而对独具特色的中国行业神崇拜则着墨极少。
创办燕京大学社会学系的美国传教士步济时(J.S.Burgess 1883-1949),在20世纪20年代曾多次主持北京地区的社会调查,在此基础上,他于1928年撰写完成了他的博士学位论文《北京的行会》,这是中国行会史区域性研究的代表作。[注]J .S .Burgess,The Guilds of Peking, New York , 1928. 中译本参见[美]步济时:《北京的行会》,赵晓阳译,清华大学出版社,2011年。步济时调查了北京及附近地区包括缝纫业行会、盲人行会、木器业行会、靴鞋业行会、理发业行会等在内的42个行会,调查人员采访行会负责人并详细记录访谈资料。在这些调查内容中,就包括了行会的行业神祭祀活动,涉及行业神的名称与祭奠活动、行业成员对行业神祭祀的看法等。差不多同一时期,日本学者也对北京地区的行会开始进行深入的实地调查和研究,持续到20世纪40年代,陆续编纂了《北京工商ギルド资料集》六辑[注][日]仁井田陞辑,[日]佐伯有一、[日]田仲一成编注:《北京工商ギルド资料集》(1-6册),(东京)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附属东洋学文献センター刊行委员会,1975-1983年。。调查人员对北京的工商行会进行调查,并一一抄录了民国时期尚存的明清以来北京各手工业行会、会馆的碑文和匾额,同时对行会组织成员和从业者进行了访谈,这些碑文和访谈资料,都大量保存了北京地区行业神信仰及祭祀活动的内容。《北京的行会》与《北京工商ギルド资料集》都采用了西方现代的社会学调查方法,不仅较为真实地反映了当时不同行业从业人员的信仰文化和心态,更揭示出近代社会转型过程中北京各类行会在祭祀行业神以及行业组织整合方式上的深刻变化。
中国学者的行会史研究则以20世纪30年代全汉昇出版的《中国行会制度史》为代表,这是第一部由中国学者撰写的研究行会史的学术专著。[注]自20世纪20年代始,已陆续有郑鸿笙、成信、张景苏、谢征孚等人发表了行会史的论文。参见朱英:《中国行会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历史研究》2003年第2期。该书从中国行会的起源及早期的手工业行会和商业行会讲起,然后按时间顺序对隋唐、宋代、元明、近代的行会分别加以论述,另撰专章讨论会馆。在论述不同时期的行会时,该书都设有专节讨论行会崇拜本行祖师的宗教活动,并认为这种崇拜活动主要是为了行会的“一致团结”。全汉昇还注意到中国的行业神崇拜有一个变化的过程,即“唐宋时代的工商业行会常祭祀其所在地的神”,而元明清以后才逐渐改为专祀行业祖师神。[注]全汉昇:《中国行会制度史》,上海新生命书局,1934年,第2页。
综上所述,20世纪上半叶,伴随着中外学者对于中国民间信仰与行会问题的关注,中国行业神问题的研究开始起步。在这两种学术路径下的行业神研究,都呈现出田野调查与文本研究相结合的特点,应该说,这为进一步开展相关研究开创了有利的局面。但在1949年后,由于受到国家政策的影响,在破除迷信的全国性运动下,行业神崇拜在社会上几乎绝迹,研究也就无从谈起。直到20世纪80年代,随着民俗学界、历史学界特别是社会史学界民间信仰研究的复兴,行业神才又重新回到研究者的视野中来。
二、作为民间信仰的行业神崇拜
1980年以后,民间信仰研究在大陆学界回归,强调“民间信仰”作为民间文化形态的存在而非其宗教属性成为当时学界的共识和策略选择,“民间信仰”而非西方语境下的“民间宗教”成为大陆学界通行的用法。[注]吴真:《民间信仰研究三十年》,《民俗研究》2008年第4期。伴随着民间信仰研究的复兴,行业神也逐渐引起学者的关注,出现了一批相关的专题研究论著,如李乔的《行业神崇拜——中国民众造神运动研究》一书,是目前可见行业神研究成果中最为全面的通论性著作。在对大量历史文献和调查采访资料进行整理考辨的基础上,作者对各行业不同的行业神源流、特征等方面进行了初步的考察和介绍,共涉及17大类、150多个行业的祖师神及单纯的保护神。[注]李乔:《行业神崇拜——中国民众造神运动研究》,中国文联出版社,2000年。此书是《中国行业神崇拜》(中国华侨出版公司,1990年)的增补版。王作楫在《中国行业祖师爷》一书则讲述了90多个行业的行业祖师,但多为概述性的介绍。[注]王作楫:《中国行业祖师爷》,中国文史出版社,2007年。另外,在一些对中国民间信仰进行综合研究的著作中,也涉及到行业神信仰的问题,或整理史籍中记载行业神的史料,或简单介绍中国历史上的行业神崇拜现象。[注]如宗力、刘群:《中国民间诸神》,河北人民出版社,1986年;金泽:《中国民间信仰》,浙江教育出版社,1989年;雪犁主编:《中华民俗源流集成(信仰卷)》,甘肃人民出版社,1994年;殷伟、殷斐然:《中国民间俗神》,云南人民出版社,2003年;乌丙安:《中国民间神谱》,辽宁人民出版社,2007年;马书田:《中国俗神》,团结出版社,2007年。当然,数量更多的还是大量的行业神个案研究。无论是通论性还是个案式的行业神研究,论者大多循着民间信仰研究的理路,探讨行业神的类型、源流、特点、仪式、变迁和功能等诸多内容。
从行业神的主要功能着眼,行业神分为祖师神和单纯保护神两类[注]李乔:《行业神崇拜——中国民众造神运动研究》,中国文联出版社,2000年,第11页。;依照行业系统,则可以分为工业行神、商业行神、职业行神三种;而依神祇本身的来源,则分为传说或“实在的发明者”与“本为天神而被附会推崇为祖师爷”两种类型[注]叶郭立诚:《行神研究》,(台北)中华丛书编审委员会,1967年,第5页。。对于行业神的起源,受史料限制目前已不可考,但至少可以肯定的是,行业神崇拜现象的出现是以行业分工为前提的。在上古时代,行业分工尚未出现或者说分工水平较低,当时对创始神的崇拜,主要是全民崇拜的性质,伴随着社会分工的细密和行业观念的增强,人们对创始神的崇拜逐渐具有行业性,并过渡到后来的祖师神崇拜。[注]李乔:《行业神崇拜——中国民众造神运动研究》,中国文联出版社,2000年,第17页。李亚农曾推测祖师崇拜溯自春秋战国时期,他主要是从手工业是否发达的角度加以推论,并没有述及关于当时信仰状况方面可凭支撑的史料。[注]李亚农:《中国的奴隶制与封建制》,华东人民出版社,1956年,第121页。从史料出发,李乔认为行业神崇拜至少可以上溯至隋唐以至南北朝时期。唐文宗时人赵璘的《因化录》卷三就有关于茶贩祭祀陆羽的记载,唐宪宗时人李肇所撰《唐国史补》卷下记有酒库祀杜康,这些祭祀活动都将所祀对象作为祖师加以供奉,业缘关系相对明确,这说明唐代已有祖师崇拜活动。[注]李乔:《行业神崇拜——中国民众造神运动研究》,中国文联出版社,2000年,第19页。而根据王永平的研究,随着工商业的发展、行业分工的加强以及行会组织的出现,行业神崇拜在中唐时已很普遍。[注]王永平:《论唐代的行业神崇拜》,《首都师范大学史学研究》(第1辑),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99-107页。宋代行业神崇拜得到更大的发展,宋人的笔记中已有较多行会祭神的记载,如“每遇神圣(北极佑圣真君)诞日,诸行市户俱有社会,迎献不一。如府第内官以马为社,七宝行献七宝玩具为社……鱼儿活行以异样龟鱼呈献”[注](宋)吴自牧:《梦粱录》卷十九“社会”条,中国商业出版社,1982年,第214页。。可以看出,在真武大帝诞辰时,各行会都会陈设本行的物品来祭献,以为祈福。当然,真武大帝只是在保护神的意义上被各行供奉。宋人蔡绦的《铁围山丛谈》中记有关中饼师“每图(汉)宣帝像于肆中”的现象[注](宋)蔡绦:《铁围山丛谈》卷六,中华书局,1983年,第107页。,应可视为糕饼行崇拜祖师神的记录。明清时期行业神崇拜现象日渐繁盛,所谓“百工技艺,各祠一神为祖”[注](清)纪昀:《阅微草堂笔记》卷四,浙江古籍出版社,2015年,第54页。。祖师神传说更趋繁杂,神灵种类不断增多,祭祀庙所逐步扩展,祖师诞辰、赛会等各种祭典仪式的程式化大有提高,规制日隆,行业色彩浓厚的祭祀组织大量出现,成为行业神崇祀活动的组织依托。
清末以来,尤其民国以后,行业神崇拜不断衰落。李乔认为近代大工业文明的发展和科学的日益昌明导致了行业神崇拜的衰亡,但并没有展开具体的论证。[注]李乔:《行业神崇拜——中国民众造神运动研究》,中国文联出版社,2000年,第20页。这种一般性的结论“更像是受既定的进化论观念影响而产生的印象,或者称之为一种在现代主义意识形态规定之下的‘常识性判断’”,沈洁认为反迷信运动固然与近代大工业文明的兴起和科学进步直接关联,但具体的过程也很难“一言以蔽之”。虽然从传统行会到近代工商业组织的改革引导了行业神崇拜衰落的总体方向,但信仰仪式的变化仍然是在延续的前提下发生的,“文化情感的牵系和实利主义的祈禳”是其得以延续的重要原因。[注]沈洁:《仪式的凝聚力:现代城市中的行业神信仰》,《史林》2009年第2期。董虹以华北地区为例勾勒出近代行业神承袭和演变的整体印象,把近代华北地区行业神崇拜衰落的原因归结于工商行会的组织变革、科举考试的取消以及战争和社会动荡。[注]董虹:《近代以来行业神信仰的变迁——以华北地区为例》,《山西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5期。丁晓冰对造纸业祖师神的研究则为我们讨论行业神崇拜的近代变迁提供了典型个案,从以秘密传承为主到对技术本身的掌控取代了对行业神的心理依赖,行业技艺传承方式的变化同样是构成祖师权威衰落的因素之一。[注]丁晓冰:《试论中国传统造纸业的行业神信仰》,色音编:《民俗文化与宗教信仰》,知识产权出版社,2012年,第169-180页。虽然上述研究可能仍然无法揭示行业神崇拜近代变迁的全部面向,但却提醒研究者注意在近代化这一宏大叙事框架下,行业神崇拜在不同区域、不同行业内部呈现出复杂多元的变迁轨迹。比如同处近代以来国家宗教政策和科学话语对迷信的批判形成的整体性压抑氛围中,不同行业的从业者关于行业神信仰和祭祀活动就各有不同的认知,如北京“袼褙业行会告诉我们,宗教祭奠仅仅‘是个传统,没有什么真用处’”,“理发业行会认为‘谋生问题要比宗教重要得多’”,皮货业行会则说“祭奠是件不重要的事情,但通过集会而体现团体精神是非常有用的”,木器业行会“建立行会的主要目的是祭奠祖师,向他传下来的技艺表示感谢”。[注](美)步济时:《北京的行会》,赵晓阳译,清华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155页。
仪式是民间信仰的重要内容,研究者也多注意从祭祀仪式入手讨论行业神崇拜现象。行业神的祭祀按照参与的人群和形式划分,主要有同行从业者自发的个体性恭祭,以及在行业组织形成后有组织的奉神两种类型。一般选择在神诞日、时令年节、店铺开张开业、拜师出徒、年例会议等场合进行迎神赛会或敬神献戏。岳永逸利用民国时期的行业神调查资料,讨论了“以磕头为基本动作的身体实践的祖师爷信仰”,将说唱艺人的祖师爷周庄王崇拜置于从业群体的日常生活中,说明磕头仪式在拜师、婚姻、表演、师徒关系等方面的体现。作者从个体与群体心态的视角来研究生活层面的祖师爷,试图将祖师爷信仰“还归特定群体日常生活”而非剥离,最终以行业神祭拜仪式的个案研究探索作为“主观感受的民俗学”如何成为可能。[注]岳永逸:《磕头的平等:生活层面的祖师爷信仰——兼论作为主观感受的民俗学》,《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3期。
祭祀行业神的空间一般有三种,有附祀寺观中者,有自建会馆内设祠堂者,有借饭庄等公共地点的。[注]叶郭立诚:《行神研究》,(台北)中华丛书编审委员会,1967年,第144页。祭祀空间的建筑样式深受信仰习俗的影响。具体来说,这种影响主要体现在行业神奉祀对会馆和寺庙空间形态的塑造方面,王莹、李晓峰就从仪式空间的角度讨论了两者的关联性,角度颇为新颖。[注]王莹、李晓峰:《行业神信仰下西秦会馆戏场仪式空间探讨》,《南方建筑》2017年第1期。而寺庙道观也因为行业神的进入改变了既有的建筑模式,比如北京东岳庙西廊诸殿就附祀很多行业神,成为东岳庙功能各异、层级分明的三重空间的建筑群之一。[注]楼萑蔺:《北京东岳庙及其建筑群的宗教文化内涵探析》,华东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1年。
采用功能主义的分析视角,强调神灵崇拜的社会功能,是民间信仰研究的常见方法,也为行业神的研究者所重视。一方面,面对来自社会和自然环境不确定风险的威胁,各行业从业者求神保佑、祈福禳灾的诉求非常强烈;另一方面,在存在差序和层级的社会体系中,通过祖师神的身份塑造以提高自身的社会地位,成为通行做法。在流传的俚语中,如厨业的“易牙本是我的祖,我们祖师也高贵”,打铁匠的“敬德也曾打过铁,老君的门徒不累赘”等,就集中体现了各手工业者希望借助抬高祖师神的地位以抬高本行业的心态。[注]殷凯:《北京俚曲》第三辑“十女夸夫”,太平洋书店,1927年,第265-270页。对于旅外的客籍从业者而言,以神集众、增强同业乡人在异地的凝聚力则是其首要功能。[注]郑永华:《清代北京业缘商馆宗教民俗的社会功能试探》,《北京历史文化研究》2007年第2期。从行业发展的角度看,对祖师神的推崇不仅可以加强同业者的敬业精神,勉励新入行者勤学苦练,努力业务,还可以“广造声势,利于宣传”[注]王锐:《市井商情录——中国商业民俗概说》,河北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159页。。旧时北京的药铺就会在药王诞辰减价促销[注]张次溪:《北平岁时志》卷四,文海出版社,1985年,第88页。;“药材不到祁州,没有药味”,河北安国之所以形成较大的药材交易市场,也与“药王的权威”有关。[注]郑合成:《安国县药市调查》,李文海主编:《民国时期社会调查丛编(一编)·宗教民俗卷》,福建教育出版社,2014年,第183页。实际上,不同的信仰群体崇祀行业神的目的也是不同的,以马神崇拜为例,马市、马行或驴市、驴行的弟子们祭祀马神,主要是出于一种祈求庇佑和感恩酬报的心理,而骡马车夫则更为直接地出于现实利益利用马神这一“象征资源”[注]邓庆平:《明清北京的马神崇拜及其功能、意义的转变》,《北京社会科学》2006年第2期。,在马神诞日,“车价昂至数倍,向客婪索,名曰:乞福钱”[注]李家瑞编:《北平风俗类征》,上海商务印书馆,1937年,第85页。。所谓的“乞福钱”,就是以马王之祭为借口向客人多收费。因而,注意不同的信仰群体对行业神赋予的不同功能和意义,将有助于多维度地理解行业神崇拜所构建的信仰空间及其社会生活基础。也有学者探究行业神崇拜超越行业团体而之于社会的作用,认为行业神的出现可视为商人对传统伦理文化的积极吸纳与利用,弥补了国家统治力量的不足。[注]李和承:《明代传统商人与职业神》,《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2年第1期。不可否认,这些实用功能构成了行业神崇拜得以长久延续的基础。
三、行业神崇拜与行业组织
在中国历史上,行业神崇拜是中国传统行会的重要活动之一,围绕共同的行业神信仰和内容丰富的祭祀活动,诸多行业往往组成了具有香会组织特点的行会组织或行业色彩浓厚的香会组织,行业神崇拜也就成为这些业缘性社会组织得以整合、维系的精神纽带,为此行业内部往往通过祭祀组织展开有序的整合与管理。因此,透过行业神的研究,可以理解中国传统业缘性社会组织的构成方式与运作机制。研究行会史的学者曾提出应该结合经济史方面的研究,同时又从文化学、宗教学的角度对行会祀神活动进行分析,以拓展行会史研究的主题[注]朱英:《中国行会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历史研究》2003年第2期。,这是20世纪上半叶行业神研究初兴时已经具有的学术传统,也是深化中国传统行业性团体研究的应有之义。
行业神与特定行业紧密相关,学界围绕着单一行业的行业神崇拜,已经涌现出相当数量的个案研究成果,主要集中于梨园行[注]由于戏曲史研究的不断开拓,与其他行业相比,戏神崇拜的研究成果也更为丰富,如廖奔的《戏神辨踪》(《民俗研究》1996年第1期),康保成的《中国戏神初考》(《文艺研究》1998年第2期)与《中国戏神再考》(《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8年第6期、1999年第1期),黎国韬的《二郎神之祆教来源——兼论二郎神何以成为戏神》(《宗教学研究》2004年第2期),陈志勇的《戏曲行业“二郎神”信仰的生成与消歇》(《民族艺术》2013年第3期),等等。、盐业[注]由于古代盐铁专营,盐神的信仰者既包括盐工、盐商,又包括盐官、运吏,体现了浓厚的官方色彩。相关研究成果,如宋良曦的《中国盐业的行业偶象与神祇》(《盐业史研究》1998年第2期)、张艳丽的《太公配飨 地方先贤 盐业之神——论古代官方祀典系统里的管仲形象》(《管子学刊》2011年第3期),于云洪与王明德的《盐业神祇谱系与盐神信仰》(《扬州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3期),王俊芳的《盐神信仰的表现形式及深层原因》(《兰台世界》2015年第34期),等等。、药业[注]药王不仅是药业的行业神,又是一般民众的生活保护神,应本着具体分析的态度,不能一概论为行业神。将药王作为行业神研究的相关成果有:赵晋《药王崇拜与安国药都的形成和发展——对一种商业神崇拜现象的宗教社会学分析》(《昆明大学学报》2006年第1期),马兰《安国药王庙庙会的类型及文化内涵》(《大众文艺》2011年第11期),杨建敏《河南新密药王信仰与药王庙考证》(《中医学报》2011年第3期),廖玲《清代以来四川药王庙与药王信仰研究》(《宗教学研究》2015年第4期),等等。、交通运输业[注]交通运输业的行业神信仰主要集中于马王神崇拜,成果主要有邓庆平《明清北京的马神崇拜及其功能、意义的转变》(《北京社会科学》2006年第2期)、林移刚《清代四川马神崇拜研究》(《兰台世界》2013年第18期)、李龙《马神形象的经典塑造与戏剧重构》(《宗教学研究》2015年第1期)等。、煤窑业[注]煤窑神崇拜与煤炭资源的分布密切相关,显现出资源导向型社会的特征。相关成果有:段友文《山西煤文化与煤神崇拜》(《民俗研究》1993年第4期)、刘雅娟《山西大同矿区煤神信仰研究》(山西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2年)、潘惠楼《北京煤窑神探析》(《河南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2期)等。、制瓷业[注]陶瓷业行业神崇拜主要集中于景德镇地区,如刘毅《陶瓷业窑神崇拜述论》(《景德镇陶瓷》1997年第3期)、王小军《景德镇制瓷业行业神崇拜研究》(《江西社会科学》2004年第12期)、李兴华等《景德镇窑神崇拜与象征空间的构建——以风火神童宾为个案研究》(《内蒙古大学艺术学院学报》2011年第4期)等。、娼妓业[注]如张艳丽《管仲为娼妓行业神考述》(《中国性科学》2013年)、刘平《近代娼妓的信仰及其神灵》(李长莉、左玉河主编:《近代中国社会与民间文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等。、蹴鞠业[注]如赵宁、董杰《论古代蹴鞠的行业神崇拜——以〈蹴鞠谱〉为中心的考察》(《管子学刊》2014年第3期)、郭晓光《“蹴鞠”行业神源考》(《兰台世界》2015年第10期)等。、书坊业[注]王成:《从琉璃厂书坊业行业神信仰中看书商的竞争与联合》,张妙弟主编:《人文北京与世界城市建设——2010年北京学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同心出版社,2011年。、说书业[注]卫才华:《艺术性与神圣性——太行山说书人的民俗认同研究》,《民俗研究》2018年第2期。等。当然,有的行业神因为受到广泛崇拜,研究也相对丰富;有的仅限某一区域,知名度相对较小,研究因而薄弱,显现出研究不均衡的现象。尽管如此,那些知名度相对较低、影响力偏于一隅的行业神仍被研究者挖掘出来,开拓了行业神崇拜的研究广度,是研究向前推进的必经阶段。
中国的行业神信仰主要体现为行业组织的群体性崇拜。中国的行业组织一般认为产生于隋唐时期,称为“行”,宋元至明初称为“团行”,明中叶至清代以来又称“公所”和“会馆”。明清时期是行业神崇拜的鼎盛时期,也是行业组织供奉行业神空前兴盛的时期,此时关于行业组织奉神活动的规定,常被写入行业组织的章程和规约中,用以团结与约束同业。因而在行业组织的研究视野下对行业神崇拜的讨论,除一般性的介绍外[注]多集中于对会馆神灵文化的介绍,比如王日根的《论明清会馆神灵文化》(《社会科学辑刊》1994年第4期)、宫宝利的《清代会馆、公所祭神内容考》(《天津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8年第3期)、郑永华的《清代北京业缘商馆的宗教民俗——以神祇奉祀为中心的探讨》(袁樊栓编:《北京风俗史研究》,北京燕山出版社,2007年),等等。,则多侧重于行业神崇拜之于行业团体作用的分析。藉着工商业者可以依赖的神祇举行共同崇祀的宗教活动为号召,“是各工商团体发起人得以召募成员进行结社的一项有效手段”[注]邱澎生:《十八、十九世纪苏州城的新兴工商业团体》,台湾大学出版委员会,1990年,第90页。,而为了保证祀神活动的正常进行,各行从业者轮流承担祭祀责任并分别设立祀产,制定章程和管理制度,同业的经营管理通过共同祭祀的形式得以实现。[注]黄挺:《会馆祭祀活动与行业经营管理——以清代潮州的闽西商人为例》,《汕头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2期。由于“人无论智愚,未有对明神而敢肆厥志者”[注]同治四年《重修正乙祠整饬义园记》,李华编:《明清以来北京工商会馆碑刻选编》,文物出版社,1980年,第14页。,因此行会往往借祖师神来约束同行,比如行会资金的筹集一般根据各铺号自己出售的商品进行“征税”,这就需要对各号账目进行检查,在年度会议上,行会成员需要在行业神面前祭祀宣誓并上交自己的账本报告,造假者将要受到严惩,而违反行规的雇工和学徒则要跪在祖师爷神像前受罚。行会借神威保证了行规的执行,同时又以行规的形式巩固了神威,正是在这种互动中,实现了对行会的经营管理。[注]孙斌:《试析神明祭祀与清代行会活动的互动与影响——以苏州地区碑刻史料为视角》,《苏州教育学院学报》2015年第3期。除了有益于行会的秩序和管理外,行业神崇拜还有加强行会组织内部团结和凝聚力的作用,如童书业即指出,“近代行会为求团结起见,对于本行的祖师,都极端崇拜,遇祖师的诞辰,有热烈的庆祝,以作纪念,如木工的崇拜鲁班,鞋匠的崇拜鬼谷子,都是例子”[注]童书业:《中国手工业商业发展史》,齐鲁书社,1981年,第183页。。有的学者将重点进一步转向以行业神为主的“象征文化体系”的创造过程及其背后的权力关系,讨论了会首是怎样巧妙地利用原有的神异性权威来加强传统权威,从而设计和控制会馆的日常运作秩序,而以会首为代表的传统权威对来自官方“神道设教”方式的制约表现出良好的合作态度,则体现出社会群体对国家的依附。[注]张涛、王永芬:《清代会馆祭祀制度研究》,王芸主编:《北京档案史料》,新华出版社,2003年,第251-266页。
行业神崇祀是中国传统行会最常见的活动之一,因而对于行业神的研究也引发了关于中国行会起源问题的“宗教团体说”的争论。近代中外学者在对中国行会组织进行的实地调查中,就已经注意到行业神崇拜对行业团体的凝聚作用。马士据此认为中国行会可能起源于宗教团体,以为“行会最初不过是崇拜手工业、商业等想象上的创始者(如泥水行之于鲁班先师,药材行之于药王菩萨)的人的结合,至于它的种种经济的机能是后来才发达的”,全汉昇对此加以反驳,认为“这种宗教上的崇拜只能算是加重行会团结的手段,绝不是产生行会的母体”[注]全汉昇:《中国行会制度史》,上海新生命书局,1934年,第2页。。李乔基本认同后者的观点,认为行会是先有了经济利益上的需求,然后才有供奉祖师等行业神的活动[注]李乔:《行业神崇拜——中国民众造神运动研究》,中国文联出版社,2000年,第78-85页。,奉神只是手段而非目的。在行会形成时间的讨论中,陈宝良强调商业社团与民间宗教社团“关系非浅”,唐代民间流行宗教“社邑”,而有些社邑则由商业同行联合组成,如房山石经天宝年间题记中出现的“小彩行社”“绢行社”等。[注]陈宝良:《中国的社与会》,浙江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215-216页。
近代以来随着新式工商同业组织的兴起,行业组织的整合方式发生变革,传统行会以行业神作为维系同业团结的精神纽带,借神威约束同业,而近代商会制度达成的行业整合,则更多依赖于利益认同、大众媒介的信息传播、法律的威权以及民主参与等更具现代性的途径。[注]虞和平:《商会与中国早期现代化》,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90-193页。行业神崇祀促成的行业聚合,最终被近现代工商同业组织的制度化、规范化管理逐渐取代,传统行会中松散的祭祀组织也被近代科层化的组织机构取代,因此,研究近代行会史的学者大多认为,相比旧式行会而言,近代工商同业组织的重要变化之一就是祀神功能的弱化。[注]彭南生:《行会制度的近代命运》,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97页。但这一变化过程并非单线性的、一蹴而就的,在行业神信仰整体式微的总趋势下,不同行业、各行业内部的变迁轨迹呈现出复杂的景象。沈洁分析了近代昆明、苏州、北京、上海等地同业公会在放弃与继承传统行业神祭祀仪式上的不同选择,并以此说明中国社会现代化改造的复杂性和多元性。[注]沈洁:《仪式的凝聚力:现代城市中的行业神信仰》,《史林》2009年2期。裴宜理在研究上海罢工时,也注意到共同的行业神信仰和崇拜仪式对于整合近代工人阶级的积极作用。以民国年间上海的机器制造业为例,这类工厂有许多改造自从前的白铁工场,传统时代,白铁工场的学徒在其3年学徒期开始之前,都必须持香向师傅和李老君各行三磕头礼。进入现代社会,上海的新式制铁工厂里仍然普遍盛行着这类仪式。不仅如此,拜祭行业神这一传统仪式在工人罢工运动的组织过程中还发挥了重要的聚合与联结作用,如1919年10月上海市油漆工人罢工前,就“先在公所里举行由来已久的仪式,在神祇面前焚香祷告”;1920年初,5000多名中医药剂师也是在“药王庙举行了一次总集会后”,进行了一次要求增加工资的罢工。[注][美]裴宜理:《上海罢工:中国工人政治研究》,刘平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41页、第102-103页。上述研究成果足以说明,旧式行会中的各类行业神信仰、庙宇等神圣空间和仪式传统,在近代中国社会的工业化和商业的现代化过程中,不仅仍然有不同程度地延续,还从另一个有趣的角度展现出新时代的文化重构和社会整合过程。
四、区域社会视野下的行业神崇拜
1990年以来,随着中国各地民间信仰活动的复兴,民俗学、人类学、历史学、宗教学等不同学科的学者纷纷意识到地方神明崇拜研究的潜力和学术价值,开始了“走向社区传统”的民间信仰研究。[注]吴真:《民间信仰研究三十年》,《民俗研究》2008年第4期。在此之前的20世纪60-70年代,西方学界对中国社区宗教传统的研究便已始具雏形,80-90年代后则以迅猛的速度发展起来。参见[美]康豹:《西方学界研究中国社区宗教传统的主要动态》,李琼华译,陈进国校,《文史哲》2009年第1期。透过地方性的民间信仰,研究者可以考察特定区域的民间文化、社会组织形态与动员机制、资源竞争、族群关系、市场体系等社会秩序的各个面向。简言之,地方社会的大小神明与神庙的仪式和象征体系,不仅可以呈现不同层级的社区系统的结构,更可以反映这一结构的历史过程,或者如高丙中所说:地方神崇拜的研究“都在有意无意地回答一个问题:特定的神的信仰如何使一个地方在时间、空间上成为‘这一个’地方”[注]高丙中:《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课题的民间信仰》,《江西社会科学》2007年第3期。。
作为一种独特的民间信仰类型,行业神研究也体现出“社区传统”的学术取向。由于行业神崇拜与特定行业及其群体紧密相关,区域性行业神崇拜对于揭示地方的产业结构、经济生态与社会网络有着重要的研究价值,特别是由于一些行业在地方发展成为主业,行业神崇拜的影响由行业扩大到地方社会,单一行业神崇拜“升格”为地方信仰,比如山西的煤炭业、景德镇的瓷窑业等。因此,对较有特色的区域性行业神信仰的考察,也逐渐成为深化行业神和区域社会研究的一条重要路径。论者多从“行业神与地方社会”出发,将行业神崇拜置于地方社会的历史发展脉络之中进行讨论,涌现了一些较有深度的个案研究。
景德镇是典型的产业型市镇,随着瓷业经济的发达,不同从业人群出于不同的原因和目的崇奉行业神的活动日益繁盛,形成了以御窑厂神灵崇拜为主导的官方信仰体系和以风火神童宾崇拜为核心的民间信仰体系,这种信仰格局随着社会变迁发生了剧烈的演变。从作为财神象征的华光神被作为忠义象征的关帝取代,到清朝御窑厂对景德镇本土的风火神崇拜的有意扶植,并使之成为御窑厂最核心的神灵崇拜,这不仅反映出“明清权力更替背后统治者对神灵之信仰崇拜的变迁”,更反映了“国家权力主导思路的转变”。[注]李兴华:《移民与景德镇瓷业神信仰研究——以御窑厂神灵崇拜演变为视角》,《陶瓷学报》2014年第2期。官方通过将原本作为对抗象征的人物转化为可以利用的窑神,实现了其介入和干预民众信仰的目的。[注]刘朝晖:《明清以来景德镇的瓷业与社会控制》,复旦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5年。
在以造纸作为地方主业的四川省夹江县,造纸匠广泛流传着对祖师神蔡伦的崇祀,芝加哥大学艾约博(Jacob Eyferth)的研究就揭示了蔡伦崇拜对于像造纸技术这样的传统技艺的传承所具有的重要影响。[注][德]艾费特:《技术的源与流:四川夹江造纸匠群体中的行业崇拜、祖先与知识的传播》,《中国科技史杂志》2011年增刊。作者的另一译名是艾约博。而肖坤冰则考察了晚清民国时期夹江县的槽户结社——“蔡翁会”,讨论了围绕蔡伦庙公产收入体现出来的地方政治以及在近代国家政权建设过程中“蔡翁会”的解体与地方社会的变化。她的研究为近代中国“民族—国家”建构进程中传统会社组织如何让位于现代新式地方组织提供了一个业缘性的个案。[注]肖坤冰:《行业信仰、祭祀组织与地方社会——以晚清民国时期四川夹江县“蔡翁会”为中心的考察》,《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1期。但是,“蔡翁会”的解体并未使祖师神蔡伦在地方社会的影响力消失,1933年,在四川省夹江县政府拟对造纸匠征收“架槽税”时,华头镇的纸匠们把洪川神像(一个与灌溉有关的当地神祇)挪出地方中心神庙的主祀位置,代之以从晚清就已收于偏室的蔡伦神像,然后开始了持续数周的游行。研究者因此认为,虽然民国政府通过压制“迷信的”崇拜活动和扩展现代教育等措施实现中国农村文化转型的改革,导致了传统造纸业的整合模式衰落,但“纸匠们依然围绕在他们的守护神周围,用旧帝国时代的生计权利和道德权利的修辞话语来进行抗争”[注][德]艾约博:《以竹为生:一个四川手工造纸村的20世纪社会史》,韩巍译,吴秀杰校,江苏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109-111页。。
提供井盐的四川、供应煤炭的山西,则是资源导向型区域社会的代表。在宋代,四川是全国重要的井盐产区,为控制财利之源,在信仰体系中,官方塑造出很多作为食盐发现者的盐神,“意图在意识形态中强化食盐垄断的合理性”。而食盐作为民众日用必需品,盐神也承载着民间利益诉求,由此,作为食盐发现者的盐神也显现出一定的平民色彩,证明“平民同样拥有盐权的合理性”,官民围绕着盐神的塑造在意识形态领域展开了博弈。裴一璞认为这种博弈“并非单纯体现为民间信仰在地方社会的功能呈现”,更多表达的是一种“资源在地方社会所触发的各群体间的互动过程以及各方围绕这种资源的博弈所呈现的纷争与妥协”,“最终官民双方在围绕食盐资源的博弈中寻求到一种合理的盐权分配秩序”。[注]裴一璞:《白鹿化龙:从宋代四川盐神信仰变化看官民盐权分配的博弈》,《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5期。不同于对盐资源的控制,官方对煤炭的开采相对开放,反映在行业神崇拜上,即窑神崇拜的平民化色彩更加浓厚。张月琴的研究为观察行业神崇拜与以煤炭资源导向的矿区社会提供了一个来自山西经验的个案。从她的研究中可以看到,窑主、人伙柜和窑工从各自利益出发,借助煤窑神对窑规进行重新阐发,“体现了他们对生命境遇的认识和对生存话语权的争夺”[注]张月琴:《煤窑神信仰与民国初年的山西大同矿区社会》,《民俗研究》2013年第1期。。
不同于产业型地区、资源导向型地区,河北安国形成了以药材交易为主导的商业性市镇。围绕着药王祖师崇拜,同样存在着多重叙事话语,而话语背后是民众、药商等多种异质性社会群体对共享符号资源的把持和诠释,徐天基认为多主体间互动过程中所呈现出的趋同性和认同,为传说、庙会及地方社会的互动提供了基本的社会语境。[注]徐天基:《地方神祇的发明:药王邳彤与安国药市》,《民俗研究》2011年第3期。
与上述拥有特色产业或资源的区域不同,在北京、上海等流动性较强的都会型城市,行业众多,行业神的种类也因而更为复杂。同时,大量工商从业者由不同的地域来源进入城市,行业组织的结合原则兼具业缘性与地缘性,显现出与其他产业型城镇不同的路径。在都市行业神信仰的研究中,北京地区最具典型性,同时由于史料相对丰富,成果也最为集中。会馆和寺庙是承载行业神信仰的祭祀空间和物化实体,明清以降北京城供奉行业神的庙宇和会馆有相当分布,研究者也多围绕这些信仰空间展开。如郑永华对清代北京商业会馆中行业神崇祀的社会功能的讨论[注]郑永华:《清代北京业缘商馆宗教民俗的社会功能试探》,《北京历史文化研究》2007年第2期。,习五一以京城祭祀行业神的寺庙殿堂和会馆为切入点,探讨近代北京行业神信仰的实用性和式微趋势[注]习五一:《近代北京的行业神崇拜》,《北京联合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1期。。在京城供祀行业神的寺庙中,又以朝阳门外的东岳庙最为突出,有很多行业性的香会组织在东岳庙中捐资修建祖师殿并定期举行祭祀活动。如鲁班会,信众多为瓦木行、石行、棚彩行等建筑行业从业者,清至民国初年这一祭祀组织经历了由多个相关行业共同祭祀到因行业间独立发展、利益冲突造成的分化过程。[注]赵世瑜、邓庆平:《鲁班会:清至民国初年北京的祭祀组织与行业组织》,《清史研究》2001年第1期。还有马王老会,其会众多为京城蓄养马、驴或从事马、驴交易的人,如马市、驴市和骡马行的弟子,从明清以降马神祭祀群体的逐渐多元化可以看出,伴随着王朝马政的兴废和北京城市经济的发展,马神从国家政治的象征符号转变为代表行业利益诉求的象征符号。[注]邓庆平:《明清北京的马神崇拜及其功能、意义的转变》,《北京社会科学》2006年第2期。至于为什么数量较多的行业性香会活跃在东岳庙中,修建殿堂供祀行业神,陈巴黎认为这主要因为东岳庙地处京城漕运要道,加之朝外地区工商业的发展[注]陈巴黎:《从碑刻资料看北京东岳庙的香会组织》,《北京档案》2012年第2期。,从业者起初只是作为普通会众附庸于某个香会捐资出力助善结缘,到独立的行业性香会组织开始形成,影响力不断加强,因而将行业祖师信仰习俗带进了东岳庙。[注]关昕:《东岳庙的行业祖师信仰》,《华夏文化》2006年第1期。那么,为什么是这些行业而非其他行业在东岳庙或建立祖师神殿,或成立香会组织举行祭祀活动?赵世瑜通过分析东岳庙西廊行业祭祀的碑刻资料认为,东岳庙虽然因其国家正祀性质而成为一个跨地域的祭祀中心,但同时也具有鲜明的街区性特点,在此供祀行业神的香会组织,主要是东岳庙邻里地区的某些特定行业群体。[注]赵世瑜:《远亲不如近邻:从祭祀中心看城市中的行业与街区——以明清京师东岳庙西廊诸神为出发点》,《东岳论丛》2005年第3期。
还有一些区域性的行业神信仰研究,也从不同角度揭示出地方社会历史进程的特点。如移民社会,伴随着地方社会的移民化过程,行业神崇拜基于同乡关系建构出的人际网络加以传播扩散,逐渐改变了迁入地的神灵系统及神灵的象征意义。如陈云霞通过对瞿真人、鲁班、虹庙信仰这三个行业神个案的研究,展现了外来信仰通过移民这一媒介进入上海城市的过程,以及上海开埠以后包括行业神崇拜在内的城市民间信仰在外来移民及社会变迁的作用下发生的转变。[注]陈云霞:《上海城市民间信仰历史地理研究(1843-1948)》,复旦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4年。潘荣阳、黄洁琼则从闽台整体区域社会的变迁入手,对戏神进行了研究,认为伴随着移民过程,戏神信仰被以各种形式带到台湾,并且在戏业艺人的行业习俗中不同程度地保留下来。当地民众按照自身需求附会了雷海青的种种传说,促成了雷海青从戏神向民间神祇的转化。[注]潘荣阳、黄洁琼:《社会变迁与近世台湾戏神雷海青信仰》,《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9期。又比如少数民族地区,因为自身行业的发展以及与汉族文化的融合,亦有其独特的行业神崇拜现象。维吾尔族行业祖师就表现出非常鲜明的宗教性,与汉族地区行业神崇拜的世俗化特征明显不同。维吾尔族的每一个行业祖师都是伊斯兰教的信徒,“在行业内构建起‘安拉——行业祖师(使者)——从业者(信徒)’伊斯兰化的宗教秩序”[注]蒲燕妮:《维吾尔族行业祖师研究》,新疆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1年。。何岭则将目光集中于广西、贵州地区布依族八仙乐演奏业的祖师神崇拜现象,论述虽失之于简单,但仍有启发意义。[注]何岭:《祖师神崇拜:布依族八仙乐名称文化透视》,《艺术探索》2004年第2期。
五、余 论
作为中国庞杂神灵系统中的独特门类,中国行业神崇拜从20世纪上半叶进入学者的视野以来,已经走过了一百余年的研究历程,民俗学、历史学、人类学、社会学、宗教学甚至文学、艺术等不同学科在这一领域持续耕耘和开拓,积累了丰硕的研究成果。总体而言,若借用民俗学的学科话语,中国行业神研究经历了从“民俗事象的研究”到“整体研究”的转向[注]有关民俗的事象研究和整体研究两种取向,参见高丙中:《文本和生活:民俗研究的两种学术取向》,周星主编:《民俗学的历史、理论与方法》(上册),商务印书馆,2006年,第127页。,即放弃将行业神崇拜这一民间信仰文化“从具体的时空坐落中抽取、剥离出来”的做法,而是将其作为“语境中的民俗”置于“民俗传承的具体时空”中加以考察[注]刘晓春:《从“民俗”到“语境中的民俗”——中国民俗学研究的范式转换》,《民俗研究》2009年第2期。。若用历史学的学科话语,行业神研究则经历了从经济史到社会史的转向,即最初将行业神崇拜现象视为附着于中国行会的传统活动之一,置于行会史的研究视野中。而后则在社会史民间信仰研究的理路下,在具体的社会群体与地方社会的脉络中探讨行业神崇拜,日渐表现出区域社会史或历史人类学的研究取向。那么,在已有较为丰厚的研究积淀之上,未来的研究应该提出并解决什么新的问题?原有研究还有哪些不足之处?有哪些新的研究方向和路径?这是研究者们应该不断反思的问题。
在研究的广度上仍可以不断拓展。比如在行业类型上,学者大多关注的是那些受到广泛崇拜、行业实力也较为雄厚的行业神,对于那些知名度较小、研究比较薄弱的行业神,还应该进一步挖掘其研究潜力,完善和丰富对于中国行业神崇拜体系的整体认识。又比如在地域类型上,除了像北京、上海这样的消费型都会城市,景德镇等产业型、资源型市镇外,一般的内地商镇和少数民族地区的行业神崇拜还应该给予更多关注。其后,在更为充分的个案研究基础上,还应该进行不同行业、不同区域的对比研究,以对行业神信仰形成一个全景式的了解。
当然,在已有大量研究成果的现状下,如何持续提升行业神研究的深度,才是更为关键的问题。如上文所示,行业神崇拜的研究大体可以分为民间信仰、行业组织与地域社会三种取向,笔者也拟从上述三个角度提出未来研究的几点展望。
第一,从民间信仰的路径出发,需要在“宗教的社会网络”中更动态地揭示行业神崇拜体现出来的中国“宗教资本”与“社会资本”之间转换与整合的机制及其过程。[注]对于中国民间信仰的“宗教的社会关系网络”以及“宗教资本”与“社会资本”之间关系的讨论,可参见陈进国:《中国民间信仰研究述评——以大陆地区为中心》,路遥等著:《中国民间信仰研究述评》,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58-61页。虽然对“宗教资本”的定义多有不同,但大体而言,“宗教资本”是指“一个人的宗教知识、技能和感受的积累储备”,“涵盖教会仪式、教义知识、与其他信徒的友谊、甚至信仰”,是“由对某一宗教文化的掌握和依附程度构成”。[注][美]泰瑞·雷:《宗教资本:从布迪厄到斯达克》,李文彬编译,《世界宗教文化》2010年第2期。而所谓“社会资本”,按照布迪厄的说法,则是“某个个人或是群体,凭借拥有一个比较稳定、又在一定程度上制度化的相互交往、彼此熟识的关系网,从而积累起来的资源的总和”[注][法]皮埃尔·布迪厄、[美]华康德:《实践与反思——反思社会学导引》,李猛、李康译,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第162页。。在中国社会,宗教是社会资本的主要提供形式之一。[注]魏乐博(Robert P. Weller)认为,在众多的中国乡村,除宗教外,家族与血缘是社会资本的另一种主要提供形式。参见Weller、范丽珠、Madsen、陈纳、郑筱筠:《对话宗教与社会资本》,《世界宗教文化》2011年第5期。作为体现业缘性社会关系网络的神明崇拜系统,行业神信仰和祭祀仪式实践构成的“宗教资本”,经由不同路径转化成中国传统业缘性社会组织建构信任机制、规范机制及网络机制的“社会资本”。同时,作为“宗教资本”的行业神信仰体系的形成与积累,也是一个强化行业群体认同的文化符号被不断建构的过程,在中国民间信仰的非排他性结构下,行业神的塑造也往往充斥着各类民间宗教资源的竞争。现有研究更多呈现的是这一复杂过程的结果,缺乏对具体历史过程的揭示,我们更应该了解的并不是或不仅仅是哪些行业信仰哪位神明以及如何奉祀,而是不同的行业组织在建构各自的行业神信仰时经历了怎样的文化选择、诠释与再创造,以及这一“宗教资本”转化为“社会资本”的路径与过程。
第二,在行业组织的研究视野下,对于传统行会近现代转型过程中行业神崇拜的变化,还有必要进行更多的讨论。由于行业神信仰具有的行业聚合功能,其研究无疑有助于我们从信仰文化、社群活动的角度对中国传统行会、近代工商同业公会等业缘性社会组织达致新的理解。但总体来看,对行业组织与行业神崇拜在中国近代化变革中趋新面向过度强调的倾向,虽然在近来的研究中得到了一定的纠偏,诸如裴宜理、艾约博、沈洁等学者,已经注意到新式工商同业组织与旧式行会组织两者并存格局的长期延续,承认行业神信仰在近代社会转型中的复杂性,但在多数情况下,行业神崇拜仍然以一种“旧式行会的落后因子”的形象存在。特别是在既定的现代科学话语下,在“传统-近代”二元对立中,行业神崇拜往往被视为“行会传统的保守性和落后性的具体表现”,甚至将“是否开展神灵崇拜活动作为区别商会(新式商人团体)和行会(旧式传统组织)的标准之一”。[注]朱英:《中国行会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历史研究》2003年第2期。因而,在作为近代的“先进”的行业组织形态——商会和同业公会的研究中,不同程度上仍然存续的行业神崇拜自然大多不在讨论之列。这显然不利于全面理解近现代中国工商行业团体的变化过程,更甚者,也不利于对中国社会现代转型问题复杂性的重新认识。
第三,区域社会视野下的行业神信仰研究,应更多关注行业神与其他社区神的关系,探究包括行业神在内的多层次的民间信仰体系在地方社会如何形成,进而揭示区域社会的历史脉络和文化进程。现有的区域性行业神个案研究,仍多以探究某种行业神崇拜的地方性特点为旨归,落脚点仍在信仰形态本身,并不在于行业神信仰所寄生的历史语境和社会空间。但是,社区民间信仰研究的意义绝不仅限于信仰本身,正如郑振满、陈春声所言:“吸引众多的研究者去关注民间信仰行为的更重要的动机,在于这种研究在揭示中国社会的内在秩序和运行‘法则’方面,具有独特的价值和意义。”[注]郑振满、陈春声:《民间信仰与社会空间》“导言”,福建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1页。或如陈进国所言:不论是华北民俗学者的整体研究取向,还是华南学者的历史人类学研究取向,“所谓的民间信仰或地域崇拜体系,其实只是诠释‘语境’和‘地方’的一个文化工具或分析符号而已”[注]陈进国:《中国民间信仰研究述评——以大陆地区为中心》,路遥等著:《中国民间信仰研究述评》,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56页。。就这样的研究路径而言,赵世瑜对明清北京行业神崇拜的研究是具有典范性意义的。如上文介绍所言,这些研究以明清京师东岳庙西廊的行业神殿为中心,讨论了土木行、骡马行和梨园行围绕各自的行业神——鲁班、马神、喜神——形成的祭祀组织及其活动,从东岳庙这个神圣空间展现清代以来北京城市的街区意识和角色日益凸显的过程。[注]赵世瑜:《远亲不如近邻:从祭祀中心看城市中的行业与街区——以明清京师东岳庙西廊诸神为出发点》,《东岳论丛》2005年第3期。而后,作者又将东岳庙诸行业神的研究,和同一座庙宇的其它研究——包括东岳庙与京师五顶即东岳大帝信仰与碧霞元君信仰关系的研究、东岳庙中各类善会组织的研究——整合在一起,讲述了一个更为完整的“东岳庙故事”,试图从“城市中的微社会场景出发”,呈现京师这一政治色彩浓厚的社会空间表现出来的国家权力与民间社会之间“温和的互动”。[注]赵世瑜:《东岳庙故事:明清北京城市的信仰、组织与街区社会》,氏著:《小历史与大历史:区域社会史的理念、方法与实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年,第188-257页。这样以“小历史”看“大历史”,以地方民间信仰活动看“国家的在场”与“文化-权力”的研究取向,是深化区域性行业神研究最有可能的路径。
总之,笔者认为,行业神崇拜是深入理解中国传统社会经济、文化与组织形态的一个切入点,有着重要的研究价值,已有的研究成果也已经显示了这一议题在解释中国社会历史诸多问题上的可能性。若能在研究的广度与深度上继续拓展、挖掘,并充分融合多学科的问题意识与研究路径,我们相信未来的行业神研究还会取得更大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