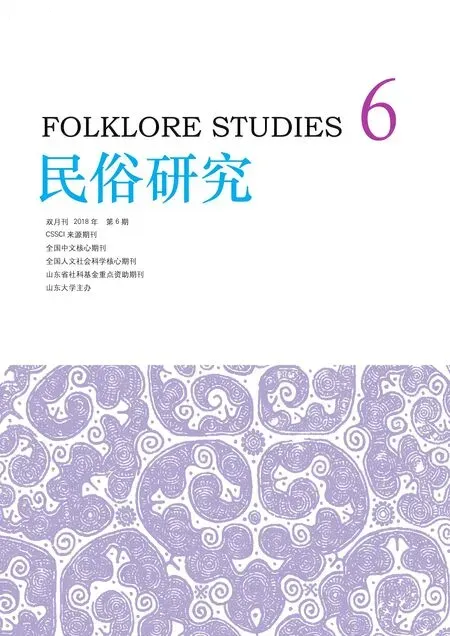两种自由意志的实践民俗学
——民俗学的知识谱系与概念间逻辑
2018-01-23吕微
吕 微
一
如果说,20世纪60-70年代的美国民俗学家是从康德、胡塞尔、索绪尔那里汲取营养,而发展了表达任意选择的自由意志的美国精神的实践民俗学(如表演民俗学、公共民俗学),那么中国现代民俗学在其起步阶段(如果从1922年《歌谣》创刊算起)的基本理念,所师承的并不是胡塞尔、索绪尔的“任意的意志”,而是康德启蒙主义的理论理性和实践理性及其统一的自由意志。可以这样说,美国民俗学的学科基本问题是“后期康德问题”(即Willkür的问题),而中国民俗学的学科基本问题则是“前期康德问题”(即Wille的问题)。
我本人曾多次援引根据周作人的思想撰写的《歌谣》周刊《发刊词》对民俗学的两个目的的阐明。*吕微:《民俗学:一门伟大的学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年。谭璐更是细微地注意到,中国现代民间文学-民俗学学者始终在“文艺的”和“学术的”两个学科目的(学科问题)之间徘徊,胡适始终强调“文艺的”是歌谣研究的第一目的,董作宾则把“学术的”作为民间文艺研究的第一目的,而周作人在民俗学的“学术的”和“文艺的”两个目的之间犹豫,且最终倒向了“学术的”第一目的。[注]谭璐:《民间文学方法论的形态学提炼:从外部视角到四种研究方式》,“当代社会口头传统的再认识——首届民族文学研究博士后论坛(2014·北京)”论文。学术前辈们所谓的“学术”指的就是康德的理论理性(“五四”时称为“赛先生”),而“文艺”则是指康德的实践理性(“五四”时称为“德先生”)。这就是说,在中国现代民俗学起步的最初阶段,民俗学家关注的问题不是人的任意选择的自由意志的问题,而是关于理性的理论使用和实践使用之间关系的“康德问题”,甚至是理论理性与实践/实用理性之间关系的“亚里士多德问题”。
如何划分理论理性和实践理性,之所以在中国现代民俗学发轫之初一度成为难题,是因为在中国古典学术传统中,几乎没有关于理论理性和实践理性的明确区分。因此导致了,一方面与感性经验有关的理论理性的实证科学不受重视(如称科学为“奇淫技巧”),另一方面则着重发展了道德实践的纯粹理性(如宋明理学)。在近现代打开国门以后,一方面同时引进了“德先生”(纯粹实践理性)和“赛先生”(理论理性),另一方面又为了实现强国梦想,用认识自然因果性的“赛先生”(科学),压倒甚至遮蔽或者扭曲了以实现自由因果性为目的的“德先生”(民主)。与“唯科学主义”的现代化进程相一致[注][美]郭颖颐:《中国现代思想中的唯科学主义(1900-1950)》,雷颐译,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年;汪晖:《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三联书店,2004年。,中国学术界也更倾向于理论理性的经验研究范式,而忽略了纯粹实践理性的先验研究范式。由于没有处理好理论理性与实践理性的关系——按照康德批判性检验,理性对自身的自我理解,实在是关系到如何为现代共同体奠基的大问题——也就无法进一步处理好实践理性内部的纯粹实践理性的普遍立法的自由意志(道德理想)与一般实践理性的任意选择的自由意志(幸福诉求)的关系,以至于在国家建设和社会治理方面,始终摇摆于道德专制的总体性国家与欲望泛滥的社会失范之间。[注]详见黄裕生:《人权的普遍性根据与实现人权的文化前提》,《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11年第1期;黄裕生:《社会契约与国家的使命》,《深圳特区报》2012年6月15日;黄裕生:《人类此世的一个绝对希望——论康德有关共和政体与永久和平的思想》,《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13年第2期;黄裕生:《有第三条道路吗?——对自由主义和整体主义国家学说的质疑与修正》,《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14年第1期;黄裕生:《论主权在民原则下的民族共治原则》,《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3期。
我们说民俗学的“学术”目的最终压倒甚至遮蔽、扭曲了其“文艺”的目的,不是说民俗学的“赛先生”完全取代了“德先生”,而是由于中国现代学术在整体上没有经历过康德所说的理性自我的批判性检验,因而导致了民俗学(其他学科也是一样)对自身的学术理性的性质(目的、方法)在认识上的模糊不清。就民俗学而言,最终走上了一条用理论理性的方法来实现实践理性的目的的悖论之路[注]吕微:《我们的学术观念是如何转变的?——刘锡诚:从一位民间文学-民俗学学者看学科的范式转换》,《中国民俗学》第2辑(2014年)。,即如卡西勒批评浪漫主义时所说的,用启蒙主义(理论理性)的方法去实现浪漫主义(实践理性)的目的[注]“通常认为,18世纪是个‘非历史的’世纪,从历史观点看问题,这一看法是没有根据的。毋宁说,这一看法是浪漫主义运动在历史领域中反对启蒙哲学时创造的一个战斗口号。……启蒙运动为浪漫主义运动锻造了武器。我们发现,浪漫主义运动就是在这一旗帜下驳斥上一世纪(18世纪)的种种思想前提的,只是这些前提的效力的结果,亦即只是启蒙运动的观点和理想的结果。没有启蒙哲学的帮助,没有对启蒙思想的继承,浪漫主义运动既不可能取得也不可能维持它自己的地位。无论浪漫主义运动对历史内容的看法即它追求实利的‘历史哲学’与启蒙运动相去多远,它在方法上仍依赖于启蒙运动。”[德]卡西勒:《启蒙哲学》,顾伟铭等译,山东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192页。,从而导致了实践理性的实用化(回到亚里士多德的分类),即前述民俗学“拿来主义”的技术化、工具化,而扭曲了实践理性本身,即用基于自然因果性的科学发展理论代替了基于自由因果性的道德信仰实践(例如普遍用理论理性的进化论评价人们的实践理性的宗教信仰,就把许多传统文化判定为落后的迷信),结果就导致了康德所说的理性使用的二律背反(自相矛盾、自我冲突)。[注]吕微:《民俗复兴与公民社会相联结的可能性——古典理想与后现代思想的对话》,《民俗研究》2013年第3期。
总而言之,回顾“五四”学者为现代中国引进的民俗学学科,我们很难为其梳理、建构出一条“知识谱系”的清晰路线图。或者说,对于中国现代民俗学的创建者来说,他们所仰仗的理论资源是相当驳杂的。[注]关于胡适和周作人的思想-学术渊源,参见李小玲《胡适与中国现代民俗学》(学苑出版社,2007年)以及周星《平民·生活·文学:从周作人的民俗学谈起》(未刊稿件)。但可以肯定的是,“五四”民俗学家特别是周作人对民俗学的性质(目的和方法)的理解,完全是根据康德对理性的古典分类(“前期康德问题”,有《歌谣》“发刊词”为证),而他对“人的文学”的理解,则蕴含了康德对“任意选择的自由意志”的“后现代”思考(“后期康德问题”),而与此同时,却又普遍地失望于民众的“普遍立法的自由意志”的先验能力(不仅周作人,郑振铎等诸多民俗学家也是一样)。[注]吕微:《接续民间文学的伟大传统——从实践民俗学的内容目的论到形式目的论》,《民族文学研究》2015年第1期。“像周作人的《人的文学》一文仍然相当完备地表述了古典的‘个人主义的人道主义’思想,在更早时期,严复在《论世变之亟》里已相当深刻地阐述了自由主义的精髓,而胡适的《易卜生主义》不啻是一篇个人主义的宣言。……‘五四’人物关于‘人的觉醒’的思考是相当广泛的。”汪晖:《预言与危机——中国现代历史中的“五四”启蒙运动》,《文学评论》1989年第3期、第4期,收入《汪晖自选集》,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320页。汪晖对周作人的评价,似乎未臻“完备”。尽管我们至今都不清楚,周作人的“民俗学”思想和“人的文学”思想究竟是通过何种途径间接地“师承”了康德。[注]周作人“1913年发表《童话略论》(周作人《童话略论》,收入《周作人民俗学论集》,上海文艺出版社,1999年,第39-45页),认为‘童话研究当以民俗学为依据,探讨其本原’,首次采用‘民俗学’一词”;1914年1月发表《儿歌之研究》,亦提及‘民俗学’这一用语。”周星:《平民·生活·文学:从周作人的民俗学谈起》,未刊稿件。
这就是说,是启蒙主义的古典理想启发了中国现代民俗学家下定决心,在现代中国发起了一场民俗学运动,但是在没有“前期康德问题”的支持下,“后期康德问题”中的“任意选择是自由意志”也就缺失了。在中国民俗学从初生到新生的将近一个世纪之后(1922年至今),“前期康德问题”仍然笼罩在中国民俗学的理论和实践的穹幕上,不解决“普遍立法的自由意志”的“前期康德问题”,“任意选择的自由意志”的“后期康德问题”就永远提不到议事日程上来。即便我们在20世纪90年代开始,从美国引进了“表演理论”等以“任意意志”为观念基础的实践民俗学流派,也即刻被理论理性化(其中“语境”概念的时空化、经验化就是绝好的例证,详见下文),进而难以发挥其像在美国本土那样广泛的实践影响。
二
中国民俗学者的心中,念念不忘的总是:中国民俗学的学科问题究竟是什么?中国民俗学自身的学科问题与欧美民俗学的学科问题有什么不同(二者是同一个问题的不同问法)?
借鉴归借鉴,他人的工作理念与工作方式一定不可以照搬到当下的中国,因为当下中国的国情不同于一百年前的中国,也不同于当下欧美日德任何一国,这也是必须给予足够重视的。[注]王杰文:《“生活世界”与“日常生活”——关于民俗学“元理论”的思考》,《民俗研究》2013年第4期。
作为一门现代化过程中兴起的人文学科,民俗学在不同的国家中针对的是不同的社会现实问题,做出的也是不同的回答。欧洲是这样,中国是这样,美国也是这样。[注]彭牧:《实践、文化政治学与美国民俗学的表演理论》,《民间文化论坛》2005年第1期。
只是,这“当下中国的国情”究竟是什么,却并不是仅仅关注了中国的“社会现实问题”,或者仅仅关注了欧美民俗学所针对的“社会现实问题”,就能够回答的;当然,“另一方面,也有一些似乎万变不离其宗的‘母题’反复出现,那就是对普通民众的关心”[注]高丙中:《民俗文化与民俗生活》,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第146、163、100页。,正是这一点能够让民俗学者在始终保持着对“当下国情”或“社会现实问题”的敏感度的同时,随时调整本学科因现实关怀而对自身基本问题的自我认知。
但仅仅是“关心”,就能够发现、确认自己的问题吗?通过梳理、反思欧美民俗学与中国民俗学的学术史[注]吕微:《现代性论争中的民间文学》,《文学评论》2000年第2期;户晓辉:《现代性与民间文学》,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尽管我们也认识到,民俗学在不同的国家、针对不同的国情即“不同的社会现实问题”应该有不同的回应,但是直白地说,在民俗学的“工作理念与工作方式”从先进国家向落后国家单向流动的过程中,“受动”国家的“国情”和“社会现实问题”往往沦落为一句空话。因为受动国的学者往往会自我矮化地认为,先进的“欧美同行们的学术路径与学术成果,已经把我们这里所谈到的问题都谈过了,而且不仅只是谈过了,甚至讨论得还更深入一些”,“欧美同行们甚至已经超出了我们现在所面对的问题了”,因此也就没有必要再奢谈什么“当下国情”和“社会现实问题”,后进者只要忠实地移植先进的“工作理念与工作方式”就可以了。
在这里需要说明的是,不同国家的民俗学之不同的“工作理念与工作方式”之间,固然可以给出“先进”与“落后”之分,但也不妨视为“工作理念与工作方式”的不同类型。但是,无论分等级地,抑或平等地看待、对待不同类型的民俗学“工作理念与工作方式”,都有待于我们还原到一个能够涵盖不同“工作理念与工作方式”的更高一层级的“工作理念与工作方式”的整体性中。
当事关决定人类心灵[注]“心灵也就是他[指康德——笔者补注]所谓的理性。”帕通:《论证分析》,[德]康德:《道德形而上学原理》“附录”,苗力田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94页。一个特殊能力的源泉、内容和界限时,依照人类认识的本性,人们唯有从心灵的各个部分开始,从对这些部分的精确而详尽的描述开始。但是还有第二个更具哲学意味和建筑学意味的应行注意之点:这就是说,要正确地把握整体的理念,并且从这个理念出发,在所有那些部分的彼此交互关联里面,借助于从那个整体的概念将它们推导出来的方式,在同一个纯粹理性的能力之中考虑这些部分。[注][德]康德:《实践理性批判》,韩水法译,商务印书馆,1999年,第8页。
这里所说的民俗学的不同“工作理念与工作方式”的“整体的理念”或“整体的概念”,就是我在上文中已经指出的康德哲学所指向的作为人类“心灵的各个部分”(这里就是不同国家的民俗学的不同“工作理念与工作方式”)所从属的理性整体性,康德称之为“理性知识的全部范围”[注][德]康德:《道德形而上学基础》,孙少伟译,九州出版社,2007年,第47页。,如果我们承认民俗学是一门理性的科学的话。以此,回到康德,回到理性的整体性,然后将“彼此交互关联里面”的“所有那些部分”(不同“工作理念与工作方式”和不同国家的“国情”和“社会现实问题”)“将它们推导出来”,就是作为理性科学的民俗学的观念(理论)反思的必然性要求,而不仅仅是学术史“知识谱系”建构的一个偶然性结果。[注]中国民俗学网(http://www.chinesefolklore.org.cn/)→民俗学论坛→2014特别策划:民俗学的中国实践→王杰文:关于民俗学理论史的知识谱系。
就我们民俗学的基本问题,即“民俗学在不同的国家中针对的是不同的社会现实问题,做出的也是不同的回答”来说,也必须从民俗学观念的整体性中推导出来。显然,康德离我们民俗学不是“太远”而是“很近”,因为康德就是作为理性科学的民俗学的内心,用康德自己的话说,就是我们学科的“心灵”,相反民俗学理论史却可能真的是离我们更远一些,因为那只是学科心灵表象的表象,谁让我们是一门理性的科学呢?也许,回到民俗学的学科反思,不一定非要通过康德,但无论如何却不可能不通过我们的理性整体性的学科“心灵”。
康德根据人的理性的不同使用目的、方式和(经验或先验的)对象、范围,把理性自身区分为理论理性(理性的理论使用)和实践理性(理性的实践使用),进一步又把实践理性划分为普遍立法的自由意志的纯粹实践理性,与任意选择的自由意志的一般实践理性。以此,理性的不同使用方式和不同使用目的,就是人的不同实践方式或不同生活形式。进而,民俗学作为一门理性的学科,也就是民俗学(者)的理性的存在方式,并且也可以根据学科理性的不同使用目的和使用方式,将学科自身划分为不同的学术范式[注]吕微:《民俗复兴与公民社会相联结的可能性——古典理想与后现代思想的对话》,《民俗研究》2013年第3期。,即:
(1)以认识自然因果性的民俗现象的经验对象为目的的理论理性的学术范式。[注]刘晓春:《从“民俗”到“语境中的民俗”——中国民俗学研究的范式转换》,《民俗研究》2009年第2期。(实然的实践范式)
(2)以认识并实现任意选择的自由意志的民俗“法象”的经验/先验对象为目的的一般实践理性的学术范式。(偶然或或然的实践范式)
(3)以认识并实现普遍立法的自由意志的民俗“法象”的先验对象为目的的纯粹实践理性的学术范式。(必然或应然的实践范式)[注][德]康德:《道德形而上学基础》,英汉对照本,孙少伟汉译,Beck英译,九州出版社,2007年,第52-65页。
民俗学的上述三种学术范式,近代以来实然地或仅仅应然地被使用于不同国家的不同时期,以达成不同的使用(认识和实践)目的。这就是说,民俗学的不同学术范式的本质规定性,是唯当我们还原到学科“心灵”的理性整体性中才能够以“哲学意味和建筑学意味”的方式“将它们推导出来”,否则,即便我们置身于某一范式之中,甚至两种范式之间,我们都会在认识上发生偏颇。这方面的例证颇多,不仅不同国家的学者之间会发生误解,同一国家的学者之间也会相互误解。
三
语境研究从来都从属于民间文学-民俗学研究的传统范式、经典范式,即上述“以认识自然因果性的民俗现象的经验对象为诉求的理论理性的学术范式”。语境研究,包括了传统的文本、历史文献(文化)研究,和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中国学界兴起的基于田野作业的生活(整体)研究。我之所以把传统的、经典的文本研究、文献研究即文史研究,与田野研究即生活研究、整体研究同样视为语境研究,乃是因为尽管生活研究、田野研究较之文本研究、文献研究,更注重语境中主体的现实存在(生活实践),但同属于在时间、空间等感性或经验性直观条件下的经验研究,只不过一个更看重当下经验(生活、事件),一个更偏重历史上“遗留”下来的经验(文化、事象)。因此,在民俗学家促进民俗学的人类学化、社会科学化的同时[注]高丙中:《中国民俗学的人类学倾向》,《民俗研究》1996年第2期。,人类学家也在力主民族志写作的历史性维度[注]王铭铭:《社会人类学与中国研究》,三联书店,1997年,第43-56页。,而时间-空间的语境条件恰恰是联结历史学的文献研究与民族志的田野研究的统一性框架。时间、空间语境之所以能联结历史学研究与民族志研究,乃是因为二者都以理论地、实证地认识经验对象(现象)为鹄的,于是感性直观的时空形式(语境)就成为了二者共享的先验条件。这就是说,在时间-空间语境条件下,同样以认识经验现象为目的的进化论和功能论是可以相通的。如马林诺夫斯基就承认进化论的文化“遗留物”理论,因为他与进化论者一样,承认事物在时间中会发生功能性演变,所以他才执意要到蛮野社会的“语境”中,去寻找charter(宪章)功能尚存的原始神话。[注][英]马林诺夫斯基:《巫术科学宗教与神话》,李安宅译,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86年。
马林诺夫斯基以后,就连纯粹研究文本、文献等文化事象的民俗学者也接受了“语境”概念,因为对以现象为对象的经验论者来说,接受康德所谓感性直观的时空形式的“语境”概念,并不是特别为难的事情。对于传统的、经典的以文本、文献为研究对象的民俗学者来说,以探讨民俗现象的自然因果性为鹄的的语境研究,不过是理论民俗学的经验范式的全面兑现而已。[注]吕微:《中国民间文学的西西弗斯——刘锡诚〈20世纪中国民间文学学术史〉读后》,《民俗研究》2008年第4期。所以,始终坚持文本、文献研究的美国民俗学家邓迪斯认为,研究文本、文献的民俗学者“对语境的重视是理所当然的、不言而喻的”。[注]正如丁晓辉指出的:“总是被当作民间文学的对立面出现的作家文学,其‘语境’对于理解其自身同等重要。在理论上,孟子早已有‘知人论世’说;在实践上,诗文系年之类的考证并不鲜见,与‘民族志式的描述’或‘立体描写’异曲同工。语境的收集并不限于民间文学,这是一个普遍性的问题,如果视其为民间文学或民俗独有,有坐井观天之嫌。我们如此大张旗鼓地追求语境,是否也暴露了民间文学研究的短视和狭隘?”丁晓辉:《“民族志式的描述”与“立体描写”——邓迪斯与段宝林之必然巧合》,“当代社会口头传统的再认识——首届民族文学研究博士后论坛(2014·北京)”论文。与此相应,中国民俗学家刘魁立的“活鱼要在水中看”,以及段宝林关于民间文学的“立体描写”的命题[注]丁晓辉:《“民族志式的描述”与“立体描写”——邓迪斯与段宝林之必然巧合》,“当代社会口头传统的再认识——首届民族文学研究博士后论坛(2014·北京)”论文。,也都没有超出语境研究的经验范式。正是因为没有超出理论理性的经验范式,邓迪斯才批评他所理解的、以鲍曼为代表的“表演理论”没有新意。[注]王杰文:《寻找“民俗的意义”——阿兰·邓迪斯与理查德·鲍曼的学术论争》,《西北民族研究》2011年第2期。在邓迪斯看来,“语境中的表演”和“语境中的文本”是等值的方法命题,而不是不等价的理论和实践命题。站在传统的、经典的理论理性的语境研究的经验范式立场上,邓迪斯只能认同“表演”的认识论价值,而不会承认“表演”的实践论(存在论)意义,因此当邓迪斯完全从认识论的意义上来理解“表演”的时候,“表演”作为“语境中的民俗”,也就不过是“以言行事”的文本。当然,邓迪斯如下反感也是有道理的,即以认识经验对象即现象的自然因果性为鹄的的语境研究,的确难有新的理论发现[注]“至于‘女性主义理论’,它哪里有什么‘理论’呢?妇女的声音与妇女在社会当中的作用被男性沙文主义与偏见所影响,这是事实,难道这也算得上是‘理论’吗?‘表演理论’又怎么样呢?没有哪个民俗学家否认民俗只有在被表演时才存在,也没有人否认民俗表演涉及表演者与听众,也没有人否认表演中的能力展示需要被记录与分析,那么,‘表演理论’当中的‘理论’在哪里呢?邓迪斯否认‘女性主义理论’与‘表演理论’是‘宏大的理论’。”王杰文《寻找“民俗的意义”——阿兰·邓迪斯与理查德·鲍曼的学术论争》,《西北民族研究》2011年第2期。“后来的‘表演理论’似乎暗示了其自身是一种新的理论,但邓迪斯在2004年美国民俗学会的讲演中对它如此评价:‘表演理论当中的“理论”在哪里?’”丁晓辉:《“民族志式的描述”与“立体描写”——邓迪斯与段宝林之必然巧合》,“当代社会口头传统的再认识——首届民族文学研究博士后论坛(2014·北京)”论文。,而是在不断地重复一件尽人皆知的常识:凡事都是有原因的。语境研究,不过是在同语反复地念叨某一文本现象、行为现象的琐碎原因。于是,当语境研究不断重复这些琐琐碎碎的自然原因的时候,的确会让人心生疑窦,除了理论理性的“认识”目的,语境研究“是否还存在着其它深层原因”?[注]丁晓辉:《“民族志式的描述”与“立体描写”——邓迪斯与段宝林之必然巧合》,“当代社会口头传统的再认识——首届民族文学研究博士后论坛(2014·北京)”论文。亦即,是否还存在着其他别开生面的目的?对此,施爱东曾提出过质疑:
我们一再强调说,记录文本时要全面、科学、客观,要记录讲述者的种种背景、形态、语态、故事的背景、听众的反应等等,听起来很有道理(也肯定是对的),但如果我们提这样一个问题:讲述者或听众是什么性别什么年龄什么文化程度在我们的研究中起了什么作用?我们有了这许多的资料后,有谁用过这些资料吗?得出了什么规律性的认识吗?没有!如果没有,为什么不去用呢?因为我们不知道怎么用!我们没有提出过问题,没有理论上的需求,只有想当然的形而上的要求。[注]施爱东:《中国现代民俗学检讨》,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第92页。
但是,语境研究真的就没有认识论以外的其他目的和深层价值吗?无论如何,通过赋予“语境”概念以新的意义,“语境”的确已经把我们带入了一个新的范式时代。
尽管马林诺夫斯基在《原始心理中的神话》(1926年)中提出“语境”概念的时候[注]Bronislaw Malinowski,Myth in Primitive Psychology,London,1926.,胡塞尔已经发表了他的现象学名著《逻辑研究》(1900-1901年),索绪尔也已经三度向他的学生讲述了《普通语言学教程》(1906-1911年),但现象学和语言学转向的国际学术-思想潮流,还没有在马林诺夫斯基身上表露出多少迹象。马林诺夫斯基本人始终坚持其像自然科学家一样的社会科学家身份,提倡科学的田野作业(field work)[注]field work,李安宅译作“实地工作”或“实地研究”。Bronislaw Malinowski,Myth in Primitive Psychology,p.111,p.146,p.147,London,1926. [英]马林诺夫斯基:《巫术科学宗教与神话》,李安宅译,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86年,第95、128页。和民族志写作,以此,马林诺夫斯基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提出的功能论“语境说”,也就最终未脱牛顿式至少康德式时间-空间观的窠臼。但是必须承认,即便是根据牛顿式甚至康德式的时空性语境观,在时间、空间的语境条件下,文化现象的实践主体已经被重新召回到学术视野中。
要理解民众的生活,通过实地调查记录他们生活的民俗过程是第一个步骤,然后必须把民俗事象置于事件之中来理解。把文本与活动主体联系起来理解;意义产生在事件之中,是主体对活动价值的体验,撇开事件的主体,也就无所谓意义。……我们希望民俗学从发挥高度想象力的智力游戏转向严肃的入世的学术,关心人,关心人生,关心生活。[注]高丙中:《中国民俗学的人类学倾向》,《民俗研究》1996年第2期。后来,高丙中对自己曾经的关于民间文学-民俗学的形式主义、智力游戏的理论范式的观点有所修正,认为民间文学-民俗学的文学方向,既可以从理论范式也可以从实践范式的不同角度予以理解和规定。见高丙中:《日常生活的现代与后现代遭遇:中国民俗学发展的机遇与路向》,《民间文化论坛》2006年第3期。
于是,主体特别是作为个体的主体——个人,以及每一个人的实践活动、行为,在时间、空间的语境条件中被突显出来了,问题只是,在时空语境中,我们是否只能够按照康德的理论认识的视角,视语境中的个人为“合于”自然因果性制约的客体(作为现象的自然人),还是也能根据康德的“实践认识”的视角,视语境中的个人为“出于”自由因果性的主体(作为本体的自由人)?[注]吕微:《民俗学的笛卡尔沉思——高丙中〈民俗文化与民俗生活〉申论》,《民俗研究》2010年第1期。但是,根据康德对理性的批判性检验,自由因果性只能是在超时空条件下,“人自身”基于纯粹实践理性的普遍立法的自由意志的任意选择,因此我们在时间、空间的语境条件下,能否像直观现象那样,直观到人作为本体(自由主体)的任性意志?康德陷入了困境,而且凡是试图通过传统的、经典的(牛顿式或康德式)语境观,揭示主体主观的自由意志的经验研究同样陷入了困境,因为没有一位民俗学家曾经在理论上明晰地阐明过“语境”到底是什么。鲍曼没有能力做到这一点,他对“语境”构成诸要素的经验式列举[注]王杰文:《寻找“民俗的意义”——阿兰·邓迪斯与理查德·鲍曼的学术论争》,《西北民族研究》2011年第2期。,只会徒增读者的困惑,而这正是他的“语境”概念往往被中国民俗学者误解和误用的重要原因之一[注]王杰文:《“文本化”与“语境化”——〈荷马诸问题〉中的两个问题》,《民族文学研究》2011年第3期。,当然,误解和误用的主要原因还在于中国民俗学者自己的范式立场。
康德所陷入的困境在于,他无法在直观的现象中,区分人的任性的自由意志和动物的任性的自由意志,但两种任性在直观中几乎没有区别,而且在先验感性的时间条件下也不容许据此而做出区分。康德的困境也就是日后美国民俗学的“表演理论”所陷入的困境,因为没有一位民俗学家能够用传统的、经典的属于理论理性的语境条件来界定人的表演行为、表演活动(若是如此,就是康德所谓“混血的解释”或“混合的定义”[注][德]康德:《道德形而上学》,李秋零译,《康德著作全集》第6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234页。),确实属于人的实践理性的任意意志,而不是“动物的任性或者奴性的任性”——“可以受纯粹理性规定的任性叫做自由的任性[arbitrium liberum],而只能由偏好(感性冲动、刺激)来规定的任性则是动物的任性(arbitrium brutum)”[注][德]康德:《道德形而上学》,李秋零译,《康德著作全集》第6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220页。——从而为“表演”作为人的任意选择的自由意志,进行美国式的辩护呢?这也就导致了美国民俗学的“表演理论”在理论上的失败。当然也可以反过来说,这正是美国民俗学成功的地方,因为这就是美国人的“实用主义”风格,重要的不是“说了什么”而是“怎么做的”,只要你通过你的研究展示了民众的表演,你也就维护了人的自由选择的基本权利,而不在于民俗学家们在理论上是否把“语境”概念讲清楚了。不过,讲不清楚的“语境”概念,却在“跨语际旅行”[注][美]刘禾:《跨语际实践——文学,民族文化与被译介的现代性(中国,1900-1937)》,宋伟杰等译,三联书店,2008年。中给受动国的民俗学者造成了理解和解释上的理论和实践困难。
由于美国民俗学家“幸运”地生活在一个表演的权利已然被确立的语境(我们暂且因其理论化、古典式的用法)当中,所以,即便美国民俗学家于“职责/责任”的实践理念,完全弃之而不用(当然不是事实),而只是戴着语境的理论眼镜,到“全国各地”去直观民众的表演,就已经是在通过“呈现社会事实”而维护、促进民众的表演权利了。[注]吕微:《“表演的责任”与民俗学的“实践研究”——鲍曼〈表演的否认〉的实践民俗学目的-方法论》,《民间文化论坛》2015年第1期。
但是,民俗学基本理论和方法论的矛盾(我们无法用理论理性的方法实现实践理性的目的)并没有因此而得到解决。美国民俗学家甚至没有意识到,自由意志不能通过经验来证明,而仅仅通过显现的现象,我们无法区分人的“自由的任性”和“奴性的任性”(甚至“动物的任性”)。因此,即便我们可以承认我们的“欧美同行们甚至已经超出了我们现在所面对的问题了”——因为我们的问题还没有进入“后期康德问题”即人的任意选择的自由权利,而是停留在“前期康德问题”即人的普遍立法的自由权利)——但我们的“欧美同行们的学术路径与学术成果”,确实不曾“把我们这里所谈到的问题都谈过了,而且不仅只是谈过了,甚至讨论得还更深入一些”。只有真正在理论上的彻底阐明,才能够让各国民俗学在引进美国民俗学的理论和方法时,即便面对不同的国情,在给出不同的解释的同时,也能够面向各国民俗学之间共同的“母题”(彭牧),并给出共同的理解。
以此揆之,“我们中国民俗学家为什么一定非要步趋于欧美同行的后面呢?”[注]王杰文:《语言人类学与民间文学的“存在论”》,《民间文学论坛》2014年第3期。而根据康德对理性的批判性检验,我们正可以推论出,欧美民俗学家们只是关注了人的自由意志的一个方面,而不是所有的方面,而欧美民俗学家不曾关注的方面,也许正是中国民俗学者应该关注的问题。
对于西方民俗学者来说,现在专讲文化的多样性及其合法-合理性就可以了……当这个任意性在构造语言、构造文化的时候,进而,当我们通过任意性来认识语言、认识文化的时候,我们已经悬置了任意性的绝对前提——主体的纯粹理性的自由意志。就此而言,仅仅通过任意性来认识语言、认识文化,这绝对不是一个起源于当下中国的问题,而是一个起源于西方的当下问题,即一个只有在今天的西方社会才有可能被提出来的问题。而现在,如果我们把悬置了自由前提的语言问题、文化问题(文化多样性正位列其中),视为一个在全世界都同质的问题来处理,那我们就是在把一个西方的内部问题当作我们中国的内部问题来处理了,或者说用一个西方问题遮蔽了中国问题[注]吕微:《走向实践民俗学的纯正形式研究》,《民间文化论坛》2014年第3期。(如“民间信仰,在中国是而在美国不是一个重要的研究题目”[注]高丙中:《中国人的生活世界——民俗学的路径》,《民俗研究》2010年第1期。)。
于是,立足于欧美同行们已经无须谈,而中国民俗学者却仍然必须谈的地方,我们就能够从“以认识任意选择的自由意志的民俗‘法象’为诉求的一般实践理性的学术范式”,过渡到“以认识普遍立法的自由意志的民俗‘法象’为诉求的纯粹实践理性的学术范式”,也即王杰文提出的“超现实主义民俗学”的命题。[注]“超现实主义民俗学”是王杰文在“当代社会口头传统的再认识——首届民族文学研究博士后论坛(2014·北京)”的评议发言中提出的命题,如果我的理解无误,则“超现实主义民俗学”也就是“民俗学的实践范式”,或“作为实践科学的民俗学”,即“实践民俗学”。
我在上文已经指出,康德对亚里士多德“理性论”的改造,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在实践理性中区分出受感性经验影响的一般实践理性及其任意选择的自由意志,和超越感性经验的纯粹实践理性的普遍立法的自由意志。这样,康德就为建立在人的纯粹理性的普遍立法的自由意志的前提下,基于道德理想的现代性实践,确立了普遍性的原则基础。而且,康德关于理性的使用方式的三分法,即便经历了现象学、语言学(语用学)的方法论洗礼,在后现代也仍然不失其理想的实践意义和现实的理论意义。[注]潘琼阁:《在真实与虚构之间——从海登·怀特历史诗学看民间历史叙事》,“当代社会口头传统的再认识——首届民族文学研究博士后论坛(2014·北京)”论文。即便后现代学术依据现象学方法论悬置了理论理性对实践理性的现代性遮蔽,建构了基于人的任意的复数的日常生活-生活世界的“理所当然”性,却也仍然未脱康德所云受感性影响的“一般实践理性”的任意意志的主观相对性[注]倪梁康:《现象学及其效应——胡塞尔与当代德国哲学》,三联书店,1994年,第132页。,进而主观相对(户晓辉解释“主观相对的”为“相对于主观的”[注]户晓辉:《返回爱与自由的生活世界:纯粹民间文学关键词的哲学阐释》,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333页。,即不是绝对必然)的任意意志,也就仍然要以纯粹实践理性的普遍立法的自由意志的客观必然性为绝对条件,道理很简单,立法的意志在逻辑上必然先于选择的意志,没有普遍立法的自由意志,何来任意选择的自由意志?没有自由意志在道德上的普遍立法,人何以任意地为“仁”?
这就是说,我们已经有了基于理论理性对民俗实践的自然因果性的经验研究(包括文本研究和语境研究),也已经有了基于一般实践理性对民俗实践和民俗学实践的自由因果性的“经验”研究,但是我们还缺少出于纯粹实践理性对民俗实践和民俗学实践的自由因果性的先验研究或纯粹研究。这样的研究范式,是我们根据康德对理性使用方式(也就是学术理性的研究范式)的三分法,从人的理性本性的整体性中必然地“推导”出来的,亦即从人的存在的最高原则或终极原理(公理)逻辑地推论出来的。强调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如若中国民俗学的“实践认识”的研究范式只是因应中国实践之本土经验的理论需要,那么“实践认识”的研究范式,对于民俗学学科来说就仍然是或然的或者偶然的(民俗学知识的经验来源)。但如果该范式是从人的先验的、纯粹的理性本性(对于本文的论证来说就是学术理性)的整体性中逻辑地推论、推导出来的,那么这样的范式对于各国民俗学来说,就是必然的共同“母题”(民俗学知识的先验起源),尽管该范式(“母题”)目前还不是实然的。因为,仅仅还原到受语言、文化限制的人的主观相对的任意意志,人(民)的自我认识就仍然是不完整的,以此,民俗学的实践研究需要还原到人(民)的纯粹理性的普遍立法的自由意志,就不仅是民俗学知识谱系的外在需求,同时也是民俗学学术理性的内在要求。
当然,当我说到中国民俗学界,还不曾有“以认识普遍立法的自由意志的民俗‘法象’的先验对象为诉求的纯粹实践理性的学术范式”,只是就学界当下的主体或整体(并非朝向未来的主导、主流)面向而言,却并不意味着中国民俗学界从来就没有这方面的尝试。如在陈连山看来,民间游戏(包括民间儿童游戏)是人们依据其纯粹实践理性的自由意志而普遍立法的社会化活动。
民间游戏具有单方面的社会文化功能。它是儿童最正当、最理想的社会活动,全面培养了儿童的社会角色意识。同时,民间游戏也体现了人类社会的一种基本理想:自由、平等、公正。[注]陈连山:《游戏》,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33页。
这就是说,游戏的能力,即纯粹理性的普遍立法的自由意志的实践能力,先验地存在于人的本性之中,要想“成为道德的人,成为理性的人,必须首先是一个游戏的人”[注]邓晓芒:《康德〈判断力批判〉释义》,三联书店,2008年,第189页。。西村真志叶对“拉家(聊天)”共同体的研究也阐明了,只要不干涉老百姓先验地拥有的立法权利,正常(不受干扰)地发挥其普遍立法是自由意志的纯粹实践理性能力,普通人就必然能够建立起一个交互主体自由、平等、公正地交往的爱的共同体。[注]西村真志叶:《作为日常概念的体裁——体裁概念的共同理解及其运作》,《民俗研究》2006年第2期。就此而言,自由、理性不是西方(文化)人的专利权,也是中国(文化)人的内在性,即彭牧所言共同的“母题”。除了陈连山、西村真志叶对民俗现象的“实践研究”,还有高丙中从“公民社会”的“范畴”即“时间化”语境的立场出发的民俗实践研究。在高丙中以建构公民社会为先验理想而提倡且践行的实践民俗学中,“公民社会”作为民俗实践和民俗学实践的先验语境条件,被提到了空前的高度。
家族组织在结社形式上是传统的,但是家族作为组织实体却是当代的。大量关于家族组织的研究忽视了这样一个基本事实,未能把城乡各地在近三十年涌现的家族组织作为当代的公民自愿结社看待。……传统社会的家族属性不能够轻易套用在当代家族组织上,当代家族组织再怎么具有传统的属性,我们也不能否认它们是当代公民的结社。……我们高兴地看到,个别学者已经在尝试用公民社会来认识家族组织,这是我们非常认同的研究方向。……农民作为公民,进行各种结社活动本来是再正常不过的,无论他们采用何种结社形式。可是,我们的社会长期简单地把家族组织当做“过去时”,当做与官方正式制度和各种现代性相对立的事物。这种社会认知使人们把家族组织当做特殊的例外看待,妨碍了人们把家族组织当做一般的社团来看待。[注]高丙中、夏循祥:《作为当代社团的家族组织——公民社会的视角》,《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4期。
我们要把龙牌会放在“公民社会”的范畴里来审视是很具有挑战性的。显然,龙牌会初看起来与中国学界关于公民社会的常识有很大的距离。但是,过去十多年对于龙牌会的跟踪观察让我们见证了传统草根社团迈向公民社会的历程。我们在多年的观察和思考中认识到,恰恰是够远的距离让这一案例具有更大的理论潜力和更强的说服力。[注]高丙中、马强:《传统草根社团迈向公民社会的历程:河北一个庙会组织的例子》,高丙中、袁瑞军主编:《中国公民社会发展蓝皮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
总之,我强调重构民俗学知识谱系的经验知识的必要性,但是我更主张民俗学观念还原的先验知识的充分必要性。而这些重构,显然都与我回到康德有关。当然,并不专断地坚持只有康德才是民俗学先验知识的回溯终点(同时也是民俗学知识的先验支点或起点),我认为,只要能够抵达“人类的心灵”[注]王杰文像康德一样强调回到“人类心灵”的重要性。参见王杰文:《“生活世界”与“日常生活”——关于民俗学“元理论”的思考》,《民俗研究》2013年第4期。,任何人都可以引导我们返回民俗学的精神故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