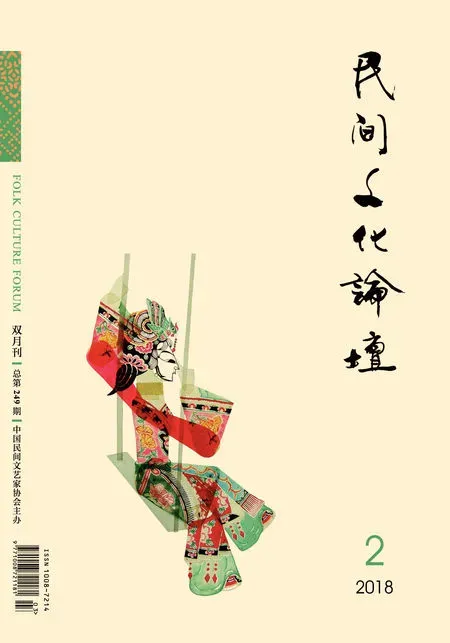民俗学的调查论问题*
2018-01-23福田亚细男菅丰塚原伸治赵彦民
[日]福田亚细男 菅丰 塚原伸治 著 赵彦民 译
20世纪民俗学随着学院式的发展,田野调查这一手法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确立了在同一时期同一地域集体分担调查的共同调查的手法,但是,其手法的确立有哪些背景、动向呢?
其次,其手法虽然提高了调查的效率性和专门性,但是,另一方面,也造成了专门领域的圈绳定界、调查项目主义的弊病。福田先生通过对《民俗调查手册》等书籍调查手法的体系化,参与了很多调查手法的确立,那些手法在现今以及今后还有效吗?
另外,20世纪民俗学的后半期,非常盛行由公共部门提供资助的地方史编撰事业,很多民俗学者被动员,在社会上对提高民俗学的认知上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是,基于国家资助而产生的大量的《民俗志(民俗调查报告书)》现在还有意义吗?福田先生积极地参与了这些地方史编撰事业,对于这些事业如何来评价它的功罪呢?
一、20世纪民俗学初期的调查方法是从各地收集事象,即“采访型=昆虫采集型”,是把民俗标本化、分类比较的方法。为了超越这样的方法,开发了一个地域的分担型共同调查和地域民俗学的调查法,但是,在其形成过程中有怎样的背景呢?这些调查方法的有效性和局限性是怎样的呢?
二、在学科手法的泛用化这一点上,对20世纪民俗学发展作出贡献的《民俗调查手册》,另一方面,在把调查程式化(不设定问题意识)、手册化、类别化这些点上受到了批评,关于这些评价福田先生您是如何看呢?
三、20世纪民俗学的很多田野调查与人类学相比,在田野调查的深度、持续度、综合度方面上还相差很多,那么,21世纪的民俗学应该以什么样的田野调查为目标呢?
四、在考虑现代社会的文化状况的时候,即使我们把民俗判定为限定性的文化,仅依靠地域民俗学的调查也会出现无法全部把握的问题吧?
五、福田先生在参与文化财保护管理等国家部门的民俗学活动方面似乎并不是很积极。但是,福田先生却积极地参与公共部门提供资助的地方史编撰事业的理由和目的是什么呢?
六、在地方史编撰事业中,与地域民俗学及项目分担型集中共同调查法的发展进行了呼应,但是这些事业给民俗学带来了什么样的学术成果呢?教育效果是怎样的呢?社会认知是怎样的呢?
七、另外,推动20世纪民俗学的地方史编撰事业给一般社会或者说给将来带来了哪些积极的成果或贡献呢?历史的贡献是什么呢?
八、另一方面,推动20世纪民俗学的地方史编撰事业被认为无论是对学科还是社会都具有积极的方面。对学科来说,发展成为由分担意识而导致的专业分化和调查方法的手册化,夺走了自发性选择田野、选择研究对象的意向和时间,不是成为民俗学知识体系发展的障碍了吗?
九、而且,组成了调查员/专门委员=学生/教员这样结构的榨取机构,偶尔不是也发生过剽窃、擅自使用他人成果的伦理问题吗?
十、更进一步,现今积累的《民俗报告书》具有与调查费用相抵的社会意义吗?没有浪费公款吗?
十一、地方史编撰是为了谁呢?研究者吗?
民俗学调查方法的改变
菅:那么进入下一个课题5“民俗学的调查论”的问题。课题如下:
20世纪民俗学随着学院式的发展,田野调查这一手法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确立了在同一时期同一地域集体分担的共同调查的手法,但是,其手法的确立有哪些背景、动向呢?其次,其手法虽然提高了调查的效率性和专门性,但是,另一方面,不是也导致专门领域的圈绳定界了吗?在民俗学中,经常会介绍自己的专业领域,例如“我的专业是人生仪礼”。这些不是相应地形成研究领域的圈绳定界了吗?
福田先生,总的来说是具有多面的才能,致力于各类的研究活动,而我只是专注我自己专门领域的研究,无论如何我也描述不出日本民俗学的整体形式。促使这样专门领域的圈绳定界、或致使调查项目主义这一弊害受到了批判。
福田先生通过《民俗调查手册》《民俗研究手册》(上野·高桑·野村·福田·宫田编、1978)等书籍的调查、研究方法的体系化,为学院派民俗学做了很多的贡献。但是,在上述论著中提出来的调查研究方法,现在以及今后还有效吗?
其次,20世纪民俗学后半期,地方社会等公共部门提供资助,非常盛行所谓的地方史编撰事业。很多的民俗学者、学生被动员参与了这些活动,对在社会上提高民俗学的认知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是,现在我们必须重新审视基于公共资金所产生的莫大的、所谓的民俗志现代的意义。
实际上,这些“民俗志”的表述也具有不协调的感觉,不能翻译成英文。作为与Ethnography的“民族志”不同的表述在使用。这仅在日本通用,或者说仅存在于日本。把它向世界介绍的时候,究竟如何翻译呢?也不存在“Folkgraphy”这样的表述,终究还是“民俗调查报告书”。只不过是报告书罢了,能说它有发挥现在性意义吗?实际上,福田先生也非常积极地参与了这些地方史的编撰事业,想说的是对于这些事业有怎样的功罪,福田先生自身是如何评价的呢?
说一下这个问题的背景。说是调查手法的进化呢,还是什么呢?是变化吧。这些现象在迄今为止的民俗学中也存在。1950年代,民俗学过渡到以大学为中心的研究体制。这就是福田先生指出的,从1930年代开始由柳田主导的山村调查、海村调查、离岛调查①以听《民间传承》讲义的柳田的直系弟子们为中心,从1934年开始了“山村调查”这一事业(从1934年开始的三年调查计划)。调查是从日本学术振兴会获得资金资助而实施的,申请题目是《日本僻陬诸村的乡党生活的资料蒐集调查》。调查使用了100个共通项目的问卷提纲,试图调查日本整体,这100个项目的问卷提纲被印制成《采集手册》而被使用。其成果作为《山村生活的研究》(柳田编、1937)出版刊行。山村调查结束后,同样取得了日本学术振兴会的资金资助实施了“海村调查”(正是名称为“离岛及沿海诸村的乡党生活调查”),从1937年开始计划调查三年,但因资助资金终止,第二年便结束了调查。无论“海村调查”还是“山村调查”都同样制作了《沿海地方用采集手册》。其成果在战后作为《海村生活的研究》(柳田编、1949)出版刊行。“离岛调查”是取得文部省科学试验研究费而进行的“本邦离岛村落的调查研究”,使用“离岛采集手册”实施了调查(从1950年开始的三年调查计划)。在离岛调查中,进行了家庭调查和把握人口数量等新的尝试,另外在报告描述中也不是以每个项目来汇总各地的调查结果,采用了以每个对象地域来进行描述的方式。这些调查成果的公开稍有些迟延,作为《离岛生活研究》(日本民俗学会编、1966)出版刊行。关于这些调查的详细内容及研究成果的评价,请参照福田亚细男《日本民俗学》(福田、2009)。等调查是个人调查,即一名调查者使用同一调查项目调查一个地域,这种方法在1950年代开始发生变化。最早发生变化的民俗调查是由东京教育大学主导的“民俗综合调查”②1958年,以东京教育大学的和歌森太郎为团长、竹田旦为干事组成的调查团获得科学研究资助资金,开始了“民俗综合调查”。初年度的1958年,以大分县的国东半岛为对象,之后陆续向日本列岛北部展开调查,1959年爱媛县宇和地方、1960年鸟根县西石见地方、1961年冈山县美作地方、1962年兵库县淡路岛、1963年三重县志摩地方、1964年福井县若狭地方、1965年宫城县陆前地方、1966年青森县津轻地方。调查团在前述介绍的和歌森、竹田之外,由东京教育大学、旧东京文理科大学、旧东京高等师范学校等相关研究者直江广治、荻原龙夫、千叶德尔、樱井龙太郎、宫原兔一、松冈利夫、龟山庆一、北见俊夫、西垣晴次等人为中心构成,每个调查地也有数名当地研究者加入。东京教育大学的学生也随行参与了调查,作为学生参加的调查者中在此后执笔报告书的人也比较多(例如,宫田登、平山和彦、福田亚细男等)。1968年开始由北向南反转,计划调查冲绳诸岛,大部分调查也结束了,但是以报告书未刊而告终。。我想,大家都了解,以1958年的大分县国东调查(和歌森编、1960)为契机,最后有些气力不继,冲绳也做了调查,但报告书没有出来,做了10年的综合调查。
在综合调查中,采取了以分担调查项目、同一日程共同调查的形式,把很多地域作为了调查对象。并不是以一个村落为调查对象。这一时期,向所谓的追求科学性、标准化、对象的类别化发展。其中,例如刚刚所提及的社会传承、信仰传承、经济传承,所谓的类别化的日本民俗学独特的区分在一定程度上被固定化。调查和研究的类别化是处于并行的发展状态中。
所以,存在如下问题。20世纪民俗学的初期,我认为,柳田国男主导的调查的方法是采取从各地收集民俗事象的采访型、昆虫采集型的方式,把民俗标本化,进行分类比较。为了超越这样的方法,开发了一个地域的分担型调查和地域民俗学形式的、即仅针对一个地区进行周密的调查方法,在这一形成过程中有怎样的背景呢?这些活动,我想是与福田先生同时代的。像在国东那一带的调查,还不是学生,我想您不了解。福田先生,您参加综合调查了吗?
福田:参加了。
菅:参加了哪一个?
福田:从宇和开始的。
菅:那么,是从1959年,大学一年级的时候吧?
福田:是的。从一年级开始。
菅:第一,关于这些调查背景,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那些调查的有效性与局限性。在这一时期发生的现象,即使是不直接,我想给在此之后的地方史编撰带来了影响,并且给日本的民俗学中独特的调查法、即经常使用集团调查这一方法也带来了影响。这是20世纪民俗学调查方法的最大的特征。
第二,在学科方法的泛用化这一点上,是给20世纪民俗学的发展做了贡献的《民俗调查手册》的问题。这个问题在1980年代已经受到了各种各样的批判。在调查不设定问题意识、程式化、规格化和类别化等点上受到批判。对于这些评价,福田先生是如何考虑的呢?
对于这些问题我也感觉是同样应该批评的部分,但是,与学科史相对应来看,我想在学院化的进行过程中命中注定这样的问题会一度登场的吧。并且,如果从时代背景来解读的话,我认为它也有作出了很大贡献的一面。问题是,简而言之,我认为是利用这些方法方面的问题,对此福田先生有怎样的意见呢?
第三,20世纪民俗学的很多田野调查与人类学相比,对于田野的深度、持续度、综合度方面还相差很多这样的缺陷问题。我想真的可以说昆虫采集型吗?从其地域抽出某些现象,在下一个调查地收集同样现象的调查。从这些现象描述出的东西,说几乎像一直摆放着的金太郎糖①金太郎糖是一种棒状糖果,断面呈日本传说中金太郎的面部形象,无论在那里切断,断面都呈现的是金太郎的面部形象,通常用来比喻同一性或统一性。——译者注也不为过吧。最近,当然,出现了比人类学还长的国内调查的例子,不过,20世纪民俗学成立以来至1990年左右为止,那样的昆虫采集型比较多。在这一背景下,21世纪民俗学应该以什么样的田野调查为目标呢?
更进一步,在考虑现代文化状况的时候,民俗作为地域限定的文化,仅是通过地域民俗学的调查,不是还会出现把握不了的问题吗?它也与传承母体论有关联,现今的调查方法,简而言之,被认为是作为一个传承母体那样的方式不是很困难吗?我的问题是,即使是只对一个村落调查,把握不到的现象,仅限于民俗这一小的对象不是也会出现吗?例如,像无形文化遗产那样的问题。
再者,另一个征集提问。刚刚介绍过的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的副研究员施爱东先生的提问。
在现在的中国,除民俗学自身发展这一问题以外,在大学或研究机构,如何提高民俗学自身的重要性呢,可以说面临学科留存的问题。在这一状况中,只是经历编撰调查报告书的民俗学是“资料学”,有被认为不是“学术研究”的担心。所以,近几年,有研究者提出应该消除外部的人对民俗学持有的“资料学”的印象,提倡“田野研究”这一概念。我听说,福田先生坚持在浙江省等地进行长期调查活动。福田先生能告诉我一下通过这些调查活动获取的资料是如何使用的?福田先生曾经指出过:“无论怎样的情况,调查包含着分析,在分析的过程中验证自己的假说,作为其调查结果的民俗资料必须作为研究的组成部分登场。”我的问题是,福田先生如何分析这些调查结果的呢?如果你能告诉我,深感荣幸。
调查手册与集团型调查产生的背景
菅:开始,我想让福田老师回答一下关于从20世纪民俗学的初期调查法到集团型调查法变化的经过。所谓的对东京教育大学的综合调查方法发生改变的经过,实际上并未被更多地认知,简单地来说,它是追求科学性那样的行为吗?
福田:如果用科学性这样的词语来说的话就是科学性,基本上,在这期间,九学联合会的调查包括在内。九学联合会的调查,换言之,在人文社会科学中以实施田野调查的学会,最终是集中了九个学科,对某一对象地域进行调查。所以就是调查地域非常广泛,例如对马、能登、佐渡等。在这些地域中,组成调查团队,不过,团队大致是以各学会为单位组成,虽然如此,根据情况也有组成学会联合调查团队而进行的调查。其中,民俗学者们参与了大范围的、以往方式的调查,在这些调查中,与社会学等学科的组成团队做了村落规模的调查。在经历这些调查后,开始了以和歌森太郎为中心的调查。简而言之,1958年就是在东京教育大学开始民俗学专业教育、接收民俗学专业学生的年度。在这一年,同时申请了科研项目,开始了科研项目的调查。所以,我认为是在九学联合会这一基础之上的调查方式。
譬如今天讨论的这些话,在这里觉得好像有非常大的意义,当然,大学的研究体制在推动地域的民俗调查这一意义上非常重要,但是,我没能怎么看出这些调查有很大的意义。这是因为,像所指出的那样,是范围的调查。20个人左右去圆形的国东半岛10天,设定好出发集合地与集合集结地,在这期间是每个人去各处调查。因此,是每个人分担调查项目,以个人的形式调查。并且,在地图上看国东半岛虽然很小,但如果一去,是10天转不完的地方。所以,调查大约是一天一个地方,根据情况,有时上午和下午分别要去不同的地方。
我是从宇和开始参加的。宇和、西石见、然后隔了很长一段时间是若狭。在此后是陆前、津轻。所以,宇和、西石见是我学生一年级、二年级的时候。在这之后,若狭是我大学毕业后做高中老师时参加的,那么陆前和津轻是我读研究生的时候吧。就是这样的感觉。我虽然一直参加这些调查,这样说有些不大好,我不大喜欢这些调查。是因为,基本上没有考虑到深入调查个别地域这样的想法。当然,不过,包括我在内的一部分调查者,用10天左右的时间走访结束调查对象全部范围,在此后采取留在当地调查个别村落的形式,限定在一定地域内调查或以补充调查的形式,下次是在冬季一个人进入一个调查地一直进行调查。
我不知道这是否是调查方法的演变,但必须考虑与此并行的是,可能会出现水平低这样的评价,大学的民俗学研究会在这一时期展开了活动。它的结果是,专业教育仅局限于大学,大体上,增设一门课程的大学在增加。在这一过程中,成立了民俗学研究会这一组织。与其说民俗学研究会活动的核心内容是做民俗调查。倒不如说,在其调查实施中逐渐地出现了进化的过程吧。
例如,国学院大学民俗学研究会也是一直到最后尽了最大努力,其方法比较古典。简而言之,调查地域没有像国东、宇和那样大的范围,以某个市町村为单位,仍然是在市町村中的诸多村落中到处走访,或者说,我不清楚是否到处走访,不过,是采取调查很多地点的方式。不是调查一个村落,是采取在市町村中调查数十个地点,然后编撰报告书的形式。此后,很多其他的大学的研究会也采用了这个方法,我想大概是在1960年代后半期左右,我不能说清详细经过,但是,民俗学研究会的民俗调查像调查个别村落那样而转变。另一方面,专业教育的民俗调查实践也向这一方向转变。所以,在这点上来说,东京教育大学的民俗综合调查确实是,在分担方式这一点上,山村、海村等不相同,在大范围综合调查这一点上也有特色,我想倒不如说在这之后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吧。
菅:诚然。我的知识面有些局限,对这一部分很不了解,是通过所谓的学校教育开发了调查方法吧。因为是所谓的教育,教员必须一个人带领学生去。在调查中,当然,如果学生做调查的话,相互去一个调查地时,特别是小范围的调查地时,研究领域、调查内容会重合。为了尽量避免这种重合,制定了所谓的分担制这样的方法。
这种划分类型的分担制,到了以后,给在这里的讨论话题,自治体史那样的类型、定型的调查也带来了很大的影响。简而言之,20世纪民俗学在学院化过程中,所谓的参与教育教学中,可以说调查论也发生了很大的根本性改变。
与其说这是福田先生的责任,不如说是我想批判20世纪民俗学中的一部分。当然,在时代上,福田先生还没具有那么大的影响力,所以我认为不是福田先生的责任。但是,20世纪民俗学在学院化时,很显然像那样的分担方式,如果现在思考的话,其方法与目的的功罪,我想具有两面性,在“描述”这一点上,与一个人深入地描述人类学那样的调查相比,打开天窗说亮话不是相差很大吗?这是罪过的部分。如果这样考虑,这样归纳也可以吧。20世纪民俗学的调查方法,并非因为学院化而得到发展。福田先生认为是变得更好了吗?
福田:这是非常难的问题。不过,作为调查的内容变得丰富了。换言之,刚刚被你说是昆虫采集,昆虫也好什么也好,是采集型调查,正是这样,调查者自身承担课题,无论对四处走访仅是调查课题还是辗转各地做些什么,可以说,更重要的不是通过更针对对象的分担来深入主题吗?像你指出的那样,成为大学的实践或研究会的调查是因为,其一,的确是还有一个人类学以外的调查,事实上,在实践的水平上人类学也同样。总而言之,以分担主义的方式来做。
如果说它是什么的话,总之它是有前辈的。前辈是什么?是社会学。无论在哪一所大学都是社会学先开始实施调查实践。它的基本操作方式是分担主义。通过项目分担,无论对象是社会、村落或都市都可以,通过对对象的各种调查、分析,编撰报告书。因此,大概,我想民俗学的调查实践或研究会的调查通过调查项目来分担任务不也是理所当然的吗?
《民俗调查手册》的功罪
菅:《民俗调查手册》饱受批评,我想福田先生也非常厌烦了吧。请福田先生给予评价。
福田:基本上,确实是这样。就是手册化了。
手册就是,简而言之,在进入大学二年级或三年级最初去民俗调查的时候,为了自己学习该如何调查的书,我完全没有预想到,一直被这本书束缚,努力地在这本书上作出红线标记,或者根据需要进行复印,拿去用于调查,也就是说也没有期待,我想这里在座的各位中也会有相当一部分的人大概至少用过一次这个调查手册吧。我觉得一次是可以的。完全没有必要一直都用这个手册,在这一点上,如果说功罪的话,我想也有功吧。至此为止,完全没有民俗调查的教科书或参考手册。有的是,“让学长某某某教你”这样的话。多啰唆几句,我们在东京教育大学接受的民俗调查实践是,约十几名学生跟着一名老师,去采访某一人家。并且,就是全部由老师提问,学生在后面只是记笔记。
我困得没有办法(笑)。但是,我们不能动脑去提问。老师一边在自己脑中描绘相关联的事项,一边一个接一个地提问,我们仅只是记笔记。对于这样的状态,在为了如何能让自己做调查这一点上,制作了调查指南手册。这也是,实际上,如果在这里介绍的话,那它是由哪一位写的呢?《社会调查手册》(安田、1960)由安田三郎先生所著,是非常出色的调查手册。我上了安田三郎先生的课,用的是出版前的手工制作的社会调查指南,以此来教授我们,在课堂上接受了各种各样的训练。此后,《社会调查手册》出版,有了“果然,没有这个不行”这样的想法,尽管仍是研究生便狂妄地撰写了《民俗调查手册》。
菅:它受柳田国男与关敬吾汇编的《日本民俗学入门》(柳田·关,1942)的影响了吗?
福田:《日本民俗学入门》只是口述采访问答提纲。基本上,只是口述采访问答提纲的排列,所以,例如如果去村里时会有不知道如何调查这样的问题。因此,那本书,对有一定调查经验的人如何更深入细致地调查会有很大的参考,不适合调查初学者。另外,调查不仅是口述采访问答,实际上,即使是现在我也经常说,有很多人认为民俗调查等同于口述采访问答,我出版调查手册就是想说并不是这样的。
菅:在那之后出版了新改定版吧。那时候,很多内容的“实质”都发生了改变。但是,出版社的人有些叹息地说改定版卖得不太好,倒不如原来的旧版卖得好。不如原版有需求,是因为改定后还有来订购旧版的。那时候新版改定的意图果然还是为了回应对手册的指南化而遭受的批判吗?
福田:基本上,多少是与应对社会的变化而改定的。一个说是调查分析地域吧,我想重点是收集作为能分析调查内容那样的数据。
菅:那么,现今,我们是更应该与时俱进而改变吗?如果想改变的话,需要剧烈的变化。以手册的形式出版了,从现在的情况来说,要是以历史民俗学为基础的民俗学的话,没有必要制作手册。今后,我想不能作手册吧。
福田:在这里我想也有相关的人吧,通过丛书的形式,在《民俗调查手册》之后,出版了《民俗研究手册》。简而言之,它记述了研究史,提供了文献讯息。当时,归根到底,在大学里没有系统的课程。大致,民俗学也就一门课程。在这样的背景中,是为了针对刚开始民俗学研究的人而编撰的。是几年的时间里出版了《民俗研究手册》吧。因为我们已经成为老人,怎么也不能捕捉到新的研究动向,所以说让现在的年轻一代继承,寄托于下一代的年轻学者,期待《民俗研究手册》的第二版。但是,并未能出版。出版的是《现代民俗学入门》(佐野·谷口·中入·古加编,1996)。简而言之,预定出版的第二版《民俗研究手册》没有成为研究手册。我们期待它是作为第二版的研究手册的研究信息、资料或者包括研究动向的内容,但出版的内容却是完全不同的东西。不过这也是一个信念,或是说思考,也无可厚非,不过还是有些不同。
菅:在您讲述中间出现了,作为对90年代开始的动向持怀疑态度的福田先生,简而言之,对《现代民俗学入门》弄清了什么也是持怀疑态度的吧。如果让我来给这本书做评价,可能会有些得罪。
福田:没有、没有。在这里有几位执笔者,让他们听一下你的想法不是更好吗?
菅:那个时候的尝试作为结果,现今我不认为是成功的。但是,最后,我想只有反复不断地进行那样的尝试。
福田:没错,是这样。
菅:反复不断地进行学术史研究也非常重要,但是,福田先生出版了学术史之后,想出新的学术史也不过是刚经历10年左右吧。
福田:是10年还是15年,我也不知道。
菅:难道不是把这一期间的学术史归纳整理成一本著作的意义,或者说是在此之前学术史的变化足以进行重构吗?
福田:这个问一下当事人就可以了嘛。
菅:罪的方面如何呢?
福田:《民俗调查手册》的罪吗?当然,把其手册化后,出现很多后辈把它作为重要工具随身携带,这是绝对不合适的。基本上,民俗调查的一个很常见方法,经常挂在嘴边,宫本常一先生等那些人我想也是这样,是“从路上闲谈到调查”。简而言之,无论是在村里、町里、任何地方、市场,去那些地方的时候,与那些地方的人从站着闲谈中得到契机,或者说形成人际关系,然后进入调查。“进入”这样的说法可能不恰当,像这样的路径从表面上消失了。
通过调查手册接受训练的人,如果某人不做准备就不能完成调查。是自己设计的调查还是做开辟调查,都会有非常不擅长的人。简而言之,调查手册是以实施集团性的调查、要进行一定的联系或采取各种手段实施的调查为基础,所以个人作为调查一员进行调查的活动被认为是理所当然。这一点在制作方式上,虽然写着是个人的调查,结果,个人并不能成为中心,大大缩小了调查应有的状态。特别是,过去还没有调查方法和调查手册的时候,自己开创的方法最后中断了。我想这是最大的问题点。
菅:即使现今像集团调查那样的活动在大学里作为教育的手段还在实施吧。
福田:是的。
菅:当然,福田先生也在大学的教育里实施着集团调查。集团调查在现今还有必要吗?
福田:我想还是有必要的。作为训练的环境,如果没有这样的环境能会调查吗?
菅:如果从那个时候以来看教育功罪兼半的历史,现在,必须要有相当的意识进行包括功罪的教育吧?
福田:这是当然的吧。不过,不是有意识地进行教育,即使参加调查的人是本科生,自己能努力做多少也是问题吧。我觉得对通过教育的形式进行指导的部分是相当有限的。
菅:这里最后的问题,对“在考虑现代社会的文化状况的时候,即使我们把民俗判定为限定性的文化,仅依靠地域民俗学的调查也会出现无法全部把握的问题吧?”这一问题如何回答呢?
福田:这确实是这样。这不是我说的,也是哪一位最近说的。例如,现今在编撰的民俗调查报告书,读民俗报告书的人可能把其当作现在的事来读,实际上到当地一看,现在几乎没有在持续,写的内容都仅是以过去式的形式的这一点上,首先可以说民俗调查以来的报告书存在不能了解现今的这一事实。所以,在这一点上,如果说不能全部把握没有错,但是,并不是没有实施现代社会调查或现代文化调查那样的体制吧。
菅:尽管说一个人能超越地域、把地域置于一个重点,但是,我想以此为开端确保一点后,展开整体调查在今后会是有必要的。大概,像在20世纪民俗学中不存在那样的,一种有别于刚才所说的,用以描述那些被“传承母体论”所概括的事物的描述方式,我想今后有可能实现,我们应该去摸索。
还有,施爱东先生的提问,请教一下今后中国的调查结果如何分析。
福田:基本上,从我的立场来说,在调查阶段中包含着分析,并且,记录下去。简而言之,我的基本立场是作为研究论文的调查报告。确实,在浙江省出版了几册调查成果,不过,我认识到这些成果还没有达到作为能被认可的论文那样的水平,大体上,我通过在调查对象地域获取的民俗自己进行了分析,虽然比较粗浅,但是刊行出版了,我想今后也可以再将它重新分析一次,不过现在我还没有这样的计划和设想。
地方史编撰事业的现在评价
菅:接着调查论的下一个课题。在调查论中稍微涉及了一下,我想地方史是点缀20世纪民俗学的另一个大问题吧。在60年代前后,由文化厅实施了民俗资料、民俗文化财的紧急调查,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地方史编撰大概是从60年代末开始的。在70年代、80年代比较兴盛,现今也可以说细水长流地做着吧,持续着。
在较早的地方,格外早的是1956年的《宫城县史》(宫城县史编撰委员会、1956),其中含有民俗编。这个是特别早的,大体上是从60年代末至70年代开始的。其中,成为地方史编撰事业划时代的是,常常被提及的《胜田市史》(胜田市编撰委员会编,1957)的民俗编。对于地方史,我也参与过编撰工作,其中,常常让参考的是《胜田市史》。福田先生也作为核心成员参与过。作为年轻的核心成员参与过。在市町村史编撰时,各地方行政之间的交流非常密切,所以在其他地域承担实施编撰活动的时候,它会成为一个信息来源,不仅技术的部分,在很多方面,也包括对调查方法起到了影响作用。
这些地方史编撰事业,虽然无意识,但是作为日本民俗学者参与的公共民俗学①公共民俗学狭义的解释是指,承担文化行政的公共部门开展的民俗文化活动。如果更具体地来说明狭义的公共民俗学的话,是指艺术或文化,或所属于教育等相关的非大学组织、机构,从应用的立场来进行民俗学的研究和活动。例如,很多标榜公共民俗学的民俗学研究者,主要活跃在艺术等文化审议会、与文化遗产相关联的历史类协会、图书馆、博物馆、社区中心、中小学校等教育机构、非营利的民俗艺术或民俗文化组织等公共部门。他们或她们不仅仅进行田野调查和记录,例如,还从事表演或民俗艺术的专门教育、展示、特别活动、音声记录、广播或电视节目、视频或书籍等的公共节目或创作教育相关素材的活动。现在,公共民俗学在概念和形态上发生了很大的改变,追求更贴近市民社会的活动。在表现公共民俗学时,作为现状、最合适的广义的定义可根据Robert Baron和Nicholas R.Spitzer提出的概念,具体如下:“(公共民俗学:引用者注是指),通过传统的继承者与民俗学者、或与文化相关的专家的协同合作,在社区内部、或能表现出超越社区的新轮廓和语境中应用与表象某一民众传统。”(Baron and Spitzer 1992:1)活动值得注意,另一方面,仅是与投入的大量公共资金相抵的价值,从积累的民俗资料中能体现出来吗?我持怀疑的态度。另外,采用了通用化的调查手法,或者通过动员学生也促成了被迫要牺牲一些东西的弊害。我认为必须要将这些地方史编撰事业在民俗学史中赋予恰当的定位,这是20世纪民俗学值得大书特书的活动。我想该必须反思一下了。
那么,下面是我的提问。总的来看的话,我不认为福田先生那么积极地参与了文化财保护行政等公共部门的民俗学活动。实际上,福田先生虽然担任了东京都的文化财审议委员等工作,但并没有参与国家层面的文化财行政工作。我想并不是完全没有邀请福田先生吧,这一点是幕后的情况,所以我想福田先生不会讲,不能认为从文化厅那里完全没有得到邀请。
福田先生没有参与所说的那些活动,可以认为他对公共部门的民俗学活动并非积极,但是,福田先生为什么积极地参与公共部门援助的地方史编撰事业呢?请讲述一下其理由和目的这是一个问题。
其次,通过地方史编撰事业,促进了地域民俗学、项目分担型或基于集团性的共同调查方法的发展,但是这也难以称为发展,它究竟给民俗学带来什么样的学术成果了呢?是教育效果呢?还是提高了社会的认知度?关于这些问题,请讲一下。
再有,推进20世纪民俗学的地方史编撰事业给一般社会、给将来带来的肯定的成果、贡献是什么呢?是说它给社会带来什么好的东西的意思吗。另一方面,我想推进20世纪民俗学地方史编撰事业无论是对学术还是对社会都有消极的方面。对于学术来说,促使了基于分担意识的专业划分与调查方法的定型化的发展,但阻碍了自发性田野调查的选择。
我在学生时代也经历过。我想那是时代的特色,受宫田登先生②宫田登(1936-2000)是东京教育大学出身的民俗学者,历任筑波大学教授、神奈川大学教授等。作为多产的民俗学者而为人所知,除30多本著作之外,文章发表于各种各样的媒体,其概要可以从《宮田登日本を語る》(吉川弘文馆、2006-2007年)系列中了解。对民俗学总体而言发挥了作为组织者的才能,积极地推动发展了各种手册、概论书的编撰,在很多地方参与了地方史的编纂。在此意义上,对20世纪民俗学来说,可以说是与福田先生并行发挥了重要作用的人物。地方史编撰的邀约,兼任了几个地方史编撰的工作。幸运的是,我在地方史编撰以外的部分,还好自己的研究也得到了发展,不过,热衷于这些的方法的时代,确也是事实。像这样的情况,不能说是夺取了自身研究对象的选择权和自己的研究时间、成为民俗学知识发展的障碍了吗?
另外,更明显的问题,有调查员、专门委员等区分,我想这里(指讨论现场——译者注)也有编纂地方史经历者,这样的区分,毫无疑问,我想这是教员利用学生建立起的结构性榨取组织。偶尔不是还发生剽窃、抄袭等伦理性问题吗?宫田登在民俗学上留下了非常多的研究成果,但是谁也不认为是榨取,在大规模性参与市町史的过程中,作为专门委员吸取学生的调查,来完成报告书。福田先生也作为核心成员参与的《静冈县史》也是典型。不过,实际上,我们作为被吸取方,完全没有认为是榨取,现今也没有这样想。我想是那个时代的地方编纂事业的结构性问题。
但是,对我个人来说,有更过分的经历。在大学课程实践中写的东西,没有得到任何预先联系,被某地方编纂人员全部抄袭,有这样被剽窃的经历。可以说,这个时期的地方史编撰事业孕育了这样轻视研究伦理的问题。
而且,更重要的问题是,像已经指出的那样,积累的民俗报告书、民俗志、市町村史的民俗篇究竟是否具有与所使用费用相当的社会意义呢?不是仅以浪费公款而告终了吗?是为谁而做的地方史编纂呢?这些问题,或许是研究者把它当作暂时性的副业来做吧?或者说不是为确保自己的调查地吗?关于这一点,我想大概不同的参与者也各有不同吧。不过,幸运的是,与福田先生有过两次左右共同调查的经历,在那两次经历中没有发生这样的问题,但是,在其他的地方还是会有发生这种问题的可能性。
如果让与地方史编纂事业涉及较深的福田先生概括一下的话,不只是自身的行为,包括其他人的所作所为,是如何的呢?我想,这是20世纪民俗学在一定程度上被社会认知的一个原动力。但是,我认为这也是20世纪民俗学所犯下的大错误。您认为呢?
福田:我认为,20世纪民俗学是学院派民俗学以自己的活动、获得发挥作用的场所这一形式开展了地方史编撰事业。所以,此前没有这样活动。与其说是1958年,不如说50年代几乎没有。在60年代的某一阶段,60年代结束的时候吧。到了70年代,这些活动更表面化了,简而言之,在地方史中,一个是确定了《民俗编》的地位,并开始登场。在此前,将《民俗编》纳入到市町村史或县史那样的想法从来没有过。
为什么《民俗编》加入地方史?
菅:那么,为什么在地方史中赋予了民俗的位置?背景呢?是文化厅的问题吗?
福田:当然有文化厅的调查,可能民俗调查或民俗资料的某些价值被认可或被认识,比这更大的理由,简而言之,我想是历史编纂方尝试比以往历史的编纂更具有丰富的内容的时候会把目光转向民俗这部分吧。在地方史中,我想几乎没有民俗学者参与整体的构想。换言之,是历史学者参与,或者邀请他们推敲框架结构。其中,这一点在那个地方也写过,东日本的地方史在较早的阶段就确定了民俗的位置。它是从60年代结束前后到70年代、80年代。不过,西日本并不是这样。西日本较晚才出现民俗编。这也是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
东京方面,或者,勉强来说,这一点,东京大学及其系列日本史等领域纳入了比较民俗。大体上,在县史的层面东京大学占据主导地位,但在市町史等方面并不是这样。在这些部分出现了民俗,由京都大学及其系列主导的地方几乎没有民俗出现。正是现今,例如,像在山口县史、鸟取县史等各个地方才增加了民俗内容,过去没有。存在这样的倾向。总之,我想,说地方史是民俗学被社会承认的呢还是什么呢?特别是作为学院派民俗学通过与其他各个学科齐头并进成为了深化民俗学存在被社会认知的契机。
我为什么积极地参与了那些活动,必须说一下此前的事情,在60年代的阶段,学院派民俗学仍然还是以比较研究为主。基本上,民俗学是通过重出立证法进行全国性的比较。最初,宫田登先生刚刚在大学任教的时候,在对学生的毕业指导中,说了“不进行比较也可以”这样的话。结果,其他大学的人感到非常吃惊的样子来和我说:“宫田先生竟然说那样话。”从60年代到70年代初,民俗学的研究仍然是做比较。所以,不通过比较的方法来写论文也可以之类的被认为是毫无道理的。这一阶段,在市町村史的编纂中逐渐出现了《民俗编》,我想,当时承担者们或许为了获得重出立证法这一比较研究所需要的信息或资料,利用了市町村史。但是他们脑子里并没有利用了这些资料的意识。如各位都了解的那样,在市町村史或县史中,很大的一部分是把《民俗编》置于《资料编》的位置。所以,与汇集在一起《资料编》的文书相同对待。这对民俗学者来说也是同一标准的。简而言之,我认为,因为是把进行全国比较的资料作为某某市史民俗资料编汇集,所以没有突出不同的部分。对此,我主张个别分析的方法,主张应该在地域中分别调查、分析,然后做出回答。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我对以前的市町村史编撰者进行了批判。如果要做的话,必须扎根于地域做出解答。如果是个别分析法,其目的或效果应该一致。总之,进行地域调查,以此分析做出解释,这或许也是民俗学的解答,在揭示地域人们的课题或指出问题这一点上有与地域史编纂的目的也一致那样的自信、那样的理解,在做民俗调查这一意义上参与了市町町村市或县史的编纂。
菅:《胜田市史》是开始的契机吗?
福田:胜田是开始。很长一段时间将其称为胜田方式,这也是,当然全部是由历史学者构成,这其中,当时,宫田登先生、平山和彦先生和我及当地的佐藤次男先生是专门委员吧。
菅:福田先生在那个时候还是研究生吧?
福田:像刚才提到的那样,如果说哪里创新的话,基本上,是编纂可理解市史。迄今为止称为资料编的内容仅是根据项目来排列调查数据。此后这些数据成为了某地某人为了做比较研究时所需的数据。如果说可理解是什么的话,是编纂包含相应的分析、解释、解说的市史。这些点作为目标,我现在仍认为这是非常创新的。不过,在编纂的过程中也是本着创新,虽然做问卷调查之类的看起来像没有价值,但还是实施了问卷调查。另外,在市史《民俗编》的正编出版前的中间阶段刊行了调查报告书。这些,在此后就成了自然。市史调查结束了,就刊行调查报告书,接着就出版正编的《民俗编》,这一过程就形成了规律化。这也是因为规律化,说是千篇一律吧,成了非常不好的形式,有这样的经历,此后一直参与了几册编纂,参与了很多。
作为权力关系要说的是,当然,因为我也了解1968年、69年和1970年,虽然以努力弱化那些问题的形式来开展工作,但是仍是存在各种各样的问题。本科学生,宫田先生貌似经常动员包括本科学生在内参与这些活动,不过因为我不是大学教师几乎没有组织过本科的学生参与。虽然这样讲,此后还是出现了很多从各个大学来的本科生,在这一点上,专门委员、调查员、还有临时参加调查的学生,这些群体关系存在非常大的问题的确是事实。现今来看也是有问题。
我不太愿意参与文化财的工作,接受了文化财审议委员是不得不的事情。虽然这个工作现在也在做,不太积极是因为文化财是固定民俗的工作。所以,无论是民俗事象的祭祀活动也好还是什么也好,是将其固定,站在不认可变化的立场,让我很难给予评定。我成为文化财审议委员的时候,我想也有觉得意外的人吧,我经常强调要把变化的东西或新的东西指定为文化财那样的主张,文化厅的人曾经说过:“欸?把那样的东西指定为文化财吗?”东京的文化财并不是我指定的,参与了世田谷旧货市场的文化财指定工作。有人说:“那样的东西怎能是文化财?”还有,如果说到横滨,在横滨的某住宅区,稻田什么都没有的地方,在此以住在区自治会为中心恢复了驱赶害虫的仪式。没有任何害虫,也没有稻田。但是,举行驱赶害虫的仪式。虽说是恢复,当然没有火把。在竹竿的一头绑上空罐儿,装入灯油用布条做灯捻,然后点燃在住宅区内巡游。参与了把其指定为横滨市文化财的工作。在这一点上,怎么也不想把文化财给予所谓的固定传统的东西、或者不认可变化的东西。说点多余的发言,无论是哪里的审议会都造成一些迷惑,与其相比,参与过的市町史可以与我的个别分析法的立场几乎不存在矛盾,以这样的方式进行调查、记录。
是否浪费公款了?有像你所说的这一方面。特别是高速成长期的地方史编纂有非常丰厚的资助,即使是我们研究生的活动,现在回想起来也是给予我们很高的资助。如果说它到底与成果是否相称,好像不相称吧。
菅:如果从全国范围来说,真的是上亿、数十亿,或许全国应该投入了约上百亿的资金。
福田:有可能是那样吧。
菅:是的吧,如果把县市町村史都算上的话。现今,这些市町村史是如何被利用的呢,也没有像这样的评价、检查,没有思考市町村史到底具有哪些意义。例如,今后,地方史的民俗报告书或民俗编这些东西,留下某一时代的历史这一事实毋庸置疑,但是它产生与其相应费用的效果是应有的行为了吗?
福田:如果说那种话便成了逃避,地方史不只是民俗编啊(笑)。地方史自身的存在也有必要反思。地方史编纂完全没有国家的补助金,基本上必须都是自筹资金编纂完成的,市町村也是,县也是。所以,如果以这种形式去实施的话,百分之百是使用了地方税金,如果这样追究的话,确实存在各种各样的问题。
对了,是熊本县阿苏的一宫町吧?一宫町出版了新书版①日本出版物的一种规格型号。比B6型号稍小一些,纵约173mm、横约106mm。——译者注的町史。虽然版面比较小,但是这样的想法是适当的。出版印制使用漂亮高级的布制装订、1000页左右的东西,用于装饰市长或议员接待室那样的东西,如果说有什么意义呢?即使说与个别分析方法相对应没有矛盾,但也没有被利用。
菅:会反省这一点。
福田:这个也反省(笑)。
菅:今后,我想这些地方史编纂运动几十年后还会在某些地方出现,不断反复。现今,当事者还健在,而且现今这些运动还在持续,所以这是一个难以接受的问题,我想这也是20世纪民俗学存在的一个很大的课题。对于这一问题的危惧意识在1990年代年轻的研究者中曾经非常高涨,我也从某一时期开始,决定即使有邀约也不参与了。实际上,我也参与了六个地方。
福田:参与了那么多吗?
菅:我最初是在大学二年级的时候参与的,是与福田先生一起的。我想你可能不记得了。我曾经也参与过那些地方史的编纂。大学二年级的时候。
福田:是吗?拿到打工钱了吗?
菅:打工的感觉,参与了市史的编纂。所以,如果从这些经验来说,我感觉让教育也停滞不前了,引发了某种伦理的大问题。我想这也是我们二十一世纪民俗学超越的一个对象。
那么,这个话题我们就暂且到此吧。最后是公共性的内容。然后进入实践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