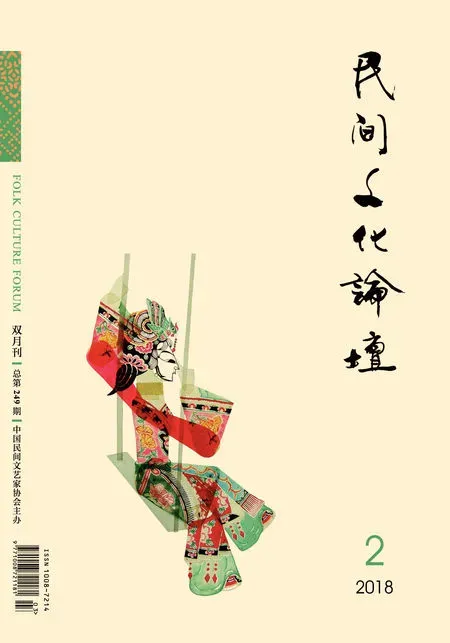壮族师公面具的叙事途径
——兼论壮族师公戏的影像化策略*
2018-01-23聂强
聂 强
壮族师公戏,指广西壮族师公在丧场、打斋和酬神还愿等活动中主持实施的过渡仪式。由于仪式过程伴有娱神和娱人的剧目演出,故也称师公舞、尸公戏。因壮族民间师公戏有“无相不成师”①相,面具的俗称,又称为木相、神面、鬼面壳等等。的说法,在仪式中扮演角色常常都需佩戴木质面具,所以师公戏也被称作木脸戏。师公戏②本文讨论的师公戏主要是指包含驱邪祈福、跳神祭祀、超度亡灵等内容的壮族师公傩仪,而非纯艺术的地方小戏;后文所称师公面具,亦指的是壮族师公开展傩仪时所佩戴的面具。源于傩,是学界较为一致的看法。也有学者认为,“尸”作为远古祭祀仪式的组成部分,在各种祭仪中都有出现,且其主要内容是“象神”表演(人扮演神祇受祭——笔者注),道具也正是面具,所以师公戏应是源于“尸”。③胡仲实:《广西傩戏(师公戏)起源形成与发展问题之我见》,《民族艺术》,1992年第2期。在历史演进的过程中,随着时间推移,远古诸多名目的祭祀仪式逐渐合并简化,至今仍然广泛活跃于民间的常见的有傩戏和社火,且现存的祭祀仪式又在流传的过程中不断经历时空洗礼,在自身不断变化的基础上再融合了其他巫术进行发展演化,因此把含有跳神祈福、禳灾祛邪、超度亡灵等丰富内容的完整的过渡仪式——师公戏归为傩戏,而不仅仅是远古祭祀仪式中的某一类角色,应更具说服力。
我国的面具史可追溯到史前,盛行应不晚于殷商。殷墟和陕西城固、洋县,以及西安老牛坡等地出土的面具已可充分证明。鉴于远古的巫术、祭祀等活动与面具的深厚渊源关系,大量文献记载殷商时期丰富的巫术与祭祀活动,也是有力的旁证。郭净认为面具的出现源于人们对头颅和幻面的崇拜,是一种基于宗教信仰的自我形象和心理的投射。④郭净:《中国面具文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32—56页。 幻面,郭净解释为“受到人们顶礼膜拜的面孔”,即人们出于对面孔形象的膜拜而把一切具有类似结构特征的形象当作面孔来阐释,这副存在于人们头脑里的面孔幻象即为幻面。从这个角度看,师公面具有同样的效应,它从远古傩面具发端,后在多元文化的碰撞中交融演进,在各种历史因素的影响下,最终形成了当下集雕刻技艺、角色扮演、法器功用于一体的当代师公面具,在师公戏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此前对师公面具的研究中,主要集中于梳理历史脉络、发掘文化内涵、探析艺术特征等方面;此外还有部分学者从角色的类型和在仪式中的功能等方面,对师公面具进行了多角度的探析。由此我们可以发现,在相关研究中,虽然对师公面具的历史、艺术、功能等方面进行了较为全面的探讨,但师公面具作为被展示的显圣物,它如何成为显圣物?如何被展示?作为被展示的显圣物又具有哪些属性?同时,师公面具作为被展示的显圣物,它在仪式内外通过什么途径来实现它的意指叙事?这些问题在此前的研究中并未获得注意。笔者带着这些问题走入田野,到实地去寻找答案。
一、被展示的显圣物
2016年7月,笔者有幸参加了华中师范大学、广西民族大学与美国崴涞大学共同举办的“第三期中美民俗影像记录田野工作坊暨《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二届博士生论坛”,到广西平果县凤梧乡上林村局六屯,对当地的壮族师公班及其班主韦锦利创办的壮族师公文化馆进行田野调查,获得了丰富的一手资料。
韦锦利,法名韦接印,生于1963年,男,壮族,高中文化,曾到福建泉州少林寺学武,祖传师公身份,1986年受戒正式成为师公。韦锦利不仅是当地师公班的班主,也是广西少数民族古籍普查工作普查员、壮族师公文化传承基地负责人、壮族师公文化馆馆长。他利用自己家里的房间创办的壮族师公文化馆,将师公面具为主的诸多师公文化载体进行布局陈列,对外展示。经过广泛搜集、精心整理,现在该馆藏有古壮字经书100多本,汉语译本经书2本,木质面具120多个,佛头(纸质面具)27张,音乐资料16种,舞蹈资料多种,还藏有100多年历史的师公服饰、法器多件。其中经书和面具的收藏最为突出。
该文化馆展示的师公面具中,只有两个具有上百年历史,其余大部分都是20世纪80年代后新制。新制师公面具一是根据师公传承讲述和故事传说来想象雕刻绘制,二是根据书籍画像和逐步普及的影视形象来雕刻绘制,甚至部分面具是根据小人书形象制作而成,因此也更具戏剧效果。师公面具一般都是师公制作,也不需要专门拜师,只要有参考样本,有基础手艺,即可制作。据韦锦利介绍,在丧场仪式中使用的一套完整的木质面具是19个,一般的丧场仪式中只需用15个,时间比较长的仪式则需要全套。而佛头在丧场仪式中一般要用26个。因此,一场完整的丧场仪式至少需要用41个面具,多则需要45个。
由此可以看出,师公面具在师公戏中占据着重要的位置,不仅在表象层面上实现角色扮演,而且还在表意层面上实现文化表达和身心过渡。小小一副面具,如何能够承载层次丰富、功能多样的文化内涵?因为师公戏中的面具在作为扮演角色的普通道具之外,还是一件联结神圣的显圣物。按照米尔恰·伊利亚德的观点,世俗的空间是均质的和中性的,而自古至今的人们,要么是宗教徒,要么是“宗教的人”,因为“不管一个人对这个世界的去圣化达到多大程度,他根据世俗生活所作出的选择都绝不可能使他真正彻底地摆脱宗教的行为”。①[罗马尼亚]米尔恰·伊利亚德著:《神圣与世俗》,王建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2年,第3页。师公戏作为神圣化的过渡仪式,经文唱诵、巫术行为以及最具表象功能的师公面具,正是构建神圣时空的手段和途径。无论任何宗教,或是具有宗教特质的民间信仰,其神圣化的行为都需要现实而具体的事物作为依凭,以实现神圣和世俗之间的沟通和联结,师公面具作为显圣物,是最直接和最具象的沟通媒介。
师公面具从普通的角色扮演道具变成师公法事的专门法器,具备联结神圣与世俗的功能,主要是因为它经过了以下三个方面的圣化:
一是师公开光赋予面具法力。面具(含木制面具和佛头)制作完成之后,必须由师公班资深的大师傅开光之后才具备法力,才能从普通的角色扮演道具变成拥有神通的师公面具。开光过程本身就是一场通神赋能仪式,由具有神圣法力的师公赋予面具神通法力,使其从普通现实物变成神圣的法器,从而具备联结世俗与神圣的功能。
二是扮演角色赋予面具法力。师公面具所呈现的角色都是世俗世界信仰的神仙,或者是由世俗之人在经历一系列圣化行为之后变成神仙,又或者是辞世之人以魂灵世界的再生形象被展示,这些神性角色的依附也使师公面具在角色扮演过程中得到法力加持,从世俗道具转化为神圣法器。
三是仪式特殊时空的神圣性。师公面具角色虽具神圣性,但在日常生活的语境中也可以进行世俗性叙事,要使其真正具备神圣性,还需要进行时空的转换。师公戏作为过渡仪式,主要用于驱邪、赎魂、酬神还愿等活动,从活动准备直至活动结束,所有的行为都是在神圣的时间机制内运行,而与仪式相关的场域,则被转化为神圣空间,在这个神圣时空的语境里,面具的神圣特质被激发到极致状态,成为最直接也最具表现力的通神法器。
面具与角色本身就具有象征意义,经过开光之后,就在普通象征意义之上进一步被赋予了神圣的象征意涵,再加上神圣时空的转换,使师公面具成为均质性的世俗世界与异质性的神圣世界对话的媒介。在仪式的既定话语体系中,如果应该使用面具的环节缺少面具这件具有通神功能的法器,就无法中断与世俗生活的联系,切断了与神圣的沟通,难以进入异质的神圣世界。在仪式过程中,师公的世俗身份以及面具的世俗属性被暂时悬置,面具在师公的操演下与其他法器、经文等等共同构建了一个具有神圣属性的异质世界,在这个异质世界的时空里,仪式参与者所得到的是区别于世俗生活的神圣体验。在师公主持的过渡仪式中,面具象征着神圣,是能与世俗世界形成区隔却又现实而具象的显圣物。
只要师公面具通过了开光仪式,就完成了它从普通道具到显圣物的过渡,从师公文化馆的展览架,到仪式中神圣演绎,无论它在与师公关联的哪个时空出现,均是象征着神圣的法器,只是由于时间节点和空间场域的区别而展示着不同的功能倾向。从根本上讲,师公面具作为具有表象和表意功能的显圣物,如果我们承认它具有文化功能和文化意义,那么它天然地就是一种被展示的文化。在师公文化馆的展览架上,师公面具静默以待,迎接亲临现场的参观者(主要是师公文化研究者和爱好者);同时作为静置的师公文化象征,还间接地受到知晓此事的当地民众的精神信仰(他们未必会亲临现场参观,但他们知道它的存在,并认可它象征的文化意义和信仰内涵)。在师公主持的过渡仪式中,师公面具同样是一种被展示的文化,展示的对象主要是参与仪式的群体。文化馆的展览更倾向于展示其现实的世俗的文化功能,仪式中则更倾向于展示其超现实的神圣的过渡功能,通过展示神圣的象征意涵,构建起神圣的异质世界,帮助参与仪式的群体从世俗——神圣——世俗的时空转换中完成过渡,同时也实现它更具深刻内涵的表意功能。
作为被展示的显圣物,在并置其世俗特质时,师公面具通过不同时空的展示,必然地具备了“文化展示的双重属性”①[英]贝拉·迪克斯著:《被展示的文化——当代“可参观性”的生产》,冯悦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14页。,在展示文化并帮助参观者和参与者完成神圣体验的同时,也使这种文化得以传承,即是具备了展示师公文化和传承师公文化的双重属性(双重功能)。师公面具通过在文化馆和仪式中的展示,分别呈现了面具角色的人物内涵、过渡仪式的功能内涵和师公文化的信仰内涵。从这些文化意义的完整获得,我们可以看出,师公面具本身也具有双重属性,即师公面具既是现实之物,又是神圣之物,它是神圣显现于世俗世界的征兆,又在世俗世界里构建起一个异质的神圣世界。结合米尔恰·伊利亚德关于神圣与世俗的看法,我们可以这样认为,在师公戏的仪式过程中,宗教的人(非宗教徒)通过师公面具及其他法器共同构建的神圣世界,在一定的时间阈限和空间场域内,获得了类似于宗教的异质的神圣体验,使原本均质性的世俗生活具有了不同层次的意义。换言之,在师公戏中,师公面具构建的神圣世界使参与者获得异质性的神圣体验,为混沌的世俗生活增加了浪漫的属性。
从以上可以得知,师公面具是一种被展示的显圣物,它具有现实性和神圣性,同时还具备展示师公文化和传承师公文化的双重属性。同时,作为被展示的显圣物,师公面具蕴涵着丰富的文化内涵。那么一个不得不面对的更为严肃和深刻的问题就呈现在我们面前:师公面具究竟通过什么途径来实现其意指叙事,即它在师公戏中的意义内涵如何得以实现?
二、师公面具的叙事途径
壮族师公的主要职能是为一方之民禳灾祈福,维护他们的安全与兴旺,具体表现为赎魂保命、驱鬼祛灾、架桥求花、酬神还愿等。①杨树喆:《师公·仪式·信仰》,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17、19、20、22页。无论是驱邪祈福、酬神还愿还是超度亡灵,任何一场师公戏都是一场严谨的过渡仪式。通过分隔、边缘和聚合三个阶段,使需要过渡的个人和群体经历分隔期、边缘期和融合期,最终实现生理和心理的过渡,回归平静的日常生活。师公面具作为显圣物,是师公戏的重要法器,在过渡仪式内外,它将与自体、师公、角色、经文唱本以及观众反馈等产生互动,通过互动建立起相互沟通和支撑的关系,并意图通过这种互动关系实现意指叙事。如此来看,要深入地认识师公面具在师公戏中的叙事途径,我们必须先理清以下几组关系:
1.师公面具与自体的双向关系
“民俗美术只是文以载道的教化文化中间一种可供直观的艺术现象。”②李辛儒:《民俗美术与儒学文化》,北京: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92年,第124页。师公面具正是这样一种民俗美术作品。如果除去师公面具被赋予的文化内涵及其功能,隐去其神圣性,那么它只是用木头雕刻或纸质绘画而成的一件物品,拥有的只是材质属性、轮廓形状、颜色集成等原始形态。当被赋予美术意义的时候,则有了雕刻技艺、色彩搭配、造型艺术内涵。当被赋予角色意义时,则有了角色形象气质、故事传说、道德象征等等文化内涵;当被赋予师公法器功能时,则又有了与神祇关联的内容,如形象、传说、法力等等。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师公面具作为一件物品本身,它并没有丰富内涵意指,但在此同时,它也提供了广阔的意指空间,即当它未被定义的同时也拥有了广阔的义项选择空间,一旦它被赋予某个角色,就拥有了角色所蕴含的文化义项;在被开光注入法力之后,则进一步被添置了神圣属性,具备了作为法器的功能。因此,面具本身具备了一种未定义和拥有多种义项可能的双向关系。
面具自身的双向关系还有一种类型我们也应注意,即当面具选定一种义项为自己定义之时,一般情况下,它就放弃了对其他义项进行二次选择的机会,也在此同时,它又从这种放弃中获得了自己的个性。从义项的选择上,它是非此即彼的,但是在放弃更多可能与获得自己个性这两者之间是一种双向互动的关系,它们共同构成了师公面具的意指空间。
2.师公面具与师公的双向关系
师公面具一般都是由师公制作,同时师公面具又需师公大师傅开光赋予法力才能成为法器。师公是师公面具的制作者、使用者、法力授予者。在过渡仪式中,师公通过佩戴面具演绎神祇角色,获得非物质的利益,如身份、名誉、地位等;在祭祀仪式结束后,师公一般还会获得物质收益。师公通过师公面具获得了物质和精神的双重利益,但同时又受到面具的规制。首先是制作上的规制,面具制作必须遵循基本规则,选材要符合面具雕刻、使用和保存的需要,雕刻要符合角色和演出的需要,演出要符合角色形象气质的需要,同时角色的形象动作要符合经文及仪式功能的需要。此外,佩戴面具时还需受到规制,戴木质面具之前要用毛巾裹头,包住面具遮挡之外的头部裸露皮肤,如脸颊后部、耳朵、额头等等部位,一是为遮挡凡人俗脸,增加所演绎角色的神性;二是避免在佩戴演绎过程中磨伤面部。
由此可知,师公面具由师公制作并授予法力,反过来师公面具又在仪式中赋予师公神性和权力,即师公面具的神圣属性源于师公,同时又赋予师公以神圣特质,在仪式中与师公共同构建神圣世界,完成过渡目标。师公面具与师公正是在这种双向关系中相互证明了彼此的合法性。
3.师公面具与角色的双向关系
师公面具与角色之间存在着一种互相定义的关系。师公面具制作完成,基本就已确定了角色。在此之前,角色的设定,也基本规定了面具的制作形式。另外,在过渡仪式中,角色出场次序的安排就决定了面具的选择,而面具的选定也同时确定了角色。再进一步,当一个师公面具被赋予某个特定的角色身份,该面具则同时被赋予了角色所蕴含的文化意指;反之亦然,当一个面具代表某一角色在仪式中出现,在该面具也同时展示了扮演角色的文化内涵。如四帅中的关公面具,当他被赋予关公角色时,制作则多是浓眉大眼、一脸正气、红脸长髯,其内涵也必然是一个功夫高强的武神,具有带兵驱邪和看护法场之功能;反之,当仪式参与者看到头戴关公面具的师公出场,关公的形象、内涵和功能也通过面具得到对应的展示。在这个互动中,面具是角色的内涵承载体,也是其文化的展示体;角色为面具的内涵赋义,同时其内涵又是在面具中寄存。简而言之,师公面具与角色具有双向定义关系,面具被角色定义和规范,同时面具也相应地规定和展示角色内涵。
需说明的是,角色对面具进行内涵赋予和寄存,少不了经文唱本的参与。师公面具作为具有时空和内容规定功能的特殊法器,并不是将角色的所有文化内涵均收纳其中,而是根据师公戏的仪程和目的需要,经过斟酌筛选,只选取必要的内容编成经文进行唱诵演绎。因此在师公面具与角色的双向关系中,经文唱本作为角色内涵的依托载体之一必然会并置其中。
4.师公面具与观众的双向关系
荣格认为:“象征是某种隐秘的,但却是人所共知之物的外部特征。象征的意义在于:试图用类推法阐明仍隐藏于人所不知的领域,以及正在形成领域之中的现象。”①转引自左汉中:《中国民间美术造型》,长沙:湖南美术出版社,1992年,第217页。师公戏作为一种过渡仪式,在集体性的仪式中,主要是群体的过渡;在丧场仪式中,则既有亡者个体的过渡也有生者群体的过渡。无论在何种过渡仪式中,面具作为一种象征,除了对角色的象征之外,还拥有更为深层的象征意涵,如仪式的文化意义、异质的神圣世界、群体的信仰属性等等。但无论面具的象征意涵如何丰富,它都与仪式参与者——观众(仪式主持者——师公之外的所有参与者均是观众,笔者注)之间都存在着一种互动关系,离开了互动则失去存在意义。在师公戏的仪式过程中,正是参与群体的过渡诉求赋予了师公面具存在的价值,而师公面具也在娱神和娱人的剧目中,通过象征性的表达演绎,帮助观众实现过渡的目的。因此,师公面具在过渡仪式中的价值认可诉求与仪式观众的过渡诉求间形成了一种互为支撑的双向关系。
5. 师公面具与时空的双向关系
师公面具意指在过渡仪式之中实现的关键时空节点,因此我们主要探讨的仍然是师公戏仪程的神圣时空与师公面具的关系。在仪式现场,师公面具的演绎与在场,显示了当下时间和空间上的特殊性。面具赋予仪式当下的时空以神圣性,使参与仪式的生者与亡者进入到过渡仪式的仪程之中,获得超越世俗生活的神圣体验。当然,面具在场与演绎的时空并不是随意置之,而是要遵守相应的规则,如族群驱邪祈福、家庭酬神还愿、亡者灵魂超度等时刻及相应场域,才是师公面具实现意指叙事最佳的合法时空,如若师公面具与它的叙事时空不相对应,则不能完整、合法地实现其意指叙事;如在师公文化馆,虽然师公面具仍然可以展示师公文化,但参观者并不能获得过渡仪式的真实的神圣体验;又如,即使是经过师公开光的师公面具,被单独置于世俗空间,从现实中切断它与师公之间的联结,那么它的神圣意涵也可能被悬置,而转化为一个普通的现实之物,不再具备神圣意义。所以,师公面具与时空之间存在着一种彼此对应的双向关系,只有在此关系中,双方才能实现内涵意指的互生共存。
6.仪式中有无面具的双向关系
在师公祭仪中,并不是所有的环节、所有的师公都需佩戴面具,师公面具主要是在配合唱诵经文进行剧目演出的时候才使用,旨在证明剧目演绎行为的合法性及神圣性,在师公的演绎下构建起神圣世界,同时也增强师公法事行为的法力。那么是否未佩戴面具的仪式过程对佩戴面具的仪式过程不形成意义支撑呢?列维-斯特劳斯在研究北美洲太平洋沿岸各民族的神话与面具关系时指出“……面具跟神话一样,无法就事论事,或者单从作为独立事物的面具本身得到解释。从语义的角度来看,只有放入各种变异的组合体当中,一个神话才能获得意义,面具也是同样的道理……归根结底,每个面具类型的基础神话之间存在的转换关系和仅在造型上支配着各种面具本身的转换关系,其性质实际上是相同的。”①[法]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著:《面具之道》,张祖健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11—12页。在此,我们可以借此模式来理解,但稍微转换一下思维,将仪式中戴面具和不戴面具的环节并置,我们可以看出,它们对于仪式本身的意义是一样的,即佩戴面具开展仪式活动的部分对于整个仪式的意义,与不戴面具开展仪式活动的部分对于整个仪式的意义,两者在实质上是相同的,也互为彼此的合法性证明。再转换一下,对于整个过渡仪式来说,佩戴面具和不戴面具是一种结构性的依存和印证关系,两者在仪式中相互支撑,共同构成了完整的过渡过程,实现过渡目的。
在理清以上几对基本关系之后,我们再看师公面具在师公戏中的叙事途径,则可以明晰一个事实:师公面具通过与其自体、师公、角色、时空、观众的在场与反馈、有无面具的仪式过程等模块的有机组合,结构性地完成了它作为一件重要法器在整个过渡仪式活动中的意指叙事。然而在此我们需要更进一步地说明,师公面具的意指叙事绝非仅在师公戏的内部即可完成。范热内普在讨论主动礼仪和被动礼仪的关系时认为:“一个禁忌(即被动礼仪——笔者注)不能自成体系;它必须与某主动礼仪相辅相生。换言之,每一被动礼仪,如单独考虑,皆有其个体性,但总体而言,禁忌只有与‘主动’礼仪相互对立地共存于一个礼仪中才可被理解。”①[法]阿诺尔德·范热内普著:《过渡礼仪》,张举文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年,第12页。列维-斯特劳斯在讨论面具时的观点与之形成呼应,他认为:“跟语言一样,每一副面具本身并不具备全部意指。意指既来自于被选用的义项本身的意义,也来自于被这一取舍所排除的所有可能替换它的其它义项的意义。”②[法]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著:《面具之道》,张祖健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45—46页。即面具完整的意指应是通过一个相对完整的结构来获得,而不是从其单方面所肯定或者否定的内容来获得。师公面具的意指叙事亦是如此。
当我们把目光转向师公戏之外就会发现,正是日常生活的世俗界域,对立性地构建了师公戏的神圣时空,而师公面具则是这个过程中的关键元素。“某家或部落内的个体是生活在世俗界域;当开始一次征程并发现身处陌生地域时,他便进入神圣界域。”③[法]阿诺尔德·范热内普著:《过渡礼仪》,张举文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年,第15页。正是作为过渡仪式的师公戏现场呈现出来与世俗界域相对的异质性,才让仪式的参与者得到净化,进入神圣界域,获得神圣体验,并对师公面具所扮演的神祇做出相应的反馈,帮助实现仪式的娱神和娱人目的,并在仪式参与过程中实现亡者和生者的过渡——亡者超度升天,生者再聚合到世俗界域,回归到日常生活群体。当然,师公面具作为一种蕴涵壮族群体信仰观念的文化符号,其丰富的内涵还可以通过与其他地区的壮族群体以及其他族群的比较来进行更广阔空间的结构性解析,这不在本文探讨范围之内。
三、师公戏的影像化策略
当前,韦锦利师公班的师公活动已经被列入平果县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作为一个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民俗项目,在当下这个视觉文化盛行的影像时代,如何通过影像化方法实现立体多维的档案记录和文化传承,是我们应该思考并实践的一项课题。孙正国认为:“民俗是日常生活里多维度的现象世界,最适合用影像去表达,也只有影像才能把这种时间流的空间形态给记录下来。”④熊迅:《民俗影像的操作化与可能性——中美民俗影像记录田野工作坊三人谈》,《民族艺术》,2016年第4期。邓启耀也认为:“从认识发生的角度看,人的思维,是从具象逐步向抽象发展和转化的;人类的文化符号,也是从具象逐步向抽象发展和转化的。”⑤邓启耀:《视觉表达与图像叙事》,《广西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1期。既要使其能具象地回到民俗实践本身,又能让人在这影像化的生活时空里对“多维度的现象世界”进行抽象化的理论研究,这就不得不在师公戏的影像化记录过程中进行策略选择,以期符合影像民俗学的要求。
我们以影像化的思维对师公戏进行全面梳理即可明白,人是活动主体,仪式是核心内容,完成过渡是仪式目的,如何把这些元素有机地组合在一起,实现影像的可视性、民俗的完整性以及内容的科学性,就是最根本的问题。回顾上文的分析可发现,师公面具的结构性叙事特点为师公戏的影像化提供了解题的密钥。
构成师公面具的各个单独的物象不能阐释面具的整体内涵,色彩、造型、角色等等都不能形成完整的面具内涵意指。同理,单个面具也无法形成其在过渡仪式中的完整意指,它需要与其他面具配合,形成一个意象群体来完成意指叙事。此外,师公面具还需要与佩戴主体、时间空间、经文唱本、剧情演绎等进行密切而生动的互动,才能形成师公戏的完整语义场,实现它在师公戏中的完整意义。最后,师公面具还需进一步将师公戏与日常生活联结成对应的结构性语义空间,在异质的神圣世界与均质世俗世界的对比考察之下,最终实现其在师公戏内外多维语境中的意指叙事,即构建师公面具在一个族群内部的完整意义空间。
综上所述,在对师公戏进行影像记录时,将师公面具作为师公戏影像化表达的核心意象,以其结构性的关系脉络为叙事之纲,抓住面具本身及其表演的可视性特征,将其置于日常生活的语境中,挖掘人、物、仪式三者之间的深层关系,最终呈现出师公戏的过渡功能及其对于当地壮族群体深刻的文化意义。当然,“既然民俗影视的目的是记录民俗活动,其记录的方法应是尽可能完整地反映局内人的声音和活动。”①张举文:《迈向民俗学的影视与民俗研究》,《民俗研究》,2007年第1期。这也是师公戏影像化过程中需要注意的问题,因此对师公戏的考察不仅要重点关注参与者,还要留心关注旁观者,内外结合考察,方得意指完整。
理解世俗界域可以更好地认识师公戏——“某家或部落内的个体是生活在世俗界域;当开始一次征程并发现身处陌生地域时,他便进入神圣界域”。②[法]阿诺尔德·范热内普:《过渡礼仪》,张举文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年,第15页。正是作为过渡仪式的师公戏现场呈现出来与世俗界域相对的异质性,才让仪式的参与者得到净化,进入神圣界域,获得神圣体验,并对师公面具所扮演的神祇做出相应的反馈,帮助实现仪式的娱神和娱人目的,并在仪式参与过程中实现亡者和生者的过渡——亡者超度升天,生者再聚合到世俗界域,回归到日常生活群体。当然,师公面具作为一种蕴涵壮族群体信仰观念的文化符号,其丰富的内涵还可以通过与其他地区的壮族群体以及其他族群的比较来进行更广阔空间的结构性解析,这不在本文探讨范围之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