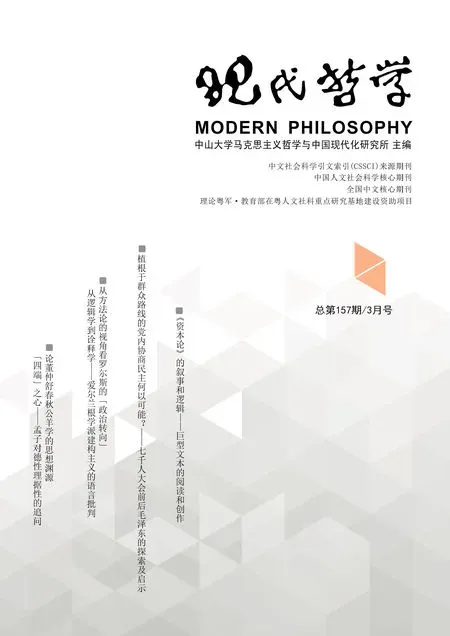周敦颐“立人极”思想的三个面向*
2018-01-23李旭然
李旭然
在《太极图说》中,周敦颐构建了一个贯通天、地、人及万物的宇宙论体系,人在其中占有特殊地位。圣人又是人之极致者,其实现了人性的全部而能“与天地参”,所以成为圣人便是“立人极”。“立人极”的圣人,因为“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故关乎天地万物,需从体上说明“人极”何以能立。“人极”非可躐等而至,必从人伦日用中辨析其精义,则如何从现实着手处用力,需从方法上加以说明。此外,“立人极”又因乐在其中,故虽受艰难困苦亦不改平生志业,则又有“立人极”之乐。鉴于此,本文拟从体、方、乐三方面对周敦颐“立人极”的思想加以分析,说明其特色。
一、“立人极”之体
周敦颐在《太极图说》中提出:“惟人也,得其秀而最灵。形既生矣,神发知矣,五性感动,而善恶分,万事出矣。”*②③④ [宋]周敦颐:《周敦颐集》,陈克明点校,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第6页,第6页,第32页,第4—5页。人在阴阳五行的演化过程中,是有善恶之分的,人的善恶之分却只是相对的,“圣人定之以中正仁义,而主静,立人极焉”②。在人而言,虽有善恶之分,又有中正仁义之极,能如此者即是圣人。之所以称圣人为“立人极”者,是因为在《太极图》描述的天地万物演化过程中,无极而太极贯通了一切事物,一旦能知晓这点,便是通透于无极而太极,这样的人便是人之中最出类拔萃的圣人。这一观点也出现在《通书》中:
厥彰厥微,匪灵弗莹。刚善刚恶,柔亦如之,中焉止矣。二气五行,化生万物。五殊二实,二本则一。是万为一,一实万分。万一各正,小大有定。③
这种说法的意义,等同于《太极图说》的“阳变阴合,而生水、火、木、金、土。五气顺布,四时行焉。五行,一阴阳也;阴阳,一太极也;太极,本无极也”④。既然要立中正仁义的“人极”,就不能停留在具体事物。万物的根本是贯通的,人与万物虽然“万一各正,小大有定”,却必须“是万为一”,“立人极”就要符合此根本之“一”,这个“一”便是道、无极而太极,“中”的目标就是道。
以善恶之分系于阴阳五行,且贯穿万物的化生过程之中,表面近似于重视阴阳五行的汉儒思想,然而,对比汉儒之代表董仲舒的相关思想,便知其不然。董仲舒认为,“吾以心之名,得人之诚。人之诚,有贪有仁。仁贪之气,两在于身”*②③ [清]苏舆:《春秋繁露义证》,钟哲点校,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第294页,第296页,第345页。。人的身体中,阴阳二气同时并存,从宇宙论讲,这是万物生成的必然结果:“身之名,取诸天。天两有阴阳之施,身亦两有贪仁之性。天有阴阳禁,身有情欲栣,与天道一也。”②在周敦颐看来,“人极”既然定之以中正仁义,人所通极的天道必然也是中正仁义的,周敦颐所说的人之“中”者,其实就是天人合一。此外,董仲舒认为“天之常道,相反之物也,不得两起,故谓之一。一而不二者,天之行也。阴与阳,相反之物也……并行而不同路,交会而各代理,此其文与!”③这是说阴阳是绝对分开的,阴阳不能调和,人性非善即恶*冯友兰认为:“董仲舒以为若性中有善端,则不能谓之为善。”(参见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下册,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20页。)。周敦颐却认为阴阳既然是一本,阴阳必然是并行而不悖,人性就不能只是非善即恶,而是要与天道之全体相一致。阴阳是天道化生万物的环节和具体显现,天道却不只是阴阳,而是无所不覆、超越了善恶之分、作为善恶的根源的全体,“立人极”的“中”也应如此。否则,圣人之性只能偏执于善恶之一端,无法遍及所有人,如此之善与恶,只是个别的、具体的、脱离了天道的全体,“立人极”也就无从说起。
人生而受到阴阳的气禀限制,偏阴者柔,偏阳者刚,必然与天道之“中”不相符合,在行事时,也就不能“和”于事。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周敦颐提出“君子慎动”的主张:“动而正,曰道。用而和,曰德。匪仁,匪义,匪礼,匪智,匪信,悉邪矣。邪动,辱也;甚焉,害也。故君子慎动。”*⑥⑦⑧ [宋]周敦颐:《周敦颐集》,陈克明点校,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第18页,第16页,第18页,第15页。
《礼记·中庸》认为:“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可离非道也。”这说明人在行动中所依据的道,应时刻与天地之道保持一致。《中庸》又认为保持与天道的一致性是慎独的依据,而后才能致中和。中和的方法,在周敦颐看来,即“德:爱曰仁,宜曰义,理曰礼,通曰智,守曰信”⑥。朱熹认为“所谓道者,五常而已。非此,则其动也邪矣。”⑦将道德修养与天道联系起来,诚就是道德修养而已,“诚,五常之本,百行之源也。”⑧在《通书》中,周敦颐将《中庸》的天道之诚与《易传》的乾元结合起来*此为学界公论,如《宋明理学史》认为《通书》“不是一部单纯的易学著作,渗透了思孟学派关于‘诚’的说教”;卢雪昆指出,周敦颐是“以诚体合释天道”、“太极之道即《中庸》诚道”。(参见侯外庐等主编:《宋明理学史》,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66页;卢雪昆:《儒家的心性学与道德形上学》,台北:文津出版社,1991年,第161—165页。),阴阳五行也就被诚统一起来。他以诚为圣人之本,仁义礼智性的根源是诚,所以,圣人是中于仁义礼智信、中于诚的。凡人不能生来如此,就必须努力使自己中于诚,具体地说就是要中于仁义礼智信的道德规范,便是自诚,也是力图成为圣人而通极于天地,就是“立人极”。由此,周敦颐通过宇宙论的途径,衍生出圣人的道德属性,就是圣人之所以能“立人极”之体。
为进一步说明圣人何以“中”,周敦颐又对善恶进行细分,认为有刚善、刚恶、柔善、柔恶,其来源是《尚书·洪范》中“一曰正直,二曰刚克,三曰柔克”的“三德”说。孔颖达认为:“此三德者,人君之德,张弛有三也。一曰正直,言能正人之曲使直。二曰刚克,言刚强而能立事。三曰柔克,言柔和而能治。”*[汉]孔安国传、[唐]孔颖达正义:《尚书正义》卷十一,黄怀信整理,上海: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第466页,第459页。《洪范》中的“三德”,在“九畴”的顺序上位列第六,次于第五的“皇极”。其内容是:“皇建其有极,敛时五福,用敷锡厥庶民。惟时厥庶民于汝极,锡汝保极。凡厥庶民,无有淫朋,人无有比德,惟皇作极。”注疏者解之为,“君上有五福之教,众民于君取中,与君以安中之善”,“民有安中之善,则无朋党之恶、比周之德,为天下皆大为中正”。“三德”本来指的是人君的道德,正直、刚克、柔克是为了使人能“安中之善”,“皇极”就是所有人都要遵从的“中”。“中”不仅是人君应有的德性,也是天下所有人都共有的,为人者必定要得“中”,则“中”不仅有政治意义,更具有道德修养意义。这就与《中庸》的“中”产生关联。
《中庸》的“中”贯通了天、地、人:“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中庸》之“中”,已经被证明是合上下、内外为一*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册,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277页。,“中”于善恶就是“致中和”的表现之一。孔子很重视“中”,评价子张与子夏的过与不及,就是认为他们都不能“中”*孔安国解之为“俱不得中”。(参见[魏]何晏集解、[梁]皇侃义疏:《论语集解义疏》卷第六,沈抱秋、谢雨东校对,上海:上海商务印书馆,1937年,第151页。)。周敦颐提出“中正仁义”的人极,就是要求落实到个人的道德修养,人性能“中”于作为善恶之本源的天道,无过与不及,“惟中也者,和也,中节也,天下之达道也,圣人之事也。”*[宋]周敦颐:《周敦颐集》,陈克明点校,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第20页。圣人即是人极,但是,在现实中“人极”并未在所有人身上确立,因而这以圣人作为范本,可以教化凡人,凡人也可以向圣人学习而“立人极”,使人自我实现、自我成就,以圣人为目标而不断地努力前进,这是“立人极”的现实意义所在。
二、“立人极”之方
为说明“立人极”如何由天道为依据、又能在现实中显发,周敦颐借用并发挥了《中庸》“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的理论。他从具体的人出发,抽绎出人之所以为人者在于“形既生矣,神发知矣,五性感动,而善恶分,万事出矣”*同上,第6页。。其立论之基在于人有知,故人能从万物中脱颖而出。人之知在于知善知恶,先秦儒家就已认可。例如,孟子认为人有心思之知,故能集义为人;荀子认为人有知、有义、有节,故不与禽兽同;《礼记·礼运》更是直接提出“人者,其天地之德,阴阳之和,鬼神之会,五行之秀气也”、“人者,天地之心也,五行之端也”。在周敦颐这里,天地的运行因无极而太极的阴阳五行之动静更迭而生生不息,人因此是生生不息的,人的可贵之处在于人通过知而把握了这种生生不息的变化。这种人心不是指具体的一人之心,而是体知了诚的心,即周敦颐所说的圣人之心。否则,局限于一人之心,不能识自身之诚与天地之诚的一致性,便不能通极于天地,也就不能“立人极”。“立人极”之体,即是与天地融为一体,是周敦颐对天人合一概念的拓展。在确立这一目标之后,就需要从方法论的角度加以阐释,由此引出“立人极”之方的问题。
天道即诚,故圣人“立人极”乃是达于诚,凡人只得刚柔善恶之一部分,从总体上来说,是不诚的。抽象的人性需要通过人的活动来体现,心是人的活动主宰,周敦颐的修身工夫落实于人,以使人性能自立其“极”,最终符合天地之“极”。
圣人立人极,中正仁义无不具备,《太极图说》将这种状况描述为“圣人定之以中正仁义,而主静,立人极焉”*同上,第6页。。因为诚者自成,万物与万物之理森然俱陈,故圣人不动而为静。其实,《太极图》与《太极图说》已经阐明静极复动的道理,圣人之静而不动也是动极而静,动静统一于圣人,圣人就能够以诚为根据而通天地万物。人生而有气禀之不均,从人自身着手,也就是从人的阴阳动静之中寻求人之所以为人的根本,通过人的自身努力而入于真实无妄的天道,人道与天道合而为一,以诚来贯通始终、体用、本末、上下。这种状态就是在《通书》所说的万事万物统统归结为圣人之诚,也是对《中庸》“至诚无息……如此者,不见而章,不动而变,无为而成”的发挥。
诚贯通终始,万物却是阴阳五行化生而成,易使人觉得万物不能连贯,于是,周敦颐以诚、神、几的贯通,来说明万物为一的特性:“寂然不动者,诚也;感而遂通者,神也;动而未形、有无之间者,几也。”*同上,第17页。处于诚之神妙不测中,或动或静,或阴或阳,此即是几。于是,诚、神、几各有功用上的区别,却又合而为一。这种区分和合一,并非普通人所能理解。周敦颐认为只有圣人方能知晓,故提出“诚、神、几,曰圣人”*[宋]周敦颐:《周敦颐集》,陈克明点校,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第18页。。圣人是儒家理想中的完备之人,被周敦颐看作是能贯通诚、神、几的人。从至诚之天道中,生成了人与万物,却唯有人得天地之灵秀;圣人又是其中最为出类拔萃者,能领悟天地的神妙,并能参透其中的难测之几。在周敦颐看来,人性中已经先天地具有诚、神、几,圣凡之分在于能否自我发掘和自我实现。
由诚之天道而生成的世界是生生不息的,即所谓“天地之大德曰生”(《系辞下》)。周敦颐发挥了这种理论,认为:
天以阳生万物,以阴成万物。生,仁也;成,义也。故圣人在上,以仁育万物,以义正万民。天道行而万物顺,圣德修而万民化。大顺大化,不见其迹,莫知其然之谓神。故天下之众,本在一人。道岂远乎哉!术岂多乎哉!*同上,第23—24页。
随着万物生成,每一物都有其自身的作用和意义,周敦颐称之为“义”。万物各自之“义”,构成了总体的天地万物的生生不息之“仁”,仁义虽有区分,根本上却是一致的,它们的关系等同于作为天、地、人根本的诚与万物中的诚的关系。把握仁义,与把握诚一样,只能由人来完成。人是天地之间最灵秀者,圣人又是人中最灵秀的,圣人通过思而通极于诚,“思曰睿,睿作圣”。圣人体会诚、无极而太极,就能够顺着《太极图》与《太极图说》中展示的万物化生路径,把握诚是如何通过万物的化生而进入到万物之中的。其中也包括人,圣人把握了人之诚,就能够用诚来教化民众,使之顺从于诚的天地化生,这样人的所作所为都是诚的,仁义即在其中。如此,诚为天、地、人之本,圣人也就成了人之本,圣人即诚。所以说,圣人作为人极而参与天地化育,是通过教化来完成的。
通过教化可教人以廉耻,能促使人复归于诚。这是一个思想逐步扩大的过程:由一个人的思想推及所有人的思想——因为人性已被预设为诚的,是以有人与人之间可以相互推及的基础——再推及于天地之思。但是,天地并不思考,只有人在思考,思考天、地、人究竟为何,以人之思来代替天地之思。天、地、人皆诚,人之思诚,即是思天地之诚,因为人的思考,天、地、人也就诚而为一。思及天地,天地之间无不因诚而思,思想即由于诚而无所不通、无所不至,人就能够通过思诚来发掘人性,达到至诚的圣人境界。圣人是合诚、神、几于一身,在思诚时,也要慎于几,体会所谓神的不测,使诚能落入实处,把诚仅仅当作头脑中空悬的抽象本体,不能达到教化的目的。将诚同时贯通于天、地、人中,与具体的思诚、使人自诚的行动结合起来,即是体用合一的道路*牟宗三却认为周敦颐未能彻底实现体用合一,“濂溪是天道诚体与仁义中正分别平说……两者犹有间而未能一”。(参见牟宗三:《心体与性体》上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第266—267页。)。
《中庸》有“诚之者,择善而固执之者也”之语,圣人之道是诚,成为圣人的途径也在于诚。人的反身而诚,就是使人自诚以至于圣人。反身而诚不是盲目的,诚既然是根本之性,本身即是明,所以诚是静。然而,孔子也自称“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论语·述而》),这意味着没有人是生而即知的,也没有人是生而即诚的,人需要以动的方式去把握诚,要求自明诚,就是以学的方式完成。《中庸》本身即是将诚与学结合起来的,人从出于天,故天道与人道应是一致的,学习如何为人之道就是学诚。天道之诚是要通过人自身的努力才能实现,这就是人的自明诚的意义所在。自明诚的具体路径,就是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这五者就是诚之之道,所以要“固执之”*朱熹认为:“此诚之之目也。学、问、思、辨,所以择善而为知,学而知也,笃行,所以固执而为仁,利而行也。程子曰:‘五者废其一,非学也。’”([宋]朱熹撰:《四书章句集注》,北京:中华书局,2005年,第31页。)。以明而诚之动,至于诚而明之静,自诚明与自明诚之天人合一,也就是动静合一。五者中,学是第一位的,由博学开始,才能有审问、慎思、明辨、笃行的渐次展开,则反身而诚以至于诚的动静相即,关键就在明了所以诚者为何物,而后能以此明了何以能诚之道。
圣人学道而与道为一,圣人就随道通达于万物而又不滞于行迹,普通人不能明道,也就不能理解圣人。圣人之学为己,故他人不知,丝毫不减损于圣人的内蕴。圣人所以学者,在于诚,圣人是人,学诚并自诚,能成圣人,如果这种路径为他人所知,并且能身体力行,也就能通向圣。虽然不是所有人都能成为圣人,却为人的发展指明了方向。从这种对他人的影响上看,圣人确实是以诚为依据而感通普通人。又由于诚是即动即静的,则圣人的“寂然不动,感而遂通”,首先应是人有志于学,而后学诚以成圣人,圣人通过自己的言行举止引导他人也学诚,在潜移默化当中使人自觉于诚,人自诚而化于诚。这就是周敦颐对孔子的赞美:“道德高厚,教化无穷。”*②③④⑤⑥ [宋]周敦颐:《周敦颐集》,陈克明点校,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第42页,第52页,第21页,第56页,第23页,第22页。
在周敦颐看来,人生天地间,和天地一样,根本上是诚而真实无妄的,任何与之不相符合的行为,皆是有悖于人性之诚的,不能中于人性,不合于天、地、人共同构成的生生不息的诚的世界,即是妄动为恶。若要避免侥幸心理并且消除之,使人发现自身真实的“幸”之所在,就要对自我之性进行寻根探源式的自我发掘,具体说来就是对自己的行为和心理加以分析。周敦颐将之称为“养心”,提出“圣贤非性生,必养心而至之”②的主张。通过“养心”,不只是寡欲,更是使心思通明而无丝毫隐瞒,个人的善与不善俱呈现出来,在此之上持续用力,便能达到“诚立,明通”的境界。具体着手之处是知耻改过,“必有耻,则可教;闻过,则可贤”③。耻辱所带来的羞愧感和负罪感,如果不对自己的行为和心理作反思,是不会产生的。诚实地面对自己之过并能勇于改正,使人之不诚复归于诚,这即是立师教的作用,以圣人之诚来引导普通人“立人极”,也是由人的复性、执性而成人之德行的具体化,这种“立人极”之方的典型代表是颜渊。
三、“立人极”之乐
周敦颐以颜渊为求学圣人之道的典范,认为颜渊“睿性通微,实几于圣”④,故而特别提出“学颜子之所学”⑤。颜渊生平艰辛,最终在贫病交加中死去,是普通人眼中的可怜人。颜渊常年“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论语·雍也》),在常人看来,处于这种生活状况下,早已经无任何乐趣可言。但是,颜渊孜孜以求的并非常人之乐。孔子称赞颜渊“有颜回者好学,不迁怒,不贰过。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则亡,未闻好学者也”,“回也,其心三月不违仁,其余则日月至焉而已矣”(《论语·雍也》)。孔子及后世皆以颜渊为门下最好学,且能有希望跻身于仁者。孔子虽然也有“食不厌精,脍不厌细”(《乡党》)的讲究,他最担忧的却是“德之不修,学之不讲,闻义不能徙,不善不能改”(《论语·述而》),其实衣服饮食之恶并不在孔子培养人之德性的考察视野之内。而且,孔子还有“君子固穷”(《卫灵公》)的说法,以颜渊对其师孔子“夫子循循然善诱人,博我以文,约我以礼,欲罢不能。既竭吾才,如有所立卓尔。虽欲从之,末由也已”(《论语·子罕》)的推崇来看,颜渊的忧乐与孔子的忧乐是一致的。颜渊对孔子事业的执著追随,即是周敦颐说的“圣希天,贤希圣,士希贤”⑥的仰慕而拳拳服膺之心。
孔子自称“乐以忘忧”,在其编订的《诗经》中也有“衡门之下,可以栖迟。泌之洋洋,可以乐(楽)饥”(《衡门》)的话语*清儒王先谦认为今本“楽”乃“療”转写所致,以河水“療饥”却不觉其苦,仍然自得其“楽(乐)”,故《衡门》之诗“言贤者乐道忘饥”,可见儒家不以清贫为苦的传统由来已久。(参见[清]王先谦:《诗三家义集疏》卷第十,吴格点校,北京:中华书局,2013年,第467页。)。颜渊作为孔子高足,必然同于其师,笃行于学仁、求仁,以仁为己任而乐此不疲,穷居陋巷而始终不改其乐。孔子自称“若圣与仁,则吾岂敢”(《论语·述而》),圣与仁是结合在一起的,求仁便是求圣,学仁可以至于圣人,孔子和颜渊所乐者就是仁而已。在周敦颐看来,诚是圣人之本,圣人即诚,孔子和颜渊所笃学力行的,其实就是诚,这就回到“立人极”之体。然而,对“立人极”之体的领悟与践履并非唾手可得,而是需要在现实中仔细体会,面对所处的外在环境做出选择的大问题。周敦颐所说的“君子以道充为贵,身安为富,故常泰无不足。而铢视轩冕,尘视金玉,其重无加焉尔”*[宋]周敦颐:《周敦颐集》,陈克明点校,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第40页。,正是强调在面对外界诱惑时,能不易其心志,坚持自得之乐。这继承并发挥了儒家“忧道不忧贫”的思想,二程奉周敦颐“寻孔颜乐处”之教的立意正在于此。由大程见猎心喜的典故可以得见:
猎,自谓今无此好。周茂叔曰:“何言之易也!但此心潜隐未发,一日萌动,复如前矣。”后十二年,因见,果知未。一本注云:“明道年十六七时,好田猎,十二年暮归,在田野间见田猎者,不觉有喜心。”*[宋]程颢、程颐:《河南程氏遗书》卷第七,《二程集》,王孝鱼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96页。
田猎之乐乃是外在的,少年时代的大程自以为已经去除掉了,实际仍潜伏于心中,并没有真正除去。周敦颐对大程的告诫直指其内心,田猎既非真乐事,又是系于外物而发,则田猎之外,还有其他可欲以求之的乐事,与周敦颐追求的 “立人极”的圣人中和之道不相符合。周敦颐以为圣人可学而至焉:
“圣可学乎?”曰:“可。”曰:“有要乎?”曰:“有。”“请闻焉。”曰:“一为要。一者无欲也,无欲则静虚、动直,静虚则明,明则通;动直则公,公则溥。明通公溥,庶矣乎!”*[宋]周敦颐:《周敦颐集》,陈克明点校,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第31页。
这里认为圣学之要在于“一”,以诚来一以贯之。既然“一者无欲也”,所有的思虑动作都是“动而正”、“用而和”,无欲即是诚。诚的自然顺化在人身上的实现,就是通过人的无为、无欲来实现,但又并非完全的无为、无欲。因为诚的实现还需要人的自诚,使人能复归于诚体。从万物化生上看,诚是万物之体,人是万物中之一,人是诚体的发用,故而人以诚为体。若要人自诚,就是从人自身去求诚体,诚的无为、无欲指的是人要积极主动地去无为、无欲,从而顺应诚的无为、无欲,然而又不能脱离现实的社会人伦。在周敦颐所处的时代与其理论框架中,这种圣人的中和之道便是礼乐,圣人“立人极”之体由礼乐而落实。
对于礼乐的起源,周敦颐的阐释是:
古者圣王制礼法,修教化,三纲正,九畴叙,百姓大和,万物咸若。乃作乐以宣八风之气,以平天下之情。故乐声淡而不伤,和而不淫。入其耳,感其心,莫不淡且和焉。淡则欲心平,和则躁心释。优柔中平,德之盛也;天下化中,治之至也。是谓道配天地,古之极也。*同上,第28—29页。
礼乐的中和能够使心思平和无欲,于是得到平和的天地之大乐,这是由礼乐之“乐”转而为和乐之“乐”。《礼记·乐记》认为音乐是“感于物而动”,圣人作乐是随外物而感动,却非专注于某一物,乃是遍及万物,故能以平和的声音去感化天下人心,由此天下皆能和。“乐”字虽音义有二,和却肯定是乐的前提。这在儒家经典中多有表述,如《诗·小雅·常棣》的“兄弟既具,和乐且孺”,《毛诗正义》解为“乐音洛……为此饫及燕礼之时,兄弟既已具集矣,九族会聚,和而甚忻乐”*[汉]毛亨传、[汉]郑玄笺、[唐]孔颖达疏:《毛诗正义》卷第九,[清]阮元校勘,《十三经注疏》第2册,台北:艺文印书馆,2002年,第322页。;又如《左传·隐公元年》言郑庄公“其乐也融融”,杜预注为“融融,和乐也”,孔颖达疏解为“融融和乐,洩洩舒散,皆是乐之状,以意言之耳”*[周]左丘明传、[晋]杜预注、[唐]孔颖达疏:《春秋左传正义》卷第二,[清]阮元校勘,《十三经注疏》第6册,台北:艺文印书馆,2002年,第37页。;再如《论语》中,有若提出“礼之用,和为贵”,皇侃解为“和即乐也。变乐言和,见乐功也”*[魏]何晏集解、[梁]皇侃义疏:《论语集解义疏》卷第一,沈抱秋、谢雨东校对,上海:商务印书馆,1937年,第10页。。周敦颐论和乐,就是将礼乐之“乐”与和乐之“乐”融贯为一,与上述经典解释相一致。由此回到“立人极”的问题,学礼乐而明其中意蕴,便能达至礼乐之和乐,于是就能乐于其中。
颜渊问为仁之方,孔子答以非礼勿视、听、言、动之克己复礼。所谓“克己复礼”,《左传·昭公十二年》引述孔子之言“古也有志,克己复礼,仁也”,《春秋左传正义》训“克”为“胜”,“谓身能胜去嗜欲,反复于礼也”*[周]左丘明传、[晋]杜预注、[唐]孔颖达疏:《春秋左传正义》卷第四十五,[清]阮元校勘:《十三经注疏》第6册,台北:艺文印书馆,2002年,第795页。,近于孟子“养心莫善于寡欲”的说法。《春秋左传正义》的解释,是以克服身体欲望为方法;孟子的说法,则以为心思不能逐于外物*孙奭以为孟子之说,与荀子所说的“养心莫善于诚”相同。(参见[汉]赵岐注、[宋]孙奭疏:《孟子注疏》卷第十四下,[清]阮元校勘,《十三经注疏》第8册,台北:艺文印书馆,2002年,第262页。)。周敦颐对此加以发挥,认为“养心不止于寡焉而存耳,盖寡焉以至于无。无则诚立、明通。诚立,贤也;明通,圣也。是圣贤非性生,必养心而至之。养心之善有大焉如此,存乎其人而已”*[宋]周敦颐:《周敦颐集》,陈克明点校,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第52页。。
行礼即是行仁,处处指向人之自身,使自我的道德修养与礼仪践行结合起来,将自己融于中和之道,圣人之道立,所乐者以天地为范围,不再局限于某一具体之乐。于是,颜渊不以富贵为乐:“天地间有至贵至爱可求,而异乎彼者,见其大、而忘其小焉尔。见其大则心泰,心泰则无不足。无不足则富贵贫贱处之一也。处之一则能化而齐。故颜子亚圣。”*同上,第33页。
周敦颐以颜渊为亚圣,肯定颜渊已入圣人之道,是“立人极”的典范。颜渊悟道,能深刻体悟“立人极”之乐,故能以礼为标准自处,得到了平和之乐,不再受外物的迷惑,于是能无欲而乐,且乐此不疲。周敦颐应也是如此之人,其妻兄蒲宗孟记述周敦颐不以贫穷为意*据蒲宗孟所记,周敦颐仗义疏财,“虽至贫,不计赀,恤其宗族朋友。分司而归,妻子饘粥不给,君旷然不以为意也”。(参见《周敦颐集·附录一》,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第94页。),他不只于学理上表达了“立人极”之乐,更是身体力行之。孔子与颜渊之乐,被周敦颐体悟并共乐之,可见“立人极”之乐的超时空性。以“立人极”之乐为纽带,孔子慕前圣而守道,颜渊求之而安贫乐道,周敦颐以及后来的理学家接续之,前贤后哲竟然乐而为一,亦是所谓的君子的“信赖社群”的表现*杜维明认为《中庸》在讲求自我修养的同时,通过“五达道”、“三达德”、“九经”的社会政治活动,形成人际关系之间的“信赖社群”。在政治活动中,儒学也很重视精神方面的一体性。本文借用“信赖社群”的概念,表达的是不同时期的儒学思想家精神追求上的继承性与一致性。(参见[美]杜维明:《中庸:论儒学的宗教性》,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年,第46—80页。)。
四、结 语
周敦颐先于宏大的宇宙论体系中,肯定人为其间最灵秀者,圣人又是人之极致者,“立人极”便是要成为圣人。天地之大,成为圣人并非易事。周敦颐引入《中庸》里的“诚”概念,以人之自诚去实现天道之至诚,具体的用力之处,便是于人伦日用中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笃行,由之身体力行。“立人极”于此,顺应了宇宙与万物的生成变化,个人的道德修养也被提升至天地的境界。对于“立人极”之道,不但能学习之、体会之、更能安之、好之、乐之。大程有感于周敦颐的气象之磅礴,不由生出了“吾与点也”之意。于是,据“立人极”之体,依“立人极”之方,得“立人极”之乐,圣人之性于人伦日用中即得以落实,圣人也就不再是遥不可及者,而是人人都可以成为圣人,汉代谶纬对圣人的神化与附会也就被破除了*对圣人的神化,由《论语谶》对孔子降生的描述可见一斑:“叔梁纥与徵在祷尼邱山,感黑龙之精,以生仲尼。”(参见[清]赵在翰辑:《七纬(附论语谶)》,钟兆鹏、萧文郁点校,北京:中华书局,2012年,第773页。)。周敦颐作为宋明理学的奠基性人物,黄百家称赞他“破暗”于“心性义理之精微”*[清]黄宗羲原著、[清]全祖望补修:《宋元学案》卷第十一,《濂溪学案上》,陈金生、梁运华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第482页。,与其“立人极”的思想是分不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