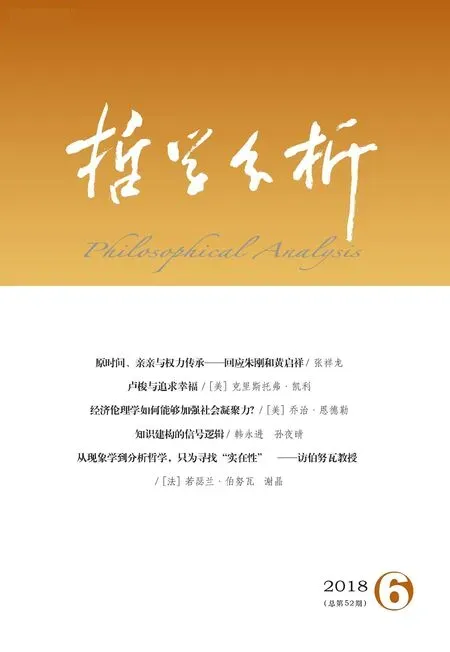经济伦理学如何能够加强社会凝聚力?
2018-01-23乔治恩德勒文陆晓禾
[美]乔治·恩德勒/ 文陆晓禾 杜 晨/译
对一个社会的社会凝聚力而言,所谓的“公共产品”是至关重要的。这是本文所要研究的主题。关于靠什么凝聚一个社会的问题,无疑极其复杂。在我们认为社会凝聚力遭到危害甚至破坏之时,提出这个问题具有极大的紧迫性。我们可以在不同的社会层次上认同这些危机经验。在我们的城市或社区,我们可能已无力修复那些破败不堪的基础设施或克服极端分化的社会不平等。在我们的国家,我们不能保障少数族群和宗教群体拥有体面的生活。在欧盟国家,我们无法找到应对中东难民挑战的共同基础。而且,整个世界缺乏为应对气候变化威胁而恪守承诺有效政策的必要凝聚 力。
这些例子清楚地表明,我们面临着大量的问题:政治的、经济的、社会学的、心理学的、法律的、道德的和其他方面的。这些问题互相关联而且在从地方到全球不同层次上的许多社会中俯拾皆是。
一个社会的社会凝聚力是一个令人生畏的问题,极其复杂而又重要。当然,为了真实认识和迫切警告社会凝聚力的破坏危险,我们也不必危言耸听。而且,社会凝聚力问题涉及广泛,远非经济伦理学所能解决。但是,经济伦理学在其有限范围内面临的挑战是:经济伦理学如何能够加强一个社会的社会凝聚力?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首先用以下方式对“社会凝聚力”和“经济伦理学”这两个关键术语下定义。按迪克·斯坦利(Dick Stanley)的定义,“社会凝聚力”是“一个社会的成员为实现生存和繁荣而彼此合作的意愿。合作的意愿指的是,他们自由选择建立合作伙伴关系并有合理的机会实现目标,因为其他人愿意尽力公平地合作并分享这些成果。”①D. Stanley,“What do We Know About Social Cohesion:The Research Perspective of the Federal Government's Social Cohesion Research Network”,The Canadian Journal of Sociology/Cahiers canadiens de sociologie,Vol.28,No.1,2013,pp.5—17.这个定义目前已经足够,本文后面将讨论这个定 义。
第二个术语“经济伦理学”,指的是按全面和有区别的含义来理解的企业和经济伦理学,正如近些年在全球化影响下发生的变化那样。它从伦理的观点涵盖了全部经济生活领域,包括理论阐述(作为学科)和实践履行 (在所有层次上的健全实践)。与被欧洲经济伦理网络广泛接受的②G. J. Rossouw & C. Stückelberger,“Supplement 1:Global Survey of Business and Economics Ethics”,Journal of Business Ethics,Vol.104,No.1,2011, pp.1—6.汉克· 范卢克(Henk van Luijk)的定义③H. J. L. van Luijk,“Business Ethics in Western and Northern Europe:A Search for Effective Alliances”,Journal of Business Ethics,Vol.16,No.14,1997,pp.1579—1587.相一致,经济伦理学的根本任务是提高在个人(微观)、组织(中观)以及制度(宏观)层次上的所有经济活动的决策和行动的伦理质量。当面对复杂的问题时,经济伦理学必须采取多层次的方法来考虑每一层次的自由与限制以及这些层次之间的相互关 系。
记得上述概念说明后,本文将分三步展开。首先,我们将聚焦企业和经济的目的。我提议,在私人财富与公共财富结合的全面意义上(包含自然的、经济的、人力的以及社会的资本),将企业和经济的目的定义为财富创造。其次,我们将视角拓展到整个社会,为社会凝聚力寻找恰当的概念和基础。在讨论了不同的凝聚力方案:开明的利己主义、新博弈论和天主教社会教义倡导的共同善概念之后,我将提出我的方案:强调公共产品的重要性。最后,基于上述对财富创造的理解,我将提供经济伦理学能够加强社会凝聚力的三种方式:(1)聚焦企业和经济的目的即创造自然的、经济的、人力的和社会的资本;(2)倡导经过伦理审查的公共产品;(3)保障作为公共产品概念来理解的人 权。
一、企业和经济的目的:作为私人财富与公共财富结合的财富创造
面临全球化、金融化和环境灾害威胁的多重挑战,迫切需要追问企业和经济的目的并考察不同的财富概念。财富的含义通常非常简单,相当于“大量的金钱”;而企业和经济的目的据说就是“尽可能多地赚钱”。或者,企业和经济的目的的定义也可以非常含糊,例如定义为“创造价值”,所以有着多种并且矛盾的解释。因此,似乎合适的办法是,用批判的和建设性的方式来考察企业和经济的目的以及财富概念这两个问 题。
财富概念具有多维度的含义。如罗伯特·海尔布隆纳 (Robert Heilbroner)所说:“财富确实是经济学的最基本概念,也许是这一学科的概念起点。然而,尽管财富概念处于中心地位,对于这一概念的定义却从未达成普遍共识。”①R. L. Heilbroner,“Wealth”,in The new Palgrave:A Dictionary of Economics(Vol.4),edited by J. Eatwell,M.Milgate & P. Newman,London:Macmillan,1987,pp.880—883.财富概念,在亚当·斯密的名著《国富论》(1776/1976)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在冈纳·缪尔达尔(Gunnar Myrdal)的著作《亚洲悲剧:国贫论》②G. Myrdal,Asian drama: An Inquiry into the Poverty of Nations,New York:Pantheon,1968.中,却显然并不存在;而在戴维·兰德斯(David Landes)的著作《国富国穷——为何有些国家如此富有,而有些国家如此贫穷》③D. Landes,The Wealth and Poverty of Nations:Why Some are so Rich and Others are so Poor,New York:Norton,1999.中,则补充为与财富的对立面——贫穷——一起出现。
为了探究和考察财富概念,我们首先可以考虑一国的财富是什么意思。是什么使挪威这样一个国家成为“富有”的国家?④据世界银行(2011)的统计,挪威在2005年是世界上最富有的国家。世界银行、经合组织和其他机构的最近研究得出了令人感兴趣的结果,纠正了通常以国民生产总值(GDP) 作为一国经济状况的决定性的通常是唯一的指标这种情况。这些研究促进了对一国财富更丰富和更现实的理解 。⑤World Bank,Where is the Wealth of Nations?Measuring Capital for the 21st Century,Washington,DC:World Bank,2016;World Bank. The Changing Wealth of Nations:Measuring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n the New Millennium, Washington,DC:World Bank,2011;D. Warsh,Knowledge and the Wealth of Nations:A Story of Economic Discovery,New York:Norton,2006;J. Stiglitz,A. Sen & J.-P. Fitoussi, Report of the Commission on the Measurement of Economic Performance and Social Progress,2009. http://www.stiglitz-sen-fitoussi.fr/documents/rapport_anglais.pdf.;United Nations Development Programme (UNDP). Human Development Report 2010. The Real Wealth of Nations. Pathways to Human Development,New York:Palgrave Macmillan,2010;OECD. How's life?2013. Measuring Well-being 2013. www.oecd. org.
从这些丰富的文献中,我们可提出并简要表征企业的规范目的,同时还可参考笔者在多篇论文中的广泛讨论。①G. Enderle,A Rich Concept of Wealth Creation Beyond Profit Maximization and Adding Value, Journal of Business Ethics,Vol.84,No.3,2009,pp.281—295;Wealth Creation in China and Some Lessons for Development Ethics. Journal of Business Ethics,Vol.96,No.1,2010,pp.1—15;Wealth Creation in China from a Christian Perspective. Qing Feng,n.s. 12,2013,pp.119—136;Exploring and Conceptualizing International Business Ethics,Journal of Business Ethics,Vol.127,No.4,2015,pp.723—735;Business and the Greater Good as a Combination of Private and Public Wealth,in Business and the Greater Good:Rethinking Business Ethics in an Age of Crisis,edited by Cheltenham:Edward Elgar,2015,pp.64—80.
(一) 一个社会的财富是私人财富与公共财富的结合
当我们着手定义“一国的财富”时,很难否认财富应该同时包含私人产品与公共产品或资产,也就是两种类型的富有:一类能够由个别行为者所拥有和控制,无论这些个别行为者是个人、团体或组织;另一类不能将这个国家里的任何一个成员排除在外。在经济学理论中,“公共产品”被定义为具有这种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的特征。②R. A. Musgrave,The Theory of Public Finance,New York:McGraw-Hill,1958;P. A. umuelson,“The Pure Theory of Public Expenditure”,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Vol.36,No.4,1954,p.36,pp.387—389;P.A. Samuelson,“Diagrammic Exposition of a Theory of Public Expenditure”,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Vol.37,1955,pp.350—356.一个经典的例子是(在民主政治背景下的)国防。一旦建立了国防,没有人可以被排除在外。而且,没有一个人能够在减少另一个人受国防保护的情况下自己从中受益。换句话说,甲对于公共产品的“消费”或“享受”与乙对于公共产品的“消费”或“享受”并不存在竞争性。相反,私人产品的特征则具有排他性和竞争 性。
公共产品的这两个形式标准也可应用于负面性的公共产品 ,或者也可叫做“公共恶品”③在经济学中,公共恶品被用作公共善品的对应术语,因为它具有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的特征并且对人和自然造成了负面影响。空气污染是公共恶品的一个明显例子。至于目前有关公共恶品的定义,参见C. D.Kolstad,Environmental Economics(2nd ed.),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0。。当疫病(如埃博拉)肆虐某个地区时,(原则上)没有一个人会被排除在外,某个疫区的某个居民受到感染的风险并不会由于另一个居民的感染而减少。(相反,这另一个居民的风险甚至很可能增大。)
当然,我之后还会对私人产品与公共产品的简要特征作进一步解释。现在,重要的是理解一个社会(从地方到全球)的财富是私人财富与公共财富的结合,而非仅仅私人财富的聚集。这意味着,私人产品的创造依赖公共产品的可用性;反过来说,公共产品的创造也有赖私人产品的可用性。
我想以中国现代历史为例来说明这个观点。邓小平在1978年开始了这个国家的经济改革和开放政策,中国老百姓纷纷“下海”。在此后的数十年里,市场经济的引入很大程度上证明是非常成功的(当然,成功并不能否定这一经济发展有着消极面)。成功的决定性因素是所谓的“邓小平效应”。 尽管当时还没有完善的法规来保护私人企业家,但这些中国人相信,邓小平不会欺骗他们,相反会承认并支持他们的努力。因此,公允而言,对邓小平的信任作为当时的公共产品,是中国经济改革中私人企业家创业成功的关键因素。
另一方面,公共产品的创造事实上也有赖私人产品的创造。只要回忆一下私人对于公共财富创造的多维度贡献,就足以说明这一点了,这些贡献可见于企业、教育、研发、艺术、医保、税收及其他领域。
因此,一个社会的财富是私人财富与公共财富的结合这种理解,隐含着某些基本的假定。我想强调两个有深远意义的假定。第一,我们知道,市场制度一般而言在创造私人产品方面是相当有效的,这也就是为何邓小平将某种市场经济引入中国的原因。从经济理论中我们也知道,市场在创造公共产品方面会失灵。尽管许多公共产品都有物质方面,但为了恰当地发挥供求功能而制定公平产品的价格,这如果不是不可能,也是极端困难的。因此,创造公共产品需要不同于市场的机制。众所周知,为了解决加勒特·哈丁(Garrett Hardin)在 1968年指出的“公地悲剧”,埃莉诺·奥斯特罗姆(Elinor Ostrom)研究出其他制度形式,为此她在2009年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 奖。
第二个基本假设隐含着一个社会的财富是私有财富与公共财富的结合这一论点:就创造公共财富而言,利己主义动机必然失灵。为什么呢?因为无论谁从事公共产品的创造,实际上都不能期望得到与投入这种创造的时间和努力相等的回报。在许多情况下,人们必须接受或至少忍受这种或那种形式的牺牲。仅仅完全以利己主义为导向,例如,按俄裔美国哲学家安·兰德(Ayn Rand)所倡导的①受安·兰德启发几十年后,美联储主席(1987—2006)格林斯潘直至2008年10月23日在美国参议院听证会上才承认:“我错误地认定,尤其是银行和其他组织的利己主义,使他们能够最好地保护其股东及其公司权益。”(引自B. Knowlton & M. M. Grynbaum,“Greenspan ‘Shocked’ That the Markets are Flawed”,New York Times,October 23,2008),人们只能在不与自己利益冲突的程度上,支持或容忍他人的利益。所以,为了创造公共产品,必然需要另一种动机:至少像认真考虑自身利益一样地认真考虑他人、团体、组织、国家和其他实体的利益。正如经济史所表明的,可以采取各种形式的动机,例如,为了创业成功而无私地参与、热爱祖国、团结穷人,以及为注定会失败的事业而战斗。 在每种情况下,关心他人的动机都超越了利己主义,无论是出于正当的或不正当的理由。因此,尽管不是创造公共产品的充分理由,但关心他人的动机却是必要的,而且创造正面的公共产品仍然需要进行伦理评估。当事关全球公共产品或公共恶品(例如气候变化)时,关心他人的动机尤其难以调动起来。所以,人们可能会期望世界上的宗教有助于加强生产(积极的)全球公共产品的动机。②G. Enderle,“Wealth Creation in China and Some Lessons for Development Ethics”,Journal of Business Ethics,Vol.96,No.1,2010,pp.1—15.
(二) 一个社会的财富包含自然资本、经济资本、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
在讨论了私人产品与公共产品的形式标准后,我们现在转向对财富的实质测定上。这样做时,我会使用一些经济学理论的概念,如资本、消费、投资和机会成本等,这可能对非经济学家来说有些奇怪。这些概念可有助于更准确地把握复杂的问题,而不会屈服于某种经济学帝国主义。
根据经合组织的报告《过得怎样?2013——衡量福祉》(2013)①OECD,How's Life?2013. Measuring Well-being, 2013. http://www.oecd. org.,我提议将一个社会(例如一个国家)的财富,定义为包括自然资本、经济资本、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的所有在经济上与私人资产与公共资产有关的总和。自然资本由自然资源减去环境负担而构成。②强调自然资本的重要概念,是金融部门对“里约+20峰会”的承诺。它将自然资本定义为地球的自然资产(土壤、空气、水、植物和动物)以及由此产生的生态系统服务,正是这些使人类的生活成为可能。宣言的签署方希望表明其承诺,也就是最终将自然资本的考虑整合进私营部门的报表、会计和决策中,以标准化方式测量并披露私营部门使用自然资本的情况 (www.naturalcapitaldeclaration.org)。经济资本由“实物”资本和金融资本构成。人力资本指的是人的健康和教育。最后,社会资本,按罗伯特·普特南( Robert Putnam)的理解,是信任关系,指的是人与人之间的信任程度。③对多层次人际关系中的社会资本,有非常多的概念(例如参见 A. Ayios & R. Jeurissen,P. Manning & L. J.Spence,“Social Capital:A Review from an Ethics Perspective”,Business Ethics:A European Review,Vol.23,No.1,2014,pp.108—124);权(Kwon )与阿德勒(Adler) 在看了 90多本书和文章后得出的结论是:“关于社会关系在提供信息、影响和团结方面可以是有效的这一基本论点已不再有争议了。”(Ibid., p.419)本文中,我专注与经济有关的社会资本,并运用普特南的定义,即指的是“个体间的联系,也就是社会网络以及由此产生的互惠和信任规范”。社会资本可以是私人产品同时又是公共产品,也可以有“黑暗的一面”(意思是限制自由和不鼓励容忍),艾尤斯(Ayios)等人从伦理角度对此作了考察。(Ibid.)因此,本文中所使用的社会资本的定义与社会凝聚力的概念不同,在后面的章节中将作清晰的说明。
财富的这一定义(接近福祉的含义)也包含了2013年经合组织报告所强调的重要特征。④同样,《国际整合报告委员会》( the International Integrated Reporting Committee)区分了六种资本类型:金融资本、制造资本、智力资本、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和关系以及自然资本(IIRC2013,特别见pp.12—13)。首先,不独经济资本,而且自然资本、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都与经济相关。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它们只在经济方面是重要的;毋宁说,它们本身也是有价值的。因而,公共产品不仅与财富创造相关,还与其他非经济的目的有关。
其次,财富的这一定义包括了人类以及与人类息息相关的事物和环境条件。这样,它超越了通常对财富的物质性定义,而重视“人的能力”(根据阿马蒂亚·森的观点)并将人的福祉置于中心地位。这一定义与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人类发展定义不同,后者似乎只在人类身上发现了 “国家的真正财富”(而没有包括对人类重要的事物和自然)。简言之,这里提出的定义旨在重视人类的身体性质的表达方面。
第三,按斯蒂格利茨—森—费图斯委员会的报告⑤J. Stiglitz, A Sen & J.-P,Fitoussi,Report of the Commission on the Measurement of Economic Performance and Social Progress,2009. http://www.stiglitz-sen-fitoussi.fr /documents/rapport_anglais. pdf.以及经合组织的报告(2013)⑥OECD,How's Life?2013. Measuring Well-being.,资本概念是指股票和资金流,在经济意义上不仅包含了处于某个时间点的相关资本存量,还包含了一段时期内的资本存量的变化。用这种方式,人们就会考虑,例如财富与收入以及自然资源和前面提到的变化。
正如这些从概念方面的考虑所表明的,一个彻底的和深思熟虑的财富概念,具有重要的意义。我们已经解释了它的一些重要方面,别的方面不能在本文中论及,但在其他地方有过讨论(参见前面脚注中作者的相关文献)。不在本文讨论范围但可进而探讨的一个特别有趣的问题是,贫困和经济不平等,可以采取这一私人财富与公共财富的全面概念来研究。
还在亚当·斯密年代,斯密就从财富的创造中看到了企业和经济的目的。今天,我们能够用更广泛和丰富的术语来定义这一目的。毫无疑问,只有少数负责任的科学和政治领导人可能具有这样的概念。然而,尽管这样的概念具有重要意义,却不应予以高估,因为它总是植根于社会环境中,在这个环境中有其他同样重要或更为重要的目标:民主对权力的控制、负责任地促进知识和艺术、谨慎地对待自然,以及其他一些目的。
二、靠什么来凝聚一个社会?
在比较准确地界定了企业和经济的目的是财富创造后,我们现在将聚焦如何从概念上最恰当地理解社会凝聚力问题。尽管这个问题不是一个新问题,近年来却引发了大量的讨论。如果我们意识到全球化对我们的社会及其多元化碎片造成的巨大压力,那么就没必要对此感到惊讶了。罗尔斯早在《正义论》和《政治自由主义》中就敦促说,我们的多元化(民主)社会的稳定需要一种“交迭共识”,或者说一种共同的伦理基础。1996年,瑞士新教教会联合会社会伦理研究所在庆祝该所成立25周年之际,举办了“社会凝聚力问题”研讨会。①L. Voyé,H.Ruh,H.-B. Peter,P. Bühler & J.-M. Belorgey,Gesellschaftlicher Zusammenhalt — in Frage gestellt,Beiträge zur sozialethischen Orientierung,Bern:Institut für Sozialethik,1998.几年前,耶稣会慕尼黑哲学学院罗腾多夫(Rottendorf)基金会邀请学者们参加了一个讨论会,主题即“靠什么来凝聚一个社会?应对多元主义面临的困境”。②M. Reder,H. Pfeifer & M.-D. Cojocaru(eds.),Was hält Gesellschaften zusammen?Der gefährdete Umgang mit Pluralität,Stuttgart:Kohlhammer,2013.2015年,克里斯托夫·卢德格(Christoph Luetge)的新书名就是《秩序伦理还是道德过剩——靠什么来凝聚一个社会?》。③C. Luetge,Order Ethics or Moral Surplus:What Holds a Society Together?Lanham,MD:Lexington Books,2015.
与社会凝聚力概念相关的讨论有很多,尤其在社会学文献中,但这一术语本身在政治哲学和经济伦理学的文献中却较少出现。经合组织报告(2011)对社会凝聚力下了一个非常宽泛的定义:“如果一个社会致力于其所有成员的福祉,反对排斥和边缘化,造成归属感,促进信任,并且为其成员提供上升的社会流动机会,那么这个社会便是‘有凝聚力的’。”①OECD,Perspectives on Global Development 2012:Social Cohesion in a Shifting World. OECD Publishing,July 27,2011. doi:10. 1787/persp_glob_dev-2012-en,p.51.社会凝聚力由三个不同但同样重要的部分组成:(1)社会包容性(由贫困、不平等和社会两极化这样的社会排斥方面来衡量);(2)社会资本(结合各种形式的公民参与来测量人际和和社会信任程度);以及(3)社会流动性(按人们能够或认为他们能够改变自己的社会地位的程度来衡量)。社会凝聚力的这一定义受到众多国际组织报告的影响,尽管相当全面,但在我看来,仍然缺乏精确性和一致性。
在加拿大政府的社会凝聚力研究网络上,迪克·斯坦利(Dick Stanley)对社会凝聚力的概念和模式,作了如下细致和有区别的讨论:
社会凝聚力可定义为一个社会的成员为生存和繁荣而相互合作的意愿。合作意愿意味着他们是自由地选择去建立合作伙伴关系和获得实现目标的合理机会,因为其他人也愿意合作并公平地分享他们的努力成果。②D. Stanley,op. cit.
这一概念包含三个关键部分。首先是,人们在多样性的集体企业中相互合作的意愿和能力。相互合作是社会成员为了生存和繁荣所必须做的。这也意味着,合作伙伴愿意公平地分享合作成果。因为合作发生在社会活动的所有层次上,所以社会凝聚力是全体个人合作意愿的总和。其次,社会凝聚力不应与社会秩序、共同价值观或诠释共同体③原文为“communities of interpretation” ,指的是这样的群体,他们有着对世界、社会的共同理解,但这种理解不必以个人参与这个群体的自由协议为基础。——陆晓禾相混淆,因为这些也可以在威权社会或被围困的社区中,通过强迫和排斥,在社会成员没有自由选择权的情况下,出于恐惧或仇恨而取得。再次,社会凝聚力与自由、平等、宽容、尊重多样性和人权等自由社会价值观之间有着密切的关系。由自由社会价值观引导的社会凝聚力产生了公平的社会结果,进而增强了社会凝聚 力。
从经济伦理学和道德责任的角度来看,这一社会凝聚力概念似乎特别合适。根据理查德·狄乔治④R. T. De George,Business ethics (7th ed.),Boston:Prentice Hall,2010,Chapter 6.所说,以道德负责的方式行动意味着能够采取行动(造成行动结果),并且是在知情和自愿的情况下这么做的;换言之,这意味着不被强迫去做,有选择权,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并有意去做。
基于上述斯坦利的社会凝聚力概念,我们现在讨论提供社会凝聚力基础的不同方案。第一种是新古典经济理论的个人主义模式,这种理论也用于所谓的秩序伦理。第二种,即博弈论方案,它超越了新古典主义模式,开辟了充满希望的新视角,可以纠正个人主义模式的弱点。第三种方案提供了天主教社会教义所倡导的共同善概念。最后,我将更为广泛地解释为何公共产品对社会凝聚力具有决定性的重要意 义。
(一) 开明的利己主义主义本身基础牢固吗?
在新古典经济学理论中,经济活动的理性和动机具有“经济人”及其知识分子后代“REMM”(即足智多谋、善于评估和追求最大化的人)的特征①F.-X. Kaufmann,“Wirtschaftssoziologie I:Allgemeine”,in Handwörterbuch der Wirtschaft swissen schaften(HdWW) . edited by New York:Springer,Vol.9,1988,pp.244ff;C. Luetge(ed.),Handbook of the Philosophical Foundations of Business Ethics,Three Volumes,Dordrecht:Springer.(特别参见 Vol. 1,Part 3:morality and self-interest:from Hume to smith to contemporary perspectives,2013,pp.251—335)。经济行为者(家庭、企业)如果各自追求自己的效用或利润最大化,那么就是理性的行为。这一理性概念基于行为理论,专注行为的各种选择,而行为的条件假定是相对稳定的。它预设了方法论上的个人主义,将所有行为溯至(家庭和企业的)个体决策。按弗朗—兹泽维尔·考夫曼(Franz-Xavier Kaufmann)在《企业和经济学手册》中所述,经济人具有三种含义:(1)经验性经济行为的现实典型重建;(2)理性经济行为的规范定义;(3)决策论计算的分析起点。②F.-X. Kaufmann,“Wirtschaftssoziologie I:Allgemeine”,pp.239—267.
相应的,对经济人的批评也包含三个方面:(1)作为概念,它是一种糟糕的现实典型的重建,可以用多种方式来驳斥(在这一点上,行为经济学已经成功地做到了);(2)作为规范,它是可疑的,因为几乎难以通过推理来证明;(3)作为分析方法,它也没有任何解释的价值。
除了这些批评外,方法论上的个人主义也可能遭到质疑,因为它没有把集体行为者的相关性考虑在内,甚至还有争议。这种行为理论的方法难以清晰地捕捉变化的行动条件。效用或利润最大化所发生的时间跨度也很难确定。最后,就像多年前肯尼斯阿罗(Kenneth Arrow)在其名著《社会选择与个人价值观》③K. J. Arrow,Social Choice and Individual Values(2nd ed.),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1951/1963.中所论证的,个体行为者的效用成为一种“社会福利函数”,这在实践上是不可能的。
尽管存在诸多问题,但令人惊讶的是,“经济人”不仅幸存了下来,而且还在经济学科和其他领域中繁盛起来。不论所有这些可疑性,这个概念如何能够提供维系一个社会的坚实基础呢?卡尔·霍曼(Karl Homann)以及最近克里斯多夫·卢德格已经尝试对经济人概念作部分纠正工作。他们承认如下批评:如果按真实典型的意义和规范意义(上述批评1和2)来理解,经济人概念是站不住脚的。然而,他们坚持认为,这一概念的建构是恰当的,可以用于分析某些问题(上述批评3)。卢德格主张,经济人为解决社会基本秩序问题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即提供了一种“秩序伦理”。以开明的利己主义来指导的态度和行为,在全球和多元化的情境中,确实会将一个社会凝聚一起。①C. Luetge,Order Ethics or Moral Surplus:What Holds a Society Together?Lanham,MD:Lexington Books,2015,pp.176—177.
卢德格小心翼翼地逐步展开其具有挑战性的论点,在讨论中还引用了许多著名哲学家。遗憾的是,这里不能提供我的评论,但至少,我想扼要地点明我的批评,主要有两个反对理由。首先,方法论个人主义建立在个人主义和西方人类学的基础之上,它未能用适当的方式认真地看待集体现象。其次,当我们考虑到处于危险中的这类产品时,这一方法就失灵了。因此,正如上面所解释的,仅仅依靠利己主义,即使是开明的利己主义,也不能激发创造和维护公共产品的动机。需要的还是利他主义的动机,这种动机才能认真地对待整个社会的利益。
为了克服仅基于利己主义的方法,朱利安·克劳斯(Juljan Kruse)与马库斯·舒勒茨(Markus Scholz)提出了一种植根于博弈论的团队导向模型。②J. Krause & M. Scholz,“Erosion of Sovereign Control:Deliberation,‘we-reasoning’ and the Legitimacy of Norms and Standards in a Globalized World”,in M. C. Coutinho de Arruda & B. Rok (eds.),Understanding Ethics and Responsibilities in a Globalizing World,Dordrecht:Springer,2016,pp.83—101.博弈论模型的目的是,把握许多利益相关者在协商最重要的全球共同标准中出现的关键问题。行为者可以在两种推理类型:我—模式(I-modus)与我们—模式(We-modus)之间切换。这种协议在这样一种程度上受到影响,即这些行为者愿意从团体的立场来提供理由。在我看来,这一模型为更好地理解公共产品的创造提供了具有前景的途 径。
(二) 天主教社会教义的共同善概念有多牢固?
共同善( common good)是天主教社会教义的一个重要概念,具有多种涵义。在《论教会在现代世界的牧职宪章》“喜悦与希望”中可找到如下重要定义:
(共同善)是让私人及团体可以充分而便利地玉成自身的社会生活条件的总和,今天亦愈显普遍化,从而包括整个人类的权利和义务。每一团体应顾及其他团体的急需及合法愿望,甚至应为整个人类大家庭的共同善着想。③Pastoral Constitution (1965) on the Church in the Modern World “Gaudium et Spes”,promulgated by His Holiness,Pope Paul VI,on December 7,1965. No. 26. http://www.vatican.va/archive/hist_councils/ii_vatican_council/documents/ vat-ii_const_19651207_gau dium-et-spes_en.html. (此段中译文取自梵蒂冈官网中文版宪章:http://www.vatican.va/chinese/concilio/vat-ii_gaudium-et-spes_zh-t.pdf,个别字略有修改。“common good”在官网中译作“公益”。——译者)
这一定义中有四个方面值得特别强调:第一,共同善属于社会(或社会性)生活条件,而并非属于所有社会成员的实质性目标(德语称作“Gemeingut”)。第二,这些条件对社会团体及其个体成员实现各自人生计划(“他们的自我实现”)是必要的。第三,共同善包括这些社会条件的总体。第四,由于全球化,即全世界范围愈加紧密的相互依赖性,所有这些条件都与全人类休戚相关。
那么,如何用实质性术语来定义这些社会条件呢?根据教宗若望二十三世的通谕《和平于世》(Pacem in Terris,1963)并经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确定,这些条件包含了1948年颁布的《世界人权宣言》以及联合国各项盟约和公约中所规定的人权。今天的天主教社会教义已经明确无误地确认了上述全部人权,尽管许多信徒和教会以外的普通人对这个事实不甚了解,或者不想注意或不抱希望。
假定这一共同善概念是存在的,我们现在要问的是,它对我们的社会凝聚力问题意味着什么呢?与人类学对“经济人”的假设相反,天主教社会教义假定人类是关系性的存在。与其他人的关系构成这个人的身份,《牧职宪章》“喜悦与希望”中着重肯定了这一点。“ [由于]人最内在的本质是一种社会性存在,因而除非他将自己与他人关联在一起,否则他就既不能生存也不能发展他的潜能。”①Pastoral Constitution (1965) on the Church in the Modern World “Gaudium et Spes”,promulgated by His Holiness,Pope Paul VI,on December 7,1965. No. 26. http://www.vatican.va/archive/hist_councils/ii_vatican_council/documents/ vat-ii_const_19651207_gau dium-et-spes_en.html.这种基本的人类学假设构成了任何一个社会的社会凝聚力的基础,同时排除了个人主义的以及集体主义的概 念。
因此,仅仅以利己主义作为动机,即便是开明的利己主义,也无法与人类的关系性相容。不用说,人们可以而且经常通过不顾或违背他们的关系来采取行动。
如上所述,共同善指的是社会团体及其个体成员应该能够追求其人生计划的条件。这些条件适用于从地方到全球的每一个社会,它们在很大程度上由人权构成。话虽如此,这里仍然有两个重要问题:首先,更确切些说,我们所说的是哪种社会?其次,这些条件是由哪种产品构成的?
正如人们可能怀疑的那样,我建议将这些社会条件从概念上理解为私人产品与公共产品的结合。这样做之后,会更易于清晰地确定所要考虑的那种或那些社会了。
(三) 公共产品的创造和维护为社会凝聚力提供坚实的基础
如上所述,公共产品被定义为具有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为了创造和维护公共产品,必须要有集体行为者,他们的动机是,至少在为他们自己的利益考虑范围内,认真地对待他人的利益和社会行为者的利 益。
在这一点上,我们将进而对公共产品概念作恰当的澄清工作。我特别提出三个方面。首先,由于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的特点,可以非常清楚地将私人产品与公共产品区别开来,按照排他性和竞争性的程度,在这两级之间,可能会出现许多混合形式。例如,软件程序可能具有最低限度的竞争性,因为某个工程师的使用,几乎不会影响其他工程师使用这个程序。然而,知识产权的法律保护则使局外人无法使用该程序。另一个例子是“公地悲剧”:如果牛没有被排除在公共草场之外放牧,那么大量的牛可能会破坏公共牧场,尽管每一头牛只有很小的竞争性消费。其次,在既定的政治、社会、文化或其他范围之外还存在大量不同种类的公共产品。例如,位于某一国家边界的核电站所产生的影响波及邻近的国家。一种公共产品的外延标准是这一公共产品对人与自然的影响范围。
第三,对公共产品的形式定义意味着,公共产品可以是“善的”(正面的)或“恶的”(负面的)。①积极的或正面的公共产品的例子有物理基础设施、获得重要信息(透明度)、法治、基本医疗保健和教育、社会资本(对人际关系和社会机构的信任)、人权(公民的、政治的、经济的、社会的、文化的),相对无腐败的企业实践、相对无冲突的(和平的)环境、安全的交通运输系统、创新的自由先决条件等。关于负面的公共产品(“公共恶品”)的例子,包括多种形式的环境退化、腐败、军事冲突、流行病、失职的政府机构。例如,一个稳定、有效、公平和可靠的金融体系是善的公共产品,而另一个不稳定、低效、不公平和不可靠的体系是“公共恶品”。公共产品的这种两面性,当然通常并不那么清楚,但能促使甚至迫使那些受到公共产品/恶品影响的人(或那些受到影响的人的代表)采取立场并做出决策,形象地说这是因为他们坐在同一条船上。不仅要考虑正面公共产品的获益,还得考虑其机会成本。通过提供公共产品和防范公共恶品,公共产品的两面性对加强社会凝聚力来说,就既是挑战也是机遇。对进一步的研究来说,一个有趣的视角是下面这个问题:天主教社会教义如何用它的团结原则和辅助性原则为认清并解决公共产品问题提供重要指导的?
三、经济伦理学如何加强社会凝聚力?
在考察了企业和经济的目的以及公共产品对于财富创造所具有的重要意义后,至少就概念的简要澄清而言,对本文开头提出的问题的回答就在意料之中了。当然,最重要的答案必须在实践中才能给出。
我们将企业和经济的目的定义为全面意义上的财富创造。它涵盖了所有与经济有关的私人资产与公共资产,包括自然资本、经济资本、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因此,它比利润最大化更具实质性,比所谓的“价值创造”更为准确。 公共产品对公共财富的重要性尤为突出,在我们今日的公开辩论中,对这些真正的公共事务的理解力正在消失,它威胁并破坏了社会凝聚力。而这一危险的发展由于全球化所带来的巨大挑战,正变得特别具有威胁性。
然而,尽管面临这些挑战,经济伦理学并非无能为力。它能够用多种方式加强从地方到全球层次的社会凝聚力。我辨明了以下三组机遇和任务:关于财富的实质性概念、公共财富的形式概念以及将人权作为公共产品的理解。②这些观点与世界宗教的积极参与在另一篇文章中作了进一步的阐发。参见G. Enderle,“Three Major Challenges for Business and Economic Ethics in the Next Ten Years:Wealth Creation,Human Rights,and Active Involvement of the World's Religions”,Business and Professional Ethics Journal,Vol.30,No.3—4,2011,pp.229—249。
(一) 创造自然资本、经济资本、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
正如经合组织关于福祉的报告(2013)①OECD. How's Life?2013. Measuring Well-being,2013.所解释的,在考虑这些资本在全体居民中的分配时,福祉的可持续性要求长期保存所有这四种资本。经济伦理学应从这个重要的框架中得到启发,无论是在经济学科还是在企业和经济实践中,坚持提出企业和经济的目的问题,并在所有个人、组织和制度层次上,提供深思熟虑后的答案。企业和经济的目的问题关乎财富“创造”(意味着创造新的和更好的东西),换言之,关乎“企业和经济中的伦理创新”②G. Enderle & P. E. Murphy(eds.),Ethical Innovation in Business and the Economy,Cheltenham:Edward Elgar,2016.。更具体地说,伦理创新适合每一种资本的伦理创 新。
(1) 自然资本的创造:也就是减少自然资源消耗和环境负担,对此必须要认真对待,在诸如消费者这样的个人行为者层次,企业、投资公司和消费者组织层次,以及制度层次上,由可持续性文化、可制定和实施的环境法和监管一齐来推动。
(2) 经济资本的创造:除了许多其他的挑战外,还需要将金融服务业与实体经济重新整合,以便在财富创造的整体意义上(重新)发挥服务性作用。
(3) 人力资本的创造:医疗保健和教育系统不应被先入为主地视作国家的巨额开支。它们反而应该被视为提高人民的健康和教育水平的有效投资。
(4) 社会资本的创造:意味着通过诚实的经济行为来加强和扩大人际关系的信任,同时,这也需要以公平和有效的制度来保证。
(二) 培育对公共财富的全面理解
经济伦理学应系统地研究并阐明公共财富的核心重要性,并证明其对创造自然、经济、人力和社会资本的相关性。
(1) 为了更好地理解公共财富,应该澄清和深化公共产品概念。要公开地探讨和阐述这个概念中所隐含的结构性前提和后果。对公共产品的创造所必要的制度和动机应该进行广泛的讨论。
(2) 由于公共产品的定义具有形式的性质,即具有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因而对它们的伦理评估是不可或缺的。“善的”公共产品”与“恶的”公共产品应该是可加区别的。(3) 因为一个社会的财富被认为是私人财富与公共财富的结合,所以至关重要的是,理解这两者之间的相互依赖性和达到两者之间的合理平衡。需要澄清两种基本制度的潜力和局限性,并且考察从地方到全球层次上的私人财富的创造所需要的市场与公共财富的创造所需要的集体行动 者。
(三) 从概念上理解并保障作为公共产品的人权
为了加强一个社会的凝聚力,一般来说,经济伦理学有助于创造全面意义上的财富,同时特别促进公共财富。更具体的,我建议从概念上将人权理解为具有伦理约束力的“善的”公共产品。
对人权特别关注的原因有多种。在全球化过程中,经济和企业已经扩展到国界之外,并日益在国际和全球的层次上联系了起来。在这一过程中,不仅私人产品而且公共产品的领域也急剧扩大了。随着这种扩大,对企业和经济的普遍规范标准的需求也在增大。自从1948年《世界人权宣言》发布以来,人权的伦理(和法律)框架已发展成一个广为接受的普遍的伦理框架,尽管并非毫无争议,但没有类似的可替代框架。而且,新千年以来全球对企业与人权的关切已大大加强。
根据这一联合国框架及其在约翰·鲁格(John Ruggie)2005年至2011年领导下开发的《联合国企业与人权指导原则》,人权已成为明确界定的全球企业责任(即组织层次的经济伦理)标准。(当然,这并不能免除在不同层次上国家和其他行为者各自的责任。)在由鲁格的团队与企业界、公民组织和来自多领域的专家,数次世界范围的磋商而得到支持的多项国际协约和公约基础上,确定了30项人权与企业有关①United Nations (UN),Promotion of all Human Rights,Civil,Political,Economic,Social and Cultural Rights,Including the Right to Development. Protect,Respect and Remedy:A Rramework for Business and Human Rights.Report of the Special Representative of the Secretary-General on the Issue of Human Rights and Transnational Corporations and Other Business Enterprises,John Ruggie. Human Rights Council. Eighth Session,A/HRC/8/5,2008.:公民权利、政治权利、经济权利、社会权利和文化权利,包括发展权利。2011年,联合国发布了《联合国企业与人权指导原则》②United Nations (UN),Guiding Principles on Business and Human Rights:Implementing the United Nations “Protect,Respect and Remedy” Rramework. Report of the Special Representative of the Secretary-General on the Issue of Human Rights and Transnational Corporations and Other Business Enterprises,John Ruggie. Human Rights Council. Seventeenth Session. A/HRC/17/31,2013.。从那以后,该原则似乎获得了越来越大的推动力。鲁格在其著作《正义企业》③J. G. Ruggie,Just Business:Multinational Corporations and Human Rights,New York:Norton,2013.中,对这些发展以及最新影响作了很好的描 述。
我的提议是,在本文做出这些考虑后,从概念上将这30项人权理解为“善的”公共产品可能就比较容易了。非排他性意味着,没有一个人应当被排除在任何一项人权之外。换言之,所有人都应该可以享有所有人权。非竞争性意味着,一个人享有任何一项人权不应当减少另一人享有这项权利;而且意味着,不同人权的享有不应当与其他人的享有相冲突。换句话说,人权之间的取舍是不可接受的。例如,参与政治的权利不应妨碍思想、良知与宗教自由的权利,反之亦然;又如,结社自由的权利不应对非歧视权利造成否定性影响,反之亦然。
除了排除负面影响外,人们还可以论证说,自己或任何人对任何一项人权的享有可能都不影响他们对其他人权的享有。例如,行动自由的权利可能不会影响免于酷刑的权利。而且,某一项权利的享有甚至还可以增进对另一项权利的享有。例如,适当生活水平(包括食物、衣着、住房和最低收入)的权利与工作权利和受教育权利可以相互加强。
人权作为伦理性要求的公共产品这一定义,显然对各个国家和政府间组织具有深远的影响,因为它需要在多层次上的集体行动(这是超越本文范围外的一个广泛话题)。就目前而言,我们将简要概述由《联合国指导原则》定义的“企业责任”的三个含义①关于联合国企业与人权的框架及其指导原则的广泛讨论,参见G. Enderle,“Some Ethical Explications of the UN Framework for Business and Human Rights”,in Sustainable Development:The UN Millennium Development Goals,the UN Global Compact,and the Common Good,edited by O.F. Williams,Notre Dame:University of Notre Dame Press,2014,pp.163—183。。首先,跨国公司和其他企业“有责任尊重人权”,并且帮助“纠正侵犯人权的行为”,而不是“保护人权”(这是国家的“义务”)。换句话说,企业除了生产私人产品外,还必须为这种公共产品做出贡献。其次,对公共产品的贡献需要超越企业的利己动机而包含利他动机。并不存在预先建立的和谐机制,能够调整专门利己的行为,以便一般地生产公共产品以及特殊地尊重人权(见上述对开明的利己主义的批评和格林斯潘的承认)。第三,对公共产品的贡献不只是对社会的某种“慈善捐赠”(或“份外事”)。相反,某些公共产品(如法治和人权、社会习俗、技术知识、教育技能和健康条件)实际上是生产私人产品的先决条件。因此,企业有道德义务承认这些来自社会的投入并“回馈社会”,包括尊重人权和纠正侵犯人权的行为。用这种方式,将社会财富理解为私人财富与公共财富的结合,可以明晰并加强企业的人权责任。我们的社会凝聚力受到来自从地方到全球不同层次、多种方式的威胁。本文中,我已试图表明,为应对这一挑战,经济伦理学如何能够做出尽管有限但是重要的贡献。对企业和经济目的这一至关重要的老问题,可以有一个崭新的丰富答案,这一答案提出了全面意义上的财富创造,包括自然、经济、人力和社会资本,并且提出了特别意义上的公共财富。我们已经讨论了凝聚社会的不同方案:开明的利己主义、新博弈论方案以及天主教社会教义所倡导的共同善概念。我个人的提议是,公共产品的创造和维护为社会凝聚力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在财富创造的目的和公共产品的重要意义的指导下,经济伦理学可以展开令人兴奋视角下的整个事业,通过创造全面意义上的财富特别是聚焦公共财富来加强社会凝聚力。就更具体和清晰定义的规范伦理学任务而言,我的结论是,按公共产品的概念来理解人权。实际上,经济伦理学正面临着令人兴奋的新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