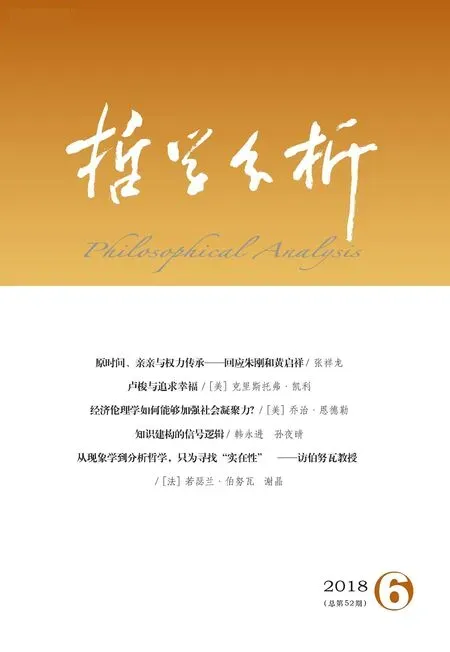卢梭与追求幸福
2018-01-23克里斯托弗凯利文曾誉铭
[美]克里斯托弗·凯利/文曾誉铭/译
一
卢梭著作等身且品类繁多,有论文、专著、小说、戏剧、词典,甚至寓言故事——人们不知道从何处开始讨论他的著作。我所讨论的这个主题贯穿于他的那些不同类型的著作。我引用的一些文献就连许多卢梭研究者都知之甚少。但人们对这个主题再熟悉不过了——追求幸福。像我自己这样的美国人从我们的建国文件《独立宣言》中就熟悉这个主题。《独立宣言》中说“人人生而平等”,而且他们对“生命、财产和追求幸福”有不可转让的权利。当然,美国并不是关心追求幸福的唯一民族。没有人能不关心这个问题。
我想用旅行至此做这个演讲的经历来开始这个主题。我习惯早起,5月11日,在波士顿的家里,我大约5点起床,费了些时间做出发前的准备,并在早餐后离家去机场。在那里,我经历了大家都熟悉的过程,办理登机手续、安检,最重要的是等待。然后,我在飞机的密闭空间里经过十几个小时才到达北京。在我办理入境手续时,又是再次等待。当我到客房时,一天多的时间已经逝去了。在数天时间里,我将重复这个经历。所有这些根本就不值得人们在意。但我不得不承认,如果没有美好未来的愿景,我们就不会想要这个经历。没有好的理由,我当然也不会做这件事。幸运的是,东道主的热情款待证明我的付出是值得的。让人印象深刻的是,那么多人自愿展开像这样的旅 程。
这个经历让我想起自己与一个美国商人及其妻子的交谈。因为生意的原因,后者在两年时间里一直生活在巴黎。她不想在巴黎待两年!这对夫妻对巴黎爱恨交加——他们因生意和家庭原因要不断来回跨越大西洋。他的妻子告诉我,她希望在自己离开公寓时不省人事并在十小时后到行程目的地时才醒来。我认为,我们所有人都有过同情这种愿望的经历。那就是我们渴望抵达我们的目的地,但我们又害怕去那里的这种经历——我们期待结果,但怕走向它的这个过程。
现代人的独特性在于我们自由地反复选择将自己置身于这种境地。的确,当我们不在其中的时候,当我们被迫静静地坐等太长时间的时候,我们甚至会变得不舒服。大约200年前,在让他写出《论美国的民主》的访美期间,亚力克斯·德·托克维尔就注意到了我们生活的这种特征及其独特性。他说令他震惊的事情之一是,尽管美国人处于所谓的“在世的最幸福境况”中,事实上,他们似乎并不幸福。这种情况的基本原因是,与享受他们可以获得的东西相反,他们时常认真地不断追求他们没得到的好东西。托克维尔这样来描述他观察到的这种不停的活动:“在一年劳作结束后他仍有闲暇的时候,在美国的广袤大地上,[美国人]到处打发他不受管束的好奇心。为了使自己从幸福分心(distract himself from his happiness),他进而会在几天内走五百里路。”①Alexis de Tocqueville,Democracy in America,translated and edited by Harvey C. Mansfield and Delba Winthrop,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2000,p.512.自从托克维尔写下这些以来,事情并未改变过,或者如果它们改变了的话,也只是强化了他的观察的真理性。一个普通美国人的经验会是,度假归来的人准备告诉每个人他们每天走了多少英里,而不是他们有什么有趣的经历或他们看了什么美景。现在,我的任务是阐述卢梭对这类追求幸福之意义的解释。为此,我不再谈自己的旅行以及美国人的生活特征,并最终回到卢梭。
在卢梭快40岁的时候,他已历经沧桑,但得到的实实在在的东西很少。他将自己的时间花在无用工上,有钱时去戏院和音乐会,还与朋友们在咖啡屋消磨时光。他的生活似乎是某种可能的现代生活典范之一。然而,在同一时期,他也在思考与学习。一旦他变成一名活跃的作家和作曲家,在数年里,他就因其论文、戏剧和小说而声名鹊起。他是我们所知的最早的文学名人。在声名鼎盛时,他被淹没于那些素未谋面的读者来信之中。一些人想要得到推荐信,让自己迄今未被认可的德性得到回报。另一些人则希望得到一个回复,那会让他因为与一个名人——想想得到一个著名作家的信件会是什么样子——的亲密关系而让朋友刮目相看。然而,一些人——主要是女人和年轻人——写信给卢梭,那是因为他们相信,他会给他们在其他地方得不到的东西。在接近《爱弥儿》——卢梭论教育的书——结尾的地方,老师对他虚构的名叫爱弥儿的学生说:“亲爱的爱弥儿,你一定要幸福。那是每个有感知的存在者的目的。那是自然施加给我们的第一欲望,而且是从未离开我们的唯一欲望。但是,幸福在哪里,谁知晓它?①Jean-Jacques Rousseau,Emile,Collected Writings of Rousseau,Vol.13,edited by Roger D. Masters and Christopher Kelly,Hanover,NH:University Press of New England,2010,p.630.该版本将引作 CW。人们不应简单地认为这是卢梭的观点。参见Fragment 21,in CW 12:279。在研究他的著作时,卢梭的许多读者得出最后这个问题“谁知晓它”的答案是:“让—雅克·卢梭”。在他们的阅读以及与卢梭的通信中,关键的事情是他们生活的幸福。对这样的读者来说,卢梭要么提出了一个他们从未思考的问题,要么重新打开了据说是封闭性的问题:在这一生中,幸福原则上是否可能。正如卢梭所做的那样,提出这样的可能性就是创造一种要求获得满足的渴望。在感受这种渴望的时候,那些读者们要求从他那里得到满足。现在,卢梭的著作碰巧提供了许多可能的方向,在其中人们可以追求幸福——宗教、政治、爱、家庭,等等。我的任务是探索那些方向中最独特、最有影响力的一个——那似乎会为我们评判其他方向提供一个标准。让我们在反思他意在解决的问题的过程中来靠近卢梭的立 场。
在卢梭的读者们将其视作谈论幸福问题的专家时,他当然远不是18世纪讨论幸福的唯一作家。他自己抱怨道:“所有的书给我们讲至善,所有的哲学家把它展示给我们,彼此传授幸福的艺术,但没人为他自己找到它。”②Jean-Jacques Rousseau,Autobiographical,Scientific,Religious,Moral and Literary Writings,CW 12,edited and translated by Christopher Kelly,Hanover,NH:University Press of New England,2007,p.180.所有那些书提出的幸福的艺术是空洞的,因为那些哲学家不曾将幸福问题置于合适的立足点,实际上他们没有严肃思考这个问题,因为他们仅仅为出名而写作。作为领会卢梭的幸福观的十分初步而必要的一步,我想分析他碰到过并将其论述奠基于其上的一种重要的哲学解释。然后,我想看一看卢梭回应过的他的某些同时代人或其前辈类似的幸福解释。我想阐明他力图解决的问题并确定其解决方案的典型性——这是他的解释如此吸引读者的原因。
二
我们先来看一些文本。卢梭的著作《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的一个注释中有他论证过并且后来被称为其“伟大原则”的最初的清晰论断:“人天性是善良的。”①Jean-Jacques Rousseau,Rousseau Judge of Jean-Jacques:Dialogues,CW 1,edited by Roger D. Masters and Christopher Kelly,translated by Judith R. Bush,Christopher Kelly and Roger D. Masters,Hanover,NH:University Press of New England,1990,p.213.正是在这个注释中,卢梭言之凿凿地解释了他自己的主张,即人类不幸的根源是社会处境而不是自然或上帝。这个注释开始于描述其自然至善论所反对的立场:“一个著名作者衡量了人生的幸福与痛苦,并从量上将它们进行比较,发现痛苦远远超过幸福,而且考虑到所有东西,生命于人类是一件很坏的礼物。”②Jean-Jacques Rousseau,Second Discourse,CW 3,edited and translated by Judith R. Bush,Roger D. Masters and Terence Marshall,Hanover,NH:University Press of New England,1993,p.74.那么,卢梭自己的新自然至善论的原初意义并不是说人类天生就是道德的,而是生活对我们是好的,它并非“一件很坏的礼物”。这个段落提到的著名作者是皮埃尔—路·莫勒·德·莫佩尔蒂。卢梭在“第一篇论文”③即《论科学与艺术的复兴是否有助于使风俗日趋纯朴》。——译者的其他地方赞扬过他。卢梭赞扬了莫佩尔蒂的科学研究,而后者的确是一位非常著名的科学家。今天,他最为人知的是天文观测以及证明地球在两极而非赤道是扁平的计算。像许多科学家一样,莫佩尔蒂认为,让他解答问题的科学方法可以用来解决政治与道德问题。相应地,他并不将自己的研究限制于自然科学,他试图将自己的计算法应用于其他问题。他写了一系列著作,用计算法解决各种各样的问题。那些著作中有一些是严格科学的并运用了可利用的最复杂的数学技巧。当那些技巧超过莫佩尔蒂自己的能力时——他是一个更好的探索者而非数学家——他就询问欧洲最有才能的数学家。在其他情况下,他使用不伴随复杂计算的微积分语言来增强自己得出严格结论的感觉。④至于莫佩尔蒂生涯的叙述,参见Mary Terrall,The Man Who Flattened the Earth:Maupertuis and the Sciences in the Enlightment,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2002。有点奇怪的是,在这项很全面的研究中,作者对莫佩尔蒂的《论文》(下面讨论)什么也没说。
在卢梭参考过的他的《道德哲学论文》 (初版于1749年并在卢梭写下“第一篇论文”六年后很快再版)中,莫佩尔蒂计算了善与弊(goods and evils)。卢梭简短提及莫佩尔蒂似乎是试图为他的另一个观点提供方便的陪衬,但如我接下来要证明的那样,在他随后的著作中,评价根据善与弊计算的人类幸福是一个反复出现的主题。使莫佩尔蒂得出他的悲观结论——“考虑到所有东西,生命于人类是一件很坏的礼物”——的那些计算是什么呢?在《道德哲学论文》中,他在数学上将幸福冠冕堂皇地定义为“在人们抽掉弊端的总和后留下的善的总和”⑤M. de Mauperuis,Essai de philosophie morale,Oeuvres de M. de Mauperuis,Lyon,Chez Jean-Marie Bruyset,1756,Tome I,p.197.在文本中引作 Maupertuis。。人们可能认为,不同的生活会产生非常不同的善的总和,蓬勃健康的人生将十分不同于疾苦的人生。但莫佩尔蒂认为,通过将人生划分为欲望和欲望的满足,他就能得到普遍有效的加减。每个人都会经历这种划分。如果幸运的话,在形成欲望后,我们会满足它。在那两个环节中间,或多或少有一个我们没有得到满足的长间隔(interval),因为我们在竭力实现一个我们尚未满足的欲望。莫佩尔蒂的关注点在这个间隔上。他认为,我们会希望消除欲望与满足欲望之间的间隔,他说道:“我们经常会想要缩减年月日。”①M. de Mauperuis,Essai de philosophie morale,Oeuvres de M. de Mauperuis,Lyon,Chez Jean-Marie Bruyset,1756,Tome I,p.202.事实上,如果我们抑制或减去这些间隔——另一个数学术语,我们就会发现,“也许最长寿命的整个延续将减少到几个小时”。这是追求幸福的含义:非常乏味地冒险追求微不足道的幸 福。
莫佩尔蒂提出这个有趣的问题来证明他的间隔观:多少人愿意再活一回?他用这个问题不是指有机会用我们获得的知识来纠正我们所有的错误,并使事情的结果不一样,他指的是再活一回,正如它充满苦乐、得失。他的结论是,如果你问任何一个人,“在任何情况下是否人们都可能这么做”,只有极少的人“想要如其曾经历的那样再次开始他们的人生,他们想要再次经历所有这些相同的境况,他们在其中找到了他们自己”②Maupertuis,p.204.。想想无聊与挫败的那么多间隔和真正快乐的极少瞬间!莫佩尔蒂说,这种几乎是普遍的不愿意经历自己一生,就是“人生由更多痛苦而非幸福构成”的“最清楚的证明”。
现在,大家可以明白我的旅程以及我与生活在巴黎的商人及其妻子交谈的要点了。莫佩尔蒂请他的读者思考所有情况,在其中,他们希望自己可以不省人事几小时或许多岁月,而不必留意等待到达他们目的地的感受。想一下那些设备——卢梭富有洞见地将其称为“幸福或快乐的大量机器”③Jean-Jacques Rousseau, Rousseau Judge of Jean-Jacques:Dialogues,p159.,我们发明它们来帮助自己跨过这段时间,我们殚精竭虑来创造幸福或快乐的小机器。有趣的是,我们发明的那些设备(如智能电话或者平板电脑)是否在间隔内让我们去做有趣或有价值的事情,或者我们发明它们只是让我们分心,得以更能容忍那些间隔,换句话说,麻醉自己。
莫佩尔蒂没有回避自己论点的必然结论。他赞扬古代斯多葛派所承认的“只要痛苦的总和超过幸福的总和,虚无比存在更可取”④Mauperuis,p.227,pp.224—225.。不管斯多葛派用“只要”指什么,莫佩尔蒂用他自己的名义说:“如果此生之外什么也没有,那么结束它通常是合适的。”⑤Mauperuis,p.189.当然,他知道大部分人不会根据这个结论行动。为了解释我们继续发现这种生存可以忍受的原因,他更深入地对人类境况作了诊断。这个诊断是,所有人——在不能满足的幸福欲望之普遍的自然原则下行动——毕其一生寻求他称所称的“活着的疾病药方”。在仔细审视时,他们承认自己虚度光阴,甚至追求快乐也只是恶化了这种境况。结果,对大部分人而言,幸福的欲望只会导致沉沦于“证明他们不幸境况”⑥Ibid.,p.203.的消遣(diversion)。莫佩尔蒂对这个问题的讨论是有趣的并且可能与我们某些人有共鸣。他注意到,一些人玩游戏,其他人打猎,所有人在严肃或无聊的职业中寻求忘记自己。莫佩尔蒂说,长远来看这么做必定失败,当这些消遣(distraction)的努力失败时,人们喝酒或用毒品来寻求解脱或麻醉自己。普遍追求消遣(distraction from oneself)或麻醉形式的解脱证明,尽管这些人可能避免面临莫佩尔蒂的悲观计算,但他们还是感受到了它们的真理性。
莫佩尔蒂提供了他所知道的治愈不了但可以治标的两套方案。在因其自杀立场而赞扬过斯多葛派之后,他也认为部分人看到了一个可选项。他们看到,追求幸福只会增加欲望与满足欲望的间隔中的不快,从而得出结论说,严格限制欲望是舒缓“活着的疾病”的方法。我们应该限制我们对幸福的追求,不是因为节制本身就是一个好东西,而是因为这种追求是那么令人沮丧。莫佩尔蒂会赞同我们将这个限制性条款称为斯多葛式享乐主义,即只要厌倦生活了,人们就应该准备结束它。
正如它实际上所导致的那样,在明白这个建议会使人们指控他写下“不虔诚之作”的时候,莫佩尔蒂总结道,以两章论宗教作为结尾的《道德哲学论文》会使某些读者认为此书是“一本虔诚之作”①Mauperuis,p.182.,那是他也试图避免的一种指控。在论证赞同人生内在痛苦的观点时,他在完全非宗教的基础上为基督教辩护。即使禁止自杀是对这种治疗方法的魅力的承认,他还是认为,基督教的神意观是提供了合理实现幸福愿望的唯一智慧(the only understanding)。事实上,即使基督徒的救赎希望建立在一个幻想之上,在他的计算中,它也能增加幸福的总和。借助基督教的一个赌赢了的例子,莫佩尔蒂含蓄地重新计算了帕斯卡尔的著名赌注。不管这种宗教是真的还是假的——如果它是真的,我们收到了我们信仰的奖赏;如果它是假的,我们已经几乎像我用物理鸦片般将自己从我们境况的痛苦中分离。
莫佩尔蒂的《道德哲学论文》当然是有一些奇怪的元素。然而,卢梭对它特别的参考明显意味着,他认为,它的分析是更一般的立场所具有的症状。不难发现这是真正的证据。数年后,当卢梭在《致伏尔泰的信》中说到一位更著名作家的时候,他回应了莫佩尔蒂。在《忏悔录》中,卢梭确定了他与伏尔泰的争论中利害攸关的核心问题,在比较伏尔泰飞黄腾达的人生——伏尔泰很精明地利用自己的文学名声发财——与他自己悲苦的人生时,他使用的语言使人想起他对莫佩尔蒂计算人生幸福痛苦的讨论。他说:“比伏尔泰有权威的是计算与权衡人生的罪恶。我公正地检查了它们,并且我向他证明,没有一种罪恶是上帝不赦免的。”②Jean-Jacques Rousseau,The Confessions and Correspondence,Including the Letters to Malesherbes,CW 5,edited by Christopher Kelly,Roger D. Masters and Peter G. Stillman,Hanover,NH:University Press of New,1995,pp.360—361,see Letter to Voltaire,CW 3,edited and translated by Judith R. Bush,Roger D. Masters and Terence Marshall,Hanover,NH:University Press of New England,1993,p.120.在这封信中,通过阐释他的立场的创新性,他为自己对这个问题——是否“活着而不是死对我们更好”——的肯定回答加了个开场白,“但在这个主题上,很难在人们中间找到任何好的信仰,从哲学家中找到好的计算”①Jean-Jacques Rousseau,Letter to Voltaire,p.120.。正如在“第一篇论文”中那样,这里的问题是恰当的计算。从“第一篇论文”到《致伏尔泰的信》以及其他文章,卢梭拓展了他的目标。它不再是某个著名作家犯了计算错误。的确,卢梭的构想暗示,莫佩尔蒂所犯的错误具有一般哲学家的特点:他们没有人在这个问题上做过任何好的计算。莫佩尔蒂的结论——生命是“人类很坏的礼物”——被卢梭视为一种普遍立场所得出的结论,并在《致伏尔泰的信》中公开反对它,他说:“无论疾病可能会给人类传播什么,考虑到所有事情,它并非一件坏礼物。”②Ibid.,p.112.
卢梭指责莫佩尔蒂及其赞同者的错误既不是其单纯的计算错误,也不是他们对人类生活单纯的错误描述,而是他们在描述人类的自然条件及对我们而言事物的必然存在方式时描述了我们目前生活于其中的社会类型的特征。在卢梭的著作中,这是一个很常见的主题。在《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的其他地方,他同样指责了霍布斯及其他人。考虑到其错误的相似性,我们对在霍布斯那里发现这个经典的论述并不感到奇怪,不是莫佩尔蒂做出的精确计算,而是它们的根本前提有问题。在意在抹黑传统的幸福解释多个段落之一中,霍布斯说:“此生的幸福,不在心灵满足的宁静,因为既没有终极目的(Finis ultimus),也没有至善(Summum Bonum),就像在旧道德哲学家的著作中说的那样。当欲望耗尽的时候,一个人不能比感觉和想象停止(be at a stand)的人活得更多。幸福是这种欲望的联系过程,从一个对象到另一个对象,前者的获得不过仍是后者的手段。”③Thomas Hobbes,Leviathan,Chapter 11,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9.最后这个论断是关键的,“幸福或者快乐,是欲望从一个对象到另一个对象的连续过程”。并不存在由真正的满足构成的幸福。霍布斯与莫佩尔蒂反对基于持续满足的任何善的观念之上的幸福解释。
他们之间的差异主要在于,霍布斯愿意将我们在没有任何持续满足的情况下从欲望到欲望的境况描述为幸福,但是,莫佩尔蒂可能接受霍布斯的著名观点:生活不过是“无尽的追逐权力的权力欲,它至死方休”。正如我此前所暗示的,他不承认幸福是可应用于这种生存的术语,他更愿称之为“活着的疾病”,这种差异看起来可能小,却的确导致了一个实际的结论,即霍布斯既很愿意忍受永不满足的欲望,同时又对即便是享乐式斯多葛派的保守性也不那么乐观。他否定的是:我们不可能为防止欲望受挫而对其加以限制,我们的欲望不服从这种理性控制。
莫佩尔蒂与霍布斯的共同点贯穿于启蒙思想的重要内容中。例如,约翰·洛克是从霍布斯到伏尔泰的桥梁——他给了我们有关追求财产与追求幸福的术语。在讨论人类如何以不同的方式追求幸福时,洛克认为:“旧哲学家们徒劳地研究,不管至善是否在于财富或身体快乐、德性或沉思;他们可能已经合理地争论过:不管是否会在苹果、铅锤或坚果中找到最好的享受,他们在此将自己划分为不同的阵营。”①John Locke,An Essay Concerning Human Understanding,II.XXI.55. 斯蒂芬·埃德(Stephen Eide)已经向我指出,洛克对否定至高善非常谨慎。参见Essay,IV.XII.11。在《哲学辞典》中,伏尔泰实际上在自己的文章《善,至善》中将这个段落转化成了他自己的风格,使他直言不讳地反对霍布斯所称的旧道德哲学家及洛克所称的旧时代哲学家。他宣布:“古代对至善做了大量争论,它本来就像是追问:什么是至高的蓝或者至高的炖肉、至高的散步、至高的阅读,等等。”②Voltaire,Philosophical Dictionary,translated by Peter Gay,New York:Basic Books,1962,p.114.他断言,由于两个原因,至善成了一个幻想:第一,它因人而变;第二,它在任何人那里都不能持续片刻。然而,伏尔泰不太同情斯多葛派或基督教对莫佩尔蒂推荐的人类境况的回应。实际上,可以将伏尔泰与其他人的方法描述为对这种症状的利用,莫佩尔蒂将其确定为人们无意识地承认他的幸福计算的真理性的证据:他们试图在摆脱和减轻痛苦中找到“活着的疾病”的药方。简而言之,这种版本的启蒙将娱乐(entertainment)和药物提升为最重要的人类追求。对许多现代人来说,这些是最重要的东西。在卢梭看来,这些尝试只会恶化这个问 题。
让我们考虑一下“减轻”与“摆脱”这两种药方。当然,在生活中,我们大部分人致力于减轻我们自己和他人的痛苦。我不会花很多时间在这个问题及与之相关的追求舒适上。在论证如何让经济运行和申请资助医疗的研究中,我们当然会在我们身边到处看到这点。
这些论点的前提是:舒适是好的,而不适则是糟糕的。人们会问,那是否是唯一的甚或最重要的幸福与痛苦,而不是详细讨论这样一个重要的观点:它更有利于我在这里强调消遣或娱乐——这是在我们的现在的日常生活中更熟悉的一个主题,即便我们很少反思它——的论述。有关公共资助要在日内瓦建一座剧院的争论中,娱乐或消遣是区分卢梭与伏尔泰及达朗贝尔的问题之一。达朗贝尔(部分是讨好住在日内瓦附近的伏尔泰)鼓励那个城市建一座公共资助的剧院。的确,像许多艺术支持者那样,达朗贝尔认为,剧院会是道德完善的源泉,而重要的是他指出,在他们的争论中,他(而不是卢梭)才是审查制度的辩护者。如果艺术的目标是道德完善,那么就很难反对审查制度以确保他们实现那个目标。没有人相信宣称是艺术品的一切东西都能产生好的道德效果。我们怎么处理那些不产生好的道德效果的艺术品呢?然而,除了他的道德完善的观点外,达朗贝尔还友好地对待没有承诺道德完善的娱乐形式。当卢梭攻击剧院是无用的娱乐时,达朗贝尔回复道:“生命如此不幸而快乐如此稀少!为何吝惜去帮助天生注定几乎只有哭泣和死亡的人们忍受生存之苦或获得某些稍纵即逝的乏味娱乐呢?”①Jean-Jacques Rousseau,Letter of M.d' Alembert to M. J.J. Rousseau,CW10,edited and translated by Allan Bloom,Charles Butterworth and Christopher Kelly,Hanover,NH:University Press of New England,2004,p.356.的确,他甚至认为剧院都不够令人快乐(diverting)。生命由“对自己和他人的不满、欲望行为与焦虑的天性懒散倾向的结合”②Ibid.构成这一事实会让我们看到,我们应该为了它自身而改善娱乐,而且我们应该寻求特别令人快乐的娱乐。它应起到这样的作用:缓解“折磨我们的躁动或它给我们提供消遣来消除我们的怠惰”。在莫佩尔蒂看到“活着的疾病”的症状的地方,达朗贝尔——而且不仅仅是达朗贝尔——看到了对这种疾病的治疗。的确,达朗贝尔担心的是,剧院太平和了而不能让我们分心。我们真的需要更有活力的娱乐来分心。我们不知道达朗贝尔会怎样看待曲棍球和暴力电影。无论如何,他的看法表明,知识分子的合适作用是:推进有助于人们追求减轻并摆脱其不幸的那些娱乐。正如传统认为追求幸福是徒劳的那样,认为幸福不可能的那些相关叙述形成的这条线索有助于指明启蒙运动方案(通过逐渐掌控自然来救赎人类)可以缓解我们对生存的不满——提供暂时安慰的物质上的舒适以及使我们摆脱无聊生活的娱乐。在所有类似的解释中,人们扮演追求幸福的角色,但没有人成功地实现了幸福。但卢梭认为,只追求片刻的安慰和分心,仅仅是一种恶化了这种疾病的体验。然而,这并非莫佩尔蒂所说的“活着的疾病”,而是现代文明生活病。卢梭反对基于它得出那些结论的计算。
三
为了让我们以后过得舒服而工作是未雨绸缪,而为了使我们自己从乏味的生存中分心去寻求娱乐意味着让我们偏离自身。这两者都涉及将注意力转向自身之外的东西。也许并不奇怪的是,卢梭提出的这些解决方案涉及使我们转向当下和我们自身。他的反对者会认为,这只会让我们不幸或更加意识到我们的不幸。卢梭对此是不是必须说点什么呢?简言之,他的方案是用当下的享受代替追求安慰,用新的关注我们自身代替从我们自己分心。
莫佩尔蒂计算的关键要素是欲望与满足欲望之间的“间隔”,我们想看到被消灭并几乎组成我们所有人生的这种间隔。通过诉诸卢梭并没有否定的一种经验,莫佩尔蒂建立了生存与这种间隔的范围。在《爱弥儿》中,卢梭使用了惊人地相似的语言:“由于他们时时刻刻都在向往一个目标,所以他们常常伤心地看到他们和目标之间隔着一段距离,这个人希望明天这样生活,那个人希望下个月这样生活,另一个人又希望十年以后这样生活,其中就没有哪一个人会考虑今天怎样生活。”③Jean-Jacques Rousseau,Emile or On Education (includes Emile and Sophie;or the Solitaries),CW 13,edited and translated by Christopher Kelly and Allan Bloom,Hanover,NH:University Press of New England,2010,p.593.在该段更早的草稿中,他甚至对面临漫长上班路程的人们特别做了更严格的计算。“我认为,他们每次旅程只投入一个小时。我还认为,他们能随意从一天中删除一小时,以至于当他们离开两个城市之一的时候,他们就抵达另一个城市了,而间隔被压缩了。我要说,他们当中没有人会接受这个提议,而且不会相信他已经获得了许多。我请问您,现在,他们会获得什么呢?一年缩短他寿命360个小时,也就是说每24年缩短一年。”①Jan-Jacques Rousseau,Emile or On Education (includes Emile and Sophie;or the Solitaries),p.151.在最终版本中,卢梭得出的结论甚至更极端,而且也和莫佩尔蒂的完全一致。他说:“如果一个人能随意消除他所感到的烦恼,能够随意消除使他急切等待所想望的时刻尽快到来的心情,如果能做到这些的话,也许大家都是愿意把寿数缩短成几小时的。”②Ibid.,p.594.结果,这种间隔的存在证明了生命的痛苦远远超过快 乐。
卢梭赞同莫佩尔蒂的看法,即追求安慰只会恶化这种间隔的经验。有时他也似乎临时推荐斯多葛式的以减少欲望作为保守性治疗的方案。欲望更少会有助于我们避免增加形成欲望与满足它之间的间隔。然而,精致的伊壁鸠鲁主义往往补充了卢梭偶尔达标的享乐式斯多葛主义。并非简单地鼓励为减少痛苦而减少欲望,卢梭认为,延迟而不是追求满足能经常增加快乐。就像他的伟大小说《朱莉》中的一个人物所说的那样:“圣人感官变得更敏锐,放弃更好的享受,那是你的哲学;它是理性的伊壁鸠鲁主义。”③Jean-Jacques Rousseau,Julie or the New Heloise,CW6,translated and annotated by Philip Stewart and Jean Vaché,Hanover,NH:University Press of New England,1997,p.544.让我们有点饿,而不是整个下午吃零食,我们会更好地享受晚餐。换而言之,卢梭用增加生存的乐趣代替了徒劳地追求幸福——即使在我们没有满足自己欲望的情况下。在《爱弥儿》中,在他计算间隔的末尾,卢梭说:“如果你们中间有个人知道如何控制自己的欲望,以至于他从未希望时间流逝,那么他就不会说生命太短暂了。活着与享乐对他是一回事。而且即使他英年早逝,他也会死得其所。”④Jean-Jacques Rousseau,Emile or On Education (includes Emile and Sophie;or the Solitaries),p.594.活着享乐代替了追求幸福或从不幸分心。卢梭描述的这个人不会简单地用限制欲望来减少间隔,他会用享乐填充剩下的间隔。这样的一个人是卢梭虚构的学生爱弥儿,卢梭说自己培养了他——不是“欲求或需要而是享受”。
在他评判莫佩尔蒂的观点及其后果时,卢梭并非独一无二。卢梭伟大的同时代人,与莫佩尔蒂友好的孟德斯鸠,在他所写的卢梭没有见到的注释中独立地提出了类似反对意见。他说:“德·莫佩尔蒂先生只是将快乐与痛苦纳入了他的计算,即告诉灵魂它的快乐或它的不幸的一切。他并未将生存的幸福与习惯性的快乐纳入它。它什么也没讲,因为它是习惯性的。”⑤Montesquieu,Mes Pensees in Oeuvres Complètes,Paris:Gallimard,1949,Tome 2,p.1267.这种习惯性的快乐或简单存在中的快乐,孟德斯鸠称之为“存在与自然”。他总结道:“并不必然要说,幸福是我们不会为了不一样地生活而改变的那个时刻;相反,幸福是我们不会为了不存在而改变的那个时刻。”他相信,我们甚少会选择不存在而不是简单存在的快乐。这些思考使孟德斯鸠得出了类似于卢梭的不同社会境况的结论,他甚至认为自然环境促进或抑制了我们的存在与自然经验——卢梭称之为“生存感”(sentiment of existence)。
四
我们可以说,享乐指学会在欲望与满足的间隔中享受,不满足使即使有限的享受也变得更敏锐。卢梭说,爱弥儿不但学会了享受欲望的满足,而且学会了享受欲望本身就像“进入欲望的对象”一样。卢梭似乎认为,甚至有可能享受想象的对象。如果我们学会正常生活,享受这个间隔及围绕它的条件(terms),就可能转向针对幸福的人生利弊计算。这种例子之一是,卢梭认为,我们可以并应该心情愉快地去旅行,而不是旅行时希望自己不省人事甚至心不在焉地到达我们的目的地。
在卢梭对“几乎没有人会想要在他们曾生活过的同样条件下重新生活”这个主张的回应中,人们可以看到这种转向。莫佩尔蒂曾经说过,他的立场,即没有人会想再活一回(这个主张是由伏尔泰、伊拉斯谟及莫佩尔蒂提出),是可以通过在无论任何条件下对人们做民意调查来加以证明。卢梭认为,这只是女人与知识分子的经验——长期抱怨自己不幸的两个群体。他诉诸不同的群体,即生活在法国与瑞士边界的质朴农夫:“我敢说,也许在上瓦莱州没有一个山人不满足于他几乎自由的生活。而且,他不愿为了永久过单调的生活而接受(即使是天堂)无休止地重生的这个买卖。”①Jean-Jacques Rousseau,Letter to Voltaire,CW 3,edited and translated by Judith R. Bush,Roger D. Masters and Terence Marshall,Hanover,NH:University Press of New England,1993,p.111.
在那些质朴者的例证上,他又加上“一位诚实的资产者”“一个善良的工匠”以及一位生活在自由乡村的农民。在那些情况下,不是一个假设的爱弥儿在充当反例接受特殊教育,而是认为他们的生活“不是一件坏礼物”的各式各样的人。
重新计算使卢梭再次思考自杀问题。像莫佩尔蒂一样,他再次支持斯多葛主义立场,即智者“在自然与命运很清楚地命令他离开的时候,自愿离开,没有低语,没有绝望”②Jean-Jacques Rousseau,Letter to Voltaire, p. 112.。然而,不像认为那些事情经常发生的莫佩尔蒂,卢梭坚信这种情况不常存在于“事物的一般进程中”。的确,如果莫佩尔蒂的计算精确,考虑到安慰、娱乐与麻醉的局限性,自杀会盛行,因而“人类不会长期存在下去”。对人类的延续而言幸运的是:“不管我们如何巧妙地借助于良好的制度挑起我们的不幸,迄今为止,我们都不能完善到这个地步,即普遍地使生活成为我们自己的负担并宁可要虚无而不是我们的生存。”③Ibid.卢梭再次主张,实际上大多数人用享受的经验代替寻求安慰。就像他后来所写的那样,他们能这样做是因为“甜蜜的生活享受是永久的,品尝它,就可以不吃亏”①Jean-Jacques Rousseau,The Reveries of the Solitary Walker,Botanical Writings,and Letter to Franquières,CW8,edited by Christopher Kelly,translated and annotated by Charles E. Butterworth,Alexandra Cook,and Terence E.Marshall,Hanover,NH:University Press of New England,2000,p.265.。总之,如果对人类的境况时常视而不见,享受而非不安或痛苦就是根本性的事。在很大程度上,我们没有意识到这点导致我们去做刺激的而不是减轻我们不安的事 情。
将富人及知识分子与那些能享受的人区分开来的是:“在人类的所有秩序中,它们是最安静的、最健康的、最具反思性的并且结果是最不幸的。”②Ibid.像伏尔泰自己那样,这些人“具备各种好东西”,但他们仍是不幸的,因为他们有满足自己手头的欲望的手段,欲望与满足之间的间隔应该是短暂的。即使这样,在娱乐与麻醉的形式中,他们是最积极寻求自我消遣的人们。
在卢梭最接近支持莫佩尔蒂的计算的著作的一个段落中,反思者明显感受不到幸福的可能性。早在《爱弥儿》第二卷中,他就断言,我们无法理解绝对幸福的意义,更不用说这种幸福的经验了。甚至在思考相对幸福的时候,他也说:“最幸福的人是受苦最少的人,最不幸的人是感受最少快乐的人。苦难总比享受多。”③Jean-Jacques Rousseau,Emile or On Education (includes Emile and Sophie;or the Solitaries),p.210.在这里,卢梭只是抱着“并非不快乐”或者“从快乐中获得的少”的希望,即便在这里,他的主张(即最不幸的人是感受最少快乐的人)也暗示某些积极的享受是可能的。当他不支持自杀的时候,他说,智者发现自己的死亡的必然性是对忍受生命之痛的安慰。在超越莫佩尔蒂“一件很坏的礼物”的生命解释时,他甚至说:“如果我们将在地球上获得永生,谁会想接受这件沉闷的礼物呢?”在这里,卢梭与他后来在该书中所说的矛盾了吗?考虑到人们可能会误解对哲学家们的计算的支持,卢梭在《爱弥儿》后来的版本中加了一个笔记:“不用说,我这里说的是反思者而不是所有人。”④Ibid.,p.742.这是否意味着,对那些反思者来说没有什么幸福可言,而且卢梭承认消遣与麻醉对他们是正确的道路?这是一个重要的问题,因为卢梭自己是那些人之一,这样的人能在哪里找到幸福 呢?
我以谈论给卢梭写信寻求幸福指南的众多读者开始。其中一人自称“亨丽特”(Henriette),她被莫佩尔蒂所称的反思式的“活着的疾病”异常强烈的情况所折磨。她写信给卢梭说,她每天早上醒来面对自己的存在感到极度恐惧,于是用卢梭批评知识分子时所说的那些社交活动来寻求安慰。实际上,她是想请卢梭帮忙并支持她的生活方 式。
通常,那些说自己在寻求建议的人实际上是在寻找对他们已经想做的事情的支持。卢梭回复说,对像她这样的反思者来说,他们的境况的最大不幸是“一个人越觉得它有病,就越会雪上加霜,而我们离开它的所有努力只会让我们更加深陷其中”⑤“Letters to Henriette”,in Rousseau on Women,Love,and Family,edited by Christopher Kelly and Eve Grace,Hanover,NH:University Press of New England,2009,p.150.。在他确实鼓励她更积极地生活的时候,他没有鼓励她像山人那样简单地停止思考并享受生活,因为“人们不能像摘自己的帽子般摘下自己的头,而且人们不会回到质朴,更不会回到童年”①“Letters to Henriette”,pp.149—150.。在遵循莫佩尔蒂所描述的模式时,通过寻找自己的消遣,“亨丽特”绝望地试图逃离自己的恐惧感。她的独特性在于这个事实:她既不是在剧院也不是在烈酒中分心。卢梭看出来的是:“你想要通过哲学来分心。”②Ibid.,p.152.他认为,不要通过这样的方式分心,她必须找到回到她自身的道路。这就是所谓的“聚精会神”(gathering oneself together into oneself),他也将它作为反思着获得享受的前 提。
卢梭在这里使用的术语recueillement(我把它翻译为“聚精会神”)在他之前与其后也都存在,这是一个与宗教冥想或沉思有关的术语,就像自己用适当的心态去接受圣礼一样。并没有合适的英语单词来表达它——我不知道是否有合适的中文翻译。卢梭很世俗地利用了这些含义。在法语词典中,也许他对该术语的独特使用是独一无二的。他的小说《朱莉》中的人物之一——一个叫爱德华勋爵的英国绅士——有好几年时间都在他的德性与对两个女人(一个已婚的意大利贵妇和一个新教妓女)爱情之间左右为难,他很难结合德性与这些爱人中的任何一个。他花时间往返于这些妇女生活的罗马与他的家乡英格兰之间。在那些长时间的旅行中,他当然会经历消除很多无聊时间的愿望。在将要决定放弃自己追求的那些女人时,爱德华向他朋友宣布:“对我来说,是时候该聚精会神了。”③Jean-Jacques Rousseau,Julie or the New Heloise,CW6,translated and annotated by Philip Stewart and Jean Vaché,Hanover,NH:University Press of New England,1997,p.534.他解释说,他打算从这种无休止的摇摆与旅行的生活中撤退。他不是指他将撤退到僧侣的沉思生活,他将撤退到自己的庄园,与他的朋友们分享他的孤独。他疯狂的爱情使他分心,这种爱情驱使他往返于英格兰与罗马之间,给他留下了欲望与满足之间的许多间隔,而对以友谊为中心的家庭生活的兴趣将取代这种分心。因而,在这个词指撤退到自身的时候,它很适合,也确实需要一种社会性存在。
卢梭只是反对解脱痛苦的享乐艺术,他反对聚精会神,让自己从通过娱乐而发现的那种自我中分心。对那些想了解卢梭对这种情况的描述的人们,我推荐《爱弥儿》第四卷末尾的解释,在那里,卢梭讨论了如果富有他会如何过自己的生活。如果要对这个问题作出完整解答,也就要对卢梭在这种寻找幸福的新方式中看到的局限性加以阐释。我试图证明,他专注于这些精确要素是他努力重新打开幸福的可能性并反对排斥这种可能性的结果。他认为,这是他同时代人的特征,他们强调的是追求幸福而不是获得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