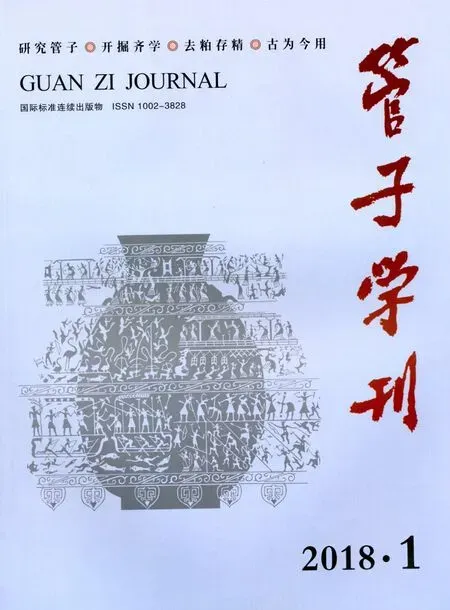论儒家义务论伦理的内生现代性转化
——兼与陈嘉明教授商榷
2018-01-23郭晓冉
郭晓冉
(西南科技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四川 绵阳 621010)
陈嘉明教授所撰写的《中国现代化视角下的儒家义务论伦理》一文发表于2016年第9期的《中国社会科学》。本人认真拜读之后,认为陈嘉明教授在现代性视角下来审视传统儒家义务论伦理,此研究视角高屋建瓴、另辟蹊径,对促进儒家义务论伦理的现代性转化研究具有深刻启示。但细思其文,仍觉其具体论证有失偏颇,遂忘其鄙陋提出浅薄愚见以俟诸学者。
一、基本路向:儒家义务论伦理的内生现代性转化即从传统文化中更新转化出现代内涵
任何学说都是为了维护统治阶级的利益及其统治地位。儒家传统思想建立的基础是阶级社会,其必然是为了维护当时的封建剥削统治之需。而现在我国是社会主义社会,阶级发展和社会现实都与儒家思想产生之时有着很大的区别,故我们需要对儒家思想进行批判性审视,既要提取出其中合理成分,也需要对这些合理性成分进行现代性转化。在传统儒家思想的现代化转化进程中,不可避免的就是如何看待中西方文化的关系问题。而在这一问题上,不外乎以下两种观点,一是如“五四”运动前后知识分子对传统文化的弃之敝履,而引用西方文化中成分;二是在西方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共在视角下来审视传统文化,对其缺陷加以克服,对其优势加以转化。第二种视角是更加符合文化发展规律的观点,毕竟人类文化是整体,且任何现在文化都是在前续文化的基础之上才能得以进一步发展。
具体到陈文中,陈嘉明教授最后所提出的对策十分可取,即“通过批判性的反思,在吸纳儒家原有的人本主义思想、原有的仁、义等德性思想中合理要素的基础上,将其更新、转化为具有现代伦理价值、与现代化的需要相适合的、并能够为现代化的构建服务的学说。”[1]53-54这种做法,即是在坚持了传统文化延续性基础上对传统文化的现代性发展,即对儒家传统义务性伦理的“推陈出新”,这种发展根源和质料都在内部,故不妨称其为儒家传统义务性伦理的内生现代性转化。这是我们在研究儒家传统义务性伦理现代性转化时必须把握的正确方向,只有坚持这条基本路向,才能保证儒家义务性伦理能够顺利实现现代性转化,以有效调节当前人们之间的道德关系,促进和谐社会的建设进程。
二、儒家义务论伦理不是单边“义务论”而是双向义务关系
陈嘉明教授认为,中国传统儒家义务论伦理中具有根本的理论缺陷,即强调单方面的义务,对此他主要列举了韩愈论述和董仲舒的“三纲五常”。
首先来看韩愈的相关论述。黑格尔曾说过,与一种理论进行论证,就要“在其最强势的地方与其进行角力”;“不熟悉别人的理论,就没有资格进行批判!”因而,为攻击一种学说,最厉害的武器莫过于这种武器本身,即“以己之矛攻己之盾”,也即马克思所言“批判的武器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所蕴含之意。在批判一种理论合理性之时必须要运用这种理论本身,对理论本身有着深刻的理解和把握,由此所进行的批判也才具备最深刻和扎实的理论根据。韩愈的思想并不能完全代表儒家的思想,为探讨儒家义务论伦理,不去列举儒家观点,却去拿韩愈观点,此种论证却在不经意之间犯了“偷换概念”的逻辑谬误。
其次,关于董仲舒的“三纲五常”。对于董仲舒“三纲五常”中的单向度义务关系,这点毋庸置疑,这也是为学界所共同认可的,但董仲舒提出了单向度义务就意味着儒家也是如此认为?通过李存山教授和方朝晖教授对“三纲”之论辩,可以清楚看出,董仲舒的“三纲”中所蕴含的单向度义务论与儒家创始人孔子、孟子所提出的双向义务论是截然不同的,可以说董仲舒的“三纲”是对儒家经典双向义务论的“异化”和扭曲。董仲舒的“三纲”并不能代表儒家创始人观点,将其作为论据有失偏颇。那么,我们如何来看待儒家的义务性伦理的单向还是双向呢?自然要通过儒家创始人的观点来看,关于儒家的双向义务论,孟子对其阐发较为完善,其主要观点可归纳为家庭、国家、师徒等三个层面。其中,家庭等级依靠父与子、兄与弟之间的双向道德义务维系。父子等级依靠子对父的服从和父对子的身教示范维系,兄弟等级依靠弟对兄的敬重和兄之学识品德维系。国家等级依靠君臣之间相互敬重和臣臣之间的不逾矩。君臣等级依靠臣子对君主的“贵贵”和君主对臣子的“尊贤”维系,“臣臣等级”依靠的是各自的各尽其职和不越级越位。而凌驾于父子、君臣等级之上的“师徒等级”依靠徒弟对师傅的尊重以及师之德才维系。可见,在孟子的义务论伦理当中,小到家庭内部义务关系,大到君臣、臣臣义务关系,再到师徒之间义务关系,均表现为一种双向性的义务关系即双向性伦理,这种双向性伦理更有利于维护人际关系之间的和谐稳定,也体现出了古代朴素的“和”思想,即各安其位、各循其道基础之上的人际关系并行不悖、和谐共生。
三、儒家思想中不存在权利缺失
陈文认为中国传统义务论中存在权利缺失的问题,而现代义务论强调对人权利的维护,因而必须要借鉴西方义务论中对人权利维护的相关论述。可见,陈嘉明教授认为现代义务论是西方的,而中国传统义务论不符合现代性要求。那么,事实果真如此吗?中国传统义务论当中是否存在如陈文所说的权利缺失?儒家思想主张一种双向性的义务关系,同时儒家思想中也不存在权利缺失。在我国儒家思想当中,不乏对权利的论述,而这些论述体现了对人权利的保障,因而认为我国儒家思想中权利缺失是没有根据的。陈文用现代社会中的权利一词套到古文中去寻找其含义,这种做法无疑是“按图索骥”。举个夸张点的例子,这就类似于拿着汉语中的词汇到日语中去寻找相关意义,虽然字形相同但其表达含义却大相径庭,这都是由于语义演化使然。在汉语词汇的发展中,现代所言“权利”与古代所言“权利”二者其意迥然,关于此陈文已论述十分清楚,在此就毋庸赘言。因而,为找寻我国儒家思想当中有无权利,就需要用权利的现代含义来去儒家思想中找寻相关论述。比如自由权,孔子指出,“道不行,乘桴浮于海”,孟子指出为官应懂进退,这都是自由权利的体现。《中庸》指出“率性之谓道”。比如财产权,孟子强调“明君”应“制民之产”,《中庸》指出“财聚则民散,财散则民聚”。而我国古代毕竟存在权利缺失,这是由于法律缺位,而同时儒家经典义务论伦理被董仲舒及历代封建统治者异化成为了单向度的义务教条所造成的。我们不能因此而否定儒家义务论伦理在肯定人权、维护人权上的重要价值。既然我国传统义务论当中不存在权利缺失的问题,那么从传统义务论过渡到现代义务论的最主要动力和理论源不在于西方理论,而是深蕴于我国传统文化当中。从儒家的双向性义务伦理中,可以开化出现代社会中的人权和权利。
四、儒家义务论思想向现代义务论的内生转化:从义务本位开出权利自由
如何实现儒家传统义务论伦理的内生现代性转化?这就牵涉到应当如何看待权利与义务这两个概念之间的关系。对此,第一,需要纠正陈文对权利义务关系的看法,陈嘉明先生过多强调了权利自由的重要性,而对于义务之于实现权利的重要性缺乏必要关注,这在权利与义务之间关系上犯了“执其一端”的独断论错误。陈文过度强调了权利、人权,而忽视了义务的遵守是开出权利的必要条件,这违反了他自己所引用马克思“没有无义务的权利”,可谓自相矛盾。结合陈文中所提到康德的《道德形而上学原理》一书,可以看出,在康德的话语体系中,责任、自律、自由这三个概念具有密切联系,理解了上述联系,有助于我们对权利和义务之间关系得出更加科学合理的认识。在康德的话语体系中,首先,责任与义务是同义的。因为康德指出:“一个不彻底善良的意志对自律原则的依赖及道德的强制性,是约束性,出于约束性的行为客观必然性,称为责任。”[2]46其次,出于责任与自律是同义的。行为出于责任即使对道德规律的遵从,这种道德规律是人自己所制定并服从的,因而只有行为出于责任才能被称为自律。正如康德所指出:“我必须把知性世界的规律看作是对我的命令,把按照这种原则而行动,看作是自己的责任。”[2]60再次,自律和自由是一致的。正如康德所指出,“自由意志和服从道德规律的意志,完全是一个东西”[2]54,“自律概念和自由概念不可分离地联系着”[2]59。正是人们以自身所制定出来的具有普遍性的道德规律来行动,这样人们便实现了意志自由,这就是康德所说的“自律”,意志自律被康德奉为道德的最高原则。此外,康德也十分重视意志自由,他认为:“自由是一切有理性的东西的意志所固有的性质……每个只能按照自由观念行动的东西,在实践方面就是真正自由的。”[2]55可见,在康德的话语体系中,自由和自律这两个概念之间具有密切联系,自律可以理解为对义务的遵守,自由则可以理解为权利的实现。总而言之,正是由于人们以出于责任的方式即遵循道德规律的方式行动,即做到了自律,这样人们才算是实现了意志自由。道德是对于理性、对规律的服从,是人为自身立法的具有普遍性的先验综合定言命令;通过对于上述道德规律的服从,人们才可以实现从他律到自律之重大转变,这样才能实现了意志自由,同时也成为一名“有尊严”的人。从上述可以看出,在义务和权利的关系问题上,陈嘉明教授所认为的权利本位即义务以权利为前提虽具有一定道理但存在一定片面性,我们不能因为过分重视权利实现而忽视了遵守义务的重要性,以及遵守义务是权利实现的先决条件。虽然在康德的话语体系中,意志自由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但康德也重视人们对于责任即义务的遵守,并且只有人们遵守一种个性而又普遍的道德义务,人们才能够真正实现意志自由即权利实现。可以说,关于权力和义务之间的衍生关系,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这样说,义务不是权利自由的前提,义务不是借助权利而实现的,而是权利以义务为前提,权利是在义务范围之中的自由,这种义务则主要包含了法律与道德两种形式。
此外,陈文所提到的霍布斯所说“人人是豺狼”的自然状态中人权利的缺失只是表象,而义务的不遵守即法律的缺失和不被奉行才是更深层次的原因。不妨寻找霍布斯本人的看法,霍布斯秉持着人性恶的人性观,他认为在人类成立国家之前,是处于一种人人自危互相争斗的自然状态。因此,人们出于理性和幸福的需要,便要通过建立社会契约的方式创建起国家,国家中有一个至高无上的主权者,而人们群众对其有着绝对服从的义务。霍布斯认为,保全自由即为自然权利,因为霍布斯指出:“著作家们一般称之为自然权利的,就是每一个人按照自己所愿意的方式运用自己的力量保全自己的天性——也就是保全自己的生命——的自由”。霍布斯认为,为了保全自由即维护人的自然权利,就需要通过法律来为人们设计其各自所应履行的义务。霍布斯还指出,“在我们的服从这一行为中,同时包含着我们的义务和我们的自由”[3]168,可以说,只有通过义务的遵守才能实现自由即维护人的权利。霍布斯之所以强调立法,其实质是通过确立人的法律义务而保障人的权利能够不受他人侵犯即权利实现。由此,遵守义务是实现权利的前提和保障,义务的重要性可见一斑。
而继英国人霍布斯之后的法国人卢梭,其所设计的“社会契约”也便是强迫人们遵守自己义务的一种国家政治体系,通过“社会契约”对人们行为的约束,人们便能够保障自身的自然权利得以维护并实现。社会契约的建立是人们自然权利实现的基础和保障,而只有人们根据社会契约建立起国家,人们遵守各自的义务,才能够保证人们各项自然权利的实现,这也是人类社会从自然状态过渡到社会状态的重要标志。卢梭认为,每位公民权利的实现是与义务遵守不可分的,而且正是由于义务遵守对于公民个人具有利害关系,即“任何人拒不服从公意的,全体就要迫使他服从公意。这恰好就是说,人们要迫使他自由”[4]24-25。可见,订立“社会契约”的重要目的就是要迫使每个人以符合“公意”的方式来行动,否则就要受到国家的惩罚,这就是一种义务的体现,而这种义务遵守是维护公民权利的必备前提,由于“社会契约”的订立,人们“所获得的,乃是社会的自由以及对他所享有的一切东西的所有权”[4]26。
第二,权利与义务之间不仅相互区别,更为重要的是,权利和义务之间可以实现相互转化,即从义务本位过渡到权利实现,在此不妨引用我国儒家经典著作《大学》中所述的“絜矩之道”和《中庸》当中的“中和”思想证明此论断。《大学》中“修身”是“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基础,这就体现了尽义务之后权利得以实现和维护的思想。具体言之,比如“所恶于上,毋以使下;所恶于下,毋以事上”,这就体现了每个人对自己义务的遵守,而这种义务的遵守同时也便保障了每个人权利的实现。而这种“絜矩之道”也并非完美无缺,这就是君主本人所尽义务的无所制约,因为“絜矩之道”是恕道在治国上的延伸,君主本人的权力处于无人制约的位置,因而封建统治者本人的“修身”才被儒家提高了极其重要的位置,正所谓“一言偾事,一人定国”。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了统治阶级即广大人民对权利的广泛监督制约机制,这便有效保障了行政权力在合理区间内运行,为群众谋利和造福。因而,这种双向义务论的弊端被社会主义制度所克服,在社会主义社会中上如果能够得以推演,便可以有效维护社会秩序的和谐稳定。所以说,在当前社会主义社会条件下儒家的双向义务论具备了转化为权利本位的现实基础和必备条件。《中庸》提出了“中和”概念,这一概念对于理解儒家义务论到权利的过渡具有重要意义。“中”即“不偏不倚”“无过不及之差”,此之谓天赋予人的本性;而将中推之于外即为“和”,即性情的合理适中,这种合理适中也可被理解为每个人对各自义务的遵守,而这种遵守必须是不偏不倚,由此权利便能得以实现和保障。“天地位焉,万物育焉”,朱熹将“位”解释为“各得其所”,也可以理解为“安于其位”,这其实说的就是每个人都各司其职即对各自义务的遵守,同时在和他人它物相交相遇时能妥善处理关系即对他人它物权利的尊重亦对人和自然的尊重,因而在“中和”这一概念中便体现了权利与义务的转化和统一。具体而言,比如尊重别人财产,这可以是一种义务,也可以说是权利,而尊重他人财产义务的实现,便保障了每个人财产权利的有效维护。如果脱离了义务本身来谈论单独的权利,那么权利始终无法得以保障,毕竟外在的强迫式义务莫如每个人都自觉意识到并遵守自身义务,这也是儒家思想中“诚意慎独”的本意,只有每个人都“一于善无自欺”,那么整个社会才能够和谐稳定,人们的权利才能得以保障,毕竟总有一些隐、微之处是“他人所不知而己独知”,法律体系当中可能存在漏洞以及针对此法律体系的不断完善正体现了此。
第三,我国儒家思想中的“恕道”与康德的“道德形而上学”彼此通契,这便说明了中西方文化共同认可遵守义务的重要性,以及从个体的义务本位过渡到普遍的权利自由状态的这样一种逻辑理路。关于传统文化中私德和公德的辩证关系,对此陈文论断有失偏颇,这便造成了他基于错误认识所得出的错误结论,因而必须要理清私德与公德之间的辩证关系,才能够理解如何从个体的义务本位开化出普遍的权利自由。陈文认为中国人的“道德意识”“偏于私德,而公德殆阙如”(引自梁启超《新民说》),这样的观点不符合我国传统文化真实情况,儒家“仁”思想的核心即为“恕”道(《中庸》有云“忠恕违道不远”)即“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而将“恕”推演到治国理政当中即为“絜矩之道”,“恕”道和“絜矩之道”都体现了一种在道德问题上的推己及人,从个体人推演出道德即“道不远人”亦从个体私道到社会公德这样的道德演绎进程。朱熹在《大学章句集注》中指出“身修,则家可教矣;孝、弟、慈,所以修身而教于家者也;然而国之所以事君事长使众之道不外乎此。此所以家齐于上,而教成于下也”,这也在某种程度上体现了私德与公德二者之间具有通融性、一致性。康德《道德形而上学原理》第二章“从大众道德哲学过渡到道德形而上学”就体现了道德哲学是根源于大众生活之寓意,康德在本章中指出,“定言命令只有一条,这就是:要只按照你同时认为也能成为普遍规律的准则去行动”[2]30,这与儒家的“恕”道“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有着相通之处,这都是一种基于主观想象层面上的先验理性,但却与现实生活中的经验具有一致性。《中庸》有云:“所求乎子,以事父,未能也;所求乎臣以事君,未能也;所求乎弟以事兄,未能也;所求乎朋友先施之,未能也。”朱熹在《中庸章句集注》中解释道:“道不远人,凡己之所以责人者,皆道之所当然也,故反之以自责而自修矣。”张载将此解释为“以责人之心责己则尽道”,这体现了每个人在要求他人给予自己权利的时候,首先应当反躬自省,以要求别人的来要求自己,这就是个人对于义务的遵守,而这种遵守是获得权利的基本前提,这体现了一种从他人身上道过渡到自己身上道的一种推人及己过程,也体现了朱熹所云“以己之心度人之心,未尝不同,则道之不远人者可见”。而每个人都对于义务的遵守,其实也就是实现了对于他人权利的维护,由此义务本位便具备了开化出权利自由的现实可能性。
[1]陈嘉明.中国现代化视角下的儒家义务论伦理[J].中国社会科学,2016,(9).
[2]康德.道德形而上学原理[M].苗力田,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
[3]霍布斯.利维坦[M].黎思复,黎廷弼,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6.
[4]卢梭.社会契约论[M].何兆武,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