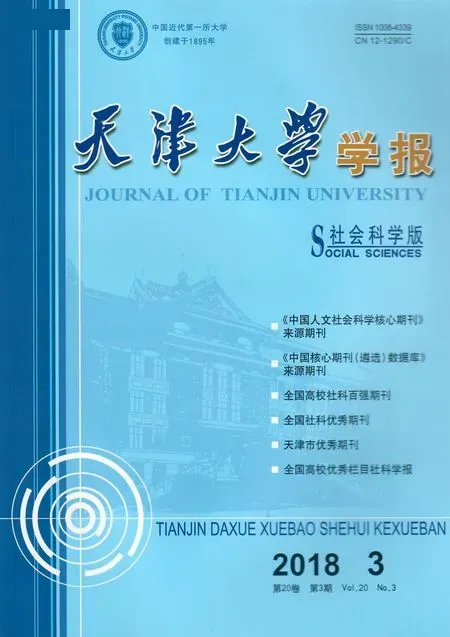文学文本的欲望书写范型及其审美效应生成
2018-01-23康建强
康建强
(1. 山东大学文艺美学研究中心, 济南 250100; 2. 白城师范学院文学院, 白城 137000)
文学是人类欲望与社会实践二元碰触而产生的审美言语,其发生根源于创作者因欲望阻滞而产生的突围意识与行为实践。因而,书写欲望不但是文学创作的原初驱动力,而且是文学的核心内容。在具体的文学创作实践层面,由于个性思维以及特定创作背景刺激下反应的差异,作家对所书写的欲望内涵的思考与处理方式多有不同。同时,人类因统一的种属共性而具有趋同性的心理与行为类型。人的“性格中存在两种普遍的基本的倾向……两种明显的性格类型(还有第三种,那是一种中间的类型)……”[1]。结合作家的心理机制与文本的实际表现,文学的欲望书写大致具象为直陈型、反寓型与绘饰型三种范型,并因之而化生出三种审美效应。
一、 直陈型
直陈型欲望书写是指作家以无遮蔽姿态观照并运施直书式方法展示自我欲望的书写范型。如传说中夏禹时期的《侯人歌》:“候人兮猗!”此歌亦称《涂山氏妾歌》,据《吕氏春秋·季夏篇·音初篇》记载:“禹行功,见涂山之女,禹未之遇,而巡省南土。涂山氏之女,乃令其妾,候禹于涂山之阳。女乃作歌,歌曰:‘候人兮猗!’实始作为‘南音’。”[2]“候人”二字实义,直接而简单地叙述了等人的事实;“兮猗”二字为语气词,是因“候人”感情激荡而发出的声音;二者自然承续,简洁而又生动地展示了候人不至的焦虑与渴盼情怀。在中国文学范畴,直陈型书写是在文学发生初期业已产生的具有简单朴素质性的欲望书写范型。史前社会自无须赘言,即使在人类步入文明时代的初期,受社会生产力与人类自身进化等多种因素的制约,先民的理性认知水平与感性体验程度尚处于低级阶段。因此,由于缺乏鲜明的绘饰意识,他们多以直观可感的方式表达欲望,鲁迅先生所云“杭育杭育派”既是鲜明例证。即使在文学日趋自觉的后期,直陈型书写依然是一种常见的欲望书写范型,如自《诗经》“六义”之一的“赋”、汉乐府民歌的“感于哀乐缘事而发”以至白居易的“讽喻诗”创作这一发展历程中,其现实表现犹明晰可见。因而,直陈型欲望书写不但渊源有自内具历史发展承续的脉络,而且是欲望表达的基本常态范型。
据实而论,直陈型欲望书写的要义主要有二。第一,创作触媒及其所引发的心理反应具有简单明确的质性;第二,对于上一要素,作家采取了直接表现的创作方式。社会生活虽然复杂,但是置身其中的个体在特定的时空中面对的却是具体的生活。因而,文学书写内容首先是生活具体性的反映。如《诗经·伐檀》、杜甫的《闻官军收河南河北》、艾青的《大堰河——我的保姆》,虽然情感向度各异,但是所表现的事件与心理反应均简单明确,创作者无需采用更为复杂的方式施以表现。与此相较,作家的个性气质与思维方式之于直陈型欲望书写的形成尤为重要因素。根据作家与生活的互动关系,王国维曾有“主观之诗人”与“客观之诗人”的大致分别。“气质是每一个个别人的最一般的特征,是他的神经系统的最基本的特征,而这种特征在每一个人的一切活动上都打上了一定的烙印。”[3]相对于“客观之诗人”、“主观之诗人”的心理与思维机制有三个突出特征。第一,心理的内倾性表现更为鲜明,更为注重自我;第二,善于想象与幻想,对客观外在现实的判定更为自我化;第三,个体的兴奋视域具有更强的敏感性,当其与外在碰触时更为缺乏克制力。故而,主观性作家更倾向于以直陈型方式表现个体欲望。如李白,本是“天纵逸才”的诗人,却渴望成为名显后世的政治家。因此,人生定位与自身特征的偏离,导致其一生处于无所适从的状态。得意之时高唱“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苦闷之时痛吟“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失意之时亦宣称“人生在世不称意,明朝散发弄扁舟”。再加之性格的孤傲狂放,使其个性与诗歌均表现出鲜明的主观性色彩。
直陈型欲望书写为文学文本的审美效应生成提供了率直鲜明的情感基调。“向来写情感的,多半是以含蓄蕴藉为原则,像弹琴的弦外之音,像吃橄榄的那点回甘味儿,是我们中国文学家所最乐道的,但是有一类的情感,是要忽然奔迸一泻无余的,我们可以给这类文字起一个名,叫做‘奔迸的表情法’。例如碰着意外的过度的刺激,大叫一声,或大哭一场,或大跳一阵,在这种时候,含蓄蕴藉,是一点用不着。”[4]现实生活给予作家强烈的精神撞击,他们无暇体味“沉静中回味过来的情绪”[5],直抒胸臆以宣泄内心情志,因而具象为率直鲜明的情感格调。如《上邪》:“上邪!我欲与君相知,长命无绝衰。山无陵,江水为竭,冬雷震震,夏雨雪,天地合,乃敢与君绝。”[6]“五者皆必无之事,则我之不能绝君明矣。”[7]女主人公以誓言的方式剖白内心,以不可能实现的自然现象反证自己对爱情的忠贞,表达直白决绝,感情激越,生发出极情感撞击力的审美效应,正如胡应麟所评:“上邪言情,……短章中神品。”[8]
直陈型欲望书写,就创作者而言,是对自身欲望的主观性升华;就表现方式而言,在于对自身欲望的直接发抒。因而,源于欲望发抒的主观、直接与开放质性,直陈型欲望书写更易于形成对读者的心理冲击,更易于生发直截强烈的审美效应。当然,审美效应的强弱则不可一概而论,因为它是由情感发抒的强度、艺术表现形式等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总之,作为文学书写欲望的基本型态之一,直陈型方式是人类心理机制演进状态在文学创作领域的具体表现。
二、 反寓型
反寓型欲望书写是指作家以艺术化方式隐藏并反向展示自身欲望的书写范型。如苏童小说《罂粟之家》中刘老侠被斗这一故事情节。当地主刘老侠被斗时,不但其本人毫无惧色,而且于台下观望的三千群众亦无一人上台揭发他。不止如此,人们还向土改工作队队长庐方讲述刘老侠的辉煌创业历史。因此,庐方自始至终都没能实现通过阶级教育激起农民对地主刘老侠仇恨的目的。文本这一描写颇富深长意味,苏童不但有意通过农民的反向表现抽空了政治意识形态赋予革命历史叙事的激情,而且使农民意气风发自觉闹革命的历史想象于此刻瞬间土崩瓦解。与直陈型欲望书写相较,反寓型欲望书写是相对后起的书写范型,它是人类思维机制趋于复杂、认识能力日益提高于文学范畴的现实反映,其核心在于理性的进步及其对感性的渗透与复合。据今见文献,反向思维机制在先秦时期已非常成熟。如《老子》一书,其于宇宙运动变化层面曰“反者道之动”,于社会人生层面曰“玄德与物反”,于逻辑思维层面曰“正言若反”,三者均是关于反向思维的深刻表述。作为中国文化思想的重要范畴,道家反向思维对于国人思维模式的显著影响已无需赘言。
在具体的文学实践层面,作家以反寓式姿态进行欲望书写,其原因主要有三。第一,特定环境或者创作触媒迫使作家隐藏自己的真实意图。如阮籍《咏怀诗》八十二首“厥旨渊放,归趣难求”[9],其原因在于“嗣宗身仕乱朝,常恐罹谤遇祸,因兹发咏,故每有忧生之嗟,虽志在讥刺,而文多隐蔽,百代之下,难以情测也”[10]。第二,作家有意掩饰自我的真实心迹。如柳永,其人热衷仕宦功名之心颇重,这于其“学,则庶人之子为公卿;不学,则公卿之子为庶人”[11]的人生宣言、中进士后所作之词《柳初新》对于“高志须酬”既得之喜悦的形象展示中可得确凿之证。然而,其人所创诸多词作,中进士前之词如《鹤冲天》“且恁偎红翠,风流事,平生畅。青春都一饷。忍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做官后之词如《思归乐·天幕清和》“这巧宦、不须多取。共君把酒听杜宇。解再三、劝人归去”,其意看似不甚重视功名或者意欲远离官场,其实是风流才子失意之时的情绪宣泄与仕宦理想实现之后的有意装饰,均非其内心世界的真实表达。第三,将其作为以理性制约感性的表述方式。如宋代诗人林升的《题临安邸》:“山外青山楼外楼,西湖歌舞几时休。暖风熏得游人醉,直把杭州作汴州。”“绍兴和议”与“隆兴议和”之后,南宋朝廷对于中原失地再无严肃认真的恢复措施,有志恢复的爱国志士对此极为愤慨。然而,林升并未直陈内心的愤慨,而是以潜在的理性思考牵引显性的主观情绪,通过对“销金锅儿”的环境与人物直写反向表达对南宋主和派君臣的不满,正言若反,言辞犀利,发人深省。
反寓型欲望书写因作家理性与感性因素的有机复合以及作家的有意建构而化生出出人意表的审美效应。如张爱玲的小说《色·戒》,就以独特的“阴性叙事”颠覆了中国传统的“色戒叙事”。在传统的“色戒叙事”中,男性多是“色戒”的主体,而女性往往处于陪衬的地位是被“戒除”的对象,体现出鲜明的父权话语意识。在《色·戒》这部小说中,女主角王佳芝出于刺杀汉奸的革命目的而奉命色诱易先生。然而,文本却以细腻的笔触详细描写了王佳芝的欲望陷落及其心理历程,“事实上,每次跟老易在一起都像洗了个热水澡,把郁积都冲掉了,因为一切都有了个目的”。“热水澡”的舒畅体验使得王佳芝觉得“这个人真爱我的,她突然想,心轰然一声,若有所失”。瞬间的怜惜之情让她忘掉了自己的重大政治使命,在诱杀的最后关头放走了老易,并最终导致自己与革命同志的悲剧命运结局。在革命叙事的表层情节之下,文本细致地描绘了女性在命运与情感陷井之前的陷落,于是“色戒叙事”顺利地实现主体转向。这一“阴性叙事”不但深刻体现了张爱玲对女性命运的深沉之思,而且以逆反叙事的方式质疑了延续已久的父系话语权威,生发出深重的思想意蕴,并进而融生浓郁的心理效应。
直陈型欲望书写与反寓型欲望书写,实为人类正向与反向思维机制分别于文学领域的投射。“反者道之动”[12],反寓型欲望书写不止是直陈型欲望书写的反向表现,“一阴一阳之谓道”[13],而且二者相反相成,共同构成了文学欲望书写的基本型态。
三、 绘饰型
“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12]158道具有生生不息运化无穷的内在质性。直陈型与反寓型不仅是文学欲望书写一元化生的阴阳两仪,而且是“道”于文学领域化生链条上的重要一环。在二极共构的基础上,“二生三”,直陈型与反寓型相反相成又融生出绘饰型书写型态。这一欲望书写范型,不仅继承了直陈型与反寓型欲望书写的基因内核,而且在二者基础上又化生出新的特质。
所谓绘饰型欲望书写是指作家以多样化方式修饰并运施多元化艺术方式表现自我欲望的书写范型。究其产生的根源,客观因素在于社会生活的复杂多样质性,而主观因素则在于作家创作思维及其表现意图的复杂性与深刻性,其中尤以后者为主要因素。与直陈型与反寓型相比,绘饰型是更为复杂的欲望书写方式,据其实际表现,又可细分为三种类型。
1. 具象式
“古者包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13]298“象”是人类认识世界的工具与结果,作为符号其蕴含着人类的理性认知与情感体验。孔颖达对于“象”有更为细致的区分:“万物之体,自然各有形象,圣人设卦以写万物之象。……或有实象,或有假象。实象者,若‘地上有水,比’也,‘地中生木,升’也,皆非虚,故言实也。假象者,若‘天在山中’、‘风自火出’,如此之类,实无此象,假而为义,故谓之假也。”[13]10“《正义》‘实象’、‘假象’之辨,殊适谈艺之用。”[14]所谓绘饰型欲望的具象式书写意指作家将自我欲望寄寓于客观之象进而创设意中之象并施以繁复正向表现的书写方式。这一书写方式是人类意象思维成熟于文学领域的体现,意味着作家“寄兴于象”创作思维的发动,是作家感性情绪与理性认知充分融和且向客观之象有效投射的形象体现。
意的深邃诗性及其正向繁复描摹,是文本生发浓郁浑融意境的根本因素,中国古代诗词于此有鲜明表现。如苏轼的《水调歌头》(丙辰中秋,欢饮达旦,大醉,作此篇,兼怀子由):“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转朱阁,低绮户,照无眠。不应有恨,何事长向别时圆!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15]宋神宗熙宁九年,苏轼时年41岁,为新党所迫到密州任太守,其时苏辙于齐州任职,兄弟已六七年未曾谋面。中秋之际,苏轼睹圆月而心生感慨,遂作此词以抒心臆。词作以中秋“圆月”为贯穿全篇的意象符号,辅以对“天上宫阙”、“琼楼玉宇”的“高处不胜寒”、“在人间”的“照无眠”之心理感觉描写,并将自我仕途坎坷人生失意的落寞与苦闷情怀充分融入,创设出孤独、缠绵悱恻而又低沉的情感格调;作者虽于下阕多次排解,其实正所谓“缠绵惋恻之思,愈转愈曲,愈曲愈深,忠爱之思,令人玩味不尽”[16]。通观全词,意象奇绝、手法妙绝、格调高绝、蕴意深绝,故而胡仔给予高评:“中秋词自东坡《水调歌头》一出,余词尽废。”[17]
2. 变形式
“人禀七情,应物斯感,感物吟志,莫非自然。”[18]然而,客观外在的景、物与事之象与作家的主观之意并不存在绝对的充分对应关系,因而在感物——写物——吟志的创作过程中,作家还需对客观之象进行裁剪,即如艾略特所说“表情达意的唯一艺术方式,便是找出意之象”[19]。对于“意之象”的处理,司空图曾有形象之论:“绝伫灵素,少回清真,如觅水影,如写阳春。风云变态,花草精神,海之波澜,山之嶙峋。俱似大道,妙契同尘,离形得似,庶几斯人。”[20]其“离形得似”之说,即认为文学创作的宗旨在于传达宇宙人生的内在精神与本质规律,不必拘泥于客观之象的外在之真,当客观之象不能充分承载主体之意时,作家应根据传情达意的需要,采取夸张、变形的方法,以取得“象外之象”效果。现代派作家追求自我欲望的主观叙述,对于文学的变形书写有更为深入的认识。余华曾说:“我觉得我所有的创作,都是在努力更加接近真实。……我觉得生活实际上是不真实的。生活是一种真假掺拌的、鱼目混珠的事物。我觉得真实是对个人而言的。”[21]格非亦认为:“现代小说的发展(尤其是福楼拜以来的一系列叙事革命),为故事的叙述结构提供了一个开放的空间,作家在讲述故事时,不再依赖时间上的延续和因果承接关系,它所依据的完全是一种心理逻辑。”[22]故而,现代派作家强调以非理性表现自我欲望,普遍使用隐喻、反讽、象征等技法,通过对现实世界的变形与陌生化处理,以揭示其异化的本质。
根源于作家的变异性思维与表现方式,绘饰型欲望的变形式书写极易生成新奇的陌生化审美效应。李贺的诸多诗歌可堪为证。如“骨重神寒天庙器,一双瞳仁剪秋水”(《唐儿歌》),将儿童的灵动目光拟作剪刀;“忆君清泪如铅水”(《金铜仙人辞汉歌》),以铅水喻泪之颜色;此外如“鬼灯如漆点松花”(《南山田中行》)、“羲和敲日玻璃声”(《秦王饮酒》),以通感思维写自我的视觉与声音感受,均想象奇特,造语奇异,生发出陌生而新奇的诗意氛围。诚如叶燮所评:“李贺鬼才,其造语入险,正如仓颉造字,可使鬼夜哭。”[23]另如中国现代派作家残雪的小说创作。其《苍老的浮云》,以梦作为现实的变形物,运用夸张、扭曲的手法,展示了对生存危机、丑恶人际关系以及病态人性的恐惧和焦虑。比如虚汝华发现自己腹腔里排列着纤细而干枯的芦杆干的冒烟即将燃烧,这其实是她焦虑的变形表现。其他文本如《旷野里》、《山上的小屋》等文本中也都充满着梦呓般的语言,展示了生活的灰暗与阴冷。在残雪的小说中,梦是生活的变形,它作为一种隐喻,深刻揭示了现实生活的残酷扭曲与人的极度压抑。因而,残雪对欲望的变形式叙述,不但实现了对现实世界的寓言式书写,而且生发出鲜明的荒诞化审美效应。
3. 抽象式
欲望是感性情绪与理性认知的二元共构,因而文学欲望书写是寓抽象思维于形象塑造的创造过程。关于抽象思维之于文学书写的实际功用,张贤亮曾说:“只有通过抽象——逻辑思维才会使大千世界通过我的视听器官传到我的脑子里的种种形象信息更为清晰和生动。而这种形象信息一旦在我脑子里抽象成了某种观念,在观念的支配下,种种形象信息还会生发、串连,以至衍变成一段情节。并且,也只有通过抽象——逻辑思维才能把这种种形象信息变为稳固持久的形象记忆。”[24]如若进之于抽象式绘饰型欲望书写,抽象思维还存在更为深刻的创作心理与审美效应的功用与价值。
就作家角度而言,当其意欲表达较为复杂深刻的人生体验而又难以或不能以确指的载体实现书写意图时,抽象式书写便成为极具优势的表现方式。在文本层面,则因其思想与表现方式的抽象性而生发出空灵深邃的审美效应。这在中国现代诗人覃子豪的象征主义诗歌创作中可以得到明证。覃子豪认为“最理想的诗,是知性和抒情的混合物”[25],诗歌应该表现“诗人对世界的一切事物的主观的意念”。因而,当具体的物象不能充分承载其主观意趣时,他便竭力“在物象的背后搜寻出以汇总似有似无、经验世界中从未出现过的、感官所不及的另外的存在,一种人类现有的科学知识所无法探索到的本质”[26]38,并运用比喻、联想、象征、暗示等手法“把平凡化为不平凡,把贫乏化为丰富,把单调化为生动”。如《瓶之存在》,堪为其抽象式绘饰型欲望书写的代表性作品。“净化官能的热情,升华为灵,而灵于感应/吸纳万有的呼吸与音籁在体中,化为律动/……禅之寂然的静坐,佛之庄严的肃立/……清醒于假寐,假寐于清醒/自我的静中之动,无我的无动无静/存在于肯定中,亦存在于否定中/……一澈悟之后的静止/一大觉之后的存在/自在自如的/挺圆圆的腹/宇宙包容你/你腹中却孕育着一个宇宙/宇宙因你而存在。”[26]38抒情主体的自我与“瓶”的物象相对而又互融,在静与动、清醒与假寐、肯定与否定的对立统一中,空灵而抽象,以深刻的哲理与纯美的诗思共同构设了一个物我两忘的禅的境界。正如洛夫所评,这首诗歌是覃子豪“思想最深刻,技巧最圆熟的一座‘智之雕刻’”[25]49。
综上所论,在欲望表现的指向与效果方面,与直陈型、反寓型欲望书写相比,绘饰型欲望书写虽既无前者的直截明快,亦无后者的讳莫如深,而是表现为复杂深刻的多维呈现,这其实是二者交合化生的状态体现,是欲望书写思维进化的结果。因此,绘饰型欲望书写既是复杂生活与作家深刻思维有机交合的产物,亦是人类文学创作思维进步的现实反映。“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三”不但具成数之义,且至“三”万物而始生成。董仲舒亦曰:“三而一成,天之大经也。”[28]直陈型、反寓型与绘饰型作为三种基本型态,不但构建了文学欲望书写的基本格局,而且仍可继续交合生发出更为繁复的书写范型,以反映社会生活与作家思维愈加趋于复杂深刻的发展态势。
[1] [英]弗尼奥克斯·乔丹.从躯体与出身中看人类性格[M]//[瑞士]荣格.心理类型学[M].吴 康,译.西安:华岳文艺出版社,1989.
[2] [战国]吕不韦.吕氏春秋[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86.
[3] [苏]巴甫洛夫.巴甫洛夫全集[M].冯小川,译.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62.
[4] 梁启超.梁启超古典文学论著[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13.
[5] 朱光潜.朱光潜美学文集[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2.
[6] 余冠英.汉魏六朝诗选[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2.
[7] [清]王先谦.汉铙歌释文笺证[M]//北京大学中国文学史教研室.两汉文学史参考资料.北京:中华书局,1990.
[8] [明]胡应麟.诗薮[M].北京:中华书局,1962.
[9] [南朝·梁]钟 嵘.诗品[M].历代诗话本.北京:中华书局,1981.
[10] [南朝·梁]萧 统.文选[M].李 善,注.北京:中华书局,1977.
[11] [宋]柳 永.劝学文[M].建宁府志,卷三三.
[12] [春秋]老子.老子[M].陈鼓应,注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153.
[13] [唐]孔颖达.周易正义[M]//十三经注疏本.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268.
[14] 钱钟书.管锥编[M].北京:中华书局,1979.
[15] 邹同庆,王宗堂.苏轼词编年校注[M].北京:中华书局,2002.
[16] [清]黄 苏.蓼园词选[M]//词话丛编本.北京:中华书局,1986.
[17] [宋]胡 仔.苕溪渔隐丛话[M]//万有文库本.上海:商务印书馆,1937.
[18] [南朝·梁]刘勰.文心雕龙[M].王运熙,译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
[19] 黄维梁.中国诗学纵横谈[M].中国台北:台湾洪范书店,1977.
[20] [唐]司空图.二十四诗品[M]//历代诗话本.北京:中华书局,1981.
[21] 余 华.我的真实[J].人民文学,1989(3):107.
[22] 格 非.小说叙事研究[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2.
[23] [清]丁福保.清诗话[M].北京:中华书局,1963.
[24] 张贤亮.张贤亮选集:三[M].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95.
[25] 洛夫.从《金色面具》到《瓶之存在》:论覃子豪诗[M]//叶维廉.中国现代作家论.中国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79.
[26] 覃子豪.覃子豪诗选[M].北京: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84.
[27] [汉]董仲舒.春秋繁露[M].北京:中华书局,19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