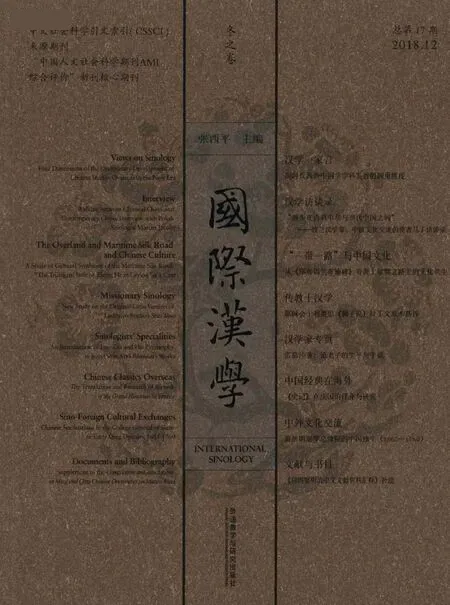新时代海外中国学学科发展的四重维度
2018-01-23
进入新世纪以来,弘扬中国传统文化、推动中国文化走出去成为时代之潮流。党的十九大更是庄严宣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中国正坚定而自信地走向世界舞台中央,当代中国人应该担负起新的文化使命,构筑中国精神、中国价值、中国力量!时代发展到今天,重塑中国文化自信,倡导中国文化走出去已成为时代最强音。与之相伴随的是中国学术界业已开始构建一套对中国社会和现象更具解释力,同时又富有继承性和民族性的理论体系。对于海外中国学研究来说,这既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新机遇,亦提出了新使命。
正是在这样的时代环境之下,海外中国学研究呈现蓬勃发展之势,已成为名副其实的“显学”。各大学及科研院所纷纷成立海外中国学研究机构或中心,相继推出专业性学术杂志、丛刊、集刊,并出版了列国汉学史、海外中国学史、海外汉学史等诸多丛书。据笔者粗略统计,国内的海外中国学研究机构或中心已有五十多个,各种期刊、集刊和丛刊则有十多种。不仅如此,国内不少高校经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批准已可自设海外中国学研究的硕士点和博士点,培养海外中国学研究方向的专业人才。有关传教士汉学、域外“中国形象”及历史变迁、中国典籍和文学作品在域外的译介与传播以及海外中国史学、海外中国女性史、海外中共党史、海外中国宗教等专题的研究成果层出不穷。
在海外中国学研究呈现一派欣欣向荣的气象时,对海外中国学研究及其学科发展的质疑和批评之声却并未消失。有学者谈到中国的历史文化研究时,认为唯有中国学者能掌握最丰富的史料宝藏,最了解、最懂得中国历史文化,无论是东洋学者,还是西洋专家,皆是门外之谈。在他们看来,域外学者仅凭其所具有的汉籍之部分知识或在华之一时见闻而欲论定千古,常如隔雾看花,难求其情真理得,因此没有必要推介海外学者的研究。还有学者则认为,今天中国学术界要致力的不是模仿西方,而是要建构自己的理论体系。亦有学者认为,海外中国学研究虽具有“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之价值,但国内的海外中国学研究仅停留在肤浅的介绍上,缺乏深入且理性的探讨。更有学者对海外中国学研究持完全否定的态度,将域外汉学研究称为“汉学主义”,认为对域外汉学的翻译和介绍是“自我学术殖民”。
这些批评,虽然并不客观,却不能不令人深思。如果从莫东寅1949年出版的《汉学发达史》算起,海外中国学研究已有近七十年历史;如果从李学勤、严绍璗、张西平、朱政惠、阎纯德、何培忠等先生于20世纪90年代倡导海外中国学研究学科化算起,海外中国学研究作为一门学科亦走过了近三十年的历程。然而,学界对海外中国学研究依然有如此尖锐的质疑和批评。这些质疑和批评无疑是一剂清醒剂,它提醒我们需要进一步深化和拓展海外中国学研究的学科内涵。
一、加强海外中国学研究的目录建设
目录是治学的基础、研究的指南,利用目录是做任何研究的第一步。借助目录,既可以确定前人有无相同或相近的著作,又可为相近的著述提供丰富的内容,同时依靠各种目录可以尽可能搜集完备的资料。美国中国研究在发展之时,出版了《中文参考书目解题》(An Annotated Bibliography of Selected Chinese Reference Works,1936)、《近代中国:1898—1937年中文著作目录指南》(Modern China: A Bibliographical Guide to Chinese Works, 1898—1937,1950)、《西方文献中的中国:续考狄中国书目》(China in Western Literature: A Continuation of Cordier’s Bibliotheca Sinica,1958)以及《哈佛大学馆藏美中关系史中文资料调查:1784—1941》(American-Chinese Relations, 1784-1941: A Survey of Chinese-Language Materials at Harvard,1960)等为数众多的汉学书目及馆藏汉学文献索引。费正清(John K.Fairbank,1907—1991)曾这样评价《近代中国》这部目录指南:“只要我手头持有这本书,我就能随时告诉我的任何一个学生他应找的中文原始资料的有关情况,并让他知道如何去找。它就像使人多了一部分大脑一样,不仅可以随身携带,而且还要来得可靠得多。”①费正清著,陆惠勤等译:《费正清对华回忆录》,上海:上海知识出版社,1991年,第398页。这或许就是20世纪初还是汉学“荒村”的美国中国研究能成为世界中国研究中心的原因之一。
对海外中国学研究而言,亦需重视目录建设,这甚至已成迫在眉睫之事。之所以如此,其原因有二:一是随着中国的崛起,域外有关中国的研究著述急剧增加。有学者统计,在伯克利校园图书馆所藏的DS类图书中,出版时间为2000—2010年的关于近现代中国历史研究的英文图书(不包括中文)共有1776册。②梁怡:《21世纪前十年美国的中国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报》2011年1月25日。有关中国的日文、法文、德文、俄文等著述,则无从计数。自考狄(Henri Cordier,1849—1925)的《西人论中国书目》(Bibliotheca Sinica,1881)、袁同礼(Tung-li Yuan, 1895—1965)的《西方文献中的中国:续考狄中国书目》等出版后,国内虽曾出版了杨诗浩主编的《国外出版中国近现代史书目(1949—1978)》(1980)、马钊主编的《1971—2006年美国清史论著目录》(2007)等书目,但前者出版于1980年,后者则是专题性书目。对20世纪60年代以来域外中国研究文献,东西方学界事实上没有再进行过系统性梳理。二是目前国内的海外中国学研究者,往往比较注重朝前看,对过去的成果和经验关注甚少。学术的生命力在于创新,但创新的前提与基础是继承,没有继承,就谈不上创新。自晚清民初以来,王国维、陈寅恪、胡适、陈垣等即已对海外汉学投以关注,其研究成绩事实上并不少。笔者粗略考察,仅1949年以前,中国学者评述域外汉学著作的书评即不下百篇。但令人遗憾的是,国内学界至今没有编纂一部关于海外中国学研究的索引目录或编年史。
有学者认为,编纂目录已是“陈年老皇历”。当今时代是一个高度信息化、数据化的时代,学者如需查找文献,完全可通过各种网络数据库。此观点虽有些道理,但也未必尽能。事实上,并非所有文献都已数据化,仍有相当一部分文献无法通过数据库查找;同时,网络数据库的查找多通过关键词、篇名、作者等进行检索,这种检索的前提是已确知要寻找的内容,但有许多是检索之前并不知晓的,这必然导致大量遗漏;再者,索引目录不仅可完整呈现学界已有的研究成果,更可为研究提供极大便利,正所谓“一册在手,信息尽收囊中”。
正是因为目录仍具有不可替代的意义,国内不少学者致力于海外中国学研究的目录建设。朱政惠先生曾主持完成“海外中国学研究中外文资料调查”的课题,“海外中国学研究之中英文论著目录”即是其中成果之一。北京外国语大学的张西平教授带领其团队致力于学术调查,将目录编制作为主要任务之一。在与德国汉学家魏汉茂(Hartmut Walravens)的合作下,再版了被誉为西方汉学目录奠基之作的《西人论中国书目》,并在全球范围内首次增加了索引卷。上海社科院的马军研究员则致力于搜集与整理1949年以前中国学术界译介海外中国研究的文献目录,先后在《海外中国学评论》《国际汉学》等刊物上发表了已完成的有关1949年以前中国学术界译介美国汉学、德国汉学、俄苏中国学、瑞典中国学的文献篇目汇编以及译介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Marco Polo,1254—1324)、瑞典汉学家高本汉(Bernhard Karlgren,1889—1978)、日本汉学家加藤繁(1880—1946)的篇目汇编等成果。
中国学术界所做的这些努力还远远不够,要深化和拓展海外中国学研究,在目录方面仍有许多亟待着手之事。比如,开设专门介绍域外中国研究动态,尤其是域外中国研究论著提要简介的刊物或栏目。早在民国时期,《图书季刊》《史学年报》《清华学报》《燕京学报》等学术期刊即刊有域外汉学著述的介绍,燕京大学主办的《史学消息》仅在1936—1937年就刊有“日本东洋史学论文提要”“现代日本东洋史学家的介绍”“西洋汉学论文提要”“各国关于汉学新刊书目”“欧美汉学研究文献目录”等介绍域外汉学资讯的文章。又如,编纂一部系统梳理近百年来国内研究海外中国学的论著目录和编年。编纂目录和编年,一方面可借此对20世纪这百年来国内的海外中国学研究史进行全面系统的盘点和梳理,另一方面亦便于学者了解前人所做研究概况,以避免做无谓的重复劳动。再如,编纂新的域外中国学家名录。国内学术界曾出版《日本的中国学家》《美国中国学手册》《俄苏中国学手册》《世界中国学家名录》以及《北美汉学家辞典》等,但这些工具书几乎都出版于20世纪。21世纪以来,海外中国研究领域内涌入一大批新生代学者,编纂新的域外中国学家名录已成当下之所需。另外,可继考狄、袁同礼之后再续编西人论中国书目。美国曾出版《美国的亚洲研究博士论文目录:1933—1962》(American Doctoral Dissertations on Asia,1933-1962,1963)、《西语中国研究博士论文目录:1945—1970》(Doctoral Dissertations on China: A Bibliography of Studies in Western Languages, 1945-1970, 1972)、《中国研究博士论文目录:1971—1975》(Doctoral Dissertations on China, 1971-1975,1978)等,并在1976年至1989年期间连续出版《亚洲研究博士论文目录》(Doctoral Dissertations on Asia)定期刊物,我们可据此整理制作较为完备的西语中国研究博士论文目录。美国亚洲学会亦曾出版《亚洲研究的累积目录:1941—1965》(Cumulative Bibliography of Asian Studies, 1941-1965,1970),我们同样可在此基础上,就中国研究书目及西语期刊中的中国研究论文进行整理编目。目录的编纂不仅是件“苦力工作”,甚至被认为“没有学术含量”而遭轻视。然而,“为人之学”的目录编纂,对海外中国学研究来说却是学科发展的基础,这亟待引起我们的重视并加强建设。
二、倡导学术批评性的海外中国学研究
中国近代以来的学术体系实际始自于20世纪20年代以来对西方的模仿。中国学术在引进西学的同时,助长了一种新的思想定见的形成,即凡是西方的都是“进步”的,凡是中国的都是“落后”的。因袭照搬西方话语,也就成了中国学术“进步”的标志,造成20世纪以来中国学术越来越“西化”。许多学者已习惯于“仰头看西方”,迷失了自我,成为西方学术的“传声器”,放弃了学术应有的主体性和批判性。每一次美国汉学模式的转换,从冲击反应说到中国中心观再到市民社会及文化人类学,中国学界都顺势出现与此相应的研究热潮。汪荣祖批评其在“跟着西方的风向转”①盛韵:《汪荣祖谈西方汉学得失》,《上海书评》2010年4月18日,“访谈”,第02版。。葛兆光亦批评说:“缺少平等而尖锐的批评,也许是这些年再次国门开启,中国学者又轮回到了晚清‘视西人若帝天’的时代罢,我们看到‘跟风太多’,以至国内学者以为外国的一切都好,只有亦步亦趋鹦鹉学舌。”②葛兆光:《从学术书评到研究综述——与博士生的一次讨论》,《杭州师范大学学报》2012年第5期。对于域外中国研究著述,我们必须清醒地意识到,它有特有的文化和学术背景,不能拿来就用,因为在不同学术传统中的概念和方法的转化和使用,必须经过严格的学术批判和反思。如果不对域外汉学著作进行学术性批判,一方面,我们不可能摸清其思路与方法,了解其话语和特点,学习其经验与长处,中国学者就不可能同国际汉学界进行真正的对话,在国际汉学界中中国只能是缺席者;更为重要的是,引进域外汉学的目的是为了我们自身学术和文化的变革与发展,立足中国本土的学问,在借鉴汉学的域外成果的基础上,从我们悠久的文化传统中创造出新的理论和方法,这才是我们真正的追求所在。如果仅限于介绍西方汉学走马灯似的各类新理论、新方法,我们自己则成了西方的东方主义的一个陪衬,失去了自己的话语和反思的能力。因此,我们在开展域外中国学研究时,亟需建立一种张西平先生所倡导的“批评的海外中国学研究”,即“站在中国学术自身的立场,在开放的态度下与域外汉学界展开对话;从跨文化的角度对域外汉学的历史展开研究,对西方汉学的西方中心主义和基督教本位主义给予学术的批判。同时,对当代的域外中国研究也应采取实事求是的态度,吸取其研究之长,批评其研究之短,在平等的对话中推进中国学术的建设和研究”。①张西平:《一个平等对话的时代开始了》,《中国社会科学报》2015年7月29日。
那么,如何才能建立起“批评性的海外中国学研究”?笔者以为,首先需要具有学术自信与自觉。无论是域内还是域外的中国研究,都是以中国为研究的本体。作为以中国为研究对象的学问,中国学人理应比域外学人拥有更具阐释的话语权。相对于域外研究者而言,生于斯长于斯的中国学人本身即拥有西人所无法具备的语言优势和“局内人”的洞察优势。在中国研究领域,中国学术缺乏的并不是研究的深度和见解,而是没有自信。自信是批判的前提,唯有具有学术自信与自觉,方能在思考的基础上进行分析与批判。当然,这种学术自信与自觉并非走向盲目排斥、一味否定的另一种极端,而是提醒我们应站在中国学术立场对域外中国研究进行富有学术性的考辨与批判,为中国学术自身发展提供镜鉴。其次需要海外中国学研究领域之外的专业学者积极就域外中国研究著述进行深度学术批评。当下的中国学界,由于学术性书评没有纳入学术成果的评价机制之内,专业学者不愿对域外研究著述进行深度学术评述;与此同时,专事海外中国学研究的学人,则又受专业限制无法对所有域外研究著述进行学术批判。建立批评的海外中国学研究,实需专业学者积极介入海外中国学,对与其专业相关的域外研究著述及时做出批判性回应。在这方面,民国学人为我们提供了有益的范例。彼时,域外每有汉学新著出版,相关专业的学人多会撰著书评对其进行评述。例如,美国汉学家德效骞(Homer H.Dubs,1892—1969)译注的《前汉史》(The History of the Former Han Dynasty,1938)出版后,专事五朝史研究的王伊同撰写了长达44页的书评,对其优点和所存错讹进行详细评述;美国汉学家卡特(Thomas Francis Carter,1882—1925)的《中国印刷术源流考》(The Invention of Printing in China and Its Spread Westward,1925)出版后,专事中国文化与制度史研究的邓嗣禹发表了长达21页的书评,指其在史料的博雅及解读上所存在的优劣得失。正是建立在对域外汉学的深度批判基础之上,民国学者成为国际汉学界不可或缺的一员。另外,需搭建开展学术批评的平台。环顾目前中国的学术出版物,没有一份专门对域外中国研究进行批评介绍的刊物,甚至与之相关的学术栏目亦不多见。这样的学术环境,不仅使针对域外中国研究著述进行学术批评的文章难觅发表园地,亦不利于形成对海外中国研究开展学术批评的氛围。1945年,著名史学家杨联陞曾向即将出任北大校长的胡适建议,出版一个像“史学评论”一类的特别注重批评介绍的杂志,他认为中国需要很多像伯希和(Paul Pelliot,1878—1945)一类的“汉学界的警察”。杨联陞的这一建议,亦是当下海外中国学研究界所亟需的。因为对域外研究中国学问的著述开展批评,是中国学人的职责所在。
三、勇于开拓海外中国学研究的新路径
对于如何开展海外中国学研究,李学勤、严绍璗、葛兆光、朱政惠、张西平等学者都有过深入思考。比如,李学勤先生认为对海外中国学的研究应该是学术史研究、思想史研究,他强调对海外中国学演变和发展规律的探讨,尤其关注中国学术思想对海外中国研究的影响及其演变特点问题。②此为李学勤先生在华东师范大学海外中国学研究中心于2006年6月举办的“20世纪上半叶的美国中国学”学术研讨会上的发言。严绍璗先生强调中国学者需要在“文化语境观念”“文学史观念”和“文本的原典性观念”上,做出深刻的反思,要关注海外中国学研究的“文化语境”,树立“学术史”观念,重视研究文本的原典性问题。③严绍璗:《对海外中国学研究的反思》,《探索与争鸣》2007年第2期。葛兆光先生认为,海外中国学研究本质上是“外国学”,“因其问题意识、研究思路乃至方法常常跟它本国的、当时的学术脉络、政治背景、观察立场密切相关。所以我们第一步就应该把‘中国学’还原到它自己的语境里去,把它看成该国的学术史、政治史、思想史的一个部分。”①葛兆光:《海外中国学本质上是“外国学”》,《文汇报》2008年10月5日。朱政惠先生从史学史的进路出发,视海外中国学研究为学术史研究,强调将其递嬗演变放在社会与思想的历史背景中考察,认为对海外中国学的研究要注意和这个国家的政治历史、中国的国际地位和国内状况、中国与相关国家的关系史、国际学术思潮、这个国家的民族文化及其母体语境、研究对象的背景和人物特点等相结合。②朱政惠:《近30年来中国学者的海外中国学研究:收获和思考》,《江西社会科学》2010年第4期。张西平先生提出应用历史学的、学术史的和比较文化的方法,在对海外中国学展开具体研究时应注意了解各国中国学研究的历史与传统、海外中国文化研究的学术背景和文化背景,同时积极与海外中国学展开学术互动,建立学术的自信与自觉。③张西平:《如何展开海外中国学的研究》,《寻根》2016年第1期。上述先生所倡导的这些研究理念,无疑是我们必须坚守和思考的方向。然而,要真正对海外中国学做深入的学术史考察,尤其是要将其置于所在国的文化语境和学术脉络中进行考察,所面临的难度和挑战可以想见。研究者不仅需要熟知研究对象国的汉学历史与思想文化史,亦需熟悉中国本土知识和文化,了解当代中国学术研究之进展。用张西平先生的话说,就是研究者需要“内外双修”。④张西平先生在中国比较文学海外汉学学会与上海外国语大学英语学院于2018年6月22—23日联合主办的第二届“全国高校国际汉学与中国文化外译学术研讨会”上做主旨发言时所提。缘于此,时至今日,我们的大多数研究仍停留在对海外中国研究的简单梳理上。对各国汉学发展史及汉学家进行“平面化”的条陈式梳理,以鸟瞰域外中国研究之总体概况,这仍是我们所需要做的。海外中国学研究作为一门学科,必须开展富有深度和学术内涵的研究。如此,海外中国学研究方能被人称为一门学科。
如何才能将这些研究理念转化为具有可操作性的研究路径?笔者以为,可结合其他学科所出现的新研究理路,探索出符合海外中国学研究特点的新路径。举例言之,概念史是一个近年来受到不少人青睐的研究方法。它所查考的是不同文化中的重要概念及其发展变化,并揭示特定词语的不同语境和联想。在海外中国学研究中,我们可应用概念史的研究方法,对海外中国研究中的重要概念及其变化进行梳理和考证,解读其变化背后的历史缘由。有学者就应用概念史的方法,查考“中华帝国”这一概念在西方的起源,梳理欧洲建构“中华帝国”话语所经历的历史过程。⑤陈波:《西方“中华帝国”概念的起源》,《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5期。又如,新文化史研究作为一种新的研究方法和研究视角,是将社会的和文化的历史作为一种整体加以看待,不以追究事实真相为研究的唯一目的,而是强调思考过程的研究。我们可借由新文化史的研究理念和方法,从书籍史和阅读史的角度切入,考察海外中国研究著述在其本国的接受和阅读,尤可探讨其在国际的流布、评议及影响,并解读不同评价背后的思想文化。再如,在以跨文化方法研究中国文化对外传播时,我们可考察中国文化传播到域外的路径方式及其在域外的译介研究,同时更应关注异域文明对中国文化的内化接受情况;对于海外中国学家的研究,需要对其人生历程和学术历程等进行平面化梳理,更需要借助“人际交往网络”或“知识环境史”的视角,探讨他的学术和人际交往圈或其成长的知识环境,从而在学术史和文化语境的观照下对其学术思想史做深入探讨。总之,唯有秉持“学术史”和“文化语境”之理念,尝试运用新的研究方法和视角,进行交错的“立体式”研究,方可能建构起真正具有学术史和文化语境意义的海外中国学研究。
四、推进不同研究领域和方向的交流与融合
海外中国研究涉及的范围非常广,既包括对中国传统历史文化的研究,亦包括对当代中国政治经济社会的研究,举凡中国的历史、文学、哲学、政治、经济、社会、军事等,都在其研究范围之内。朱政惠先生认为要对海外中国学开展研究,只能是各个学科按照自己的学科规范对其进行探讨,倡导“化整为零”“各个击破”。①朱政惠、吴原元:《近二十年来国内海外中国学研究的基本状况及若干思考》,《汉学研究》第10辑,北京:学苑出版社,2007年。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海外中国学研究大多是依托某一学科,按照其学科的规范和方法展开研究。比如,有从史学史和史学理论学科出发对海外中国历史研究专家、海外中国历史著作、海外学者中国观及其史学理论、史学方法、史学机构沿革等进行研究;有从比较文学的学科方法论出发,探讨中国文化域外传播的轨迹和方式以及进入对象国后的传播及其变异的状态;有从翻译学学科出发,注重探讨域外对中国典籍或文学作品的翻译,以及不同翻译策略背后所隐含的思想文化意义等。
依托各自学科的规范和方法,无疑有助于推动海外中国学研究的开展。与之同时,亦存在不容忽视的问题。域外中国研究注重跨学科,倡导在从事中国研究时采用多学科的理论与方法。费正清在从事中国研究时,就呼吁应“在历史学家、语言学家、考古学家、艺术史或是文学家们所熟悉的汉学方法基础之上增加一些人类学、社会学、经济学和政治学方面的技巧”。②Edwin O.Reischauerl, John K.Fairbank, “Understanding the Far East Through Area Study,” Far Eastern Survey 17.10 (1948): 122.这或许就是域外的中国研究能够提出新颖理论和观点的原因所在。正如王汎森所说,“西方汉学的长处是在建构、理论、框架、比较的视野,以及说出某一个东西比较广的意义”,它们是“以众学来治一学”。③王汎森:《海外汉学研究的长短之处》,《新京报》2013年10月16日。如果仅按照某一学科理论和方法来开展海外中国学研究,不仅无法对其进行正确解读,更无力对其理论观点进行应有的学术批判。
张西平先生曾就西方汉学分析指出:“在西方有一种误解,似乎当代中国研究和历史中国研究是对立、分割的。有西方学者认为历史中国灿烂辉煌,但已消失,只存在于博物馆里;当代中国经济成就伟大,但由于政治体制不同,无法产生亲近感。”他认为:“对西方汉学界来说,打通历史中国和当代中国的视域界限,用完整的中国观深化汉学研究非常重要。”④转引自毛莉:《用完整的中国观深化汉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报》2014年8年18日。澳大利亚著名“中国通”陆克文(Kevin Rudd)亦就西方汉学所存问题表示:“汉学在内部建立了很多派别,这些派别要么叫做古典中国学,要么叫做现代中国学;有可能是儒家学者,也有可能是唐史学家,相互之间不能集大成。甚至有的派别是中国经济方面的专家,但是他们没有把对中国经济的理解和中国的政治、经济状况结合起来,不能理解中国政治中的核心概念。”他认为,“在汉学领域发展出这么多的专业是一件好事”,但“应该对中国有集大成的分析”。⑤陆克文:《新汉学,让世界读懂“学术的中国”》,《中国社会科学报》2017年12月15日。他们虽是就域外中国研究而言,笔者以为这亦是国内的海外中国学研究所面临的问题所在。在推进以各自学科的规范和方法开展海外中国学研究时,我们应考虑如何建构起所研究对象国的完整中国学图谱,如何用整体性视阈观照和深化所探讨对象国的中国研究。
陆克文就未来汉学发展提出应倡导“新汉学”,必须“打破过去很多年来所形成的各个专科之间的人为的壁垒和藩篱”,以形成对中国的“更大的全局观”。未来的海外中国学研究亦应如此。面对涉及如此多领域的海外中国学,我们仍需以具体学科为依托展开研究,舍此别无他法。然而,在此基础上,我们亦必须意识到推进不同学科及研究领域的交流与整合之必要性。就像费正清倡导以“区域研究”开展中国研究那样,在致力推动经济学、政治学、法学、人类学等学科涉入中国研究之同时,亦强调各学科在开展中国研究时的融合。在他的努力之下,曾专门组织“中国研究与社会科学学科”讨论会,来自不同学科领域的学者就中国研究的学科融合进行讨论。牟复礼(Frederick W.Mote,1922—2005)的观点颇具代表性,他认为无论是语言文字、哲学还是社会学、经济学、人类学等,都“只是一个更大的研究领域的分支”,“我们必须把它们当作工具而不是偶像,或者再借用地理比喻来说,必须把它们看作是地图上的完美线条而不是标明中国文明实际划分的沙漠和海洋”。⑥Frederick W.Mote, “The Case for the Integrity of Sinology,”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23.4 (1964): 533.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倡导运用多学科理论和方法,注重各学科理论方法的融合在美国中国学界蔚然成风。因此,唯有从事海外中国学研究的各学科之间形成有效的交流与融合,海外中国学研究才能真正走向深入,才能加深对域外汉学的理解。
如何推进海外中国学研究内不同领域和方向的交流与融合?笔者以为,首先应打破“学科拜物教”,树立交流融合之意识。史华慈(Benjamin Schwartz,1916—1999)曾精辟指出:“如果一个修养有限的人只会机械地应用某种孤立的‘学科’方法,而这门学科又是狭隘地孕育于某种自我封闭的文化‘模式’或‘体系’(无论是当代的还是‘传统’的),那么往往都会得到呆板甚至荒谬的结果。”①Benjamin Schwartz, “The fetish of the Disciplines,”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23.4 (1964): 537-538.其次,在培养海外中国学研究的专业人才时,应有意识地鼓励其跨学科的知识视野。另外,应倡导“合作研究方法”。比如,可由依托不同学科及方法论的中国学研究者组成合作研究小组,定期举行研究讨论,进行学科观点的交流。跨学科研究和多学科方法理论的融合已是当今人文社会科学发展之趋势,唯有形成有效的交流与融合,海外中国学研究才能走向深入。
今天的时代,是一个急剧变革的时代。伴随着时代变革,海外中国学研究正面临全新的时代环境和使命。作为一门学科,唯有勇于革新,担负起所应承担的使命与任务,才能拥有美好明天。在新时代里,海外中国学研究只要继续坚持不懈,朝着上述方向不断努力,富有学术内涵和深度的海外中国学研究之“春天”一定会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