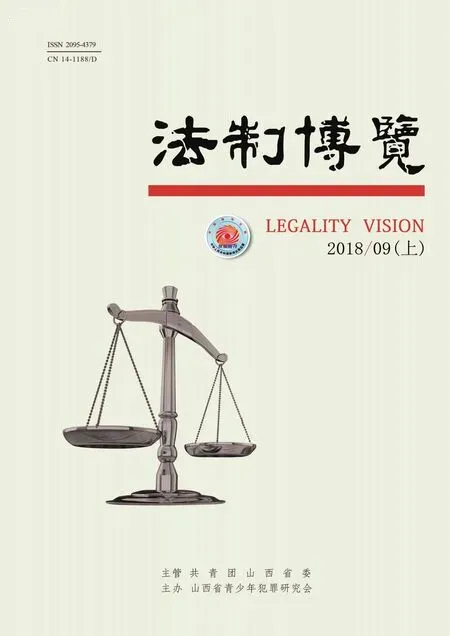不方便法院原则在我国涉外离婚案件中适用研究
2018-01-22李婷
李 婷
西南政法大学,重庆 310018
一、不方便法院原则的概况
(一)不方便法院原则的概念
无论是从当事人角度还是受诉法院角度出发定义该原则,都可提炼为:法院在受理某一涉外民商事案件时,本国法院是具有管辖权的,可以进行案件的审判,发现但若进行下去会造成对被告的不公平或者本国法院不方便,并且又存在另一国法院可作为受理此案的替代法院,于是法院便以本院是非方便法院为由,拒绝行使管辖权,以避免平行诉讼的发生。
(二)不方便法院原则的历史沿革
不方便法院原则起源于英美法系国家,至今已有四百多年的历史。这一原则在英美法系国家的发展过程也是源远流长的。起初由最先的个案判例衍生到成为法院适用的一项法律原则,其发展的空间进程也由苏格兰地方法院过渡到英国法的适用,进一步传播欧美,走向全球乃至世界的发展进程当中。随着时代的变迁与进步,经济全球化节奏的加快,体现法官自由裁量权的不方便法院原则也处于不断变化发展中。可见我国作为大陆法系国家,并不接受不方便法院原则,通常却都存在一些替代性规则,尤其在婚姻家庭法领域。值得关注的是在2015年我国出台的《民诉解释》中,第一次将不方便法院原则的适用从海商事领域扩展到了涉外民事领域。[1]
二、我国涉外离婚管辖的现状
(一)立法现状
涉外离婚案件管辖权是指一国法院受理涉外离婚案件的权限范围。我国关于涉外离婚管辖权的规定不集中且不完整,都是零散的分布在之后的司法解释中,民事诉讼法的一般规定也涉及到一部分,从而一步一步实现了“管辖权扩张”。[2]
(二)司法实践
在涉外离婚案诉讼中,由于双方当事人的国籍不同,或者在两个或两个以上国家拥有住所,[3]原告方向法院提起诉讼时,有可能存在两个或两个以上国家的法院对同一涉外民事案件同时行使管辖权的情形。而且各个国家采取确立管辖权的原则和依据不同,关于涉外离婚案件的规定也不相同。尤其婚姻案件的特殊属性,各个国家不一样的历史文化传统,关系到各自的公序良俗,目前国际社会也没有一套合理、有效的关于离婚诉讼管辖权的法律制度。
三、不方便法院原则在我国涉外离婚案中适用的必要性及可行性分析
在涉外离婚案件中选择遵循不方便法院原则,是要解决管辖权积极冲突和由此产生的挑选法院、矛盾判决这两方面的问题。在这一原则的指引下,当事人可以在两个具有管辖权的法院之间选择一个最合适的法院来进行诉讼。[4]不方便法院原则以公平正义为前提,法官加以运用自由裁量权,使双方利益都得到最大程度的保护,从而使涉外离婚案件的双方当事人感受到公平正义。
(一)必要性
1.修正我国涉外离婚“过度管辖”的需要
涉外离婚案件的过度管辖虽然能保护我国当事人和国家的利益,与此同时会给对方造成了不公正的审判结果,得到的判决在外国也很难会去承认与执行,最终我国当事人的利益还是得不到保护。所以,从坚持国际协调原则的角度出发,有必要修正我国涉外离婚的“过渡管辖”。
2.限制我国涉外离婚管辖中平行诉讼的需要
在涉外离婚平行诉讼中通过向英美国家学习以不方便法院原则来限制平行诉讼,从而解决管辖权的积极冲突。[5]在我国不方便行使审判权的涉外离婚诉讼中,运用不方便法院原则,避免了两个及两个以上国家间的管辖权积极冲突,使案件得到更为公正、合理的审判,一国的判决也将会得到他国的承认与执行。
3.平衡双方当事人利益
由于涉外离婚诉讼法院的可选择性,涉外离婚案件当事人在选择法院管辖时必然会优先选择最有利于自己的法院。这样带来的不利后果是对方当事人的权利受损,难以从实质上保证司法公正。一旦建立了不方便法院原则,我国法官在处理涉外离婚案件时,就能够运用自由裁量权,凭借理性判断原告选择管辖权选择是否能够保证司法公正、维护当事人双方利益,作出最佳的管辖权判断。
4.适应我国区际司法现状
不方便法院原则旨在解决不同法域之间的管辖权冲突。法官行使自由裁量权,从维护公平正义、选择最佳法院管辖等方面来实现不同法域之间的当事人利益。但它建立在不同法域的基础之上,而我国由于众所周知的政治、历史原因,内地和港澳台分别采取不同的司法制度来处理案件。那么构建不方便法院原则就非常有必要,它有利于解决我国区际之间的离婚管辖权冲突,从而同样能够维护区际之间的当事人利益。
(二)可行性
我国法官享有自由裁量权。规则是僵硬的,而案件各有其特定,要通过一套成文法平等地适用于所有案件显然不利于实质上的正义。因此,无论是在立法事实上,还是在司法实践中,我国法官都能够行使自由裁量权,在面对各类复杂的案件中运用理性作出判断。
中国引入不方便法院原则从立法上和实践中两个方面来看,是可行的。立法现状中没有宪法上的障碍,在诉讼法中亦有很多关于法官行使自由裁量权的规定。立足实践方面,已然出现了相关判例。立法有其局限性,它没有和社会发展亦步亦趋,而是滞后于社会发展。我国是成文法国家,一切司法行为都应当有法可依。但在司法实践中,法官在经验的积累中,能够形成一套真正有利于司法公正和纠纷解决的知识。比如法官遇到不应受理的案件时,会采取与不方便法院原则精神内涵相一致的处理方法,即行使自由裁量权拒绝受理个案。比如赵碧琐确认产权案、东亚银行信用证案,在这类案件中法官应用了自由裁量权来实现个案的正义。我国立法没有在管辖权中规定法官的自由裁量权,但却隐含在立法事实和司法实践中。法律的本质是实践性,应当在实践的基础上不断完善立法。可见,对于不方便法院原则,应当通过立法的途径予以规范,使之更加明确,更具有可操作性。
四、涉外离婚案件中适用不方便法院原则可能存在的弊端
首先,由于我国民事诉讼法缺乏对不方便法院原则的明确规定,司法实践中并未明确适用该原则,而是以“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和“本案应由当地法院管辖为宜”等作为拒绝管辖的理由,不方便法院原则的适用仍然是模棱两可的处境,也不利于判决的统一和个案的公正。
其次,也是由于缺乏明确细致的规定,导致具体案件中适用不方便法院原则没有明确的标准和适用的方式。现有规定对于不方便法院原则的适用将被告作为启动程序的唯一主体,却未规定被告提出案件由更方便外国法院管辖的期限和当事人的举证责任,采用驳回起诉的方式拒绝行使管辖权,将会为实践的操作带来诸多困难,必须加以完善。[6]
再者,适用不方便法院原则可能导致司法成本的大量消耗以及案件无法院受理的局面。一旦法官适用该原则,当事人就不得不另选法院,在其中消耗时间成本,导致案件得不到及时有效的解决。此外,在原受理法院行使该原则作出拒绝受理的决定后,其他有管辖权的法院也作出了拒绝受理的决定,案件又不能回到原受理法院,最终的后果是案件没有法院来受理。这对于纠纷的解决显然是非常不利的。
五、不方便法院原则在涉外离婚案件适用中的完善与构建
兼采当事人主义与职权主义模式能够取长补短,利于不方便法院原则的构建。当事人主义的核心要素是意思自治,职权主义的核心要素是司法权的介入,两者兼而采之能够平衡两者,使之优势互补,在发挥当事人的作用的同时,增加法官对当事人诉求的审查和判断。从民诉法解释(二)第532条的条款中可以看出,我国采用了当事人主义启动模式,较之兼采模式多有不足。应充分考虑当事人与法院的权利与职权,建议我国不方便法院原则以兼采模式为优。这一原则的运用条件和前提应进行合理地限定。[7]
完善不方便法院原则的核心是构建以限制法官的自由裁量权为核心的制度。首先,应在立法上规范赋予法官的自由裁量权,这有待于我国立法和司法解释在这方面的投入。而涉及不方便法院原则的规定在我国当前的立法中较为零散,亟待体系化与制度化。只有在立法上对不方便法院原则予以明确,使之制度化与具体化,法官在行使自由裁量权的时候才能有法可依;其次,不方便法院原则有其灵活性的特点,即赋予自由裁量权于法官,要求法官在适用个案的过程中,结合具体的情形,适用不方便法院原则以优先顾及案件的公平正义。那么,这个自由裁量权应当在什么时候适用,适用范围以及权限有多大就绝不能忽视。否则,很容易导致法官滥用自由裁量权。因此,除了立法对不方便法院原则予以明确之外,还必须建立一套严格的程序来限制法官的自由裁量权。合理的自由裁量权非常有赖于法官的职业道德,应当在实践中注重法官职业道德的培养;此外,我国已经构建了一套较为完善的纠纷解决机制,完善不方便法院原则应当注意与我国现行制度的衔接。我国纠纷解决机制包括诉讼解决机制与非诉解决机制(如仲裁、调解),完善不方便管辖原则尤其应当发挥非诉解决机制在国际民商事纠纷的作用。
在涉外离婚领域中,不方便法院原则确能起到实现个案正义的作用。法官在进行管辖权审理时,一旦发现本院受理此案可能造成不利于司法公正的后果,便可以行使自由裁量权来排除本院对该案的管辖权。不方便管辖原则是对宽泛管辖权的一个回应与限制,它在一定消除了宽泛管辖权带来的不利后果,同时使得管辖权适用规则更具有灵活性。显然,不方便管辖原则的出现使管辖权的应用达到了一种平衡,司法在这种平衡状态中趋于公正。但是,不当的自由裁量权适用也会带来多种不利影响,不仅有可能损害司法公正,还有可能引起外国法院的反报,如对案件的裁判不予承认。因此,必须赋予当事人以救济权,最大可能地防止法官错误适用自由裁量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