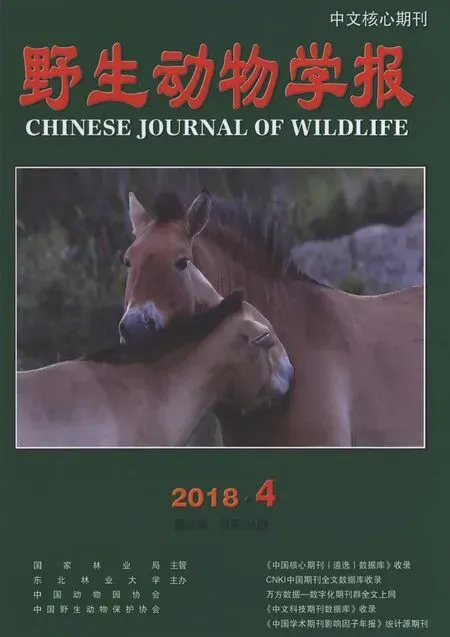我国在CITES公约附录动物保护执法中存在的问题
2018-01-22周用武马艳君刘大伟
周用武 马艳君 刘大伟
(国家林业局森林公安司法鉴定中心;南京森林警察学院刑事科学技术学院;野生动植物物证技术国家林业局重点实验室,南京,210023)
《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简称CITES公约)已有5600多种动物和30000多种植物被列入附录,使得世界范围内60%~65%的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得到了有效控制[1],强有力地保护了全球的濒危物种。CITES公约于1981年在中国正式生效,中国政府为了履约,专门设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濒危物种进出口管理办公室,并于1988年制定并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出台了一系列配套的法律法规来保护全球濒危野生动物。38年间,中国在保护濒危物种方面展示了负责任大国的形象,成功保护了藏羚(Pantholopshodgsoni)、朱鹮(Nipponianippon)、大熊猫(Ailuropodamelanoleuca)等国际濒危物种,并信守对国际社会的承诺,自2018年1月1日起在中国全面禁止象牙的商业贸易,为全球濒危物种的保护树立了良好的典范[2]。中国进入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新时代,建设生态文明和谐美丽新中国,保护濒危野生动植物等自然资源将显得更为重要。
CITES公约在中国的实施,对保护国内外濒危野生动植物资源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尤其是那些进入中国的在中国无自然分布或者已经野外灭绝的动植物物种资源。当然,CITES公约在中国要得到贯彻并执行,必须要得到国内相应法律法规的配合。近40年来,我国配套的法律法规在执行CITES公约方面起到了良好的助力,在打击涉及CITES附录物种的违法犯罪方面收到了良好的效果;我国濒危物种的保护执法机关,森林公安和海关缉私部门多次获得了克拉克·巴文野生动植物国际执法奖,受到了广泛的赞誉[3-5]。但是,目前我国在CITES公约附录动物的保护执法中也还存在一些衔接方面的问题,需要进一步梳理并研究,以便下次相关法律法规修订时能理顺,使相关的执法更顺畅,更有力度,取得更好的效果,更好地保护国际濒危野生动物。
1 存在的问题
1.1 保护级别参照困难
2017年1月1日起,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第三十五条提出“中华人民共和国缔结或者参加的国际公约禁止或者限制贸易的野生动物或者其制品名录,经国务院野生动物保护主管部门核准,在本法适用范围内可以按照国家重点保护的野生动物管理”。根据《国家林业局、公安部关于森林和陆生野生动物刑事案件管辖及立案标准的通知》(林安发[2001]156号)规定“非法猎捕、杀害、收购、运输、出售、走私《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附录Ⅰ、附录Ⅱ所列陆生野生动物的,其立案标准参照附表中同属或者同科的国家Ⅰ、Ⅱ级保护野生动物的立案标准执行”。
由于上述有关的法律法规都比较笼统,且存在新法旧规同时都在执行,具体操作的时候就存在保护级别不对应或者分类地位不对应的问题。
有些国外进入中国的野生动物物种与国内分布的物种同科同属,但是保护级别不同,即CITES公约附录Ⅰ中列入的动物有些在中国国家重点保护动物名录里没有与其同科同属的国家Ⅰ级保护动物,要想对应参照就无法实现。例如非洲灰鹦鹉(Psittacuserithacus)目前在CITES公约里列入附录I,对应参照就应该是中国分布的鹦鹉科(Psittacidae)中的Ⅰ级重点保护动物,而实际情况是中国分布的所有的鹦鹉都是Ⅱ级重点保护动物。
类似的情况是,有些列入CITES公约附录Ⅱ的物种在中国分布的与其同科同属的物种里没有国家Ⅱ级重点保护动物可供参照。例如,近年来两栖爬行动物宠物饲养和贸易已成为不可遏制的潮流[6-7]。有很多寻求刺激的年轻人喜欢当宠物养的球蟒(Pythonregius)属于蟒科(Pythonidae)[8],而我国的蟒科动物中只有蟒(Pythonmolurus)是国家Ⅰ级重点保护保护动物,与球蟒被列入CITES公约附录Ⅱ不对应。
另外,有些CITES公约附录Ⅰ或Ⅱ中的物种在中国就没有与其同科同属的物种分布或者同科同属的物种就没有被列入我国的重点保护动物名录。例如,鳄目(Crocodylia)鳄科(Crocodylidae)的暹罗鳄(Crocodylussiamensis)被列入CITES公约附录Ⅰ,我国分布的鳄目鼍科(Alligatoridae)的扬子鳄(Alligatorsinensis)被列入国家Ⅰ级重点保护动物名录[9],保护级别虽然对应,但是分类地位不相同,即不属于同一个科或属,按现有的立案标准和司法解释,则不可参照。类似的还有红尾蚺(Boaconstrictor)、绿树蟒(Chondropythonviridis)、各种避役(Chamaeleospp.)等物种。
1.2 涉案价值不易核定
目前进入到我国的CITES公约附录动物种类非常丰富,相应的动物制品也越来越多,我国关于此类动物制品的立案通常是根据其价值来确定的。目前关于CITES公约附录动物制品价值的核定要根据国家林业局2017年公布的46号令《野生动物及其制品价值评估方法》来执行。该令第八条提到《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附录所列在我国没有自然分布的野生动物,已经国家林业局核准按照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管理的,该野生动物及其制品的价值按照与其同属、同科或者同目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的价值核算。而同一文件的第五条提到“野生动物制品的价值,由核算其价值的执法机关或者评估机构根据实际情况予以核算,但不能超过该种野生动物的整体价值”。
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自2017年1月1日起实施以来,国家林业局没有对CITES公约附录所列在我国没有自然分布的野生动物的物种进行过核准,只能按原林业部(林护通字[1993]48号)文件《林业部关于核准部分濒危野生动物为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的通知》来执行。而此文件至今已有25年,过于老旧,CITES公约附录Ⅰ中的暹罗鳄在中国有大量合法与非法的繁育,如果还将其核定为国家Ⅰ级重点保护动物,参照国家Ⅰ级保护动物扬子鳄来折算其价值则明显过高。
如上文所述,“野生动物制品的价值,由核算其价值的执法机关或者评估机构根据实际情况予以核算,但不能超过该种野生动物的整体价值”。如何根据实际情况予以核算?该评估方法无具体细则,其价值变动幅度过大,不具备可操作性,不利于保护执法。因为林安发[2001]156号文件的立案标准中关于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制品的立案标准中有两档,野生动物制品价值达10万元或非法获利5万元应该立重大刑事案件,制品价值达20万元或非法获利10万元应该立特别重大刑事案件。评估的价值变动幅度过大,可能导致的直接结果就是不同人、不同的执法机关、不同评估机构评估的价值就会有很大差异,会造成案件的性质截然不同。
1.3 保护名录更新不同步
由于我国地域比较辽阔,物种比较丰富,对很多动物的研究不是很透彻,再加上不同的学者观点不一致,水生动物和陆生动物的管理部门不同,造成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名录自1989年公布以后,除了2002年10月24日国务院批准将麝科(Moschidae)动物的保护级别从国家Ⅱ级重点保护动物调整为Ⅰ级重点保护动物以外,近30年来几乎没有什么变动。2000年由国家林业局制定并公布的《国家保护的有益的或者有重要经济、科学研究价值的陆生野生动物名录》(2017年改称《有重要生态、科学和社会价值的陆生野生动物保护名录》,简称“三有动物”名录)也有18年未曾变动。然而,整个自然环境和社会经济发生了重大变化,各种动物的濒危情况也发生了很大变化,CITES公约附录则是根据物种的濒危情况在很短的间隔时间就会变更。因此,目前的问题是国内的野生动物保护名录与CITES公约附录动物名录不同步,造成在中国分布的列入CITES公约附录中的动物保护执法力度有偏差。
比如穿山甲(Manisspp.)在全世界共有8种[10],由于药用、食用和栖息地破坏等诸多原因,现在已经非常濒危,第17届CITES公约缔约方大会已将其提升为CITES附录Ⅰ的物种,严格禁止贸易。然而,目前在中国分布的穿山甲(Manispentadactyla)仍然为国家Ⅱ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虽然8种穿山甲都列入了CITES公约附录Ⅰ,但在中国目前也只能按Ⅱ级重点保护动物的相关规定来立案。
1.4 执法程度有偏差
有不少在我国分布的物种,既被列入了“有重要生态、科学和社会价值的陆生野生动物”名录(简称“三有动物”名录),同时也被列入了CITES公约附录Ⅱ。如果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破坏野生动物资源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00]37号),列入CITES公约附录Ⅱ的物种按珍贵濒危物种对待,就应该对应Ⅱ级保护动物,而如果按照原林业部的文件,只有非原产我国的CITES公约附录Ⅱ的物种才能核准为Ⅱ级。就其效力来说,应该是时间在后的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大于已被裁撤的林业部的部门规定,也即是这些物种在中国本来就有分布列入“三有动物”名录的动物得按珍贵濒危动物对待。其结果就是,根据相应的立案标准,原来按“三有动物”可能不够刑事案件的行为,现在按“珍贵濒危动物”就达到了刑事案件的构成要件。例如豹猫(Prionailurusbengalensis)、画眉(Garrulaxcanorus)、银耳相思鸟(Leiothrixargentauris)、鹩哥(Graculareligiosa)、孟加拉眼镜蛇(Najakaouthia)等中国分布的既列入“三有动物”名录同时又列入CITES公约附录Ⅱ的物种,目前在自然状态下还是比较常见的,人工繁育的种群数量也比较大,如果将其作为CITES公约附录Ⅱ物种以“珍贵濒危野生动物”来对待,非法捕捉、杀害、收购、运输和出售这类动物都构成犯罪,花鸟市场中买卖画眉、鹩哥等动物都将构成犯罪[11-12]。很明显,如此执法就会过重,将普通的养鸟人作为罪犯进行打击,不利于社会的和谐稳定,违背了立法的初衷。也有不同地方对司法解释和部门规章采用另外的处理方式,认为主管部门对野生动物的情况更了解,更加专业,应该根据主管部门的行政规章来执法。但是,主管部门制定的“三有动物”名录已有18年未更新,原有的问题也没有得到修正,据此执法对某些物种而言则又存在执法过轻的问题。例如,东方白鹳(Ciconiaboyciana)数量非常稀少[13],在中国被列入“三有动物”名录,同时也列入了CITES公约附录Ⅰ,但是涉及“三有动物”的罪名只有“非法狩猎罪”,收购、运输、出售这些动物都不构成犯罪,对惩治这类犯罪活动的执法力度是很小的。因此,这类在中国有分布列入CITES公约附录Ⅰ的动物的保护执法力度则偏轻,没有达到列入CITES公约附录Ⅰ的目的。
1.5 鉴定难度大
在保护执法中,需要对动物的物种进行鉴定,以确定是否属于CITES公约附录物种。然而由于CITES公约是国际公约,附录中的动物来自全球,种类极其丰富,其中有些物种列入了附录,而有些相似的物种却没有列入附录。要将这些种类极丰富的或者极近似的物种确定出来,对鉴定机构和鉴定人而言都有很大的难度。而且随着我国法治化国家建设的需要,以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司法鉴定管理问题的决定》的相关文件出台,对鉴定机构和鉴定人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目前,能从事CITES公约附录动物鉴定的有资质的鉴定机构和鉴定人员都很缺乏。
由于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与国际上的来往越来越频繁,从国外进入中国的CITES公约附录动物也越来越多。由于执法中涉及的附录动物物种数量多,来源地丰富,有不少物种在中国甚至没有同科的动物,例如悬猴科(Cebidae)、吸蜜鹦鹉科(Loriidae)、美洲鬣蜥科(Iguanidae)、避役科(Chamaeleonidae)等很多科的动物,我国的鉴定人员可能根本就没有见过这些动物,要想准确确定其物种是非常困难的,超出了现有鉴定机构和鉴定人员的鉴定能力。由于来源地不同,世界各地对这些物种的研究也不一样,有些新近发现的物种可能还没有更进一步的研究,用于鉴定的资料还不全面,而且我国的各鉴定机构也很难收集齐全分布于全球的所有CITES公约附录动物的鉴定资料。
由于鉴定机构和鉴定资料的欠缺,鉴定人员的鉴定能力不足,目前关于CITES公约附录动物的鉴定也还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CITES公约现有183个缔约方,各方的执法情况和力度都会有差异,例如对象牙的贸易,中国和美国的国内执法就有很大差异。自2018年1月1日起,中国已在国内全面禁止了象牙的商业贸易,而美国的情况就不一样。执法标准的不统一,服务于执法的物种鉴定也没有统一的规范,不利于CITES公约附录动物物种执法信息的交流,这些都给执法带来了很多困难。
2 对策
随着人类活动的日益全球化,CITES公约附录动物的保护执法也会越来越重视,这也是共建全球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一个部分。针对上述CITES公约附录动物在我国保护执法中存在的问题,提出如下相应对策,以期能进一步加强相关的保护执法,更好地保护CITES附录动物。
2.1 加强对CITES公约保护机制的研究
CITES公约已成为控制野生动植物及其产品国际贸易、保护生物多样性的一项有效的、可操作性强的国际条约[1]。我国是CITES公约的缔约方,积极履约必须以对公约的了解和掌握为基础,我国有必要加强CITES公约研究[14]。
要加强对公约条款的研究,CITES公约在我国要符合实际的国情,要实现本土化,要与我国的野生动植物保护结合起来。既要履行对公约的约定,又要符合我国的实际情况,还需要把我国需要国际配合执法的物种加入到公约附录中去,加强濒危物种进出口贸易的规范和监管。同时,对公约涉及物种保护、物种管理、相关立法和执法以及相关合作的机制也需要进行研究。
2.2 加强相关的国际合作
CITES公约是一个国际条约,在执行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需要加强相关的国际合作。
首先,要加强物种信息的国际合作。CITES公约附录动物的物种信息是非常重要的,这是公约控制野生动物及其制品国际贸易的根本和基础。如前文所述,CITES公约附录动物关注的是全球的珍贵濒危动物,而这些物种的信息没有一个国家可能全部收集齐全,它需要国际合作以保证物种的信息能广泛传递,让执法者能准确确定控制的对象,否则会发生张冠李戴的情况:该被保护的没有得到保护,不该被保护的反而得到了保护[15]。
其次,要加强执法信息的国际合作。CITES公约附录动物及其制品的非法贸易是国际化的,有多个中间环节。其各环节和渠道的封堵和执法也需要国际合作,来源地、中转地和目的地大多数时候会跨越多个国家,需要各个国家之间互通信息、互相配合。非法贸易的过程中还涉及资金的流动,运输工具移动和违法犯罪人员的活动,这些都需要通过国际合作来提供信息。
2.3 加强CITES公约附录动物的研究
CITES公约附录动物是我们保护执法的对象,要对其进行保护执法,必须要加强对CITES公约附录物种的研究。
CITES公约附录动物与我国重点保护名录及“三有动物”名录采用的分类系统目前也不一致,有些物种还存在同物异名的情况,目、科等级别的分类阶元也有不统一的情况。我国的野生动物名录一般以种为具体的保护对象,而CITES公约附录中有些物种则以种下分类阶元——亚种甚至根据来源地确定保护对象,在具体的保护执法工作中如何更准确地实施是很重要的。这些情况都需要在对附录物种进行研究后,加以明确,使之与国际接轨。
同时,还需要加强对在我国分布的CITES公约附录动物的数量、种群情况和生存状况的研究。对于既列入CITES公约附录也列入“三有动物”名录的动物要挑出来专门进行调查研究,确实非常濒危的动物应该逐一核定为珍贵、濒危动物,数量很多且生存状况良好的动物则明确为一般保护动物。
2.4 加快法律法规的制定
2017年1月1日起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正式实施,其中提到了CITES公约附录动物在中国的保护条款。然而配套的法规和细则目前还有很不完备的地方,有的法规和细则还没制定,有的还是以过去的文件来代替,还有的则在实施过程中发现不具有可操作的情况,比如如何参照级别、核定价值等。这些情况都不利于CITES公约附录动物在中国的保护执法。因此,必须加快相关法律法规的制定,并根据执行情况不断加以修正,使CITES公约附录动物的保护在中国落到实处。
主管部门应该根据CITES公约附录动物在我国保护执法的具体情况,制定专门的法规对其如何参照在我国分布的野生动物的保护级别进行规定。
主管部门需要对常见涉案附录动物制品的价值情况进行调查,制定相应的动物制品价值折算细则,规定不同动物种类、不同动物制品类型应该如何折算其价值。
同时,主管部门还需要积极协调野生动物保护涉及的各部门,及时对国家重点保护动物名录加以更新,尽量与CITES公约附录动物名录的更新同步,使之与国际野生动物保护的执法相衔接。
2.5 加强动物鉴定技术与规范的研究
CITES附录动物及其制品的鉴定难度大主要是物种丰富、鉴定资料、鉴定技术和规范欠缺,要解决这个问题,必须加强动物鉴定技术和规范的研究。一方面可以通过国际合作,获得国际上成熟的物种鉴定技术和规范,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进行研究,内化为我国的鉴定技术和标准。另一方面各从事动物研究和鉴定的机构要联合起来,从不同的角度相互协作,加强我国野生动物鉴定技术的研究,制定相应的标准和规范[16],尤其是需要加强CITES公约附录动物近缘物种及其制品的鉴定方法和技术的研究,为野生动物的保护执法提供技术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