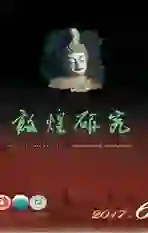论吐鲁番随葬衣物疏中的“海东头、海西壁”
2018-01-20许飞
许飞
内容摘要:吐鲁番出土的麹氏高昌国时期的随葬衣物疏中常有一句“若欲求海东头,若欲觅海西壁”比较难解,中日学者认为这是指鬼魂的去处。而从当时吐鲁番汉民族的冥界观来看,鬼魂的去处不是“海”而是地下的坟墓。南北朝时期的买地券的制作者为了避免鬼神烦扰,在落款处常使用替身,并且有的同时给替身一个无法找到的去处。衣物疏作者也使用替身,而且替身有的与买地券相同,因而这句话实际是指替身——张坚固、李定度的去处。
关键词:随葬衣物疏;冥界观;张坚固;李定度;替身
中图分类号:G25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106(2017)06-0113-08
An Archeological Analysis of an Unusual Entry on a List of Funerary Clothing and Goods Unearthed in Turpan
Xu Fei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Ningbo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Ningbo, Zhejiang 315211)
Abstract:On a list of funerary clothing and goods found in an underground tomb from the kingdom of Gaochang ruled by the Qu Family, a sentence reading,“If seeking, you may find it either to the east or west of the sea” has proven difficult for modern scholars to understand. Both Chinese and Japanese scholars believe this entry refers to a good place for ghosts to go, but from the view of the underworld held by the Han population living in Turpan at the time, the most suitable place for ghosts is not the sea but underground graves. In the Northern-Southern Dynasties, the maker of grave plot purchasing receipts would use substitutes and non-existent addresses out of propriety to avoid disturbing spirits in the afterlife, as did the writer of funerary clothing and goods lists. It is thus concluded that this sentence refers to the place where the substitutes-Jiangu Zhang and Dingdu Li-went, this entry on the list being created out of respect for the world of the dead.
Keywords:commentary on lists of funerary clothing and goods; view of the underworld; Zhang Jiangu; Li Dingdu; substitute
隨葬衣物疏一般由陪葬衣物的清单及附加文两部分构成。其渊源可以追溯到西汉的遗策和告地策。吐鲁番古墓群出土的随葬衣物疏,从五胡十六国时期到唐代,历史跨度很大,书写格式和出现的神名等,表现出明显的时代性特点。麹氏高昌国(501—640)时期的随葬衣物疏几乎都有附加文,而且格式和语句基本定型化,其中有“若欲求海东头,若欲觅海西壁”这样难解的句子。以往的研究者对此莫衷一是,本文略作考证,求教于方家。
一 吐鲁番随葬衣物疏附加文的释读
高昌延昌三十六年(596)无名某甲衣服疏的附加文部分从第五行开始,原录文为竖写:
5延昌卅六年丙辰岁三月廿四日,大德比丘
6某甲敬移五道大神:仏弟子某甲持仏五戒
7专修十善,宜向遐龄,永赐难老,但昊天
8不吊,以此月十九日突然徂殒。径涉五道,幸
9勿呵留,任意听过。倩书张坚固,时见
10李定度。若欲求海东头,若欲觅海西
11壁,不得奄遏留停,急々如律令。[1]
其中“若欲求海东头,若欲觅海西壁”一句比较难解。日本学者白须浄真将其与后面的“不得奄遏留停”连在一起解释:如果(佛弟子某甲)想寻海东头,想觅海西壁的话,不要阻拦、扣留他{1}。其它的日本学者读法也大体相同{2}。只是浅见直一郎进一步把“海东头、海西壁”理解为“天涯”{3}。
国内方面,上世纪90年代刘昭瑞认为“海东头”、“海西壁”的“海”是在其他随葬衣物疏中出现的“东海”,把这句话解读为:“意思是说死者家人等若要相寻、可往东海见之。”并进一步指出:“衣物疏中的‘东海一语,反映了高昌人对死后去‘东海的渴求。”{4}这种观点颇有影响{5}。后来,刘志安进一步论证认为:“五道仅是死者途经之地,其最终的归宿之地是‘东海……最后一句‘不得奄遏停留。急急如律令。似针对五道大神而言,意即遵守相关律令,让死者速速归往东海,不得途中有所阻留。显然,这种在吐鲁番所出众多‘移文中所体现出来的死者归东海的说法,无疑是那一时期当地民众盛行的一种冥世观念或信仰。”[2]endprint
这些观点,各有各的理由,妥当与否光靠吐鲁番出土的衣物疏还不能简单地做出判断,需要首先搞清楚汉民族的冥界观。
二 汉民族魂归何处
所谓的冥界观,简单地说就是“魂归何处”,我们可以通过传世文献、墓葬考古以及出土的与丧葬有关的文书等方面加以考察。司马相如《哀二世赋》云:“坟墓芜秽而不修兮,魂无归而不食。”[3]王充《论衡·四讳篇》曰:“墓者,鬼神所在,祭祀之处。”[4]表明坟墓是鬼魂所在之处、家人祭祀之所。墓葬反映冥界观念,首推秦始皇陵园。秦始皇“把地上王国模拟于地下世界”[5],无非是认为地下的陵墓是他死后继续生活的地方。
汉文帝十三年(前16)的告地策云:“十三年五月庚辰,江陵丞敢告地下丞:市阳五大(夫)燧(自)言:‘与大奴良等廿八人、大婢益等十八人,轺车二乘、牛车一两、□马四匹、■马二匹、骑马四匹。可令吏以从事。敢告主。”{1}大意是阳世的“江陵丞”向冥界的“地下丞”移交死者——五大夫燧,并附燧申告的随行奴婢和随葬财物数。发掘报告称,墓中出土的明器与告地策所列的奴、婢、车、马等基本一致。不仅如此,墓中还发现用竹木或者陶土制成的家畜、生产工具、粮仓、船、灶、餐具、化妆工具等等,可以说为死者准备的生活、生产用品应有尽有。可见当时人们认为死者受地下冥官的管理,以墓为家生活在地下。这种观念不是一种随意的想象,而是与土葬附加明器这种丧葬习俗密切相关的。
死者魂归丘墓的观念,还直接表现在东汉的墓画榜题、镇墓文及买地券中。东汉墓刻有“王君威府舍”[6]、“万岁吉宅”、“万岁神室”[7]等字,把墓室作为死者久居的宅舍,也有墓石刻“死者魂归棺椁”[8],表明鬼魂的归属。镇墓瓶上书写着:“王氏冢中先人,无惊无恐,安稳如故。”[9],显示“先人”们还在墓中。买地券的目的是证明死者拥有墓地所有权,其前提是鬼魂要在墓地长期居住。买地券中还有“死人归蒿里,地下[不][得]何止”{2},意在告诉冥界官吏,鬼魂归到蒿里,地下不要呵喝阻止。“蒿里”到底指哪里,曾有不同意见,但就镇墓文和买地券等丧葬文书来看,它指的就是墓地,也就是鬼魂的“村落”{3}。
六朝志怪小说反映鬼在墓里生活的篇目很多,如《搜神记》:文颕“梦见一人跪前曰:‘昔我先人,葬我于此。水来湍墓,棺木溺。渍水处半,然无以自温。闻君在此,故来相依。欲屈明日暂住须臾,幸为相迁高燥处。鬼披衣示颕,而皆沾湿。”[10]水淹棺木而鬼的衣服沾湿,表明鬼就生活在墓里。
另外,丧葬文书中也出现鬼魂上天或者鬼魂属泰山之语,六朝小说中也有死后鬼魂被带到天上或者泰山的故事。东汉的“序宁简”写:“下入黄泉,上入苍天……所祷,序宁皆自持去对天公。”[11]意思是序宁死后,下入黄泉,上登苍天,书写着祈愿内容的文书由序宁自己带上天去接受天公的校检。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冥婚墓券”中描述缔结冥婚的两个青年鬼魂的生活情景:“共上苍天。共作衣裳,共作旃被。共作食饮,共上车。共卧,共起。共向冢,共向宅。共取(薪),共取水”[12],表明鬼魂既在“宅冢”中过着与生人并无二致的生活,而又可以上天。
鬼魂既要上天,又在地下生活,看似是一对矛盾,如何解释?《异苑》记章泛:“死经日,未殡而苏,云:“被录天曹。天曹主者是其外兄,料理得免,”[13]这里的天曹具有冥界官府的性质。东汉镇墓文中有“天帝下令别移……”[14],“天帝使者告丘丞、墓伯、地下二千石”[15]等句,表明天帝主宰着地下冥界。也就是说,天上有冥界的管理机构,亡魂上天就相当于去官府,或者被官府录去,这与其在墓中生活并不矛盾(传世文献中还有王侯死后登天、道士升仙的事例,并不具有普遍意义,这里不论)。
东汉熹平四年(175)胥文台镇墓文中有以天帝的名义向丘丞、墓伯、地下二千石等地下冥官移交死者的内容,也有:“生人属西长安,死人属东(太)山……(太)山将阅,人参应[之] 。”{4}意思是:生人属于西边的长安、死人则属于东边的泰山,如果泰山(君)要校检死者的话,可以用人参做替身。这篇镇墓文表明鬼魂既受地下冥官的管理,也隶属于泰山君,而天帝是冥界的最高统治者。
《搜神记》中胡母班拜访泰山府君时:“如厕。忽见其父着械徒作。此辈数百人。”[10]44-45这反映出泰山类似府城衙门,泰山府君相当于太守一级的官员。《三国志·魏志·管辂传》中记载术士管辂感叹自己不能作为洛阳令来治理生人,只能到泰山去治理鬼魂{5}。两处的“泰山”性质相同,即所谓的“泰山治鬼”。
《后汉书·乌桓传》云:“……如中国人死者魂神归岱山也。”[16]此话常给人以误导,以为中原人的鬼魂都要以泰山为归宿,而从以上证据来看,“归岱山”的“归”应该不是“回归”,而是“归属”。正如吳荣曾先生所言:“汉人既说人死归泰山,又说人死归蒿里,二者是有区别的。泰山为冥府中最高枢纽所在,而蒿里则是死人聚居的地方。前者相当于汉之都城,后者则相当于汉之乡里。”[17]泰山被作为冥府并非自古有之,而是冥界观念的一种变革,这种观念很可能形成于东汉中后期,而且只局限于北方地区{1}。
从西汉告地策中的“地下丞”,到东汉镇墓文中的“丘丞、墓伯、地下二千石”,“天帝”,“黄神北斗”,“泰山君”等,可以看出汉民族观念中的冥界管理体制存在着不同的等级,而且不断发生着变化,具有时代性和地域性。但无论“管理者”如何变化,鬼魂们在墓穴中生活这一观念没有本质的改变,一直延续到现代{2}。因为与这种观念密切相关的土葬加明器,上坟祭祀这样习俗没有发生根本性的改变。
三 吐鲁番汉民族的冥界观
自汉宣帝派士卒携家屯田,吐鲁番地区始有汉人聚居的记载,至魏晋一直属中原政权治下。从前凉到麹氏高昌割据政权,也是以汉族为主体{3},“其刑法、风俗、婚姻、丧葬与华夏小异而大同”[18]。在丧葬风俗方面,墓葬考古印证了这种说法{4}。随葬衣物疏中的语词也能找到相关证据。哈拉和卓的残衣物疏中有“归蒿里”[19]。阿斯塔那的翟万衣物疏中有:“延寿里民翟万去天入地,谨条随身衣裳物数如右。”[20]“去天入地”即离开能够见到天的人世间而进入地下{5}。阚氏高昌时期的阿苛母衣物疏云:“右条杂物,与母永供身用。”[21]意思是随葬衣物让母亲一直用下去。随葬品、尸身都在墓中,母亲生活下去的地点自然是墓中。endprint
麹氏高昌时期的衣物疏,没有明确表达死者去向的语词,而又融入很多佛教因素,这常常给人误导,以为鬼魂生活在地下墓葬的观念发生了大的变化。但是,衣物疏罗列死者的衣物,是随葬在墓中,衣物疏最终放在死者身边,这样的做法本身反映出死者在墓中生活的观念。与吐鲁番麹氏高昌的衣物疏内容很相似的北齐武平四年(573)王江妃物疏中写有:“江妃所赍衣资杂物、随身之具,所径之处不得诃留。”[22]意思是要求所经之处的冥界官吏不要扣留死者江妃带着的随葬物品。死者带着随葬品去哪里?不言而喻,也就是说死者与随葬衣物是绑定在一起的,因此我们考察死者的去处时,不能抛开随葬的衣物。冥界观念不是凭空想象的东西,它是与特定风俗结合在一起的,只要吐鲁番地区汉族的土葬、修墓、放随葬品这样丧葬风俗没有改变,那么死者的去处就不会改变{6}。马雍先生考察吐鲁番衣物疏指出:“说明汉族文化在高昌民间生活中根深蒂固,远非外来佛教所能动摇,乃至佛教徒也不得不遵循固有的风俗习惯。”[23]总之,吐鲁番地区汉民族的冥界观念与中原地区并无本质的不同。
既然当时吐鲁番地区汉民族的观念中,死者要归蒿里,地下的墓葬是他们的归宿,那么认为当时的冥界观念是:“死者归东海”,或者把附加文中的“若欲求海东头,若欲觅海西壁,不得奄遏留停”解释成:“让死者速速归往东海,不得途中有所阻留”等,就有疑问。而日本学者们认为死者要去“海东”“海西”或是“天涯”,也不能令人信服。因为鬼魂们没有带着随葬衣物去东海的理由。那么,那句话到底是什么意思?我们还得从与衣物疏有关联的买地券等其他丧葬文书谈起。
四 买地券制作者的“替身”
买地券是随葬在墓中的墓地买卖契约,其目的是向地下鬼神表明死者对墓地拥有合法所有权,衣物疏的主要目的在于表明死者对随葬衣物的所有权,二者本质相同。南京出土的太康六年(285)曹翌铅质地券:
太康六年六月廿四日,吴故左郎中立节校尉曹翌字永翔,年卅三亡。买石子岗坑虏牙之田。地方十里,直钱百万。以葬。不得有侵持之者。券书分明。
(以上正面)
奴主、奴教、奴西,右三人是翌奴婢。故[布]褠一领。故练被一张。[24]
(以上背面)
可以看出铅板的正面属于买地券,而背面则属于衣物疏一类,二者的目的无非是主张死者对土地、奴婢和衣物的所有权。这块铅板也表明两类文书其实是由同一人、同时制作的。也就是说,二者基于相同的理念,在考察时完全可以相互借鉴。
目前出土的买地券始见于东汉,其俗传承至今。黄景春2003年调查西北地区买地券、镇墓文的使用情况时,请延安地区的一位阴阳先生写了一份他常用的买地券样本。样本最后的书写人署名处写的是“白鹤仙子”。明明是阴阳先生所写,为何要假托“白鹤仙子”?黄氏的解释是:“这种假托仙人为作者的落款方式在两晋时期就有发现。假托神仙或动物书写随葬券文是为了防止死者对真正的作者的祟扰,是阴阳先生自我保护的一种手段。”[25]
黄氏所指的两晋时期的“随葬券文”有买地券也有衣物疏。出土于南京的晋永宁二年(302)大中大夫买地券最后的落款是“若有问谁所书?是鱼。鱼所在?深水游。欲得者,河伯求”[26],说书写买地券的是鱼,鱼已经游到深水里,如果要找的话,去问何伯。“鱼”并非确指,而“深水”也不是实地,作为契约表面上备附书写人,但实际上这个书写人是找不到的。人物是假托,去处是虚设,分明是作者在故意隐瞒真实身份。
长沙出土的晋升平五年(361)周芳命妻潘氏随葬衣物疏的末尾云:“东海童子书,书迄还海去。如律令。”[27]书者假托不见经传的东海童子,而且也告诉了一个实际上无法找的去处——东海,与前面的买地券可谓异曲同工。
南北朝时期的北方墓券制作者们采用另外一种表述方式,北魏延昌元年(512)孙抚买地券文末是:“来时恍惚,不识书人。”[28]北齐王江妃物疏说:“来时匆々,不知书读是谁。书者观世音,读者维摩大士。”[22]前面是一种推脱,后面则是替身,其目的不言自明。
那么,为什么丧葬文书的制作者要假托神仙或动物以隐瞒自己的身份呢?原因很简单,契约的书写者同时也是证明人,如果墓地或是衣物财产起了纠纷,鬼魂、鬼官很可能要上门来找契约的证明人。《淮南子·墬形训》高诱注云:“死而为鬼、能为祅怪病人也。”[29]《颜氏家训·风操篇》曰:“偏傍之书,死有归杀。子孙逃窜,莫肯在家。画瓦书符,作诸厌胜。”[30]意思是:旁门左道书上说,人死后若干日鬼魂会回家,当日子孙们都惧怕受害四处躲避,并请人作瓦券符箓来厌镇,可见鬼魂之可怕。宝鸡铲车厂二号汉墓出土的镇墓文云:“葬犯墓神墓伯,行利不便。今日移别,殃害须除。死者阿丘等无责妻子、子孙、侄弟、宾者。”[31]这都表明不但死者本人有可能对家人、宾客不利,而且如果葬禮冒犯墓神、墓伯之类冥界官吏也会带来祸殃。死者的家属尚且惧怕,书写丧葬文书的人也没有理由不忌讳。
而且,丧葬文书的作者并不是一个普通的会写字的人,且必须是能够沟通阴阳两界的巫师之属才能保证其有效性,因而其本身就担负保证人的责任。镇江出土的晋永康元年(300)李达买地券的末尾云:“任知者东王公、西王母。若后志宅,当诣东王公、西王母是了。” [32]这里的保证人是东王公和西王母,并强调如果以后有鬼魂试图占用这片墓地的话,请找东王公和西王母了断。作为普通的契约形式,后半句本来不必要,而添加之后,就是此地无银三百两,书写者想脱清干系的意图表露无遗。由此可以看出,作保证人的东王公、西王母本质上也是替买地券制作者承担证明人责任的替身。
鲁西奇列表梳理了魏晋南北朝买地券的概况[33],从中可以看出东晋以前保证人的表述比较多样化,有东王公、西王母,有乡吏,也有主日月、四时之神等,也有的干脆不写。而东晋之后出现了两个新面孔:张坚固、李定度。广东始兴出土的刘宋元嘉十九年(442)妳女买地券尾:“分界时有张坚固、李定度。沽酒各半,共为券莂。”[34]沽酒各半是买卖双方各出一半钱买酒致谢在场者,也是汉代买地券常用的格式。古代把契约从中间分开双方各持一半叫做莂,这里券莂就是指买地券。此券中张坚固、李定度是作为在场证人出现的。在其他南北朝买地券中他们前面的定语有“时人”、“时证知”、“时任知”等,角色都是保证人。而且比较有意思的是自从他俩出现以后,其他的诸如神仙乡吏之类的证人便逐渐销声匿迹,他俩似乎成为了专职的保证人。endprint
五 张坚固和李定度的本质
对于张坚固、李定度的性质,黄景春认为:他们是冢墓的“专职神仙”;“坚固”表示买卖成交后固若金石,“定度”表示土地度量准确交易公平;他们是为了确认土地买卖的合法性与可信性专门创造出来的[35]。
江西临川县出土的庆元三年(1197)朱公买地券中张坚固是“知见人”、李定度为“保人”。而同墓中出土了标着张坚固、李定度名字的陶俑,而比较有意思的是墓中还出土了一位手中抱着罗盘,俨然是“地理阴阳堪舆术家”的张仙人[36]。造墓先需要看风水,确定墓地位置,测量墓门方向等,这些都是阴阳风水师的工作,把风水师与张、李二人同埋在墓里,又是什么意思呢?
陈进国考察了闽南和台湾地区的买地券情况,其中福建惠安县在新坟破土时,风水先生要颂念破土文式:“恭迎过往神明、本山土地、历代地理祖师、张李(即张坚固和李定度——笔者注)二分金师同临”。坟墓定好位线后,在坟庭的前后分别钉一根用新杉木制作的“分金木代”,前面的木代代表张坚固,后面的木代代表李定度,每根木代上各用红线绑上“寿金”五张。陈氏论文还转述了赖旭贞对台湾高雄美浓地区破土仪式的调查:地理先生用罗盘测出坟地的风水的走向后,立两根竹竿定位墓地的中轴线,并在中心位置的地上嵌入两块砖,以两砖中间的缝隙标记中心轴线,沿轴线前后立两根竹竿分别代表张坚固和李定度[37]。
张坚固和李定度在颂词中被放在地理祖师之后,而且被称作“师”,在造坟破土仪式的测量标记过程中,又被用木桩或竹竿代替,以标记中轴线,表明二者是与卜墓相关,是被作为观察墓地风水、测定墓葬方位的风水先生的象征。这给我们一种启示:“坚固”和“定度”的本意,可能不是表达“土地买卖”的牢不可破,而是形容选定墓址方位的准确与不可动摇。也就是说张、李二人实际上是风水阴阳师们的化身。
而买地券的作者与卜墓的风水阴阳师是否有关联呢?前面提到的曹翌铅券是买地券与衣物疏的合体,说明二者同出一人。甘肃高台县出土的魏晋十六国时期的耿少平、孙阿玿墓券的上方是一幅表明墓地走向的卜宅图,而下方是墓券,其内容既含有两位死者冥婚的事宜,也有命令死者不得妨害生人的所谓镇墓的内容{1},表明卜墓、主持冥婚、镇墓行为是由同一人实施,镇墓和卜墓看似不相关的行为实际上是由同一巫师或方士{2}担当。黄景春调查的现代阴阳师们既写买地券也作镇墓文。[25]190-203从经济角度讲,巫师们活动与其说是一种宗教行为,还不如说是一种有经济利益的社会服务。既然是一种有偿服务,那么服务方就有尽力提供全套服务的动力,而需求者也没有雇佣多家服务的必要,因此在一场葬礼中的巫师不仅卜墓,还制作买地券,主持买地、镇墓等丧葬仪式{3}。
因此,“坚固”和“定度”二词无论是源于卜墓还是买地,本质上都是巫师们对他们自己工作的描述,或者可以说成是一种对服务质量的承诺和宣传。也就是说张、李二人是精心设计出来的“代言人”,用他们做替身既符合实际见证人的身份,又添加了服务承诺,可谓一举两得。这应该就是张、李出现不久便逐渐取代了东王公、西王母和乡吏等占据丧葬文书的见证人主角的原因。
以张坚固、李定度为见证人的买地券,最早出土于湖北,纪年为元嘉十六年(439)[33]112-114,其后见于广东、广西,出现在北朝时是北魏延昌元年(512) [28],而他们出现在吐鲁番随葬衣服疏中,最早是高昌章和十三年(543) [21]60,结合吐鲁番墓葬受中原文化影响比较明显{1}的情況来看,高昌地区衣物疏中的张坚固、李定度应该源于南方。
六 “若欲求海东头,若欲觅海西壁”的
意思
既然明确了丧葬文书制作者的自我保护意识和张、李二人的替身本质,那么就可以回头考察吐鲁番麹氏高昌国时代随葬衣物疏附加文的疑问了。还以前面所举高昌延昌三十六年(596)无名某甲衣服疏为例,最后的两句应该断作:“倩书张坚固,时见李定度。若欲求,海东头;若欲觅,海西壁。不得奄遏留停,急々如律令。”也就是“若欲求……”句与前面“书人”和“见人”连着一起解读。即:书券人是张坚固,证明人是李定度。如果要找他们的话,请到大海的东头、大海的西岸。这里的张坚固、李定度是衣物疏制作者的替身,海东头和海西壁是给出的替身的去处。后面一句则是对把守关津的冥官的要求,这一点需要结合衣物疏的本质和行文格式等另题讨论。
麹氏高昌国时代的衣物疏的作者使用替身、并给出替身去处的方式,与前述晋永宁二年(302)大中大夫买地券中的“若有问谁所书?是鱼。鱼所在?深水游。欲得者,河伯求”[26]、晋升平五年(361)周芳命妻潘氏随葬衣物疏的“东海童子书,书迄还海去”[27]是同样的思路。也就是:找替身,再给出一个去处,而这个去处实际上是找不到的。这是作者的一种自我保护的方式,其目的就是避免鬼神来烦扰。
这样的思路在唐宋时期也还在沿用,唐开成二年(837)弋阳县姚仲然买地券末:“何人书?水中鱼。何人读?高山鹿。鹿何在?上高山。鱼何在?在深泉。”{2}唐末漳州漳浦县陈氏买地券:“何人书?星与月。何人见?竹与木。星月归于天,竹木归于土。”[38]宋元丰五年(1082)王二十三郎买地券:“何人书?海边鱼。何人读?□山鹿。要来寻相请,但来东海边。”{3}这些表述更加直接,想隐瞒证明人、书券人、读券人身份的目的非常明显。在这里,无论是高山、深泉,还是天、地、东海,本身并不重要,只是一个被设置的无法找到的去处而已。
张、李二人在麹氏高昌时期的随葬衣物疏中,还有另外两种出现方式。高昌和平元年(551)赵令达随葬衣物疏末尾:“时见张定杜、请书李坚固。此人在水中定。”[21]31-32延昌三十二年(592)缺名随葬衣物疏:“清书史坚故,缺 [张]定杜。正(欲)得海中(停),正(欲)觅海 缺 ”[21]314都是在证明人张、李之后,给出一个去处:水中、海中。这与“海东头”、“海西壁”没有本质区别,其内在的逻辑相同的。endprint
另外也有“若欲求东海头……”一句在前,证人张、李二人在后的例子。如高昌欠名随葬衣物疏的附加文辞部分:“ 缺 廿五日,倩信女 缺 [持]佛五戒,专修十善。宜享 缺 [得]道果。攀天思万万九千丈。若□□海东头,若(欲)觅海西辟。谁(欲)觅者,东海[畔]上柱。倩书里坚固、时见张定杜。”[39]这篇衣物疏首先是错别字很多,比如:倩(清)、果(过)、思(丝)、柱(住)、里(李)等。从错别字语音基本吻合来看,制作过程也许不是正规文本转抄而只是口语的转录,而且作者的识字水平并不高。其次是次序混乱,“攀天丝万万九千丈”尽管是虚拟的,但它应该出现在衣物目录部分,而不是附加文中。再次是意义重复,“若欲求,海东头;若欲觅,海西壁。”意思已经很完整,根本不需要再加“谁欲觅者,东海畔上柱。”说明作者对前一句的意思并不理解。第四是张冠李戴,把张坚固和李定度的姓搞反。这很可能是在记忆和回忆过程中的差错。把“定度”写成“定杜”,也说明并不理解“定度”的本意。从这些情况我们可以推测这篇衣物疏不是某个正规版本,而是言传口授,凭借记忆书写的,而且作者对其中一部分文辞的意义并不十分清楚。
小田义久整理的麹氏高昌随葬衣物疏有34篇[40],其中提到“水中停”和“海中停”的各2篇;张坚固、李定度在前,“若欲求……”在后的有23篇,前后位置颠倒的有5篇,前者附加文逻辑关系清晰,而后者文脉比较混乱。因此可以说前者是主流,后者应该是在前者传承过程中产生讹变的结果。
参考文献:
[1]唐长孺.吐鲁番出土文书:第3册[M].北京:文物出版社,1981:66-67.
[2]刘安志.从泰山到东海——中国中古时期民众冥世观念转变之一个侧面[G]//.唐研究: 卷13.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370-373.
[3]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82:3055.
[4]黄晖.论衡校释[M].北京:中华书局,1990:972.
[5]徐吉军.中国丧葬史[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2:273.
[6]汤池.中国画像石全集:卷5[M].山东:山东美术出版社,2000:141.
[7]杨爱国.汉代画像石榜题略论[J].考古,2005(5):69.
[8]许玉林.辽宁盖县东汉墓[J].文物,1993(4):55.
[9]唐金裕.汉初平四年王氏朱书陶瓶[J].文物,1980(1):95.
[10]干宝.搜神记:卷16[M].汪绍楹,校注.北京:中华书局,1979:193.
[11]陈松长.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藏简牍[M].香港: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2001:99.
[12]赵雪野,赵万钧.甘肃高台魏晋墓墓券及所涉及的神祇和卜宅图[J].考古与文物,2008(1):87.
[13]刘敬叔.异苑:卷8[M].范宁,校点.北京:中华书局,1996:80.
[14]陈林泉,张翔宇,张小丽,王久刚.西安东汉墓[M].北京:文物出版社,2009:96.
[15]下中弥三郎.书道全集:巻3[M].东京:平凡社,1931:4.
[16]范晔.后汉书:卷90[M].台北:鼎文书局,1981:2980.
[17]吴荣曾.镇墓文中所见到的东汉道巫关系[J].文物,1981(3):56-64.
[18]令狐德棻.周书:卷50·高昌传[M].台北:鼎文书局,1980:95.
[19]马雍.吐鲁番的“白雀元年衣物券”[J].文物,1973(10):62.
[20]唐長孺.吐鲁番出土文书:第1册[M].北京:文物出版社,1981:176.
[21]唐长孺.吐鲁番出土文书:第2册[M].北京:文物出版社,1981:2.
[22]端方.陶斋藏石记:巻13[M].台北:台北台联国风出版社,1980:525-529.
[23]马雍.略谈有关高昌史的几件新出土文书[J].考古,1972(4):53.
[24]朱江,李鉴昭,倪振达,张寄庵.南京近郊六朝墓的清理[J].考古学报,1957(1):187-191.
[25]黄景春.西北地区买地券、镇墓文使用现状调查与研究[J].民俗研究,2006(2):192.
[26]南京市文物保管委员会.南京板桥镇石闸湖晋墓清理简报[J].文物,1965(6):44.
[27]史树青.晋周芳命妻潘氏衣物券考释[J].考古通讯,1956(2):97.
[28]叶昌炽,柯昌泗.语石·语石异同评[M].北京:中华书局,1994:361-362.
[29]何宁.淮南子集释[M].北京:中华书局,1998:341.
[30]王利器.颜氏家训集释增订本[M].北京:中华书局,1993:98.
[31]宝鸡市博物馆.宝鸡市铲车厂汉墓——兼谈M1出土的行楷作朱书陶瓶[J].文物,1981(3):48.
[32]镇江博物馆.镇江东吴西晋墓[J].考古,1984(6):541.
[33]鲁西奇.中国古代买地券研究[M].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14:146-149.
[34]廖晋雄.广东始兴发现南朝买地券[J].考古,1998(6):567.
[35]黄景春.地下神仙张坚固、李定度考述[J].世界宗教研究,2003(1):46-92.
[36]陈定荣,徐建昌.江西临川县宋墓[J].考古,1988(4):329-335.
[37]陈进国.“买地券”习俗的考现学研究---闽台地区的事例[J].民俗研究,2008(1):135-136.
[38]王文径.漳浦唐五代墓[J].福建文博,2001(1):40-45.
[39]唐长孺.吐鲁番出土文书:第5册[M].北京:文物出版社,1983:22-23.
[40]小田义久.吐鲁番出土葬送儀礼関係文書の一考察 : 随葬衣物疏から功德疏へ[J].東洋史苑,1988(30/31):57-73.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