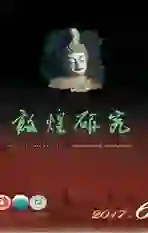敦煌写本《圆明论》录校与研究
2018-01-20韩传强
内容摘要:敦煌写本《圆明论》现有S.6184(英藏)、P.3664(法藏)、北7254(北图藏)、石井光雄旧藏本(日藏)、Дх.00696(俄藏)、傅斯年图书馆藏第188106号(傅图藏)等6份写卷。本研究以现存敦煌本《圆明论》诸写卷录校为基础,并基于《圆明论》写本与校本的梳理而展开讨论,以期对《圆明论》写本分类、内容解读以及归属判释作深入研究。
关键词:敦煌写本;《圆明论》;写本录校;写本研究
中圖分类号:G25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106(2017)06-0086-14
Correction and Research on the Dunhuang Manuscripts
of the Yuanming Lun
Han Chuanqiang
(School of Humanities, Southeastern University, Nanjing, Jiangsu 210093;
College of Marxism, Chuzhou University, Chuzhou, Anhui 239000)
Abstract: There are six manuscripts of the Yuanming Lun in the Dunhuang documents, S.6184(in the British Collection), P.3664 (in the French Collection), B7254 (in the Peking Library), Original Collection of Ishii Mitsuo (in the Japanese Collection), Дх00696(in the Russian Collection) and No.188106(in the Fu Sinian Library). Based on a transcription and correlation study of the Yuanming Lun from these manuscripts, this paper sorts the transcription versions and revisions of the text, then presents a discussion that makes a thorough study in regard to the classification of these manuscripts, interpretation of their contents, and their mutual relationships.
Keywords: Dunhuang manuscripts; Yuanming Lun; transcription and correlation; manuscript studies
目前所见,在敦煌写本中,《圆明论》共6份写卷,分别为S.6184、P.3664{1}、北7254(服06)、石井光雄旧藏本、Дх.00696、傅图藏188106。这6份写本情况如下:
(1)S.6184为英藏敦煌文献,该写卷收于《敦煌宝藏》第45册,所存《圆明论》首全、尾残,仅存4行文字,有效信息极其有限。[1]
(2)北7254(服06;BD08206)为北图藏敦煌文献,《敦煌宝藏》第105册、国际敦煌项目及《国家图书馆藏敦煌遗书》第101册[2]206-215等都收有该写卷图版。该写卷所收《圆明论》首全、尾残、中乱,存239行,5900余言,抄至第7品后开始接续抄录《大乘起信论》的相关内容。值得注意的是,该写卷首题后有“马鸣菩萨造”字样[2]206。
(3)P.3664为法藏敦煌文献,《敦煌宝藏》第129册及国际敦煌项目(IDP)都收有该写卷图版。P.3664是一份长卷子,分别抄有《圆明论》、《阿摩罗识》、《导凡圣悟解脱宗修心要论》、《秀和上传》、《导凡趣圣心决》、《夜坐号一首》、《传法宝纪并序》、《先德集于双峰山塔各谈玄理十二》、《稠禅师意》、《三字观》、《稠禅师药方疗有漏》、《大乘心行论》、《寂和上偈》、《姚和上金刚五礼》、《大般若关》等15种文献{2}。该写卷所存《圆明论》相对完整,首、尾俱全,存277行,约8800余言。遗憾的是,该写卷所存《圆明论》亦缺第8品内文,图版前半部分较为模糊,而国际敦煌项目收录有该写卷相对清晰的彩色图版。
(4)石井光雄旧藏本为日藏敦煌文献,该写卷未公布图版,笔者也未能见到该写卷全貌,甚是遗憾。不过,据田中良昭介绍,该写卷首缺、尾全,抄有《圆明论》第7品(无第8品)及以下内容,其后继续抄有《阿摩罗识》、《绝观论》两种文献[3]。
(5)Дх.00696为俄藏敦煌文献,收于《俄罗斯科学院东方研究所圣彼得堡分所藏敦煌文献》第7册。该写卷首缺、尾残,存56行,共1400余言。该文献存有《圆明论》从第3品至第4品部分内容,有一定价值[4]。
(6)傅图藏188106号为傅斯年图书馆藏敦煌文献188106号写卷,收于傅斯年图书馆,并有图版。{3}其所存《圆明论》首缺、尾全,存6纸,内容从第6品开始至结尾,亦缺第8品。接续《圆明论》后抄《阿摩罗识》与七言诗,台湾学者黄青萍有专文研究[5]。
目前所见《圆明论》校本有马克瑞(John R.McRae)博士在1986年出版的《北宗禅与早期禅宗的形成》一书末尾附有校本(下称马校本)[6]18-44及高小伟在其硕士论文中对《圆明论》进行的录校(下称高校本)[7],两校本均以P.3664为底本进行录校的。
一 《圆明论》写本录校endprint
本文以P.3664为底本,以S.6184、北7254(服06)、Дх.00696、傅图藏188106为辅本,以马校本、高校本为参照而校录{4}。
《圓明論》一卷{5}
明心色因果品苐(第)一{6}
要门方便品苐二(1)/
辩明脩{7}道釋因果品苐三
辩明三乘逆順觀品苐四
簡(異外道{1})/緣生(根{2})本品苐五
入邪正五门辩因果品苐六{3}
自心現量品苐(七{4})/
简妄相(想{5})品苐八
辩明聲骵品苐九
明心色因(果品第一{6})/
夫入道之初,須明心色二门。心色各有二種:一者生滅心;(二者真/(5)實心。生滅心者,消念{7})想前乎緣慮。不斷名為妄(想,妄想无體/湛备。虚空遍周法界,{8})名为真實。真實之性,元来不善,(其義/謂有{9})生滅。若見真心,元{10}无妄想。既得真性,常須覺悟。行、/(住、坐、卧,息{11})緣轉心,心實不動。作此解時,行、住、坐、卧,常在禪。/(定心无{12})罣■{13},名心解脱也。
色者,即是身也{14}。身想(相{15})從何而生,推導/(10)□□□。一者從无始妄想熏習而生,二者即從現在香味因緣/□□。從熏習而生,熏習則是因,身則是果。熏習是色相□/□□。若習非有想,身亦非色相,何以故?為因是无相,果亦(?)□□□。/□不善其義,謂身自性而生。若從因緣習氣起者,即知是虛(?)。□(因/{16})既是空,果亦是空。依香味中推,亦无有身。何以故?色從香味飲(?)/(15)食為命。食又非色,如人飲食,變為羹穢。亦非作色,細少香味(?)□□□/□因緣香味為色身香味。若有質色,身是其有,香味本色本性□,/身亦是空。若有作其色,色即是其有。將无作其色,明知色是空。/為□心{17}色无二,本性平等,名曰真如。得此平等无二法门時,了其心色也。
要门方便品第二
夫學道多端,趣悟不同。執(見名異,略述{18})/(20)其门有其三種。一者漸教,二者頓教,三者圓教。其義不善,浪相誹(?)(謗{19}),/為各執自許,根基不會,餘人所悟,各相非毀。若契會根基,趣(悟不/同{20})者,即辨{21}其漸、頓、圓、成,其別也。若不解者,即言同也。余今所(見,其實){22}/不同也。須臾之間,悟者即隔塵沙劫數,豈得是其同也?今為(學者)/略簡其教,即知別也。
云何為漸教?時人解者,皆悉附經文。經文无(是非)/(25)過,良為將自根基所解,不會餘人所悟。根基有其三品,若依(經文/{23})及善知識,取其解者,不在內外,得其无我者,是小乘人也。/(以{24})為自知根基大小故,便執所解,自謂名為大乘觀也。又復有人(作其觀{25})解所有境界,并是自己妄想心作。若自无妄想者,畢竟(无有{26})/境界。作此觀時,即无前後(二{27})際。即不住涅槃{28},執其所解,自謂是其頓教。(余{1})/(30)今所聆,乃是漸門,非是頓也。
云何頓教?頓教者,善知身相心骵(來去{2})/之處也。其身相者,元從妄相(想{3})心中生。其妄相(想{4})心,元无有(骵{5})。
(問:“若{6})/言无骵,云何与身為本?”
答曰:“其心无體,亦不与身為本。所以者何?(其{7})/心自相不知處所,亦不知生身。心若知處所,可能生於身相;以心不自/知其處所,及不知從何處而去來,亦不知至何處受身{8}□□□/(35)從何處而生。若也身心各得相知者,可道身從心生,心復可言生/其身也。身{9}心既是不相知,及不知來去處所者,何能相生也?作此解/者,身是誰家身?心是誰家心?心復不自知其處所,云何与身為本{10}?/身心各不相知,即是元來不能相生也。何以故?空花所誑眼,□/身既非身。明眼是空,以將空作其有,有亦是其空。故說眼根□□/(40)迷空作其心,心亦是其空。辟如依泥起其器,器亦□□□。/器若非是泥,身心是其有。今既覺非實,三世亦復此□□□。/所言聖賢及地位者,并言空以為作也。空{11}中无起滅,故言(不生滅){12}。/作此解者,名為悟。所有山林土地、日月星辰、眾生等類,(并总(?)是)/{13}虛空、法性波浪也。是故名頓。觀於无我,故言別也。今顯漸(頓積有)/(45)所悟。不{14}知若為,合其圓也。凡愚之知,不可{15}測量圓門之理也。”
(圓){16}門者有十種義。云何名十?
一者,須明眾生界;
二者,須明世界(義){17};
(三){18}/者,須明法界義;
四者,須明法界性;
五者,須明五海;
六者,須明(十知){19}/義;
七者,須明眾生法界體;
八者,須明世界體;
九者,須明法界(體){20};
(十者,須明){21}諸仏方便體。
(有){22}此十門不同,就其中了了分明者,即解圓教之(義。其/(50)漸){23}頓門中,定力多,三昧用少,圓門之中三昧用多,惣无(其定。若不/){24}明者,雖有定行二門,終不名了義。其人愚情未改,更不求(勝義){25}。/非直(真){26}自悮(誤){27},亦復悮(誤)他。此義是《法華經》仏已訶責{28}學道之者(善須新){29}/簡圓門之義。余今一一為次苐(第)釋名,又出其體也。令諸行(者有所依{1})/憑也{2}。
云何眾生界者?有三種眾生界也。何等為三?□□□/(55)眾生相□□相。二者,三世流轉,亦是眾生之相。三者,受用□□/別(?)亦是眾生之相。其相者,若以法性為體,眾生心性元本□。□/□陰之相,元從因緣而起。一一和(?)合,无有自性。緣未合時,本□□□/□此因緣元將法性為體。故眾生界量,并因法起,并因法(?)滅(?)/。□□□有眾生之界,元是涅槃之氣也。endprint
“若依涅槃而起(者,涅槃可與眾/(60)生為)體{3},已(?)不?”
答:“既是涅槃之氣,何處更言眾生(亦不立涅槃,亦不存作/此觀{4})時,亦非眾生界,非非眾生界;亦非涅槃界,非非涅槃界。(何){5}以故?(通)/中无二故。是誰為眾生、是誰為涅槃?故言无漸无頓,号之為圓成也。/其圓成之法,是畢竟无眾生、斷煩惱。若迷於涅槃,即見有眾生,/即有煩惱。既有煩惱,即有心識,即有內外。既有內外,既有諍(論{6})/。(65)
言心內者,是愚人法也{7}。若在内,即是无常,亦是煩惱,亦是生滅,亦是(地{8})/猿,亦是人天放逸,亦是恐怖。既有過去,即有未來,即有現在{9},即/(是{10})流轉。既是流轉,即非仏性{11}。仏性體者,不生不滅、不斷不常、不來/不去,非三世、非過去、非未來。如如實際,始名仏性。寧以生命作其/(仏{12})性也。
余以經文{13}及禪觀得其解者,等虛空,遍法界,即是真實性/(70)(也{14})。心在外者,即初教悟法界之心,故言外也。既等虛空,滿于色內,何/(處{15})有色與心為■?心色既是无■,豈不通於虛空也?即是法界之/用也。
圓宗之中,通於眾生界也。翻眾生界,以為圓宗也。以此解者,/(即非{16})眾生界也。世界(者{17}),一眾生是一世界,大眾生是大世界,小眾生是/(世界{18}),勢分各別。辟如{19}王者之界,四方數万餘里。州郡之界,並在王/(75)者之界內也。縣界復在州郡之界內,鄉界復在縣界內,村界復在/鄉界內,居宅之界復在村界內。房舍之界復在居宅之界內。作是觀/者,從王者轉轉相容,各得世界之用也。若依此解者,人天地獄,/及一切眾生,重重相依,各得勢分,不相鄣{20}■也。”{21}
問曰:“世界同處,以何為體,/得不相■?”
答曰:“大世界元將盧舍那仏、復將菩薩巧方便、大悲願/(80)力,復將三昧為體。三昧復將虛空為體。虛空无鄣■,故能生无/■法界智。法界之智无■,故能生无/(■{22})三昧智。以三昧无■,故/能生卢舍那仏。无■无邊身,与一切眾(生{23})依止。以世界本是无/■故,是以不相鄣■也。
人身亦是眾生依止界,何以故?以人身/中有八万户虫,虫中亦有諸小虫。轉轉相依作世界,各自相名以為(世){1}界/(85)也。作此解者,種種是世界,何處更有眾生界?盡是畢竟空。□/无眾生也。尋體而觀,元是法水而流,分其水而作世界,世界還□/法水。作此解時,亦非眾生界,非非眾生界;亦非世界,非非世界。/作此觀時,名為通於世界義也。”
辩{2}明脩釋因果品第三/
彼諸受道人等,要須明其因果。若不明者,例墮摩訶羅外道/(90)見也。為此,因緣要須分明{3}。
難曰:“如上《要決論》中所立世界義(重重{4}),/并是世界。此義不成就,此門中更不見眾生體乃至諸仏(境界{5}),/皆悉是空。
又,上文中立世界體、乃至眾生體,法界體乃(至諸{6})/仏方便體,並將虛空為體。既是虛空,即應无體。所以得知,(无體{7})/如愚下見,虛空无因,所以有无因果。果橫從何起?若(也有{8})□/(96)虛空,誰之所作也?虛空有其作者,万法有其因果。若(其虛{9})/空无其作{10}者,万法无因復无果。此依禪師立體起□□/(非{11})是厶(某{12})甲橫生難。惟願禪師大慈悲,為除疑惑{13},令得解脫。”
(答{14})/曰:“如上所難,大有(道{15})逗留。終日(是{16})慈悲,欲除眾生疑惑{17}。故(作其/{18})難,為汝解釋。若{19}依其體,无本无末,實无因果。所以者何?/(100)但以《般若經》云:“因亦空、果亦空、行亦空、非行亦空,非非行亦/空。惣而言之,仏亦空、法亦空、僧亦空、乃至賢聖亦空{20}。”准此經/文,如上所難,亦復如是。雖然与(為{21})一切眾生无始已來,住於/色香味子身,非是无為化起。若是无為化起,合以蓮花、/不依父母。既依父母,明知无始習氣,熏資其身具足。煩惱/(105)未除,習氣未盡。
如上法界體中所明義者,并是依他諸仏般若/文得解悟,未是自用功而得悟也。若是用功而得悟者,其身{22}如死灰,/復无有血{23}。設使有血,猶如雪色。既不如是,明知具(足{24})煩惱,若為不/信因果。尔時設難外人,雅伏屈躬,深信因果。”
復問:“若為為因、若為為/果?”
答曰:“當須住{25}禪般若,空觀成就,不住有无,身心平等,猶如虛空。行、/(110)住、坐、卧,无有癈息,隨緣救{26}物,濟弱扶傾,憐貧愛老。當念眾生三塗/等苦,及以人間貧寒困苦,常以捨命,救之不以。辝(辭{27})勞如是,行行/常在禪定。經於三大阿僧祇,仍須眾願。備如眾生意,莫如己意。須滿/眾願,莫如己願。如斯行行,是名因。”
又問:“若{1}為為果?”
答曰:“果者,不離於因。但/住般若,不住有為。故度眾生,莫作盡意。但行其行,莫限了時。捨命救/物,莫生自他之想。所以者何?空禪三昧,无有自他之行,即非菩薩所入。遠劫/(115)勤苦,莫生顛倒之意。常行此行,不立滿足之想。如斯行行,无始習/氣,自然滅盡,唯有空行。所以(名{2})為空行,習氣俱盡,不住彼我。假与立名,/名之為果。行行滿足,果自然至,故名因果。果若滿時,智一滿虛空、/行亦滿虛空、身亦滿虛空。國土及化身,并皆滿虛空。雖然等{3}虛空,/与虛空{4}无別異也。
依空起其身,身亦是其空;依空起其行,行亦是其/(120)空;國土及方便,皆悉如虛空。所以者何?元依虛空法界起,不異/於虛空。猶如水上波,波元依水起,波還即是水。水既不異波,化身亦如/是。理行如證,名之為因果,故名因果。”
(問曰:{5})“若習氣未盡,名為因果。習/氣既盡,豈得名為因果?”endprint
(答曰:{6})“不得為因果。所以者何?唯有空行救物,更/无心意。猶如幻等,故名為果。果語{7}諸行人等,不可以將凡情、依文/(125)取解。即言得其理要,須用功日久。捨俗塵勞,靜坐思惟,已送報身,/莫以誦得文,謂言得理,全不相關。此是他解,非是我功;此是他行{8},非/是己行也。作此思惟,得免其過也。”
辩明三乘逆順觀品苐(第)四
欲明三乘差別,各須知因緣不同。一有順觀四大,二逆觀四大。逆順俱/達理盡,齊等虛空,證羅漢果。順觀者,直至羅漢果。逆觀者,/(130)例入四聖果。聖然後入(羅)漢果{9}。
因緣觀中,亦有逆順。雖同虛空,名證辟/支仏。所以分別,時人不明此義。大小遠近,是以惣名為大乘。其實非/是大乘,并是小乘義也{10}。
聲聞人迴心入菩薩道,望八識習氣藏而得,而/生菩薩道,并行六波羅蜜。凡夫逢善知識方便善巧因緣,於卅七助道法/門而行六波羅蜜。久行復依何門,入得{11}菩薩大行,得成仏果{12}。
又,說教不同,/(135)或先說因,然後行菩薩道。上乘聲聞迴心,及凡人入道者,先說因,然後說果。/久種善根人,於此門中得悟者不同凡夫。及久行菩薩道,并皆得入。
問曰:“上來/聲門迴心及凡夫入道所以不解,未知久行菩薩復依何行菩薩道?未審久行/菩薩,行六波羅蜜已不?”
答:“云行亦得,不行亦得。所以須不行慈悲{13}門中,行六/波羅蜜,入三昧門{14},復入法界門。行行者,即不見六波羅蜜也。若為是法界/(140)門、若{15}欲明者,先須明世界義。若不明世界者,无由得入法界門,是以先須/明世界。”
問曰:“何者名世界義?”
答曰:“一眾生十年一世界。大眾生是大世界,/小眾生是小世界也”{1}。
簡異外道緣生得根本品苐(第)五/
順觀四大者,為利根凡夫,久種善根,惠情爽達。仏即為說緣起/法門,即懸見空理。就此根基,為說順觀也。
逆觀者,為凡夫愚鈍,/(145)不見玄門,唯見色、香、味、觸,妄生記著。為此凡夫,即說逆觀也。/
若無利鈍凡夫,實无說逆順觀。多愚有其二分,凡夫逆觀,從聲、/香、觸、味推至微塵,推至虛空。色心不起,即取菩薩,是即獲得羅/漢果。此是鈍根之人獲果如是。若利根凡夫逆觀者,不然。從/聲、香、味、觸次第觀之,亦非微塵,并是自心妄想現。
問曰:“若為是/(150)自心妄想現?”
答曰:“一切眾生,具有六根。何以有之?皆從八識。”
(問曰{2}:)“眼、耳、鼻、/舌、身、意等根,何處得來?若是自然而有者,即外道所見,即非仏法。/既非是自然而有,即合有來處?既合有來處,未知從何處來也?”
答/曰:“亦非是自然,并有来處,皆從賴耶識中來。賴耶識,猶如大地;眼、/耳、鼻、舌、身、意等,猶如百草萌芽。若无大地,草木、叢林,依何而得/(155)生長?草木、叢林、種子,皆是地之所持,不失種子。今見眼耳鼻并/是賴耶之氣。
赖耶本性无有形質,及諸根身是有形質。今時凡夫不/見赖耶為本,謂言父母能生。是以浪作色身之觀,推至微塵,乃/至虛空妄取羅漢之果。若知身本來依赖耶而起者,即无眼、耳、鼻、/舌。
何以得知識元无有形質,唯有四似?何者名為四似?似根、似塵、似/(160)我、似識,此是四似。一一似中,推覓元无有識根等,并是賴耶之/中影像也。但見賴耶,本性无有生滅,即捨諸根之見。何以故?元无/諸根故,并是本識種子相分故。本識之相分者,即无眼、耳、鼻、舌之/根。本識中先无根識之質,唯有似也。其似即體是空,推趁即无。只為不見識,謂言眼、耳、鼻、舌自然生。
今本識體者,唯有似/(165)无有質。以質无故,名為自心影像。既是自心影像者,何有我也?/既无有我,誰取果也?以不取果故,不同鈍根凡夫。推於四大,至於虛/空取其果。”
問曰:“取果有何過也?”
答曰:“取果有我之過。若羅漢入/定,猶如死人,復如死灰。經於千劫,更復出定。出定以後,還同凡夫,/分別既同。分別者,何處更得識來?既有識生,明知本識所持,是以得/(170)出其定,為此元來未斷一分煩惱。有此過故,既有此患,只為不見/身是本識影像。若知身是本識之影像者,无不須斷煩/惱,亦不須證涅槃。不斷煩惱故,離其我也。既无我,誰取涅槃,唯有習/氣未盡。
菩薩即自知習氣未盡,當念眾生具无量縛,乘起大/悲。因此,即有菩薩行門。雖起菩薩之行,不同凡夫我見之行。所起化報/(175)之身者,為凡而起。非是自為。若是自為者,還是我也。以為凡而起故,/是以離其過也。”
入道邪正五門辩因果品苐(第)六{3}/
凡欲脩道,先須識其因果,二須識其邪正兩門,三須依解起行,四須/常觀莫癈,五須明行位深淺。有此五門,三世諸仏之所共脩,非今獨/說。
苐(第)一,明因果者,凡人之言道人,須自知此是俗情,盖亦是虛。若不自/(180)知,即多失道。若自知者,先觀我身,從頭至足,相好具足已不,曰若下/人共聚,我身最為第一。眾生共許,朝市有名;郡官共許,即眾人共/觀,坐即人皆美之。當知前業脩行,忍辱不瞋,并復莊嚴尊像,/具足眾戒,獲果如是。
若觀此身,從頭至足,无所可觀。眾人不讃,/朝市无名,行則无人記,坐復无人美,衣不盖形,食不充口,衣馬不具。/(185)當知前身未曾忍辱,悭貪具備,不曾為福。如此觀者,深須慙(慚)愧。自/知不具足者,當須種福,是名因果。
苐(第)二,須解邪正兩門者,凡人依有其深/淺。如似有人脩持五戒不犯,其人意功德具足,望与仏齊。如此意者,/是人悉尔,非獨一人。為更不求无漏聖道,名為耶(邪{1}),非是仏{2}弟子也。若為作解,/得令正道。若欲會其正道,先須達其心本,二須達其色。何以故?一切眾/(190)生皆以心{3}色合和為凡夫,不得聖道。今須了達,始得出纏。是以須達/其元。若為心本,本有兩種。一者真實心,二者妄相(想{4})心。凡夫生滅,都由妄想,/不聞真實,今須達其妄想。若為達其妄想,凡夫愚癡不了,謂心是/實。智者所觀,元无有體。若為作解,得知无體。endprint
若欲知虛實者,/端坐思惟,觀其妄念起動。所緣前境,无問遠近,皆悉緣至。雖言緣至,/(195)而實不到,所以得知不到。正由不觀其虛實,謂心是有。若觀去時心,若/也是其去者,身即應合死。若也是其去者,應合了前頭境界。何故唯/緣舊事,不知新事。若作此解,明知不到前境,已舊事謝故。舊事既謝,即是无境,境即是虛。所{5}言緣者,豈不是妄?為此得知,是其妄也。
若言心/在腹内者,亦復不然。何以故?若在腹內,應知腹內五臟中一一事。(若責五臟中一一事{6}),皆悉不知/(200)明心,(心{7})不在內,心{8}不在內故,即无有我。不到外塵,即无有彼我。彼我既空,名心无/彼此,故名心解脫。何以故?已不住二邊故。作此觀時,其心寂然,猶如虛空,是/名了心。
若為觀色,觀色亦有兩種。一者外色,二者內色。外色者,山川大地是/也;內色者,五陰四大是也。先觀外四大,山川大地,万物所依。即此大地是微/塵(為{9})積聚厚重{10},始名為地。即此微塵未聚以前,元本是空。從虛空眾生/(205)業力所感,始有微塵。若眾生元无業力者,微塵亦空,乃至積聚竟時,亦是/微塵。何以故?若索地體,只得其塵,不得其地。其地若離微塵,更无大地。明/知微塵未聚以前,大地元空。大地既空,明知微塵亦空。何以故?虛空无性,/化起微塵;微塵无性,化起大地。從其虛空,尋觀大地,微塵本是其空。/作此觀時,明知五陰及四大,亦復如是,是名皆空也。
若為明其內色,內色者其身/(210)四大,皆依外四大生。外四大既是空,內亦如是。何以故?人依食而立,衣食從地/而生。大地既是空,衣食亦非有。衣食既非有,內色依何立?內色既不立,/明{11}知即是空。
觀心无內外,及色亦復然。色心无內外,是名為寂。寂无所/有,故號為涅槃。作此解時,是名為正。遠離顛倒,亦名正見,亦名正定,亦名/正業。作此說者,亦可正說。三世諸仏,共乘此法,得至彼岸,是名正道。
(三{12}、)雖然/(215)得此解,仍須依解起其行。若不如是,即入外道耶(邪){13}見位中。若為依解,/始起其行,為凡夫无始已來,煩惱熏習,積累非今,不可一時頓盡。亦/復依今解悟,常覺現前。勿令无明煩惱重起,是名因行。習氣、煩惱/都盡,更不得与色塵、境界重合,始名斷盡。
若自知未盡者,常須觀/行覺照{1},菩薩行六波羅蜜,慈悲一切,饒益於人,推直於他,攬曲向己,計/(220)足向他,欠損向己。何以如是?前觀心色,空无有我,即是虛空。虛空若有色,/即色有我爭。我既是空,誰有誰爭?一虛空无我,是以須行无爭慈也。/若不如是,即理行相乖,非菩薩之行。故言依解起行也。
四、須常觀莫失/者,若不作理行相副之觀者,恐其有失。是以須常觀莫癈。
五、明行位者,莫已得此解,現前即言共仏等。未同諸境界,約位判時,始是脩信/(225)賢人,非是究竟人也。若不知其位者,定入无因果謗。故以此言也。/
自心現量品苐(第)七
依《楞伽經》自覺聖智宗,立{2}一切諸法皆/是自心現量義。若解者,山川大地、及以己身,并是自心,非是謬也{3}。
且論/身分四大,四大所感。何无五大?天地所成,乃四輪而立。云何不說五輪/而成?有何所益?
《釋》曰:“實是自心所現,非是謬也。所以得知,自心所現。且/(230)論身四大者,為內有四種妄想。感得四大以為身,是以无(其{4})五大。何以故?內有/沉重妄想故,感得地大以為身;內有津潤妄想故,感得水大以為身;/內有忿熟妄想故,感得火大以為身;內有飄動妄想故,感得風大以為身。/是以得知,皆是自心現量。”
問曰:“其身信知不惑,山川大地,若為得知(是{5})自心?”
答/曰:“亦由內心。何以故?已有高下妄想故,感得山川大地不平。其地下厚三百六十万/(235)里,名為地輪;其地下有水,復深三百六十万里,名為水輪,已承大地。其水輪/下復有大火,(其火{6})復深三百六十万里,已上衝承其水輪。其大火下,復有風輪,復/深三百六十万里。上下四輪,次第相承,大地得存,名為世界。
其風輪下,/即是懸空,更无物也。何以故?只有四輪,而无五六者,為眾生內心有四種妄/想。還為內有沉重妄想故,感得地輪;為內(有{7})津潤妄想故,感得水輪;為/(240)內有忿熟妄想故,感得火輪;為內有飄動妄想故,感得風輪。以相成/也。作此思惟,皆是自心所現。除心以外,更无一法。
今時有人問言,天地万法/无數者,只由未悟,諸法是其心。為此因緣,即有疑心,即見諸法。是有是/无?為此因緣,即起有无謗也。為破除諸法,即起相違戲論謗也。
若/知其心所感者,惣是自心,元无諸法。若也有法,即言有无。既是自{8}心,元/(245)无諸法,何得言有過也?作此解者,即於諸法,離其謗也。”
問曰:“山川大/地是无情,人是有情。云何忽言无情之境是其心也?若為得信,實/難可信。”
答曰:“辟(譬{9})如夫妻二(人{10})无智愚痴,相共平章,作酒欲沾。酒既(酉+豆{11})/已,其夫往看其酒,酒已澄清,乃見自影,即以成瞋,打其婦,婦(即){12}分疏,我/有何辜?其夫即言,你何故將一男人藏着瓮中?其婦不信,即看瓮中,/(250)乃見自影,還復大瞋,即語夫言,你何(故){1}將一婦女藏着瓮中,不語我知?/尔時,夫妻相打,各不識自影,相打至死。
并舍(來{2})救,問其所由,各如上說,其解/闘人(解{3})釋,亦復不信,即將夫妻就瓮看影。乃見三人影,又復不信。若/其是(我{4})影,合在瓮外,何故在瓮裏?其解闘人即語,若不是你影者,/我即共你夫妻,并在瓮中。乃見三人明知,是你夫影。尔時,其婦更瞋口/(255)云,有一男人送一個女婦來。又復相打,不知休息。畢竟不信,是其影/也。
凡夫亦尔{5},山川大地、日月参辰,并是自心業所現,盡是自心影像。何/以(故{6})?凡夫不名心作,决定不信。亦如夫妻二人,諍影像相似,决定不信是/自影也。瓮中實影者,喻山川大地,亦是自心現量。若非自心現量/者,既見雷車,震其虛空得作聲,明知此身是其空也。又見乘車在/(260)地,雖震其地以作聲,若无虛空,終不出聲。明知,此聲亦是空也。作/此解時,一切諸法,盡是虛空。endprint
元无法也,只由凡夫妄想未盡,見山川/大地;妄想若盡,畢竟不見也。諸仏菩薩,以去處无鄣■,只由妄想/盡,是以不見山川大地。明知万法皆是心業所現也。”/
辩明聲體品苐(第)九{7}
凡言聲者,時人作解,耳所得聲者,大錯;/(265)言聲到耳者,亦大錯。
問曰:“若為作解,契會仏意?”
(答曰:{8})“若欲解聲真源者,/先須識其聲緣,亦須明其聲體。”
問曰:“何者是緣、何者是體?”
答曰:“鐘杵/及人功用,并是其緣;鐘內空及鐘外空,并是其體。(以將緣撃其體{9},遂出其聲。即此/聲者,是其體聲,非是鐘也。”
問:“其體者,處處皆遍。何以只滿十里,不滿/百里?”
答(曰{10}):“以緣有大小。聲雖不滿虛空,猶如(石{11})下震其百出,皆悉大動,其/(270)地可以{12}流轉以不(否{13})?若審思量,其地雖震,不曾流轉,即是不動,聲/亦如是。雖緣撃震虛空,乃震處作聲,亦不流轉。既不流轉,即是不/動,即是不生,即是不滅也{14}。
如五海十智之義,是一切諸仏菩薩大行之根/本也。若不善五海十智之義者,无由得解圓門義也。”
又,圓教之義是/何法?圓教法門者,眾生是諸仏,諸仏是眾生。舊來如是,不由今悟,/(275)不与三乘菩萨同也。
又,圓教門中明義者,亦非眾生界,亦非涅槃(菩薩{15})界也。/
圓明論一卷。/
二 《圆明论》内容剖析
据录文可知,《圆明论》开头列举了九品目录,但因第八品只有标题,没有内容,所以该写卷实际只有八品内容。就整个写本而言,其内容可归纳为以下几个层面:
其一,关于缘起论。缘起论是佛教义理重要范畴之一,被视为“佛法的基石”[8]。《圆明论》开宗明义,阐述了其所持的缘起论。黄青萍曾指出《圆明论》在分析自心想时援引了摄论宗的重要概念,因而得出《圆明论》的缘起论是“瑜伽学之阿赖耶识缘起”[5]219-220。我们仔细研读《圆明论》,就会发现其在缘起论上不仅持阿赖耶识缘起,更侧重于以《楞伽经》立论,力倡如来藏缘起[6]40、19。
《圆明论》实以《楞伽经》为基础,力倡如来藏缘起。笔者并非要否定《圆明论》对阿赖耶识缘起的拒斥。相反,《圆明论》在阐释时,多处援引了阿赖耶识缘起思想[6]33-34。
可见《圆明论》在诠释具体问题时,亦援引阿赖耶识缘起思想。无论是基于《楞伽经》的如来藏缘起,还是基于摄论宗的阿赖耶识缘起,此皆是《圆明论》诠释其思想的方式[6]41。
基于此,笔者认为,就《圆明论》而言,很难说其所立缘起论究竟是依止如来藏缘起还是阿赖耶识缘起。实际上《圆明论》所立缘起论是对两者的融合,这也是宗派尚未泾渭分明时佛教论疏的特征之一。
其二,关于修道论。如果说缘起论是佛法的基石,那么修道论则是佛教修行解脱的依据和路径。《圆明论》指出:“凡欲修道,先须识其因果;二须识其邪正两门;三须依解起行;四须观莫废;五须明行位深浅。有此五门,三世诸佛之所共修,非今独说。”[6]35可见,“识因果”、“辨邪正”、“依解行”、“观莫废”、“明行位”是《圆明论》所立的修道之五门。
第一,识因果。因果是佛教义理重要范畴之一,识因果也成为修道者必修之课。《圆明论》中有关于因果的诠释[6]29,还特别强调:“明因果者,凡人之言道人,须自知此是俗情,盖亦是虚。若不自知,即多失道。”还指出:“若观此身,从头至足,无所可观。众人不赞,朝市无名,行则无人记,坐复无人美,衣不盖形,食不充口,衣马不具。当知前身未曾忍辱,悭贪具备,不曾为福。如此观者,深须惭愧。自知不具足者,当须种福,是名因果。”[6]36
第二,辨邪正。所谓辨邪正,主要是指执念与否。
第三,依解行。所谓依解行,即是通过观行觉照,逐渐断尽凡夫习气、烦恼[6]39。
第四,观莫废。常观莫废,实际上是指理行相辅之观。
第五,明行位。明行位深浅,实际上就是要求修行者确知具体果位,而又不执于具体果位[6]39。
其三,关于判教说。《圆明论》提出渐教、顿教、圆教三种,此可被视为《圆明論》的判教学说。判教,其旨归既是一种修道之方便,亦是一种立宗之依凭。就前者而言,诸如《圆明论》所示渐教、顿教、圆教三种;就后者而言,诸如宗密的“教三种会禅三宗”[9]。
《圆明论》所言渐、顿、圆实际上可追溯至北魏慧光甚至勒拿摩提。慧光承佛陀三藏及勒拿摩提之学,立“渐、顿、圆三教”,判“因缘、假名、诳相、常住”四宗,开创了地论学派南道系的判教系统[10]。虽《圆明论》主渐、顿、圆三教,但是否能就此将其归于慧光判教思想体系或地论学派,实则要深入检视。《圆明论》所述渐、顿、圆三教思想如下:
第一,渐教。《圆明论》据众生根基有别,而言有小乘人、大乘观(者)及自谓顿教的渐门[6]20。
第二,顿教。顿教即是修行者善知自我身相心体及其来去之处。修行者悉知其“身相元从妄想心中生”,而其妄想心,则“元无有体”。
第三,圆教。圆教实际上是一种无分别的境界,即“圆教法门者,众生是诸佛,诸佛是众生”;而“圆教法门中明义者,亦非众生界,亦非菩萨界”。
三 《圆明论》归属判释
关于《圆明论》归属问题,学界分歧较大,主要有两类观点:一是《圆明论》属于禅宗尤其是禅宗北宗一系;二是《圆明论》更接近于摄论宗与地论师的义理系统与修行方法。
关于《圆明论》与北宗禅之关涉的判释,最具代表性的学者为柳田圣山在《传法宝纪とその作者》中认为《圆明论》以《楞伽经》“自觉圣智”立论,并与北宗禅文献合抄,故将其归为北宗禅师之著作{1}。田中良昭于1969年在《敦煌本<圆明论>について》中认同柳田圣山的观点,并指出北7254首题署名“马鸣菩萨造”为伪托之辞,再据池田温的研究,推测法藏本P.3664可能抄于8世纪末[11]。师从柳田圣山的马克瑞,在其1983年完成并于1986年出版的博士论文中指出,《圆明论》可能为神秀所述或是北宗某位重要禅师的辑录,并在该书附录以P.3664为底本,对《圆明论》进行的录文和校勘[10]18-44 。2012年,柳干康以《圆明论》第七品夫妻二人愚痴不识酒中自影之喻为立论点,通过将《圆明论》与《观心论》、“五方便”等北宗文献进行比较,认为《圆明论》是受唯识思想影响而成书于《二入四行论》之后的北宗早期禅文献[12]。换言之,自柳田圣山后,日本学界对《圆明论》归属问题基本上未出柳田圣山“《圆明论》为北宗禅早期文献”的判定{1}。endprint
关于《圆明论》与摄论宗与地论师的义理系统与修行方法的关涉,见黄青萍发表于《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的论文。该文以傅图所藏写卷188106号为中心,从《圆明论》写卷发现及刊布史切入,对《圆明论》与《阿摩罗识》两者关系、思想内容与修行方法等方面做了深入研究,认为两份文献更接近于摄论宗与地论师的义理系统与修行方法。黄青萍还指出《圆明论》与《阿摩罗识》的流传虽与禅宗有关,但两者思想内容与修行方法却异于北宗,因此强调对《圆明论》与《阿摩罗识》的研究,要跳出北宗文献之框架[5]199-233。
那么,《圆明论》究竟应归属于禅宗北宗文献还是其在义理系统与修行方法上更接近于摄论宗与地论师呢?对于这一问题的回答,不宜仅以“是”或“否”来统摄之。换言之,对《圆明论》的归属判定,既要考察其传抄系统,更要检视其思想内容。
其一,关于《圆明论》的传抄系统。目前所知,《圆明论》有S.6184、P.3664、北7254、石井光雄旧藏本、Дх.00696、傅斯年图书馆藏第188106号等六份写卷。这六份写卷抄写情况主要参考了黄菁萍博士《敦煌写本〈圆明论〉与〈阿摩罗识〉初探——以傅图188106号为中心》一文的相关资料,本文不再详列。可知在《圆明论》六份写卷抄本系统中,实际上只有P.3664、北7254、石井光雄旧藏本及傅图藏第188106号是有效的,因其余两份写卷尾残,其后是否接续文献及接续何种文献,皆不得而知。就四份有效写卷来看,P.3664、石井光雄旧藏本及傅图藏第188106号对《圆明论》和《阿摩罗识》都有抄录,但其后接续的文献都不一致。据此,笔者认为《圆明论》-《阿摩罗识》之间的关涉非常弱,至少形式上是如此。至于《圆明论》能否置于北宗禅文献系统中,从抄本系统形式上看,并不存在强关涉关系。换言之,《圆明论》是否与北宗禅文献有关,不能仅凭文献抄录情况来判定。
其二,关于《圆明论》的思想体系。如果说文献抄录情况只是判定《圆明论》归属的一个外在要素,那么,其内在要素则应是其思想内容。
北宗禅部分文献的内容,如《大通禅师碑》[13]、《观心论》[14]、《秀禅师七礼》[15]、《秀禅师劝善文》[16]等,与《圆明论》相比较,不难发现二者的内在关涉是非常紧密的。当然,此说并非要硬拉近两者的关系,而是就文本间所呈现的内在关涉而言的。因此,无论如何,我们都无法割舍《圆明论》与北宗禅文献之间的内在关系。
简要言之,以《圆明论》录校为基础,可以发现,北7254与傅图188106号可对P.3664进行较好地补充与完善,这是目前学界尚未开展的工作;从《圆明论》内容来看,其所立缘起理论实际上是对如来藏缘起与阿赖耶识缘起的融合,而非仅以某一种缘起立论,这亦是隋唐时期佛教诸宗派之间融合的呈现;从文本结构与核心内容来看,《圆明论》与北宗禅文献之间有着非常强的关涉,因此,我们无法割舍《圆明论》与北宗禅之间的内在关联。尽管马克瑞博士的“《圆明论》为神秀所述或为北宗某位重要禅师辑录”[1]163这一推论缺少强有力证据,但其对《圆明论》与北宗禅文献之关系的判释是无可厚非的。笔者赞同杨宝玉教授所言,对文献作者的辨析、文献归属的判定,这不仅是文书整理研究工作无法回避的问题,更对文书内容性质的正确解读及文书史料价值的发挥利用都具有重要影响[17]。
参考文献:
[1]韩传强.禅宗北宗研究[M].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13:162.
[2]中国国家图书馆.国家图书馆藏敦煌遗书:第101册[M].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8:206-215.
[3]田中良昭.敦煌禅宗文献の研究[M].东京:大东出版社,1985:389-400.
[4]俄罗斯科学院东方研究所圣彼得堡分所,俄罗斯科学出版社东方文学部,上海古籍出版社.俄罗斯科學院东方研究所圣彼得堡分所藏敦煌文献:第7册[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31.
[5]黄青萍.敦煌写本〈圆明论〉与〈阿摩罗识〉初探——以傅图188106号为中心[J].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2013:199-233.
[6]John R.McRae,The Northern School and the Formation of Early Chan Buddhism.Honolulu: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1986:18-44.
[7]高小伟.敦煌本〈圆明论〉校录研究[D].兰州:兰州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5:31-42.
[8]赖永海.中国佛教与哲学[M].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4:3.
[9]王仲尧.隋唐佛教判教思想研究[M].成都:巴蜀书社,2000:165.
[10]赖永海.中国佛教通史:第3卷[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366.
[11]田中良昭.敦煌本〈圆明论〉について[J].印度学佛教学研究(第18卷),1969(1):204-207.
[12]柳干康.〈圆明论〉の思想的位置について:经典援用と譬喻表现から见る心の理解[J].印度学佛教学研究(第60卷),2012(2):1081-1084.
[13]张说.唐玉泉寺大通禅师碑铭并序[M]//董诰,等.全唐文:第231卷.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1030-
1031.
[14]宗性法师.问学散论[M].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8:63.
[15]圣凯法师.中国佛教忏法研究[M].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4:323-324.
[16]陈祚龙.敦煌古抄中世诗歌—续.敦煌学海探珠[M].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79:169-171.
[17]杨宝玉.法藏敦煌文书P.2942作者考辨[J].敦煌研究,2014(1):62-66.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