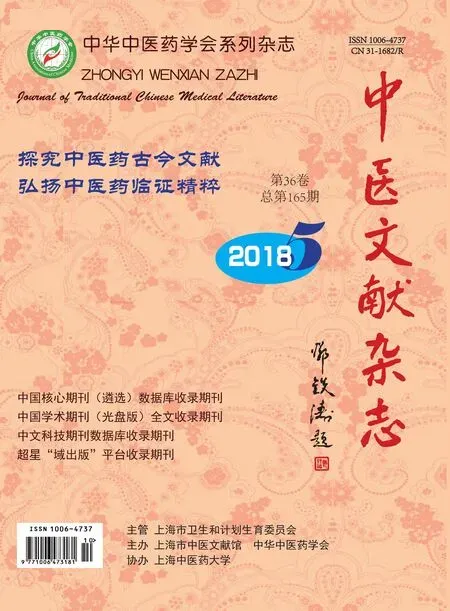肖晓亭《疯门全书》与麻风病的因机论治
2018-01-19广州中医药大学广州510006
广州中医药大学(广州,510006)
陈天红 吴培灵1 刘孝忠 刘 晟2△
麻风病是一种慢性传染性疾患,自古以来长期影响国人的健康,斯疾为病尤甚,残害尤烈,特别是其中的疣型,顽固不愈,可致严重的皮肤损坏和肢体残废[1]。历代医家针对本病的病因病机和防治曾有大量论述,但直到明代嘉靖时期之后,才有麻风病专书陆续出现,肖晓亭所撰《疯门全书》便是其中重要一种[2]。肖晓亭,祖籍江西省分宜县(今属新余市),生卒年不详,约生活于嘉庆、道光年间。曾为廪膳生,后以医济人,有记载其“医人神效”,“于治疠一门,尤属专家”。《疯门全书》是其广搜博采,悉心救治麻风患者数百余人,集其多年经验,“弹心竭力,三易寒暑”而成,其于治疠,百不失一,汇集了其对恶疠(即麻风)病因、病机、辨证、防治等多方面的认识。
《疯门全书》成书经过及版本流传
《疯门全书》写于乾隆嘉庆年间瘟疫大流行后,成书于嘉庆元年。乾隆嘉庆年间瘟疫大流行,此次流行范围极广,状况惨烈[3],如书中记叙:“村落中十里九里,处处咸有。”当时少有麻风病专书,缺少治验良方,肖晓亭怜悯麻风患者的悲惨境遇,广搜博采,寻求各种方法全力救治麻风患者数百余人,后为求治疠之法能传于后世,集其多年经验,“弹心竭力,三易寒暑”,分列纲目,简洁而清晰地论述了麻风病的成因辨证及防治之法,于嘉庆元年(1796年)撰成《病疾辑要》、《病疡备要》各一卷,但无力刊印,病故前托付于友人刘全石,然亦因种种原因未能成事。直至道光十二年(1832年)始由袁春台注而付梓,定其书名为《麻疯全书》(见袁春台按语)。道光二十三年、二十五年曾由敬业堂重刻刊行,光绪初亦有刻本。1936年裘吉生先生主编之《珍本医书集成》将该书编入刊印。1959年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曾校印出版。现所见版本为道光二十三年敬业堂刊本,现通行书名为《疯门全书》[4]。
麻风病的病名及症状表现
麻风病,在医史文献记载中,或以病因命名,或以典型症状命名,常有“疠”或“厉”,“大风”或“恶疾大风”、“癞”或“风癞”、“天刑”、“疠疡”等多种不同名称[5]。关于书中麻风病的病名,虽然肖晓亭已了解其发病与空气中一种“浊气秽气毒瓦斯”(即麻风杆菌)相关,但囿于时代局限,书中仍以“疠风”名之。“疠”言其恶疾,缠绵难愈,并会使患者有极大的身心痛苦;所谓的“风”,从虫从风,一言与空气中由风携带的毒气有关,二言与不正之风有关。即如《素问·脉要精微论》篇所言的“风寒客于脉而不去,名曰疠风”[6]。
麻风病的症状多表现为麻木性皮肤损伤、神经粗大、毛发脱落、感觉障碍、运动障碍、畸形、深在性浸润、腹股沟、腋窝等处淋巴结肿胀,涉及皮肤、骨骼、内脏等多种组织和器官损害。《疯门全书》对于麻风患者症状的观察极为准确。书中记载的“面紫发泡”,“遍身生疮,上损眼目”,“眉毛先脱,重则鼻梁崩塌”,“四肢浮肿”等全身症状,以及“虎口肉珠必焦”和特征性症状,及“皮死麻木不仁”、“血死溃烂,脓水淋漓”等局部症状,均与现代医学对麻风病的认识相吻合。
对麻风病病因病机的认识
麻风病的病因,《疯门全书》中认为其与东南地势低而近水有关,再加上气候的异常,故而造成此病的流行,且认为其发病与五风生五虫密切相关。肖晓亭在书中写道:“嘉庆元年(1796年)孟夏,盖东南地卑近水之处,此疾尤甚。天地较炎,地气卑湿”,“湿热相搏,乘人之虚,入于营卫……故此病血热居多。又卧于湿地,受其熏蒸……皆能受病。初则血滞不行,渐生麻痹。”其观点与《脉要精微》中“疠风者,营卫热,其气不清”的观点无二。近年由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主导的一项研究证实,瘟疫的爆发大部分是突如其来的严重气候变化而引起,此研究结果与《疯门全书》气候变化引发瘟疫流行的观点不谋而合。至于“五风生五虫”的观点,作者囿于当时有限的医学知识,不可能从现代病原学的角度去认识麻风病。事实上西医亦直到1873年才发现麻风病的病原体——麻风杆菌,证实了麻风是麻风杆菌导致的一种慢性传染病。而在今天看来,肖晓亭提出空气中由风携带的微小虫体加上气候异常导致麻风病流行的观点不但不荒谬,且有一定的先进性。对于虫与该病的关系,书中写道“黄风生黄虫,青风生青虫……黑风生黑虫”,“此五种虫食人五脏……鼠食人肝,眉睫堕落,食人心,遍身生疮……”,说明肖晓亭当时已经意识到有一种特殊的生命体的入侵,才使得人的五脏长期被消磨。但是肖晓亭并未认识到“无形”的虫才是该病的传染体,而是将其作为一种有形的必须杀灭的寄生虫,以诸如苦参、大黄等“利出瘀恶虫物”入方中,作者以此等缺乏实证的理论来诠释麻风病的病因,是该书的局限之处。
肖氏认为,麻风病的直接病机在于营卫不和。相较于其他时行疫证,麻风最典型的症状即是“肌肤麻痹”,至于此症状出现的原因,肖氏认为“卫气不行则为麻木……营气虚则不仁”,亦由“卫气内伏,湿热日久,血随火化而致”。麻风病的根本病机为“阳明一经”气血不和。阳明经多血多气,气血败坏,则“食人五脏骨髓皮肉筋节”,如薛己所言,“疮疡所患,非止一脏,然其气血,无有不伤”。麻风病虽是时行疫证,但肖晓亭倾向于从六经辨证认识此病。《疯门全书》“麻疯三十六种辨症图说”一节所列的“唇翻齿露,手足指脱”的大麻疯,或是“手足麻木,身有死肉,皮肉常似虫行”的暑湿疯,或身有红块手拳足吊的拔发疯,或发泡生疮且多痹肉的血热疯等多种麻风证型,确与阳明病密切相关。如“脾主口主唇主四肢主肌肉”、“阳明病法多汗反无汗其身如虫行皮中状者,此以久虚故也“(《伤寒论·辨阳明病脉证并治》第196条)、“阳明病,若能食,名中风”(《伤寒论·辨阳明病脉证并治》第190条)。结合对本病常见症状的综合分析,可以将麻风病的病机归纳为营卫不和,气血乖错,恶血稽留不去,血随火化而生此病。
针对麻风病的防治特点
1.治法多样,涉及病程各个阶段
作为一本麻风病防治专著,《疯门全书》所载麻风病的治疗方法极为丰富,大致可分为内治法与外治法。内治法载方126首,先是统治方,以古方为主,特别是上古方;其次分治,分五脏经络的不同,酌加引经药,以疏其流;当病情稳定时,投以缓治、补治,以治本气不足的病人;如果受病既久,投缓剂不效,则以峻治;气血凝滞,湿热相搏,则以泻治;如果遇到先患麻风而有并发症者,或由于本病而引起麻风者,则兼治之;最后断根时,重视麻风病人的善后,即“补其血气壮其筋骨”,此为余治。外治法载方49首,涉及针法、灸法、烧法、蒸法、熏洗法、淋浴法、涂抹法、熨法等,甚至有专门去腐烂之肉的“瘰烂法”。全书共计列方175首,剂型包括丸剂、散剂、膏剂、丹剂、饮剂、油剂、饭剂、水剂、浆剂、酒剂、粉剂等,涉及预防、治疗、调护等各个方面[7]。
2.紧抓病因病机,和营卫调气血
关于本病的治疗原则,肖氏紧抓外邪入侵的病因以及营卫不和、气血不调的病机,提出“以凉血和血为主,驱风驱湿为佐,审元气之虚实,按六经以分治,斯治厉之要道也”。治疗上立足皮肤之疾为营卫之气不仁不用,重视调和营卫,调治之余不忘使用五脏引经药,解毒之中凉血和血,驱风除湿,融入血药,散结化瘀。难得的是,肖晓亭并不拘于血热凉血之说,更主张因机论治、方证相印,虽桂附亦可用之。如针对危重病症,书中有录“疠疾回阳起痿方”一首,专门针对麻风病人由于后期弥漫性浸润,损害遍及全身出现的阳虚重症,方中用了附子、肉桂以引火归原、回阳救逆,以破故纸和枸杞温养肝肾,在治疫病多用清热解毒之法的明清时期,显得极为可贵。
3.抓住典型症状,提出以针砭刺络放血
与其他麻风病防治专著相比,《疯门全书》的最大特色是紧紧抓住麻风病人肌肤不仁这一典型症状,标本兼顾,虚实并重。既能从外感病的角度认识麻风病,在治疗中贯彻祛邪的原则,又能认识到麻风病内有“恶血”、“死血”的病因病机,提出“若恶血凝滞在肌表经络者,宜刺宜汗”的治疗法则。这与《长刺节论》“病大风,骨节重,须眉堕,名曰大风,刺肌肉为故,汗出百日,刺骨髓,汗出百日”的做法不谋而合。其做法或刺十指甲并臂腕以去肌表毒血,或针足指缝并腿腕以去下肢毒血。其将解决“痹”的问题,当作治疗的要务,防其“有一二点痹肉未活,或痹肉活而皮色未撤消,以致复作”。
4.反对滥用毒药、戗伐正气
肖晓亭在记述麻风病治疗方法时,提出不能过度使用攻毒之药,“当先助胃壮气,使根本坚固,而后治其疮可也”。他认为,“丹溪止用醉仙散、再造散二方,但服轻粉,多生轻粉毒,恐一疾未愈,又添一疾。又有大黄皂刺牵牛之类,然惟实者可用,气血虚者,反耗元气”。肖氏提出,非病之极重、不得已而用之,主张用平和之药亦可去病,而重药以蛇蝎即可,不可过用毒药,以致过于伐正而病情愈重。
5.提倡戒“食”,顾护脾胃
肖晓亭在对麻风病人的治疗过程中极其重视日常饮食调护。他认为“发毒之物助毒,生冷之物凝血”,“凝滞之物固毒,煎炒之物助火”,故其立足病人体质及疾病特点,对于营卫不和、气血乖错的麻风病患者,嘱其冷食煎炒“皆宜切戒二三年”,特别是“若自死禽兽之肉,终身宜戒”。对于治愈的病人,亦强调不能轻忽善后,要固本祛邪,培补脾胃。
6.重视疾病预防,提出防传染措施
书中有载“疯疾传染,事故常有”,“患病疾者父子离散、夫妻睽违、亲友避之、行道叱之”,明确指出麻风是一种具有强烈传染性的疾病。是故肖晓亭针对麻风病的传染性也提出了相应的预防措施:“但回避可也,不共用器,不同饮食,各房各床,尽力求治……调停处置,令衣食不缺,若夫妻离弃,切莫劝解”,又云“大小便不同器,人皆知之,外此病人吸烟,亦宜避之……病人之尿,不可淋烟草,淋则吃者必生疯病,此则人所不知。”在作者生活的年代,这些方法的提出极具前瞻性,亦具有一定的科学性,是很难能可贵的。
综上所述,肖晓亭所著《疯门全书》为麻风病学专著,书中作者基于自己治愈多例麻风病的实践经验,述其对于麻风病因、机、论治及预防等多方面的认识。肖晓亭治疗麻风病,辨证精微,用药独到,方法多样,其所撰《疯门全书》对清末麻风病的治疗作出了卓越贡献。虽然由于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加强了麻风病的社会性防治措施[8],麻风病例在上世纪末已经显著减少,但这并不意味着麻风病得到了彻底的根治,报刊杂志仍时有麻风病例的报道[9- 11],《疯门全书》所载的麻风病治疗经验在当今社会仍具有较大的参考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