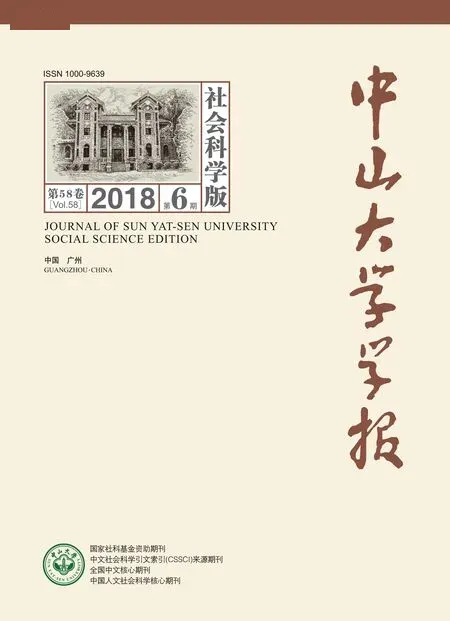清末“国体”“政体”区分说的源起与变异*
2018-01-19邓华莹
邓 华 莹
清末以来,“国体”“政体”的涵义所指及其异同长期聚讼纷纭,难得一是,以至毛泽东1940年初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感慨“这个国体问题,从前清末年起,闹了几十年还没有闹清楚”①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北京:人民出版社,1952年,第18页。。“国体”“政体”概念闹不清楚,其源起及关节在于《明治宪法》颁布后日本学者基于君主主权论、旨在尊崇天皇的“国体”“政体”区分说传入中国,由此衍生“国体”“政体”异同的无穷争论。近年来,学界对“国体”“政体”区分说在近代中国生成衍变的历程的探讨逐渐增多②相关研究主要有:林来梵《国体概念史:跨国移植与演变》(《中国社会科学》2013年第3期)、《国体宪法学:亚洲宪法学的先驱形态》(《中外法学》2014年第5期),范贤政《“国体”与“政体”在近代中国的演变与分化》(《学术研究》2014年第3期),高力克《宪政与民主:梁启超的政体与国体理论》(《二十一世纪》2014年4月号),王宏斌《“政体”“国体”词义之嬗变与近代社会思潮之变迁》(《安徽史学》2014年第5期),喻中《所谓国体:宪法时刻与梁启超的共和再造》(《法学家》2015年第4期)等。,本文将在此基础上依据清末汉译的日本法政论著,详细考察“国体”“政体”区分说在中国如何从无到有地发生,探析不同学者的观点之间的联系与区别,并具体呈现国人接受、认知的复杂情形。
一、君主主权论与“国体”“政体”区分说的兴起
作为法政概念,与国家类型知识紧密相关的“国体”“政体”在近代中国出现与流行,主要是受清末大规模引进日本幕末明治时期借用汉字翻译西学而形成的东学影响。由于不同时期欧美各国学者区分国家种类的方法和所用概念多样,从日本传入的“政体”除表达“政府形体”之涵义外,又与“国体”一样指称“国家形体”,加以“国家”“政府”经常混用和区分“国家形体”“政府形体”不直接等同于区别“国体”“政体”,“国体”“政体”的意涵指称虽有分别,亦有重叠,并非迥殊。汉文文献中明确区分“国体”“政体”的论述,最早出现在1900年12月起连载于《译书汇编》第1、2、7、9期的《政治学提纲》,其中第7期重新收录前两期已刊的章节并略加删改。经查,《政治学提纲》译自鸟谷部铣太郎著《通俗政治泛论》[注]《吉林官报》第13期(1909年6月8日)、第24期(1909年9月24日)也曾节译《通俗政治泛论》。。
《政治学提纲》第1章《国体及政体》第1节《总说》定义“政体”说:“凡国家必有统治之机关,其机关之组织及举行之迹象,即名之曰政体。”近代“政体”有专制、立宪二种。“一人主权在上,乾纲在握,万机独断,是之谓专制政体。设立宪法以组织国家统治之机关,谓之立法、行政、司法,是之谓立宪政治。”“然同一立宪政体,有因其政体之不同,而其统治机关之组织亦不同者。有民主国体而中寓立宪政体者,有君主政体而中寓立宪政体者。然而民主国体之中有美与法之不同,君主国体之中亦有英、德、奥之不同,因之而其统治之机关及主权之所在亦不能以一定之理相论。”[注][日]鸟谷部铣太郎:《政治学提纲》,《译书汇编》第1期,1900年12月6日,第3、5、6页。按这段话的意思,立宪政体因“政体”而异指民主国体、君主政体下的立宪政体有别,“国体”“政体”所指相同。对照原著,可发现引文中加下划线的“政体”均为“国体”[注][日]鸟谷部春汀:《通俗政治泛论》,东京:博文馆,1898年,第7,7页。。
区分“国体”“政体”的观念在后续章节进一步凸显。文中比较德、英、日等国制度异同时写道,“德意志主权不在皇帝一人,而在联邦参议院”,“英国君主不得谓统治之主体……其主权之所在为众议院”,“日本帝国乃纯然之君主国体,其主权由天皇总揽之,惟既立宪法、开国会,与君主专制不同”。在鸟谷部铣太郎眼中,“欧洲于国体、政体无所区别,日本则君主国体而君主政体,天皇于名实上均为国家之主权者。约言之,即君主者,国家之主体是也”[注][日]鸟谷部铣太郎:《政治学提纲》,《译书汇编》第7期,1901年7月30日,第9、10、14,15、32、33、36,18,6页。。
《政治学提纲》接着说,日本自古即君主国体,近来则由专制政体变为立宪政体。立宪君主国有皇帝或国王“统一三权而总揽万机”,故君主是“国家统治之最高机关”。由此可见,“日本则君主国体而君主政体”指日本君主既是主权所在,又是国家最高机关。有人认为:“主权者乃国家之主体,有自存独立之概,所谓政治机关者,不过主权者设置之,使分掌国家统治权之作用而已。故以君主为政治机关,则君主非主权者矣。”鸟谷部铣太郎用“国体”“政体”区分说解释道:“以君主为政治机关之一者,非就统治之实质而言,就其作用而言也。统治之实质由国体而定,统治之作用由政体而定者也。”日本是天皇钦定宪法,“故自国体上言之,君主独立于宪法之上,而自政体上言之,则君主亦不得不依宪法以施行其主权”。“就君主国体而言,君主固兼统治权之本体与作用而有之。惟统治权之作用复由政体之专制与立宪而不同,专制政体之君主统治权之作用毫无制限,立宪政体之君主则必依宪法以行,故统治权之作用即受宪法之制限。”⑤[日]鸟谷部铣太郎:《政治学提纲》,《译书汇编》第7期,1901年7月30日,第9、10、14,15、32、33、36,18,6页。
总之,“国体”“政体”明显分别,“国体”因主权所在、统治权的主体而异,指称君主、民主等;“政体”因国家统治机关如何组织、活动,亦即统治权的作用而分别,除相互对立的专制、立宪外,又有君主等“政体”。《政治学提纲》还有其他区分“国体”“政体”的论述,如:“法兰西殆无一定国体,亦无一定政体,时而为君主国,时而为民主国,革命屡起,政体亦随之屡变。”“现今法国为共和国体,然其共和制度,与美国不同。”⑥[日]鸟谷部铣太郎:《政治学提纲》,《译书汇编》第7期,1901年7月30日,第9、10、14,15、32、33、36,18,6页。“国体”“政体”亦可指称其他相关事物。《译书汇编》第2期的《政治学提纲》说:“德意志虽称帝国,与日本帝国政体则大不同,何则?日本帝国,则政府在上,郡县在下,纯然一国家之制也。至德意志帝国,则联邦国也。”[注][日]鸟谷部铣太郎:《政治学提纲》,《译书汇编》第2期,1901年1月28日,第7页。《译书汇编》第7期重刊的《政治学提纲》也有类似语句:“德意志虽曰帝国,其国体与日本不同,何也?日本帝国,乃单一国家,德意志帝国,则联邦国也。”⑧[日]鸟谷部铣太郎:《政治学提纲》,《译书汇编》第7期,1901年7月30日,第9、10、14,15、32、33、36,18,6页。一国家之制变成单一国家,含义相同,至关重要的是“政体”改为“国体”。查对《通俗政治泛论》可知原文是“国体”⑨[日]鸟谷部春汀:《通俗政治泛论》,东京:博文馆,1898年,第7,7页。。目前难以知悉何以出现此变化,但至少说明“国体”“政体”又在一般意义上指称单一国、联邦国等“国家形体”。
《政治学提纲》上述内容在清末经辗转抄述后流传颇广。1902年,邓实将该书第1章第1节改名《国体及政体总说》,登在《政艺通报》壬寅年第4、6期[注]《国体及政体总说》,《西政丛钞》卷1,邓实辑:《光绪壬寅(廿八年)政艺丛书》,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第27辑(267—270),台北:文海出版社,1976年,第664—666页。。1903年,汪荣宝、叶澜编纂《新尔雅》,是书“释政”篇解释“政体”完全剿袭《政治学提纲》。《新尔雅》又参考《政治学提纲》,介绍法、美等国政治,如说:“法兰西者,现今为共和政体。溯十八世纪初,时为君主国,时为民主国,革命屡起,政体亦随之屡变。”[注]汪荣宝、叶澜辑:《新尔雅》,上海:上海文明书局,1906年第3版,第9、11页。就这段论述而言,前一句话中原文的共和国体被改成共和政体,后一句话删去“国体”,仅留“政体”指称君主国、民主国,无形中消解了“国体”“政体”的区别。《译书汇编》《政艺通报》《新尔雅》等书刊广泛流传后,人们固然了解到区分“国体”“政体”的知识,但此类误译删改无疑又容易使“国体”“政体”变得异同难辨。
伴随日本法政译著剧增,“国体”“政体”区分说不断涌入。《译书汇编》第5—7、9期译载的樋山广业著《现行法制大意》指出,必须具备土地、臣民、主权三要素“才成国家,才得人格”。“国体”即“国家之组织,以表示国家主权之所在”,主要有主权在民的民主国体和主权在君的君主国体;“政体”为“政治之组织,即统治权之形式”,分为“立法、行政、司法咸私于一人之手”的专制政体和“设统治机关,立法、行政、司法各有其地,分掌其权”的立宪政体。“凡国体与政体,各有异同,非有一定之例”,“国体同而政体异者,政体同而国体异者,不胜缕纪”[注][日]樋山广业:《现行法制大意》,《译书汇编》第5期,1901年7月14日,第1、2、3页。。与《政治学提纲》近似,《现行法制大意》主张“国体”与主权(统治权)所在有关,“政体”指统治权的行使形式,此外还提到“国体”“政体”对应“国家组织”“政治组织”。
目前学界一般认为这种“国体”“政体”区分学说在日本兴起与东京大学教师穗积八束的积极提倡关系密切[注]参见林来梵《国体概念史:跨国移植与演变》《国体宪法学——亚洲宪法学的先驱形态》二文。。1902年,东京大学法科大学政治科留学生王鸿年听穗积八束讲授宪法,并“于课暇摘录其要旨,更旁征诸说,搜罗欧米各国宪法以互相比证,勒为一卷,命曰《宪法法理要义》”[注]王鸿年:《宪法法理要义叙》,[日]穗积八束著,王鸿年译:《宪法法理要义》上卷,王惕斋发行,1902年,第1页。。此书集中反映了穗积八束的“国体”“政体”区分说的内涵与主旨。
和当时流行的观念一样,穗积八束把人民、土地、主权视作构成国家的三要素,主权即“最高无限之权力”,独一无二[注][日]穗积八束著,王鸿年译:《宪法法理要义》上卷,第7,10—13、15,23页。。他进而定义“国体”“政体”说:“国体者,主权之本体……主权之所在,非因法律而定,而实为历史之结果。”“国体”主要分为君主国体和民主国体,前者“以特定之一人为主权之人,其人之所以得主权者,则在于自己有固有之力”,后者“以国民为主权之所在,国会或政府皆受国民之委任,而为行政治之机关”。民主国体可细分为纯粹共和国体、贵族共和国体,后者现已不存。“政体”是“统治之权力动作于形式上者”,可分为专制、立宪二类。专制政体是立法、司法、行政三权握于一人之手,有君主专制、议员专制、大统领专制、数人合议专制等情况。立宪政体以“三权分立之精神及国民所选国会之参与立法”为主要特征。穗积八束强调:“立宪政体之特质,不以民主主义为要义,而法理上亦决不认民主主义为宪法之基础,学者于此处当格外注意,不可误解。”⑦[日]穗积八束著,王鸿年译:《宪法法理要义》上卷,第7,10—13、15,23页。
穗积八束指出,日本是君主国体,以君主为主权的本体,总揽统治权。他解释统治权为“统治其国家之命令及强制人民自由之权”⑧[日]穗积八束著,王鸿年译:《宪法法理要义》上卷,第7,10—13、15,23页。,在其论述中,与主权无甚分别。穗积八束认为君主总揽统治权是“立宪君主政体之本领,日本现今之政体,即系如此,而立宪君主政体与他种政体相异者,亦在于此”[注][日]穗积八束著,王鸿年译:《宪法法理要义》下卷,第2页。。由立宪君主政体等词可见,“政体”又可指称君主、民主“国体”与专制、立宪“政体”结合后衍生的国家类型,内涵所指相对较广。穗积八束说,德国“国法论虽采君主主义”,但“不敢断言君主为统治之主体,国民为服从统治权之客体,而以国家为人民之集合体,君主为国家之机关”。他不认同这种暧昧的态度,截然区分“统治权之主体及客体,而以客体属之人民,以明人民之为服从者,而非主权者”[注][日]穗积八束著,王鸿年译:《宪法法理要义》上卷,第33,9、10页。。
穗积八束强调日本国法学应以自身的“国体”为依据,“不得以外国国体及历史与本国相异者之国法法理,解说本国国法”。在他看来:“日本之国体,以君主为主权之观念,此观念由历史上国民信仰之心所维持发达者,而为建国之大则。”“君主与主权一体而不可分离,于君主之外无国家,君主即国家。”②[日]穗积八束著,王鸿年译:《宪法法理要义》上卷,第33,9、10页。他认为君主立宪国决不可有“国会为统治之主体”的思想,“盖其向来国体不同故也”[注][日]穗积八束著,王鸿年译:《宪法法理要义》下卷,第2页。。诚如王鸿年所言,穗积八束“阐扬君主主权说,以痛遏孟德斯鸠之三权分立论及鲁所民约论之流弊,而维持忠君爱国之大义以鼓舞人心”[注]王鸿年:《宪法法理要义叙》,[日]穗积八束著,王鸿年译:《宪法法理要义》上卷,第1页。。
其实,自主权概念诞生以来,其归属问题备受争议。日本明治立宪的过程中,各方对主权所在多有争论。具有标志意义的事件是,1882年1月14日,《东京日日新闻》发表社说,认为“凡君主国,不问独裁制与立宪制,主权不可不在君主”。此说一出,舆论哗然。“《每日》《朝野》《报知》等诸大新闻皆揄笔驳击之,其中或曰立宪国之主权在议院,或曰在君主与议院之间,或曰主权乃万能力而不受制限,又或曰君主止分有主权之一部,异说纷纷。要之,于主权在君乃独裁政治,在立宪政治人民握之,则全然同见。”[注]考政大臣编辑:《日本立宪史谭》,《北洋法政学报》第44册,1907年11月,第73页。
因主权所在已成焦点问题,伊藤博文等人制定、1889年2月颁布的《明治宪法》明确规定:“天皇为国家之元首,总揽治统,依此宪法条规行事。”治统即统治权。作为伊藤私人著作刊布,实际上带有官方性质的《日本帝国宪法义解》特别解释:“天皇宝祚,承之祖宗,传之子孙,国家统治权之所存也。宪法特揭大权而明记之于条章者,非表新设之义也,以见固有国体因之而益巩尔。”[注][日]伊藤博文撰,沈纮译:《日本宪法义解附皇室典范义解》,金粟斋,1902年第2版,第1页。协同制宪的金子坚太郎将此理念表述得更清楚明白:“我日本帝国以2500年的历史为根本,以2500年的国体为基础,吸收世界上通用的立宪政治即议会政治的一部分——只符合日本国体和日本历史的部分,以保全2500年的君权即天皇陛下的统治权,不变更国体,不割断历史,但却能加入欧洲宪法国的行列。”[注][日]金子坚太郎:《伊藤公与宪法制定事业》,《国家学会杂志》第24卷第7号,第25—26页。转引自肖传国:《近代西方文化与日本明治宪法——从英法思想向普鲁士·德意志思想的演变》,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第139页。
按照伊藤博文等人的观念,日本立宪后君主握有统治权是其历史及固有“国体”使然,那么此处“国体”指什么呢?“在日本,所谓‘国体’一语,依德川时代之水户学派而普及,其本义决非为法律的观念。《神皇正统纪》说:‘大日本乃是神国,从天祖开基,日神传极长之流,独我国有此事,别国无其例,因此故称为神国。’这种思想为发生后世的国体说之根底。”[注][日]美浓部达吉著,欧宗祐、何作霖译:《宪法学原理》,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277页。经不同时期的学者不断叠加意义后,这种“国体”思想日益饱满。它主要宣扬日本是神国,继承神统的天皇万世一系,同时牵连到推崇天皇和强调君臣大义等方面。由于伊藤博文认为“确定君主的唯一主权者身份,是保障国体的首要条件”,便将君主握有主权的观念注入“国体”思想中[注]潘昌龙:《试论〈明治宪法〉中的国体论思想》,《外国问题研究》1989年第1期。,不过他所说的“国体”仍不是对应西学的法政概念。
穗积八束也十分认同推崇天皇的“国体”思想。他曾说,“我千古之国体,由我日本民族之特性建设维持”[注][日]穗积八束著,章起渭译,刘景韩校:《国民教育爱国心》,光绪乙巳,两广学务处仿京师大学堂官书局本排印,《原序》第1页,第1页。,此特性即祖先教、“崇敬祖先之大义”。崇敬祖先须“服从祖先之威力”,祖先威力“在国则天皇代表之,对其国民而行统治之权”[日]穗积八束著,章起渭译,刘景韩校:《国民教育爱国心》,光绪乙巳,两广学务处仿京师大学堂官书局本排印,《原序》第1页,第1页。。
在尊崇天皇的“国体”思想的主导下,伊藤博文、穗积八束均认为日本天皇在立宪后仍总揽统治权。穗积八束更利用“国体”“政体”区分说将此观念理论化,从法理的角度阐论日本实行立宪政体后仍是以天皇为主权、统治权主体的君主国体,推重君权的旨趣表露无遗。那么,国人如何看待《宪法法理要义》呢?张缉光在给汪康年的信中称,此书“立说于吾国历史、民俗极为相宜”[注]《张缉光致汪康年函》第6通,上海图书馆编:《汪康年师友书札》第2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第1790页。。留日学生编辑的《新学书目提要》则评价:“穗积氏盖素主君权之论者(原序亦明言之),其大旨自有所见,未必定非。”对于宪法“非所以束缚君主而实君主之所以束缚人民”的说法则不敢苟同[注]通雅斋同人编:《新学书目提要》,熊月之编:《晚清新学书目提要》,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7年,第406页。。由于此书明显置重君权,有论者认为王鸿年乃“译界中之蟊贼”,借《宪法法理要义》“倡违悖公理之说,执为眩吾民智之具”[注]《大陆报》第1年第8号,1903年7月4日,“问答”,第2页。。
值得深究的是,穗积八束的“国体”“政体”区分说是其独创呢,还是受欧美政治知识影响?从学术渊源来看,此理论可能来自德国。德国不乏从二元对立的角度分类国家的学说,岩井尊文指出,“关于国体、政体之有无区别,学说共分三种”:
德儒依挨林克谓国体、政体并无区别,总揽统治权之机关为君主,则为君主国体,即为君主政体;为人民,则为民主国体,即为民主政体。盖专从组织机关上言之,宜其无分也。德儒黎姆则谓国体与政体有分,自是确论,但专以人数及机关之多寡为区别,亦有未当。如谓总揽统治权为一人为君主国体,为多数人则为民主国体,然行贵族制度之国,亦以多数人总揽统治权,将亦谓为民主国乎?况以行使统治权之机关之多少分政体,尤与立宪、专制之区别无关系,故黎姆之说,未可尽从。德儒斯密特则谓国家有三种机关,曰立法,曰行政,曰监督,三者合则为专制政体,三者分则为立宪政体。至国体之分,则专以监督机关为标准,监督为君主,则为君主国体,监督为人民,则为民主国体。是说也,亦不能无弊。国家政务分立法、行政,固为学者所公认,至监督则无积极的行为,此制虽各国偶一有之(德意志以君主为监督),然在一般国法上言,则未为正当也。[注][日]岩井尊文讲述,熊元翰编辑:《国法学》卷上,北京:安徽法学社,1914年第4版,第41—42页。
由此可见,虽然标准不一,也有德国学者区分君主、民主与专制、立宪为“国体”“政体”两个范畴。其中穗积八束的观点与1882—1890年任教于东京大学的德国学者那特硁(Karl Rathgen)提出的“国体”“政体”区分说相当接近。
那特硁的英文讲义由弟子山崎哲藏、李家隆介翻译成《政治学:一名国家学》,1891—1893年间分成上(国家编)、中(宪法编)、下(行政编)3卷出版,后多次重刊[注]孙宏云:《那特硁的〈政治学〉及其在晚清的译介》,《中华文史论丛》2011年第3期。。1900年12月,《清议报》第66册刊载麦孟华节译的《政治学》[注][德]拉坚讲述,玉瑟斋主重译:《政治学》,《清议报》第66册,1900年12月12日,“译书附录”,第1—3页。。1901年,冯自由受广智书局聘将《政治学》全书译出,请章太炎润辞[注]冯自由:《记章太炎与余订交始末》,《革命逸史》上册,北京:新星出版社,2009年,第216页。,1902年分4次印刷出版。此书颇流行,1903年底已重印至第3版。商务印书馆也在1902年3月、8月分两编出版戢翼翚、王慕陶译《政治学(国家编)》。
冯译《政治学(国家编)》第2篇第1章《国体及政体》指出:“欲区分理论上、历史上之国家,以究其性质发达,则必先明国体、政体及宪法意义之区别与其关系。”具体如下:
(第一)国体。国体者,国家之形式,以主权之主体、客体所在而变者也。主权之主体为君主,其客体以国民全体而成,此谓君主政体;主权之主体为国民之总意,其客体以国民各个而成,此谓民主政体。方今文明诸国,国体虽异,然据法理而类别之,则不外此二者。世所称君主政体或贵族政体者,是国体之类别,而非政体之类别也。(第二)政体。政体者,执行主权之形式也。独裁君主国执行主权,常依君意,立宪君主国执行主权,常依宪法。主权之机关,谓之政府。主权之形式,谓之政体。方今宇内各国,政体虽异,然据法理而类别之,则不外此二者,一独裁,亦曰专制政体,一立宪,亦曰制限政体。[注][德]那特硁著,冯自由译:《政治学》上卷,上海:广智书局,1902年,第2篇《国家之生理》第1—2,4—9,9、12、29—30页。
参校日文版《政治学》,上面加下划线的君主政体、民主政体本是君主国体、民主国体[注][日]山崎哲藏译:《政治学》,东京:明法堂,1891年,第59页。。戢翼翚、王慕陶也误译了部分语句,他们译“是国体之类别,而非政体之类别”为“则政体之别,非国体之别”[注][德]那特硁著,戢翼翚、王慕陶译:《政治学》,上海:商务印书馆,1902年,第2篇《国家之生理》第1页。,对调了“国体”“政体”。原著又说“政体”是“政治形式”,换言之,分别被定义为主权所在及其执行形式的“国体”“政体”对应国家形式和政治形式。据日本学者研究,它们源于德文词汇Staatsform、Regierungsform,英文表述是Form of State、Form of Government[注][日]藤井隆:《政体论から「开明专制论」を読む》,《修道法学》34(2),2012年。。
辨别“国体”“政体”后,《政治学》指出“类分国体之法”有二种,“理论分类,由于国体之性质;历史分类,由于国体发达之次序”。理论分类有主观、客观之别,“其主观据主权之主体而观察之,其客观据主权之客体而观察之”。
主观的“国体”分类标准有二:一是“主权者之数”,亚里士多德根据主权在君主一人、贵族数人、国民全体而区分出君主国体、贵族国体、民主国体。二是“主权者之目的”,亚里士多德根据主权者的目的是为公益抑或私益而区别出正体国家(Normal State)与变体国家(Abnormal State),前者即君主、贵族、民主三种“国体”,它们分别对应暴君国体、寡人国体、暴民国体三种变体国家。孟德斯鸠则“以道德主义为国家主权者之目的而类分主(按:原文如此,应为‘国’)体”。主权者以名誉为主义的是君主国体,以德义为主义的是民主国体,以温和为主义的是贵族国体,以胁吓为主义的是压制国体。
从统治的客体的角度来看,可区分国家为:一、国民全数有服从义务,无参政权利的无自由国体;二、国民多数有服从义务,无参政权利的半自由国体;三、国民全数均有参政权利的自由国体⑤[德]那特硁著,冯自由译:《政治学》上卷,上海:广智书局,1902年,第2篇《国家之生理》第1—2,4—9,9、12、29—30页。。
至于从历史上类分“国体”,可大别为古代国家、近世国家。古代最初是家族国家,后衍生出神权国家、市府国家、封建国家;近世国家有近世专制君主制、立宪君主制、代议共和制、联邦制四种⑥[德]那特硁著,冯自由译:《政治学》上卷,上海:广智书局,1902年,第2篇《国家之生理》第1—2,4—9,9、12、29—30页。。从历史的角度类分的“国体”显然与“主权之主体、客体所在”的内涵联系不大,可见“国体”亦可在广义上指称各种国家形式。
光绪戊戌、庚子年后,留日及国内法政教育勃兴,大量法政著作被译介到中国。通过课堂讲授和个人阅读,越来越多国人接触到以主权、统治权所在及其行使形式为标准区分“国体”“政体”的观点,受“国体”“政体”难以厘然区分和法政知识水平不高等因素所限,对概念的内涵所指的理解因人而异。1906年起在京师法律学堂开设法学通论课程的冈田朝太郎编有讲义《法学通论》,张孝栘、汪庚年、熊元翰等人先后将其汉译出版。由张孝栘译《法学通论》可见,冈田认为“国体也者,主权所在之形式”,分为主权属于贵族、国民、君主及国民、君主的贵族国、民主国、君民共主国、君主国。“政体也者,主权行使之形式也,即统治作用之外形”,有专制、立宪之别[注][日]冈田朝太郎著,张孝栘译:《法学通论》,东京:富山房、有斐阁,1908年,第9—10页。。
熊元翰译《法学通论》也有相同的“国体”“政体”区分说,但译者在讲义的基础上以“讲堂笔记,补其所无”,又加按语“间附己见”[注]熊元翰:《例言》,[日]冈田朝太郎口述,熊元翰编,何勤华点校:《法学通论》,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经掺杂个人见解后,该书所见“国体”“政体”的所指前后互歧。熊译《法学通论》写道:“而阅世既久,又有国体、政体之区别焉。国体之区别何?即君主国、民主国、君民共主国是也。政体之区别何?既专制政体(以一人为治者)、贵族政体(以少数人为治者)、共和政体(以国民之全体为治者)是也。”介绍宪法时又说:“宪法为规定政体大纲之法(有成文宪法、不成文宪法),与立宪政体不同。盖既为国家,无论其国体如何(成为专制国、成为立宪国),皆不可谓无宪法。”[注][日]冈田朝太郎口述,熊元翰编,何勤华点校:《法学通论》,第7、9页。
熊译《法学通论》既以主权所在及其行使形式为标准区分“国体”“政体”,分别指称贵族国、民主国、君民共主国、君主国和专制、立宪政治,又厘别君主国、民主国、君民共主国和专制、贵族、共和为“国体”“政体”,还用“国体”指称专制国、立宪国,使得“国体”“政体”的指称涵盖淆乱错杂。熊氏并不十分注意概念的涵义所指,以致观念前后矛盾固然是因为其法政知识水平相对较低,但这也与“国体”“政体”难以截然区分密切相关。汪庚年辑《法学通论》有一段与熊译《法学通论》相近的论述:“各国之政体亦不同,有以一人为治者,为君主政体。有以数人为治者,为贵族政体(一曰寡人政体)。有合国民之团体为治者,为共和政体。历史上与政体上之关系,既有种种之不同,而要以治者出命令,被治者服从命令。”[注][日]冈田朝太郎:《法学通论》,汪庚年编:《法学汇编》第1册,北京:京师法学编辑社,1911年,第5—6页。在不同的国家分类学说下,君主、民主等政治本身就可以称作“政体”。熊元翰接触关系复杂的“国体”“政体”后,一时难以理清头绪,难免拼凑杂糅,随意运用。
二、“国体”“政体”区分说的多重面相
明治日本法政学界派系林立,观点纷歧,即使同是基于君主主权说区分“国体”“政体”,大同之下的小异仍是不少。岸崎昌、中村孝著《国法学》的“国体”“政体”区分说就与穗积八束等人不尽一致,东京大学法科学生章宗祥曾翻译此书,1902年3月由译书汇编社收入《政法丛书》出版。
岸崎昌、中村孝定义统治权说:“国家有独立主权,依之而统治,是曰统治权”,其性质一言以蔽之即“在一国疆土内唯一无限之权力”[注][日]岸崎昌、中村孝著,章宗祥译:《国法学》,东京:译书汇编社,1902年再版,第19、20,22,23,23、24,24,24,26页。。统治权、主权内涵基本一致。二人进而区别“国体”“政体”,认为“国家之组织由主权之所存而异,是谓国体之区别。国体之区别与政体之区别不同。政体者,由统治之形式而定,主权之所存,非所当问也”④[日]岸崎昌、中村孝著,章宗祥译:《国法学》,东京:译书汇编社,1902年再版,第19、20,22,23,23、24,24,24,26页。。“国体”分为主权在君、在民、在君与民的君主国体、民主国体和君民同治国体。亦可概括为君主国体与共和国体,共和国体指“主权之全部或一部存乎人民,合民主与君民同治而为一类”⑤[日]岸崎昌、中村孝著,章宗祥译:《国法学》,东京:译书汇编社,1902年再版,第19、20,22,23,23、24,24,24,26页。。作者从后说。
岸崎昌、中村孝强调日本是不同于欧洲国家的君主国体,其形成与“皇位与统治权合为一体”的特殊国情相关。简言之,欧洲国家“本乎主权在团体而君主治团体之观念组织而成”,都是共和国体,即使有帝王,也不过是政治上的尊号,为国家机关而已⑥[日]岸崎昌、中村孝著,章宗祥译:《国法学》,东京:译书汇编社,1902年再版,第19、20,22,23,23、24,24,24,26页。。“日本国体异是,国家组织之法,基于家族制度。”全国人统一于同一始祖的威力之下,皇统为国民先祖的代表。“故皇位之于国民,代祖先而统治之也。皇位与统治权合为一体,此日本国体之特质也。故同曰君主,全与欧洲不同。君主者,非机关之谓,而统治之主体也。欧洲诸国及其他各国,皆共和国体,纯然之君主国体,地球上惟日本一国而已。”章宗祥在此句之后附加按语说:“此说不过一家之言,日本学者反对者甚多,读者不可执一而论也。”⑦[日]岸崎昌、中村孝著,章宗祥译:《国法学》,东京:译书汇编社,1902年再版,第19、20,22,23,23、24,24,24,26页。
至于“政体”,乃“统治方法之名”。欧洲国家“主权常在团体,而国家为统治之主体”,皆共和国体,故“不言国体之区别”,只讲“政体”分类。但国法学通行世界而不限于欧洲,“欧洲国体之外,别有所谓君主国体者,于是国体之区别与政体之区别不得不分言之矣”⑧[日]岸崎昌、中村孝著,章宗祥译:《国法学》,东京:译书汇编社,1902年再版,第19、20,22,23,23、24,24,24,26页。。所以,作者说:“辨国体之异同者,自日本始。”⑨[日]岸崎昌、中村孝著,章宗祥译:《国法学》,东京:译书汇编社,1902年再版,第19、20,22,23,23、24,24,24,26页。岸崎昌、中村孝采用格立司的分类法,以“统辖国家施政之机关”——国家元首的组织及其地位为标准区分“政体”。细言之,“政体”大别为元首由一人组成的独任政体和由数人组成的合议政体,它们又分别包括元首无责任的君主政体和元首有责任的共和政体,组合后衍生出独任君主、独任共和、合议君主、合议共和四种“政体”。独任君主政体、合议君主政体又分别有元首与其他国家机关分其权限而统治的立宪政体和不分权限的专制政体两种情况,由此可以细分出专制独任君主、立宪独任君主、专制合议君主、立宪合议君主四种“政体”。值得注意的是,格立司所说的“政体”原本未必是与因主权所在而异的“国体”相对的概念。
从表面上看,“政体区别之名目往往与国体相符合。然国体自国体,政体自政体,二者各有独立之观念也”。“国体”同而“政体”异,“政体”同而“国体”异比比皆是。如日本、英国、普鲁士三国以君主一人为国家元首,是君主政体,但英、普“统治之主体在国家”,是共和国体;至于日本,天皇同时是国家元首和统治的主体,为“君主国体而君主政体”[注][日]岸崎昌、中村孝著,章宗祥译:《国法学》,第25—26,189页。。
在《国法学》中,“国体”又可在广义上指称单一国家、联合国家等“国家形体”。卷4《论国家之联合》写道:“世界国家之形体,非仅单一国家,如德意志帝国、北美合众国等,与英国、法国、日本等单一国家不同,国家有与他国家联合而成者,是谓国家之联合。欲知世界各国之国体,国家联合之法不可不研究也。”②[日]岸崎昌、中村孝著,章宗祥译:《国法学》,第25—26,189页。
随着日本法政论著源源不断的译介,以君主主权论为基础的“国体”“政体”区分说因人而异的复杂情形有增无减。1903年,日本早稻田大学政治经济科留学生林棨将菊池学而的《宪政论》译成汉文,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1916年重刊时已至第10版,流行程度可见一斑。
菊池学而定义主权为“有最高惟一之位置,而为团体之主力者”[注][日]菊池学而著,林棨译:《宪政论》,上海:商务印书馆,1916年第10版,第9,28,14,14—15,30、41,45,36、46,36、37—38,40页。,他也经常混用主权、统治权。关于统治权的主体(统治权所在),主要有君主主权说、人民主权说和国家主权说。菊池学而批评人民主权说,认为人人有主权则无服从权力者,“国家必不能一日存”。他认可君主主权说,但此说不适用于共和国体。至于国家主权说,此说认为国家“以己之意志,自事实上国家一变而为法律上国家”,遂有人格,成为法人[注]所谓人格指具备权利义务能力的主体,除奴隶等外,一般自然人均有人格,法人则是“自然人以外之人格者也”。谭传恺:《法学通论》,《湖南法政学堂讲义》,出版时间不详,第20—21页。,因而是统治权主体⑤[日]菊池学而著,林棨译:《宪政论》,上海:商务印书馆,1916年第10版,第9,28,14,14—15,30、41,45,36、46,36、37—38,40页。。菊池学而指出:“谓国家可以为法人则可,谓国家必不得不为法人则不可。”⑥[日]菊池学而著,林棨译:《宪政论》,上海:商务印书馆,1916年第10版,第9,28,14,14—15,30、41,45,36、46,36、37—38,40页。且国家法人说与日本国情不相吻合。日本“乃家族制度之发达者也”,皇室臣民同其祖先,天皇是国民的家长、族长,“国家主权与一家之家长权,其性质固未尝或异,惟观念之大小而已”。故“天皇之有主权,固事之无可争者也”。他批评日本倡导国家主权说的学者“徒艳羡外国宪法所宣言,学说所论述,迳欲采用诸吾国,学步效颦,唯恐不肖,亦见其惑矣”⑦[日]菊池学而著,林棨译:《宪政论》,上海:商务印书馆,1916年第10版,第9,28,14,14—15,30、41,45,36、46,36、37—38,40页。。
说明主权所在因国而异后,菊池学而区分“国体”为“主权属乎特定之一人”的君主国体和主权属于由多数人所构成的“无形之团体”的共和国体⑧[日]菊池学而著,林棨译:《宪政论》,上海:商务印书馆,1916年第10版,第9,28,14,14—15,30、41,45,36、46,36、37—38,40页。。君主国体须以主权归于一人,“今日欧洲诸国之君主,其名则君主也,然而非主权者,团体主权之一官而已”,故并非君主国体⑨[日]菊池学而著,林棨译:《宪政论》,上海:商务印书馆,1916年第10版,第9,28,14,14—15,30、41,45,36、46,36、37—38,40页。。“政体”因“主权者统治一国之方法”,亦即统治权作用方式的不同而有专制、立宪之别⑩[日]菊池学而著,林棨译:《宪政论》,上海:商务印书馆,1916年第10版,第9,28,14,14—15,30、41,45,36、46,36、37—38,40页。。“国体”有“悠久存续之性质”,“政体”“非历久而永存,世之愈进,则其变愈赜”。日本明治维新“能明国体、政体之区别”,故仅变专制为立宪,不变更君主国体。菊池学而批评一些学者“徒见欧米诸国元首之权弱,而国会之权强,动唱君主之无责任,否则思大国会议决之效力,是皆不明国体、政体之别之过也。国体、政体论与主权论有密切之关系,问统治权所在则国体论也,别统治权行使之形式则政体论也”[日]菊池学而著,林棨译:《宪政论》,上海:商务印书馆,1916年第10版,第9,28,14,14—15,30、41,45,36、46,36、37—38,40页。。言下之意,在立宪政体下,君主权力、地位不容减损。
菊池学而更严格限定“国体”的指称范畴。他认为单纯国家、复杂国家这些国家形态“不可以为国体之类别也。为国体论者,察一国主权之所在而已。国家之形态,置之可也。”[日]菊池学而著,林棨译:《宪政论》,上海:商务印书馆,1916年第10版,第9,28,14,14—15,30、41,45,36、46,36、37—38,40页。
其实,“国体”本就可宽泛地指称各种“国家形体”。东京大学讲师市村光惠在《宪法要论》中说:“国体者,国家之种类也,故异其区别之标准,应其各种之分类。”市村光惠也主张根据“一国内统治权在何人之手”,即“主权者”的不同区别“国体”为君主、贵族、民主三种。“政体”则是“统治权行使之形式,故与国体同,依种种之标准得为区别”,他以统治权的作用有无“独立意思机关”的限制为标准区分“政体”为专制、立宪。“政体之区别,基于国权之行用,故与国体之区别不矛盾。”[注][日]市村光惠著,[日]井上密评,李维翰译,黄宗麟校:《宪法要论》,普及书局,1906年,第42、44—45,29、30页。市村光惠混用统治权、国权、主权、最高权这几个概念。
虽然市村光惠与穗积八束都主张君主是统治权主体,但个别观点仍略有不同。穗积八束曾说“国家者,主权,即统治权之主体也”,又说“天皇为主权之主体”,认为“君主即国家”。市村光惠指出:“以国家解作统治权之主体,则君主者,国家之机关也。君主为统治之主体,则国家非统治之主体也。国家与君主二个统治主体同时并存,则矛盾之说也。故其断案,君主即国家,亦隔于矛盾之说。”②[日]市村光惠著,[日]井上密评,李维翰译,黄宗麟校:《宪法要论》,普及书局,1906年,第42、44—45,29、30页。他批评穗积八束说国家是统治权主体的用意是避免由此引发君主是国家机关的联想,从而坚定天皇是统治权主体的观念。
另一日本学者清水澄也反对国家是统治权主体,君主是国家机关的观点,其论著在清末流传甚广。清水澄强调国家是“权力之结果”,并非统治权主体。基于君主是统治权主体的观念,他反对把君主当作国家最高机关[注][日]清水澄著,卢弼、黄炳言译:《宪法》,政治经济社,1906年第3版,第5、7、46页。。在他看来:“君主为统治权之主体,统治权之主体与机关,不能一身而并兼之,故君主不得称为直接机关也。”[注][日]清水澄讲述,俞亮公笔译:《宪法》,《法政速成科讲义录》第44号,1907年5月22日,第145页。与此关联,清水澄区分“国体”“政体”说:“国体者视其权力之所在而定,政体者视其施政之方法而异。”前者有君主国、民主国之别,后者分为专制、立宪[注][日]清水澄:《宪法》,[日]户水宽人等著,何燏时等译述:《法制经济通论》,上海:商务印书馆,1909年第3版,第1页。。
结 语
与欧美纷繁复杂的国家类型知识相对应,明治时期日本法政论著中的“国体”“政体”并非迥殊,相当程度上可以混用。“国体”“政体”区分说的衍生与流行,除直接受西方的国家学说影响外,更根本的原因是《明治宪法》颁布后,穗积八束等尊崇天皇、君权的学者极力主张划分“国体”“政体”为主权、统治权所在及其行使形式这两个截然不同的范畴,从而论证日本实行三权分立的立宪政体后仍是天皇总揽统治权的君主国体,即不变“国体”变“政体”。“欧洲于国体、政体无所区别”“辨国体之异同者,自日本始”一类说法,一方面反映“国体”“政体”区分说在欧美学界可能不是主流,一方面说明这种学说的兴起深受日本特殊的国情影响,是为了强调日本尊崇天皇的历史与政治文化。由于君主主权论下的“国体”“政体”区分说本身只是一种法政理论,持相近观念的学者在“国体”“政体”具体有哪些类型,是否严格限定“国体”指称范畴以及国家、君主能否同时是统治权主体等问题上其实多有分歧。随着这些多元的“国体”“政体”区分说陆续传入且在译介的过程中频繁出现随意调换概念和杂糅不同说法等情况,“国体”“政体”异同的困惑开始在中国产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