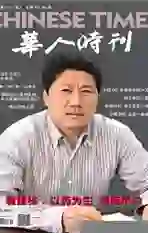从汪曾祺的一页手稿说起
2018-01-18金实秋
金实秋


不久前,看到了刊登于2017年第10期《雨花》封二上的一页手稿,是汪曾祺先生《故乡的食物》中第一篇《炒米和焦屑》中的第一页。稿纸上留下了汪先生秀逸的字迹,也留下了编辑工作的印痕。看了这一页只有400字的《人民文学》出版社稿纸,不禁使我想起与汪先生手稿相关的一些事来。
手稿的开头是这样一段话:“小时读《板桥家书》,‘天寒岁暮,穷亲戚朋友到门,先泡一大碗炒米送手中,佐以酱姜一小碟,最是□□□□(此四字失记,待查)之具,觉得很亲切。”文章发表于1986年第5期《雨花》,不知编辑出于何因删去了括号,也删去了括号中的六个字。其时,高邮的一位文学青年王树兴读了这篇文章后,特意查找了郑板桥的原文是“暖老温贫”四字。这四个字为什么要“□□□□”呢?王树兴百思不解,以为或许有其深意。于是,便致信汪先生求教。不久,便收到了汪曾祺的回函。信中云:
王树兴同志:
感谢你的来信。关于炒米的四个字,我确实是失忆了,并非有意写不出,有什么深意。这篇散文将来如果收集子时,当根据你所提供的材料改正。你对我的文章如此认真对待,很使我感动。……
汪先生是个认真的人。此后收入集子里的《炒米和焦屑》都有了“暖老温贫”这四个字。不仅如此,汪先生在《对读者的感谢》一文中特地提及此事。此文发表于1992年10月25日的《文汇报》,距王树兴的信己七、八年之久矣,但汪老仍记住这件事。我与王树兴是同乡,也是文友,早就知道了这件事。如今,王树兴己成为一名颇有成果的作家,他说:“此事过去了好多年,给我的印象仍然非常深刻。这是一个文学大家,对一个文学青年的认真,对自己作品的认真。我对自己在为文方面要求‘认真二字,大概就是从汪曾祺给我的这封信开始的。”(见王树兴《汪曾祺给我的一封信》,刊王树兴编辑《高邮人写汪曾祺》一书,广陵书社2017年版)
所以说,看到此手搞我才知道了其中的原委,也明白了这四个字的空白及括号、括号里的字还是不删改为宜。在徐强所著的《人间送小温———汪曾祺年谱》中,也说了一处汪曾祺文章留白的事。1981年是裘盛戎逝世十周年,汪曾祺写了《名优之死———纪念裘盛戎》寄托缅怀之情,文中第二段第一句是“再有些天就是盛戎的十周年忌辰了”。汪先生生前此文未公開发表,作者手稿原文上于“再有”二字后没有“些”这个字,而是空着格子的。显然,这是汪先生当时未及标明具体日期而暂留空白的。《汪曾祺全集》出版时收录了汪老的这篇佚文,并将空格处填上了“些”。一般而言,如此一改似无不可。但我以为,此处还是保留空白为宜,在文末另添上编者的说明即可。这样既尽量保持了文稿的原貌,也使读者体会到作者的认真与编者之严谨。
正如王树兴所言,汪曾祺对自己的作品是认真的。而由于认真,有时不免会对那些编辑的鲁莽乱改颇有意见。
何立伟说过一件事。1986年,汪曾祺去湖南,何立伟去看他。“这位看去极平和的老人,说到一桩事时,忽然表现出了近乎孩子似的生气。他说:他们乱改文章,简直不像话。东北的某一杂志,把他的一篇小说里很多话改了,叫人啼笑皆非。比如,写一个木匠,早上蹲在门口吃完饭,末了,‘就走进了他的工作。编辑大概觉得,咦?工作怎么走进去呢?遂改成‘就走进了他的工作室。旧社会一个穷木匠,哪里来的‘工作室呢?一字之差,境界殊异,可谓化神奇为腐朽一例也。汪先生说完又揺摇头,一笑说:‘算了,算了。”汪先生说的这篇小说是《故人往事》中的第一篇《戴车匠》,后来出的相关集子中已经改正了。
汪先生还说过一件事。也是在1986年,他写了一篇《谈读杂书》,文中原稿中其文是“我从法布尔的书里知道知了原来是个聋子,实在非常高兴……。发表出来,却变成了‘我从法布尔的书里知道他原来是个聋子……这就成了法布尔是个聋子了。”汪先生接着说:“法布尔并不聋。而且如果他是个聋子,我又有什么可以高兴的呢?阅稿的编辑可能不知道知了即是蝉,觉得‘知道知了读起来很拗口,就提笔改了。这个‘他字加得实在有点鲁莽。“《谈读杂书》发表于当年的《新民晚报》上,该报乃是一家颇有影响的大报,“有点鲁莽”的编辑行为极少,汪先生算是碰上了。
汪先生的名作《受戒》也碰上过类似的情况。1981年10月,汪老应邀回家乡高邮。在高邮师范学校,他作了《文学的语言及其它》的讲座,讲座中说他的一篇小说中写到高邮妇女的头发用了“滑滴滴”一词,结果发表时被改成“滑溜溜”了。当时还在高邮师范任教的诗评家叶橹先生回忆道:“说到这里时,他的表情是一种无奈的幽黙,并加了一句:‘这么一改,成了什么味儿了?”汪先生说的小说,就是发表在《北京文学》1980年第10期上的《受戒》。后来出版的《汪曾祺全集》,“滑溜溜”也已订正为“滑滴滴”了。
我们再回到《炒米与焦屑》的这一页手稿上来。这仅有400字的手稿上,编辑还有两处修改:一是删去了“的溜圆的”四字,二是删了“自己”二字上的引号。我认为,这二处修改亦可谓是鲁莽之举,如前之所言“滑溜溜”之鲁莽差不多。“滑滴滴”与“滑溜溜”虽可说是近义词,但“滑溜溜”是汪老家乡一带的口语,多少带有一点欣赏、褒扬的意味,而“滑溜溜”就没有这个成分了。改成“滑溜溜”,似无大碍,但这就属于“普通话”的范畴了,丢失了地域语言的味道与妙趣了。
汪先生曾说过一句很睿智、很到位的话,他说:“一个作家‘只会说‘普通话,干什么都无碍,只是到了文学这里,就会语言无味、语境不美。”“自己”二字,也是苏北一带的话,家里,当然是“自已”的家里;这个“自己”往往带有强调的成分,是强化语气的,是自诩自信的一种表述。那“溜圆”也是强调炒米团之圆的,带有赞赏的意味。删去了“溜圆”二字和自己二字上的引号,行文似乎简化顺当了,却不免多少有点淡化了汪曾祺的味儿,弱化了文学上的语境。
上面说了那么多汪先生对编辑的意见,似有片面之嫌。其实,汪先生对编辑是相当尊重的,只是对那些编辑的鲁莽乱改不满而已。即如《受戒》吧。汪老的哲嗣汪朗说:“如果没有《北京文艺》,如果不是李清泉拍板,《受戒》在当时要发表,难。……李清泉和爸爸不熟,只是相互知道名字而已,但是他毫无顾忌亲笔签发了《受戒》,爸爸因此对他一直很敬重。”1981年第1期的《人民文学》发表了他的《晚饭后的故事》,发表前,他至少与编辑涂光群沟通过二次,在给涂光群的第二封信的末尾处写道:“今年北京奇热,伏案写一短信,即已汗滴纸上。你们终日看稿,其苦可知矣。”1988年,浙江文艺出版社编辑出版了他的文论集《晚翠文谈》。时为该社的编辑、终审徐正纶说:“我向他提出的意见和建议,他也全部接受”;汪老几次致函徐正纶,说“深为你对编辑工作的认真、细致而感动,谨先表示我的谢意”,“承细心勘校,甚谢!”1991年,应徐正纶之嘱,还手书一帧自已写的七绝相赠。至今,徐正纶还珍藏着汪老给他的九封信与那幅汪老的墨宝。
平心而论,汪先生对编辑也是理解的,也深知编辑的责任与辛苦。早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初,汪先生也曾在编辑岗位上干过,在《说说唱唱》及《民间文学》度过了六年左右的编辑生涯。汪先生的挚友林斤澜、邓友梅曾撰文描述过当时汪曾祺的工作状况。“冬日,羊羔长袍长及脚面,小步踢踏,背微驼,一杯绿茶,一支纸烟。年方三十,不够遗老足够遗少。整日看稿却是不遗余力。”“他全部精力都奉献给编辑工作了。那时期《说说唱唱》和《民间文学》的原稿上,每一篇都能看到他的劳动痕迹。……来稿每天以百件计,可用量不到百分之一,壁橱里废稿如一座小山。……新收到的来稿还处理不完,也没谁花功夫到那里钻探,可汪曾祺竟从这里沙里淘金般淘出篇名著来。……那篇稿子涂抹很乱,满纸错别字外加自造怪字如天书一般。……可汪曾祺以超常的毅力读完了后,认为思想丶艺术都大有新意!是篇不可多得的佳作!花工夫改了些勉强他能辨认的错别字,把它呈到了主编赵树理面前。”于是,这篇小说才得以发表,一鸣惊人。这篇小说是《活人塘》,作者是陈登科。邓友梅文中还有一个细节尤为感人。《活人塘》“原稿中写了好几个‘马字,下边都少四个点(即简化字那一横),前言后语的情节也都跟‘马不相干,汪曾祺面对这个字抽了半盒烟,最后也没认出来。幸遇高人康濯,猜着念‘趴,理由是‘马看不见四条腿,那不是趴下了吗?为慎重其见特别去信问陈登科,他回信证明就是念‘趴,并为编辑能认出他创造的字而欣慰!”邓友梅感叹道:“整篇中汪曾祺碰上的这类难题有多少?他从来没跟人谈过。”
看来,汪先生是把自已对编辑工作的态度和精神去要求同行了。我以为这是对的,是应当提倡和践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