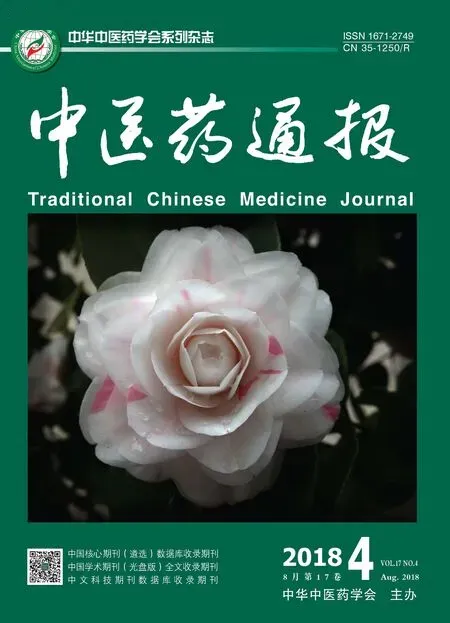基于李东垣阴火理论探讨小儿疳证诊治
2018-01-18陈四文
● 张 萍 陈四文
疳证作为病名最早记载于《颅囟经》,后在《诸病源候论》《太平圣惠方》等著作中也有记载。到了宋代,著名的儿科学家钱乙继承了《颅囟经》及诸家学说,不但编著了儿科专书,而且对疳证另列专章[1],认为“疳皆脾胃病,亡津液之所作也”,主张扶脾阳、养胃阴之法,故以白术散治疳之初疾,益黄散疗疳之久疾[2],尔后医家多从此说。近来笔者研习李东垣阴火理论,发觉其论高屋建瓴,甚切实用,可为小儿疳证的诊治提供新的思路,现探讨如下。
1 从阴火论疳证的理论依据
疳证多因喂养不当、乳食不节或其它疾病影响,导致脾胃受损,气津耗伤,机体失养,而见形体羸瘦,精神萎靡,毛发干枯,面黄纳少,脘腹膨胀,甚则青筋暴露等临床症状。宋代·钱乙在《小儿药证直诀·诸疳》中首先提出“疳皆脾胃病,亡津液之所作也”“脾胃虚衰,四肢不举,诸邪遂生,鲜不瘦而成疳矣”。清代·陈复正在《幼幼集成·诸疳证治》中亦指出:“有因幼少乳食,肠胃未坚,食物太早,耗伤真气而成者;有因甘肥肆进,饮食过餐,积滞日久,面黄肌削而成者;有因乳母寒热不调,或喜怒房劳之后乳哺而成者。有二三岁后,谷肉果菜恣其饮啖,因而停滞中焦,食久成积,积久成疳。”可见幼儿脾胃成而未全,全而未壮,若喂养不当,饮食失节,则必损伤脾胃,导致脾胃虚弱,运化失职,从而产生挑食、厌食,甚至拒食等症状。若此时强迫幼儿多进食,则易生积滞,如此日久,则成疳证[3]。
李东垣的阴火理论,是对《内经》相关理论深化和临床发挥后的产物,李东垣认为阴火的产生乃饮食、劳倦、情志等因素损伤脾胃元气后引起,在其《脾胃论·饮食劳倦所伤始为热中论》中即明确提出:“若饮食失节,寒温不适,则脾胃乃伤。喜、怒、忧、恐,损耗元气。既脾胃气衰,元气不足,而心火独盛。心火者,阴火也,起于下焦,其系系于心,心不主令,相火代之。”“脾胃气虚,则下流于肾,阴火得以乘其土位。”可见阴火的产生源于脾胃虚弱,元气不足,气机升降失常,即《内经》所云“上焦不行,下脘不通”,阴火的本质乃心肾君相之火,不安其用,进而乘犯他脏,侵害机体[4]。李东垣在《兰室秘藏·劳倦所伤》中进一步论曰:“脾胃气虚,不能升浮,为阴火伤其升发之气,荣血大亏,荣气不营,阴火炽盛,是血中浮火日渐煎熬。”以上论述说明了阴火与小儿疳证均有脾胃损伤、气营不足这一共同的病变基础,故可从阴火论治疳证。
2 从阴火论疳证的病变机理
李东垣认为因饮食、劳倦等因素损伤脾胃,影响了脾胃的纳化功能,则元气乃伤,元气又名真气,非胃气不能滋也,若脾胃之气损伤,则元气亦不能充,而诸病之所由生。又认为元气在生理上是主升发的,而阴火是主降藏的,元气升发则和煦心肺,下济肝肾;阴火降藏则温养肾肝,上滋心肺。倘若脾胃元气不足,清阳下陷,谷气不升,不足以上煦心肺,迫使肝肾阴火上乘阳位。火与元气不两立,阴火越升,元气越陷,且壮火食气,阴火上冲,又可耗伤元气,如此恶性循环则产生内伤热中的病变[5]。正如李东垣《脾胃论·饮食劳倦所伤始为热中论》所谓:“火与元气不两立,一胜则一负。……盖阴火上冲,则气高而喘,身烦热,为头痛,为渴,而脉洪大……皆脾胃之气不足所致也。”可见,脾胃虚弱,元气不足,清阳下陷,导致阴火上乘是内伤热中病产生的主要病理机制[6]。
对于疳证,钱乙论治最详,认为:“乳食不消,伏在腹中,乍凉乍热,饮水或喘嗽,与潮热相类,不早治,必成疳……令儿不食,致脾胃虚而发热……益不食,脾胃虚衰,四肢不举,诸邪遂生,鲜不瘦而成疳矣。”说明了喂养不当或饮食不节等损伤脾胃,致其运化失常,壅聚中焦,形成积滞,日久化热,纳化失权,对乳食精微,无从吸收布散,致脏腑肌肉、四肢百骸失于濡养,形体日渐羸瘦,气血虚衰,营养不良,诸脏皆损,则成疳证[1]。《诸病源候论》也明确指出:“蒸盛过伤,内则变为疳,食人五脏。”可见,疳证也属于内伤热中病之一,盖饮食劳倦,既伤脾胃,则元气不足,而阴火独盛。壮火食气,则可见神疲乏力、纳谷呆钝等症状;火盛伤阴,营血不足,无以奉养周身,则可见面黄肌瘦、毛发干枯等症状。对于这些内伤热中之病,李东垣认为“惟当以甘温之剂,补其中升其阳,甘寒以泻其火则愈。”
3 从阴火论疳证的治法方药
李东垣认为饮食失节及劳役形质等损伤脾胃元气,阴火乘于坤土之中,致谷气、营气、清气、胃气、元气不得上升滋于五脏六腑,是内伤百病产生的根源,所以强调益气、升阳、泻火是治疗脾胃内伤病的基本方法[6]。《脾胃论》第一方“补脾胃泻阴火升阳汤”便全面地概括了李东垣的这一治疗思想。方中人参、黄芪、白术、甘草以益气健脾,培补元气;柴胡、升麻、羌活升阳举陷,以利枢机、复运化;黄芩、黄连、石膏以泻阴火,顾护元气。若阴火灼伤真阴,东垣谓“少加黄柏以救肾水,能泻阴中之伏火。如烦犹不止,少加生地黄补肾水,水旺而心火自降。”可见益气、升阳与泻火是相辅相成的,对于饮食劳倦,损伤脾胃,内生火邪,致生百疾的治疗尤为适宜,目前仍为临床所常用。
需要说明的是,诸多因素均可致脾虚气陷,而其除了产生阴火外,还会并发湿浊、热毒、痰饮、瘀血等内伤之邪,乘虚侵袭土位,从而产生种种病变,兼夹血瘀、湿热之候[7]。所以治疗内伤杂病还需根据所乘入的各种病邪产生的兼夹症候不同而作随证加减。如阳气郁陷,以气虚为主者,不必加升阳风药,待脾气足,则脾阳自可升发;火不盛者,不必加清火药,待脾气升,元气充,则阴火自熄;若火势剧则可随证择加清火药;若用大剂补气药,可加少量清火药,既制补气药之温,又防止补气有余生火。可见李东垣深旨脾胃调理之法,提示后人不可执于成方,要师其理法,辨证用药。
4 结语
疳证的治疗多以扶脾阳、养胃阴之法为主,但李东垣阴火理论告诫我们,对于内伤虚损之疾,不可一味拘泥于补,因过用温补,不但暗耗阴血,且易闭门流寇,加剧病情。亦不可过于攻伐,因幼儿乃稚阴稚阳之体,染疾多虚实夹杂,若攻伐太过,则必耗夺元气,变生它疾。故临证审病,理应谨守病机,不可胶柱鼓瑟而犯虚虚实实之戒。总之,李东垣在《内经》《伤寒论》以及张元素脏腑辨证等基础上,形成了独树一帜的内伤脾胃学说,并归纳了内伤热中病以脾胃虚弱,元气不足,清阳下陷,阴火上乘为主要的病因病机,以益气、升阳、泻火为主要的治疗法则,在论治内伤杂病方面确有其独到之处,为疳证的治疗提供了新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