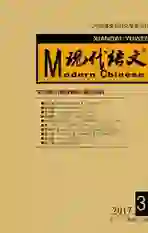题元理论视角下的动词“晕”与合成词“动词+晕”
2018-01-17陈洁娜
摘 要:汉语动词“晕”在与其它动词合并之后形成特殊的论元结构及题元角色,需要引起足够重视。文章在解释题元理论相关原理与概念的基础之上,结合“晕”的语言事实和语义特征,分析动词“晕”和合成词“动词+晕”的论元结构及其句法特征,期以更好地理解汉语的句子結构与语义解释之间存在的密切关系。
关键词:动词+晕 题元理论 论元结构 句法特征
一、引言
近几十年以来,“动词+动词”结构形式成为了广大汉语学者关注的焦点。不同语言学派的学者采取迥异的视角对此种复合结构展开了大量分析与探讨。施春宏(2003)根据配价理论对“动词+动词”结构形式的配价层级及歧价现象开展了深入的调查研究[1]。沈家煊(2004)采取了认知语言学的概念结构,对“动词+动词”此类动结式的合理解释提供了预测方式[2]。乔姆斯基转换生成语法在汉语语法的研究方面具有显著的影响力,汉语界的学者们通过学习借鉴乔姆斯基开创的研究理论与方法,着眼于汉语语言系统中的复杂问题,期以寻求合理有效的解释。黄龙、杨成虎(2012)借用最简方案中的轻动词理论阐述了“动词+动词”此类结构形式的语法特征[3]。熊仲儒、刘丽萍(2006)在生成语法的框架中对动结式的论元实现形式进行了一番剖析[4]。本文立足于乔姆斯基生成语法的框架,透过题元理论着眼于现实生活中“晕”的语言事实,深入剖析单词素动词“晕”与合成词“动词+晕”这两者的论元结构及其句法特征,旨在使读者对动词“晕”及“动词+动词”结构的句法语义特征有一个较为明晰的解读。
二、相关理论概念阐释
题元理论作为生成语法的一部分,在生成句法学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下面将对题元理论及论元结构和论旨角色的相关概念作简单介绍。
(一)题元理论
语言学家最早是从形式逻辑谓词演算中借来“论元”(argument)的表达。在逻辑学中,命题的意义通过谓词及其论元这两个要素来体现,也就是说任何一个命题都可以视作谓词与论元的相互关系,Chomsky将逻辑学中的“论元”称为个体词(individual)[5]。一般而言,谓词主要由动词性成分充当,通常情况下在句子中担任谓语的角色。而论元往往由名词性成分充当,多数时候在句子中充当主语、宾语、介词宾语和部分表语的成分。具体来说,仅仅携带一个论元的谓词称作一元谓词(one-place predicate),以此类推,携带两个论元的谓词称作二元谓词(two-place predicate)。
题元理论(或称论元理论)的研究最早可以追溯到菲尔默(C.J Fillmore)的格语法理论。菲尔默(1968)认为题元理论中使用了“深层格”[6]。他所创立的格理论直至目前都存在争议,不过大家普遍认为所谓的论元角色(又称题元角色或语义角色)有下述几项:施事(Agent/Actor)、述题(Theme)、感受者(Experiencer)、受益者(Benefactive/Benificiary)、目标(Goal)、来源(Source)、方位(Location)、受事或当事(Patient)。
(二)论元结构与论旨角色
一个词的论元结构指的是该词项所能拥有的已标有论旨角色名称的论元,通常以组的形式出现,一组论元中的数目至少大于等于一。袁毓林(2002)认为论元结构事实上可以被视为论旨角色关系(或者称作题元角色关系)的同义词,论元结构中所包含的内容是一系列论旨角色各不相同的集合体[7]。通常来说,动词的主目结构规定了动词要求主目数量的最低值,一个合乎语法的句子必须存在足够的主目语才能符合主目结构的要求。而动词的论元结构不仅要求动词的主目语达到规定数量,还必须具有地位合法性即能够胜任动词指派的题元角色。
目前来看,汉语动词的论元结构的基本内容包括论元属性、论旨属性、语法特征等。其中,论元属性可以用来确定每一个动词所能支配的必用论元与可用论元的数量。论旨属性用来标明所存在的论元在语义层面的功能,也就是论旨角色。语法特征用来描写这些论元在动态和静态时呈现的不用语义特征。
三、“晕”的论元结构和句法特征
单词素动词“晕”的论元结构在与其它动词合并形成合成词结构,两者的论元结构及论元角色发生变化。下面结合动词“晕”的例句,从“晕”的语言使用入手,分别探究单个动词“晕”和合成词“动词+哭”的论元结构和句法特征。
(一)单词素动词“晕”的论元结构和句法特征
在传统语法的范畴内,单词素动词“晕”往往被认为是不及物动词,而不及物动词后面不携带宾语,所以被视为一元谓词,这样一来,“晕”的论元有且只有一个。在不及物动词中,“死、来、沉、哭、笑”这类动词所携带的唯一论元均处于主语位置,表达形式即“NP+V”,而它们往往不能出现于“V+NP”结构之中,比如“小明晕了”符合汉语语法需要,但“晕了小明”则不符合汉语语法需要。一旦不及物动词“晕”被视作一元谓词,这也就意味着动词“晕”后面必须是零受事,即不允许宾语的存在。那么,为了满足单词素动词“晕”的最低主目语数量,就只能在“晕”的前面配上主语。该主语应该承担一定的论元角色,也相当于“述题角色”。因此,单词素动词“晕”组成的句子之后承担了“XXX因身体不适或受到强烈的精神刺激而昏厥”的语义特征。根据上述语义特征,可以发现单词素动词“晕”对充当其主目语的名词有严格的要求。该类名词应该是[+拥有生命的]或[+带有情感的]。例如:
(1)老太太的丈夫晕了。
(2)老虎晕了。
上述事例中,例(1)中“老太太的丈夫”属于人类,拥有至高无上的生命和丰富的情感,既满足[+拥有生命的]的属性,又满足[+带有情感的]的属性,当其由于身体不适或受到过强的精神刺激而昏厥的时候,我们可以像上文那样表达“老太太的丈夫晕了”这个句子,此时“老太太的丈夫”在句中被分派的是“述题角色”。例(2)老虎是有生命的动物,具有[+拥有生命的]的属性,符合动词“晕”所要求的主目语特征。由此可见,单词素动词“晕”不能与不具有生命体征的事物搭配组成句子,由于“苹果”“树苗”“桌子”既不满足[+拥有生命的]的属性,又不满足[+带有情感的]的属性,所以下述句子一般不属于可接受的汉语表达:endprint
(3)苹果晕了。
(4)树苗晕了。
(5)桌子晕了。
由于不及物动词“晕”所要求的唯一主目语在深层结构中占据主语位置,在单词素动词“晕”之前应该只出现一个论元,虽然“张三、老虎、学生”均满足[+拥有生命的]或[+带有情感的]的语义特征,但是单词素动词“晕”之后不能出现任何論元。由此,下述句子将被视作不符合汉语语法:
(6)张三晕了李四。
(7)老虎晕了老鼠。
(8)学生晕了老师。
(二)合成词“动词+晕”的论元结构和句法特征
“动词+晕”的句法结构和语义关系词一般被视为一个复合词。这类复合词能够形成一个复合结构,表示一个复合事件,即致使事件。复合事件是由使因事件和使果事件这两个子事件通过语义整合之后所形成的主事件,这两个子事件分别由构成动结式的述语动词和补语动词来表达。在致使结构中,我们把致使关系的引发者即致使者称作致事,将致使关系的承受者即受使者称作役事。
日常生活中,“动词+晕”这种语言现象普遍存在,一般而言属于动补结构,是动结合词的一种表现形式。该类合成词语往往有“V1+V2”或“V1+Adj”这两大类。“动词+晕”归属于前一类,即“V1+V2”类,前者“V1”表示动作,后者“V2”说明“V1”造成的结果,如“饿晕”“气晕”“哭晕”“打晕”“撞晕”“热晕”“吓晕”等。根据结果补语V2的语义与功能差异,Ross(1967)将汉语中的动结合词列为三大类别:表述型、方位型和成就型[8]。这样看来,“动词+晕”当属于第三类,即成就型合成词。徐菊(2007)将这里所说的成就型合成词看作 “V2”由“到、死、住、过、掉、动”等成就型动词充当,表示取得目标的状态[9]。根据上述定义,成就型合成词中的自由语素可以充当V2的角色。当汉语动词“晕”界定为自由语素之时,那么 “动词+晕”就被视为是一个复合动词,而该复合动词包括两个自由语素。这样一来,合成词的论元结构便成为了分析的重点。我们认为“动词+晕”可以大致分为两类:“行为动词+晕”和“心理动词+晕”。为了表述方便,暂且把这两类都用“动词+晕”代替,下文中将不再另作说明。“动词+晕”中的“动词”和“晕”都是自由语素,“动词+晕”的论元结构与“动词”和“晕”各自的论元结构关系十分密切。举例如下:
(9)武松打晕了老虎。
(10)持续的高温天气热晕了户外作业的电工。
(11)小偷用砖块砸晕了那个男人。
(12)小明的空白试卷气晕了班主任。
(13)电视上生离死别的那一幕哭晕了这位家庭主妇。
(14)墙角的死老鼠吓晕了我的妹妹。
需要说明的是,前面三例子属于“行为动词+晕”类型,后面三例则属于“心理动词+哭”的类型。例(9)中,动词“打晕”由“打”和“晕”组成,动词“打”是二元谓词,如“武松打了老虎”,其中“武松”是动词“打”的施事,“老虎”是“打”的受事,而“晕”往往被认为是一元谓词,如“老虎晕了”,“老虎”是述题,“打”和“晕”二者的论元结构分别为[武松,老虎]和[老虎]。合成词“打晕”的论元结构是[武松,老虎],也是“打”和“晕”各自论元结构的合并。例(11)与例(9)有所不同,“持续的高温天气热晕了户外作业的电工”中,“热晕”由“热”和“晕”组成,而“热”和“晕”都是一元谓词。既然如此,那么“持续的高温天气”充当何种题元角色呢?“持续的高温天气”应该是使“户外作业的电工”感到“热”的原因,被分派的应该是“致事角色”。因此例(11)的句子可以分解成“持续的高温天气使户外作业的电工(感到)热”“户外作业的电工晕了”,从上述两个分解句来看,“户外作业的电工”被指派了两个论元角色,在前面一句中充当“热”的受事,在后面一句中充当“晕”的施事。乔姆斯基(Chomsky)在论元角色标准(θ-criterion)中指出,“每一个论元带且仅带一个语义角色,每一个语义角色分且仅分给一个论元”(Chomsky,1981)。例(11)中,“热”和“晕”共享一个论元“户外作业的电工”,这是否违背了乔姆斯基(Chomsky)的论元准则(θ-criterion)呢?事实上,例(11)中的动结合词“热晕”的论元结构依然是“热”和“晕”各自论元结构的合并。“热”的论元结构是[持续的高温天气,户外作业的电工],“晕”的论元结构是[户外作业的电工],合并之后的论元结构是[持续的高温天气,户外作业的电工]。由此可见,题元角色与论元都以动词为中心,但是两者并非一对一的关系,此处即为一对多的关系。
“心理动词+晕”与“行为动词+晕”的语义特征存在差异,前者侧重于心理动词,用“晕”来呈现“气、哭、吓”的程度,而后者侧重于“晕”这样一个后果,此时用来指明“晕”的原因或方式。综合上述“动词+晕”的具体事例,不难发现“动词+晕”这一复合词论元结构包含了自由语素“动词”所有的论元结构信息。值得一提的是,由于“晕”属于自由语素,因而上述两者的论元结构信息在被充分吸收的过程中完整保留下来,从而复现于合成词的论元结构之中。
综上所述,“武松打晕了老虎”即可作如下解释:
事件1“武松打老虎”+事件2“老虎晕”=复合事件“武松打晕老虎”
单词素动词1“打”+单词素动词2“晕”=复合语义“打晕”
[武松,老虎]+ [老虎]= [武松,老虎]
纵观“动词+晕”的语言事例,可以发现“晕”的形态差异影响了合成词的词化程度以及论元结构表达。单词素动词“晕”被视为一元谓词,带且仅带一个论元,而在与其它动词一起构成复合动词“动词+晕”之后,可以携带的论元数目发生变化,本身作为自由语素所具有的论元结构信息被吸收在复合动词构成的论元结构之中,与此同时,其它动词所具有的论元结构信息也同样存在于复合动词构成的论元结构之中。而复合动词形成的论元结构实际上整合了“晕”和“其它动词”这两者的论元结构和语义信息。
四、结语
本文结合单词素动词“晕”和合成词“动词+晕”的具体事例,从论元结构和语义角色的视角出发,并通过借助乔姆斯基生成语法的相关理论和概念,详细解读汉语动词“晕”的论元结构和动词“晕”对论元角色的分派及其相应的句法特征,使得语义成分(如动作的施事、受事等)与句法成分(如主语、宾语等)关系能够浮出水面,从而句子结构在一定程度上便显得明晰可见。
注释:
[1]施春宏:《动结式的论元结构和配位方式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3年。
[2]沈家煊:《动结式“追累”的语法和语义》,语言科学,2004年,第3期。
[3]黄龙,杨成虎:《汉语V1+V2类动结式的最简方案分析》,现代外语(语言研究版),2014年,第3期。
[4]刘丽萍,熊仲儒:《动结式的论元实现》,现代外语,2006年,第2期。
[5]Chomsky,N.:Lectures on Government and Binding, Dordreeht: Foris,1981.
[6]Fillmore,Charles:The Case for Case, Universals in Linguistic Theory,1968.
[7]袁毓林:《论元角色的层级关系和语义特征》,世界汉语教学,2002年,第3期。
[8]Ross,John R:Constraints on Variables in Syntax,Cambridge,Mass,1967.
[9]许菊:《英语动结句的论元结构》,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学报,2007年,第4期。
参考文献:
[1]施春宏.动结式论元结构的整合过程及相关问题[J].世界汉语教学,2005,(1).
(陈洁娜 上海 同济大学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专业 200092)endprint